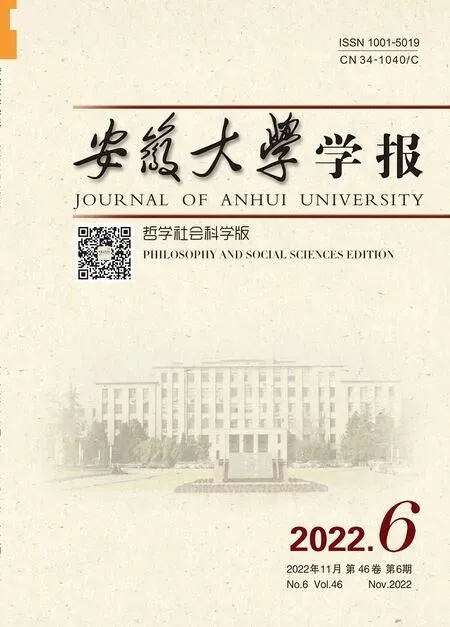“信朱子不如信饶氏”
——陈栎、倪士毅四书学对饶鲁的接受及意义
2022-03-23许家星
许家星
一、“双面”饶双峰
陈栎、倪士毅师徒是元代前期新安理学的代表人物,二者各自所著《四书发明》《四书辑释》是四书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著作(1)学界对陈栎《尚书》学、四书学和文本辑佚方面有所留意,对其思想方面的讨论,则涉及他与朱子学的关系、与胡炳文在《四书集注》定本上的分歧、对心与理关系的认识、史学观等。史甄陶《家学、经学和朱子学——以元代徽州学者胡一桂、胡炳文、陈栎为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对此有专章论述。关于倪士毅的研究更少,只有个别文章讨论其著述与文章学理论,廖云仙《元代论语学考述》(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有专章论述其《四书辑释》的版本及流传。。二者之学通常被视为家学和地域之学,被认为是纯粹的朱子学。学界通常视陈栎、胡炳文等元代前期新安理学为朱子学的门户守者(2)李霞:《论新安理学的形成、演变及其阶段性特征》,《中国哲学史》2003年第1期。,然却少有学者注意,二者之四书学实受到南宋朱子再传余干饶鲁(号“双峰”)之学的深刻影响。鉴于《四书发明》(下文简称《发明》)已佚,我们以倪士毅《四书辑释》(下文简称《辑释》)为中心来讨论陈、倪师徒对双峰学的接受。仅从最直观引用频率来看,双峰说被《四书辑释》引用约564处,仅次于其师陈栎。陈栎对双峰存在正反两面之看法:“饶氏《四书讲议》内多有好处,亦多有可非处。……吾尝疑其人有心疾……晚年自号饶圣人,真心恙矣。”(3)陈栎:《定宇集》卷7,《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05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69页。他一方面认同饶双峰有功于朱子,其《四书》解有甚多精彩之处,但同时指出其说亦存在诸多谬误,批评双峰奇特处在于对朱子说展开精妙发挥后,往往又对之加以吹毛求疵般的讽刺。陈栎对此甚觉难解,认为此等反差难以想象是同一人所为,故判定存在“双面”双峰——正常之双峰与心疾发作之双峰,二者互相矛盾悖逆。然而在元儒史伯璿看来,陈栎对被他视为“心恙”之双峰的信从程度,远远超过了胡炳文(号“云峰”),以至于判定陈栎水平不如胡氏,斥责他“信朱子不如信饶氏”。其《四书管窥大意》言:
陈氏《发明》亦欲勒为一家之言者也。……至于宗信饶氏,则又过于《通》,口虽非之……以其信朱子不如信饶氏。(4)史伯璿:《四书管窥》(一)卷首,黄群辑:《敬乡楼丛书》第三辑之三,1931年,第1页下。
史氏这一判定是基于陈栎极少驳斥双峰批评朱子的不当言论,反而是胡炳文不时站出来维护朱子,反驳双峰。史伯璿认为陈栎《四书发明》相较《四书通》(下文简称《通》)有两个不如:不如其高明,亦不如其谫陋。但在推崇双峰上,《四书发明》又超过《四书通》。批评陈栎口是心非,表面批评双峰,内心实认可之,断定此根源在于对朱子之崇信实不如信双峰。饶双峰在朱子学界以“多不同于朱子”著称,陈栎则被赞誉为朱学功臣、朱学嫡传,如此一来,则他对饶鲁之推崇与其朱学功臣之声誉似相冲突,这体现了二者关系的复杂性。若就陈栎、倪士毅对饶双峰之说态度来看,他们主要采用了直接引用、暗主其意、摒除其说的方式(5)因饶鲁之说失传,陈栎《四书发明》亦失传,无以直接窥探其对饶鲁之说的引用。而史伯璿《四书管窥》专门挑出陈栎等对饶鲁之说的引用加以评述,故本文在相关材料的使用上,多采史伯璿之说。。
二、引双峰说者
陈栎、倪士毅对双峰说的引用,注重选取对朱子说“大有发明”的条目,此为引用之主体。须指出的是,如与胡炳文《四书通》所引双峰说相较,则二人所引饶说多有为胡氏所未引者,显示出对饶双峰说的不同接受。《大学》部分,如引双峰“明明德”之“明”的两种理解,“明之之功有二:一是因其发而充广之,使之全体皆明;一是因已明而继续之,使无时不明”;“知止”节引双峰八目之两种表述乃是分别指逆推工夫与顺推说;“克明德”章引“静存动察皆是顾”说(《辑释·大学》)。双峰此三条反响颇大。即便同引双峰之说,《辑释》所引有时较《通》内容更多,如“忠恕一贯”章,《辑释》引4段长条,而《通》仅引短短两句,体现出《辑释》对双峰忠恕说更为重视。《辑释》所引显示其眼光独到处,如“漆雕开”章一条,所引饶氏说指出《四书集注》去除程子原文“曾点”二字,原因在于此处尚未涉及曾点,担心学者躐等而进,“故去上二字”(《辑释·论语》)。可见《辑释》对工夫次第之看重。有时《辑释》所引很简略,仅仅拈出其所看重的核心观点,如“可使南面”章《四书大全》长段引用双峰说,而《辑释》仅引一句:“简于行事上用得,于治己上用不得。”(《辑释·论语》)
“但引饶说”。面对诸家之说,《辑释》存在独引饶说而放弃他说的情况,颇得史伯璿认可。如“不得中行”章,《辑释》仅引饶氏关于狂狷近于中行之说而放弃不够完备的辅广及《发明》之说的做法,史氏赞之:“今观《辑释》但引饶说而不引二说(辅广及《发明》说),可见愚言之有契矣。”(6)史伯璿:《四书管窥》(四)卷7,第22页下,“敬乡楼丛书”本。然今《辑释》无辅氏说,而有陈氏(先师)说。又如“一言可以终身行之”章,《辑释》引双峰“此问在未闻一贯之先,子贡于事上学得多,欲知博中之约,故发此问。‘一言’是一字,所以只以一‘恕’字答之”(《辑释·论语》),而《四书通》则未引末句,且引冯椅说,认为夫子对曾子、子贡回答之异在于二者出发点不同,曾子兼体用而子贡问用不及体,“曾子兼言体用,故曰忠恕;子贡问用而不及体,故曰恕而已矣”(《四书通·论语通》卷8)。史氏批评冯氏错用双峰之意,故《辑释》不取其说,而《通》取之为不妥(7)史伯璿:《四书管窥》(四)卷8,第5页下,“敬乡楼丛书”本。。
引双峰说新奇而引发“不当”判定者。双峰喜提新解而多为《辑释》引用,如《论语》“不逾矩”章,双峰认为本章致知、力行、立志、不惑等皆是绕“矩”字展开,甚至《集注》所引胡氏“用即义”的“义”字也是“正为矩字而发”(《辑释·论语》)。此说引起史氏不满,批评其不合解经之法,流于举子作文游戏。又,双峰认为《孟子》“无严诸侯,恶声至,必反之”的“恶声必反,不专谓诸侯”(《辑释·论语》),史氏认为不必如此强解,此处只是一义(8)史伯璿:《四书管窥》卷4,《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04册,第791页。按,以下引用该书不再标注版本。。如《中庸》“中节”之解,双峰以为是节限所止之义,是防止情感过度之节制,“中节之节,有限止之义,喜怒哀乐之未发,患其过,不患其不及,故以节言之”(《辑释·中庸》),史氏认为此说新奇不妥,盖情感亦存在不及者,如孝。又,双峰提出“至诚无息”章的“至诚”只是说圣人,以之论天地不合适,盖天地无所谓至与不至,“圣人,诚之至,故可以说至诚。若天地只是诚,无至不至”(《辑释·中庸》)。史氏认为此说过于拘泥(9)史伯璿:《四书管窥》卷8,第922页。。史氏还认为《辑释》所引双峰说存在正误夹杂者。如双峰关于三纲重在至善的理解,史氏认可之,但不满双峰把明德新民工夫皆收归于至善(10)史伯璿:《四书管窥》卷1,第689~690页。。
引双峰说与朱子相背离者。此等引用与胡炳文《四书通》相较,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与《四书通》同引者。如双峰关于慎独诚意为全书之要说,《辑释》不仅引此说,且引《通》阐发饶氏说,引起史氏不满(11)史伯璿云:“《通》者援《章句》‘自修之首’四字以合于饶氏‘诚意不特为正心之要’之说,亦似矣。殊不思饶氏何尝以朱子之说为是耶?”《四书管窥》卷1,第697页。。关于“修身齐家”章“皆诚意慎独之意”说,《辑释》《发明》《通》皆引之,史氏驳斥双峰此说不合朱子及文本之意(12)史伯璿:《四书管窥》卷1,第703~704页。。又如《辑释》《通》皆引双峰“忠信即是慎独,以此观之,可见诚意不特为正心修身之要,而又为治国平天下之要”说,史氏驳斥此说有以诚意包罗正心等工夫嫌疑(13)史伯璿:《四书管窥》卷1,第706页。。“正心修身”章所引双峰心不在与心不正之分说亦然(14)史伯璿:《四书管窥》卷1,第700~701页。。其他类似情形尚有引双峰《中庸》分章说,不睹不闻,中和性情,庸德庸言,无入不得,费隐,改而止,大孝达孝,人鬼对说,生知安行,怀诸侯为尊贤,等等,皆与朱子不同。另一种则是陈、倪所引而《四书通》未引者。史伯璿多次痛斥陈、倪师徒信朱子不如信双峰,判定他们对双峰之信远甚于云峰,乃有感而发。事实上,他们对双峰说的引用确乎超过胡炳文,尤其是对双峰背离朱子说的引用更是如此,甚至与胡炳文相对立。
兼引双峰与他说而不折中者。此等情况当以所引南轩(张栻)说为常见,盖陈栎推崇南轩之说,显然影响《辑释》的看法。如《论语》“贫而无怨难”章,《辑释》同时引双峰和南轩说,南轩讨论了富而无骄与贫而无怨,认为后者更难,难在内心之必有所安。至于处富贵则失去本心者,乃是不知无怨。无怨之难在心中无不平而进于乐。“能安于义命,则能无怨;若乐,则心广体胖,非意诚心正身修者不能及此。”(《辑释·论语》)所引双峰说则强调了无怨与乐的差距,与南轩说恰相反,故史氏指责《辑释》引南轩与双峰矛盾之说而不加评语(15)史伯璿:《四书管窥》(四)卷7,第27页上,“敬乡楼丛书”本。。如《论语》“事父母几谏”章,陈栎引南轩说,以“几谏”为谏尚未表现出来,同时又引双峰说,以“不违”是顺从父母而不违逆。史氏批评此二说乃朱子《语录》所放弃者,《发明》存此朱子反对之说,只会增加学者困惑(16)史伯璿:《四书管窥》卷2,第735页。。然《辑释》并未引此二说,显出师徒之别。又陈栎《发明》既采用双峰“《中庸》要处不专在首章”说,又采三山陈氏“此章盖《中庸》之纲领,此三句又一章之纲领”说。史氏认为二说互相矛盾却不加以任何折中评价,令人不知其意,恐在助长双峰之说以乱朱子(17)史伯璿:《四书管窥》卷6,第855页。。
引双峰直接批评朱子说。双峰不少新说直接针对朱子而发,带有一争高低意味,《辑释》引用之,引起史伯璿极度不满。如关于《中庸》分章,《辑释》引双峰说,以第27章“大哉圣人之道”至32章为一节,认为此六章分两层,27~29章论贤希圣,30~32章论圣希天,不满于朱子人道天道之分,而转向德性人格层级之论。不仅如此,《辑释》还引鄱阳李靖翁之说,判定双峰断定“天道人道,只到至诚无息章住”说,“可谓朱子忠臣矣”。但李氏又不满双峰以此六章为论小德大德,而据26章“苟不至德至道不凝”说断定六章宗旨为至德至道。史氏既不满于饶氏之说,同时反驳李氏说,取消饶氏忠臣之称号,认为当以朱子天道人道说为准(18)史伯璿:《四书管窥》卷8,第951页。。又如《论语》“民可使由之”章,《辑释》引双峰“两‘之’字皆指此理而言”,批评《集注》“由是由其所当然,知是知其所以然”说似乎过于分析为两事。史氏首先批评倪氏仅引双峰答词而故意不引双峰弟子之问,有误导之嫌疑。继而指出朱子之说本是指一理,非是指二事。双峰弟子强行分析所以然与所当然,自误误人,反而吹毛求疵于朱子(19)史伯璿:“析当然、所以然而二之,此则饶氏师弟子所见之误,而反归咎于《集注》,不亦异乎?《辑释》去其问辞而唯引答辞于编,使若有所发明于《集注》然者,而实则不然,误人甚矣。”《四书管窥》卷3,第762~763页。。又《论语》“益者三友”章,《集注》认为益友与损友三者正相反,双峰则认为三者并不相反,批评朱子之说不贴切,“以三者为相反,终说得不自在”。史氏根据“无相反之迹,有相反之实”说驳斥双峰,维护朱子(20)史伯璿:《四书管窥》(四)卷8,第11页,“敬乡楼丛书”本。。又引双峰关于《中庸》“不息则久”与“悠久”的“久”分别指内、外说,史氏认为这违背了朱子以久皆为内之说,乃强分悠远、悠久之病根。斥责双峰勇于背叛朱子之说,此即一证(21)史伯璿:“不惟不足以释问者之疑,又且勇于背《章句》之旨,亦独何哉!”《四书管窥》卷8,第923页。。关于《孟子》“天下言性”章,双峰不满《集注》引程子说,以为本章宗旨非是论智,而是论性。陈栎大为赞赏双峰说,认为解除了其心中疑惑。《辑释》全引双峰说,未引《发明》推崇双峰之按语,而自加按语,认为双峰说虽与朱子不同,但应当有所知之,与其师态度似乎有所不同。但史氏认为,倪氏仍然保留双峰说之做法,只会引起后世疑惑,增加对朱子说权威性的动摇,最好是删除之,不留痕迹(22)史伯璿云:“《发明》信双峰深于信朱子,其言正不足为轻重也。《辑释》不引《发明》之说,固不为无见矣。然犹不忍弃双峰之说,以为亦宜知之。则虽有见而不甚明,存之只以惑人而已,何补于经注之旨哉。”《四书管窥》卷5,第822页。。
“改易字面以助其澜”的协调朱、饶说。面对朱子与双峰不同之说,陈栎师徒存在调和与折中的心态,有时甚至不惜删改双峰文字,以求合乎朱子。如《论语》“圣人吾不得”章,《集注》引南轩说,以圣人、君子归于学力,善人、有恒者归于天资。双峰则以圣人、善人是天资,君子、有恒是学力。《辑释》为弥合二者,故意改动双峰说为“圣人是天生底,君子是学而成底,善人是气质好底,有恒者是有常守底”(23)史伯璿:“《丛说》既与《集注》不合,则删之可也,辩之可也。《辑释》为之修饰而同用之,过矣。”《四书管窥》卷3,第753~754页。。史氏认为双峰说既然与朱子不合,当删之,或辩之,不可修饰弥合之。陈栎《发明》亦引饶说,强调有恒者之重要,是入德成圣之门户。史氏批评陈氏只知引双峰求新奇之说而不加辨析,所谓有恒入圣说虽合于《集注》学以成圣之论,却与其所引双峰“此圣是天生的,是生知安行底”说相冲突(24)史伯璿:《四书管窥》卷3,第754页。。如《孟子》“规矩方员之至”章“幽厉之恶名”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说。双峰以“改”是“要改其恶”,史氏认为双峰此说正与朱子“皆恶谥也……不得废公义而改之”说相对,然陈栎《发明》对饶说补“谥”字,变为“改其恶谥”,同时又补“公义废矣”四字,以求合于《集注》,《辑释》则如《发明》之改(25)史伯璿:《四书管窥》卷5,第811页。。此显出《发明》《辑释》删改双峰说以求与朱子说一致之努力,从反面提醒吾人不可径直以二书所引双峰说为其原文,难免有删改以就己意者。此似乎受到朱子处理《集注》时对所引说“改易本文”之影响(26)许家星:《〈四书集注〉“改易本文”述作精神发微》,《哲学研究》2019年第11期。。《论语》“知及之”章“动之不以礼”,陈栎受双峰影响,欲把《集注》“小疵”改为“设施”,遭到史伯璿批评(27)史伯璿:《四书管窥》(四)卷8,第7页下,“敬乡楼丛书”本。。对此等既认可朱子说,又改写双峰批评朱子之说者,史氏判定为徘徊于朱、饶之间的“主见不定”。
“饶氏说与《章句》不同者,亦宜知”。除了改易双峰原说以弥缝与朱子之说差异外,《发明》《辑释》还坚持保留双峰不同于朱子之说,认为此属应当知道的知识。在史氏看来,此会造成蛊惑人心的不良后果。如关于“强哉矫”,陈栎引用双峰以“矫”为矫揉之说,又云此说实来自吕大临而为朱子所否定者。《辑释》亦引此说(28)史伯璿:《四书管窥》卷6,第880页。。又如对《中庸》与朱子不同之分章,二人亦认为是应知者而保存之。“《发明》按:‘饶氏说与《章句》不同者,亦宜知,今载于下。’《辑释》亦载饶说及《发明》此语。”(29)史伯璿:《四书管窥》卷7,第913页。史氏对此极为不满,认为如肯定双峰说优于朱子,则当明言之;否则,则当删除之(30)史伯璿:“似是而非之说则当辞而辟之,以晓后学。若以其说为优于《章句》,则亦当明其如何是优之实,乃可存尔。苟得其实,何畏于朱子,何私于饶氏,存之乃公心耳。今皆不然,而但兼存异论以眩学者,依违两可,无所折中,岂不有愧于‘发明’名书之义乎!愚故谓其信朱子不如信饶氏,其于饶说每口非而心是之者,此也。如此等之存,正是私于饶氏又畏朱子,而不敢明言之者也。”《四书管窥》卷7,第913页。。此等两可模糊之态度正反映其私心认可双峰,而又不愿触犯朱子权威的曲折心态。
三、对饶说的暗主与摒弃
对《四书》的理解,陈、倪师徒虽未直接引用双峰之说,但在史氏看来,却暗中采用其意而略变其辞。此即史氏认为的暗主饶说。史氏认为陈、倪师徒暗主饶说具体有两种方式:
(一)暗以双峰说批评朱子。如《中庸》“中庸其至矣乎”,陈氏认为此“中”与《论语集注》之“中”皆是言无过不及之“中”,而非不偏不倚之“中”。史氏认为此是主双峰说来批朱子之不足(31)史伯璿:《四书管窥》卷6,第877页。。又如《集注》解“于禽兽又何难”的“难”为“校”,双峰则解为“患”。陈、倪师徒所引南轩说正是解为“患”,而暗合双峰说,不同于朱子(32)史伯璿:《四书管窥》卷5,第823~824页。。关于《或问》对明德、新民的理解,陈栎认同并本于双峰说,以为乃明明德于天下之新民事,不满朱子“合在人、在己之明德以为一而言其体用”说(33)史伯璿:《四书管窥》卷1,第684页。。又如“博施济众”解,史氏认为《发明》虽未引饶说,却是“以饶氏意为己意”(34)史伯璿:《四书管窥》卷3,第747~748页。。又指出陈栎于《孟子》圣神之论,祖述饶氏两种圣人不同之说而背叛朱子之意:“《发明》盖祖述饶氏生知安行之圣与大而化之之圣不同之言以为说,而不思子思、朱子之意不如此也。”(35)史伯璿:“曾谓学问极功与圣神能事有二致乎?”《四书管窥》卷6,第871~872页。又《中庸》第二章“君子之中庸”解,《发明》亦祖述饶说,不满朱子“无时不中”说,认为是“推其本而以知为重”。史氏对此加以批评(36)史伯璿:《四书管窥》卷6,第873页。。
(二)“剿饶氏之意而删润之以为己有,以求合于《章句》之旨”。史氏指出陈栎暗主饶说的一种隐秘而强烈的表现是暗自袭用双峰思想,删改润饰其言辞,表面看未曾引双峰说,实则一样。其目的仍在追求协调朱、饶之说,以尽量合乎朱子思想,承担着调和二说的角色。如关于《中庸》“上下察也”解,双峰不满朱子“专说费不及隐”之论,主张“以此证用之费而体之隐在其中”。陈栎认为,“此察字实对隐字”,“而其所以然之妙则终非见闻所及”,“虽察也而实隐也”。史氏指出,陈栎是饶、朱调和之说,前两句分为双峰之意、朱子之意,而“虽察实隐”则是推求饶说以合乎朱子,即“剿饶氏之意而删润之以为己有,以求合于《章句》之旨者”(37)史伯璿:《四书管窥》卷7,第886页。,终是不合朱子而走向双峰。又如《孟子·离娄下》“以仁存心”说、《孟子·告子上》“仁人心”章之解,史氏批评陈栎非但不能辨析双峰之谬误,反而一味迎合,误导后学,罪甚于双峰(38)史伯璿:《四书管窥》卷5,第823页、834页。。又如陈栎把《中庸》“诚者自成,道自道”分别解为实有诸己与躬行于己,“实有诸己,故曰自成。……躬行于己,故曰自道”(39)史伯璿云:“《辑释》亦引之……《发明》‘实此者也,实有诸己’之言,则未免有搀说人力之病。……故于双峰之说,每惓惓而不能舍也。”《四书管窥》卷8,第922页。,史氏认为此说是受双峰影响,偏离了论道之自然的主旨。
其实,陈、倪师徒对饶氏还另有摒弃不用的一面,即放弃双峰对朱子的批评之说。陈、倪师徒对双峰说之选用,仍是以发明朱子为主,对双峰有关批评朱子之说的选取极为慎重,有意刊落了双峰过于新奇及直接批驳朱子之说,这一点不通过比较史伯璿《四书管窥》所引双峰说,实无以观之。史氏之书,以清算双峰不同于朱子之说者为宗旨,故特别提出双峰约236条“悖逆之论”加以辨析。而陈、倪、胡对此等悖逆之论除若干条认同外,大部分皆摒除不取。如《论语》“忠恕一贯”,《四书通》《四书辑释》所引双峰4条皆为正面阐发朱子之说,而《四书管窥》所引双峰3条则是批评朱子,完全不同于二者所引。可见新安学者对双峰批评朱子说有意作出了选择性刊落,并非一味崇信饶氏。明乎此,有助于全面准确把握新安理学的观点、立场。对双峰批评朱注说刊落者甚多,如批评格物补传说“朱子补传似乎说得太汗漫,学者未免望洋而惊”(40)史伯璿:《四书管窥》卷1,第690~691页。;批评“正心修身”章“《章句》注文似可省”(41)史伯璿:《四书管窥》卷1,第702页。;指责“三年无改”章《集注》所引尹氏、游氏之说“似太费辞”(42)史伯璿:《四书管窥》卷2,第712页。。删除双峰新奇而不同于朱子之论者,如“明明德”章“姑以释明明德之义,未有下工夫处”;“至善”章“所谓新民之止于至善者,非是要使人人为圣为贤”;“平天下”章“过之罪小,命之罪大”(43)史伯璿:《四书管窥》卷1,第687页、689页、706页。。
四、《辑释》《发明》《四书通》对待双峰说之异同
胡炳文、陈栎、倪士毅三者立场大体一致,既以发明朱子为任,又不废双峰之好处,但彼此对双峰之取舍亦有差异。史伯璿精细察觉此点,他根据对双峰之维护、批判之程度来判定学者水准,据此断定《四书通》优于《四书发明》;据此断定学者学术道德,孰为阿私,孰为大公,孰为朱子忠臣,孰为逆臣等。在他看来,站在朱子还是双峰立场,事关为学根本。此狭隘的视角自然不足为取,然却对辨析三者之学提供了一条线索。
(一)胡炳文反饶护朱与陈、倪的挺饶反朱。如关于“洒扫应对”章,《四书辑释》引双峰说,认为程子与朱子对本末的理解不同,程子以理之所以然为本,朱子则以正心诚意为本,故朱子是顺子游之意而论。陈栎力挺双峰,认为其解乃自成一说,并非为解释程子而发,故与程子思想不冲突。史氏则据胡炳文说反驳双峰,认为其说击中了双峰误解程朱不同的原因,朱子乃是以本末皆为事,而不可分为二事者则是理,双峰反倒认为程子以末为事、本为理,造成理事分裂。“朱子解程子之言,以本末皆为事而不可分为二事者是理。饶氏解程子之言,以末为事而本为理。”(44)史伯璿:“则双峰谓程子以所以然为本者,乃是误看了程子之意,又岂难知哉!”《四书管窥》(四)卷8,第31页上,“敬乡楼丛书”本。又史氏最不满陈、倪师徒于“尊德性道问学”解中力挺双峰说以反对朱注,大赞胡炳文维护朱子、反驳饶说之立场。陈栎认为经过反复思考,始终无法认同朱子对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存心与致知之划分,主张是力行与致知的知行关系,并以吕本中、饶氏知行之分为根据。史氏批评陈栎乃“蹈袭双峰之说而小变之,以为己有”,赞赏胡炳文之说是双峰与陈氏说的对症之药,并驳斥倪氏的陈栎得子思义、云峰得朱子义说,讥讽其陈栎为朱子忠臣之论(45)史伯璿:《四书管窥》卷8,第942页。可参许家星《朱子学的“求真是”与“护朱”之争——以陈栎〈四书发明〉为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
(二)不阿其师:《辑释》《发明》之不同。倪士毅尽管推崇其师陈栎,但并非无原则者,实能坚持独立看法,不时取他人如胡炳文之说,而放弃其师之论,体现了实事求是之精神。如“温良恭俭让”章,陈氏取双峰而不取胡炳文之说,而倪士毅则取胡炳文说,被史伯璿赞为“不阿其所好”(46)史伯璿:《四书管窥》卷2,第712页。。又《孟子》“不孝有三”解,赵岐与饶双峰之解不同,双峰认为赵岐完全以自家之意揣测论之,辅广则认为赵岐说乃根据古书得出,非臆测之论。胡炳文兼取饶、辅二说,陈栎则去饶取辅,倪氏则同于胡氏之兼取(47)史伯璿:《四书管窥》卷5,第817页。。关于《中庸》二十五章“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陈栎认为此“道”即“诚之道”的“道”。史氏认为陈说明显抄袭双峰“诚即道也,非是两般”说。胡炳文则批评双峰之说,认为“诚”有不同含义,不可等同于“道”。倪士毅采胡氏说而不取陈栎说,可见师徒观点不一(48)史伯璿云:“《辑释》引《通》而不取《发明》,宜矣!”《四书管窥》卷8,第921页。。又如“天下言性”章,倪士毅虽因双峰说,但却删除了陈栎对双峰的推崇之辞(49)史伯璿:《四书管窥》卷5,第822页。,体现了与其师之不同。
五、双峰学对新安理学的意义
学界对新安学者陈栎、胡炳文之思想,常追溯于地域或家学。如《宋元学案》置胡炳文于董梦程为代表的“介轩学案”,盖其父胡斗元曾从学朱洪范,故被置于“孝善家学”,认为“笃志家学,又潜心朱子之学”(50)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卷89,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986页。。而对陈栎亦强调其家学及捍卫朱子学之贡献,“其为学得于家庭之讲贯为多”(51)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卷70,第2354页。,“凡诸儒之说,有畔于朱氏者,刊而去之”(52)熊赐履:《学统》卷41,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399页。。倪士毅是徽州祁门人,乃陈栎弟子。事实上,在学宗朱子的同时,他们皆受到作为朱子再传余干饶鲁之学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体现在他们以不同的方式采用饶鲁之说,或明引,或暗引,有时甚至表现出某种执着与倔强,以至于引起史伯璿极度反感与痛斥,认为他们“信朱子不如信饶氏”,此虽过激而非持平之论,然至少反映出他们对饶鲁之说大量采信所引起的朱子学者之观感。尤其令史伯璿反感的是,饶鲁本就以多不同于朱子著称,具有自成一家之说而颇与朱子立异之思想,而陈栎等人在朱子与双峰之说的取舍上,却时有舍朱取饶之倾向,自然不能不让充满护朱情结的史伯璿愤慨。这一“信饶不信朱”的取向,恰体现了陈栎等新安理学虽然以朱子为宗,却并非一以朱子为是,而是秉承了朱子求真是之精神。故“信朱子不如信饶氏”情况的存在,有助于反省长期以来视陈栎、胡炳文等为朱学门户株守者的看法(53)胡炳文对朱子的反思批评,可参拙稿《“胶执门户”还是批判发明——论〈四书通〉的批判精神兼驳〈四库提要〉之诬评》(《人文杂志》2011年第3期)。另,史甄陶分析了胡炳文《中庸通》对饶鲁的批评与吸纳,认为据此看出胡炳文并不全同于朱子。她指出陈栎在风水、丧葬、深衣等问题上皆提出对朱子的批评,体现出陈栎“是个具有独立思考精神的学者,而不是只顾注疏朱子著作的‘训诂之儒’而已”(史甄陶:《家学、经学和朱子学——以元代徽州学者胡一桂、胡炳文和陈栎为中心》)。可见新安理学之陈栎、胡炳文、倪士毅之学并非完全拘泥朱子学而实具求真是之反思精神,而饶双峰影响不可忽视。。
在中国思想学派的研究中,学界比较注重地域、师承、家学等因素的影响,如以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借助何基年少从学黄榦之因缘,经由金华学人不断的累世建构,而被称为“朱学世嫡”。此“朱学世嫡”说显然有意排斥江西朱子学与新安朱子学而有大言不惭之成分。事实上,无论是师承还是地域,江西与新安朱子学之“资本”皆较金华更为雄厚而正统。而就宋元朱子学来看,双峰学影响广泛,不仅在江西经程若庸、吴可堂而传承于程钜夫、吴澄,且作用于浙江金华朱子学,尤其深刻影响了元代新安朱子学。此点似乎罕有人道。此与双峰著作无传有关,更与学界形成的对江西、新安朱子学的固定看法有关。盖学界视双峰与吴澄为宋元和会朱陆之代表,而以陈栎、胡炳文等元代前期新安朱子学为朱子学的忠实守护者,彼此似乎针锋相对。考之事实,其实不然。正如本文所揭示的,双峰学构成元前期新安四书学除朱子之外最重要的思想来源。
新安理学受双峰学之影响,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形成了非常强的辨名析理特点,对概念字义的辨析达到了精细、深入的程度。朱子学本以穷理精密、辨析深入著称,这一特点为陈淳、黄榦所继承,而再传弟子中尤以双峰为代表,学界将北溪(陈淳)与双峰并称为朱门精于穷理者,吴澄语带反讽地指出二者的精密分析已经堕入训诂辞章之学(54)吴澄:《吴文正集》卷40《尊德性道问学斋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8册,第422页。可参许家星《略论朱子学中的穷理精密派——以北溪之陈、双峰之饶为中心》,《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双峰的精密之学深深影响了新安理学,使得其同样带上了解析精密的特点,推动了朱子学穷理的进一步深入。其次,双峰对朱注的诠释体现了极强的怀疑批判精神,有助于破除对朱注的盲目崇拜,消除故步自封之倾向。应该说,新安理学在阐发朱子学的同时,亦基于各自理解,积极吸收了双峰对朱注的批判,故绝不可视其为不敢越朱学雷池半步的拘泥者。正是因为受益双峰思想之深,故无论胡炳文还是陈栎,在指出双峰不足之时,总是能语带敬意地肯定双峰之说确实“大有发明”“大有好处”。似乎是冥冥之中对双峰说的回报,以陈栎、胡炳文、倪士毅之说为底本的《四书大全》引饶双峰之说多达570条,既使得双峰思想能够流传于世,同时也在一定意义上保证了《四书大全》的学术水准。故肯定元代新安理学所受双峰之影响,对于准确把握新安理学,充分认识宋元以来朱子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