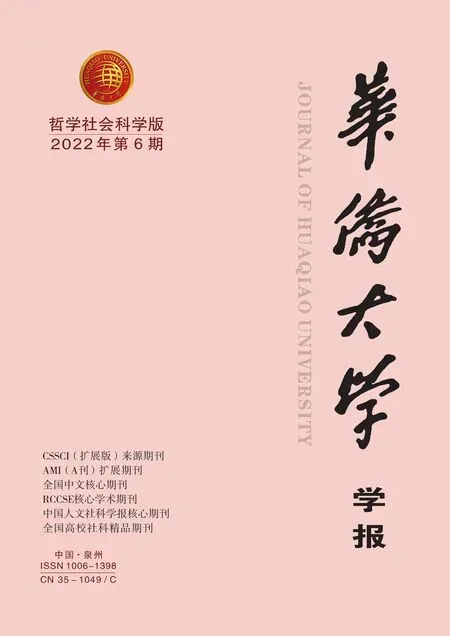历史记忆与女性自我建构
——佩内洛普·莱夫利《月亮虎》中的历史书写
2022-03-23谢丹凌
○谢丹凌
20世纪70年代,当代著名英国女作家佩内洛普·莱夫利(Penelope Lively)亮相欧美文坛。历史与记忆的话题及对现实世界的哲理式认知在莱夫利的作品中被反复探讨。“她深谙后现代主义的传统,对心理时间、主体经验及语言和现实的关系有很大的兴趣”(1)Mary HurleyMoran.Penelope Lively’s Moon Tiger: A Feminist ‘History of the World’.Frontiers: A Journal of Women Studies,1990, 11(2), p.89.。小说《月亮虎》获得了1987年的布克奖,还在2018年入选了“金布克奖”的决选名单,被评委推荐为“20世纪最优秀的布克获奖小说”——“其超越了包括鲁西迪的《午夜之子》、库切的《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及石黑一雄的《长日将尽》在内的其他同年代布克奖获奖作品。”(2)[英]佩内洛普·莱夫利:《月亮虎》,郭国良译,北京:燕山出版社,2019年,第2页。而这部受到西方文学评论家与大众读者广泛好评的英国小说,直到2019年才由国内出版社引进,谈者寥寥。
作为一名牛津现代历史系毕业的女作家,莱夫利对20世纪中产阶段女性在社会里所经历的情感危机与困境谙熟于心,她往往“在自己的创作中探讨写作及年龄、性别、历史与叙述之间的关系。”(3)SusanWatkins.Summoning Your Youth at Will: Memory, Time, and Aging in the Work of Penelope Lively, Margaret Atwood, and Doris Lessing.Frontiers:A Journal of Women Studies,2013, 34(2),p.239.莱夫利深受欧美评论界和广大读者青睐,她的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流传。关于她生平的研究专著早在1993年已在美国出版。根据Jstor期刊检索数据,国外研究莱夫利的论文主要集中在记忆、女性主义、图象艺术、战争描写、帝国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等方面。在方兴未艾的女性主义研究视域下,莱夫利与A.S 拜厄特、多丽丝·莱辛、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等女作家相提并论,并多次入选英国各类文学史。然而对于国内评论界和读者来说,莱夫利的名字还很陌生。《外国文学》杂志最早曾于20世纪90年代末刊载过一篇莱夫利及其作品的研究文章——《历史与现实的融合——谈佩内洛普·莱夫利及其作品》,迄今为止关于《月亮虎》的研究仅有3篇文章,主要探讨《月亮虎》的叙事艺术风格;硕士论文1篇,集中分析《月亮虎》是如何呈现与描摹记忆的。《月亮虎》在过去与现实的交互中,探讨了战争、死亡、记忆、传统、反叛等深刻话题,将女性的自我建构置于风云诡谲的历史书写中。小说中的历史不仅包括公众历史,还包括女主人公的个体“历史”。小说将“个体回忆”作为书写历史的主要动力,不仅再现了20世纪重要的历史事件,也展示了女主人公如何通过历史书写回应性别话语霸权。因此,它既是一部探讨历史书写的经典之作,又是一部优秀的女性成长小说。自我主体建构或身份认同叙事,一直是英美女性文学中的重要传统。反父权书写、反凝视的姿态与反线性的叙事结构、女性独特的语言与声音,是莱夫利展现历史从而建构女性自我的主要手段。本文将从批评家们较少涉及的“历史书写”入手,以女性主义批评视角为观照,在小说主题思想、叙述结构与艺术手法层面探讨莱夫利书写历史、表现历史记忆的策略,以丰富学界对英国20世纪女作家的研究,并籍此分析女性展现自我历史与公众历史时的独特视角及价值。
一 彰显个体价值的反父权历史书写
“女性书写”(L’écriture feminine)(4)也有译者译为“阴性写作”或“女性身体书写”等。一词最早由法国著名女权主义批评家埃莱娜·西苏(Hélène Cixous)提出,是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重要概念。西苏在《美杜莎的微笑》一文中提到,女性自身的情感和欲望被强大的男性权威话语钳制,是被男性价值观评判与审视的客体,惟有写作是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西苏的“话语即是权利”及对女性书写重要性的认识对西方文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写作能让女性从压抑关系中解脱出来,更接近自身的能量,从而彻底改变旧的游戏规则。”(5)HélèneCixous.La Jenue Née.Union Générale d’Editions, 1975, p.43.
在《月亮虎》里,莱夫利将“女性书写”作为小说的主题,展开女性对历史与记忆的言说,形成了文本内外意味深长的互动。小说一开篇,躺在医院病床上的克劳迪娅就声称自己正在书写一部世界史。这位女主角生于1910年,当大多数女性仍然扮演着“屋子里的天使”(angel in the house)时,她已出入男性的世界。在童年时期,她就热衷于与聪明的哥哥戈登展开激烈的辩论,成年后又在历史和传媒这两个长期被男性霸占的行业崭露头角,以写作为生。不安于女性常规成长模式的她周游世界,享受两性自由,未婚先孕,甚至不和自己女儿的父亲缔结正式的婚约,一心追寻事业的成功。她秉持宗教怀疑论,反对“上帝即父亲”的观念,拒绝父权社会潜在的价值与标准。但小说并不仅仅在于描摹一个独立女性的一生,作为一名自我历史与大众历史的书写者,克劳迪娅试图通过个体回忆重新确立历史书写策略,建构与个体生命体验相连的叙述节奏,从而消解以男性为主导的历史话语霸权。
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Paul Ricoeur)在《记忆,历史,遗忘》中探讨了公共记忆和历史记忆的关系,阐述了社会框架对于个体记忆的制约。对于历史书写来说,记忆与遗忘相伴相生,而个体经历是“无法被记忆之光照亮的阴影”(6)[法]保罗·利科:《记忆,历史,遗忘》,李彥岑、陈颖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9页。。因此,莱夫利在小说中有意将历史的宏大叙事转化为个人叙事,并从性别意识出发回应以男性为中心的书写传统。在西方女权主义者看来,什么是值得被记忆与书写的历史话题,一直以来被一代代男性历史学家定义。在《第二性》的导言前,波伏瓦即引用了17世纪哲学家普兰·德·拉巴尔(Poulain de la Barre)的话:“但凡男人写女人的东西都是值得怀疑的,因为男人既是法官又是当事人。”(7)[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I》,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年,第1页。在《月亮虎》里,克劳迪娅以“书写历史”的形式主动介入对历史的言说,她将眼光投向无法被传统历史学之光照亮的阴影,即危难时刻个体的情感与普通人的生活。伴随20世纪兴起的重写历史热潮,克劳迪娅清醒地意识到历史企图复制事实的冲动是荒谬的,“我们与现实的联系总是脆弱的”(8)[英]佩内洛普·莱夫利:《月亮虎》,第13页。。在传统历史书写中自以为是的“父权”模糊了个体的存在,使真实的世界图景越来越模糊。克劳迪娅的历史观在她与哥哥一家参观重建的普利茅斯殖民地时清晰地显现出来。当她发现一路所见的景观不过是复刻1627年殖民地居民的扮相、谈吐和风俗,“每个人的回答都是对17世纪的身份的定义”(9)[英]佩内洛普·莱夫利:《月亮虎》,第51页。时,她表示出强烈不满与质疑。
“共同的过去提供了这一切。它是公共财产,但也是高度私有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有我的维多利亚时代,你有你的维多利亚时代。”(10)[英]佩内洛普·莱夫利:《月亮虎》,第5页。以往共同的、主流的记忆抹煞了个体在历史中的差异与价值,“使个体成为一种机器人,被动地遵守植入其内部的集体愿望”(11)[美]杰弗瑞 ·奥利克、[美]乔伊斯 ·罗宾斯著、周云水编译:《社会记忆研究:从“集体记忆”到记忆实践的历史社会学》,《思想战线》2011年第3期,第9—16页。。在传统历史书写中,当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产生冲突时,总是以集体记忆大获全胜告终,弱小的、个体的声音在宏大话语权面前消弭于无形。夏洛特·吉尔曼曾强调历史的字面就是男人的故事——“历史原是为人类生活的记录,但在以男权文化为主宰的社会里,历史恰是一部男性对女性的战争史与征服史。”(12)Charlotte Perkins Gilman.Our Androcentric Culture, or The Man-Made World.Montana: Kessinger Publishing, 2010, p.25.在父权话语压制下的女性历史,更是在集体记忆里处于边缘中的边缘,反历史权威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也可视为对男性权威的质疑和反叛。因此,克劳迪娅拒绝被“集体”代为言说的命运,渴望在历史中确立自己的位置。
在克劳迪娅看来,每个人都曾和历史发生某种特殊的联系,都迫不得已被卷入时代的洪流中。正如地质学家可以通过考古挖掘发现地球的历史奥秘,晚年的克劳迪娅想象病理学家同样可以通过解剖她的尸体了解自己人生中的重要经历。此外,她的身体“也记载了一段比较不带个人色彩的历史:它铭记爪哇人、南方古猿和早期哺乳动物及飞的、爬的、游的奇特生物。”(13)[英]佩内洛普·莱夫利:《月亮虎》,第242页。正因为自己的身体里也“住”着各种各样的历史元素,她喜欢用一些地理学术语来描述自己的成长。她将自己的过去与宇宙的岩石分层相对应——“核心”(core)记忆与“层级”(strata)记忆,并将自我记忆融入公众历史的书写中。这些记忆不是转瞬即逝的,它们不断被唤醒,与历史建立起了联系,恢复了往昔的光彩。小说在探讨个体与历史的关系时,不仅表明个人躯体里印刻着历史的记忆,也通过克劳迪娅的沉思探究个体记忆与日积月累的种族记忆和人类经验之间的关系。
各种重要的历史事件塑造了克劳迪娅,也影响着她对历史的回忆与书写。她在书写历史时有意疏离宏大叙事,使残酷的历史变得哀婉,充满了日常与凡俗的气息。克劳迪娅的父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死,她作为战地记者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尽管她没有参加匈牙利革命,但由于自己为革命写了一篇饱含同情的新闻稿,使得一位匈牙利男人联系她,请求她为自己在伦敦的孩子拉兹罗提供庇护,她的家庭也因此添了一名重要的成员。莱夫利花费了大量的笔墨描写了克劳迪娅在二战时期的经历,以最大限度地彰显历史与个体的联系。在这段公众历史事件背景下,克劳迪娅“创造”和书写了自己一生中最刻骨铭心的经历——与年轻的坦克军官汤姆热恋。尽管这段爱情因汤姆战死而告终,但它成为克劳迪娅一生最为珍视的“核心”记忆。书名“月亮虎”是一种埃及的绿色盘状蚊香,它就出现在克劳迪娅与汤姆幽会的一家酒店房间内。正如“月亮虎”缕缕上升的青烟,这段历史幕景之下的个人回忆始终萦绕于克劳迪娅的内心深处,也成为她触碰权威历史书写的个体化途径。
法国女权主义者露丝·伊瑞格瑞(Luce Irigaray)曾在西苏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女性谱系”理论,她认为在“俄狄浦斯”阶段,父权制文化建立了象征上帝的男性形象,彻底切断女儿与母亲的潜在关系,由此女性谱系处于父权制的不断压制中,“女性是被动和被阉割的”(14)张岩冰:《法国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语言理论》,《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第104—110页。。《月亮虎》在一些评论家看来“在性别的斗争中仍夹杂着浪漫恋爱情节”(15)MargarettaJolly.After Feminism:Pat Barker, Penelope Lively and the Contemporary Novel.Alistair Davies and Alan Sinfieldeds.British Culture of the Postwar: An Introduction to Literature and Society, 1945-1999,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p.60-61.,但莱夫利并没有遵循传统的爱情套路,为克劳迪娅设计一个按部就班的成长历程。克劳迪娅一直以来都将她与汤姆相遇相爱的经历视为自己生命历史中的“核心”记忆,然而她不像《米德尔马契》(Middlemarch)里的多萝西娅将理想寄予美满的婚姻,这段爱情也没有“给先前混乱和不确定性带来顿悟”(16)Debrah Raschke.Penelope Lively’s Moon Tiger: Re-envisioning A‘History of the World’.Ariel, 1995, 26 (4), p.131.。在汤姆死后的随后几十年里,克劳迪娅依然活得光彩照人、独立自信。小说在一系列闪回中不断重温克劳迪娅与汤姆的爱情,但这些情节并非全书的高潮,伴随着回忆的不断推进,它们逐渐从属于克劳迪娅的其他经历——她在事业上的成功、她对历史的理解,她与戈登、贾斯珀、丽莎和拉兹罗的关系。换言之,这段发生在二战时期的爱情是克劳迪娅情感生活的“核心”,但是其他“层级”的过往经历却决定了她生命的厚度与深度。克劳迪娅没有采用政治化的视角,而是凭借个体真切的生活体验与情感还原了历史的进程,以女性的视角创造性地记录了属于自我的“历史”瞬间。
尽管克劳迪娅不断强调个体对历史言说的权利,但她同样对自我的观点保持审慎的态度。在探访重建的普利茅斯殖民地时,她很清楚地知道:“我不可能是你们肚子里的蛔虫,我不能剔除脑袋里的知识和偏见,不能用孩童般澄澈的目光审视世界,我被囚禁于我的时代,正如你们是你们时代的囚徒”(17)[英]佩内洛普·莱夫利:《月亮虎》,第47页。。克劳迪娅多次表达自己对“另类历史”的兴趣,她曾写过一部有关墨西哥的书,其中涉及阿兹克特人被西班牙人埃尔南·科尔斯特征服的历史。这段历史曾由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书写,“自然是一个智慧开明、有所思考的1843年的美国人思想的真实写照。”但克劳迪娅进而坦言,自己的观点“也是一位好争论、固执已见、独立的1954年的英国女性思想的写照”(18)[英]佩内洛普·莱夫利:《月亮虎》,第225页。。由于对历史的阐释总是囿于时代背景和书写者的身份,克劳迪娅并未标榜自己的写作一定是客观准确的,女性的质疑权和言说权是她在书写历史时的重要手段。“我的性别从来不是绊脚石”(19)[英]佩内洛普·莱夫利:《月亮虎》,第21页。,精力充沛的、骄傲独立的克劳迪娅以自己的写作消解了男性的权威,对抗“集体记忆”的霸权,从而将女性自我放置在了历史叙述的中心。
二 反“凝视”的姿态与非线性的叙述结构
英国艺术史家约翰·伯格在探讨艺术与社会关系的经典之作《观看之道》中曾提到,女性生活在男性的观看中。女性观众只有两个位置,一个是认同具有主体性的男性地位;一个是认同作为欲望客体的女性角色。(20)转引自[英]约翰·伯格:《观看之道》,戴行钺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在波伏娃看来,父权制社会把男性看作超越的主体,而女性则沦为男性凝视与观赏的第二性。不同于少数族群,女性是另一种类型的他者。在传统小说文本中,“看”与“被看”是权利和身份的象征,而女性只能屈从于男性的审美眼光,才能获得社会认同。《月亮虎》里克劳迪娅在书写历史时多次提及男性的眼光,但与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金色笔记》(TheGoldenNotebook)中的女主角安娜·沃尔夫不同,克劳迪娅在男性的注视中很少感到强烈的挫败感或质疑自身的存在价值,她相信自己的能力在很多方面远超男性。在二战期间,她曾被哥哥嘲笑不是做战地记者的那块料,但当她以记者的身份前往北非战场时,丝毫没有显现女性“应有”的恐惧与软弱。她的历史小说创作尽管受到来自男性世界的争议,但常年雄踞畅销榜……出色的天赋、异乎寻常的勇气、不甘于平庸的心灵,成就了克劳迪娅的一生。但在一个由男性主宰的世界,在通往成功的慢慢旅程中,她不断地遭遇来自男性的歧视与“凝视”。在二战期间的埃及,“一位自由法兰西军官颇为欣赏地打量着她的双腿、秀发和装束,其打扮与一般女记者迥然不同”……在男性们看来,传统女性应该呆在屋子里,而不应与男性为主导的战场产生任何纠葛。克劳迪娅拒绝这样刻板的凝视,在建构自我的过程中,她渴望通过书写历史以颠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传统定义。在《月亮虎》里,女性争取到了“看”的权力,男性在她的历史中,成为被凝视的对象、被观察的客体。当克劳迪娅以历史顾问的身份出现在电影拍摄片场时,她多次以自己的视角“观看”扮演入侵阿兹特克帝国的侵略者——科尔特斯的男演员:“他其实不是真的胖,看上去皮肤紧致而有光泽。他的衬衫、裤子和海军蓝上装都剪裁巧妙,将他的身材衬托得比实际的要轻盈一些”、“他有一副深沉摄人的男低音嗓音,这嗓音能令其他人停止讲话,仿佛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意义非凡”(21)[英]佩内洛普·莱夫利:《月亮虎》,第231页。。历史书里凶残暴虐的男性形象在现实中的“代言人”却是猥琐、胆小、虚伪的,克劳迪娅以鄙夷的目光无情地揭露了现实中男性权威的荒谬性。小说中女性的眼光既向父权社会的既定观念发起挑战,也构成了自身与历史交流的独特方式,形成小说观察历史的视角。
“反传统”不仅表现在小说书写历史时采用的视角,也内嵌于小说的叙述结构层面。被文学读者熟悉的传统小说是一种“时间的艺术”,即一种发生在“线性时间”中的叙事。巴赫金依据“时空型”理论将现代小说理解为一种时间意识,他所探讨的“成长小说”即指的是建立在线性时间之上的“历史意识”自然生长的过程。法国叙事学家热奈特(Gérard Genette)在1980年出版的《叙述话语:新叙事话语》提到,“叙事是一组有两个时间的序列,被讲述的事情的时间与叙事的时间”(22)[法]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王文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2页。。他进而将“被讲述的时间”称为“故事时间”,即“真时间”,而“叙事时间”是话语或文本叙述之下的时间,也被称为“伪时间”。在热奈特的时序理论中,他将故事时间和叙述时间的不一致性称为“倒序”或“倒错”,指“故事时序与叙事时序之间各种不协调的形式”(23)[法]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第14页。。在20世纪以来的现代小说或后现代小说中,事件的叙述顺序很少按时间先后依次呈现,这种时间上的错乱和倒置在增加阅读难度的同时,也极大了丰富了文本的意涵,形成了有趣、复杂的多层次叙述。福克纳曾说,“世上只有现在,我让它包括了过去和未来,这就是永恒。”(24)Meriwether,James and Michael Millgate.Interviews with William Faulkner: 1926-1962.Lincoln, N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65, p.58.
作为一部大众历史的书写者,克莱迪娅与她的男性同行对“过往”的理解有很大区别。一直以来,后者舒适地呆在自己的专业圈里,认为历史应该摒弃任何个体的、情绪化的嘈杂因素。更重要的是,在他们看来,历史应是关于重要事件的客观线性描述。而对于克劳迪娅来说,传统的线性时间观与客观的学究式的视角并不适用于她的历史书写。在《月亮虎》中,时间倒序不仅是一种建构文本的策略,更是一种反叛常规历史书写的武器。它完全打扰了叙事时间和故事时间的序列顺序,利用时间倒错的方法将关于自我的故事拼凑起来。莱夫利在2009年被英国《卫报》采访时提到:“认为记忆是线性的看法是荒谬的。”(25)SusanWatkins.Summoning Your Youth at Will: Memory, Time, and Aging in the Work of Penelope Lively, Margaret Atwood, and Doris Lessing.Frontiers: A Journal of Women Studies, 2013, 34(2), p.222.《月亮虎》中呈现的历史事实由一连串非线性的、零碎的回忆构成。有些片断发生在当下,如以第三人称(或全知叙述)视角展现的克劳迪娅与前来探视的亲友们的对话,多数片断发生在克劳迪娅早年生活的闪回中。这些时间被拆解、撕扯、折叠,不再是不可撼动的因果相承链条,而旨在于建构一个真实而深刻的女性个体生命。
在20世纪的艺术史上,女权主义艺术家米里亚姆·夏皮罗(Miriam Schapiro)发明了一种称之为“女性拼贴”(femmage)的形式,对传统的妇女身份进行探索并表达质疑。它“来源于女性的生活体验,反抗男性在艺术中的文化特权”(26)GwenRaaberg.Beyond Fragmentation: Collage as Feminist Strategy in the Arts.Mosaic, 1998, 31(3), p.160.。作为女性审美隐喻的拼贴模式也经常出现在20世纪英美女作家的作品中,传统小说里稳定的故事主线和文本结构在这些女作家看来仿佛社会中坚若磐石的男性权威,因此,莱夫利也有意规避因单一线索推进而造成的叙述紧张感。正如杰克森在评价莱夫利1993年出版的小说《克莉奥帕特拉的妹妹》(Cleopatra’sSister)时提到:“(莱夫利)知道混乱的历史书写从始至终都乐衷于寻找唯一的答案(结局)。”(27)Tony E.Jackson.The Consequences of Chaos: Cleopatra’s Sister and Postmodern Historiography.Modern Fictions Studies, 1996, 42(2), p.413.“唯一的答案”有可能被扭曲或被权力挟持,因此引入多个人物的叙述是莱夫利挑战传统历史书写、形成非线性的“女性拼贴”叙事的重要策略。《月亮虎》叙事顺序大体从眼前回溯过去,再从过去回归眼前,首尾呼应,构成一个封闭的回形结构。零散的画面之间呈现出一种嵌入、连贯、交织的场景,像项链上的串珠,串起了克劳迪娅内心一连串真实的感受。 实际上,多重叙述视角是20世纪以来小说常用的技巧,现代主义大师们往往通过破碎的意象、混乱的语言和倒错的时间展示人物背后的视角。如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展现了不同人物不同的心理活动,体现了不同思想主体之间的分裂及人与人之间深刻的隔阂,拼接出蒙太奇般的荒谬现实。但在《月亮虎》里,不同的视角间隐含着共同的元素,他者的视角里也有克劳迪娅自我认知的影子。莱夫利通过不同视角着力强调的不在于差异性和分离感,而更多地强化了不同意识碎片之间的关联,从而共同解构了父权制社会中的既定象征秩序。 莱夫利喜欢在自己的小说中使用“拼图”和“万花筒”的概念作为移动视角的隐喻,在《月亮虎》里,她延用“万花筒”来形容回忆的片断。同样的人物、背景、细节,却由于不同的视角而形成了多样的彩色碎片,并揉和形成不同的图案。这种集合式的叙述策略构建了共同关联的话语层面,从而强化了作者的意图,使个体经历成为大历史叙述中的闪光部分。“万花筒”不仅作为文本里的隐喻,它也意味着小说的结构本身——这些不断变换视角的叙述声音在故事上空交错响起,此起彼伏,它们与零碎、非线性的历史回忆形成一系列遥相呼应、互相补充的意义网络,最终汇聚成一部充满张力的女性活动史。
三 女性独特的叙事语言与声音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法国女权主义者认为语言是一项重要武器,它不仅是一套命名与交流的系统,更是意义、价值与权力产生的场所。不论是朱莉亚·克莉斯蒂娃(Julia Kristeva)的符号学,还是西苏的女性书写都否定了语言本身的稳固性特征。美国女权主义者玛丽·戴莉(Mary Daly)、卡罗琳·赫尔布伦(Carolyn Heilbrun)认为话语被男性垄断,因此这个被男性命名的世界导致女性集体失声。二战后不少女作家通过叙述与语言实践,来彰显自身的写作立场。如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让她笔下的女性像天真的孩子,时常面对语言表现出一副懵懂无知的样子,巧妙地质疑、嘲讽了已经确立的传统话语形式。英国女作家玛格丽特·德拉布尔(Margaret Drabble)则让一个全能的叙述者不时地闯入小说,对小说的情节与结局进行评论。在《月亮虎》里,莱夫利通过人物不间断的回忆与多种叙述视角,对用于描述现实的传统语言进行质疑、颠覆,从而构建女性独有的历史言说策略。克劳迪娅在童年时期就对语言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当她问母亲:“有人知道世上所有的词汇吗?”母亲的回答含含糊糊,“我想只有极其聪明的(男)人才知道的吧。”(28)这句话的原文是“I expect veryclever men do”,这里的men应该是特指男人。母亲的看法不言而喻,只有男性才能精准地阐释现实。成年后的克劳迪娅有意通过不断的写作来回应社会中的性别话语歧视,建构与自我生命体验相联的表达方式。小说中不同的声音虽然裂解了以一贯之的女性叙述视角,却成功地赋予文本以复杂的精神特质。同时,小说的语法凝练,在语言、用词、句子结构与语体的转换中呈现作为女性的“我”笃定的目光、真诚的思考和感受,也保留了一些处于变化中的思想与情感。
自埃莱娜·西苏提出“女性书写”以来,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关系是女权主义者关注的重要议题。西苏在《新生女》中提到女性作为不同于男性的“他者”,是“在包容差异和性别的基础上选择一种明显的、特有的存在”(29)HélèneCixous.La Jenue Née.Union Générale d’Editions, 1975, p.154.。因此,她们在写作中是开放的、无中心的、流动性的和包容性的。美国女性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南希·乔多罗(Nancy Chodorow)继承了前辈卡伦·霍尔奈(Karen Horney)对女性心理发展“本质论”的批判,反对以男性为视角和标准度量女性心里的做法。她认为,伴随成长,男女婴童逐渐形成分离意识,产生了自我的界限,但相比于男性,女性对分离的感受体悟较晚,“女性的两性经验(如怀孕、分娩等)都会妨碍她形成明晰的分离意识,因为孩子曾经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30)Nancy Chodorow.Family Structure and Feminine Personality.Michelle Zimbalist Rosaldo and Louise Lamphere eds.Woman, Culture,Society,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59.。卡罗尔·吉利根(Carol Gilligan)也认为女性的自我界限较少,“与男性相比,自我意识的表达更为流畅”(31)CarolGilligan.In A Difference Voice: Psychological Theory and Women’s Development,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1982, p.6.。晚年的克劳迪娅声称自己不会“选择冷静平和、毫无感情的叙述语气”(32)[英]佩内洛普·莱夫利:《月亮虎》,第13页。,但她尽力避免虚伪,在讲述中尽量保持平稳、真诚的声音。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我”的意识自如流畅,甚至不受外界舆论与道德成见的制约,毫无顾忌地袒露真实心声。莱夫利一开篇就向读者展示了克劳迪娅与哥哥戈登的关系,她的性格和对自我的认同很大程度上缘自“质层”记忆中自己与哥哥的相处经历。童年时期他们时常就某个问题展开激烈争论,克劳迪娅也因此形成了独立思辨、勇于抗争的性格。女性与男性生而平等,这在克劳迪娅看来牢不可破的观念就形成于自己与哥哥的相处模式中,一直以来,她都将哥哥视为自己的灵魂伴侣。但克劳迪娅毫不避讳地从自己的视角暴露了他与哥哥存在着的难于启齿的乱伦关系。她自述,“我从戈登的阳刚中窥见自己的情欲在闪烁;而他注视我时,我从他的眼眸也见到了令人怦然心动的回应。我们就像两面相对的镜子,将无穷的影像抛给对方。”(33)[英]佩内洛普·莱夫利:《月亮虎》,第199—120页。但在与戈登产生“情愫”之后,克劳迪娅没有因此屈从于男性或对男性心存敬畏,相反地,她从“他者”的镜像中进一步强化了对自我的认知。因此,在自我的声音中大胆地暴露为社会规训所不耻的隐私,正体现了克劳迪娅对自我的建构和对自身独立价值的不懈追寻。
诚然,女性书写中的叙述声音不应简单被视为某种写作技巧或策略,它与社会历史、意识形态与象征寓意之间存在复杂的关联。苏珊·兰瑟(Susan Lanser)在其著名的论著《虚构的权威》(FictionsofAuthority)里探究了文本里叙述声音隐藏的意识形态,她提出的叙事学理论为剖析小说中的女性自我意识建构和话语策略提供了富于启发的视角。兰瑟将女性主义与结构主义叙事学结合于文本批评的实践中,探讨女性特有的言说方式与审美价值,同时将叙述声音与女性的时代处境、社会权力关系相结合,从而丰富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范式。在女性文学的传统里,从夏洛蒂·勃朗特到弗吉尼亚·伍尔夫,作品里的个人声音越来越清晰。与传统小说里全知的叙述者相比,个人的声音“有意讲述自己的故事”(34)[美]苏珊·S·兰瑟:《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黄必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2页。。女性的声音是对社会性别文化权力关系的有力回应,“自我故事的叙述者‘我’也是结构上‘优越的’声音,它统筹着其他人物的声音。”(35)[美]苏珊·S·兰瑟:《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第20页。兰瑟从对“故事”的考察转移到对“话语”重要性的发掘,她指出,任何一个叙述主体都需要通过构建话语权威主导社会权力,基于此,叙述声音即文本写作的话语策略,成为建构权威的重要方式。“声音”既是性别身份的符号,更负载着特定的性别权利,“能够发出声音就意味着女性个人或群体作为实体的话语存在”(36)黄必康:《建构叙述声音的女性主义理论》,《国外文学》2001年第2期,第117页。。
在《月亮虎》开篇,克劳迪娅声称自己在写一部世界史,即奠定了小说回忆历史的基调。“历史之声当然是复合而成的。有许许多多的声音……我的故事与其他人的故事交缠在一起……他们的声音也必须被听到,因此我当遵循历史惯例。”(37)[英]佩内洛普·莱夫利:《月亮虎》,第9—10页。小说由以克劳迪娅第一人称回忆与第三人称叙述相交错,几位人物在克劳迪娅人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参与构建、述说她的个人历史。一些重要片断分别由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重述两次。其中“我”作为主要叙述者,不仅描述人物的行为,而且掌握着书写重要历史事件的节奏,使自我意识在不同的“层级”间流动。正如多丽丝·莱辛所说:“年老是记忆的伟大复兴时期,而我们可以用多种方式触碰记忆。(38)DorisLessing.“Old”in Time Bites: Views and Reviews, London: Fourth Estate, 2004, p.215.晚年的克劳迪娅脑海里构思的是如何用不同的叙述声音阐述历史——一段段包裹着个体生命体验的公众历史。 小说旨在反权威,因此多种声音有利于打破单一话语权,但声音之间却存在微妙的差别。克劳迪娅第一人称的叙述语调是真诚的、有感染力的,相比之下,第三人称视角的语气却是干瘪的,因尽力维持客观而显得缺乏激情。在病房里,当读者通过第三人称视角看到一个奄奄一息的老妇时,另一个清醒的来自克劳迪娅的声音却时不时提醒读者她一如既往的尊严与骄傲。小说写到:“既然我的故事也是他们的故事,他们也就必须发声……只不过,当然由我最后发言。这是历史学家的特权。”(39)[英]佩内洛普·莱夫利:《月亮虎》,第10页。“我”作为个体历史与大众历史的书写者,在叙述过程中可以管理其他角色的声音,凸现自己的权威,建构具有话语效用的叙述场景,从而构建自我在历史中的独特价值。
评论家玛丽·赫利·莫兰(Mary Hurley Moran)认为,“莱夫利的创作风格介乎实验性与现实性之间,她不仅关注文学的纯粹形式与审美,更关注文学的道德内涵”(40)Mary Hurley Moran.Penelope Lively, New York: Twayne Publisher, 1993, p.5.。莱夫利赋予笔下女性的反抗勇气和人性关怀,源于她对于社会历史现实的深沉关切。彰显个体价值的反父权书写、反凝视的姿态与反线性的叙事结构、女性独特的语言与声音,既是克莱迪娅也是莱夫利书写历史时的主要手段。正如保罗·利科所说,“书写生命却是另一种历史。”(41)[法]保罗·利科:《记忆,历史,遗忘》,第73页。在《月亮虎》里,克劳迪娅在她一生最后几天的光阴里,以回忆的形式一层一层地拨开自己生命的层级,书写了一部关于自我与世界的历史。在自我历史与大众历史的书写中,克劳迪娅不断质疑男性设立的权威的时间观念,以非线性的、碎片式的追忆模式向传统的历史书写发起挑战。“离经叛道”不仅可以用于描述克劳迪娅的行为,更深藏于小说的内部纹理。小说在语言、用词、句子结构与语体的转换中呈现了一种简洁的、干练、清醒的知识女性声音,旨在从内部颠覆权力机制,构建个体的话语权威,表现了女性在书写历史时的真实与真诚。在莱夫利看来,岁月的流逝对于女性来说,并不意味着衰老,反而使自身与时间、记忆、社会、历史产生了新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女性的性别意识、个体意识和言说方式不仅能够由内而外编织出一部历史,更能从内部架构中展现出一套女性独特的历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