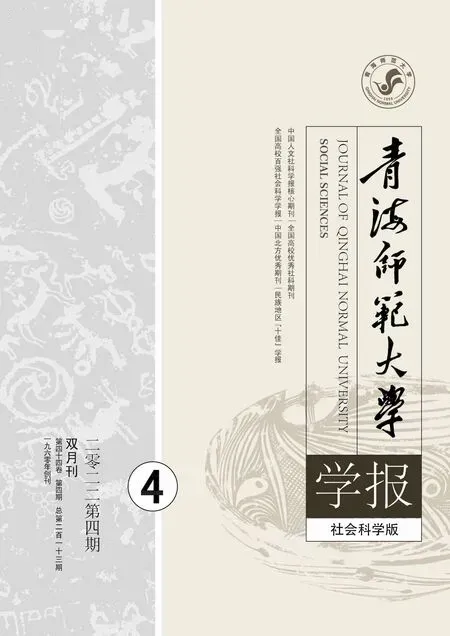“民主儒学”引论
——定公八年鲁国“宝玉”被盗事件详考
2022-03-23刘斌
刘 斌
(山东大学 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100)
中华先民与玉的接触至晚在一万六千年前就已开始。其后经历过以轩辕黄帝为首的传说时代,以夏启为首的三代时期,以汉唐为代表的晚近岁月,至于今天,玉依旧是华夏儿女日常生活中不可或替的财富与瑰宝,围绕玉发生过的贵族交谊、家族故事、情感传奇数不胜数,这其中鲁定公八年(公元前502)鲁国“宝玉”被盗事件因为被记录在《春秋》当中尤为引人瞩目。故事的大体经过是西周初年周天子出于拱卫周室,同时也是为了表彰周公德行的目的,分给鲁国的夏代宝玉“夏后氏之璜”,在鲁定公八年失窃后又在鲁定公九年失而复得。
孔子在《春秋》当中这样记载:
(八年)盗窃宝玉、大弓。[1](P2141)
(九年)得宝玉、大弓。[1](P2143)
据《鲁周公世家》,武王克商以后封周公于鲁,但周公为辅佐武王并未就封,而是命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鲁,之后不久武王故去,成王即位。因成王年幼,周公继续辅佐周天子直至故去,成王则为褒扬周公之德,命鲁国得以郊祭文王而有天子礼。我们要讨论的“宝玉”应该就是周成王统治期间赐予鲁国的一件玉器。
鲁定公四年也就是鲁“宝玉”被盗之前四年,卫国的祝鮀还曾有过这样的追述:
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为睦。分鲁公以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1](P2134)
所谓“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即《春秋》所记“宝玉、大弓”,前者据说为夏代宝玉,后者为古封父国所制。《周礼·大宗伯》有“以玉作六器”“玄璜礼北方”[1](P762)之言,概周天子赐予鲁的宝玉本是夏朝时人用以礼敬北方之神颛顼所用,三代相沿周室得之,其后出于表彰周公的目的赏赐给了鲁国。至于鲁定公时期应该已在鲁国保存了五百年之久。遗憾的是鲁人晚节不保,作为国之重器,“鲁宝玉”居然被人盗走,还作为一次历史性事件被写到了史书之中遭人讥笑。
一、内外背景
任何偶发事件都展现着历史发展的大逻辑。本来周公是周代礼制的制定者,作为周公封地的鲁国理应成为这一方面的楷模,而且自伯禽以降至于鲁真公时期历代鲁公立嫡以长、兄终弟及,鲁国在遵行礼制方面一直都中规中矩无可挑剔。然而自周宣王时期开始,因为周宣王欲立鲁公少子而强行干预鲁国继承制度,导致鲁国统治阶层欲循礼制行之而反不可得,鲁公室依礼传国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其后“诸侯多叛”,[2](P1528)公室日趋式微和衰落。鲁僖公、鲁文公之世季氏、孟氏、叔氏三桓势力崛起,鲁国政治开始进入私强而公弱的新阶段。“鲁宝玉”被盗事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当时的大背景是,随着晋楚争霸局面的形成,特别是晋国在北方中国的崛起,鲁国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特别是鲁昭公时期,任期内的第二年、第五年、第十二年、第十三年、第十五年、第二十一年、第二十八和第二十九年先后八次主动访问晋国,六次被拒,导致鲁国的实际地位某种程度上比宋国和郑国还低。而且鲁执政三桓,先是鲁昭公十三年第六代季氏(1)从季友开始算起季孙意如为鲁国季氏第六代人物。参见《史记·鲁周公世家》。季孙意如在鲁昭公莅盟的情况下被晋国拘禁,后是鲁昭公二十三年叔孙氏又因为小诸侯国的控诉亲自赴晋说明情况时再次被晋国羁押(两年后于昭公二十五年卒),十年之内两位上卿接连被诸侯盟主所拘禁,对于周公的封邦而言无异乎奇耻大辱。叔向说:“会朝,礼之经也;礼,政之舆也;政,身之守也。”[1](P1972)鲁公室既不得于诸侯之会,鲁三桓复不能自保其身,这是一个公室丢脸而三桓蒙羞的时代,地位极低。
其二,国内形势矛盾复杂。首先是公室与三桓之间相互支持又相互打击。鲁公室欲去三桓势力由来已久,早在“公室卑,三桓强”[2](P1536)局面刚刚出现的鲁宣公时期鲁公室就曾尝试借助势力打击三桓,至于鲁昭公时期昭公伐季氏不成而逃亡国外,已是公室打击三桓的第二次尝试。而以季氏为代表的三桓对于鲁公室更是“离心离德”。昭公十三年平丘之会,晋国因小国之讼而拒绝鲁公与会,同时拘禁季氏自秋天至于第二年春天,其后隔了两年为了当年之事(鲁公被拒并季氏被禁)昭公再次访晋,又为晋国人阻挠羁绊于晋国多达半年之久始得回国,旧籍记载云:
公至自晋,子服昭伯语季平子曰:“晋之公室,其将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强而奢傲,将因是以习,习实为常,能无卑乎!”平子曰:“尔幼,恶识国?”[1](P2080)
说昭公几经阻挠和羁绊终于回到自己的国家,满怀正义感的子服景伯在对话时批评晋,季氏不仅不为鲁君说话,反而讥讽子服景伯不懂关系和国家政治,以鲁公之被阻为应然,这自然是有负其臣子之职。事实上,当时的鲁国政治一边是三桓执掌政权而公室形同虚设,一边是三桓势力内部“世卿”偏废而陪臣当政。先是鲁昭公十二年季氏有南蒯之叛,后是定公年间季氏再逢阳货之乱,陪臣当权而执政失势,世卿违公室,陪臣令世卿,鲁国极其微妙而复杂的政治形势是“鲁宝玉”被盗事件的第二重背景。
其三,宝玉文物行情看涨。春秋中后期以来诸侯之间索贿受贿屡见不鲜,甚至当时的周天子都不能幸免,旧籍记载公元前527年周景王居然在妻子刚刚安葬后就公开向参与葬礼的晋国人索贿,其时政界风气之不堪于此可见一斑。随着政界人士的贪婪成性,宝物彞器的价值和价格亦随之大涨。鲁昭公十六年就在周景王索贿事件后一年,晋国执政韩宣子亲赴郑国索要“玉环”。(2)旧籍叙述更为详细但不免铺张,为行文计引文有缩略。韩宣子索要“玉环”或者更有其他的政治目的,但“国际市场”上“宝玉”价值渐增也是不争的事实。旧籍称:
宣子有环,其一在郑。韩子买。商人曰:“告君大夫!”韩子曰:“敢以为请。”曰:“失诸侯。”韩子辞。(引文较文献所载有删减)[1](P2079-2080)
晋国是当时诸侯国中的盟主,以盟主国家执政的身份亲赴小国索要玉环,足见当时的诸侯贵族中爱玉之风的兴盛。
其四,以孔子为代表的民间力量崛起。如上所言,鲁国从周宣王时代以来上自公室下至私家违背和僭越礼制的事情屡见不鲜,无论是礼制、礼仪还是礼义至于鲁国宣公和昭公时代在公室和贵族生活层面早已如深秋枯叶一般零落殆尽。旧籍记载鲁昭公七年三桓之一的孟孙氏随同国君出访,郑楚期间两次都因为缺乏基本的礼仪知识而出丑,旧书谓其“郑伯劳于师之梁,不能相仪”,“及楚,不能答郊劳”[1]P2048。这说明到了鲁昭公时期,至少是鲁国的孟孙氏家族,在礼学知识方面已经匮乏到不足以应付基本国际政治需求的地步。这对于天选的“礼仪之邦”而言实在已是太过不堪。同不学无术的贵族集团不同,就在礼学衰微的襄公和昭公时代孔子应世而来,一片早春时期才能见到的叶开始在鲁国的大地上悄悄生长。而且大约当时当世的智者早就已经知晓此事并开始悄悄向外传播圣人降世的消息。所以恨不懂礼仪的孟釐子对自己的家臣讲:“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吾闻将有达者曰孔丘,圣人之后也。”[1]P2051孟釐子随访楚国的时候孔子才十六周岁,还只是一个刚刚笃定自己志向学习礼文化的青年。十七年之后孔子过而立之年,孟釐子去逝,鲁贵族孟孙氏正式从学孔子,积年好学的孔子开始在鲁国上层贵族集团中崭露头角。而所谓礼仪之邦的鲁国也终于在迷失很久以后迎来了一次借助民间力量重回礼教正统的最佳契机。
以孔子为代表的民间政治文化集团的崛起是鲁“宝玉”被窃事件即“阳货之乱”的第四个重要背景。
二、阳货之乱
从相关资料的记载来看,阳货为人博学多识、骁勇善战又专横跋扈。鲁哀公九年宋国人攻打郑国,晋赵鞅在救郑的问题上犹豫不决诉诸占卜,阳货占以《周易》谓:“宋方吉,不可与也。”[1](P2165)众所周知孔子壮年后素以博学著称,但独于《周易》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1](P2482),说明早年的孔子对《周易》并不精通,反倒是阳货能以之断大事,作为季氏家臣和实际在当时的国际政治中驰骋多年的精英,至少从《易》学的角度来看阳货算得上博学而多识。又据记载阳货为季氏臣期间曾于昭公二十七年、定公六年两次参与征伐与作战,一次是与孟孙氏携手攻打鲁国的郓城(实际攻打鲁昭公),一次是随同鲁定公、季氏和孟氏一起侵略郑国,两次作战均获成功,第二次还从郑国获匡地,大约阳货确也算得上骁勇善战之辈。当然或者与个人能力有关,作为家臣的阳货最大特点是专横跋扈,且不说鲁国无君的背景下与孟懿子一起攻打鲁昭公明显属于大逆不道、蔑弃公室,就算是鲁国的实际执政若季氏、孟氏也不被阳货放在眼里,据记载鲁昭公六年鲁定公攻打郑国后返鲁阳货曾强迫季氏和孟氏从卫国国都穿城而过,惹起卫国人的极大愤慨,而以臣令主的行为更是将专横跋扈的特点暴露无遗。
阳货作乱之前曾经和孔子有过一次会面,也就是今传本《论语·阳货》的首章,章文谓:
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涂。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仕矣。”[1](P2524)
我们推测本章内容所及应该是在鲁定公八年的春天或夏天,理由是:一,本章提到孔子对阳货自己“将仕”的承诺。孔子初仕在鲁定公九年(3)《孔子世家》提到阳货在定公八年作乱,其后不久鲁国以孔子为中都宰,再后来鲁定公十年孔子相鲁公于齐鲁夹谷会盟,由是我们推断孔子初仕当在鲁定公九年(公元前501)。,依孔子“人而无信,不知其可”的做人做事风格,[1](P2463)既然亲口承诺“将仕”,对话当时距离实际出仕在时间上应该不会相去太远;二,孔子弟子当中直接就有鲁国统治集团的核心人物孟懿子,所以我们分析从孔子做出出仕的承诺到真正实现出仕时间上不会间隔太久;三,从章文叙述来看当时的阳货既然能从容地馈礼孔子而后与之相见于中途,无疑依然是在扮演着季氏家臣的角色,所以我们推断其时约是在鲁定公八年阳货为乱之前,也就是说本章文字最有可能或者说最合理的时间应该是在鲁定公八年的春天或夏天。
这个时间就阳货为乱和鲁“宝玉”被窃事件而言无疑十分微妙。
此前鲁昭公十三年不能辅佐国君参与平丘之会而自己更被公开拘禁半年多的鲁国第六代季氏季孙意如刚刚在定公五年去世,而有意思的是这位曾经被外国人公开拘禁的鲁国第六代季氏的继任者甫一履职就因为人事矛盾被本国人也就是自己的家臣阳货拘禁,后者更在其后半个月时间内对亲近季氏的基本力量进行了彻底清洗,还胁迫季桓子与之盟誓,定公六年更是挟定公并三桓再次盟誓。可以说阳货在当时的鲁国近乎权势熏天。《公羊传》有谓“阳虎专季氏,季氏专鲁国”确乎不假。[3](P600)
我们分析阳货见孔子或者恰是要为自己作某种舆论和人才方面的准备,部分地也是更主要的应该是要借包括孟孙氏在内的力量牵制新任第七代季氏季桓子。季桓子继任的第二年赴晋国出访阳货强迫孟懿子随行一定程度上大概正是出于此一目的。至于定公八年这种专政思想进一步发展为取季氏而代之的思想和实践。《公羊传》记载季桓子当时曾以“某月某日,将杀我于蒲圃,力能救我则于是”之言向孟孙氏、叔孙氏求救,[3](P600)旧文言之凿凿,自然是确有其事。只是事情并没有阳货计划的那么顺利。首先是阳氏亲近临南(或谓林楚)不忘季氏旧恩关键时刻背叛阳货;其次是孟氏集团在相关地点伏兵数百以救季氏,于是阳货的计划尚未执行就中途夭折在了前代季氏的荣宠与孔子门徒(孟懿子及孟氏所准备的武装力量)的搭救上。然而阳货或是为昔年旧事所激或是一时的气愤所致也或者为了其他目的,居然在打仗打输之后公然进入定公的宫殿取走了鲁国的镇国之宝,也就是我们开篇提到了“夏后氏之璜”与“封父之繁弱”。据记载鲁国当时还有一件宝玉名曰“玙璠”,孔子曾有“美哉玙璠!远而望之,奂若也;近而视之,瑟若也”的感叹。[4](P3)鲁定公五年季孙意如卒后阳货曾想用“玙璠”为之随葬却被季氏的另一名亲近仲良怀拒绝,此或正是计划落败后的他盗取鲁国镇国宝玉的直接诱因。
阳货盗走鲁宝玉后辗转去了晋国,其后第二年夏天又把宝玉还给了鲁国。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一时不好考证。就当时的鲁国而言,昔年周天子所赐的镇国宝物失而复得倒也算幸运。
但是真正值得鲁国人为之庆幸的大约还不在“宝玉”的失而复得,而在关键的时候他们启用了孔子。鲁昭公二十四年或稍后孔子访周归来后一直在鲁授徒讲学。其后昭公出走,孔子一度入齐,不久又因为齐不能以季氏待之,且包括齐国官僚的排挤愤而返鲁。
三、鲁用孔丘
我们讲,尽管对阳货不大感兴趣,但在追平季氏这一点上,两人倒是颇为一致,而且较诸阳货欲去季氏而自立,孔子在齐国时在个人待遇上追平季氏的努力似乎还要早好几年时间。说起来在争取“更大权利和待遇的问题上”,孔子还算的上季氏家大夫的前辈。
关于孔子与阳货的关系,在我们看来至少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阳货和孔子一定程度上都代表着鲁国社会中下层力量的崛起。同鲁公室和鲁三桓相比,阳货作为季氏的家臣属于鲁统治集团中的下层力量,而孔子作为曾经的贵族后代至于鲁襄公时代已经与平民无异,所以无论是阳货在季氏集团中权势的增大还是孔子在鲁国贵族中学术影响的增强,一定程度上都代表着春秋中后期鲁国社会下层力量的壮大,不过是一个居于上层表现为某种反叛和暴动形式,一个处在民间呈现出积极救世的态度,或者某种程度上这正是所谓“先贤的民主”。第二,阳货代表着颠倒的政统而孔子代表着复兴的学统。鲁国的继承制度周公时代以来一直都是兄终弟及、立嫡以长,所谓“一继一及,鲁之常也”[2](P1532),季氏的先祖季友本来是鲁庄公的三弟,既属于合法的鲁公继承人,又不是第一位的继承人,而在当时鲁庄公既未立季友更没有立季友的两位兄长,而是立了自己的儿子,就鲁国的继承制度而言事实上属于违制,所以季氏集团后来在鲁国成为执政的世卿,某种程度上反倒代表着鲁国长期以来错位政统的一个回归,尽管客观来说属于颠倒的政统(4)在周代封建统治秩序的意义上鲁国季氏集团长期执政还带有某种部分的“下层”官僚统治国家的“民主”气息。,因为季友之后的历代季氏既便作为世卿也断然已经没有继承政权的资格,但是作为实际执政的季氏似乎确又接续了鲁庄公时期应然的继承法则,所以我们称之为“颠倒的政统”。与阳货长期以来一直待在季氏集团不同,孔子最初不过是一个喜欢礼学的没落贵族、事实上的平民,但他年少好礼,在鲁国正统的礼制以及礼学衰落之后积极向学,希图重建“郁郁乎文”的宗周文明,[1](P2467)更曾为礼学专程赴周都城访学请教,代表着长期以来礼学衰微的鲁国渐渐复兴的“官学”正统或者说正宗的学统。第三,从相去甚远到渐走渐近。因为小的时候曾经被阳货公开拒绝,孔子本来对阳货并没有什么好的印象。但几十年服务季氏的家大夫终究不是等闲之辈,同在鲁国之内的孔子大约也不可能不对在执政集团内部影响巨大的阳货的存在每有风闻。当然,鲁昭公二十四年孟懿子从学孔子之后,阳货对于孔子的学问大概也会略有知晓。所以,从鲁昭公二十四年开始孔子和阳货之间的关系应该就已经出现了从渐行渐远到渐走渐近的转变。至于鲁昭公二十七年阳货和孟懿子一起攻打鲁昭公,作为世卿师的孔子和作为家大夫的阳货某种程度上已经站到了同一条战线里,因为无论是季氏也好,还是孟氏也好,无非代表着实际控制鲁国政权的三桓势力。
至于鲁襄公八年,阳货作为家臣为季氏服务已有三十四年时间。对于孔子而言,从年龄上来说阳货算得上他的兄长。当然孔子一直以来对阳货都没有什么好印象,即便作为季氏家臣阳货越来越位高权重。更何况二人一者为季氏的家大夫,一者为孟氏(孟懿子)的世卿师,作为不同政治集团的人物不可能不因为各自的利益而存在这样那样的矛盾与冲突。虽然至于鲁定公五年第七代季氏季桓子的时代,因为共同的目标,在对待季氏的问题上孔子和阳货又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某种不结盟的统一战线。
从《论语》全部记载来看,无论是称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好,[1](P2465)还是说“季氏富于周公”也好,[1](P2499)孔子对鲁国的季氏集团实在没有多少好感。(5)但事实上,鲁国的季氏大约并不向孔子所说的那样一无是处。至少鲁昭公被三桓赶出鲁国以后,当时的诸侯盟主晋国没有过度责备季氏,而是继续让其执掌鲁国政权,这本身无疑也是对三桓执政能力的一种肯定。对于鲁定公五年之后第七代季氏季桓子时代的阳货而言同样如此。而且,因为长期服务季氏,对于第六代季氏的晋国受辱、鲁昭公入晋时的连番被拒以及鲁国国内包括季氏在内三桓势力的种种作为,阳货更是有其切身的体会,就像季桓子继任伊始入费邑时的仲良怀辈之类。所以与大多数鲁人至于成襄昭时代已经“不知公室”,即所谓“民忘君矣”[1](P2128)一样,阳货对鲁国政治之不堪大约也是早已心生厌倦,所以在“政变”(阳货攻季氏算不得政变,我们姑且以“政变”相称)失败以后扔下“孺子得国”[1](P2340)的不屑之词率性而去。不过对身处民间的孔子似乎颇有不同。阳货包括季氏集团阳货一派的家臣大约都对孔子——一位凭借个人能力三四十岁左右折服齐国国主的年轻才俊——的学问颇为欣赏。究其原因来看,我们认为且不说为孔子所折服的齐景公对当时逃亡在外的鲁昭公都不怎么待见(6)《史记·孔子世家》所谓:“昭公师败,奔于齐,齐处昭公干侯。其后顷之,鲁乱”云云。[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910页。,即令与当时的诸侯盟主晋国国君相比齐侯的份量也不遑多让,所以孔子虽不用于齐,但其出访齐国的经历包括阳货及阳货一派家臣在内的鲁人应该颇有了解,而作为周公封地的鲁国所需要的正是孔子这样的人才。
所以,阳货才说“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说孔子口口声声宣传“仁”与“知”,实际上“怀其宝而迷其邦”,“好从事而亟失时”,以“仁”与“知”责之,孔子于是爽快地答应说自己“准备出来当官”。这之后大概没过多久,阳货“政变”未遂去鲁赴晋,鲁国则正式启用孔子,官居中都宰。史书谓:“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之。”[2](P1915)
于是,更有意思的一幕出现了。作为阳货集团骨干成员的公山不狃,在孔子被鲁国启用之后不久居然不顾鲁公室和三桓统治集团的猜忌,又一次向孔子抛出新的橄榄枝,《论语》中记载说:
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1](P2524)
中都在鲁曲阜西偏北,公山不狃所在的费这个地方在鲁曲阜东偏南,[5](P26-27)从孔子对子路的回答来看,大约做中都宰后仍觉得才不能尽,如果说中都比于宗周,那么费邑至少是成周洛邑之类的存在,说不定还能再造一个东周文明,所以孔子颇有些动心。《孔子世家》说:“公山不狃以费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弥久,欲往。”[2](P1914)自然大约孔子并没有真的如自己所讲的那样去公山不狃那里主政,但鲁国统治者包括三桓大约又一次感觉到了某种政治力量和政治优势有可能失衡的危险,于是进一步提拔孔子为司空,而后又做了鲁国的大司寇。
四、结 语
如果我们的分析不错,那么,过程上来看正是鲁国的镇国宝玉给了孔子真正出仕的机会。我们不知道“鲁宝玉”失窃以后孔子当时是什么态度,但子贡与孔子的一段对话颇惹人遐想:
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1]P2490
“待价而沽”这个成语应该就是出自孔子师徒之间的这一段对话。
我们推测孔子所以在子贡的追问下公开承认自己是一位待价而沽者,有这样两条原因:一者,鲁国自鲁真公以后礼制衰坏民心思变,一生好礼的孔子早已对鲁国政治不抱什么希望,所以对他而言国宝丢失亦无需大惊小怪反倒是在言谈之间与子贡开起了玩笑;二者,孔子饱学宿儒门徒广众,又不断有弟子追问自己为什么不出来从政之类问题,所以本人确也希望有机会将自己的学识运用于政治生活以安邦定国一展头角,而子贡所提到的美玉当售的观点恰合了孔子宝玉若己可以待价而沽的的心理;其三,如果说子贡和孔子讨论的正是“鲁宝玉”(7)在孔子和子贡,在鲁定公时代早期孔子正在授徒讲学这一大的言说背景下来分析,我们认为这一章所提到的“美玉”确有相当的可能就是作为夏后氏旧物被阳货窃走后给鲁国带来空前政治危机和政治机遇、《春秋公羊传》所提到的鲁之“宝玉”。而且就算其谈论的不是“夏后氏之玉”,在关于“玉”的讨论的意义上,我们用为分析孔子关于“鲁宝玉”丢失以后可能的态度也有其相当的参考价值。,那么,最重要也最值得人们遐想的正是阳货给鲁国留下的对孔子大有利的一个“国事大象”:
鲁有宝玉大弓,持国重器,请君上寻之。
《易·系辞》谓:“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6](P343)“象也者,像也。”[6](P373)
幸运的是,就在阳货作乱后的第二年,孔子的才华第一次真正在鲁国政坛得以绽放,恰如“阳货所‘期’”一定程度上亦如孔子所“愿”。至于不久孔子又在另一位阳货集团重要成员公山不狃的反向推动下进一步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我们只能承认阳货“公山不狃”对于孔子从政确实从侧面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同阳货和公山不狃不同,在孔子从政的问题上,作为鲁国“宝玉”的“夏后氏之璜”一定程度上则从正面起到了特殊而关键的“呈象”和推动作用,孔子走上政途,鲁国之“宝玉”事实上功不可没,而这大约是很多学人,儒学研究者包括历史学人所考虑不到的。(8)孔子主政包括以后周游列国再返回鲁国研究文化,对于鲁国国祚的延续都有突出的正面价值和意义,其后鲁国作为周初封国继续享国二百四十多年,孔子之功与有力焉。
尽管一生谈不上十分成功,但是以“一介布衣”通过勤苦学习而官至大司寇,开派讲学弟子三千,整齐经书传承文明,至于身后“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余室”[2](P1945),当时后世文化影响之大无出其右,作为早期中国民主政治的代表人物,孔子的成功是民心所向、是志士之选、是早期中国民主精神的巨大成功与光辉实践。而在这个过程中,阳货、公山不狃等人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亦可谓早期中国民主精神的先贤人物。某种程度上或者还可以说,后世以孔子为导向的儒学本就是“民主精神”之子。近现代以来关乎儒学可不可以开出民主价值的讨论至此可以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