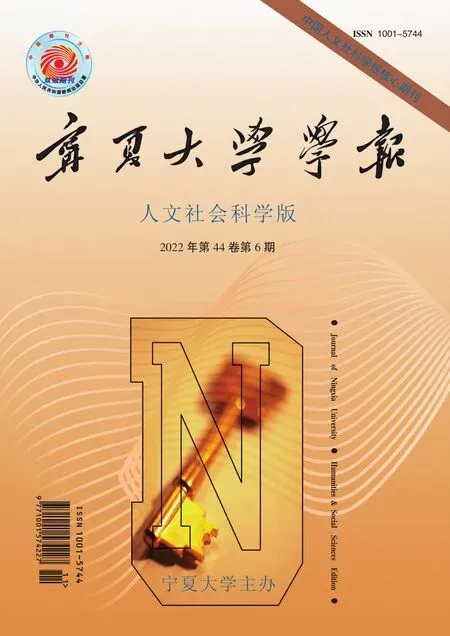本质与多面:近代以来中国历史虚无主义的三次流变及其批判
2022-03-23李世荣
李世荣
(宁夏师范学院政治与历史学院,宁夏固原 756099)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历史虚无主义在中国似乎从来没有彻底中断其传播的轨迹,几乎与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相伴而行,即便是在一定时期隐匿于世,但绝没有彻底灭亡。它往往以“坚韧”的延续性、富有欺骗的隐蔽性若隐若现于历史、社会乃至人们的生活周围,稍有不慎就会破土而出,冲击主流意识形态,造成社会思想的混乱。习近平总书记对此有着清晰的洞察,旗帜鲜明地提出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概括而言,历史虚无主义在中国经历了前后相继的三个历史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改革开放初期以及21 世纪以来。充分认识历史虚无主义的三次流变轨迹及其基本特征,深刻揭示历史虚无主义相对隐蔽的真面目,彻底廓清历史虚无主义的流毒与贻害,这对于扶正主流意识形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以正确的历史观正本清源、去伪存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意义重大。
一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史虚无主义滥觞及其批判
近代中国,国力衰微、民族危机日趋严峻主要源于思想禁锢、文化落后、制度腐朽。国力的全面落后很容易导致固有文化体系和意识形态的土崩瓦解,为新思想、新改造、新革命奠定了无限可能性,但主流文化体系和意识形态的失位,却很容易为“思想混乱”创造悄然滋生的温床。
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精英知识分子群体总结了自鸦片战争以来挽救民族危亡所走过的道路,从以李鸿章、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主张学习西方之器物,到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主张学习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度,再到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践行民主共和制度,由“器物”到“制度”的变革追求,在实质上并没有使近代中国摆脱如影随形的民族危机。因而,精英知识分子群体很自然地转向学习西方文化,以西方文化为武器,力图唤醒民族意识,挽救民族危机。一时之间,“文化救国”成为时代潮流,各种新文化、新思潮竞相并起,勾勒出蔚为壮观的文化转型时代画卷。思想转型不仅意味着文化体系的重构和社会秩序的再建,当然也意味着混乱和无序,这正是诸多文化与社会思潮,包括历史虚无主义滥觞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的动因。
历史虚无主义伴随着“文化救国”的时代潮流发端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以胡适、陈序经为代表的“全盘西化派”,以张东荪、张君劢为代表的“吉尔特社会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以黄凌霜、区声白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构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史虚无主义的主要思潮。实际上,除了上述三派,在学习西方文化的基础上产生的许多新文化、新思潮,诸如科学主义、平民主义、实验主义等,都或多或少具有历史虚无主义的倾向和痕迹。众所周知,历史虚无主义实际上是西方自由主义的“变异”,“近代以来,以自由主义为中心的西方文化作为一种迷惑性极强的社会意识形态伴随着西方列强资本的扩张而肆意传播,在中国以文化救国的名义形成了鲜明风格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想潮流”[2]。以历史变迁的眼光观之,滥觞于近代中国的历史虚无主义至今有三次影响较大的传播浪潮,每一个历史阶段的特征均有所不同,但“虚无”却是历史虚无主义最基本的特征。近代中国,面对先进的资本主义,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状况和社会环境等方面十分落后,尤其在文化与思想层面更是相形见绌。学习西方先进文化,进而达到挽救民族危亡之目的确然无可厚非,问题在于历史虚无主义者学习西方文化的方式、途径乃至价值观却陷入“虚无”之境地不可自拔,同样值得深刻反思。历史虚无主义之“虚无”首先体现在对待西方文化和中国本土文化的态度上,决然否定本土文化而追求全盘西化是历史虚无主义淋漓尽致的体现。从根源的“虚无”必然蔓延至政治、经济、社会等其他领域的“虚无”,导致不能正确认识近代中国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由此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陷入“虚无”的怪圈而不可自拔。
以胡适、陈序经为代表的“全盘西化派”首先掀起历史虚无主义的传播浪潮,“在近代中国,历史虚无主义是作为同‘全盘西化’论相呼应而出现的一种错误思潮”[3]。十分明确的是,“全盘西化派”是西方“自由主义”坚定的宣传者和实践者。正如许纪霖所言,“中国的自由主义主要是两路”,一是“新自由主义”,以胡适、傅斯年为代表;二是“社会民主主义传统”,以张东荪、张君劢为代表[4]。胡适等人的初衷是希冀以自由主义为内核的西方文化改造中国,这一初衷本身无可指责,反而应成为褒扬的对象——落后就意味着要学习和改造,这是一个民族由落后到强大的必经之路。问题在于,胡适等人决然认为中国文化一无是处,唯有全盘西化,走欧美资本主义道路才是挽救近代民族危亡的唯一路径。不论在学习的方式、途径上,还是在对待不同文化的价值观上都陷入“虚无”,造成很大的危害。在文化上的“虚无”必然导致政治理念和社会实践的“虚无”,从而全面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境地。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的历史也恰恰证明了这一点。胡适等人在政治理念的追求上主张以欧美资本主义制度为参照,施行一点一滴的改良,反对激烈的阶级革命和社会革命,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上同样秉持虚无主义的历史观,认为近代中国全面落后的主因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而非“帝国主义”的侵略[5],完全抹杀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社会实践中,胡适等人主张在中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好人政府”,以实现“宪政治国”的希望[6]。“好人政府”黯然失败以后,又寄希望于蒋介石作一个“宪政的中国领袖”[7],同样成为镜花水月。
以张东荪、张君劢为代表的“吉尔特社会主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又一重要的历史虚无主义派别。依据左玉河的研究,张东荪的中西文化观是典型的“输入论的文化观”,并认为张东荪虽然是一个“西化论者”,但与胡适等人所强调的“全盘西化”又有不同[8]。实际上,仅就对中西文化的态度而言,张东荪的“输入论”和“全盘西化论”基本一致,如张东荪强调,要挽救民族危亡非输入西方文化不可,主张“彻底采用西方文明”[9]。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掀起“科玄论战”的张君劢对于中西文化的态度似乎要务实很多,“有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柢”[10]。但无论政治主张还是社会实践,张东荪、张君劢无视近代中国的国情,致力于“吉尔特社会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沦落为彻底的历史虚无主义者。从严格意义上说,张东荪、张君劢的政治主张较为复杂,一方面他们在早期也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如在上海创办《时事新报》及副刊《学灯》,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11]。另一方面,他们逐渐接受了“吉尔特社会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理念,最终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概而言之,张东荪、张君劢复杂的政治思想及其社会实践主要具有三个鲜明的特征。一是不能正确认识近代中国社会性质,惧怕剧烈的阶级革命和社会革命,希望用温情的、合作的方式实现对社会的改造,这显然是“全盘西化派”所推崇的资产积极改良主义思潮的翻版。如张东荪强调,社会改造不在于“革命宣传”或“革命行为”,而在于“思想的传播”[12]。二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如张君劢强调,“国家社会主义”才是挽救近代中国民族危亡的唯一出路,并宣称共产主义以“阶级”为立场,而“国家社会主义”则以“民族”为分野,因而要反对共产主义[13]。三是崇尚西方自由主义,把“自由”作为“国家社会主义”的核心理念,宣称以“个人自由”为前提,才能实现社会的改造。这些论点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政治主张,显然与近代中国的国情背道而驰,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潭而最终走向沉寂、归于失败。
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影响最大的历史虚无主义流派当属以黄凌霜、区声白等人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与其他文化思潮相比较,无政府主义的传播更为广泛,影响也更为深远。一方面,无政府主义者创办的社团组织数量众多、影响广泛,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广州、四川等地,著名的社团组织如安社、青年互助团、大同合作社等[14]。另一方面,无政府主义者创办了《进化》《新生命》《学汇》等多种报刊杂志[15],形成强大的宣传网络。无政府主义最初的思想主张颇有些离经叛道的味道,主张“民粹主义”、反对“国家权威”、崇尚“个人自由”、追求“道德完美”、注重“下层社会”,这些理念尤其对于致力于挽救近代中国民族危亡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有着天然的诱惑力,因而能够广泛传播。事实上,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渊源颇深,李大钊、陈独秀、恽代英等人就深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16]。但是,面对复杂的社会现实,无政府主义在发展过程中,逐渐迷失自我,走向反动,滑向历史虚无主义的深渊。李光一较为完整、科学地总结了无政府主义的反动特征:“攻击中国共产党”为其一,“反对中国人民革命”为其二,“堕落为社会改良主义者”为其三[17]。客观地看待,无政府主义思潮在最初的传播过程中,亦有着进步的作用,如反对强权和专制、追求社会平等、倡导青年思想之解放等,而且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也曾经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同样功不可没。但在其流变的过程中,以西方自由主义为底色,脱离近代中国社会实际,走向反动,走向历史虚无主义,“注定是一棵不结果实的花”[18],不免令人唏嘘。
二 改革开放初期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及其批判
20 世纪80 年代末至21 世纪初,在伟大的改革开放有序推进的过程中,历史虚无主义以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形态来势汹汹,在意识形态领域掀起了不小的风浪,影响较为恶劣。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几乎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全盘西化”的升级版,把“全盘西化”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打着“文化反思”的旗号,在“拿来主义”(全盘引进西方文化、范式及理论)的刺激下产生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全盘西化论”的继续和深化,本质上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
民族文化虚无主义首先滥觞于文学领域。“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以控诉“文化大革命”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本意在“纠左”,却不可避免地走向“否定过去”和“否定传统”的歧路。20 世纪80 年代中期,“寻根文学”异军突起,其主要特征是“片面地‘写阴暗面’,偏激地‘干预生活’,丑化现实,富于煽动性,制造思想混乱”[19],为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思潮的形成和传播摇旗呐喊。1988 年《河殇》的推出,矛头直指中国传统文化,在全国迅速形成“文化反思”的巨浪,把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思潮推向高潮。“果决地否定传统文化”成为《河殇》的主题,亦是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主题。《河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对西方文化的向往可谓触目惊心,全盘否定“黄河文明”(中国传统文化),全盘引进“蔚蓝色文明”(西方文化),拥抱工业时代,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其基本主张,并宣称,“中国的许多事情,似乎都必须从‘五四’重新开始”[20],亦即重构学习西方之路。至此,以民族文化虚无主义为表征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突破了文学领域的界限,开始浸染学术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成为一个时代的标签。
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思潮对传统文化的决然否定是极其荒谬的。首先,文化是民族性和时代性的统一,“任何一个文化既是民族的,又是时代的”[21]。民族性是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是民族的精神,时代性则是民族文化的与时俱进性,是民族的秉性,正如黑格尔所言,“(民族传统文化)它的宗教、礼仪、伦理、风俗、艺术、宪法和政治法律,实际上它的所有制度、事件和事态,都是它自己的产物,而正是这些内容使一个民族成为一个民族,成为它之所是。”[22]。以《河殇》为代表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思潮割裂了民族的传统和民族的历史,彻底否定民族精神,是典型的历史唯心主义。其次,民族文化虚无主义者视传统文化为糟粕,以西方文化为珍宝,将现代化与传统文化对立,认识不到现代化不等于西化、传统也可以通过与时俱进地创新走向现代化的客观历史发展规律,蒙蔽了双眼,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潭。最后,“文化反思”的旗帜本身值得肯定,但“文化反思”需要科学的态度,从民族文化的立场出发,应该学习先进文化,提升民族文化,而非“全盘否定”民族文化。“文化反思”的根本目的乃是创新民族文化和构建文化自信,正如毛泽东强调:“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23]
20 世纪90 年代始,学术领域突出的特征之一就是如饥似渴地“拿来”西方理论范式,用于阐释、构造以及“重估”中国历史与社会。“拿来主义”与五四运动时期的历史虚无主义“全盘西化”相比,其学习西方的狂热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本质上亦是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表现。学术领域的“拿来主义”突出地表现为全盘接受“现代化(西方化)范式”,并以此作为解释中国近代历史、研究中国社会的基本理论范式。在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以及“现代化范式”的左右下,学术领域亦兴起了历史虚无主义的浪潮,突出地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否定革命,主张用“现代化范式”取代“革命范式”。历史虚无主义者错误地认为近代以来的中国革命只是“对社会的破坏”、带给“中国很深的灾难”、革命的结果只是“专制复辟”、革命是“幼稚和疯狂”,等等。甚至抛出令人惊愕的观点,即近代以来的中国革命,抑制了现代化在近代中国的进程,“只有改良主义才是近代中国的唯一出路”[24]。这些观点与五四运动时期历史虚无主义者反对激烈阶级革命和社会革命的观点如出一辙,根本不值一驳。鸦片战争以后,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及官僚资本主义始终是造成近代中国民族危机的根源。要挽救民族危亡,争取民族独立,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动彻底的阶级革命和社会革命,推翻“三座大山”,别无他途。正如毛泽东明确指出的:“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个伟大的革命到达彻底的完成,除了中国共产党以外,是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政党(不论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或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能够担负的。”[25]
二是讴歌西方自由主义文化、制度,主张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从根源上言之,历史虚无主义的所有理论都是建立在对西方自由主义文化和制度的片面追求上,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的“全盘西化”“吉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到“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其赖以存在的根基就是以西方自由主义为本体的文化和制度。历史虚无主义者错误地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造成近代中国社会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脱节,“以英美为师”转变为“以俄为师的歧路”,导致近代中国社会完全落后于西方社会。历史虚无主义者还认为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破坏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只是一部荒唐史”[26]。因而,他们主张中国只有走资本主义道路才是正确的选择。实际上,近代中国民族危机如影随形,到底“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一直是“近代中国问题”的终极之问。回顾历史,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立宪派期盼中国走西方资本主义君主立宪之路,最终雨打浮萍、黯然失败;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希冀西方资本主义共和制度,也没有挽救中国的民族危亡;以“全盘西化”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期盼通过“宪政改革”和“好人政府”,在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达到挽救民族危亡之目标,但在蒋介石独裁统治面前成为海市蜃楼。历史证明,近代中国,走历史虚无主义者所倡导的西方资本主义改良道路根本行不通,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最为广泛的统一战线,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消除内忧外患,才能彻底解决“近代中国问题”。历史同样证明,新中国成立以后,也只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锐意改革、开拓创新,才能使中国人民富裕起来,国家强大起来。邓小平曾明确指出,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根本不符合中国之国情,波澜壮阔的近代奋斗史促使中国人民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27]
三是以唯心主义史观分析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与社会。价值观决定了一个人的立场,同样的道理,史观决定了观察、分析和研究历史与社会的立场。杨军说:“历史虚无主义秉持唯心主义历史观”[28],准确地说,历史虚无主义不仅秉持唯心主义历史观,而且遵从唯心主义价值观,始终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科学价值观的对立者。何谓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其基本原理可主要概括为以下六点:一曰人类社会及其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二曰人类社会历史按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规律向前发展;三曰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四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五曰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社会革命)和科学实验(指自然科学技术)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六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29]。历史虚无主义肆意割裂历史发展的规律,既看不到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实际状况,也看不到新中国成立以后面对的复杂和艰难社会境况,随意否定近代以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污蔑阶级斗争理论,恣意怀疑社会主义道路,夸大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历史虚无主义从唯心史观出发,以心理分析方法为准绳,把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描述为偶然性,把“臆想历史”当作客观历史。如对重大历史人物的评价依靠“断想”“推测”以及所谓的“心理分析”,把历史发展归结为人的主观因素,脱离科学的历史价值观,陷入“虚无”,完全罔顾事实。此外,历史虚无主义往往以“寻找真相”“学术创新”为由,热衷于用“历史选择论”来“研究”历史。以此出发,毫无底线地解构中国文化、历史与社会,完全否定一切革命的行为,如否定太平天国运动、否定辛亥革命、否定五四运动、否定新民主主义革命,反而大肆宣扬“殖民有理”“侵略有功”,为负面人物翻案,等等,令人瞠目结舌。
学术领域的“虚无化”“西方化”必然导致意识形态领域的颠覆、甚至反叛。历史虚无主义本质上是在意识形态领域掀起的一股逆流,否定马克思主义、否定新民主主义革命、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否定中国人民来之不易的伟大事业,其最终目的是割裂、分化、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把整个中国重新拽入四分五裂的近代社会,“倒退回旧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30],重新沦落为西方列强任意宰割的对象。意识形态领域无小事,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决抵制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廓清历史虚无主义的流毒与贻害。
三 新世纪以来历史虚无主义新特点新趋势及其批判
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的发展出现了新趋势,产生了许多引人注目的新特点,集中表现为“四化”,即“学术化痕迹”“文艺化倾向”“网络化途径”“社会化常态”,更应值得警惕、反思和批判。
新世纪以来的历史虚无主义首先呈现出明显的“学术化痕迹”。历史虚无主义者打着“科学研究”旗号,“标榜自己的纯学术、超党派性和价值中立”[31],醉心于“重估一切价值”,重视细节和心理的描述、猜测与评估,采用“解构主义”的方法来观察、分析和研究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完全脱离历史事实。历史虚无主义者通过搜集、整理和片面解读史料,甚至以某些失意人物的“口述史”“回忆录”作为正史资料,肆意解构新民主主义革命。其中的“五四割裂论”“侵略有功论”“革命有害论”“国民党抗战贡献最大”“长征重估论”“非毛化”,等等奇谈怪论甚嚣尘上,强势冲击着正统史观,其目的是凭借“学术”的外衣否定近代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历史虚无主义者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仇视,几乎是历史虚无主义者的共性。历史虚无主义者用解构主义的方法攻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把中国选择社会主义视为“离开‘近代文明的主流’而误入歧途”,鼓吹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32]。事实胜于雄辩,更胜于诡辩。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精诚团结、锐意进取、创造世纪伟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焕发出前所未有的光芒。事实充分证明,唯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才是中华民族取得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根本保证,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获得源源不断发展动力的根本保证。历史虚无主义者还以“探求真相”为名,否定马克思主义,错误地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伪科学”“伪史学”,这个观点更是不值一驳。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弊病深入考察,结合欧洲的社会实际,经过欧洲工人运动的实践,科学社会主义的洗礼而形成的科学理论,其本身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特质,是人类文明的结晶。
新世纪以来的历史虚无主义有着浓郁的“文艺化倾向”。近年来,文艺领域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较为严重,其以历史唯心主义为出发点,以“再现历史”“颠覆价值”“恶搞历史功勋人物”“重新评价”“戏说红色经典”等内容,庸俗化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渗透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冲击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颠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毋庸置疑,文艺作为历史阐释、生活再现的重要形式,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和传播力,倘若文艺虚无化,带来的危害则会十分严重。如质疑雷锋及雷锋精神、质疑黄继光、质疑刘胡兰、质疑邱少云等功勋历史人物,甚至诋毁、戏说、恶搞红色经典,影响十分恶劣。历史虚无主义者罔顾历史事实,兴起一股“负面历史人物翻案风”,如正面描述慈禧、为汪精卫的卖国行为辩护、同情蒋介石的不抵抗日寇政策,等等,颇有一幅乌云压境、群魔乱舞的气象。因而,清除文艺领域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刻不容缓。首先,文艺是主观的艺术产物,文艺作品要尽可能地接近史实、再现史实、立足现实、呈现现实,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避免“模糊价值观”“异化人性史”等历史虚无主义倾向。其次,文艺创作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遵循真史、正史。最后,文艺创作要以文化自信为出发点,热爱一个民族,就必然热爱这个民族的文化,“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33]。
新世纪以来的历史虚无主义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构成“网络化路径”强势传播。21 世纪最为耀眼的技术创新是网络化的普及,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兴技术把世界浓缩成触手可及的对象,通过“网络”的对话、评论、转发、写作、直播以及图像化叙事等各种灵活便捷的方式迅速传播观点,形成广泛的舆论效应,对主流意识形态构成强势的挑战。在网络世界,历史虚无主义无处不在、无孔不入,“实现了历史虚无主义即时、高效、广域地传播”[34]。概括而言,网络化的历史虚无主义主要特点集中表现为以下几点。第一,形成“碎片化”信息表达与传播的形态,冲击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科学价值观。网络化增强了人们猎奇和表达的欲望,历史虚无主义者正是利用网络化的“网民心态”,大肆传播与主流意识形态相悖的虚无价值观,从而达到其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险恶目的。第二,形成“主观臆想”的庸俗史观,以此来攻击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网络化的历史虚无主义者完全以个人喜好为出发点,戏说历史、恶搞历史、丑化英雄人物、美化反面历史人物,以“揭露历史真相”为噱头,片面曲解、解构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及历史人物,宣扬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引起思想混乱。第三,形成所谓广泛的“网络反华”意识形态主阵地。历史虚无主义者以网络为阵地,在意识形态领域渗透西方价值观,鼓吹“中国威胁论”,以“人权”为名,散布反华言论,分化、瓦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企图破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面对历史虚无主义“网络化”的强势传播现状,首先,要强化“四史”学习,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强化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和价值引领。其次,规范、净化网络环境,提升公众网络媒介素养,同时,要加强网络法治建设,从根本上廓清历史虚无主义的传播源,肃清历史虚无主义的传播流毒。最后,要坚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发展,扶正主流意识形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抵制历史虚无主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新世纪以来历史虚无主义具有“社会化常态”的新特征。和前两次历史虚无主义流变主要局限于文化、思想及意识形态等领域的特征不同的是,21 世纪以来,历史虚无主义悄然向“社会化常态”的特征转变。所谓“社会化”指历史虚无主义不仅在思想、文化、学术、文艺等领域传播,更是向教育、宗教、民族乃至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渗透,历史虚无主义的“社会化”成为常态,对主流意识形态和中国社会的冲击力度空前,危害极大。历史虚无主义在教育领域通过宣扬“后现代主义”“自由主义”“普世价值”等西方价值观,动摇青年学生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淡化青年学生的爱国情怀和责任担当,以此从意识形态上瓦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基。在宗教、民族领域,历史虚无主义宣扬“超然宗教观”“绝对平等论”,制造宗教间隙和民族隔阂,企图推行“和平演变”,颠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日常生活中,历史虚无主义提倡“泛娱乐化”“佛系文化”“躺平文化”,以此麻痹人们奋斗的动力,移花接木转移人们的视线,把矛头直指所谓的“制度固化”“阶级固化”以及“资源固化”,达到“颜色革命”的目的[35]。因此,我们要从根本上廓清历史虚无主义的“社会化常态”,一方面注重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引导和培育;另一方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心聚力、开拓创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向前进。
四 结语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精英知识分子群体以“文化救国”为旗帜,掀起了学习西方的热潮,作为西方自由主义的“变异”——历史虚无主义乘虚而入,形成了以“全盘西化”“吉尔特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为主要表征的思潮。改革开放初期,历史虚无主义以“民族文化虚无主义”为主要形态,片面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崇尚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主张“告别革命”,追求以西方文化为主体的“现代化范式”,否定马克思主义,追求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拥抱资本主义制度。新世纪以来,历史虚无主义的传播及其影响更是登峰造极,形成“学术化痕迹”“文艺化倾向”“网络化途径”“社会化常态”等鲜明特征,带来更为广泛的社会危害。
历史虚无主义自产生以来,至今经历了前后相继的三次流变,虽然每一次流变都有不同的特征,但其本质特征却一目了然: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意识形态领域无小事,我们要不断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全面建设,彻底肃清历史虚无主义的流毒,引导人们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