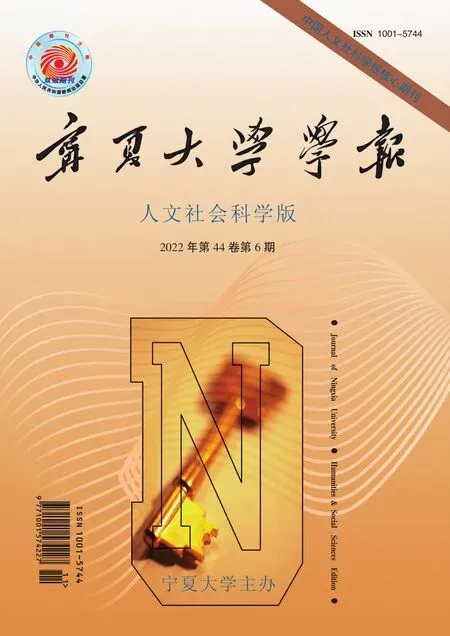论“诗言志”命题的整一性阐释
2022-03-23王昌忠
王昌忠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重庆 401331)
在陈列于中国古典诗学版图的众多命题中,“诗言志”无疑最为显眼。经《尚书·尧典》首次推出之后,“诗言志”命题的纲领、基础地位几乎没有动摇过。“诗言志”作为原生细胞,逻辑性蕴含着中国诗学的整体建构[1],的确,连绵不绝的中国诗学长河中,即便有“诗缘情”“诗言事”“诗言意”“文载道”等命题展显身姿,但它们往往也要想方设法依附、挂靠于“诗言志”命题以纳入其麾下。“诗言志”命题的经典性、权威性,自是得益于宗教、政治、伦理、文化、美学等各种外力因素的造就、作用;另一方面,也与诗学内部对它的认知、处理紧密相关。“诗言志”的意义指涉不是固定而是衍化的,内涵规定不是封闭而是开放的。翻开中国诗学册页不难发现,“诗言志”命题是在意义不断被灌注、内涵不断被赋予中漂移、行进着的。历代由政治、文化以及诗学潮流授予了话语权力的诗人、诗论家各取所需地指认、各依所用地阐释,正是“诗言志”命题延展意义、扩容内涵的主要途径。诗学理论源起于诗歌实践,同时又引导、规约着诗歌实践,因而作为中国古典诗学的旗帜,在告诉人们如何理解诗,如何受用诗的“诗言志”命题[2],不仅指引着诗学建设,而且直接规约着诗歌生产。认知、处理“诗言志”,事实上成为了中国诗学的核心问题,很大程度上可以认为中国诗学的主体内容,便由应对和演绎“诗言志”命题组合架构而成。中国诗学对于“诗言志”的阐释、言说,自是有其有效性、合理性的一面,但也暴露了一些缺陷、误区。厘清、呈现并审视、辨识中国诗学阐释“诗言志”的话语形态,既有利于光大“诗言志”命题,也有利于中国诗歌艺术的健全发展。
一 界说、理解“诗言志”命题的误区
通俗地讲,一个命题是什么意义、意思,不取决于它自身,而在于人们说它有什么意义、意思。“诗言志”是中国诗学的发生学基因和元观念,更是中国诗学的逻辑框架和体系结构,其意义、意思就“充塞”于该框架和结构里面。在《诗》的系统中,“诗言志”多关涉政教伦理及社会功能;而在《诗》外之诗的系统中,既有共享“诗”名的歌诗、乐府诗、玄言诗、宫体诗等体式,又有不以“诗”称名的赋、词、曲等体式。“诗言志”的理论内涵,随着“诗”的变化,亦不断得到更新,保持着充足的理论张力和活力[3]。阐释和言说“诗言志”命题之所以占据了中国诗学史的大量篇幅,就是因为该命题涵纳着丰富的意义,以至为诗人、诗论家开发意思、攫取意义提供了众多可能性。历代诗论家、诗人持之以恒、绵延不绝地言说、阐释“诗言志”命题无疑具有巨大的诗学价值。就诗学本身来说,它使数千年中国诗学谱就了内在理路从而有迹可循。尽管诗学命题层出不穷、诗学观念花样翻新,但中国诗学万变不离其“宗”,这“宗”就是阐释、言说“诗言志”命题。在比较视野中,它使中国诗学因获得了历史连续性和整体性而成为了世界诗学之林的“这一个”。以阐释、言说“诗言志”贯穿的中国诗学,与其他诗学体系有交集,但没有叠合。“诗言志”命题得以坚劲地挺立,中国诗学得以焕发持久生命力,表明中国诗学对于“诗言志”命题的言说、阐释还有着社会文化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不过必须看到,中国诗学对于“诗言志”命题的言说和阐释,也的确存有这样那样的缺陷和误区。在对待“诗言志”命题时,将“诗言志”拆解为“诗”“言”“志”分别加以界说,便是建构“诗言志”诗学话语的一个显著特征。
“诗言志”的“字面意思:诗以言语表达心愿/心意, 可以译为:poetry express in words the intent of the heart(or mind)[4],所以切割、裂解化阐释“诗言志”命题,是中国诗学的惯习和常态,而将“诗言志”命题裂解为“诗”“言”“志”三个维度后,中国诗学则主要又将言说视线汇集于“志”、将阐述重心置放于“志”。中国诗学着重从四个方面展开“志”的阐释。
首先也是占据主要篇幅的,是对诗所言之志的内涵、意义的厘清。关于中国诗学视域中的“志”之所指,最为笼统的认定,是志即心,心则囊括了思想、情感等各种心理因素,如“蕴藏在心谓之为志”(《诗序》)。较为概括的指认,是志或者即情、或者即思、或者即意、或者即理,如“思虑为志”(《春秋纬·说题辞》)、“志,意也”(《说文》)等。较为具体因而较为狭隘的指认,是志即志向、志意,以及志即记忆、记录等,如“志,记也”(郑玄《注》)等。
其次,是对诗所言之志的性状、特征的澄明。这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第一,志与情、思、理、意的意义关系,这其中又以志与情的意义关系最为突出,诸如“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孔颖达《正义》)等;第二,志与礼、乐的作用、制约关系,“思无邪”(《论语·为政》)、“发乎情,止乎礼义”(《诗大序》)、“君子以钟鼓道志”(《荀子·乐论》)便是这样的阐释。
再次,是对诗所言之志的发生、形成的揭示。这里涉及的主要是志(情)与物(事)、性、心的生发、感应关系。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民生而志,吟歌所含(《文心雕龙·明诗》),便是志(情)源于性、静于心、动(感)于物(事)的代表性论断。
最后,是对诗所言之志的目的、效用的呈现。中国诗学从“上”“下”两方面阐述了志之目标指向,所谓“风化”“美教化”“温柔敦厚”等便是向“下”的方面,如“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毛诗序》)等,而“风刺”“谲谏”等则是向“上”的方面,如“志污其上”(《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诗大序》)等。
人们通过言“志”的诗,也就能在不同程度上认识社会。“志”既然是诗人的思想感情,言志的诗必须具有从思想感情上影响人和对人进行道德规范的力量”[5],诚如郭绍虞所指,将“诗言志”命题的阐述集中于“志”,表明中国古典诗学对于诗歌艺术源于“德教”“政教”“载道”等中国传统文艺价值观,看重的是话语内容,是认识论价值。更进一步,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经世致用、人文化成的入世精神的彰显。然而,内容于诗歌固然重要,但内容毕竟不是诗歌的全部。同时,内容又并非经验视界中的而是诗歌文本中的人类内外生活事实,也就是说,内容是诗歌所特有的文体形式“安放”的内容。因而,诗学话语仅仅注目于“志”的纯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心理学考察,无疑背离了文艺美学(诗学)的本质、要义,只会给诗歌生产造成“非诗学”的阻滞作用。另一方面,将“志”从“诗言志”里分割出来作单一性把握,自然就切断了志与诗、言的内在关联,淡化了志与诗、言的共生互动特点,从而忽视了志的形式化、言语化品质,漠视了志的艺术化、诗意化存在。从“诗言志”里过滤了“诗”“言”单方面阐述、指认“志”,势必导致“诗言志”命题诗学含量的严重降低。
裂解、分割式阐释、指认“诗言志”命题,即将“诗”“言”“志”视为三个独立的意义单元,考察它们各自的意义所指以及它们之间的意义关系。从语法学角度看,就是将“诗”“言”“志”区隔为主语、谓语、宾语语法成分,并界定它们的意义所指,考察它们之间的意义关系。中国“诗言志”诗学的关注点和核心固然在“志”,但也兼及“诗”和“言”。这种兼及,有的是对“诗”或“言”的独立言说,更多的是在“诗”或“言”与“志”的意义关联域即“诗”或“言”于“志”的作用视点下阐释“诗”或“言”。在关联于“志”阐释、言说“诗”或“言”时,侧重发掘并呈现的是诗、言服务、配合“志”的功能、方式、特征等。显然,这是在“志”的引导下的对“诗”或“言”的言说,其起点是“志”,归于的也是“志”。在中国诗学中,诗往往是作为一个有着不言而喻的自明性概念加以运用的,其意义主要在与文、赋等文类的比较中得以显现,而考察点主要在其文体形式、与言相关的音律和文采等。这方面的典型论断如“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陆机《文赋》)、“诗赋欲丽”(曹丕《典论·论文》)、“言之美者为文,文之美者为诗”(司马光《赵朝议文稿序》)等。在这样的阐释体系中,诗是“志之所之”(《诗大序》)、志之所存,是将志展示、陈列其中的框架、器物。而“诗言志”命题中的“言”,用作名词即是审美化、文学化的语言样态,用作动词即作修辞、使用声韵、调整语法以组织成诗的言语行为。根据中国诗学的阐释逻辑,诗的“志”是诗人主体之志的表达、释放,而表达、释放所使用的工具、介质是语言、文字,所谓“言以足志”、“不言,谁知其志”(《左传》)、“情动而言形”(《文心雕龙·体性》)、“在心为志,出口为辞”(《新语·慎微》)。因此,中国“言志”诗学对于“言”的阐释、言说,主要落实于围绕志的传达、释放而采取的语言策略。这就如林岗所言:“将诗句看作能够透析心志的言辞,意味着诗句的言辞只是透析、观察心志的出发点而不是中心点,言辞所要到达的目的地毫无疑问是内在于人心的志。”[6]“言”的阐释、言说主要涉及三点:言的音乐性,如“其为言也而易知,而吟咏之间,抑扬反复,其感人又易入”(朱熹《四书集注》)等;言的修辞性,如“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易·系辞上》)等;言的风格化,如“对人主语言及张疏文字,温柔敦厚尤不可无”(杨时《龟山集》十《语录》)、“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发 ”(黄庭坚《冷斋夜话》)等。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中国“言志”诗学在将“诗言志”切割为“诗”“言”“志”分别加以处理时,志成为了本、体,而诗成为了器,言成为了用。如此一来,“诗”其实只是名义性的存在,它是对作为话语主体的诗歌写作者的置换,“诗言志”其实是“人言志”,这使得关于“诗言志”的阐释失去了与诗的关联;“言”是运用、操作语言文字的行为、动作,由于“诗”不过是“人”的代称,也由于“言”的意图不过是促成“志”的出场,这样“言”也就成为了只与人、志相关而与诗无关或关系不大的言;不管将“志”的意义指认为情、思还是志(志向)、意义,“志”都是心理学意义的而非诗学意义的,即都是人的志、都是言的对象的志,而非诗中的志、诗性的志。撇开了“诗”,“言”就是语言学上的言,“志”就是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文化学上的志,因而,诸如此类“诗言志”命题的阐释都属于语言学和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文化学的阐释,而非诗学的阐释。
二 阐释、言说“诗言志”命题的应然方式
中国诗学将“诗言志”命题拆解为“诗”“言”“志”进行的分割式阐释、认知,是中国诗学语境的产物,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诗学的存在态势和性状特征。这样的阐释客观上展显了积极的诗学价值,如对诗、言、志的各自言说使它们的意义、内涵得以明晰。不过,既然将诗、言、志三者组装、整合在一起成为了“诗言志”诗学命题,对诗、言、志三者的分别阐释、言说固然必不可少,但更需要将它们贯通起来,进行有机阐释。在诗学平台上,“诗言志”命题中的诗、言、志三者之间不是分裂、独立关系,“诗言志”命题也不是诗、言、志三者依主、谓、宾语法关系的简单拼接,赋诗言志,不能仅仅将“诗”看成一个主词,“志”是一个宾词,通过动词“言”去表达、决定、支配宾词”[7]。“诗言志”命题中的诗、言、志三者的意义之间,不仅相互渗透、彼此交融,而且互生共动,这使得“诗言志”具备的是整体内涵。此外,由于有了意义的生成、内涵的扩容,使得“诗言志”命题的整体内涵大于诗、言、志单维意义的总合。整体认知“诗言志”命题,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展开。第一,诗言为志,即诗歌中的言、诗意化的言为诗歌中的志,也就是诗性化的志(诗意)。第二,诗志为言,即志在诗歌中或诗性化的志(意)落实为诗歌中的言、诗性化的言(诗言)。第三,言志为诗、志言为诗,作为一种言语行为,诗性化地言说志、诗意化地指示志的语言操作成就为诗;作为一种表意符号,表征、指代志的诗性化语言、诗意化语言就是诗,诗是对应志(意)的言语形态。以上方面可以简化表述为:诗言→志(意)、诗志→言、言志(志言)→诗。
在根本上,“诗言志”命题属于诗学命题,本位意义是诗学意义,有效性、合法性当来自对诗的诠释和定论。既然是“诗言志”命题的肌体组织,其中的“诗”“言”“志”所具备的诗学意义也是统一于“诗言志”命题的整体诗学意义。对“言”来说,具备的便是超越语言学指意的诗学指意。“言”视为名词,有各种形态,如生活语言、科学语言和文学语言;看作动词,有各种行为方式,典型的如“直言”与“婉言”。就诗学有效性而论,“诗言志”命题的言指的是诗中的言,是作诗所运用的言语方式。言组合成诗,诗由言结构,但并非任何语言“装”入诗的“箩筐”都是诗,诗中的语言也并非等同于诗外的语言。诗中的言是文学语言,是诗言,即诗意化的言。言语方式是文学的方式、诗的方式,也就是“婉言”,即音乐化、修辞化、非语法化的诗意化方式。任何形态的语言都是用以“命名”对象的指意符号,诗言当然也是如此。诗言表示与指代的“意”就是“志”。只是,与日常语言、科学语言与志的关系不同,诗言不是对客观、自然之志的直接指称、明确传达,而是经由音乐化、修辞化、非语法化的诗意化方式发酵、酿就出志。在诗歌文本中,诗言生发出内容,内容就是志,因而诗言即志。诗言与志之间不是表达与被表达的关系,而是等同、一致关系,这样的诗言对应于这样的志。当将音乐化、修辞化、非语法化的语言指认为诗意化、诗性化的诗言,它所酵发、酿造的志就可指认为诗意化、诗性化的志了,这志也就转换为了“意”——“诗意”的意。
“志也者,藏也”(《荀子·解蔽篇》),“志”本义的着重点在“停止”,即将包括情感在内的心理内容“停止”在心里[8],从本源上说,志是“止于心”也就是潜藏于心的心理活动、情思状况,具备的是心理学意义。然而,一旦嵌入“诗言志”命题,志就不是心中之志而是诗里之志了,志具备的也不是心理学意义而是诗学意义了。“志发于言”(许慎《说文》),“言”处于“心”和“诗”“文”的中间,它比“诗”“文”更为先发和根本。“诗”“文”与“心”的关系因此也由“言”与“心”的关系所决定。……“诗”之所以能够“言志”……乃是建基于相信“言”与“心”之间存在着自然的对应关系[9],由于借助语言可以表达志,所以就有了“言志”之说。正如上文所说,诗歌之言并不是直接指称、明确传达外在于诗的既有自然之志、经验之志,而是生成、造就诗意之志、诗性之志即诗志。诗志是“诗言”的志,是音乐化、修辞化、非语法化的诗歌语言生成、酿就的诗性化的志,自然之志于诗志具有的只是发生学意义。这样,诗学层面上,志就不是“止于心”而是“驻于诗”了,而在诗歌之中,正是诗言化约了诗志。诗志并非以诗言为表现载体,诗志本身就是诗言的表征,说到底,诗志就是诗言。在诗歌之中,这样的诗志召唤着这样的诗言,这样的诗言应答着这样的诗志,二者合而为一、相形相生。“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万章上》),正如孟子所指,诗中之志是说诗者(读者)以“意”“逆”得的产物,诗中之志即诗志如果没有读者领会就等于不存在。在诗歌之中,诗志不是依附于诗言,而是以诗言的形式存在并成为了意(诗意),因而读者无法经由诗言告知、传达而被动地获得诗志(诗意)。诗志即诗言,面对诗歌时读者只能通过对诗言的咀嚼品味到诗志、诗意。
诚然,诗是一种有着自身文体样式、形式结构的文学门类,然而,诗毕竟不是定于一尊的空框,写诗的过程不是对业已成型的“诗”体的简单填充。也就是说,不是只有那“一首”诗而是有着这“一首一首”诗。任何一首诗的具体性都取决于其“言”的具体性:且不说外在形式、文体是言组织、拼接而成,诗的内在意涵更要由言生成。在“诗言志”命题的理论视野中,成诗的言语行为反映为使用语言处理志的活动,诗之语言乃指征志的语言;而对“诗言志”作统一、整体性的阐释、言说,就是言志为诗、志言为诗。“言志为诗”是从行动上说的,指的是诗的行动就是言语的行动,而这一行动的表现就是使志出场、亮相;“言志为诗”也表明,只有言语的运作所造就(而非仅仅是表现、传达)的是志,才是诗的运作,至于什么也生成不了、造就不出的纯粹语言游戏、文字积木的言语行为,更是与诗的运作差之千里。正如上文所论,诗、言本为一体,诗言生成、造就的是诗志,也就是诗意。因此,言志为诗便相当于“言意为诗”。“志言为诗”是从性状上说的。如果前面“诗言为志”中的“诗言”(诗即言,言即诗)说的是诗歌语言的存在、形式性状的话,如音乐化、修辞化、非语法化等,那么“志言为诗”中的“志言”,说的是诗歌语言的意义、内容性状。在对“诗言志”命题作整体性阐释时,诗、言、志具有同一性、通约性。言等于诗、等于志表明,诗之言除了音乐性、修辞性、非语法性等形式特征外,还具备内容上即意义、内涵上的规约性,那就是对志的标识、指代。语言一经表征志而成为志言,就升华为了诗言、升华为了诗。反过来说,诗、诗言的意义指向必然是志,必然是志的标识、指代;就算表面上是事(物)、理、景等,深层次也要统摄于志因而只能是志。当然,这里的志是在对“诗言志”作整体性、统一性阐释、言说诗学背景下的志,因而等同于情、意等诗学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