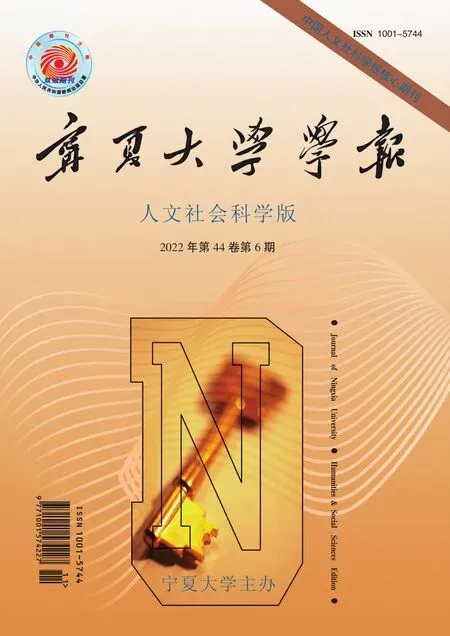《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研究
2022-03-23贾海燕
贾海燕,林 敏
(宁夏大学文学院,宁夏银川 750021)
张贤亮的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是中国新时期文学轰动一时、引起广泛争鸣的作品,小说在1985 年发表后被多次转载,单行本印行后频频再版,被翻译成英语、法语、德语、日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等多种语言。《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英译本由艾梅霞(Martha Avery)翻译,于 1988 年首次出版。英译本一经问世便引起出版界与评论界的关注,《卫报》(The Guardian)、《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出 版 家 周 刊 》(Publishers Weekly)、《 柯 库 斯 评 论 》(Kirkus Reviews)等均发表书评介绍。在报刊书评评介之外,《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也迅速进入英语世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的视野,金介甫(Jeffrey C.Kinkley)、魏玛莎 (Marsha L.Wagner)、佛克马(Douwe W.Fokkema)等学者对小说展开了深入解读。英语世界如何评介、诠释这部中国当代文学经典?本文梳理了《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英译本的出版情况,基于英文报刊书评考察该小说在英语世界的反响,对海外学者的研究视角与观点进行分析,以此勾勒出该小说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研究的全貌。
一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英译本的出版与评介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英译本曾先后在英国、美国、加拿大多地出版。1988 年,维京出版社(Viking)在伦敦首次推出艾梅霞的译本;美国诺顿公司(W.W.Norton & Company)与加拿大丹尼斯兄弟出版社(Lester & Orpen Dennys)也分别在纽约与多伦多出版了这一译本,其中,诺顿公司的译本分为精装与平装两种。1989 年,企鹅出版集团(Penguin books)再版维京出版社的版本。1991 年,美国巴兰坦出版社(Ballantine Books)又将诺顿公司的版本再版。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并不是张贤亮第一部译为英文的小说,早在1982 年,《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第6 期就刊载了《灵与肉》的英文译文。之后,《肖尔布拉克》与《绿化树》也经《中国文学》的译介走出国门。但这几篇小说并未在英语世界引起广泛关注,真正为张贤亮带来国际声誉、使其步入世界文学之林的是《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该小说英译本出版后,英国、美国、加拿大及澳大利亚的一些主流报刊都曾发表书评推介。这些评论向西方读者传递了小说的基本信息,诸如作者张贤亮的经历、小说的自传性质、在中国的畅销与争议、性与政治主题等,其中,性的主题与争议备受关注。1988 年9 月4 日的《洛杉矶时报》(The Los Angeles Times) 发表卡洛琳·威克曼(Carolyn Wakeman)的书评,指出张贤亮对性的公开探索在中国读者中引起了矛盾反应,有读者认为这部小说过于直露,也有读者赞赏作者突破文学主题界限的勇气以及作品的艺术性[1]。加拿大《凤凰星报》(Star-Phoenix)告诉读者,《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在中国是一部轰动一时、引起争议的作品,小说的先锋性就在于它公开讨论了性[2]。澳大利亚《悉尼晨锋报》(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称《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考察了身体与心灵的阉割的主题。这就是为什么它于1985 年在中国出版时引起了如此大的轰动”[3]。美国汉学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曾谈到,美国读者一般喜欢三种中国小说,“一种是sex(性爱)多一点的,第二种是politics(政治)多一点的,还有一种是侦探小说”[4]。评论家厄普代克(John Updike)在论及《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时也说,“西方读者最容易被小说中对婚姻的描述以及对两性之间典型关系的可悲,甚至是悲剧性过程的勾勒所打动”[5]。《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主题与争议性似乎非常符合西方读者对中国当代小说的阅读期待。
在英语世界报刊的评介中,张贤亮与昆德拉、索尔仁尼琴等西方作家相提并论,获得了高度评价。《柯库斯评论》称赞《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用残酷而荒诞的心理之光传达出主人公的精神痛苦,指出小说“超越了近来中国小说的一些地域界限。张贤亮成功地加入昆德拉、奥威尔等人的行列”[6]。汉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在发表于《纽约书评》的评论中称《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是一个悲剧性的爱情故事,“作者张贤亮被称为中国的昆德拉,他的自传体小说一定会被全世界阅读”[7]。加拿大《卡尔加里先驱报》(The Calgary Herald)的评论认为,“《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在范围、表达和启示方面可与索尔仁尼琴的划时代作品《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相媲美”[8]。《蒙特利尔公报》(The Montreal Gazette)发表书评称“《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是中国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东方版的《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9]。
英语世界报刊的评论还肯定了《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社会价值,论者把这部小说作为理解中国社会的一个窗口。美国《堪萨斯市星报》(The Kansas City Star)论及,“虽然它不是一部学术著作,但《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让西方读者真正感受到了那个动荡的时代的生活”[10]。其实,帮助他者理解中国也是作者与译者的初衷。张贤亮曾为《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英译本写过一段前言:“中国是一个神秘的国家。她不但在外国人眼里难以理解,在中国人心目中也是一个谜。正因为她是一个谜,所以她才可爱。这本书向读者透露了一点谜语。请读者去猜测她。”[11]艾梅霞在小说的“译者序”中解释:“任何翻译都无法公正地体现出表达的微妙性和使这个故事在原文中如此生动的俚语。作者和译者希望,即使在这种形式下,这部作品也将帮助非中国读者理解当代中国。”[12]小说的艺术性与译笔同样得到了赞扬。英国诗人恩赖特(D.J.Enright)在发表于《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的书评中称赞《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是“一部堪称典范的作品”[13]。作家简·达利(Jan Dalley)评价《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是“发人深省的、人性化的和有趣的”[14]。捷克作家约瑟夫·史克沃莱茨基(Josef Skvorecky)称小说“令人感动,具有悲剧性和美感”[15]。英国作家希拉里·贝利(Hilary Bailey)肯定了《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价值与译者的译文,她说:“书中对风景的描述和鲜明的个人形象、笑话、对话……这一切构成了一个出色的、平衡的整体。译者对此做了最充分的呈现。”[16]加拿大学者包如廉(Julian F.Pas)评价艾梅霞的译本流畅、优雅,忠于原文[17]。《出版家周刊》也称赞道:“张贤亮敏锐的分析、闲适的抒情,以及用象征性的梦境表达的丰富的诗歌想象力,通过艾梅霞流畅的翻译毫不费力地展现在我们面前。”[18]《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英文书评的作者主要是编辑、作家或书评人,其对中国文学、语言的了解有限,对译本的评价也不乏言过其实、有失公允之处。荷兰汉学家高柏(Koos Kuiper)曾指出,艾梅霞的译本受到不了解情况的英国评论者的欢迎,但译本有很多错误和误解,削弱了小说的政治意义[19];葛浩文也指出译者有明显的错误[20]。
二 英语世界研究者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研究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英译本出版后很快进入英语世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的视野。荷兰学者司马翎(Rint Sybesma)在《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国评论者的声音》一文中介绍了韦君宜等人对小说的评价[21]。金介甫、魏玛莎、钟雪萍、吴燕娜等学者从作品主题、人物形象、性别关系等角度对小说进行了深入解读。整体而言,英语世界学者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研究从两个层面展开:一是分析小说中的性别关系;二是解读小说中主人公章永璘的精神创伤与心路历程。
一些研究者从女性主义视角阐释《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主题,魏玛莎、玛格丽特·德克尔(Margaret H.Decker)、钟雪萍、方津才等人都论及小说折射出的女性从属、被压迫的处境。魏玛莎认为,《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这个题目暗示了男性的优越性,作品将女性作为客体的非人化修辞使“女人”成为缩小、虚化、窒息的“男人的一半”,这种性别修辞削弱了小说的悲剧性力量[22]。玛格丽特·德克尔在《政治评价与中国当代小说的再评价》一文中提出,张贤亮将他对性别和男性性行为的关注转化为一个广泛的政治寓言,小说忽略了性别问题[23]。方津才也指出,《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掩盖了潜在的女性压迫主题。他论及《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有许多二分法,包括文化与自然、精神与肉体、身体与灵魂、人性的与野蛮的、受过教育的与未开化的、社会与家庭、男人与女人等,“每一对二分法中的前一个词表示优越性,而后者则表示低劣性。这些二分法中的分界线被清楚地划定。在每一对中,女性无一例外地被认为是低等的”[24]。钟雪萍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的欲望表达、性与政治的隐喻进行了批判性解读。她在《男性的痛苦与欲望: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阅读政治》一文中指出,多数批评家对这部小说的讨论都集中在性的问题上,往往将性与政治含义联系起来,并未质疑小说中对主人公章永璘的性欲表现,而只把欲望理解为人类自然的原始力量,没有考察欲望如何被建构与表述。在她看来,“这种解读不屑于,或者说根本无法去质疑欲望的本质,去追问这是谁的欲望,去审视在欲望的表现中女性是如何被变成对象、变成欲望被结构化的‘场所’或‘空间’的”[25]。关于性别与政治的隐喻关系,她批评了剥离性别的政治解读的误区,认为性别就是政治,而政治总是已经被性别化了。当张贤亮围绕性欲问题展现被扭曲的人性时,他表现欲望的方式是性别化的,并与父权制的权力关系相联系[26]。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章永璘是父权关系的主体,而黄香久只是恢复男性尊严的“工具”。钟雪萍的质疑揭示了女性作为欲望表达场域的客体位置,而男性则处于主体地位,“女人的形象在文本中不仅主要是作为代表男性欲望的一个方面而存在,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女人成了流血伤口的承受者”[27]。
魏玛莎、钟雪萍等人的批判性思考揭示了《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表达/被表达、主体/客体的男女性别权力关系;乐刚与吴燕娜则从救赎/被救赎的维度作出了另一种观察。二者都论及张贤亮小说中的女性是一个理想化的母亲形象。乐刚称《绿化树》中的马缨花是一个“喂食的母亲形象”,“她被固定为一个救赎的人物,其唯一的功能是培育章永璘的身体和拯救他的灵魂”[28]。吴燕娜指出,男主人公通过女性救赎自己的身体与精神是张贤亮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主题[29],马缨花、黄香久在小说中扮演着美丽的哺育者和救赎者的角色,章永璘则是被救赎者。救赎与被救赎在表面看来似乎反转了小说中的性别权力关系,但如吴燕娜所论,这样的女性角色仍然是理想化的男性建构[30]。
精神分析理论是英语世界研究者阐释张贤亮小说与创作的另一把钥匙。谭国根在《张贤亮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的性与权力》中指出,小说表面上对道德困境等问题的描述是伪现实主义的[31]。他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解读主人公章永璘的心理,认为“《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应该被看作一个揭开‘外皮’,找到主人公心中的‘内核’的过程”[32]。小说表现的是主人公的精神之旅,章永璘通过性完成自我身份的找寻。小说中,章永璘的身份寻求可以概括为“丧失—重生”两个阶段,其与黄香久的结合意味着身份的丧失,这种丧失通过性无能表达出来;用身体堵住大渠决口的英雄行为使其重获性能力,得到了重生。在谭国根看来,小说中的章永璘处于“父—母—子”关系的权力结构中,曹学义代表父权,黄香久代表母权,这两种力量压迫、阻挠着他对新生和自我的追求,与黄香久的分离意味着章永璘最终的精神解放。吴燕娜运用弗洛伊德的创伤理论分析张贤亮的《土牢情话》《绿化树》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三部小说,借用“伤口”的隐喻探讨男主人公的心理创伤。她认为,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中,张贤亮充分揭示了男主人公在身体创伤之外所承受的心理痛苦[33]。金介甫则借用心理学家布鲁诺·贝特尔海姆的术语,将张贤亮及其小说中的主人公称为“极端情况”的幸存者,他分析了章永璘作为幸存者的形象与心理,同时指出,张贤亮通过小说解决自己所受的精神伤害[34]。由于《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自传性质,英语世界论者在用精神分析解读小说时往往将其视为张贤亮的经历与意识的投射。刘自荃的博士论文《张贤亮自我虚构中的压抑之旅》从心路历程角度探讨张贤亮的小说,指出“张贤亮的小说旅程经历了五个阶段:改革、回忆、爱情、性和死亡”[35]。其论述的出发点是张贤亮的虚构作品乃是作家本人的愿望实现,因为“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虚构的语言实际上是被压抑的愿望的象征性实现”[36]。刘自荃认为,“讲故事对张贤亮来说是一种对历史和文化创伤的心理反抗。在语言的伪装下,他幻想了一种虚构的反抗”[37]。
三 “批评”的批评:英语世界研究者的理论自觉与隔膜
从上文分析可见,英语世界研究者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解读具有鲜明的理论色彩。《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发表后曾在中国文坛与评论界引起广泛争议,1985—1989 年,《文汇报》《文艺报》《小说评论》《文艺争鸣》《当代作家评论》《读书》《当代文坛》等报纸、刊物发表了多篇评论。中文评论界争论的焦点之一就是小说中的性别关系,如黄子平曾批评小说对女性的漠视,称“女人不是首先被看成一个平等的‘人’,而是首先被看成一个异性”[38]。这一论断精辟地指出小说中女性遭遇的文化偏见与所处的历史困境。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结尾处,章永璘与黄香久离婚,这一情节引发了对于男主人公“道德感”的争议,《章永璘是个伪君子》[39]、《政治上的志士 道德上的小人》[40]等文章观点鲜明地作出了道德评价并进行批判。对于章永璘的选择,西方学者更多的是从个人自主性角度来理解,如佛克马就认为《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核心是章永璘追求保持个人自主性的问题,性只是主人公寻求自主性的一部分,情欲的满足意味着另一种禁锢,最终,为了精神自由,他牺牲了婚姻生活[41]。谭国根曾指出,中国评论界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批评是一种道德主义的批评,这些批评谴责主人公不道德,但并没有指出主人公作出这种决定的心理条件和政治影响,对小说进行精神分析解读比道德解读更具启发性[42]。在他看来,理论介入超越陈旧的批评范式,可以带来更深入的理解。钟雪萍等人对小说中两性间权力关系的挖掘,以及金介甫、吴燕娜等人对“精神创伤”的分析都是运用西方理论诠释的结果。
西方论者的理论自觉意识与20 世纪90 年代英语学界中国文学研究的发展息息相关。金介甫总结中国当代文学在北美的批评状况时曾指出,批评界运用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理论研究中国新时期文学。他提及东亚研究在美国被边缘化,跨学科与跨文化方法普遍衰微,“中国研究,也像其他研究领域一样,偶尔遇到的挑战,就是需要借取理论本身的思想能量——这种能量主要在哲学领域——将之运用于文学而又不使其变成衍生物或业余爱好,或者以修辞掩盖实质内容”[43]。运用西方理论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似乎是对抗边缘化的一种策略选择。王德威曾指出,20 世纪90 年代的西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出现了巨大的变化,第一个方面就是“‘理论热’成为治学的一大标记。20 世纪70 年代以来,各种文学批评方法在欧美学院人文领域轮番登场,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年轻学者也群起效尤。对理论的关注当然说明学者磨练批评工具,以便更深入地探讨学术问题的用心——因此产生的史观和诠释也的确令人耳目一新”[44]。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理论热”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同样存在。在英语世界《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批评文本中,对弗洛伊德、福柯的援引,以及性别建构、权力关系、心理创伤、被压抑的欲望等批评话语都显示了研究者充分的理论自觉与对理论话语的熟稔。理论的运用拓展了文本诠释的空间,但同时也会带来过度诠释的危险。当英语世界的研究者用精神分析理论来解读《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时,往往从小说投射到作者本人,作家的经历与小说的自传性质又强化了这种投射,在先入为主的理论预设下,张贤亮通过小说缓解自己所受的精神伤害,以语言的虚构来对抗现实。这样的诠释固然可以自圆其说,但却简化了作者与作品之间的复杂关系,理论阐发同时造成理论与作品的隔膜。
王德威曾犀利地批判海外中国文学研究者对西方理论的“拿来主义”与“人云亦云”,他说:“我以为尽管90 年代以来西方中国现代文学界众声喧哗,挟洋以自重者多,独有见地者少。”[45]这样的批评虽过于严苛,但不无警醒。西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同样存在“理论转嫁”的弊病,考察英语世界学者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研究可以发现,很少有论者关心小说产生的中国语境,也鲜有论者援引作家本人的论述,小说成为一个被割裂的文本,被不断解释与阐发。毋庸置疑,性别研究、精神分析等理论的运用的确为理解《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提供了更多元的视角,但这种诠释在某种程度上固化了对小说的理解。批评者窥探作家的潜意识,将权力作为解读文本的利器,丰富的人性、生动的叙述被平面化了。可以说,英语世界学者的理论阐发虽然拓展了小说的文本阐释空间,但却忽视了小说的历史维度,遮蔽了张贤亮创作的文学经验及其在中国新时期文学脉络中的价值。
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译介传播是近年来的热点研究话题,相关理论探讨、策略分析非常活跃,产生了“走出去”“走进去”“走下去”和“走回来”等多种提法,但是学界对具体作家作品海外译介的研究多集中于莫言、余华等作家以及《狼图腾》《解密》等获得商业成功的作品,对海外学者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观点与成果却缺乏深入的研究。笔者认为,作家作品的海外译介传播个案研究是探讨当代文学“走出去”的基础,一方面,深入的个案梳理将厘清当代文学海外译介传播的史实,为当下文学“走出去”提供镜鉴;另一方面,总结海外汉学界的研究观点有助于打破单一视野,形成跨文化对话。
杜博妮(Bonnie S.McDougall)与雷金庆(Kam Louie)曾评价张贤亮小说是“少数在国外赢得批评关注和商业成功的作品”[46]。从《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在英语世界的译介来看,作品的话题性与质量是吸引关注的前提,西方读者的文学观念及其对中国当代文学的阅读期待也是影响作品接受的关键因素。中国文学的海外译介传播是一个跨文化领域,译介传播与诠释、接受是文学向外传播的两个阶段。从英语世界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诠释来看,研究者的“洞见”同时伴随着“不见”,只有客观地评价域外学者的观点,在跨文化的双重视野中观照当代文学,才能寻求中国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