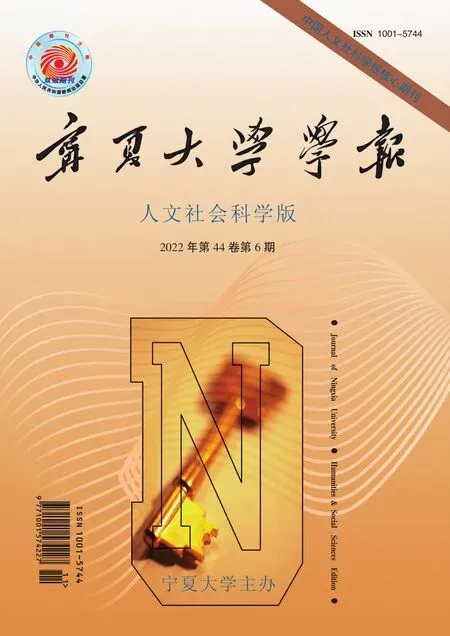革故鼎新:五四新文化与古典小说研究新格局的确立
2022-03-23王瑜锦
王瑜锦
(南通大学文学院,江苏南通 226019)
五四新文化思潮与中国学术的现代化转型有着密切的联系,站在学术史的角度来看,这场轰轰烈烈的知识革命对此后中国学术的现代化进程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从古代小说的发展历程来看,20世纪初,梁启超所倡导的“小说界革命”只是偏重于小说在政治上的功用,并未对小说概念和理论进行全方位的改造和阐释。直至新文化运动时期,小说观念才逐渐成熟,并最终完成了由“旧”到“新”的转变。胡适、陈独秀、钱玄同等人借新思想之势,极力发扬小说的价值,抬高小说的位置,胡适也投入小说的研究中。这种新思潮完全改变了旧有古典小说的研究格局,无论是在小说作品之选定,还是在小说观念之阐释,抑或是具体的研究方法,都与20 世纪以前存在着显著不同。此后,在“新文化”精神的滋养下,小说成为最重要的文体之一,大量学者参与古代小说的研究中,小说史的构建、小说文献的挖掘、小说理论的阐释都取得了重要进展,古典小说由此开启了现代化的新征程。
一 经典作品之厘定:由“四大奇书”到“第一流小说”
中国古代选评作品的传统源远流长,这一选定不只是对优秀作品进行表面上的排列认定和品评鉴赏,其深层次更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文学观念和文学风气。从古代小说的发展历程来看,关于古代小说最有影响力的选评是明清文人选定的“四大奇书”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第一流小说”,而从“四大奇书”向“第一流小说”的转易也说明此间小说观念发生了重要变化。
古人常对经典作品进行选定,这一品评和选定的思想可上溯至魏晋时期。魏晋时期实施“九品中正制”的选官制度,来“平次人才之高下”[1]。这一以品评为主的选官制度影响极为广泛,以致当时的文学艺术领域亦多品评之论,南朝时《诗品》《画品》等作品的出现即为明证。另外,南北朝时期选文的思想业已成熟,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便设有“选文以定篇”部分。其所谓“选文以定篇”便是选出各种文体的代表作品加以评论,而萧统的《文选》可谓真正的“选文”之作,此书选录了先秦至梁代人们公认的经典之作。虽然上述《诗品》以及刘勰、萧统之作均不曾论及小说,但这一选文和品评的思想一直影响着后来者。
明清时期通俗小说的品评与创作是相伴的,这一时期的通俗演义体小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文人亦多品评之论,其中最典型的是,他们将几部代表性的小说作品称为“奇书”,李渔《古本三国志序》云:
昔弇州先生有宇宙四大奇书之目,曰《史记》也,《南华》也,《水浒》与《西厢》也。冯犹龙亦有四大奇书之目,曰《三国》也,《水浒》也,《西游》与《金瓶梅》也。两人之论各异。愚谓书之奇当从其类,《水浒》在小说家,与经史不类,《西厢》系词曲,与小说又不类。今将从其类以配其奇,则冯说为近是[2]。
从李渔此言可得知,“四大奇书之目”最早由王世贞提出,但是王氏所言的“四大奇书”只含有一部小说,而冯梦龙所言之“四大奇书”则全为小说,李渔从文体的角度更赞同冯梦龙的看法。李渔之前的西湖钓叟在《续金瓶梅集序》中将《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三部小说并称“三大奇书”,并加以品鉴,但是这一“三大奇书”概念并未产生多大的影响。而在李渔提出“四大奇书”之后,这一名称则广泛流传,同时,清代文人们的改定和评点更强化了这些“奇书”的经典性。
“四大奇书”只包含了四部明代的章回小说,而清代以来产生的《儒林外史》《红楼梦》等著作并未加入上述选定的行列中。《红楼梦》在嘉庆以来更是备受读者欢迎,有“家家喜闻,处处争购”[3]之盛况,一些文人也对《红楼梦》极加褒奖。赵之谦《章安杂说》称《红楼梦》为“小说家第一品”[4],杨恩寿亦称其为“小说中无上上品”[5],张新之云:“《石头记》脱胎在《西游记》,借径在《金瓶梅》,摄神在《水浒传》。”[6]这些评论都有抬高《红楼梦》位置的趋向,在这一趋势下,新的“小说经典”亟待选定。
晚清时人已开始将明清几大部小说联系起来互相对比而谈其优劣,谢鸿申《东池草堂尺牍》卷一云:“说部优劣可传可宝者,《三国》《水浒演义》《聊斋志异》《红楼梦》四种而已。”[7]谢氏认定的四种小说中,明清各占两部,他将“四大奇书”中的《西游记》《金瓶梅》改换为《聊斋志异》与《红楼梦》。1898 年,梁启超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论及《水浒传》与《红楼梦》,他认为中国的小说创新较少,佳作亦不多,且重复的情况较为严重,“述英雄则规画《水浒》,道男女则步武《红楼》”[8]。梁氏拈出《水浒传》与《红楼梦》,意在指出古典小说的“陈陈相因,涂涂递附”之病,然而梁氏也在无意间承认了章回小说最具代表性的两部作品为《水浒传》和《红楼梦》。后来,曼殊在《小说丛话》中也指出了《水浒传》与《红楼梦》,但他舍弃了梁启超对古典小说的消极评价,其云:“《水浒》《红楼》两书,其在我国小说界中,位置当在第一级。”[9]这一以《红楼梦》和《水浒传》为章回小说代表的观点在当时颇有影响。稍后,卧虎浪士在《女娲石叙》一书中有海天独啸子之语,也持此观点,其云:“我国小说,汗牛充栋,而其尤者,莫如《水浒传》《红楼梦》二书。”[10]除这一“二选”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之外,时人还有提及“三选”者,1908 年,王钟麒《中国三大小说家论赞》曰:“是以天僇生生平虽好读书,然不若读小说。读小说数十百种,有好有不好,其好而能至者,厥唯施耐庵、王弇州、曹雪芹三氏所著之小说。”[11]王氏以《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为三大小说。1916 年,《余兴》第十九期刊载的丛笑的《策问》中则提出了四部小说,其言:“问中国小说,除《三国》《聊斋》《水浒》《红楼梦》外佳构绝少,至译述欧美小说,为时不过二十余年,究竟第一次译述外国小说起自何人?发现于何时?是何名目?”[12]他认为的小说佳构是《三国演义》《聊斋志异》《水浒传》《红楼梦》四部,这一看法与上述谢鸿申的看法相同。要之,新文化运动前,清末民初的文人已开始对他们心中的“经典”作出选定,“二选”“三选”与“四选”的观点为之后的胡适、钱玄同等人对“第一流小说”的选定起到了良好的指引作用。
五四时期,胡适等人明确提出“第一流小说”,并对其作出选定。1917 年,钱玄同在给陈独秀的回信中对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进行评论时说:“小说之有价值者,不过施耐庵之《水浒》、曹雪芹之《红楼梦》、吴敬梓之《儒林外史》三书耳。今世小说,唯李伯元之《官场现形记》、吴趼人之《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曾孟朴之《孽海花》三书为有价值。”[13]稍后,胡适给予回应,胡适首先指出了钱氏对《西游记》和《三国演义》的评价有失公允,他认为《西游记》和《三国演义》均为非常出色之小说。而对钱玄同认定的六部最有价值的小说,胡适认为,钱玄同这一选定只重视内容方面,忽略了对作品结构的把握,站在这一角度,胡适认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在同类书中为最上物,而“《孽海花》可居第二流”。最后胡适给出了自己认为是“第一流小说”的名单,其曰:“故鄙意以为吾国第一流小说,古唯《水浒》《西游》《儒林外史》《红楼梦》四部,今人唯李伯元、吴趼人两家,其他皆第二流以下耳”[14]。由此可以看出,胡适认为的“第一流小说”为四部,加之上述对《三国演义》的评价,实际上是五部。而关于《金瓶梅》一书,胡适的观点与钱玄同、陈独秀有所不同,钱玄同和陈独秀给予《金瓶梅》很高的评价。1917 年6 月,陈独秀致信胡适,认为《金瓶梅》“描写恶社会,真如禹鼎铸奸,无微不至”[15]。钱玄同也认为,从文学的眼光来看,“则《金瓶梅》之位置固亦在第一流也”[16]。胡适却持相反的观点,他认为在当时的社会里《金瓶梅》应该被大力排斥,这类小说有破坏社会风气之嫌,并且应该大量翻译一些高尚的言情之作以移风易俗,很明显,胡适不选《金瓶梅》的着眼点在“转移风气”上。综上,胡适给出了他所认为的最有价值的“第一流小说”名单:《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另外,他对《三国演义》也给予较高的评价,实际上,胡适认为好的小说有五部。
由于胡适在当时文化界所处的地位,这一评价影响深远。1923 年,胡适在《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一文中又列入多达13 种章回小说,上述五部古典小说都赫然在列,而胡适所推荐的版本正是亚东图书馆出版,并由他和陈独秀、钱玄同作序的“新式标点本”。这些小说由于胡适等人的推荐,更是一版再版。胡适等人的观点对20 世纪20 年代以来的小说史和文学史著作的影响清晰可见,身处新文化运动中的鲁迅在这之后出版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小说史略》一书。鲁迅主要论述了七大部小说,除了胡适所言的五种,他还纳入陈独秀和钱玄同所认为较好的《金瓶梅》,又加入了《聊斋志异》,对其他“第二流”著作进行了分类归纳,鲁迅从“史”的角度为“第一流小说”定论。此后,明清的七大部小说成为文学史中的“经典”,也成为一般文人心中的“经典”。
二 研究方法之转换:由零碎感发到科学论证
古人研究小说之论述常以个人感发的形式呈现出来,这一形式虽然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独特的妙悟精神和著述体例,但以今日之眼光看古人的研究方法,无疑显得较为零碎。五四时期,胡适等人挟科学方法以考证小说,这一研究方法在此后逐渐成为一种“典范”式路径。这一所谓“科学的方法”是在新文化运动中形成的,此种对史料进行归纳论述的写作逻辑经历了胡适等人的提倡和实验之后而大兴。
在小说研究中,这一古今研究方法的转换十分明显,古人对小说的讨论多集中在以下几类材料中[17]:小说内容;小说的序跋;小说评点;学术性笔记著述中关于小说的部分;目录学著述;史论;诗文。以上分类基本涵盖了古代的小说学论述,与今日的小说研究相对比,这些论述以个人感发为主,在书写上呈现出琐碎的特征,以下试举例言之。
小说的序跋为古代小说理论史料的大宗,丁锡根先生编著的《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一书收录了大量的小说序跋,就古人小说序跋的内容来看,无论是自序,还是他序,除了介绍生平和小说内容之外,对小说的评判大多数深受古代“小道可观”观念的影响。在这一观念的影响下,大多评论者认为小说皆为“资治体,助名教,供谈笑,广见闻”之作;另外,受制于序跋的体例,其中多客套之语,对小说的评论并未深入。小说评点起源于刘辰翁的《世说新语评》,明代通俗小说评点开始繁盛,容与堂本《水浒传》是较早的评点本,清代金圣叹、毛氏父子等人为评点名家,其评点作品更是风行一时,甚有盖过原作之势。纵观诸家之评点,有眉批,有旁批,也有回末总评,并无一整齐划一之形态规定[18],这一形式决定了评点多是短小的、感发式的,并不能对小说艺术进行系统之论述。学术性笔记往往以条目的方式呈现,这类著述往往随笔记之,其中较为系统性的著作以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为代表,其《九流绪论》上、下篇均有对于小说之论述。目录学著作分为官方目录与私家目录,前者以史志目录为主发端于汉,后者兴于宋,对小说的评论常集中于小说家序中,多是简短地阐述小说之定义、范围、分类、价值等。史论著作论及小说者以《史通》《文史通义》为代表。诗文中也有对小说的评论,如刘克庄《后村集》卷四十三《释老六言十首》其三:“道家事颇恍惚,稗官书多诙谐。帝居非若溷也,天上岂有厕哉”[19],指出了小说诙谐的特点。从上述各类论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在传统著述体例和学术文化的影响下,当时有关小说的论述无疑呈现出琐碎化、断片化的特点。
传统小说研究的这一特征在晚清得到了部分改变,晚清以降,西方印刷技术的引入大大降低了书写成本,一批报刊应运而生,这些物质技术的更新和改善为长篇评论文章的出现提供了可能。作为开风气之先的代表性人物,梁启超较早采用“新文体”来评论小说,这种新式文体将古文、俚语、外国语等各种文章之特色融为一体,其突出特征便是“精练和平易畅达”。梁氏所发明的这一文体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其著名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便运用了这种新文体。从形式上来看,此文完全摆脱了传统序跋体和笔记体的限制,将小说与政治联系起来,深入论述了小说的价值、社会功用与艺术特点等。此文是维新派关于小说理论的纲领性文章,标志着小说理论由古代迈向近代。除梁启超之外,1904 年,王国维也撰写了长文《〈红楼梦〉评论》,此文运用西方哲学与美学知识来揭示《红楼梦》的独特价值,不仅在内容和思想上呈现出现代性的一面,在形式上也呈现出现代性,全文分为五部分,逻辑清晰、层次分明,纵观王氏文章的架构和写作方式,几乎与今日所言论文相同,其开创之功不可谓不大。后来,天僇生《中国历代小说史论》(1907 年)、管达如《说小说》(1912 年)等文承继了梁启超、王国维二人的这一论述体式。但此时的小说评论仍有不少序跋评点之论,传统的小说论述方式直到五四时期才得以彻底改观。
一方面,传统小说研究的现代化转型与上述著述体式的转变有关,另一方面则与科学研究方法的流行密切相关。晚清“西学东渐”之际,西方“科学”观念的传入带来了归纳与演绎的方法,1896 年,严复在《译〈天演论〉自序》中将归纳和演绎概括为“内籀之术”和“外籀之术”[20]。严氏所谓的“内籀之术”指归纳法,“外籀之术”指演绎。19 世纪末,内忧外患的窘迫局面使国人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自然科学领域,力图挽国运于危亡中,因此,严氏所言的“内籀”与“外籀”并未在人文思想领域广泛运用。至新文化运动,“赛先生”被当成一面旗帜树立起来,科学的思想和方法几乎影响所有领域。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对“科学”的定义可以看作新文化运动时期人们对于“科学”的一般看法,其云:“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21]而后,胡适更是极力推崇科学方法,胡适的科学方法来自杜威的“实验主义”,在《实验主义》一文中,他将杜威的思想总结为五步,又在《杜威先生与中国》一文中将其奉行为科学的实验主义总结了三点。在提倡科学的实验主义过程中,胡适将这一科学的方法和清代乾嘉之际的“朴学”相联系,为中国传统学术中的这一科学方法找到了合理的依据。在《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一文中,胡适多次运用科学方法来评价清人的考证,在该文第四部分,他认为汉学家的治学法是“归纳和演绎同时并用的科学方法”[22],在该文第六部分,他认为王氏父子的治学法“完全是归纳的方法”[23]。最后,胡适用两点来总结清人的治学方法:“(1)大胆的假设,(2)小心的求证。假设不大胆,不能有新发明。证据不充足,不能使人信仰。”[24]至此,胡适将西方这一以实验主义为主的科学方法与清代“朴学”建立了完整的联系,为其在中国的运用找到了合理的内核。
胡适也将此科学方法运用到小说研究中,他的小说考证方法和关于材料的处理方式成为20 世纪小说研究的典范。胡适的这一科学考证小说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亚东图书馆出版的古典小说的18 篇序跋中,在这些序跋中,胡适充分运用归纳、推理来进行“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一方法见诸其对古典小说作者的考证、版本的梳理、故事流变的梳理等多个方面,以下试举两例。他在考述《醒世姻缘传》的作者西周生为蒲松龄时,先提出假设,而后从《聊斋志异》与《醒世姻缘传》中寻找“内证”,然后又搜求其他外部证据,如《骨董琐记》所载之内容,接下来又证实古文作者是可以创作白话文作品的,用《聊斋志异》的白话曲词推定《醒世姻缘传》的作者为蒲松龄。胡适这样一步一步、环环相扣,从提出假设到解决问题,皆由归纳史料而得出。关于故事流变,以他为《水浒传》作出的“历史的考据”最为典型,他首先提出《水浒传》是南宋初年至明朝中叶这四百年的“梁山泊故事”的结晶[25],然后依次罗列宋代、元代及明前期的史料,一一归纳推理后得出上述结论。上述所言几个层面在胡适的考证中并非截然分开的,而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他在考证作者时常引入版本作为证据,又从故事内容以及作品语言等方面进行综合归纳,这些研究井井有条、娓娓道来,颇使读者信服。
在古典小说研究中,胡适对这一科学实证方法的运用成为后来者争相效仿的对象,当时著名的小说研究者郑振铎、孙楷第等人无一不受胡适的影响,或搜求史料,或考订版本,或考证作者,虽然研究方向不同,但是内在的研究方法并未超越胡适的这种“典范”。随着胡适这一研究典范的确立,传统的小说研究方法彻底完成了转型,走向了“现代”。
三 小说地位之更易:由“小道可观”到“文学正宗”
自《汉书·艺文志》首次著录小说并对小说作出“小道可观”的评价之后,这一价值标签始终伴随着古代小说的发展,无论是笔记小说,还是章回小说,历代文人皆以“小道”观之,这一定义“给小说文体立了一根无可逾越的标尺,规定了小说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基本位置”[26]。由于《汉书·艺文志》在小说学史上的重要位置,这一定义被后人一直作为“金科玉律”而奉行,古代小说的文体形态虽有变化,但这一价值规定一直未曾改变。
《汉书·艺文志》中这一规定的巨大影响一直持续至晚清,虽然梁启超等人掀起的“小说界革命”极力提升小说的地位,视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但梁启超的这一倡导只是部分改变了小说在文学中的边缘位置,并没有完全扭转人们长期以来深植于脑海里的“小道”观念。通过相关文献我们可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在“小说界革命”前的1897 年,邱炜萲在其《菽园赘谈》中云:“诗文虽小道,小说盖小之又小者也。”[27]此乃传统文人千篇一律之论,常视小说为“小道”,且价值地位低于诗文。“小说界革命”之后,视“小说”为“小道”的言论仍较多,吴沃尧的《两晋演义序》、黄人的《小说小话》、新楼的《〈月月小说〉评议》等文章都视小说为“小道”。
至新文化运动,这一视小说为“小道”的观念才被彻底终结。1917 年 1 月 1 日,《新青年》刊载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在此文中胡适倡导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他详细剖析了这八项内容,同时也论及了小说,直称小说为“文学正宗”。其云:“今人犹有鄙夷白话小说为文学小道者,不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皆文学正宗,而骈文律诗乃真小道耳。”[28]胡适在上述论述中直言明清章回体作家及其作品为“文学之正宗”,将其誉为“世界第一流”文学,而将骈文、律诗等传统文人视为正统的文体贬斥为“小道”。事实上,胡适的这一“文学正宗论”观点有着浓厚的进化论色彩。一方面,胡适用进化之观点推出明清小说之文的优越性,他认为每个时代都有属于时代的“文”,而“施耐庵、曹雪芹之文”[29]正是在先秦、两汉、唐宋之文的基础上进化而来的;另一方面,他又用进化之观点大力批驳古文家的复古观念,视这种创作为“文学下乘”[30]。胡适明确认为今日之文学当以小说为正宗,而今日之古文家仍然规仿韩、欧、姚、曾诸家,明显与进化的文学史观相背离。
再者,胡适的这一“文学正宗”论与他的“白话正宗”论紧密相连,事实上,胡适所认为的“真文学”和“活文学”正是白话文学,而最有代表性的文体便是小说,故胡适以白话文学为文学之正宗和以小说为文学之正宗的观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合二为一的。其云:
吾唯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为文学正宗,故有“不避俗字俗语”之论也。盖吾国言文之背驰久矣。……然以今世历史进化的眼光观之,则白话文学之为中国文学之正宗,又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可断言也[31]。
胡适认为“吾国言文之背驰久矣”,而这一现象严重阻碍了文学之发展,因为“文言不足以达意”。元代以降的小说却不同于以往之作品,这些小说用白话,所以是一种“通俗行远之文学”,但这种“活文学”却被扼杀了,胡适将矛头指向以明代“前七子”为代表的一批文章家和他们所倡导的复古思潮,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胡适之后,陈独秀、钱玄同均部分重申了胡适的观点,此三人为新文化运动的标志性人物,他们合力使“小说为文学之正宗”的观点风靡当时,终结了历史上以小说为小道的观念。陈独秀更是大力表彰戏曲与小说,并痛斥正统文学家为“妖魔”,其云:
元明剧本,明清小说,乃近代文学之粲然可观者。惜为妖魔所厄,……此妖魔为何?即明之前后七子及八家文派之归、方、刘、姚是也。此十八妖魔辈尊古蔑今,咬文嚼字,称霸文坛。反使盖代文豪若马东篱,若施耐庵,若曹雪芹诸人之姓名,几不为国人所识[32]。
陈独秀此处以小说和剧本为“近代文学之粲然可观者”,但是因为“十八妖魔辈尊古蔑今”,致使当时的文学“猥琐、陈腐”,很明显,胡适的上述观点得到了陈独秀的认同。而钱玄同虽然对古代很多小说作品持批判之态度,认为其“秽亵”和“肉麻”,但仍然认为小说为“文学之正宗”[33]。
胡适等人的“小说为文学正宗”观点产生了广泛影响,彻底终结了残存的小说为“小道”的观念,小说作为一个代表性文体与诗词共存于之后的文学史中。当小说不再被视为“小道”后,胡适、鲁迅、郑振铎等人均专攻小说研究,或搜集史料,或撰写专著,正如毕树棠所言:“小说向视为小道,刻印的从不讲究,藏书的更不重视,所以很少见于著录。关于研究,向无专书,只在笔记一类书里有些零篇文字,偶尔道及,材料可谓极散漫。自清季译著小说之风盛起,几经演变,小说文字遂入于正统文学之流,而对于旧小说之考证材料,亦渐有人着手搜集。”[34]这种作品的搜集和整理亦改变了长期以来传统四部所限定的古代典籍的学术布局,词曲小说逐渐被重视,由此成为古典文学中之一大部。施蛰存就曾指出:“中国文学,浩如烟海,即传统的所认为文学者,已有四库之富,而又益之以近世文学观念扩张,词曲小说,都已不再被视为小道,于是中国文学典籍益夥矣。”[35]
综上,视小说为“小道”的观念长期存在于古代,晚清的“小说界革命”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看法,其后这一观念仍时有出现,直至胡适等人提倡明清白话小说为“文学之正宗”的观点,小说为“小道”的观念才被彻底终结,此后,这一论述基本未再出现。细观胡适之观点,其背后有着浓厚的进化色彩,这一进化论史观经过20 年的传播已为国人所深信不疑,故而,当胡适倡导小说为“文学之正宗”时,其传播效果可想而知。当这一观念完全转变之后,小说与诗词文赋等文体一起进入文学史,成为文学史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四 余论
本文主要从三个层面论述了五四新文化思潮对古典小说格局的改变,上述三个层面是互相联系的,胡适、钱玄同等人对小说的选定,其背后正是小说观念发生了改变,而科学的考证方法的运用无疑又促使经典小说的选定和小说观念的转变。20 世纪20 年代的这些改变形成了古典小说在今后的格局,经典小说进入小说史和文学史的叙述中,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归纳推理的研究方法更成为现代研究者的“必备技能”,最终,古典小说这一文体列入文学史的书写中,与诗、文、赋等“平起平坐”。
同时,我们也看到新的小说研究格局与文学风气的西化和教育制度的新建有着密切的关系。20世纪以来,文学史这一著述体例逐渐适应了现代教育的分科体制,故而大肆流行,且不论以“文学史”为名的大量著述,就是诗、词、小说、戏曲等分体文学史亦数量甚多。自20 世纪30 年代以来,“论文体”著述备受学者和期刊的青睐,逐渐成为主流的著述方式。新的著述方式固然是学术共同体的不二选择,但却带来了更多的“隔膜”,使我们对古人之著述缺乏必要之同情和理解,过度阐释和曲解十分常见。另外,就小说而言,其经历的古今之变非常明显,20 世纪以来所建构的小说从形式到内核已与古代截然不同。上述所论小说地位与小说研究观念之更迭仅为小说观念之一隅,此外,新的小说术语、小说概念、小说文体观、小说分类观、小说叙事观、小说情节观等都随之确立,逐步成为古代小说主流话语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古今小说的裂痕也越来越大。总之,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古典小说的研究格局产生了极大影响,一方面,这一影响推动着小说史快速、有序的发展;另一方面,五四时期反传统的主张和追求割裂了小说自身的发展脉络,使得今日之小说距离其本来之面貌越来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