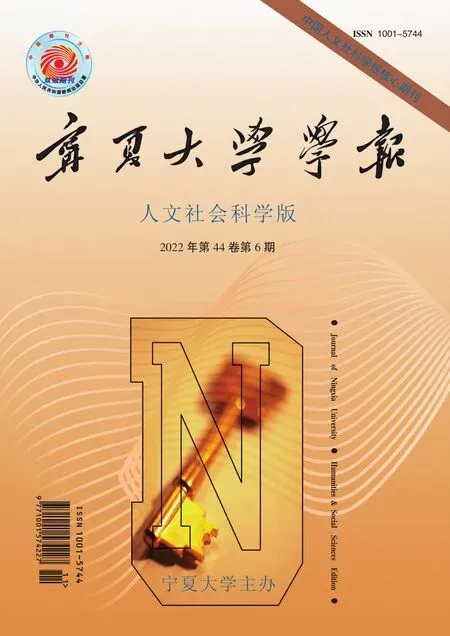论钱锺书对情景关系的再造和省思
2022-03-23万明泊
万明泊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北京 100872)
在中国古典诗学研究领域,情景关系问题一直备受关注,论者纷纭。王国维指出:“文学中有二原质焉,曰景,曰情。”[1]径直将情与景指称为文学的原质。基于此种判断,文学研究中的“情”“景”概念得到进一步的厘定与扩充。“景”不再局限于自然风物,还囊括人事之代谢,物态之万殊,如王夫之评价杜甫“亲朋无一字”一联,认为其“情中有景”[2],此处之“景”便已非寻常理解的风景,而是社会人生的图景。“情”也不是某种幽情单绪,而是被放大到了诸种心情与态度。由此,情景关系问题走向了一个更为深刻的讨论场域,从原先的借景生情、寓情于景等技法表达,迈入到一个更趋理论化的学术探讨。而同时,古人针对情景关系的讨论也累积了深厚的思想资源,如王昌龄将其划分为“物境”“情境”“意境”三种层次,考辨关系,细致入微;王夫之则从易学语法抽绎而出,借乾坤、阴阳的符号演绎情景间的关系,指出“景生情,情生景”,二者“互藏其宅”[3]。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均显示出情景关系问题可供探讨范围之广、内容之繁。
面对这样的一种经典诗学命题,如何跳出既定的思维框架,从诗眼文心处把握二者关系,成为进入该命题的关捩所在。因为前人的评说与研究既是一份资源,同时又易化为思维窠臼,限制论者进一步考求。所以如何从成熟的路径走向理论的生新,是把握该内容的应有之义。而钱锺书在面对这一经典问题时,借助旁搜博采的写作策略,多次论述,于题无剩义处琢磨考索,对情景关系问题给出自己的判断与看法,显示出带有明确脉络的批评主张。比如,在他业已成型的学术著作《谈艺录》《管锥编》中,就对情景关系形成一套鲜明的看法,在《钱锺书手稿集》中也多层次展现他对情景关系的思考,相关意见在阅读批注中时有流露,而这部分尚未有学者发掘。所以本文力图从这些内容入手,尽可能展现钱锺书对情景关系的批评思考,试图还原钱锺书的艺术主张,勾勒出情景关系研究的新角度,展示出一条研究中国古典诗学的新路径。
一 类型厘定:对情景关系的划分
钱锺书作为贯通古今、博采中西的学者,其评诗观念颇多。值得注意的是,钱锺书在评骘诗歌时不光以学者的观念去判断,有时更从一个诗人的立场去体悟。这一观照方式令其倾心“古来雅人深致”[4],更着眼于古人之文心诗眼。易言之,与大多数学者不同,钱锺书的品评更多展示出和诗歌同好作别具会心的把玩,由此来指摘利钝,评论中带有娱己的色彩。在《钱锺书手稿集》中,他截取杜甫诗句并称引相关诗文,由此申发出他对文学的独到领会,展现其对诗歌技法的独特感知,洋洋洒洒,时有新见。
在这些看似繁杂且多样的点评中,有一条批语颇值得注目。那便是钱锺书品读杜甫《遣怀》:“愁眼看霜露,寒城菊自花。”钱锺书抓住其中的一个“自”字,给出了才情丰富的阐发,胪列出多种写作情况,以广博的征引方式去表现“自”字用法的复杂性。并且,他之所以会对这样一个虚字着墨甚多,也是根源于其对情景关系的独到理解。葛兆光指出:“在诗歌里,实词的变化只是意味着人们所接触的世界的变化,而虚词的变化则意味着人们的思维的变化。”[5]由虚字入手,则表明论者跳脱出一般文字趣味上的赏会,迈入到诗作的文本内核,走向对诗人写作思维的深刻洞察。在文中,钱锺书将“自”字视作一个基点,由此出发,辐照万千,将情与景划分成三种关系。这三种关系依次递进,映照出钱锺书的治学眼光与学术特色。
在《钱锺书手稿集》中,钱锺书将第一种定义为“觉其可供览赏,徒资摹写物色之篇”[6],诗人只对面前的风景做机械式的模仿,既缺少情感上的投注,也没有情景融会。钱锺书认为,这在古代写景诗作并不鲜见,易流为俗品。诗作停留在这样的层次,往往会把情与景视作两个互不干涉的范畴,从而难以直抵诗心内核。在这样的诗作中,诗人只对景物负有说明的责任,却丧失了心灵的关怀。《文镜秘府论》指出诗中景物必须要同诗人情意的抒发相结合,“一向言景,亦无味,事须景与意相兼始好”[7]。诗歌写景的宗旨不是为了空言物色,如果缺少意兴寄托,描绘得就算再详尽也难以动人。故推而论之,一首写景诗不应只满足于景物的描绘,更应关注于情景的融会,不为情景虚实间的束缚所拘牵。《筱园诗话》云:“然在大作手,则一以贯之,无情景虚实之可执也。”[8]因为情景看似两个泾渭判然的范畴,实则在诗歌写作中,却难以任意切割,无法仅凭形迹进行划分。所以当诗歌只将摹写物色视作旨归时,其内里也忽视了诗之所以为诗的艺术追求。
第二种是“觉其与人欢戚相通,类有情者”[9],此时景物与情感相勾连,从机械式的刻画升格为情感上的沟通,景物染上了人的色彩,顺应着中国传统的认知方式。在中国传统观念中,万事万物之间存在着某种感应。这种感应,不仅反映在物与物之间,也发生在人与物之间。“……异类相感者。若磁石引针,琥珀拾芥”[10]。宋明理学家进而把“感应”这一现象提高到哲学的高度,认为包括人在内的世间万物均是由“气”等物质元素构成,所以人与其他诸种事物间具备同质异构性。如张载指出:“天地生万物,所受虽不同,皆无须臾之不感。”[11]这种看似神秘的心物感应,也促成诗歌创作的重要动力。“人禀七情,应物斯感”[12],此处的“物”也绝非普遍意义上的物,而是进入到人的视野之中,与人形成审美关系,并产生出某种感知。人与物的这种审美感应,在一定意义上解决了主体与客体间的审美关系问题。因为在这样的话语体系中,天地人间所形成的美,都是由心与物、情与景交互感应所产生的。不光是景触发了情,也是情移置于景。值得注意的是,钱锺书于此标举“欢戚相通”四个字,就表露出他并没有将景视作被动承受的物体,而是指出它存在与情感沟通融会的可能。
从这样的一种理论视角出发,便会更加容易理解钱锺书的诗学主张。《谈艺录》中,钱锺书由李贺诗歌感发,提出“执情强物”与“即物生情”两种概念。所谓“执情强物”是从创作者本身出发,起于对李贺用字特色的体悟。钱锺书注意到李贺作诗,喜欢用“泣”“啼”诸字。观照景物时,专注抒发自身愁苦悲戚之音,近于“连篇累牍”[13]。在描摹风景时,创作者局限在自身强烈情感冲突,执而不化,故常会产生误读,忽略物态万殊,“执情强物”的问题便由此彰显。而“即物生情”为创作主体抛下诸多主观判断,不为功利观念所拘牵,促成物我两忘的艺术效果。由此,创作主体将自我融入进自然世界中,“无容心而即物生情”[14],在天地间优游涵泳,促使主客体间的体认。
研究者论及这两个概念时,总会将其与王国维的说法相混同:“按‘即物生情’与‘执情强物’,即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说的‘无我之境’与‘有我之境’。”[15]但实际上这种评语是对钱锺书的诗学理念作窄化解读,并没有将这个概念理解到位。因为他的“即情生物”说不同于王国维的地方,不只在于其专注创作主体的有无,更在于其展示出物我之间、情景之间的交感过程。在《谈艺录》中他反复论及描摹景物时要“不期有当于吾心”[16],如此方能摆脱僵化的创作思维,与身历目见的景物形成真正的情绪共鸣与心灵感应。恰如前文所论述的那样,关注情景间的沟通兴感,这是钱锺书别具手眼的关怀所在。汪荣祖在考察钱锺书诗歌创作时,对此也深有体会,认为:“心物交感而后情动,激发之情则须牢而笼之,始为己有。”[17]在写作时一方面要注重情景心物间的交互感应,另一方面也不能放任这种情绪,要让自己的理性驾驭住这种情绪,不致空有情感的释放而无文意的统摄。
第三种关系是“觉其自行其是,自便其私,而与人却风马牛”[18]。这第三种关系陈义颇高,对情景关系作出了一种别样的划分。此处的景虽含情,但不跟人心意相通,如杜甫“欣欣物自私”正指此。第三种关系视角独特,他将外在于人的物象景色视作主体,这些山水风月不是被动等人欣赏,而是具备着自我生长的情思。长期以来,诗歌作为审美意识的表现物,经常被认为要在主客体交互感应中才得以产生,需要自我情思与外在景物相结合。刘熙载谓:“在外者物色,在我者生意,二者相摩相荡而赋出焉。若与自家生意无相入处,则物色只成闲事”[19]。即认为物色需要同自身情感意志相融合,才能产生审美感应,否则便是一堆没有价值的陈迹。而钱锺书则将这些看似不能与人产生沟通的物象提炼出来,指出这些景色即便没有与人倏然相遇,也蕴藏着深厚的情感。这样独到的思考方式,摆脱了以人为主体的评判模式,建立了从物出发的分析路数,看出物自有心,景自有情。
以上就是钱锺书对情景关系三种模式的划分。简单来说,钱锺书的划分依据并不是来自精确的统计、烦琐的数据,而是纯粹从自身的阅读积累出发,将情景关系重新定位。而恰恰是这种来源不甚精确的划分,使得其所依托的学理视角愈发凸显。因为一般的研究者谈艺析理,论及情景关系间的诸种差异,总会走到情景交融、寓情于景等寻常路数中去。实际上,这种思维方式还是仅从人的本位出发,忽视了物本身在关系构建中的复杂性与细密性。而在钱锺书划分的三种关系当中,景物所占的比重和意义远超人情,将隐而不显的物作为论述的重要来源,这也是对中国诗学观念的一种厘清。
二 焦点转移:对抒情传统的反思
长久以来,研究者对情景关系的分析,总是聚焦于以人为主体的范畴。比如在论及王夫之“情景交融”的理论时,论者笔墨更着重于创作主体所生发的情,却忽视了物本身所具有的种种姿态与言说,认为:“能否产生诗情,全在于诗人是否能够赏取,‘情’与‘景’是否能够产生诗兴。”[20]物色只需提供赏玩的内容,其余的价值应尽数省略,意义的产生仰赖诗人的兴会所至和内在情感。这样的审美态度,实际上消弭了景物自身所能产生的审美意义。并且,论者往往将其视作一种值得追慕的写作风尚,指出王夫之追寻情景交融的诗学境界,“正好表示船山将生命个体外在的变局与事物,全纳入审美系统内以安顿融合”。景物的价值只是一种承接诗人意兴情思的心理寄托,其本质不过是诗人得以介入现实情境的方式,“抒情诗的保存与确立,作为一个不容‘史为’介入的情境与本我书写,为中国古典文化境遇划出一个精纯的范畴,以安顿己身与时代变局下仍可以安守的一片文化净土。”[21]景物于抒情诗的价值也似乎言尽于此,成了诗人进入世界与展现自我的工具与容器,而其他的价值与意义要么被舍弃,要么被忽视,成为抒情背景下的赘余或附庸。
然而实际意义果真局限于此吗?20 世纪后半叶,陈世骧标举“中国抒情传统”的命题,首次借西方文类中抒情诗这一概念来反观中国文学大传统,依靠新的解释与评价来完成文学传统的跨文化研究。在文学创作上,他指出《诗经》“弥漫着个人弦音”,《楚辞》突出展现出“文学家切身地反映的自我影像”[22],乐府进一步开拓抒情诗的音乐性,而汉赋则凭借引人入胜的词句,拓展了“描写”在中国抒情传统的价值。至此,依据他的划分方式,中国文学主流便行走在这四大类型的道路中,在文学作品中弥漫着抒情的声音。由此陈世骧得出结论,将中国文学的道统总结为“一种抒情的道统”[23]。此后,这一命题经高友工、林顺夫、孙康宜、蔡英俊、吕正惠、王德威等学者拓展建构,渐次形成一套囊括文学史、文艺理论与哲学基础的研究体系。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少古典文学研究者对此“罕有异议”,甚至径直将抒情传统视为“研究工作的前提”[24],成为他们思考文学的方向与旨归。而持有不同意见的研究者,多半也只认为这种提法漠视了中国文学的叙事传统,没有看出叙事对中国文学的建构力量。叙事传统与抒情传统应“共生互补,相扶相益”[25],二者紧密结合,不可切割。或有论者提出伴随该命题的不断拓展,抒情传统演变为“一种生命境界,一种深具感性的风格”[26],致使其在文体适用性上过度扩张,在形式上存在胶柱鼓瑟的问题。但这些异议,并没有直面抒情传统本身在逻辑表述上的困境。
在抒情传统的逻辑表述中,陈世骧强调其“关注意象和音响挑动万有的力量。这种力量由内在情感和移情气势维系,通篇和谐”[27]。这种从西方抒情诗的角度反观中国诗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的做法,实际上所涉甚浅,只读出了其中“发愤以抒情”的一面,没有看到中国诗学中对“情”的讨论本就极其复杂:“情”既根植于作者内在情感,又源自外在景物的触发。古人讲气类感应,“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正是在诸种因素相互影响下,创作主体才得以“摇荡性情,形诸舞咏”[28]。所以具体来看,诗人的创作不只是根源于内心情感,更重要还在于感物的这一层面,由景物诱发诗人兴会的产生。在西方文论中并没有这种气类相感的理论背景,所以讨论诗歌,便只关注浪漫主义的抒情。而从中国诗人的创作方式来看,往往是感物而动情,外在的景与内在的情共生,情绪的起落系于景的挪移。清人黄子云指出:“一日有一日之情,有一日之景”,要求创作主体懂得“随境兴怀,因题著句”[29],诱发的情感与眼前的景物相随共生。所以,当借助西方的抒情诗标准来衡定中国文学时,难免会出现一种概念上的游移。一是因为气类相感的思想背景,诗人的情感抒发常借助景物的触发,通过观景来完成自我情绪的传递;二是因为中国诗歌“情”的状态更为复杂,既有内在情感的直接表达,又表现为多种生动的阐发模式。
钱锺书对情景关系的三种划分,则明显地道出中国诗学中“情”本身的复杂性。回归到诗文写作的过程中,诗人的情感抒发不只是单向度的宣泄,其情绪层次更为复杂,时常受外在景物的引导,情与景交相辉映,方能使诗人丰富的意绪得以传达。
而陈世骧的抒情传统理论将中国文学的道统定义为抒情,其问题在于没有看出情感所依托景物的价值。情是由景所生、因物而动,景物在诗歌创作中所占据比重与意义颇大。如果反观钱锺书所划分的三种层次,便能明显感受出他在观念上的别具手眼:首先,前人论及情景关系,乐于将情的价值提到景的前面,如陈世骧抒情传统中引入的观点,所有的言说皆导向于情。而钱锺书划分的三种层次,则是从景物的角度出发,视景为论述的主体与对象,将景的意义与价值提到首要位置。其次,不同于陈世骧如此看重诗人的内在情感,强调心中意绪的流露。在钱锺书的三种层次中,只有第二种“欢戚相通”提到了诗人内在情感的抒发,像其他的“可供览赏”与“自行其是”都没有将抒情放到极为显豁的位置。或者严格说来,在钱锺书的批评观念中,创作主体内在情绪的显现是有一定的存在意义,但并不值得大书特书,升格成为某种独特的传统。相反,倒是那些着眼于景物的描摹内容,凸显了中国文学独特的关怀。最后,钱锺书论情说景,其缘起是对杜甫用字的考索,他无意于去建构某种传统或体系,或是将其归类固化为某种诗学路数,而在于赏析文字本身的修辞机趣,关注诗歌写作的脉络肌理。
打比方说,陈世骧的抒情传统说像是拿秦砖汉瓦搭建起的西式房屋,里面陈设丰富,一应俱全,却半土不洋,似中实西;而钱锺书则是拾起洋房周边废弃不用的瓦砾,摩挲把玩,展示这些东西的设计妙处,推想出它们本应堆叠出的面貌。当然,搭建洋房是这些砖瓦的用途之一,但如果把这其中之一的用途看成正途,甚至当成唯一的用途,这可能就偏离了它的本来面目。
情感抒发与文学表达始终存在着一定的距离,这种距离在钱锺书看来,是形成文学情感价值与观感价值分野的原因。举例来说,人们通常用“杏脸桃颊”“玉肌雪肤”等词语来形容美人外貌,但如果倘将这些夸饰一一坐实,则“想象女之脸颊真为桃杏,女之肌肤实等玉雪,则彼姝者子使非怪物即患恶疾耳”[30],美好的形容瞬间转变为恐怖的描写。所以读者要善于读出文辞背后蕴藏的内涵,关注到二者间的距离,“当领会其‘情感价值’(Gefühlswert), 勿 宜 执 著 其 ‘ 观 感 价 值 ’(Anschauungswert)”[31]。并且,钱锺书这一论断的提出,将那些本是诉诸视觉的描写手法,拔高到抽象的审美空间上来。王运熙在讨论骈文敷藻和用典的技法时,指出古人妃白俪黄的炼字追求,其旨在“诉诸视觉的形态色泽美”[32],营造出一种带有空间感的视觉美。而根据钱锺书所作的区分,那些敷藻的内容需要发生转向,由“观感价值”转向“情感价值”,在原本视觉美的具象空间上添加一份抽象空间,这样才能尽显文辞之义。面对这样独特的诗学情境,钱锺书总结道:“盖由情生文,义归比兴,则胡越可为肝胆”[33]。正是这种文与义的区隔,情感价值与观感价值的距离,造就了那些相隔遥远事物得以融会的可能。
所以,基于这样的理论背景,钱锺书认为对文辞的理解不应寻行数墨、死在句下,而是应在文字构建的具象空间外在寻找到背后的真实意涵。在分析文义的同时,也关注到那些遥远事物得以融会的原因,唯其如此,方能挖掘出隐藏在文辞中的作者情思。这种分析方式,令人想起福柯在《词与物》中宣扬的理论范式。福柯指出,当处在某种分类模式下,“两个极端不同的事物一旦接近会产生的令人窘困的结果……把这些事物碰撞在一起的这个纯粹的列举活动独独具有它自己的魅力”[34]。把握这种模式下遥远事物得以聚合的原因,便能更为清晰地勾勒出作者情感抒发的状态与方向。
解乎此,也就理解了钱锺书对情景关系的划分理据。在他眼中,情感固然是文章思想得以生发的基础,但更为重要的是把握景物于其间的流变规律。通过思考景物所发挥的文学作用,一条清晰的情感线索便也得以展现。
三 思想潜流:对既定范式的超越
钱锺书对情景关系的划分之所以颇具意义,其原因不只在于展现从景物出发的思考范式,重审景物在情景关系构建中的重要价值,更在于其揭示了在抒情传统之外的书写模式。长期以来,研究者在讨论情景关系模式时,或陷入情景二元对立的思维困境,或纠缠于情景是否融合的问题上,王国维便是其中代表。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虽反复提及“情语”与“景语”,但落脚点仍“仰赖情语、景语这两种美‘相济有功’的结合,才能完成画面的剪裁,境界的塑造”[35]。讨论的内容皆不出如何把握景语、情语之关系,论述内容仍以创作主体的情感为本位起点,着重于书写上的熔裁技法。
而观照钱锺书对情景关系的三种划分,其中的“自行其是,自便其私”,明显勾勒出一条以景物为主体的感发模式。钱锺书在《管锥编》中讨论《北山移文》时,就已经对此多有注目。论及该文的写作特色,他强调其妙处在于“物之若自怅欤,抑人代之惜欤,要皆空谷独居、深闺未识之叹尔”[36]。当人与物同处于类似孤苦寂寞的环境中时,心境往往颇为类似,但诗人在描摹情状时,往往只着眼人物,对景物的情感处境却殊乏领会。《北山移文》的妙处便在于将景物的情绪勾勒出来,把一条久被遗忘的叙说角度重新拾起。随后,钱锺书指出类似的表达内容并不罕见,胪列多篇诗文以资旁证,发掘出一条以物本感应为特色的书写方式。
所谓物本感应,指的是在审美过程中以物为主体的感应模式。不同于抒情传统旨在针对人内在情感的抒发,物本感应的最终导向为无我忘我,尽归于物,完成一种以景物为主体的独立表达。写作策略则表现为自我情感的物化,如邵雍指出:“以我徇物,则我亦物也”[37]。此处“徇”为依从之意,指的是自我情感顺从外在景物,不是执情强物,也非即物生情,而是以一种拟代景物的书写方式去表达。钱锺书在论及物本感应模式时也强调:“水声山色,鸟语花香,胥出乎本然,自行其素,既无与人事,亦不求人知。”[38]一如诗中常有“无人柳自春”“山空花自红”的句子,景物自有一套表述逻辑,诗人之情难以尽托付于景,此时倒不如直接以景物立场去书写。从某种意义上说,景与情天然存在某种悬隔。而这种悬隔,又为中国诗学中过度强调自我抒情、情景交融等理论所遮蔽。在中国诗学的批评传统中,要求诗人“目击其物,便以心击之”[39],认为创作者要即目所见、即景会心,面对自然景物直接抒怀,吐露真实的心境,从而忽视了情与景间本就天然存在的界限。
而以景物为叙述主体,则生发出一种别样的审美趣味。它需要创作者采用忘我的写作状态,回归到纯粹的写作情境,幻想自己化身为景物,代其发言,揣摩诸种意绪。但这种揣摩拟代的口吻,很容易流向一种取巧与圆滑的写作套路,或是转变成游走于各色物象中,变成一种文字游戏。所以,人们对类似景于人无情的现象殊乏关注,或将其置于一个较为低下的位置。
长期以来,传统文学批评对拟代的写作手法评价不高,《围炉诗话》认为“自六经以至诗余,皆是自说己意,未有代他人说话者也”[40]。那种“代他人说话”的作品,即使描写得生动异常,也不会收获很高的评价,正如戏曲小说这样的文体之所以在传统学术中不受重视,就也包含了这样的原因。袁枚指出:“惟时文与戏曲,则皆以描摩口吻为工……此其体之所以卑也。”[41]而钱锺书对物本感应的发掘,其价值在于将这种隐而不显的传统揭示出来,于抒情传统之外重拾起对拟代传统的关注。因为无论是抒发创作者的内在情感,还是代他人说话,在真正的创作过程中,都需要字斟句酌的语言修辞,深刻细腻的情感捕捉,文本中作者所赋予的情感与心力并不因口吻的转化而有所不同。二者真正不同的是,前者因为专注自我,缘情而发,更容易收获批评家的青睐与认同;而后者则因为拟代形式,隐匿个人情感特征,更考究字法上的锤炼,故而较难辨识出真情实感的流露,王夫之讥其“只是妄想揣摩”[42],倚重虚构幻想的写作方式,也容易被看成炫耀才藻,被当成与自我生命无涉的产物。
但这样的认知方式,其实忽视了在拟代的创作状态中,依然要求写作者流露情感、揣摩心思。只不过这种写作角度不再强调创作者关注眼前的经历,而要求将更多的笔墨放置在一个相对遥远的时空,如诸多以“拟古”命名的作品。这些作品虽然托名古人,但其所述心志,依旧是人所共通之情感。钱锺书进而指出,那些貌似是亲身所见的记述,实际也未见得真。比如《诗·淇奥》中“瞻彼淇奥,绿竹猗猗”一句,钱锺书列举《筠廊偶笔》《黄嬭余话》《勉行堂诗集》等书考证,均发现淇奥无竹,其内容无非是创作者凭借自身想象虚构出来的,此后的许多作品,依然存在类似的问题。所以这便要求读者在阅读的同时,切不可仅凭借想象中的虚构,便要到处索隐,刻舟求剑,将文学表达视作刻板的记录。钱锺书指出:“窃谓诗文风景物色,有得之当时目验者,有出于一时兴到者。出于兴到,固属凭空向壁,未宜缘木求鱼。”[43]那些一时兴到的作品,本属向壁虚造,读者一味刻意考求,则难免陷入一种误读的境地。
所以,对于那些出于拟代的作品,不应随意否定,或者将其放置在一个低下的文学位置。因为这样的作品同样寄寓作者情绪,虽然并不是直接抒发自我,但是通过对某种模式的再度演绎,发挥着自我的情思,同样也具备着动人心魄的力量。实际上,正如伽达默尔所提出的视域融合的观点,我们永远无法处在一个孤立的现代视域,并且同一个封闭的过去视域相脱离。所以,“每个文本就不只是某个作者的意图和思想的表达,或某种一定历史时期精神潮流的表现,文本的意义整体是表现一种世界,而这世界说出了在者得以被问和文本得以回答的空间。”[44]文本意义生成于两种互相对话的空间中,拟代的书写方式也是契合这种理论逻辑——用一种幻想揣摩的方式与之前的文本形成对话空间,生成新的文本价值。
钱锺书在辨析情景关系时,跳脱出既定的思考路数,从以景物为主体的角度对情景关系重新反思。事实上,当他标举物本感应为重点的讨论范围时,其妙处在于重新发掘拟代的写作价值;在抒情传统之外,勾勒出一条常遭贬抑弃置的另一条传统。在这一传统的范畴下,创作者的构想空间得以重新打开,从“有我”与“无我”的话语对立下,走向随物而化的忘我境地。
对于这项传统的价值,钱锺书藉由三个方向予以阐释:第一为作者方向,虽然拟代的形式并非由身历目见的景物生发出来,但其揆一也,当中所蕴含的感情并没有在相形之下黯然失色,同样传达出自身或直接或隐秘的感情。这同样也提醒着人们重视那些以拟代为主要内容的文体,重审其在拟代技法的推毂。第二为读者方向,读者在阅读文本时,不应过于拘泥于表层的文本描述,要善于厘清“观感价值”与“情感价值”间的差异,寻行数墨或死于句下皆不可取,“历历如睹者,未必凿凿有据,苟欲按图索骥,便同刻舟求剑矣”[45]。阅读上感受的真实并不等同于现实的真实,在文本上所发生的形变与转换同样值得重视。第三则为所要摹状的客观世界。维特根斯坦说:“我们不可能看见我们自己到处走来走去,因为正是我们自己在走(因此我们不可能站着不动而且看自己走)。”[46]易言之,人无法拥有一个既全面且客观的视角来观察和把握世界。无论是拟代幻想的书写方式,还是宣称身历目见的自我抒情,其本质皆囿于作者自身的审美判断经验,这也提醒人们在分析文本时注重其内里所发生的演化与变形,探寻其书写脉络的演变之迹。
综上,钱锺书分析诗歌时,常从作品文本内部出发,由某些具体的字法来探求诗眼文心,厘清其背后所蕴藏的思维方式与审美取向。故而他在分析情景关系时,更着重于书写视角的转换。不同于抒情传统的理论范式,钱锺书力图挖掘出一条以景物为主体的书写方式,重新确定出拟代传统的理论价值。该传统因表现形式的原因而长期受到贬抑,隐而不显,相应的评判内容也处于一个缺失的状态。将该传统予以重新审视,或可揭示出其背后所隐藏的文化理据和诗人心态,提供一种权衡甄别的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