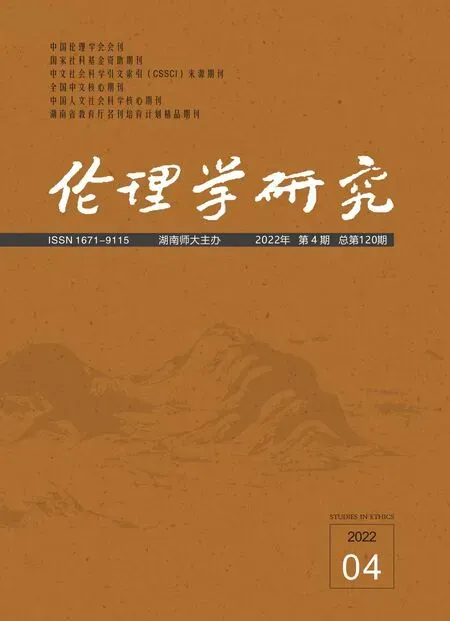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伦理认同研究论纲
2022-03-23关健英
关健英
霍布斯鲍姆认为,“民族”(nation)以及衍生自民族的种种概念,是诠释近两个世纪以来人类历史的必由之路[1](3)。虽然这种观点代表了西方学者关于民族形成于近代欧洲的普遍看法,但他将“民族”看作是理解历史不可绕开的一个概念,无疑是非常深刻的。即便认为民族是人类偶然建构与发明的西方学者,也不能不承认民族身份对于人的不可或缺。盖尔纳说,一个没有民族归属的人,如同一个人失去了自己的影子,这是不可思议的[2](7)。对“民族”的理解,关乎作为个体的“我”和作为人们共同体的“我们”的身份认定、文化认同以及意义确认。因此,哲学伦理学不但要回答“我是谁”的问题,还要回答“我们是谁”“我们因何而成为我们”的问题。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演变中的民族认同
“中华”取“中国”之“中”与“华夏”之“华”组合而成,“中华”一词出现于两晋时期。作为一个语词虽较为晚出,但作为一种观念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经历了漫长的延续与演化过程。“中国”一词古已有之,在《诗经》《尚书》等先秦典籍中较为常见。西周初年的何尊铭文中有“宅兹中国”之语,是目前可知的“中国”一词出处的最早物证。“夏”“华”“诸夏”“中夏”等屡见于先秦典籍,与之相对应的概念则是蛮、夷、戎、狄或四夷、夷狄、戎狄。历史上的“中华”“中国”概念既包含地理、血缘、王朝国家的含义,同时也包含人文相续、伦理认同的文化意义。唐代学者在解释“华夏”概念时,认为“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左传·定公十年》,孔颖达疏),已然从中华文化及其认同的意义上进行阐释。建立政权的辽人与金人既将自己称为“中国”,也把当时的宋朝称为“中国”。元代统治者在对外交往中自谓“中国”,称高丽、爪哇、日本等为“夷”(《元史·外夷列传》)。在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过程中,各民族的“大中国”意识以及文化认同逐渐萌生、明晰。随着历史上民族融合进程的推进,“中华”的政治趋同性特征和文化认同意味越发凸显。
学者经大量考证认为,“民族”一词并非由日本传入。黄兴涛教授认为,中文里的“民族”一词最晚到1837 年时就已经出现[3]。郝时远教授通过对古籍中十例“民族”语词的源流考辨,认为“民族”是中国固有词汇[4]。“民族”一词见于中国史籍,但总体而言较为少用,亦偶有版本错讹,如《南齐书·顾欢传》有“民族弗革”,与明南监本、汲古阁本以及《册府元龟》参校,“民族”乃“氏族”之误,其义同“族类”一词[5](646)。吕思勉先生认为,中国的民族概念“虽未见晶莹”,但中国的民族现象,则是自古以来的事实存在,可见民族观念明晰与否,与实际上民族存在与否毫无关系[6](263)。此说虽不免有些绝对,但也确实道出中国历史上丰富的民族史实与史籍中较少使用“民族”一词这种不相匹配的现象。在中国古代,多使用华夏、匈奴、鲜卑、契丹、女真等具体族称来记述各民族的史实;强调夷夏之别,则用夏、华、诸夏、中夏等与蛮、夷、戎、狄对称;强调具有共同利益和文化认同的人们共同体,则使用“族”或者“族类”。
近代以来,发端于欧洲席卷世界的民族主义思潮进入中国,与近代中国自强保种、救亡图存的时代诉求相呼应,中国固有的“民族”一词成为英文nation 的汉译概念。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知识界领袖,从中捕捉到挽救民族命运的时代信号,创造性地提出“中华民族”概念。1902 年,梁启超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率先在中国各民族融合的“大民族”意义上使用“中华民族”一词。在梁启超于1905 年发表的《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中华民族”包含多民族混合而成的内涵已然非常清晰。虽然,近代知识界在使用“中华民族”一词时,仍不免将其主体看作是汉族,反映了他们的历史局限性,但他们能够以“中华民族”超越“汉族”,反映了对中华民族本非一族,而是由多民族融合而成之特性的自觉认识。此后,“中华民族”概念内涵逐渐由指代汉族共同体,发展为指代包括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共同体。20 世纪初,近代知识界对“中华民族”概念的创造、讨论与宣传,切合了近代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时代需要,反映了中华民族意识的自觉与苏醒,增强了中国人的民族认同感,具有鲜明的爱国主义性质,对现代中国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具有重要的意义。
20 世纪60 年代,考古学家夏鼐基于对中国各民族关系的考察,提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夏鼐提出,少数民族虽与汉族不同,但在中国悠久的历史过程中,各兄弟民族的祖先与汉族祖先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大家一起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7]。20 世纪80 年代,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说,各个民族和中华民族虽则都称“民族”,但层次不同,“五十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8](1)。中华民族不是56 个民族的简单相加,而是具有整体性、共同性和实体性的民族共同体。多元一体是相互依存的统一体,一体离不开多元,多元共同构成一体。
通过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相关概念的概念史回顾梳理,我们可以发现,“中华民族共同体”内涵所指是中华民族,其强调由多元构成的一体,凸显了中华民族的实体性特征和价值认同本质。“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的形成和发展植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过程,反映出在多民族融合的历史中一直存在连续而稳定的“中国”“中华”认同传统。
二、多元一体:“中国现象”及其历史必然性
一个民族以何种形象出现在其他民族的视野中,又被“他者”解读或者“塑造”成为何种样子以及背后的缘由,从来都是比较文化视野中重要的研究主题。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说,中国的独特性在于,它是一个由占人口大多数的汉族及众多少数民族组成的“多民族实体”。历史学家许倬云在谈到中国与世界上其他民族共同体的比较时,也认为中国确实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相当特殊的个案。尽管民族多元现象是普遍的,民族融合也并非中国所仅有,但无论是从“他者”视角对“我者”的审视,还是基于“我者”立场与“他者”的比较,中国各民族融合成为多元一体的历史是独特的,由此形成了世界民族史上独特的“中国现象”。
第一,中华民族由多元而一体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中国历史上有丰富的民族现象,既有传说史中的以黄帝、炎帝、蚩尤为首的古老氏族,也有夏、商、周诸族,以及建立政权的鲜卑、契丹、女真、党项、蒙古、满洲等少数民族。这些古老民族不断发生接触、冲突,同时又在冲突中不断地融合,这是一个持续而漫长的历史进程。汤武革命既是夏、商、周三代的政权更迭,也是夏、商、周三个部族的冲突与融合。至西周时期,形成了以“夏”“华”为族称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雏形。他们“宅兹中国”,在地域上区别于生活在“四方”的其他各族;他们的礼乐制度郁郁乎文,在文化认同方面有别于四夷;他们是夏商周各族漫长融合后的民族共同体,区别于当时尚未融入华夏的荆蛮、犬戎、淮夷、肃慎、鬼方、猃狁等其他族群。可以说,在距今三千多年前,出现在黄河中游由若干古老民族集团冲突融合而形成的诸夏,就是最早的、以自在的民族实体形式出现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诸夏是其核心,但此时期的诸夏已是民族融合的结果。“汉人”称谓的出现则表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凝聚核心汉族已然形成,但此时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是融合各民族的历史产物,而非诸夏单一民族演进的结果。此后,经过魏晋至隋唐时期中原地区民族的大混杂、大融合,经历唐末五代、宋元明清时期北方各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族的接触、融合,中华各民族逐渐融汇合流,由多元而一体,成为融合在一起、生长在一起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在中国历史上,这是一个通过无数次交融与重组、逐渐形成多元一体格局的过程。导致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因素是复杂的,民族间的武力冲突是事实,各民族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文化上的交互影响以及伦理上的相互认同也是事实。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主要不是人为建构,不是血统、地域和宗教的因素,也不能简单归因于军事征服和政治干预。这是一个渐进发展的过程,是在特定的条件下,各民族所作出的适合自身生存发展、符合中华民族整体利益、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选择。
第二,多元一体内蕴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的重大进展实证了中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不仅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历史脉络和丰富内涵,也揭示了在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
现有的考古成果实证了中华民族在创生期的多途、多元起源论。中华各民族先民们如满天星斗一样,分散在从南到北、从西到东的古老中华大地上。在周人看来,“中国”首先是一个地理概念,他们居住在中土,与四方的蛮、夷、戎、狄合称“五方之民”,五方之民共居天下九州。随着时间的推移,作为地理概念的“中国”,其边界渐次扩大,“中国”的含义也在不断变化。在春秋时期,南方的楚国是尊王攘夷的主要对象,位于黄河中下游的周朝及晋、鲁、齐、郑、卫、宋等诸侯国,即“中国”,而作为“蛮夷”的楚国,断发文身的越国,均不在彼时“中国”的范畴中。至秦汉时期,“中国”的边界已将秦、楚、越包含进去。“中国”疆域在某些历史时期是缩小的,在某些朝代又在不断扩大,但总体上渐趋拓展。这是一个随着历史发展自然形成“中国”疆域的过程。到清代自然形成了“东极三姓所属库页岛,西极新疆疏勒,至于葱岭,北极外兴安岭,南极广东琼州之崖山”(《清史稿·地理志》)的中国版图。历史上的“中国”不专指周代的王畿,也不能将两宋时期的辽、夏、金排除在外,当然更不能如美日的元史、清史研究者那样把元、清划出“中国”。在各民族共同开拓中国疆域、形成“中国”版图的过程中,自在形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同步形成。
第三,多元一体凸显了历史上的中华民族认同。在中国史籍中“民族”一词虽出现较晚,且相对较为少用,但关于民族现象的记载是十分丰富的。《诗》《书》《国语》以及“三礼”、《春秋》三传记载了丰富翔实的民族史料,二十四史均可谓中国古代多民族史撰述的杰作。“族”是一个会意字,许慎认为,“族,矢锋也。束之族族也。从㫃从矢。所以标众,众矢之所集”。段玉裁从“族”的字形,指出“族”字的引申义,“引申为凡族类之称”(《说文解字注·第七篇上》)。“族”本义是锋利的箭,引申为聚集在一起的人们。最早的“族”首先是一个军事单位,聚族而居的人们即“我族”,共同的敌人即“他族”。从共同利益和族类认同的角度来解释“族”字,表明中国古人对于民族现象朴素而深刻的认识。
钱穆先生在谈到中西民族特性问题时认为,西方历史的重要特点是看重民族区分,无论古埃及、古巴比伦还是现代欧洲,民族相异、民族分歧是共性特点[9](57)。世界上一些民族曾经创造了自己的历史,但与在民族冲突中被取而代之的后起民族之间没有形成连续的民族认同,伴随着文明的中断,民族的历史随之中断。中国历史则建立起民族的连续性认同。孟子认为舜属东夷,文王属西夷,虽地域不同,时代不同,但他们是“行乎中国”的“先圣”与“后圣”,其道无不同,认同趋一致,“若合符节”(《孟子·离娄下》);司马迁认为,“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国号”(《史记·五帝本纪》),黄帝、颛顼、帝喾、尧、舜有着一脉相承的血缘谱系。夏的创立者禹、商的始祖契、周的始祖弃,他们的族源和文化都可追溯至黄帝;苏秉琦认为,夏、商、周既是政权更迭的三个方国,也是具有不同族源的三个古代部族[10](16),他们的民族认同与文化共性大于差异性,共同构成了华夏族的三支主要来源。
第四,多元一体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四个共同”的历史。传统历史叙事不仅追溯了诸夏的共同族源,而且将其他各族纳入王朝治理体系,将其他民族的历史纳入中国共同的历史,建立起其他各族对“中国”的认同。肃慎是满族的族源,据史记载周代肃慎即生活在黑龙江流域。《书》云“成王既伐东夷,肃慎来贺”(《尚书·周官》),史载肃慎以“楛矢石砮”向周天子进贡,“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于是肃慎氏贡楛矢石砮,其长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远也,以示后人,使永监焉,故铭其栝曰‘肃慎氏之贡矢’”(《国语·鲁语》)。西周创立“五服”制度,肃慎生活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格局中的“北土”(《左传·昭公九年》),隶属于周代的五服制度和朝贡体系。宋朝是与辽、金、西夏并存的时代,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的王朝叙事只以宋代作为中国的朝代,而将辽、金和西夏放在中国的历史圈之外[11](121)。从中华文化主体地位而言此说不错,但从修史传统看并不尽然。南宋灭亡后,元代议修辽、金、宋三史,但在修史的体例上,即以哪一个朝代为正统王朝,则一直论而不决。直至元末,形成共识性的修史体例:辽、金、宋各为一史,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辽、金、宋三史虽分别修撰,但归根结底都是中国的历史,都是中华民族的历史。
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很多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这些建立政权的少数民族无不认为自己是“中国”,同时在相对于“中国”的“他者”看来,这些少数民族也被认为是“中国”。建立北魏的拓跋氏与漠北中亚交往较多,当时中亚人就以“桃花石”(“拓跋氏”的汉语译音)来称呼中国人。契丹建立辽,在当时与中国北方接壤的俄国人眼中,契丹的地域、政权和民族并不明晰,既指与北宋并存的辽,也指灭辽后继承了其土地的金,以及与金并立对峙的南宋;既指契丹族,也包括汉族、女真族、党项族以及其他北方少数民族。虽然辽、金有别于宋,但在作为“他者”的俄国人看来,他们并无不同,都是“契丹”,都是“中国”(“契丹”的俄语译音为Китай,至今仍是俄语的“中国”)。因此,“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统一天下为己任,都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分立如南北朝,都自诩中华正统;对峙如宋辽夏金,都被称为‘桃花石’”[12](4)。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民族间冲突融合的历史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相伴相生。历史上各个民族,包括已经湮没无考的民族和族群,共同开拓了中国辽阔的疆域,共同书写了中国的历史,共同创造了中国的文化,共同培育了中华民族的精神。
三、伦理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中的精神密码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认同是一个民族最深层的认同。在一个民族的文化系统中,伦理道德是对社会生活秩序和个体生命秩序的深层设计,居于该民族文化系统的核心地位。伦理认同是人们对基于共同的社会生活而形成的共同体之“伦”的价值共识。伦理认同是实体性的认同,是个体对普遍物的精神归属和价值服膺。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在冲突融合中结成的相互依存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既是利益共同体,也是精神共同体、伦理共同体。
首先,“行同伦”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精神纽带。《中庸》有言:“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不敢作礼乐焉。”“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是战国时期儒家思孟学派关于天下“定于一”的构想:既要在制度层面同衡、同轨、同文,也要用儒家伦理作为天下一统的准则——同伦。秦统一天下,变封建为郡县的同时,采取了量同衡、车同轨、书同文之制,“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器械一量,同书文字”(《史记·秦始皇本纪》),但《史记》并无秦朝“行同伦”的记载。思孟学派用儒家价值观作为天下“同伦”构想之精神内核,与奉行“不务德而务法”(《韩非子·显学》)与“以法为教”(《韩非子·五蠹》)的秦政显然无法契合,“行同伦”之说见于《中庸》而不见于秦史,也属当然。实际上,秦强调同文同轨,而无“行同伦”,并不意味着秦没有“行同伦”的理念和实践。在记录、歌颂秦始皇巡视天下的石刻中,有“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尊卑贵贱,不逾次行”,“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说明秦并非不重视“同伦”,只是秦所强调的“同伦”,不是儒家的人伦观念,而是以法家思想为内核的伦理准则。汉代独尊儒术,儒家纲常成为此后中国社会伦理道德规范体系的核心。在儒家看来,一个国家不仅要有统一的制度设计,而且需要共同的人伦价值观。共同的伦理准则是维系社会、柔化人心的重要力量,行同伦与车同轨、书同文一样,对于一个统一的国家来说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即宋儒所言“三者皆同,言天下一统也”(《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同伦”是一个民族文化基因的重要方面,镌刻着民族的精神标识。
其次,伦理认同与夷夏之辨是相伴相随、辩证统一的关系。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过程,是伦理冲突—伦理选择—伦理融合—伦理认同的过程。其间既有不同伦理价值的冲突,也有交互影响、融合与认同。古人以地理区位、生产方式等特性指称区别于华夏族的其他各族,北方为狄,东北为貉,南方曰蛮、闽,西南为僰,西方为羌、戎,东方曰夷,又称东夷、东南夷。蛮夷戎狄合称四夷、四裔,也统称为“夷”或“夷狄”,与夏、华、诸夏、中夏相对而言。夷夏之辨是传统伦理的重要议题,但中国历史上的夷夏之辨重点不在于强调生物学意义上纯粹的华夏族血统,而是文化的优劣之辨、先进性之辨、主体性之辨。华夏的先进文化影响了周边少数民族的文明化进程,一些开明的少数民族统治者认同中原华夏文化,以一种文化自觉意识主动用夏变夷,向华夏文化学习,加快了本民族的中国化(华化)过程。北魏孝文帝改革将鲜卑姓氏改为汉姓,放弃鲜卑语改说中原话,改穿汉人服饰,将《孝经》译成鲜卑语,这些基于对中华伦理认同而采取的举措,客观上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融合。与此同时,变于夷的文化现象在民族融合的历史过程中亦不鲜见。南北朝隋唐时期,社会风尚方面出现了大量“胡化”现象,胡食、胡乐、胡舞、胡服等对中原文化习俗产生重要影响,在胡俗的浸润下,“胡心”萌生,人们的价值观念悄然改变,“长安中少年,有胡心矣”[13](269)。胡俗与胡心一表一里,说明伦理道德的交互影响也是民族融合中的客观现象。夷夏之辨虽然表现出一定的华夏中心主义和文化优越意识,但总体上并没有成为中华民族融合历史进程中的阻滞因素,而是与民族融合的浪潮相互激荡,华夏文化与各少数民族文化的交互影响越发深入,中华民族的伦理认同越发明确,民族共同体意识越发清晰。经过中国历史上几次大的民族融合,中华民族逐渐融汇合流,成为血脉相连、血浓于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最后,中华伦理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精神内核。文化的主体是民族,民族创造了文化,文化亦陶冶民族。推动中国历史上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除了各民族互补依存的经济联系、彼此亲近的民族情感,还有文化认同。而且,文化认同是促进民族融合的最重要的精神黏合剂。血缘融合固然是民族融合的一个因素,但更重要的是伦理认同。荀子说“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荀子·儒效》),唐代人讲“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14](189),都是从伦理观念的角度区别华夷,而不是以地域、血缘而论。中华民族共同体伦理认同根植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所积淀的深厚历史文化传统,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的共同的、稳定的、世代相续的人文传统和伦理精神。
一是整体主义的价值取向。周代确立了“五服”的天下观和治理体系,“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狄荒服”(《国语·周语上》)。北魏的拓跋氏自称黄帝后裔,在周代五服制度中隶属于“荒服”(《魏书·序纪》)。所谓“服”,即“服其职业”(《国语·周语上》,韦昭注),意谓周天子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天下中心,而且是国家权力的中央、文化的象征。五服体系内,在贡赋和治理方式上可采取不同的制度,但在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方面则是一致的,从而形成五方之民共天下的格局。中国文化注重整体和整体利益,强调“夙夜在公”(《诗经·召南·采蘩》),“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左传·昭公四年》),“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左传·僖公九年》)。尚公尚忠的整体主义价值取向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维护共同体的团结统一,反对任何分裂国家、民族的企图和行为,一直是中华民族主流的伦理观念。
二是和而不同的文化理念。西周末期,史伯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之论。孔子主张“和而不同”,反对“同而不和”(《论语·子路》)。《中庸》提倡“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和而不同的伦理精神使得中国文化能够包容各个民族在生产方式、生活习俗等方面的民族个性。中国自古以来广土众民,民族差异性以及发展的不平衡是客观的存在,“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其性也,不可推移”,因此在治理上要因地制宜,因俗制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使五方之民各得其所,“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礼记·王制》)。和而不同的伦理精神促进了民族间的交流交往,在文化上彼此碰撞、吸纳、融合,各民族共同成为中华文化和中华伦理的创造主体。
三是天下一家的同根意识。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不是种族血缘。中国古代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左传·成公四年》)之说,这里的“我族”指的是姬姓血缘。周代政治与文化建立在宗法制基础之上,周天子通过赐姓、胙土,将生物意义的血缘推扩为文化意义上的血缘,纳天下五方于宗法网络之中。因此,血缘作为区分“我族”与“他族”的一个基本标准,已从关注血统的纯粹转换为建构文化的认同。因此儒家的夷夏之辨,不在于强调血缘的生物性特征,而在于凸显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地位。古人有同姓不婚的朴素认识,但并无华夷之间禁止通婚的法律与伦理。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各民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血脉相连、同根同种的共同体,天下一家、中国一人、华夷一体的民族共同体意识超越了生物学意义上的血缘血统观念,成为中华民族的伦理共识。
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国道路”与中国话语
民族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典作家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洞察人类历史发展客观进程,揭示出民族共同体产生、发展和消亡的一般规律。中国共产党自建立之初就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民族工作始终是国家治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具体国情结合的实践产物,以制度的形式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各民族平等。党的十八大以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进程继续推进。在2021 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回顾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指出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就是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15]。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服饰和饮食习惯,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民族发展道路。从“中国现象”到“中国道路”,体现了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解决民族问题“中国道路”重大论断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源自中国文化、解决中国问题、符合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中国道路,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创造性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民族是理解历史的一把密钥。民族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民族问题是世界性的问题,也是中国问题。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要坚持中国立场和中国话语,传承并创新性地发展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历史过程中作为精神密码的中华伦理认同。在西方学者看来,民族是晚近出现于欧洲的现象,18—19 世纪是民族创建的时代[1](3)。西方学者普遍认为,民族是“偶然”的产物,是民族主义造就了民族[2](61);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它一旦被想象之后,就开始了模塑、改变和改造的过程[16](137)。在海外中国史研究中,日本学者曾提出所谓世界史中的“蒙古时代”和“蒙古时代史”,试图以此来改写中华民族的历史;美国、日本的“新清史”研究认为清朝并非中国,将清的历史独立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之外,否认历史上客观存在的中华民族认同和中华伦理认同。而文献史料和考古实证表明,在中国多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中,一直存在持续的民族认同和伦理认同,历史上的中国从来都是一个稳定的文化共同体。西方已有史学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他们的某些理论和观点可以用来说明一些民族的发展历程,在一定地域和文化传统中具有合理性,可以借鉴和参考,但不能作为中华民族历史研究的基本准则,无法揭示中国自古以来多民族融合的历史过程和世界民族史上独特的“中国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