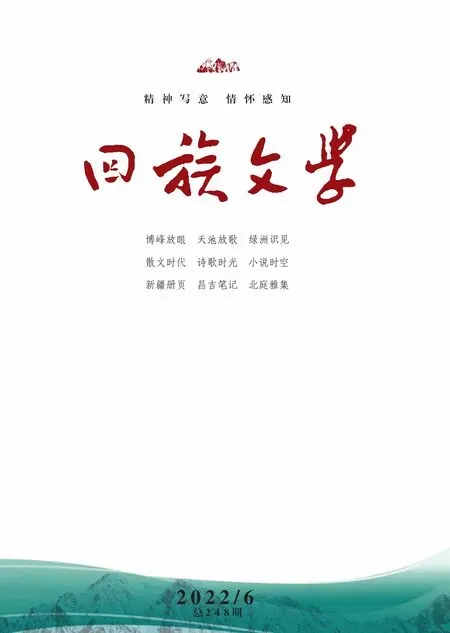那年新风起天山
——新边塞诗派诞生始末
2022-03-22吴平安
吴平安
“1980年代是文学的流金岁月,”多少年后周涛在其口述自传《一个人和新疆》里说,“我们这茬人就像地里的红高粱,得到了时代雨露的滋润,就齐刷刷地冒头了。”彼时的文学版图,已渐成各路诸侯群雄逐鹿之势。中央军兵强马壮自不待言,而沪军、湘军、鄂军、陕军、东北军等一干“地方豪强”也声威日壮,令人不敢小觑,反观天山南北的自然气候和文学气候,都明显比内地晚一大截,就连正猛烈冲击着中国文学的西方现代派文学,浪潮波及西北一隅时,也已是强弩之末了。
不过春风既度,草长莺飞是迟早的事。
初出茅庐的评论家周政保,对西部文学的基本盘,已经有了比较清醒的把握:西部小说的传统是极其贫困的,新疆主要的文学积淀是各民族的民歌和民间文学,《玛纳斯》《福乐智慧》与阿凡提传说是其中瑰宝。结论是:新疆是一个诗歌的宝地,新疆文学的突破口,希望只能寄托在诗歌上,而面对西方现代派,新疆文学界的青年才俊,应该将更多目光投向脚下的大地。
新疆的文学实践证明了这一判断的正确。《诗刊》1976年1月复刊号上,章德益即有组诗《塔里木人》发表,旋即有诗集《大汗歌》《绿色的塔里木》问世;周涛的长诗《天山南北》于1978年登上《诗刊》,有近200行,《八月的果园》于1979年出版单行本,是一部2000多行的长诗;杨牧的长诗《在历史的法庭上》,洋洋600行,登上《诗刊》1979年11月号头条。曹禺、徐迟一行踏访新疆,在千人大会上,说新疆有人才,特别提到了周涛当时发表的《天山南北》。《新疆文学》老编辑郑兴富对推动新疆的诗歌发展功不可没,当时,其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在乐观昂扬的氛围笼罩着西部诗界时,遥远的首都北京,1978年12月23日,有一家民间刊物《今天》悄然问世了,1979年第3期和第4期《诗刊》,分别转发了原刊于《今天》的北岛的《回答》和舒婷的《致橡树》。如果说这两篇新人新作并没有在新疆诗坛引起多大反响的话,那么随着北岛、芒克、舒婷、顾城、江河、多多、杨炼、梁小斌等人相继走到前台,在主流刊物竞相亮相,随着《福建文学》因讨论舒婷诗触发了长达一年的论争,随着1980年8月章明《令人气闷的“朦胧”》一文在《诗刊》的发表,“朦胧诗”终得赋名,随着谢冕、孙绍振、徐敬亚诸人的“三个崛起”论文对“新的美学原则”的力挺,新疆的诗人就再不可能从容淡定了。我至今还清晰记得周政保捧着一本当期《诗刊》,向我和周涛传阅《中国,我的钥匙丢了》的情景,那是一种瞬间被电流击中的震撼感,是一种无论读旧诗新诗中国诗外国诗从未有过的阅读体验。
很多年后,周涛在其口述自传《一个人和新疆》中,回忆当时心中的感受:“我在七十年代末给自己定的方向,概括为‘郭小川的声音、闻捷的色彩’,我把这两个人结合在我这里,而且我当时心中有一个感觉,我用这一手可以迅速打败中国诗坛,不在话下。谁知道出来个朦胧诗,梁小斌那个《中国,我的钥匙丢了》,也觉得搞得不错,很新鲜,别有一种诗味。这时候弄得我们不好写了,找不到自己了,明显地感觉到用郭小川、闻捷那里学来的东西打发不了这个世界。”
新疆诗人往何处走?“新的出路”在哪里?周涛接着说:“一个是坚持这一套,一个是投降朦胧诗,搞一个二鬼子。”跟风学舌不是有出息的人,这不是新疆诗人所为,也不是所能为的,因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新疆二周(周涛、周政保)英雄所见略同:“我们的文化条件不具备写那种诗的要求。”
这一方水土,是大西北的高天厚土、沙漠瀚海、雪山冰峰,是荒蛮苦寒的生存环境;这一方人,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十三个兄弟民族,是王震将军麾下的军垦战士,是内地支边的热血青年,是在政治风暴中如沙尘般吹落到边塞的各界精英,是被饥荒驱赶走西口的盲流……再远一些,还有大汉开拓欧亚孔道的探险家,行走在古丝绸之路上的商旅,在石壁上开凿洞窟描画飞天的画家,出使塞外吟咏边关的诗人……正是这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滋养了这一方诗人,锻造了他们的文化人格和精神气质,涵养了他们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趣味,建构了他们的话语方式和语言表达:
荒野的路啊,曾经夺走我太多的年华,
我庆幸:也夺走了我的闭塞和浅见;
大漠的风啊,曾经吞噬我太多的美好,
我自慰:也吞噬了我的怯懦和哀怨。
——杨牧《我骄傲,我有辽远的地平线》
兀立荒原
任漠风吹散长鬃
引颈怅望远方天地之交
那永远不可企及的地平线
三五成群
以空旷天地间的鼎足之势
组成一幅相依为命的画面
——周涛《野马群》
远古奔突的激情冷却了,
凝成了一种立体的冷峻,
固态的力量,
曲线中起伏着庄严,
铁色中放射着凝想。
——章德益《大漠的山》
浅吟低唱不属于他们,他们的旗帜上写着刚健、沉雄、凝重、豪放,旗下伫立的是以“半个胡儿”为集体人格的铁骨铮铮的西北硬汉,向世界展示炼狱中升腾起的血性及伴随的呐喊。
周涛清醒地认识到,“新疆是古代边塞诗产生的地方”,“创造一种‘新边塞诗’”的想法,开始在心中萌动,并且与杨牧、章德益一拍即合。“我们三个人经常聚一聚,坐在一块说说话。我就提出来,新疆是古代边塞诗产生的地方,唐诗中边塞诗是重要的一章,新疆这种边远之地想独霸文坛是做不到的,大不了做一个当代文坛的分支,在现在的条件下创造一种‘新边塞诗’,这种边塞诗不是写征战、打仗,而是反映新疆地区的独特风貌。……章德益和杨牧都认为这个主意不错。”“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三个人都意识到单打独斗恐怕在风起云涌的中国文坛上像树叶一样迅速地被吹走,如果一个枝子长三个杈杈,可能摽着稍好一点。”(周涛口述自传《一个人和新疆》)
此后,三人联手,用军旅诗人周涛的军事术语说,“做成集束手榴弹,三个手榴弹一块扔出去炸的面大”。于是,从《诗刊》《人民文学》《上海文学》开始,“把全国所有的省刊撸一遍”,未几,杨牧、周涛、章德益,“新疆三剑客”的名声大振,而李瑜、杨树、东虹、石河、孙涛、柏桦、杨眉、高炯浩、郭维东、安定一,还有更年轻的一茬王小未、秦安江、郭有德、曹永正、贺海涛、张小平、谷闰、曲近、晓虹等紧随其后。新疆是诗歌的沃土,此言不虚。
1981年11月26日,周政保在《文学报》发表评论《大漠风度 天山气派——读“百家诗会”中三位新疆诗人的诗》,分析了“三剑客”诗作的美学风格,明确指出:“一个在诗的见解上,在诗的风度与气魄上比较共同的‘新边塞诗派’正在形成。”这是“新边塞诗派”首次在中国诗坛树起自己的旗号。
刘湛秋、余开伟、郑兴富、孙克恒、张功臣、谢江华、高戈等评论家,先后撰文评论和研究新边塞诗,而最翔实的理论阐发,则是周政保发表于《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的论文《新边塞诗的审美特色与当代性——杨牧、周涛、章德益诗歌创作评断》。
周政保在文中写道:“严峻的边塞生活,极为自然地使他们获得了一种豁达而粗放的世界观(包括诗歌艺术观),那就是深邃悠长的历史意识,昂扬进取的人生态度,排斥了孤立性的整体眼光,以及那种能把一切抒情对象纳入自己情绪轨道的思辨能力。”
周政保的敏锐之处,在于他能从三剑客的诗篇中,捕捉到特定历史时期的时代气息。如果说朦胧诗表达的是特定历史时期一代青年人的迷惘,新边塞诗则是迎接新时期发出的第一声呐喊,周政保热情地将其比喻为八十年代的进行曲:
杨牧、周涛、章德益诗的当代性色泽,正是通过多姿多彩的地域性特点而获得显现的。在这里,地域性只是一种诗情诗意的外壳;而在这层外壳所包笼的内核中,却奔突着岩浆般的、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地热力量。因此,我们也就从一个亘古而神秘的天地中,窥见了另一个播放着八十年代进行曲的诗情世界。
当三剑客渐成气候之时,为了彼此的个性不至于被新边塞诗的共性淹没,周政保在细读分析了三人作品的基础上,归纳总结了他们不同的诗风诗格,划清了彼此的区分度:
周涛是一位军旅诗人。他的主要抒写对象是新疆的民俗风情与边地的军旅生涯,冷峻,沉雄,深邃,潇洒而又充满悲壮感,构成了他的作品的主要美学特色。
而杨牧,则倾向于那种充满了社会思潮力度的、豪迈而又奔放的抒写方式。他从土地来,又回到土地去,荡漾着底层劳动者的热忱与思索。
而章德益的当代性,则是在恢宏奇诡的幻想中实现的。他是当代诗坛的幻想家。他在他的作品中,不断塑造着一个巨人的形象,一个拓荒者的高大身影。
周政保的导师雷茂奎教授深谋远虑:有了创作的一定实绩,又有了理论的初步宣示,便应该依照学术生产的机制,让新边塞诗在大学里占一席之地。雷先生策划了一个“新边塞诗大型学术研讨会”,以期为这一诗派,为崛起中的西部文学凝聚人气,辐射影响。
雷茂奎与当代文学教研室刘维钧、常征协商,拟定了一个阵容庞大的邀请与会者名单。中文系研究生郭澄、朱思信、沈贻炜、严荣赓、邢欣等人,加班加点,用毛笔郑重地填写邀请函信封,参与新疆当代文学史书写的激情,使他们心潮澎湃。
1982年3月18日,倾注了许多人心血的研讨会,终于在雷茂奎先生主持下召开了。二百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会聚新疆大学,著名诗人艾青、田间、严辰、袁鹰、李瑛、蔡其矫等人寄来了贺诗和贺信。会后出版了《边塞新诗选》,谢冕先生欣然为之作序。
那些来自马背驼峰上的吟唱及伴随的理论宣示传到了京都,彼时“归来的诗人”群体中的“七月派”诗人绿原,在《诗刊》1984年第2期撰文《周末诗话》,盛赞“周涛的《牧人集》,章德益的《大漠和我》,杨牧的《夕阳和我》……都是近年来不可多见的力作”。曾为朦胧诗鼓与呼的北大教授谢冕先生,也把目光转向了大西北,《阳关,那里有新的生命——从敦煌文艺流派到新边塞诗》(《阳关》1982年第6期),《丝绸路上新乐音——〈边塞新诗选〉序》(《当代文艺思潮》1983年第5期),《新边塞诗的时空观念》(《阳关》1984年第4期)先后发表。谢冕先生从历史的纵深处梳理旧边塞诗,又将新边塞诗纳入新时期文学的语境中,高屋建瓴地对新边塞诗作出准确的定位和学理上的肯定:“当前的诗歌运动,处于微妙状态。一方面,一九七九年的高潮过后,发展渐趋沉寂,现状未能令人满意;另一方面,新诗无视旧日的积习,在每一个角落悄然而又扎实地发展着……就在一些人认为新诗危机四伏的时候,西北地区的诗人和理论工作者首倡并建设着新边塞诗。”
天时地利人和,在那个万卉争荣的季节,风云际会,新疆文学从地域性、边缘性的存在,向中心地段大大推进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