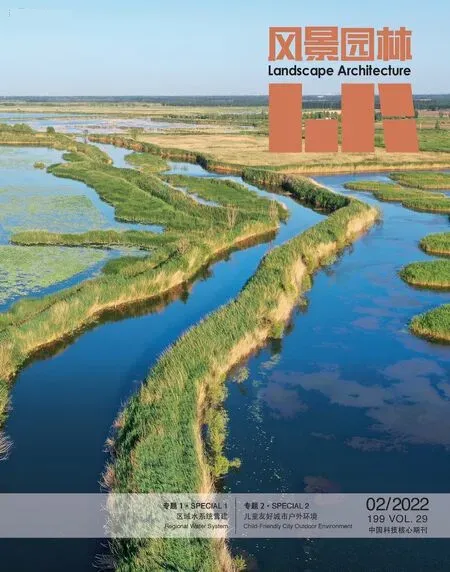童年场所依恋与成年后幸福感的关系研究
2022-03-22王颖王巍静孙子文胡秉真
王颖 王巍静 孙子文 胡秉真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发展迅速。对个体而言,这不仅意味着人们物理上从农村到城市环境的迁移,而且还涉及心理上对新生活方式的适应和社会联系的建立[1]。由于个体适应力不同,环境适应性有所差异,加之个体经历的环境变迁程度不同,这一差异有可能被加剧。随着人类对景观干预程度的不断加大,越来越多的居民感到与过去较为自然的童年场所失去联系,并陷入了一种心理上“无家可归”和失去“根性”的痛苦[2]。因此,如何提高新城市居民的环境适应性以及如何使他们更好地融入新场所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社会学家已根据这一问题,基于人地关系理论(human-land relationship),提出了“场所依恋”(place attachment)这一概念。近几十年来,大多数研究都聚焦在当前场所的社会依恋(如社会关系),而对过去场所(如童年居住地)的依恋及对场所的物理环境依恋(如自然度)缺乏关注[1]。与中国不同,由于西方当代城镇化速度缓慢,环境变迁较小,西方学者很难意识到快速环境变迁带来的场所依恋问题。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讨人们对童年居住地的依恋是否与童年居住环境的自然度有关,以及童年场所依恋是否因环境变迁而影响人们成年后的幸福感,从而为土地管理者提供一种方式来预测、识别和回应人们与场所形成的关系[3],减少居民在拆迁和搬迁过程中因为环境适应性问题带来的心理疾病,提高幸福感。
1 研究背景
1.1 场所依恋
“场所”(place)与“空间”(space)不同,空间是指客观的地理位置和物质形式,而场所则指对某一个体或群体而言充满意义的空间,这种意义是通过人与场所的互动而形成的[4]。“场所依恋”的经典二维结构包括“场所依赖”(place dependence)和“场所认同”(place identity)[5]。场所依赖作为功能成分,反映了一个空间具有支持特定目标或预期活动的特征和条件[6],它对于人们在初次选择某一特定的空间进行互动时具有重要作用。当该空间靠近人们日常活动范围时(如居住地),人与场所的相关互动将增加[7]。随着互动次数的累积,个体不断地赋予这个空间含义和意义,从而使该空间成为场所并使个体具备自我认同感,最终个体对该场所形成情感性依恋,即“场所认同”[7]。因此,“场所依恋”是指人们在不同场所发展起来的情感纽带[8]。
自然环境是场所依恋形成的重要空间因素。这与人们对自然环境的偏好及该偏好所引起的互动可能性有关,但学者对自然环境偏好的起源并未形成统一的观点。一种观点是,在数百万年的进化过程中,人类更熟悉自然环境,因此在生理上能够更有效地接收和处理自然环境中的信息,从而有利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9]。例如,相比建成环境中的人工造型,自然中存在大量的分形模式(fractal patterns),即一种视觉上更容易被人类处理的信息[10]。因此,在自然环境中,人们可以花更少的注意力和认知功能来处理视觉信息,从而有了放松的机会[11]。同时,这种容易的处理过程能够激发人们的控制感和成就感,产生积极的情绪[12]。第二种观点认为,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偏好是社会学习过程的产物[9]。高密度、拥挤的城市环境以及高压、快节奏的城市生活对居民造成了负面的精神影响[13]。而自然环境中丰富的感官刺激(如视觉、听觉和嗅觉)是持续变化的[14],赋予人们温和、宁静和放松的愉悦感受,具备康养效果[15]。这种感官刺激可以增强人们在自然环境中的心理恢复效应[16]。
童年阶段是场所依恋形成的重要时期。童年时期建立的依恋关系有助于大脑微观结构的正常发育以及未来生活中基本信任态度和安全感的形成[17]。6~12岁是儿童探索外界环境并发展场所依恋的关键时期[18]。在此阶段具有较强场所依恋的人群,更容易在日后生活中与新的场所建立情感联系[17]。此外,各个时期的场所依恋相加可以增强人们的自我连续性(self-continuity)[19]。
1.2 场所依恋与幸福感
场所依恋对幸福感的积极影响主要通过以下3种机制:1)场所依恋出现的前提是因为某些空间提供了生存优势[20],这与幸福感应建立在安全的客观环境之上的条件相符合;2)场所依恋提供了对目标的支持和对自我的调节作用[21]。前者可通过场所依恋的定义看出,而后者是由于场所依恋增强了个体的积极情绪并减少了个体的认知负荷。积极的情绪和压力的减少能够有效地支持个体去达成个人目标,从而有助于激发个体的自我满足感并感到幸福[22];3)场所依恋构建了自我连续性。一方面,如前文所述,人们经常依恋于他们认为符合其个人价值观的环境[21],这促进了自我和世界(环境)之间的关联建立;另一方面,通过记忆可以建立自我与过去之间的连续性。两者有利于增强个体对身份的认同,提高幸福感。然而,过度的场所依恋可能危及幸福感,如个体在面对环境变化时无法较好地融入新环境,因此出现焦虑、抑郁等症状,降低个体对生活的满意度[23-24]。
1.3 研究假设
综上所述,场所依恋的形成在儿童阶段较为重要,并与自然环境关联较大。童年场所依恋可以直接影响成年后幸福感,这一影响与环境变化程度间接相关(图1)。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H1:童年居住在自然环境中的农村居民会比住在建成环境中的城市居民具有更强的场所依恋。H2:具有较高童年场所依恋的人群在成年后具有较高的幸福感;H3:较高的场所依恋预示着个体与童年环境具有较强的积极情感联系,因此幸福感与个体童年居住环境变化程度呈负相关。然而,较弱的场所依恋可能有两种不同含义:较弱的场所依恋代表个体与童年场所的联系较弱,因此幸福感与个体经历的环境变化程度无关(H3a);较弱的场所依恋代表个体对童年的场所不满,因此幸福感与个体经历的环境变化程度呈正相关(H3b)。H4:当环境变化程度较小时,个体的幸福感随场所依恋的增强而增强;当环境变化程度较大时则相反。

图1 童年场所依恋与成人幸福感模型Model of childhood place attachment and adult well-being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地选取
浙江省位于长江三角洲地区,省域管辖面积10.55万km2,常住人口5 850万[25]。省内地形起伏多变,西南以山地为主,中部以丘陵为主,东北部是低平的冲积平原。土地利用类型以林地和耕地为主,但建设用地处于快速扩张状态[26],大量居民从农村自然环境迁移到了城市建成环境中。截至2019年底,浙江省城镇化率位居全国第六名[27]。这些特点为研究快速城镇化带来的场所依恋问题提供了基础。此外,不同区域、不同年龄段的人群经历了程度不一的环境变化。
2.2 混合方法论
本研究采用了混合研究方法,包含试点研究、问卷调查和半结构访谈。试点研究是为了检验网络问卷调查的可行性,探讨人们是否依恋童年场所,以及该依恋是否与物理环境(如景色)或者社会因素(如人际关系)有关。问卷调查包含了4个部分。1)受访者的社会人口信息,包括居住城市、性别、年龄、在童年居住地和当前居住地的居住时长。2)童年及当前居住地的4类景观自然度(表1)。“自然度”,即自然元素在场地中的占比程度[28]。本研究首次将自然度和自然度变化(在童年和成年时期)引入调查,并借鉴了杨思程在景观偏好研究中提出的由人工到自然的分类思路[28],将景观类型分为以下4类(图2):①以人工建筑为主;②半建筑半人工绿化;③半建筑半农田;④以原生态自然景观为主。3)场所依恋量表。Williams等设计的问卷常常被应用在场所依恋、娱乐参与以及个人项目等方面[5],并被证明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29],本研究对其进行翻译并增加适当的解释。该量表采用5分制李克特(Likert)量表。4)Tennant等开发的华威–爱丁堡幸福感 量 表(Warwick–Edinburgh Mental Well-being Scale)[30]。该量表涵盖了心理健康中的积极情绪、人际关系满意度和积极心理功能方面,在中国已有相关研究,被证明具有较高的信效度[31]。该量表同样采用5分制李克特量表,以便数据分析。

表1 4类景观类型Tab. 1 Four types of landscape

图2 4类居住地景观类型(从左到右自然度依次上升)Four types of residence landscape (increasing naturalness from left to right)
半结构访谈是指在问卷调查参与者中,选取部分人群进行访谈,用于检测定量结果的有效性,以及解读数据背后的原因和机制[32]。问题如下:您能描述下您童年生活过的地方吗?这个地方给您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什么?您能谈谈对于您小时候生活环境的感受吗?您离开或留在童年环境中您觉得幸福吗?您觉得幸福感程度与环境有关吗?作为成年人,您是如何记得您的童年经历和成长过程呢?
2.3 数据采集与分析
调研于2020年6—7月进行,调查问卷由问卷星平台发布,在微博和微信社交平台上传播。本研究共收回480份调查问卷,剔除未满18周岁的参与者和无效作答,最终有效问卷353份。随后,对所收集数据进行整理和编码,其中居住地的自然度被编码为2、3、5或6(表1),并且计算童年和当前居住地的自然度的差值(0、1、2、3或4),即得到“环境变化程度”。场所依恋的得分借鉴Kaltenborn和Bjerke的分析方法[4],为所有项目的平均分(保留两位小数),且以此为分类依据按组将样本分为弱、中、强3个等级(分别对应1.00~2.33、2.34~3.66、3.67~5.00)。幸福感评估得分依据华威-爱丁堡幸福感量表所推荐的分析方法,为所有项的总和[30]。半结构访谈选取17位受访者,征求同意后对谈话内容进行录音,每位时长为30~60 min。采用主题分析法[33],提取每个问题中聚集程度最高的主题和关键词并进行分析①。
使用数据分析软件STATA 16.0进行定量分析,具体步骤如下。
1)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包括人口分布特征、场所依恋和幸福感得分的平均值以及各等级占比;
2)采用常最小二乘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 OLS)回归模型探索场所依恋的决定因素。回归因素包括年龄、年龄平方、性别、童年居住地的自然度、自然度变化、在童年居住地和当前居住地的居住时长。由于1978年改革开放带来的快速社会经济发展和巨大环境变迁[34],本研究将样本分成青年组(≤42岁)和中老年组(≥43岁),重复以上分析过程,以探索年龄差异。
3)为了解自然度等级对场所依恋强度的具体影响,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4个等级的自然度之间的场所依恋值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性。
4)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个体对童年场所的依恋是否直接影响成年后的幸福感。在此过程中不断加入更多的变量以观察β系数是否保持稳定。并且,使用工具变量(Instrumental Variable, IV)来探索场所依恋和幸福感之间的因果关系。
5)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具有弱、中、强3种场所依恋程度的人群,如何因环境变化程度的不同而影响其成年后的幸福感;并且检验假设H3,即弱场所依恋代表个体对童年场所不明显的情感态度(H3a)还是强烈的负面情绪(H3b)。
6)计算童年和当前居住地环境变化程度的绝对值,并以此为分类依据将样本分成5种变化程度(0、1、2、3、4)。使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在经历相同环境变化程度的人群中,个体对童年场所依恋的强度是否可以调节其成年后幸福感。
3 结果与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在调查问卷参与者(n=353)中,在1978年后出生的占74.5%,女性占55.0%,出生于农村地区的占65.7%,其中有63.3%目前在城市居住;一直居住在自然度(5或6)较高地区的人群占35.1%。参与者对童年居住地的依恋程度较高,平均值为3.89(最高为5.00),弱、中、强场所依恋组分别占6.0%、31.4%和62.6%。虽然居住环境的自然度发生了明显变化(变化绝对值为1.40,最高绝对值为4.00),但参与人群的幸福感较高(平均值为52.03,基于华威–爱丁堡幸福感量表的平均幸福感范围为40~59)。此外,中老年组(平均值为1.67)经历的环境变化程度大于青年组(平均值为1.30),但是前者(平均值为55.51)的幸福感却高于后者(平均值为50.84)。在半结构访谈中(n=17),9人与所有假设一致,5人与所有假设相反,3人与所有假设无关。其中14人的童年生活在农村自然环境中,9人目前生活的环境与童年截然不同。
3.2 场所依恋与自然度的关系
采用OLS回归模型探索场所依恋的决定因素(表2),在总样本中,童年居住地的自然度与场所依恋呈显著正相关(β=0.179,P<0.01),这与假设H1相符。但是,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在童年居住地的居住时长是场所依恋的一个强有力的预测因素。在总样本中,年龄与场所依恋的关系不显著,表明年龄不能预测场所依恋。但是,在区分年龄组后,在青年组中,童年居住地的自然度具有统计学意义(β=0.210,P<0.01),但在中老年组中童年居住地的自然度则失去了显著性。

表2 场所依恋的决定性因素的回归分析Tab. 2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determinant factors of place attachment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4个等级的自然度之间的场所依恋值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性,结果表明随着童年居住环境的整体自然度提高,人们的场所依恋程度也随之增加(表3,图3)。但是,只有自然度最低的环境(自然度=2)和其他3组(自然度=3、5或6)之间的差异才显著。也就是说,一旦场所依恋达到一定的阈值,增加居住地的自然度已不再显著地增强场所依恋。尽管如此,后3组中95%置信区间在平均值附近越来越集中,说明越高的自然度能够产生越稳定的场所依恋水平,即原生态的自然环境对人类的吸引力具有普遍性(图3)。

图3 童年居住在不同自然度地区的样本的场所依恋箱线图Boxplot of place attachment and different naturalness of childhood place

表3 童年居住地的自然度与场所依恋的单因素方差分析Tab. 3 One-way ANOVA of naturalness of childhood places and place attachment
半结构访谈结果表明,受访者在回忆童年居住环境时主要涉及自然环境和活动2个主题。
1)自然环境。除了2位来自城市的受访者,其他受访者关于童年场所的记忆都是发生在户外环境,共有15种。其中主要包含农田(75%)、河流(66.67%)、动物(66.67%)、植物(58.33%)和山(33.33%)等,说明自然环境是场所依恋的重要因素。此外,受访者在描述场景时,童年居住在农村的受访者比居住在城市的受访者的描述篇幅要长2~3倍,说明童年居住在自然环境中的人群对场所的记忆更深刻,因而具有更强烈的场所依恋。
2)活动。所有受访者童年记忆的形成均与在场所内发生的活动有关,常见的4种活动形式为农田劳作(76.47%)、采摘植物(58.82%)、抓动物(47.06%)和河里游泳(29.41%)。这些活动即为人与场所的互动,能够增强人们的场所依恋。
3.3 童年场所依恋与成年幸福感的关系
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个体对童年场所的依恋是否直接影响成年后的幸福感(表4)。结果显示,随着控制变量的增加,场所依恋的系数均表现为显著正相关,且量级无明显变化。此外,IV结果与OLS结果方向是一致的,且两者的量级几乎相同。IV系数的显著性水平保持在5%,表明童年场所依恋和成年后的幸福感之间有很强的因果统计学关系。Kleibergen-Paap值为13.342(>10),说明IV并不弱。另外,Hansen J值不显著,这表明IV不太可能是内生性的。以上结果表明,童年场所依恋可显著提升成年后幸福感。

表4 童年场所依恋和成年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Tab. 4 The independ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hood place attachment and adult well-being
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具有弱、中、强3种场所依恋程度的人群,环境变化程度如何影响其成年后的幸福感。环境变化程度的系数在弱场所依恋组中显著为正,说明弱场所依恋人群经历的环境变化程度与幸福感呈正相关(表5)。考虑在弱场所依恋组中只有20个观察值,结果可能存在极端值的偏差。此外,在中场所依恋组和强场所依恋组中,环境变化程度系数不显著。尤其是在强场所依恋组中,环境变化程度与幸福感之间反而呈正相关,这与假设H3相反。一方面说明,从农村到城市(或从原生态到人工景观)的环境变迁基本是单向的;另一方面说明,弱场所依恋的人的幸福感与环境变化程度的关系更直接,而中场所依恋和强场所依恋的人的幸福感可能受到环境变化以外的因素影响。

表5 环境变化程度在不同的场所依恋程度下对幸福感的影响Tab. 5 The influence of environmental change on well-being under different attachment intensity
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在经历相同环境变化程度的人群中,个体对童年场所依恋的程度是否可以调节其成年后幸福感。当环境变化程度为0~2时,幸福感随场所依恋的增强而提高(表6)。但是在此过程中,随着环境变化程度的增大,场所依恋对幸福感的影响幅度减小,β系数从4.388减小到3.466,这说明虽然童年场所依恋可以提升成年后幸福感,但是较小的环境变迁也足以削弱这种幸福感。并且,当环境变化程度达到最大值时(即为4),场所依恋的系数显著减小到负数,说明剧烈的环境变化程度能够使个体对童年场所的依恋变成削弱其当前幸福感的重要有害因素。

表6 场所依恋强度在不同的环境变化程度下对幸福感的调节Tab. 6 The regulation of place attachment intensity on the well-being under different environmental changes
4 讨论与结论
童年居住地的自然度可以正向预测人们成年后对该童年场所的依恋程度。更自然的居住环境能够唤起人们更强烈的依恋情感,这一点与本研究的假设相符,也与Bow和Buys[35],Scannell和Gifford[36]以及Kim和Kaplan[37]等的研究结果一致。无论是出于前文所讨论的进化论观点还是社会学习过程产物的观点,人们通常偏好自然度较高的场所,从而产生人与场所的互动。随着频繁的互动,人们赋予了该场所更多的个体含义和意义,从而促进了场所依恋的形成和增强。本研究在半结构访谈中询问受访者关于童年场所的记忆时,童年成长于农村地区的受访者更频繁地提到户外活动,且有更强烈的情绪表达,如快乐、自由、自豪感等。因此,这也证实自然环境确实能鼓励更多的人与场所的互动行为和更深刻的个体情感体验,该体验中包含了人们对该场所的个体解读和认同。值得注意的是,当自然度达到一定阈值时,场所依恋不再显著提高,即只要人们的居住环境中存在一定的绿地,不管其性质为人工或天然,人们都能形成较高的场所依恋。在中国人口密度大且城市用地紧张的国情下,这一发现对指导城市规划师优化土地资源分配,同时满足经济开发需求和居民幸福感具有重要作用。
个体对童年场所的依恋可以正向影响成年后的幸福感。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表明,在控制了潜在影响幸福感的变量后,童年场所依恋与成年后幸福感之间存在着显著相关性。此外,为避免个体当前的幸福感可能导致的记忆偏差,从而造成不真实的场所依恋评分,本研究使用IV策略验证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结果仍然支持上述结论,并且排除了遗漏变量和从幸福感到场所依恋的反向因果关系。这一现象与Morgan[17]、De Haan等[38]和Schore等[39]的理论相符,即在童年时期能够建立较高依恋机制的人,其大脑结构发育更加完善且更容易产生安全感,因而在成年后更容易具备对新场所建立依恋的能力,提高对当前场所的满意度,进而增强幸福感。半结构访谈中,部分高场所依恋和高幸福感的受访者表示,他们能够在一个陌生的地方较快地建立归属感。
对童年场所依恋的程度会受童年与当前环境差异程度的调节,从而对成年后的幸福感产生不同的影响。首先,弱场所依恋组的人群随环境变化程度增大,幸福感增高。这表明该类人群对童年场所存在一种明显的负面情绪,并将移居到不同环境类型(自然度)的行为视为摆脱自己所厌恶对象的胜利。这一点在半结构访谈中得到支持,也与De Sa关于巴西人移民到美国后幸福感变化的研究结果一致[40]。在De Sa的研究中,那些对过去场所有消极感觉的女性将此场所视为自己痛苦经历的被动见证人和共犯,进而将成功移民到美国视为从痛苦中的解放。其次,中场所依恋组的人群的幸福感与环境变化程度无关。半结构访谈中,该类人群对童年场所的回忆缺少情感表达,在离开该场所后也很少产生由环境变化引起的心理落差。这可能与较频繁的搬家经历有关,削弱了他们与居住地的深入互动,难以形成较强的场所依恋。最后,强场所依恋组的人群的幸福感与环境变化程度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一方面,个体对童年居住地较强的依恋可以促使其成年后有能力在新的场所建立新的依恋,提升幸福感;另一方面,过度的场所依恋或巨大的环境变化使部分个体主观或客观上无法融入当前场所,降低幸福感。值得注意的是,当环境变化程度达到最大等级(本研究中为4)时,场所依恋越强则幸福感越弱,因为对过去场所具有强烈依恋的人群无法在全新的环境中找到与过去的联系,从而失去自我连续性,并降低幸福感。第三点有助于更好地将利益相关者的价值观和行为纳入土地管理决策过程。在经济发展驱动下的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城市规划设计和管理部门应该适当地保留过去的场所,作为人们情感的寄托和寻根的需要。
本研究中的量表均来源于西方国家,需要结合我国国情进行优化和细分。此外,本研究中的所有数据均为主观数据,未来研究可使用客观的测量方法,如脑电图技术等。最后,本研究的样本量相对较少,对某些地区的代表性不足。但是作为探索性研究,本研究使用混合研究方法,使定量研究中的参与者在定性访谈中解释数据的缘由和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数据解释的偏差。同时,本研究结合我国高速城镇化的特点,首次提出环境变化程度和场所依恋的联系,相关方法和结论为未来研究奠定了基石。
注释(Note):
① 本研究获得英国爱丁堡大学艺术学院伦理审查委员会批准(批准日期为2020年6月11日)。
图表来源(Sources of Figures and Tables):
图1、3由作者绘制,其中图3数据来源于表3;图2由作者拍摄;表1~6由作者绘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