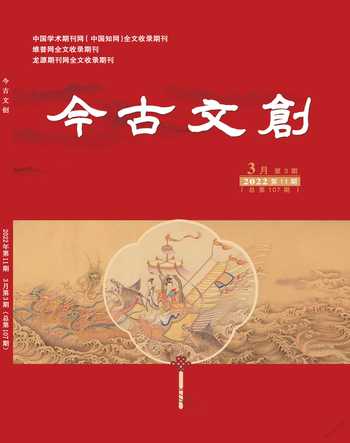民国婚姻小说的 “ 典妻 ” 习俗叙事
2022-03-22孙玥菡
【摘要】 “典妻”是旧时中国社会一种起源甚早的畸形婚姻形态,它历经岁月变迁,虽然封建社会消失,进入现代社会,时至民国时,这种陋俗仍残存社会中,甚至变化出新的形式。众多民国婚姻小说对此有所表现,在各种类型的“典妻”习俗叙事中,心理矛盾扭曲了女人的心灵,社会变化让男人无可奈何,一幕幕生活的悲剧由此造就,体现出彼时社会婚姻观念中传统与现代交织的时代特点。在对此类民俗事象书写中,作家们所透露出的情感态度亦不尽相同,这反映出他们对时代变迁的理解及所持社会立场的不同。
【关键词】 民国婚姻小说;典妻;习俗;叙事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2)11-0028-04
一、古代社会的典妻习俗
典妻是中国旧时的一种特殊婚俗,是指夫家一方将合法妻子典借出去,出让性的权利或生育的权利,以换取某种物质利益的形式。一般而言,出典女子与其原夫仍然具有既定的婚姻关系,但在约定期限内出典女子与承典者之间形成事实婚姻关系。但其还有变形的形式,在维系婚姻关系的前提下,得到丈夫许可,女子还与其他男人存在性的关系,实施性权利的分享与出租。
据社会学家考证,婚姻上的典妻制在中国起源甚早,可能在人类进入单偶婚时代就已出现,发展于秦汉,成熟于宋元,至民国时仍留存民间。出于谋取钱权的利益考虑,丈夫将妻子或明或暗奉献他人以求获回报之事亦时有所闻。
作为古代社会一种特殊的婚姻形态,当儒家思想盛行社会后,典妻即被认为悖人伦理,被视为社会陋俗,而遭官方明令禁止,元明清三朝均有法令对此予以严禁 ①。但在民间典妻习俗却并无绝迹,尤在穷乡僻野之地常有发生,这反映了民间伦理的变通性及其在某种状况下与主流伦理的悖离特点。
在性质上,典妻制近乎买卖婚,但又具特殊性,表现在其婚姻关系带有时效性,出典妇女的夫方与承典者之间通常以书面约定出让期限,当期满后立约失效,出典妇女仍要返归本夫家庭。通常情况下,典妻行为能够达成,出典一方多因家庭生活窘迫无以为继,或丈夫无力承担养家重担,而承典一方或因妻妾不能生育,或因不能生育妻子不容纳妾,或因经济条件局限,只能短期典租女子为妻,借其子宫生育子嗣,以完成传宗接代任务 ②。
宁波地区民间,典妻被形象地称为“借肚皮”,《寿宁待志》记载:“或有急需,典卖其妻不以为讳。或赁与他人生子,岁仅一金,三周而满,满则迎归。典夫乞宽限,更券酬直如初。亦有久假不归,遂书卖券者。” ③出典后所形成的事实婚姻中,出典女子承担的角色仅是生育机器而已。与皆为出资而来买卖婚相比,买卖婚中被买女子可通过生育改变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典婚中出典女子即便生育后,仍无法改变在承典者家中近乎为奴的地位,除非最终被完全卖给承典者。出典期结束后,出典妇女回归本夫家庭中,其地位通常不会因曾为家庭处境改变做出贡献而受到家人尊重,甚至还会因为失贞于他人而受到家人鄙视。
典妻制完全是夫权社会中女子被物化的产物,因而当中国进入现代文明社会后,这种社会陋俗便受到新思想洗礼的知识分子们激烈的批评。
二、民国典妻习俗叙事及类型
上世纪初期,封建王朝覆亡,民国建立,中国进入现代文明社会,一切都处在破旧立新的变革中,封建礼教受到了彻底批判,自由平等的婚姻观念在社会中逐步确立,婚姻形式也发生了诸多新的变化,因处在新旧过渡时期,此时的婚姻形态呈现出新旧交错的特点,一些旧时代的婚姻习俗依然存在,如典妻陋俗亦有残存,甚至还发生了形式上的某些改变。这在民国时期众多婚姻小说中得到了反映,典妻习俗叙事展现了在新时代中女性依然在婚姻中从属丈夫而不得自主的命运,作为特殊时代的留影,其对于研究中国人婚姻的时代变迁具有标本性的意义 ④。就民国婚姻小说中的典妻习俗叙事而言,以其形式作区别,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典人为妻叙事
民国作家笔下,如许杰的《赌徒吉顺》、罗淑的《生人妻》、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等作品,均对彼时乡间的典妻习俗有所表现与描写,其中柔石的小说对这一习俗给妇女带来的伤害揭示最深,最为感人,最具代表性意义。
1930年柔石发表了《为奴隶的母亲》,展示了一个出典给秀才家生儿育女,归家后被先前所生孩子鄙弃疏远的母亲的悲剧。这个隐忍无助的苦命母亲正是民国时期千万乡村母亲的缩影,在家庭中,她从属丈夫,没有任何决策话语权,只能牛马般操劳维持家庭日常事务的运转,她没有意识到在婚姻中不能自主的悲剧,更可悲的是她们被当成物品典出后,既没有做出抗争的努力,亦没有发出怨天尤人的话语,只能一味顺从命运的安排。在为奴做人妻的日子里,她没有对遭受的屈辱怨天尤人,只是对原夫家自己的儿子牵肠挂肚。就此小说的主题,以往文学评论多强调其揭示了旧时代礼教吃人的血腥冷酷的意义,批判封建婚姻将妇女压迫到完全喪失自我的地步,如唐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论及这篇作品时,即认为它“描绘了农村中苦难深重的一隅,具有强烈的控诉意义。” ⑤但评论侧重了它的社会意义,却忽略了母亲的角色设定,忽略了母爱无私而自我牺牲的普遍意义。
出典的母亲最关心孩子的温饱问题,无论是秋宝还是春宝,她都是他们的母亲,她心底有生养他们的欣慰与荣耀。但这种情感懵懂而畸形,因为她在生育权利上不能自主,出典生子是一种屈辱。从法律意义或伦理角度而言,母亲的基本权利受到侵犯,非是传统评论所谓她对自己的悲惨命运麻木不仁,而是她根本就没有生之为人的权利意识,不知道为人的尊严,没有意识到自己生活在不公平环境与婚姻中。新时代的婚姻观念与人权观念,对她而言仍闻所未闻,因此对面对被典当的命运,她只能逆来顺受,勉强地活下去,等待再次见到她的春宝,回到原先的生活中。但是等来的却是春宝的疏远,自己对秋宝不能忘怀的挂念,“在她已经麻木的脑内,仿佛秋宝肥白可爱地在她身边挣扎着,她伸出两手想去抱,可是身边是春宝。” ⑥沦为生育机器的母亲为家庭奉献了自我,却很难再回到从前,她陷于恍惚与痛苦中迷失了自己。
理学的兴起给古代社会妇女带上了一道沉重的伦理枷锁,婚前守贞,婚后从一,夫死守节,贞操成为女子之命。但在民间,尤其在偏僻乡村中,当百姓生活无以为继时,女子的贞操便成为牺牲品。传统社会夫为妻纲,“从夫”是妇德要求,不得忤逆丈夫,丈夫的决定就是妻子的金科玉律。丈夫做出“典妻”决定,虽“守贞”要求与“从夫”原则相违,但夫命如天,几经矛盾心理撕扯,最终许多妇女不得不妥协而“从夫”,牺牲贞操,出借肉体以赚取财资。如货物般出典有性和生育需求之人,女性的美色、年龄便是决定报价的因素。对“借肚皮”而言,多与生育相关,因子嗣关系到家庭财富继承与香火延续。民间传统观点认为,生育与否并生男生女是由女子决定,年龄与美貌决定生育质量,于是相貌端正,尤其是生育过男孩的青年妇女,便在“典妻”中成为抢手货。这也是小说中的母亲能够顺利出典的原因,也是其悲剧的开始。
柔石的小说,通过母亲归家后的自我迷失对夫权专制的残忍进行了控诉,但开头他又写到,丈夫原是插秧能手,日子原本不错,艰难世道让生活日渐贫困,又渐染恶习,最终把结发妻子典了出去,似乎在為其典妻寻找借口,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批判力度。但是小说以其写实性而具有了全面的文化意义,如封建礼教的顽固、启蒙教育的缺失、社会管理的缺位等时代特征,均可从中得见。
(二)典人作妓叙事
民国时,还有一种丈夫把合法妻子当作妓女接客获利的婚姻形式,其与生育无关,但在出让性权利以获取利益上,与典人生育的婚姻形式目的一致,应为一种变形的典妻形式。
1930年,沈从文发表的《丈夫》即描写了一段如是婚姻,年轻丈夫照例把妻子送至妓船上作“生意”,目睹妻子接客生意后,他作为男人的意识觉醒,终将妻子接归乡下。但丈夫所为不是理性意义上的觉醒,他并无意识到典出妻子为妓是对女性的压迫与侮辱,他只是朦胧意识到了作为丈夫靠妻子出卖身体赚钱的耻辱感,“男子摇摇头,把票子撒到地上去,两只大而粗的手掌捂着脸孔,像小孩子那样莫名其妙地哭了” ⑦。作者先有说明,典妻为妓是湘西一种常见的生意,人们习以为常,故而丈夫身份意识的突然觉醒在读者看来奇怪,其突然的转变多少令人惶惑。在小说中,女人们似乎亦无以为妓为非,她们称之“生意”,她们为做生意而来,可以将所赚交付乡下“诚实耐劳”种田的丈夫,以后可以过好日子,女人的节操与尊严问题,她们并无考虑。
宋代始妇女贞节问题即为汉地百姓所重,但在这偏远闭塞的湘西地区民风殊异,道德评判亦异于中原,但小说中丈夫萌生的朦胧羞耻感,还是反映了传统道德对于此地稍显滞后的渗透。这对年轻夫妻没有被作者给予过多心理描写,散文笔法的小说故事性稍弱,奇异的湘西风情叙事吸引读者以猎奇心态阅读完文本后,还是能够感受到作者不动声色中对这一习俗的批判态度。小说中,作船妓的“老七”对回乡下“很为难”,但最终还是随丈夫“回转乡下去了”,丈夫对妻子仍然具有绝对支配权。丈夫的耻辱感之所来还是出自传统道德教化的渗透,而民国社会所宣扬的人权与自由的思想,在这偏僻地区对这些在穷苦生活中挣扎的人们而言,可能闻所未闻。
(三)纵妻交际叙事
民国都市婚姻小说中,许多作品写到丈夫纵妻参与交际,女人出卖色相肉体,周旋在权贵社会中,为丈夫捞取名利之事,这可以看作传统典妻习俗在现代社会的变种。与乡土小说典妻叙事不同,都市女性甘做丈夫牟利工具多出于自我的选择。
张爱玲1943年发表的《第一炉香》中,葛薇龙由曾经的上进学生变为替姑母弄人、替丈夫弄钱的卖笑交际花 ⑧,何尝不是被丈夫典当给纸醉金迷的世界呢?这只是流行于上流社会中的卖淫新形式而已。但这条道路是她的主动选择,非如被出典的村妇般出于被迫与无奈,她在新年夜有言,她是自愿的。没有生活压力,亦无人强迫,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子甘愿出卖灵肉,原因令人深思。
葛薇龙为捍卫所谓的爱情,看似做出了牺牲,但丈夫对她的感情更像是一场游戏,除去同被上流社会边缘而惺惺相惜之外,他最爱的是金钱,并因此放纵了妻子的行为。早在婚前葛薇龙就对爱人的人品心知肚明,故而她的捍卫爱情只能是自我欺骗,她在姑母的圈套里越陷越深无法自拔,沉迷奢华、爱慕虚荣才是其自甘堕落的主要原因。
老舍1935年出版的《阳光》早将彼时上流社会里以妻换利的丑事爆出,道德楷模娶了社交能手,貌似忠厚的丈夫默许乃至纵容妻子以美色去结交位高权重的人物,牺牲妻子以使自己逐步高升 ⑨。老舍的小说揭示了以妻换利的肮脏交易,这正是典妻手段的现代变形。
民国三、四十年,许多城市女子已能接受教育,大家闺秀甚至能够接受高等教育,从而接触更多新时代的现代思想。相对于农村女性,都市新女性在婚姻中已经拥有了一定的主动权,传统贞操观也已然失效,但城市中流行的拜物主义还使得一些人放逐了贞操观,利用色相置换利益,并陷于享乐主义的泥潭中,这是彼时女性意识的新变。但在婚姻中,她们仍然没有独立人格,甚至没有独立意识,不能摆脱婚姻的操控,依然有从夫的理念,为了丈夫而甘愿牺牲自我,成为利益置换的工具,传统伦理在家庭中仍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支配作用。张爱玲、老舍的小说真实反映了其时城市上流社会的婚姻状况,民国时的城市婚姻已经表现出现代观念与传统观念新旧杂糅的时代特点。
三、典妻习俗叙事中作家的情感寄寓
民国时乡村与城市的婚姻状况给了作家们创作小说鲜活的素材,小说中典妻习俗及其现代变形叙事,非为其纯然的构想,而是有着现实依据,在或冷或热的叙事中,作家的情感寄寓亦不尽相同。
柔石为典妻的男人找寻到社会原因,其情性的转变是黑暗时代的逼迫,荒乱时代中苛捐杂税压迫下,正直善良之人没有出路,日子日益穷困,精神亦日渐萎靡,自我麻醉走上了堕落之路,其将妻出典可恨亦可怜。
但柔石非为男子开脱,文字亦没有呈现鲜血淋漓的批判感,特殊的婚姻只是增添了荒诞感,孩子是女子在先后两段婚姻中唯一考量的因素,为了春宝不被卖掉或饿死而同意出典为人妻,归家后又因秋宝而怀念在出典的日子。中国传统婚姻大抵如此,亲子关系远比夫妻关系更重要,作为血脉延续的孩子才是婚姻缔结后家庭维系的重要纽带,否则仅凭两性关系婚姻感情的维系就变得艰难。由柔石小说可见,在婚姻中孩子成了男性压迫女性的重要砝码。为了自己所生的孩子,女性就会成为被动者,而为男人所操弄。孩子是已婚女性的一切,为了孩子女性甘愿付出一切。
传统女性的悲剧性意义由此而来,一个女子可以是为丈夫而活的好妻子,可以是为孩子而活的好母亲,唯独不是为自己而活着的人。柔石站在反封建立场上,在赞美母亲伟大牺牲精神的同时,亦为其性别的不幸发出悲鸣。
沈从文的小说展现了他对乡人婚姻的暧昧态度。沈从文向来以乡下人自居,自称中或许带有自矜、自卑等诸般情感,但他对都市文明的融入无力或抗拒态度亦可从中得见。没有都市归属感的沈从文心系故土湘西,于是在其笔下,湘西的任何事物都笼罩着纯美的情调,但在赞美中亦有对乡土民俗风情变迁的忧思,《丈夫》就是对故乡一种婚姻形态的思索。小说写到,让妻子出去做船妓赚钱是当地农人的自然之事,赎回妻子是丈夫耻辱感的骤然生就,丈夫男权意识有所萌生,非心疼妻子遭人欺辱,或出于對女性尊重而将妻子带归,他觉得丈夫权利的某种旁落。沈从文似乎对丈夫的行为暗持赞赏态度,他所担心的是,女人做了生意,慢慢变成城里人,与乡村离远,学会了城里人才有的恶德,这妇人“也就毁了”。自己的女人说话口音变了,有了城市太太的大方自由,全非“在乡下做媳妇的神气了”,这才是丈夫最大的心病。小说实是立于民粹主义立场的沈从文借以表达他对湘西淳朴民风正在失去的忧心。
张爱玲小说多以客观冷静为特色,通常不涉及道德评判,生活中红男绿女的情事以原生之态尽现笔下,无论两性世界多么混乱复杂,“出轨”“偷情”“夺妻”等诸般情状,她都视之为自然,不做任何掩饰予以描绘。她的小说涉及婚姻问题,既不批判荒诞的婚姻,亦不赞美旷世的爱情,婚姻皆充满了苍凉感与虚无感。在她看来,葛薇龙等人皆为芸芸众生中被情感欲望摆弄的可怜之人罢了,她以自然主义的立场揭露了为男女关系而人皆颠倒的真相。
老舍对上层人物的游戏婚姻持以明确的批判态度,他以小说规劝女子们在婚姻中要自尊自爱,不要甘为丈夫附庸,莫为名利虚荣而沦为男人玩物,成为可悲的牺牲品而不觉。老舍的小说中,甚至融注了因果报应的劝诫味道,他流露出独有的宗教情怀。
可见在明智渐开民国之时,作为社会精英阶层的作家群体接受现代文明洗礼后,其思想状态与心智水平各不相同,对社会的认知存在差异,对婚姻的态度亦各有异,所以对于同样的婚姻习俗或情态,所持情感与观点亦不尽相同,或同情,或惋惜,或默然,或愤愤,落在笔下,亦展现出不同的叙事风格与思想特点。
四、结语
典妻是父权时代的产物,是男人对女人的物化,是一种充满了女人屈辱与血泪的畸变的婚姻形态,时至步入现代门槛的民国时代,这种婚姻陋俗仍残存于僻远的乡村中,在城市中亦变化出一种受都市文化中物质主义至上思想熏染的新形式。作为那个时代婚姻状况的两个极端,其在谋利的形式上是一致的,但却各有其内涵。这种特殊的婚姻形态反映了彼时人伦关系的实际状况,是其时社会思想与道德的具体体现,其中大有意味。而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作家们捕捉了这一社会习俗的存在,出之为小说,在其笔下典妻叙事中,有着他们的时代感受,有着他们对社会的思考、对婚姻的认知,他们的小说亦因此而具有了深广的内涵。所以其小说对于社会学家研究社会发展、民俗家研究婚姻变迁、文学家研究文学嬗变,也就具有了重要的标本性意义。
注释:
①陈顾远:《中国婚姻史》,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10页。
②徐海:《略论中国古代典妻婚俗及其产生根源》,《沈阳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第77-81页。
③(明)冯梦龙撰,黄立云校辑:《寿宁待志校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④刘传霞,石万鹏:《论五四以来典妻题材小说的演变》,《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第101-104页。
⑤唐弢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二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43页,
⑥柔石:《柔石小说精选》,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6年版,第47页。
⑦沈从文:《沈从文小说全集(卷十)》,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89页。
⑧张爱玲:《张爱玲全集·倾城之恋》,北京十月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
⑨老舍著,舒济选编:《老舍小说经典(第二卷)》,九州出版社1995年版,第365页。
作者简介:
孙玥菡,山东青岛人,上海大学社会学院2019级民俗学专业研究生。
15625017053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