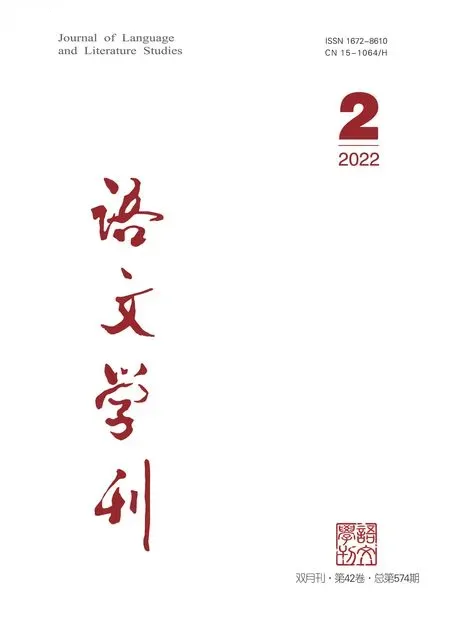从爱德华·萨义德《最后的天空之后》看巴勒斯坦问题
2022-03-18吴昊汪依然
○ 吴昊 汪依然
(四川外国语大学 东方语言文化学院,重庆 400031)
爱德华·萨义德一生著书立说,为巴勒斯坦事业奔走呼号,充分展现了自己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勇敢担当。他认为“巴勒斯坦人有权表现他们自己,有权为自己说话,有资格叙述具有它自身的价值和独特性的历史”。他在作品中用另类的叙述向读者描述了巴勒斯坦难民流亡的困苦与他们执着抵抗的决心,号召巴勒斯坦人以“记忆”抵抗“遗忘”。以他为代表的巴勒斯坦流亡知识分子也透过书写,为塑造民族认同做出努力。他们的流亡书写抒发了巴勒斯坦人的哀怨,同时也成为支持他们奋斗的力量。
一、爱德华·萨义德——巴勒斯坦之音
爱德华·W·萨义德(Edward W. Said),于1935年在三教圣地耶路撒冷出生,至2003年因白血病离世。他是在美国的巴勒斯坦人,后殖民论述的重要奠基者,颇具影响力的文学与文化批评家,在国际上极负盛名的学者。萨义德在早年就读于阿拉伯国家的西方学校,后前往美国留学,并在那里获得其学士、硕士与博士学位,之后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作为一个流亡的公共知识分子,萨义德的一生都处于漂泊与矛盾之中,他介于不同的文化与历史之间,从未真正感觉到安定,也从未拥有过真正的归属感,不论之于阿拉伯世界还是美国,他都被置于一个尴尬的境地。但正是这样“格格不入”的边缘化处境,使萨义德既属于“局内”又属于“局外”,为他提供了流亡者所具备的独特“双重视角”,不受权势者的威慑与主流文化的挟持,时刻保持着清醒的批判意识和独立的思维方式,为作品融入更加深刻的政治思想。
在1967年之前,萨义德一直都单纯地进行文学创作,是一个纯粹的学院派人士,不愿从学术研究向政事活动跨越。但在1967年战争爆发后,更多的巴勒斯坦地区被占领,巴勒斯坦人在以色列的高压下长期过着艰苦不堪的生活,而世界却对这些历史漠视甚至误解,萨义德无法对此坐视不理。时任以色列总理的梅厄夫人也曾发表过“没有巴勒斯坦人”、称其“不存在”的言论,这一说法使萨义德十分愤怒,他下定决心,必须去否证这种荒谬的论断,他要清楚地讲述出一段真实的、关于“失去”与“剥夺”的历史。自此,萨义德便将文学与政治结合,为巴勒斯坦民族解放事业而不断奋斗。关于写作,萨义德并不认为这是一种“退让的努力”,相反,他认为写作能使他最为直接地参与政治,是对在现实社会中无力参与政治实践而采取的沉默态度的一种反抗,他通过大量著述、发表文章和评论、在媒体平台上发声等,积极地“以人文介入政治”,抨击殖民、帝国主义,并向世界展示真正的巴勒斯坦。
萨义德一生中创作了极为丰硕的学术作品,如其享誉世界的重要著作《东方学》,开启了他的后殖民主义研究历程;《知识分子论》是萨义德对知识分子角色的思考,认为知识分子应提升意识、承担责任、谋求公正。而萨义德作品的另外一个关注点则在于对巴勒斯坦问题的研究,《巴勒斯坦问题》《报道伊斯兰:媒体与专家如何决定我们看待世界其他地方》《最后的天空之后——巴勒斯坦人的生活》被认为是萨义德“巴勒斯坦问题三部曲”,他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研究在国际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改变了世界看待巴勒斯坦的方式。爱德华·萨义德这位“巴勒斯坦之子”,不惧权威,言人之所不敢言,在边缘审视,为巴勒斯坦发声。
二、《最后的天空之后》——巴勒斯坦人的困境与反抗
萨义德期望能够以一种巴勒斯坦叙事来取代以往的亲以色列叙事,这也是他一直致力于的事情。《最后的天空之后——巴勒斯坦人的生活》出版于1986年,不同于萨义德以往的作品,这本书不仅包含了他政治上的思考、关于时政的评述以及自传性的片段,还配有大量的瑞士籍摄影师吉恩·莫尔拍摄的巴勒斯坦人生活的照片。该书既不是一个连贯的故事,也不构成一篇政治论文,而是采用一种断续的、非传统的表现形式来呈现真实的巴勒斯坦人,这也与巴勒斯坦人生活中混乱、流散但有力量的特点相契合。萨义德虽然是巴勒斯坦人,但是他已加入美国国籍,并长期在“远方”写作,仅有几段短暂的回归经历,所以他并未亲身经历过“创伤”。吉恩·莫尔的图片对于真正经历磨难的巴勒斯坦人来说并没有什么特殊意义,但对于萨义德来说却是深深的震撼,它们的确是沉默、静态的,却是真实且有力量的。这些黑白颜色的照片与新闻里常见的、似乎固定化了的关于巴勒斯坦的“暴力”“血腥”的恐怖画面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而后者却并不是巴勒斯坦人的“真正图标”。萨义德说:“写作这本书的全部目的就是要迎战困难,否认这种对巴勒斯坦人的习惯性简单甚至有害的表现,然后代之以更能够捕捉巴勒斯坦人复杂现实的描述。”
联合国大会在1947年11月29日通过了第181号决议,即分治决议,规定巴勒斯坦在1948年结束英国的委任统治后建立犹太国和阿拉伯国。阿拉伯民族和犹太民族的战争在随后爆发。1948年,以色列建国,“独立战争”开始。次年8月,近两千年来处于离散状态下的犹太民族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占领了西耶路撒冷,开始“重建家园”。但是,巴勒斯坦自此再也无权左右自己的命运,实现民族独立和建国至今遥遥无期。在持续的暴力冲突中,以色列执行“民族清洗”的战略需要,对在当时境内的巴勒斯坦居民进行大规模的血腥屠杀和暴力驱赶,最具代表性的“罪证”有“代尔亚辛”事件以及吕大城的大屠杀事件。武装战争摧毁了五百多个巴勒斯坦村镇,巴勒斯坦人被迫离开故土、远离家园,成为分布在以色列的“二等公民”以及规模庞大的分布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约旦、叙利亚、黎巴嫩、埃及等周围阿拉伯国家甚至世界其他地区的“难民”和“流亡者”。
萨义德在《最后的天空之后——巴勒斯坦人的生活》中描绘了巴勒斯坦人的流亡之痛:“他们从一个地方穿越到另一地方,成为不断迁徙的任何地方的移民,或者混血,但却从不属于这些地方。”他们处于连续的流离失所和迁移不安之中,“不论巴勒斯坦人身处何方,都不是在他们的巴勒斯坦,因为巴勒斯坦已经不复存在”。巴勒斯坦已经沦为一个离散和始终在迁徙的民族,“离散”成为这本书也是巴勒斯坦人生活的关键词汇。他们被剥夺了建立在自己的民族和国家形成之上的基本身份,“恐怖分子”“名单上的名字”“非犹太人”……都是巴勒斯坦人被贴上的标签,不论他们在东道国是否从事着有名望的职业,也永远是那里的“外来者”。萨义德也有身份的危机和焦虑,他选择在创作中建构那片他渴望的“家园”,但他内心中的“不安全感”始终存在,比如旅行时经常携带太多用不上的行李,而这种古怪的“过量”和“失衡”也恰好显现在巴勒斯坦人团体内部,在书里任何一张带有巴勒斯坦人房子的图片中都可以发现,他们会在“餐桌上摆放提供给客人的过量的食物”,在“桌上摆设过多的照片和物件”等等,由于过量,有些东西总是缺少。而这一切“相似的失衡”和互相感染的“不安全感”,都在说明它源于也象征“离散”。
萨义德将本书的最后一章命名为“过去与未来”,他似乎在巴勒斯坦过去的“破碎”与“不平衡”中辨认出“坚持”与“希望”。巴勒斯坦人在艰难的处境中自我维系生存,这不失为是一种“抵抗”。书中展现的“安曼巴喀难民营的裁缝”“比尔泽特大学实验室的学生”“约旦大学医院的儿科医生”……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里专注于自己的工作,这些工作虽然相对封闭且受限,外部的环境还萦绕着混乱和不安定,却是巴勒斯坦人适应能力最好的佐证,他们在目前没有任何解决方案的困境中找到了从自身生出的动力。这些人在经历过巨大的劫难和创伤后,仍有勇气和决心直面世俗的生活,它正代表了巴勒斯坦人具体的、遍布的、无法摧毁的力量。萨义德毕生都在期待巴以之间实现和平,他曾经针对巴以长期以来的冲突提出了“一国两族”的构想,设想两国今后基于平等独立而非对立敌视存在,时至今日,这种构想仍然是一种乌托邦,巴勒斯坦的未来仍没有答案,但他的所思所述确为世人描绘了被忽视的巴勒斯坦民族形象,也改变了巴勒斯坦以往被看待的方式。
三、流亡书写的重要意义
1948年的战争将巴勒斯坦从曾经的“天堂”变成“失乐园”,巴以双方的争斗不止于武力层面,还涉及文化与心理等更深层面。以色列建国之后,为了实现对原巴勒斯坦民族土地的彻底掌控,选择对巴勒斯坦实行一系列“除名毁忆”的政策,力图抹去巴勒斯坦民族之前存在过的印记,彰显其建国的合法性。如更换新地名、《圣经》考古、全境造林、毁坏巴勒斯坦文献等,以色列有计划地清除巴勒斯坦的历史。以色列设立的“地名委员会”对疆域内的地方、河谷、道路等实施“希伯来化”计划,将阿拉伯名字翻译或替代为希伯来名,更新后的犹太化地名加深以色列人与故土的历史情感。《圣经》考古作为以色列寻找历史根源的纽带,在其建国初期具有极高的地位,但以色列的这种考古事业在“发明”古代以色列的同时,却对巴勒斯坦的历史保持“沉默”。以色列还在境域内实行大规模的造林行动来纪念纳粹屠杀中的逝者,也通过改变地貌、清除原有的橄榄树、大量种植代表犹太民族形象的松树,来消除巴勒斯坦文化的痕迹。此外,以色列还炮轰了拥有大量巴勒斯坦历史与文化资料的机构,将大量有关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的资料封存,并一再延长档案资料的保密期,以防影响以色列的形象和外交。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记忆战争中,巴勒斯坦人并没有屈服。在以色列种种的驱逐、压制之下,巴勒斯坦人已经不再拥有实体上的“家园”,他们的身份仅仅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而基于1948年大灾难的集体记忆,则逐渐成为他们排遣思乡之愁、流亡之苦、实行文化抵抗和增强民族认同的重要手段。记忆不灭,抗争不止。流亡的巴勒斯坦人用记忆来抵抗,用记忆来维权。他们将以色列庆祝独立的第二天作为“灾难纪念日”,用熟悉的名称命名难民营,难民们在其中聚居,他们保留着旧的房契、钥匙以及社会习俗,像在萨义德的办公室中就有着巴勒斯坦的镀金地图,他们以此证明着对故土的所有权。而时间流转,巴勒斯坦人意识到仅靠这样延续记忆是不够的,在这记忆抵抗的过程中,便催生了一大批巴勒斯坦流亡知识精英,他们致力于用历史书写来保存记忆,再现民族创伤。
爱德华·萨义德就是这类流亡知识分子中的杰出代表,他有着浓厚的巴勒斯坦情结,被誉为巴勒斯坦在西方的代言人。他一生的著述大多围绕巴勒斯坦问题,巴勒斯坦人的真实处境与诉求也是由于他才没有被掩盖。不止萨义德,还有本书开篇引用的诗句“在最后的国境之后,我们应当去往哪里?在最后的天空之后,鸟儿应当飞向何方?”的作者——著名巴勒斯坦民族诗人马哈茂德·达尔维什,他一生漂泊,几乎他创作的全部诗歌都在激励着巴勒斯坦人抵抗压迫。书中还提到了中篇小说《阳光下的人们》,它的作者格桑·卡纳法尼同样是一位巴勒斯坦斗士,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千千万万有着悲惨遭遇的巴勒斯坦人的影子。正是这些知识分子的流亡书写,支持着巴勒斯坦人的抵抗,使得受难记忆得以保存,难民的遭遇得以展现。可以说,流亡书写作为一种“再现的力量”对于保存创伤记忆、完成历史书写、维系民族认同具有重要意义。
四、结 语
《最后的天空之后——巴勒斯坦人的生活》作为萨义德“巴勒斯坦问题三部曲”之一,真实、另类地展现了巴勒斯坦民族的流亡之苦,它是“在重建巴勒斯坦人经历和生命中产生的一种政治需要”。而萨义德等人的流亡书写也为世界了解巴勒斯坦问题做出了巨大贡献。直至萨义德逝世,这位伟大的文化批评家都没能看到他一生热衷的巴勒斯坦问题得到解决,但他独到的见解与开放的思想为世界留下了一笔珍贵的“民族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