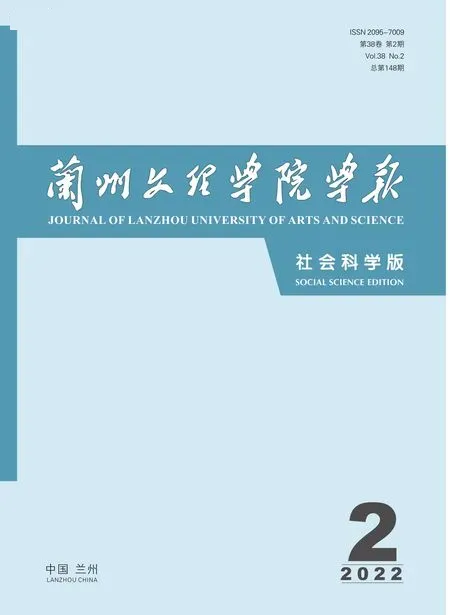生命、爱情与乡土质解
——论严英秀小说的三重主题取向
2022-03-18田文倩
田 文 倩
(新东方兰州学校,甘肃 兰州 730070)
在中国当代藏族作家的汉语文学创作中,严英秀是一位独具特色的知识分子女性作家。她工于小说,2011年入选“甘肃小说八骏”。但作为大学教授,她涉猎广泛,游走于诗歌、散文、评论等多种文体之间,成就不凡。新世纪以来先后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纸飞机》《严英秀的小说》《一直很安静》《芳菲歇》,长篇小说《归去来》,散文集《就连河流也不能带她回家》《走出巴颜喀拉》,同时还出版了评论集《照亮你的灵魂》等,获得过省内外多个文学奖项。
严英秀是甘南籍的藏族作家,她的家乡舟曲气候温润适宜,被域外人士称之为“藏乡江南,泉城舟曲”。严英秀虽然出生在这里,但成长中的大多时光是在城市,成为现代城市中少有的藏族女性作家。虽然她没有游牧、草原生活的经验,但藏族文化“胎记”却深深烙印在她的心中,使得她的作品处处渗透着藏文化的气质。新世纪以来,除了评论和随笔外,小说和散文成为她书写的两大文学体裁。受藏文化熏陶和都市生活经验的影响,她的小说形成了明显的三重主题取向:一是她对生与死的浪漫“轻构”;二是她对都市女性的爱情书写;三是她以乡土单元“家”为聚焦点的知识分子命运的关照,这三类主题呈现了其新世纪以来小说创作的基本特征。
一、“灵魂不灭”与“生命轮回”的生命书写
生命书写既是文学的本能,又是文学的重要方面,文学只有关注生命,方能呈现出它的厚重。受藏文化中“灵魂不灭,生命可以延续持久”[1]和“灵童转世”等观念的影响,新世纪以来,阿来、万玛才旦、次仁罗布等作家始终秉持藏文化中“生命不死可以再生”的价值观来看待生命、书写死亡。对这一生命观的呈现也成为严英秀小说主题的一大取向。藏地境域中的出生、藏文化胎记,使得她对生命的书写自然回归到了藏文化的生命价值观中。
对于生命,佛教文化认为:人不仅有一“生”,而且有无数循环之“生”,“死”是轮回中“生”的“中转”,人的生命按出生方式分为胎生、卵生、湿生、芽生这“四生”;生存的环境分为:天界、空界、地界这 “三界”;死后的去向又分为可乐、不可乐、苦乐交融的“三途”,依据众生在尘世中所造的业力牵制,在三途、四生中无休止地上演生死轮回。当代藏族作家的汉语小说中对生命 “转世轮回”的文化理念给予了不同的理解和表达:阿来《云中祭》中那些不死的灵魂,《群蜂飞舞》中转世灵童的寻访,次仁罗布《放生羊》《红尘慈悲》《奔丧》《界》中那些救赎的生命,万玛才旦《嘛呢石,静静地敲》《气球》中轮回转世的生命,《我想有个小弟弟》等小说中期待的生命等都不同程度地思考了灵魂与生命的相关问题。
深受藏文化的熏陶,藏传佛教文化中“灵魂不灭”的生命观,较早地注入了严英秀的血脉中,成为她理解生命和书写生命的主要方式。从她的评论集《照亮你的灵魂》中可以看出,她不同程度地领悟了阿来、央珍、万玛才旦、尼玛潘多等多部汉语小说的生命叙事经验,并加以不同的书写和评说,这无疑拔高了她对生命的领悟力度。
自然灾难、家庭悲剧等都构成了严秀英小说的生命书写谱系。2010年8月8日,她的故乡江城遭遇了特大山洪泥石流之后,多少家庭妻离子散、人畜瞬间消失、房屋转瞬倒塌,面对如此意外且真实的自然罹难,作家应该怎么办?当然严英秀不是人类灵魂的救赎者,但她仍然无法释然荡涤心境的任务,她深知用文学作为心理的补偿并非是宣泄,同样是慰藉。因此,她的小说《归去来》《雨一直下》《雪候鸟》《玉碎》等别开生面地书写和表达了死亡的悲剧与对重生的期许,尤其是以藏传佛教文化为理念,对死亡进行了诗意化的“轻构”,使其充满了“重生”的期许。
中篇小说《雨一直下》中,作者对一大批遇难的灵魂进行了诗意化的书写,一位来舟曲域外朋友黎帆失踪,当大家都陷入悲痛时,藏族阿妈说黎帆已经投胎转世,前天夜里托梦给她,谢她日夜念经为他超度,现在他已得新生。梦醒后等不到天亮,藏族阿妈就去离江城30多公里的大寺院里点灯拜佛,为其祈祷重生,然后满载活佛转世轮回的生命确证结果,奔赴到遇难的地方,告诉那些失去亲人的悲痛者:“遇难者已经转世,并且是男性。”[2]藏传佛教认为生命的自然消亡,意味着旧的生命结束和新生命重生。《雨一直下》借这一价值观书写了生命的死亡与重生的到来,对沦陷在故乡所有不幸的生命而言,便是去向“来世”,对所有悲痛者而言便是心灵的“慰藉”。
在小说《手工时间》中,杜芮与丈夫之间存在长时间的情感隔膜,一次意外怀孕,给这个冷漠多日的家庭带来了无限的阳光,夫妻之间有了诗意般的浪漫。高龄的夫妇呵护着肚子里蠕动的小生命,杜芮心中也滋生出将要做母亲的期待,可最终未能如愿以偿。这个小命未出世又离去了,在情感最艰难的时刻,夫妻二人彼此给予理解和包容。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当他们慢慢走出了没有新生命到来的“绝望圈”之后,又一个新生命到来了,这个生命便是第一个生命的重生,依照作者的构思意图,那个失去的“旧生命”带走了孕妇胎体里所有的毒瘤和原罪,第二个新生命便会安然无恙地降临到这个家里。
热爱生命是人的天性,拒绝死亡是文学和文化共同的“终极关怀”。就像云格尔所说:“每一个生命的经验均以死为方向,这乃是生命经验之本质。死乃是一种形式与结构,我们唯有在此形式与结构之中才被给予生命。”可以说,书写生命必然要书写死亡这个沉重的话题,但严英秀以藏文化的生命观“轻构”死亡的沉重与悲痛,对“生命过程”进行诗意化的表达,形成了其小说独特的气质,这样的书写,使其小说充满了东方悲剧的审美韵味。
二、被撕破的爱情书写
在中国文学中,女性作家写爱情似乎体现着一种合理性与话语权。爱情是旧而又旧却永远不旧的话题,中国式“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爱情开场在经历了“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的礼教限制,到梁祝化蝶的团圆之后,终于焚烧在黛玉书稿的灰烬里,其间或也有“西厢”“牡丹”“才子佳人”大团圆式的结局,都成为千古流传的爱情佳话。在中国古代社会乃至民国三十年里,爱情成为青年男女反抗旧社会的砝码。在新时代里,被剥夺了数千年爱的权利失而复得,这让她们手足无措,爱上了爱情本身,时常陷入爱情的深渊,不能自拔。总之,爱情是中国现当代女性作家无法绕开的文学主题之一。中国当代女性作家大多通过书写爱情来找回女性的“主体性”与“话语权”,也赢得了读者对女性群体的关照。
在严英秀的小说创作中,爱情成为基本主题。她对不同代际的女性爱情有着细致入微的观察和书写。她所建构的爱情故事,并不是“空穴来风”“纸上谈兵”,她对现当代女性作家的爱情经验有着不少的借鉴,这主要体现在她对新型都市少女的爱情、都市成人的婚外恋、成人恋的书写。
严英秀给大学生讲授中国现当代文学20多年,对现当代文学作品如数家珍,自然也对现当代文学作家的叙事手法有所借鉴。打开她的评论集《照亮你的灵魂》就可以发现,她对三毛作品的痴迷。她说:“三毛写父母之爱的名篇《背影》,选取了父母艰难独行的背影作为抒情的泉口,字字融注了父母对女儿苦难的痛惜,句句包含了女儿对父母的感恩和深情。”[3]她将三毛的亲情书写方式移植到散文《天之大》中,写出了自己的失母之痛。受张爱玲、霍达、张洁、林白等女性作家书写爱情方式的影响,她书写出了“70代”知识女性在社会变迁中的爱情轨迹。这主要表现在《纸飞机》《沦为朋友》《被风吹过的夏天》《苦水玫瑰》《自己的沙场》《一直很安宁》等作品中,她如实地讲述着大学校园里鲜为人知的爱情故事。从中可以看出她所关怀的是女性爱情,能感受到那些看似美好的爱情在现实变迁与伦理规约中最终不欢而散的悲剧。
《1999:无穷思爱》写的是20世纪80年代里发生在大学校园里一对师生爱情。女学生粟爱上了老师桑,爱情让粟在桑的面前既是学生又是女友,在日常交往中,粟发现才高八斗的桑是个自私的伪君子,她后来离开了桑。在曾经的大学生活中,叙述人“我”看到了大学女友个个在爱情中的挫败,而十年之后,当我再次回味曾经美好的爱情时,感觉充满了无限的伤痛,在这样的伤痛中,那些女性艰难地走到了今天。在小说《纸飞机》中,大学生阳子迷恋上了年轻的男老师剑宁,但是面对剑宁和睦的家庭,阳子只好将自己的爱埋在心底。后来剑宁因出轨导致了家庭的解体,阳子在初吻中杀了剑宁。在小说《自己的沙场》中,苏笛因为大学时代一场刻骨铭心的初恋深受伤痛,几乎失去生活的勇气,在悲痛绝望的低谷生活中,她又爱上了一个在文字里认识五年的男性作家陶一北,相处了一段时间后,苏迪发现她如梦如痴的爱在陶一北那里只是打情骂俏而已。小说《玉碎》中的小姑被大学男友抛弃之后绝望地选择了跳河自尽。诚如刘巍所说:“女人最大的弱点就是爱,太需要爱也太容易爱人。爱在女作家那里常以救世主的身份出现。拜伦说爱情是女人的整个生命,尼采也讲:“女人对爱情是整个身体和灵魂的奉献。”[4]严英秀通过撕破爱情的书写,来关照都市女性的命运沉沦。但她小说中塑造的那些敢于追求爱情自由、敢于反抗男权地位的女性(比如阳子),无疑代表了“70代”女性对世俗社会的不妥协。
综观严英秀笔下的爱情,她是通过以道德和生活的现实来书写爱情的成败。避开文学世界,我们从今天解构的家庭和大学校园里那些爱得死去活来却最终万念俱灰的结局中得知,决定爱情成功的几率不是你爱得有多深,而是道德规约、现实生活,因为人尤其是女人要必须“止乎礼”、必须回归现实。
三、知识分子生活的乡土空间书写
郑斯扬说过:“乡土文学是百年来中国文学的重要成就,这一点已经成为共识。”[5]从乡土文学表现的主题看,中国最早的乡土文学可以追溯到《诗经》诞生的年代,乡土文学表现的是离别与送别、闺怨与思乡、乡土的裂变、诗人作家的乡井意识等等。从鲁迅、王鲁彦等作家起,乡土文学更多的回归到了“生育问题”“儿女情长”“夫妻关系” “家庭”“家园”等话语圈中。新时期以来,迟子建、铁凝、王安忆、孙惠芬、林白、马金莲、李娟等作家创作了足够分量的乡土文学。而这些乡土文学把男权、性别话语、家庭、生育、生命、婚姻、爱情、伦理、女性的理想等不同的议题引入到乡土写作中,在读书界兴起了一阵风浪。严英秀把对此的感悟和经验撰写在评论集《照亮你的灵魂》中。
严英秀出生于甘肃南部的舟曲藏地,她从6岁学汉语(之前用母语与家人交流),10岁出头便离开故土,从此也就离开母语环境进入汉语“世界”。与生俱来的文字敏感较早地成就了她,她20出头便发表诗歌名作《独守苍茫》,20世纪90年代末大学毕业之后任教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受巴金、沈从文、林白、铁凝、池莉等中国现当代作家乡土经验的写作启发,她把目光更多地聚焦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家庭结构中,并且很自然地回归到了她自己工作生活过的相对封闭的大学空间中,并以女性乡土经验(家的意识)、藏族文化的价值观关注生活在甘肃乡土境域中的知识分子的命运变迁。这自然与巴金的《寒夜》,沈从文的《八骏图》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她的中篇《一直很安静》《遇见》《纸飞机》等小说,在写普通高等学府中知识分子的家庭矛盾时,更多地关注到了知识分子外遇、出轨、死亡、家庭的解构,以及离婚、破镜重圆等,以此聚焦了“家庭”这一乡土结构中的人心和人道。
在中篇小说《一直很安静》中,作者对高校知识分子诗人高寒给予了无限的同情,高寒因以写诗每每获取稿酬而惹得别人眼红,尽管院系办公室主任对其藐视,但高寒还是保持了自己的个性,安心做着自己喜欢的事。作者对焦一苇也给予了生活的关怀,他的爱人去给学生补课时不幸遇事,这个备受学生喜欢的先秦文学老师,因为妻子的瘫痪,生活跌入了低谷,后来迫不得已离开高校,去到一个闲散的单位照顾生活不能自理的妻子。焦一苇的形象是新世纪以来中国男性知识分子的典范,是作者所追求的具有“内在美”理想男性人格的化身。
在《一直很安静》中,作者捕捉到知识分子复杂的心理矛盾与孤独怪癖的性格特征,详细书写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浮躁心态与精神焦虑。在这篇小说中,作者试图追问大学校园里的安静意味着什么?如何才能做到真正的“安静”。小说中的高寒因为高龄单身的生活困苦,成为徐导等人的笑柄,作者给予他的人性关怀便是“找伴”。费孝通说过:“全盘的生活教育只能得之于包含全盘生活的社会单位。这个单位在简单的社会里是一男一女的合作团体。”[6]正如评论家叶淑媛所说:“文学要深入生活,必须要以真诚的态度凝视并用心灵感悟和发现现实人生。现在的文坛,热心热点题材,比如商场、官场、情场以及隐私揭秘等等。这种热衷当然有道理,因为生活本身提供了这种素材。”[7]。显然严英秀小说更多地关注到了高校这个社会单位中知识分子的人事生活。
小说《一直很安静》中,作者通过乡土社会的基本生存结构思考当代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对于那些在大学里受到冷漠和歧视的知识分子而言,哪里才是他们最理想的安身之地?作者在《一直很安静》里书写的人生困境,似乎在小说《可你知道我无法后退》中得以缓解。这个小说中的娜果,上有体弱多病的娘,下有小升初的女儿,但她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读研究生。小说更多地展开了对娜果的家庭叙述:她青梅竹马的丈夫杀了人,判了死刑,她唯一的弟弟也赔上了命,她独自一人支撑着这个家等。在后来的读研生活中,出现了貌似跟她很般配的罗有,但是从天而降的张教授却与娜果结成了半路夫妻,娜果也因此调入大学编辑部,重新开始了她的幸福生活。对于这个知识女性,作者赋予的是藏文化情怀和基本的生活关照。我们可以看出娜果的生活转折中,学位并不是关键,而恰恰是与张教授结合后组建的家,给她寡居多年的悲伤生活带来了阳光。
可见,严英秀对知识女性赋予的乡土生存经验是——女性必须依附于男性,女性必须有圆满的“家”,否则女性永远是漂泊者。这也就印证了刘巍所认为的“寻夫,物质家园”[4]92之说。刘巍认为:“‘家’不仅展示了乡土与传统的诗意,更以贴切的概括形式,将中国想象成有悠久历史的泱泱大国,它的苦难、它的文化优势——凝聚成可感的艺术造型”[3]92。可见严英秀的知识分子乡土生活空间的书写,对中国知识分子如何走幸福之路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
总之,严英秀是一位有情怀和有深厚乡土经验的女性作家,她对中国乡土生活、礼制秩序有着独特的见解。她自己曾说过:“在一个满目疮痍的世界里,谁能够独善其身?中国男权制度不仅仅是女性所要致力于批判和消解的目标,它在严重压抑和窒息女性的生存和发展的同时,也压抑和‘窒息’着男性的生存和发展。”[7]严英秀是大学教授,又是知识分子“70后”女性作家,这样的生活境域与乡土观念逼现出她对都市爱情的书写和对知识分子命运的关怀。同时她把藏文化中慈善的普世情怀与中国当代文学的爱情和女性乡土写作经验有机结合在一起,建构了她的精神图谱与都市写作套图,从她建构的缓慢叙事工笔及浪漫的语言风格中,可以看出新世纪民族小说所抵达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