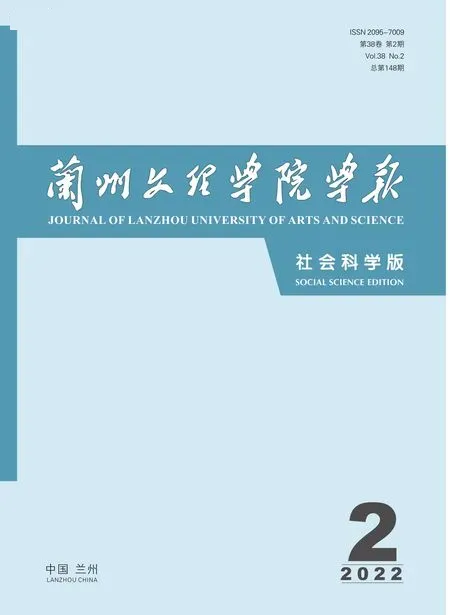论严英秀小说中的家庭伦理书写
2022-03-18朱永明
朱 永 明
(兰州文理学院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新世纪以来,在益希卓玛、完玛央金等女作家的影响下,藏族文坛上出现了央珍、梅卓、严英秀、扎西措、何延华等一批优秀的藏族女性作家,她们在各自的小说创作中融入了不同的地域文化风格,试图在同一民族文化族系中实现超越。梅卓小说以民族民间文化为主要取材对象,凸显了其小说的传奇性与生态观;何延华、扎西措等作家,更多地将童年记忆与新时代扶贫攻坚的主旋律有机结合在一起,努力凸显新时代党的阳光政策关照下藏族牧民所走的致富之路。相比之下,严英秀的创作更多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她的小说将传统文化与藏族文化有机结合在一起,凸显了新世纪藏族汉语小说与多元文化水乳交融的多向叙事。
严英秀是一个地道的藏族作家,出生于中国西部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汇地带的甘肃南部,她的家乡气候温润,被域外人士称之为“藏乡江南,泉城舟曲”。严英秀从6岁学汉语(之前用母语与家人交流),10岁后离开母语环境接受汉语教育,与生俱来的语言天赋较早地成就了这位藏族女作家。她20出头便发表了高水准的诗歌《独守苍茫》产生了不凡的影响力。20世纪90年代在求学生涯中受到三毛、琼瑶等作家影响,开启了小说创作。新世纪以来,她在小说、散文、评论等多种文体创作中取得了显著成效。先后出版中短篇小说集《纸飞机》《严英秀的小说》《一直很安静》《芳菲歇》和长篇小说《归去来》等,散文集《就连河流也不能带她回家》《走出巴颜喀拉》,评论集《照亮你的灵魂》。2011年入选“甘肃小说八骏”,获得过省内外多种文学奖项。
严英秀的家乡在甘肃南部的舟曲,她离开故乡之后,并没有完全背弃故土,常常游走于故乡与省城之间,将乡土伦理观念融入到小说创作中,努力强化小说的传统文化意识,尤其是小说中的家庭伦理书写,对“后乡土时代”出现的“空巢”“悖理”“孝亲文化的日趋式微”[1]等家庭伦理道德滑坡趋势具有一定的“疗救”性作用,同时也对和谐家庭的建构具有一定的启示性意义。
一、“齐家”及“家和”意识的强化
家庭是中国乡土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是乡土社会的组合群体。家也是人个体生存和活动的空间。中国民间所讲究的成家、有家、家庭等与“家”有关的生活群体构建起了国家,因此,可以说“有国才有家”“保家为国”等,在此基础上,“祖国情”也就自然生成了。中国乡土社会认为有了家就有了祖宗、有了尊老爱幼的长幼秩序、有了兄弟姐妹情同手足的血缘情结,由此产生了生离死别等悲欢离合的人情世故。当然“家”最初的起源是男女组合体,这个组合体的分工必须是合理的,是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组合形式。费孝通在《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中认为,家的前提是男女必须是健康的。儒家传统的思想观念中对人的成长历程概括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当人完成平天下,也就完成了人的使命。可见儒家观念中“齐家”意识的提出,就意味着人必须成家,必须依附于家。当然,家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人际关系网,在这个关系网中要以和为贵,家和才能万事兴,家和的前提是长幼有序,夫妻恩爱,兄弟姊妹常来常往。
严英秀的小说在强调“立家”观念的同时,特别注重“家和”重要性,为此他在小说中写了一些“解构之家”与“和睦之家”,将此作以对比,强化“家和万事兴”的重要意义。在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中“家和”的前提来自于男女双方的责任和担当,严英秀是很认可这一点的,她在小说《一直很安静》中塑造了一位品德高尚的古代文学老师焦一苇,他不凡的气度和扎实的学识深受学生们的喜爱,而且他不平凡的人格魅力使得大二学生田园暗恋上了他,一次偶然的湖畔邂逅,田园知道了老师的心思,并把老师递给她擦眼泪的手帕永远珍藏下来。而焦一苇始终没有忘记他所从事的职责和担当,作为老师,他没有忘记对学生诲人不倦的教导,他理性地处理了学生对他的爱恋,并为学生田园争取了留校任教的机会。作为丈夫,他无微不至地照顾因公致残的妻子,最后离开自己热爱的教学岗位,调到了一家闲散的文化单位。正是因为焦一苇有责任和担当,无论走到哪里,这个家永远充满了阳光和温馨。
在中国人的乡土观念中,子女是家庭和谐的基本前提。费孝通在《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一著中论述了“社会结构中的基本三角”并将这种意识框定到一个家庭中,他说:“婚姻的意义就在于建立这社会结构中的基本三角。夫妇不只是男女间的两性关系,而且还是共同向儿女负责的合作关系。”[2]严英秀小说书写人性的同时,注重表达人的社会性,她小说中的许多人物基本都是不背弃男女结合组建的家庭,最终融入社会的生活规约,她的小说中没有终极“单身汉”和“独身女”形象的塑造,即使那些与群体格格不入的男性或者是半路丧夫的女性,也会最终找到携手的伴侣,重新组建家庭后开启新的生活,比如小说《一直很安静》中性格孤僻狂妄的诗人高寒,被大家认为“资深光棍”的他最终和巩梅走在一起,将要开始新的人生。《仿佛爱情》中娜果半路丧夫后,拉扯着女儿艰难地过着寡居生活,但她最后考上博士遇到了丧妻的张教授,结成半路夫妻,重新开启了美好的人生。
而在小说《手工时间》中,作者回归到费孝通的“社会结构中的基本三角”理论来强化“家和”的重要性。小说中杜芮的失眠与老公的贪睡形成了明显的反差,但是因为女主人公迟迟不能怀孕,使得这个家庭关系一直处在紧张的状态中,后来意外的怀孕缓解了紧张的夫妻关系。小说中说“我老公欢天喜地”[3]。为此夫妻之间有了更多的呵护和照顾,再不是背对着背,一个呼呼大睡,一个失眠嫉妒,失去言语交流的夫妻关系。但是因为身体机能的原因,这个未出生就失去了生命的胎儿再次给和谐的夫妻关系蒙上了阴影。作品中说“我老公很痛苦,我看得出来他很痛苦”[3]42。可见,子女成为维持家庭家和睦的前提条件。雷蒙德·弗思说:“舞台上或者银幕上的三角是二男一女(近来也有二女一男)间的爱情冲突;可是在人类学者看来,社会结构中真正的三角是由共同情操所结合的儿女和他们的父母。”[4]为了进一强化子女对家和的重要意义,作者严英秀巧设了杜芮的再次怀孕,她认为第一个胎死腹中的婴儿带走了孕妇胎体里所有的病源,带走了生命深处的“毒瘤”和原罪,伴随着的是第二个生命的安然降临,这个家也会走向和谐,重新建构稳定的“三角社会关系”结构。
毋庸讳言,失去三角稳定关系,家也就失去了稳定的根基。她在小说《沦为朋友》中进一步强化了这一事实。这个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梅沁少年时代父母离异,哥哥不幸溺亡,她饱受打击,变得孤独甚至自闭,后来她与大学时代的好友安好哥哥安康见面后二人情投意合,安康照顾妹妹安好的点点滴滴深深打动了梅沁,梅沁感觉到在安康的身上找到消失多年的哥哥的影子。正是出于感同身受的境遇,梅沁顺然接受了安康的求爱和婚约。但婚后日常生活中,由于安好的过分亲昵和介入,让他们的生活充满酸楚、无奈、压抑甚至绝望,使得他们的婚姻处于解构的边缘,最终他们选择了分开。与安康分别后梅沁又重新踏上了另一段爱的旅程,这一次她遇到了京城著名的评论家于怀杨,当她准备和安康离婚的那一刻,于怀杨却逐渐地疏远了她,她独自承受着爱情的悲剧。
我们不难发现导致梅沁和安康之间家庭关系紧张的原因不是妹妹安好的介入,而是他们之间没有维系家庭关系的子女,他们组建的家庭只能是临时的,不稳定的。由此看来,严英秀强化的家和意识是符合费孝通所认为的中国乡土社会的基本结构理论的。
二、夫妻的出轨与反省
在书写人类情感的文学巨篇中,有诸多的作品写到了婚外恋的故事,比如劳伦斯的《查特莱妇人的情人》,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等,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并不是不道德,而恰恰是人情感的合理性表现,因为人的情感是没有极限的,人对美的追求也是永远没有节制的,包括男性对女性美的追求。从中国“男欢女爱”的一词中可以看出,男性注重性、身体和感官的享受,女性更重情、心理和精神抚慰。中国女性追求的是被爱,痴情,情感的专一等等,所以在人类情感的天平上,女性所受到的感情伤害要远远大于男性,尤其是成家后的出轨、初恋对她们的伤害更为惨烈,因此中国戏剧文学中出现了那么多“负心汉”与“痴心女”的形象。
严英秀的小说善于强化男权意识,她特别注重对男性人伦道德加以强化和塑造,试图凸显出男性在家庭中的主导地位。不难发现,一个家庭中男性的出轨、或者负情都会不同程度地破坏和动摇这个家的和睦与稳定,很大程度上也会让一个家庭解体。史志瑾在论述鲁迅伦理思想时说:“鲁迅强调爱情的持久性,要求男女双方要经得起人生道路上的种种波折和考验。”[5]也许受鲁迅的影响(因为她任教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多年)作为女性作家的严英秀也追求爱情的持久,为此她以鲁迅的《伤逝》为样板,写下了男女出轨的小说《纸飞机》《仿佛爱情》《沦为朋友》等,向新时期以后迈向小康生活的中国城市家庭发起了伦理道德的匡正和警示。
小说《纸飞机》中,作者开头写到了剑宁、萧波和儿子这样一个非常和睦的家庭,剑宁疼爱儿子,经常给儿子叠纸飞机,叠好纸飞机后儿子坐在中间,爸爸扔过去,妈妈扔过来,一家人看起来很浪漫,但这样浪漫和睦的家庭生活中,仍然隐藏着很多的玄机,首先是学生阳子喜欢上了剑宁,剑宁也对阳子产生了爱慕之心,他认为阳子有阳刚之美。看着天伦之乐的剑宁一家,阳子只好将自己的爱埋在心底,一藏就是八年,八年中,他们的儿子已经长到了十多岁,阳子也无奈地与马海岩结婚。后来剑宁有了外遇,使得这个高级知识分子结合的家庭解构了,阳子同情剑宁的妻子萧波,她约剑宁到一家咖啡店里,在初吻中杀了剑宁。作者设计了类似于英国唯美主义作家奥斯卡·王尔德《沙乐美》式“吻”与“死”的悲剧故事结束了小说。小说中阳子杀剑宁是因为他的背情和负心,也类似于杜丽娘那样为自己看错人而投江自尽。这既是对他人的毁灭,也是对自己的毁灭。
在这篇小说中,作者将“家”置于世俗欲望之中,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剑宁进入世俗的洪流后,丧失了自己的为师尊严,最后被学生以“仇情”的方式杀死,死亡的背后两个家庭的悲剧也就同时发生了。小说中“纸飞机”意象承载着剑宁一家的幸福,也营造着其家庭的和睦氛围。正因为阳子看到了老师剑宁一家融洽幸福的玩乐场景,她默默地忍着对老师的爱,虽然她后来结婚生子,但是她把自己的初吻永远给老师留着,最后当剑宁出轨时她在初吻中杀了剑宁。
在小说《仿佛爱情》中,作者也设置了一个赤裸裸的男性出轨的事实,小说中娜果的前任丈夫和一个女人偷情,她的弟弟得知消息之后领着伙伴准备给不道德的姐夫施以颜色,谁知在打斗中惹出了人命。小说中说:“她,没有死,她唯一的弟弟死了,她青梅竹马的丈夫死了。在她丈夫被执行死刑的那天中午,她的父亲猝发心脏病,也死了——命中注定,娜果不会死。”[3]221这一切死亡皆因出轨偷情而起,背后更大的悲痛留给活着的人。值得庆幸的是娜果艰难地拉扯着这个负心汉的女儿,最后重新与张教授组建了家庭。
严英秀小说中不光有出轨的男性,也有出轨的女性,这正如刘敬伟所说:“当现实婚姻生活并不符合她们理想追求时,便会精神出轨或者肉体出轨”[6]。严英秀笔下的女性出轨是有节制性特征的,她们大多是情感出轨,而很少有肉体的出轨,基本上都是受“发乎情,之乎礼”传统礼教的克制。她笔下的女性是对家庭、丈夫、孩子都负有责任的,而且这些女性在伦理道德的钳制下,最终会悬崖勒马,重回家庭。比如《被风吹过的夏天》是作者依托于藏传佛教文化“缘”之说的基础上建构的一篇小说,小说开头借以抗战的历史事件为梦境拉开了序幕。而在故事的发展中,我们才发现梦中相依为命的何染和董一莲原来是一对情侣,从他们的相遇、相爱等曲折的经历来看,一切都是那么的有机缘,但是小说最后,何染千里迢迢的来和董一莲相约在一家酒店,董一莲在身体即将出轨的关键时刻却迷途知返,悬崖勒马。董一莲最后的觉醒,却让何染失望地离开了她,从此这个曾经想着背叛家庭出轨的女性,迷途知返重新回归于自己的家。
不难发现,男女的出轨在严英秀的小说中只是一种设想、思考,真正出轨的男女双方都是没有好结果的,这其实是作家对人性和家庭伦理关系遽变的各种思考。
三、不孝与孝的意识凸显
中国传统文化中特别注重强调尊老爱幼等孝悌礼仪。孔子说过:“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7]他在《论语》中也强调过“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7]53。中国古代的《孝礼》中说:“父母有疾,冠者不栉,行不翔,言不情,琴瑟不御食肉不至变味,饮酒不至变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复故。有忧者侧席而坐。有丧者专席而坐。”[8]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古典戏剧中写了许多“不孝子”的故事,也塑造了许多具有贤孝品质的女性形象,她们或是“祝发葬老”或是“千里寻夫”,比如赵五娘、秦香莲等。她们的贤惠品德成为后世学习的典范。
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中国社会“孝亲”文化的日趋式微(主要表现在农村分工赡养老人及城镇出现的空巢老人现象),弋舟等中国当代作家对其做了更多的描写和呈现。严英秀是一个有着强烈“孝亲”意识的知识女性(我们可以从她散文中得知)。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中国社会城镇化的加速,年轻一代子女的敬老、养老等观念日趋淡化,因赡养老人而引起的家庭矛盾、夫妻失和等问题日趋凸显,严英秀不是道德伦理的教化者,她只能以文学作品的方式加以呈现。从她的散文《天之大》《我的表哥晋美嘉措》中,我们能够明显地感受这一点。而在她的小说《夜太黑》写了子女对养老的争议推卸等有悖“孝亲”的主题。为此她在长篇小说《归去来》中她进一步书写子女的牺牲,以此来强化和提升新时代的孝亲意识,这对新时代重建伦理秩序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
《夜太黑》是作者在借鉴巴金《寒夜》的基础上创作的一个短篇小说,小说以乔月和陈宏凯冬至吃饺子的故事展开了一个家庭的叙事。这个故事中夫妻因为赡养老人而产生了间隙,使得夫妻关系遭遇了诸多的危机。小说中,乔月的大姐出了车祸意外离世,乔月的父亲将其原因归咎于母亲,他仇恨母亲和这个家,独自一个人居住在老屋里,无路可去的母亲,只好由女儿乔月赡养,因为照顾母亲,使得乔月和丈夫陈宏凯之间失去了自由的生活空间,为此,夫妻之间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夫妻之间经常吵吵闹闹快要到了离婚的地步。乔母无法想到,这个曾经在自己眼中最相中的女婿现在却变成了“白眼狼”。当乔月为抚养母亲向陈宏凯提出离婚时,陈宏凯才无可奈何地选择了顺从。小说结尾中作者又引入了小曼一家赡养老人的情况。小曼和丈夫剥夺二老的财产,名义上是要赡养老人,实质逼迫老人无可奈何跟着他们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小曼的养老观念,进一步潜移默化了乔月的心,在小说的结尾,乔月离家出走后,她打给母亲的电话中作者进一步强化了孝亲的观念。不难发现,《夜太黑》是典型的家庭伦理的“反照镜”。从这篇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出进入新世纪以后城镇化的加速进程中,快速发展的社会异化了中国传统美德,使得一部分年轻人变得平庸、虚假和自私。严英秀小说正是以家庭为空间呈露了那些自私、虚伪的男性。
每一个作为个体的人,都会在社会中承担一定的责任和义务,这受到法律的规约,同时也是迫于道德舆论的要求。就乡村伦理而言,这也是人们常说的人情味与烟火味。从父母与子女的家庭结构层面看,父母对子女具有多重义务,包括对子女的抚养、供子女上学、帮子女成家、甚至立业,几乎自己无所诉求地把一生的心血都花在子女的身上。正是因为如此,鲁迅认为“觉醒的父母,完全应该是义务的,利他的,牺牲的”[9]。作为子女,当父母年老时也应当有义务赡养父母,为父母牺牲,因此中国当代文学中将子女的牺牲作为一种美德不断加以宣扬,比如《百鸟朝凤》《血盆经》等小说。
在文学创作中,女性作家自然有女性的立场,严英秀小说中的女性大多是迷途知返的女性,或者是觉醒的女性,这些女性不但可以和自己有悖伦理的丈夫相抗衡,也可以同这个世俗社会相抗衡,比如乔月、董一莲等女性。可见她在反思人性的同时,也揭示了这个社会的复杂性。严英秀也是一位很有理性的作家,她的小说中既写了子女的不孝,又写了子女为父母的牺牲。在长篇小说《归去来》中,她将赞颂的笔墨放在了文本的尾声中,写到江城遭遇的自然灾难,失去了女儿的桑蔚晨的爸妈都陷入了极度的悲痛之中,但长年扎根于江城乡土的爸妈拒绝了儿女们接去大城市安度晚年的意愿,无奈之下,作为女儿的桑蔚晨夫妇放弃了大城市理想的工作,守候在江城照顾年迈的父母。小说最后作者用藏文化的生命观升华主题:姐姐的遇难,换来了桑蔚晨的意外怀孕,这对完全还没有走出悲痛的父母来说,又是一个意外的惊喜。
而在小说《前后左右都是喜事》中,作者仍然塑造了一个十分和谐的家庭,这个家庭中的子女对父母都是言听计从的,当姐姐何卫红与教师顾一鸣婚姻受到何母的反对时,子女们都支持姐姐,说服了何母,到最后何母接纳了顾一鸣,尽管后来何母阻止了何卫红与彭歆交往,何彭之间造成爱情的误解,但子女们仍然坚持了父母的立场,最终促成了何卫红与顾一鸣的婚约。中国乡土社会伦理结构认为,女子对父母的孝,不只是行为上的孝,而且还表现在言行上,对父母言听计从其实就是心理上的孝,说白了就是不惹父母生气。顺应父母相中的婚姻实际上是免去了父母对子女的担忧,减少了父母的心理负担,这其实是最大的孝,这也需要子女们付出一定的牺牲。
总之,严英秀小说中的家庭伦理叙事大多是以夫妻关系为视角加以观照。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异化了一部分人心,也动摇了后乡土时代留存的传统文化、文明伦理秩序。她的文学书写无疑对损坏伦理的不道德行为赋予启示和救疗,这也对建构和谐社会、促进家庭和谐与美丽乡村建设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