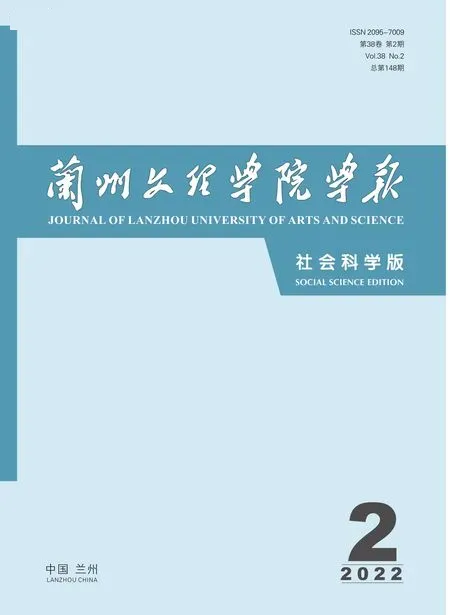疲惫生活中的英雄梦想
——严英秀小说论
2022-03-18魏春春,吕文锦
魏 春 春,吕 文 锦
(西藏民族大学 文学院,陕西 咸阳 710282)
严英秀认为写作之于女性的意义,是“在无底无痕的时间中”,“在对时间的恐惧和信仰中走过时间”,进而逐渐走向自己的方式[1],即写作是写作的女人在与时间的厮磨、对抗、和解过程中逐渐认识自我的方式,时间是写作的女人必须直面的话题,这与迟子建所慨叹的“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他们给看老了”[2]的时间美学认知有异曲同工之妙。严英秀的文学作品基本以女性为言说中心,极力勾勒出女性精神空间的多面性和多层次性,以实现“寻找心灵、精神的同类”[3]的人文诉求。通过散文,严英秀实现了“我与自己的狭路相逢”“短兵交接”[4],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出严英秀特定时期的精神反思和情感状态;借助小说,严英秀在虚构的世界中“力图表达广阔人生”,以展现“疲惫生活中时远时近但从未丧失过的仅有的英雄梦想”[5],为我们呈现出当代中国知识女性温婉而不屈“生活中的白日梦想”[6]。
一
关于自传体小说,严英秀认为除了丰富的经历,“端出来给别人看的勇气”,还要具备“回顾自己的人生时与自我形成审美距离,把自己当成他者进行理性审视和自我批判的写作精神,以及能从生活的形式之真实中提炼出、升华出人生的实质之真实的艺术能力”[7],就是说个人的历史经历和文化体验只是生成小说的题材,而非小说本身,小说自有其独属的文化品格。基于这样的文化认知,严英秀的小说创作基本立足于她的人生感受和生命历程,融汇她的生活体验和生命思考,进而表现出她的自我审视和自我塑造。
严英秀的小说基本取材于她的生活,带有一定意义上的自传意味。在严英秀的小说中,出现频次较高的大致有童年生活、大学记忆和中学教师生活。关于童年生活,严英秀集中体现在《夜太黑》《玉碎》《前后左右都是喜事》《归去来》等作品中,在其他作品中皆有零星的展现。严英秀出生的时候,她的母亲“已近四十岁,已经生育了六个孩子”,“等把我拉扯到五六岁时,病魔已牢牢控制了她”,“那时候,大姐已嫁了人,大哥在省城当兵,二姐和小哥哥在县城上学,而父亲在远离我们的地方正指挥着农业生产和阶级斗争的狂潮,连过年都回不了家”,“在我七岁时……开始在城镇上学”[8],多年之后,严英秀仍在感叹“那些记忆太强大了,年深日久它们已深入到我的血液里,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8],因此,当严英秀要表达童年生活时,就会不自觉地把自己的童年记忆和童年体验渗透在其中,试图建构出作品中人物成长的童年底色,以展现出童年经历对个体人格成长的深重影响。从特定角度而言,严英秀作品中的家庭生活,都带有她童年生活的印迹,但严英秀采取严格的文化审查,使得她的童年记忆服务并服从于作品叙述脉络发展的要求,规约于人物伦理关系的建构需求,这就使得严英秀不得不在虚构的文学世界中撕扯开自身的童年记忆,并依照一定的秩序将这些记忆元素重新安置,在这样不断反复的过程中,她更为深刻地展现出童年记忆之于她成长的重要价值,呈现作品中人物的成长初体验,当这两者相互交织在一起,就完成了她童年记忆的小说化展现。
严英秀在散文《唯有旧日子给人安慰》中回顾了她的大学生活,她的懵懂而又充满激情的青春年华,“那些早凋的花事,还未呈现出应有的意义,它们似乎仅仅是以一种修辞学的存在,衬托了我怅廖的心情”[9],在校园中,严英秀徜徉在友情、音乐、文学的欢歌笑语中,打量着、窥探着青春男女的喜怒哀乐,感受着上世纪九十年代浓郁的即将退潮的人文理想气息,这些要素为严英秀打开了一片广阔的天地,即逃离家庭束缚后的自由呼吸,“走过急功近利的高中阶段,我要的不过是安静地自由地读一切我愿意读的书”[9],既包括文本之书,也包括人生体验之书,她在大学生活中体验到别样的青春激情。这段经历对严英秀精神世界的丰富和充盈有着难以估量的价值。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严英秀先后发表了《心梦无痕》《与我共舞,好吗?》《指尖上弥漫着你的气息》《往事温存》等散文作品以追忆大学时光,这些散文中涉及的人事物后来陆续进入到严英秀的小说中,如“我用无穷思量织一件平平常常的毛衣”[10]衍化成名为《1999:无穷思量》的作品,长发歌手的形象出现在《自己的沙场》《骊歌》《说好的,让白海棠一会开》《归去来》等作品,历经岁月的洗涤,这些青春往事以不同的形态出现在她的作品中。尤其是《1999:无穷思爱》,严英秀自谓“这篇作品,其中的人和事都来自我生活的真实,它记录了我人生的一段重要心路历程”,体现了她对“女性的友情,爱情,事业,家庭,关于付出,伤害,关于挣扎,妥协,关于破碎,救赎”[11]等等话题的思考,奠定了严英秀后续创作的情感基础和文化基调,“许多年后,我一次次地回味90年代初我曾感觉到的孤独和残缺,一次次地沉迷于那永不再来的青春体验”[3]。当严英秀进行小说创作是,那难以忘怀的青春体验自然就进入到她的文学视野中,自然成为她关注女性生存状态的取材。但在具体处理的过程中,严英秀溢出了青春体验的新鲜活泼,赋予其全新的文化意义,着力彰显现代知识女性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自觉和文化独立。
严英秀的作品中屡屡出现“中学老师”的形象,这与她大学毕业后的中学老师经历密切相关。尽管严英秀公开发表的文字中,未曾清晰地描述这一段生活状态,但可想而知,中学教师是严英秀大学毕业后从事的第一份工作,个中滋味估计在严英秀的生命体验中留下了浓重的色彩。严英秀的《纸飞机》《苦水玫瑰》《恋曲1990》《非典型性医疗事故》《前后左右都是喜事》等作品中都塑造过中学老师的形象,这些老师大都是女性,她们善良聪慧,充满理想激情,又屡屡遭受残酷现实的打压,在成长的过程,她们正视自己的内心,坚持自己的操守,“长大了,才知道不管去哪儿,不管在哪儿,人面对的总是自个儿的日子,自个儿的心”[12]。这或许就是四年的中学教师生涯留给严英秀的感受,她实现了身份的转换,从女大学生变成社会知识女性,从象牙塔走向社会生活,体味着理想遭遇现实生活中的种种艰辛。
严英秀在作品中还展现出大学文化生态,如《纸飞机》《一直很安静》《仿佛爱情》《芳菲歇》等,这是对她高校职业生涯的呈现和思考;亦表达出对故土的无限眷恋和感慨,如《雨一直下》《雪候鸟》等,这与她多年远离故乡的游子情怀密切相关。严英秀的小说中,皆掺杂着她的影子,但严英秀却给这些影子注入灵魂,让她们真诚地生活、真切地思考,而非成为她的傀儡,在严英秀与其生活对视的过程中,她重新发现生活之美,人生之魅,以此,严英秀超脱了“自传”的经验性、回忆性而实现了小说的文体属性。
二
严英秀钟爱音乐,尤其是流行音乐,她检讨自己“作为一名上世纪90年代的文学青年,我从港台流行歌曲,从心爱的齐秦这里得到的文学启益,并不比从当时风靡一时的一些高大上纯文学书籍得到的少多少”[13],严英秀回想“在90年代初的大学校园,吉他是文学青年的标配……青春是多么寂寞的事情,风和日丽的成长中隐藏着残酷的疼痛,躁动与迷茫,绝望与反抗,都找不到恰当的出口,年轻的心日夜战斗在无物之阵中……音乐之于我,从来都是和文学一样重要的事”[4]。音乐和文学成为年轻的严英秀认识自我、认识生活、憧憬未来的蕴藉方式,在音乐和文学的扶持下,她插上了梦想的翅膀,执着而又顽强地跋涉于心灵之旅。
音乐之于严英秀有着非同一般的价值,尤其是振奋人心的音乐使得她寻找到心灵共鸣的途径,由严英秀几篇以音乐作品命名的小说如《恋曲1990》《自己的沙场》《雪候鸟》《悲伤西班牙》,我们或能感受到她对音乐的挚爱。这些作品与这些歌曲同声共气,表达出人到中年的严英秀对往日青春时光的无限眷恋,以及对当下中国知识女性生存情态的慨叹与伤怀。
《恋曲1990》描述了“二十年前”的某中学若干女教师的精神状态,尽管生活平淡甚至是平乏,但这些知识女性以自己的理想对抗着生活的单调,李清执着于爱情的纯粹单纯,宁可孤独绝不苟且,寻找着属于自己那诗与远方的爱情;桑平“渴望沉入生活的最底层”“在生命中体验生命”,她坚信爱情的持久炽热,即便再大的风雨也无法消融她心中的熊熊烈火;胡春桂尽管摆脱了贫困,“调到城里,嫁到城里”,但无爱的婚姻让她陷入新的困境,唤起丈夫的爱成为她不得不直面的难题。这三位女性尽管都遭遇情感的瓶颈,但她们从未放弃期望,最终“真正走出了那些不忍醒转的迷梦,迎向真正的成长”[14],为我们展现出一曲曲荡气回肠的纯情恋歌。可以说,《恋曲1990》是严英秀向纯情年代的致敬之作,也是她向纯情年代的回眸之作,“二十年前”已然成为心中永远的激荡,那二十年后的知识女性又处在怎样的情态呢,这就成为她写作征途的新起点。
《自己的沙场》和《悲伤的西班牙》展现的皆是人到中年的知识女性的生存境遇,当热烈爱情遭遇平凡生活,激情消退,女性们该如何建构自己的精神高地,无爱的婚姻有无持续的价值,这些成为严英秀重点思考的问题,她力图展现出中年女性的痛苦与挣扎、艰辛与扭曲。严英秀看似并不关注日常伦理道德,她作品中的女性极力要挣脱所谓“好就好”[15]的束缚,世俗所看重的“好”更多地是从生活、生存境况进行的评判,是拂面歌吟的“好”,然而严英秀所期待的“好”更侧重的是精神世界的富足和存续,或者可以说,严英秀小说中的女性追求的是超脱世俗幸福的心灵满足,但残酷的现实却不断地打破她们的迷梦,因为社会人的身份使得她们不得不直面自身的生存境遇,不得不屈从于世俗伦理。故此,《自己的沙场》中的苏迪大学时期在音乐的感召下感受到生命热闹而又孤独的意味,她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无法 “冲破铁一般坚硬的世俗,去贴近一个在社会的边缘挣扎着的心灵”[15],直到在一曲《空白》中告别青春年华,在歌手晓楠的死亡日记中掩去了青春光泽,在无爱的婚姻中浑噩度日,“经营着自己的无所事事”,苏迪失败于自己的沙场。而陶一山“睿智、深刻和犀利”的言辞唤起了苏迪尘封的心灵,唤醒了苏迪沉睡的理想之光,唤回了苏迪少女时期甚至是童年时期渴求挣脱一切束缚开辟自我人生的热望,但最终苏迪清醒过来,摆脱了心灵梦魇,回归“像岸一样等在我的黑夜里的丈夫”[15]和家庭,获得了精神的自我解脱,实现了自我和解。而《悲伤的西班牙》则颠覆了《自己的沙场》中回归家庭获得安适的思考。严英秀借助知识女性黛诺和她师友的情感遭遇,展现出女性在喧嚣世界中的精神孤独和寂寥,“有些感情像天籁之音,有多珍稀,就有多脆弱,易碎,而且不可复制,它经不起躺在床上去把玩,也不耐生活的磨蚀”[16],再纯粹磅礴的感情也无法抵御时间、生活的磨砺销蚀,阿潘与老普一直以模范夫妻示人,却在晚年遭遇情感危机;黛诺与老公,看似相濡以沫、相敬如宾,实则无聊乏味、冷漠空虚;黛诺与柏大夫,看似激情澎湃,实则互为倾诉对象、无法耦合;何琦不停地周旋于不同男性之间,以身体的忙碌排遣心灵的凄惶和软弱,严英秀意在呈现“中年女子在生活中感受到的无处不在的孤独”[4],尽管她们顽强地维护着自我内心的骄傲,实际上“美丽包裹着的是真正难以触碰难以言说的疼痛”[17],因而这些知识女性在现实生活中无处安放自己的悲伤,无法实现真正地自洽。
从《自己的沙场》到《悲伤的西班牙》,在确证女性自我精神的道路上,严英秀表现出现代知识女性即便拥有了爱情、家庭,即便获得了社会认同的独立、自主,依然无法实现自我精神的富足,依然如同无根的浮萍一样飘摇在寂寥的长空,于是,如何获得根性而实现内在的圆满,就成为严英秀思考的话题,为此,她将目光回转到个体文化根性生成的故乡大地,试图为现代知识女性找寻到更为宏阔的精神家园。小说《雪候鸟》以歌曲《雪候鸟》中“随候鸟南飞,风一刀一刀地吹。我不信你忘却,你遗弃的世界,我等你要回,我又回头去飞,去追……” 为线索,勾勒出远走他乡的知识女性岳绒重返精神故乡的心路历程。在岳绒的记忆中,故乡一派田园牧歌风情,和谐的家庭、绚烂的色彩、亲密的朋友、甜蜜的爱情,而突如其来的变故打破了她的迷梦,故乡成为岳绒的伤感之地,不愿回乡、不忍回乡成为岳绒生活的常态,当她不得不面对故乡的亲人、朋友,不得不行走在故乡的大街小巷,不得不直面心中的隐痛,在亲情、友情的慰藉下,经过痛苦地挣扎,“她闻到了它遗留在青春之夏的气息,也听到了它在今天历久弥新的流淌声”[18],最终消融了积郁在心头的寒冰,心灵释然,获得了精神的飞升。故乡的大雪等待着候鸟的回归,候鸟何尝不期待故乡的漫天飞雪,雪与鸟的关系构成了岳绒心中永远的故乡想象,是岳绒割舍不断的精神家园象征,正如严英秀所谓的“如果对故土的审视,必得以候鸟的姿势才能完成,我只能继续前行。也许,前方尚未澄明,归途已相失于云水,但我相信,只要心底有一条回乡路,所有的断肠春色便都在”[19],故乡为知识女性增添了人生奋进的勇气,也为她们提供了心灵休憩的居所。
严英秀以小说的方式演绎其对流行音乐的体认,流行音乐是流动在她心灵中的文学,文学是跃动在她血脉中的音符,乐曲和乐词敲动着严英秀的心弦,澡雪着她的精神,使得她的小说作品与特定音乐作品同声共振,共同演绎出当代知识女性的心灵成长过程,表现出她们追求美好的希冀、努力、挣扎、彷徨与坚守。
三
陈思和曾指出严英秀“在一个短篇框架下适合讲述一个半故事”[20],指的就是严英秀采用故事延展的小说架构方式,一个故事中包裹着或裹挟着另一个故事,并且这两个故事有主次之分,由主要故事连带出次要故事,而次要故事则是主要故事生发的前置条件或必要条件。严英秀通过两个或多个故事的相互连接,建构出其小说的历史纵深性和时空交错性,具有极强的文化包孕性和共生性。
严英秀坦诚她创作于1999年的《1999:无穷思爱》“几乎是我后来很多小说的母体”[11],纵观严英秀发表的小说作品,几乎都与《1999:无穷思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该作不仅奠定了她所有作品忧郁感伤的感情基调,而且是她所有小说作品的滥觞,因此,从一定程度上看,《1999:无穷思爱》是严英秀小说故事核的根本所在,如其中青年女性之间历久弥新、愈发醇厚的友谊,大学时代青年男女的青涩爱情,大学校园中师生之间的爱恋,逃逸别人眼中幸福婚姻生活的女友,以奇怪的宽容接纳朋友的婚外情等等,这些元素在严英秀的小说中反复出现,她将之纵横交错地结构起来,构成其小说的“一个半故事”,如《沦为朋友》主要展现的是梅沁要逃离和安康的无爱婚姻才衍发出与于怀杨的一段婚外恋情,主体是梅沁的情感遭遇,其中穿插的则是梅沁与安好的相互依赖而又相互伤害的友谊,这两个彼此关联的故事相互合作,完成梅沁精神风貌生成历程的塑造。
而在实际的文学操演中,严英秀找寻到小说衍发的起点是家庭生活,这与严英秀童年的家庭生活记忆和成年后组建的家庭生活体验密切相关,这就使得严英秀看似聚焦于家庭生活、夫妻关系,实则外延到对特定的社会现象的思考和反思,如关于老人赡养问题的《夜太黑》、灾难之后重建精神和物质家园的《雨一直下》、畸形权利影响下亲情扭曲的《非典型性医疗事故》、青少年时期家庭变故引发的创伤性体验的《手工时间》等,由此,严英秀建立起以女主人公的情感经历为线索,旁逸斜出与其相关的其他人物的故事,共同组建起暗流涌动、异彩纷呈的人生景观。
另外,严英秀还尝试采取故事叠加的方式,深化某些事件的深度叙述,值得关注的是严英秀以系列中篇小说《前后左右都是喜事》《说好的,让白海棠一直开》《骊歌》等为基础,创作完成了长篇小说《归去来》。究其实,《归去来》似乎是严英秀对其之前所有创作的集合,我们在《归去来》能够找到之前她所有小说的痕迹,因此,或可以说,严英秀所有的小说创作都是在为《归去来》做题材和情感上的储备。相比较之前作品中一味地呈现女主人公的精神煎熬和爱的缺失,《归去来》表现出坚信真爱、执着信仰、脚踏大地、眼望星空是现代知识女性获得自我情感认同和精神归属的重要方式,这是对《雪候鸟》的精神家园思考的进一步升华。而《归去来》大团圆式的结尾体现的是严英秀在《遇见》中通过叶子衿的口吻所表达的文学期待,“我不愿意你为了所谓的小说艺术性,再给她一个百折千回的结局,或者是你最擅长的那种没有结局的结局……一个女人,走过了那么多坏日子,等待了一生,寻找了一生,她当得起那样一个交待。你们写小说的人为什么认定一个绝望的尾声,一个模棱两可的结局,就一定比电视剧的大团圆更高明呢?”[21]这意味着严英秀小说格调的蜕变,她已经突破了为了“小说艺术性”而刻意“掘进人类公共情感和经验的幽深,抵达文学应有的高度和广度”,而是回到女性的生活实际,展现她们“小小的悲喜浩荡的人生”[4],执着于她们宁静人生的幸福美满。
四、结语
严英秀的小说着眼于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展现当代知识女性掩抑在亮丽生活背后的隐微而绵密的精神情态,她冷静而又坚韧地撕裂生活的浮华而呈现当代女性心灵的孤单寂寥。严英秀几乎无视世俗生活的伦理而力图呈现女性的心灵焦虑和精神苦闷,她认为女性的幸福在于独立地畅享生活的欢愉,自由地翱翔在梦想成真的现实生活,即谢有顺所谓的从俗世中来,到灵魂里去,因此严英秀作品的女性都是自己生活的英雄,是追寻自我梦想的英雄,是对抗疲惫生活的勇士和斗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