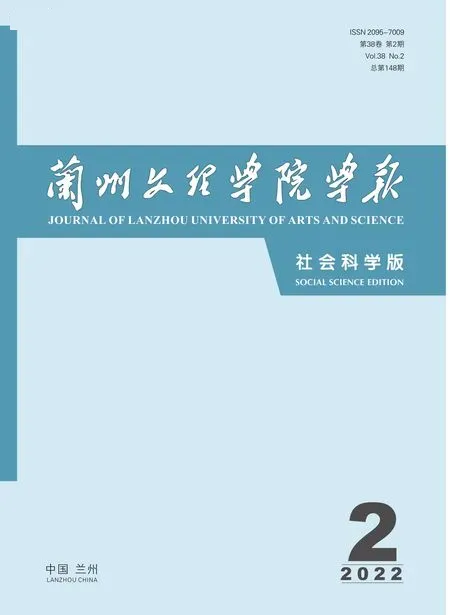论文学介入政治的“想象”与“正义”
——评刘锋杰的《“文学政治学”十形态论》
2022-03-18龚游翔
龚 游 翔
(浙江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自“文学政治学的创构——百年来文学与政治关系论争研究”至“文学政治学的历史形态与当代创新研究”,刘锋杰基于文学理论与政治学的跨学科交叉领域探究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并且提出“文学想象政治”[1]的命题指向一种具有自然法特性的“文学正义论”[2]。从中国现当代百年来文学的“政治化”“去政治化”“再政治化”的历程演变辐射到古今中外文学政治的史论脉络,他提倡用“政教论”“文道论”“诗史论”“人本论”“理念论”“自由论”“批判论”“权力论”八种理论形态来阐释文学与政治的交缠关系,并且另创“想象论”“正义论”来揭橥文学政治学学科的本质特性与终极价值。《“文学政治学”十形态论》的出版与“文学政治学”学科的创构彰显了刘锋杰以文论介入现实、满怀政治正义的理想抱负,为“中国当代文化政治美学”[3]版图的理论建构拼接了一隅。
一、文学介入政治的历史形态
当代对“文学介入现实”命题的探讨最早可以追溯至现实主义文学的缘起以及对其手法、目的与功能等要素的阐释,而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讨论一方面源自20世纪法国的重要文学现象“介入文学”,它“经由萨特的文学理论与实践而发展至顶峰”[4];另一方面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至今中国文坛百年来始终围绕着文学的“政治化”与“去政治化”的论争。从古至今,文学参与政治的“介入”现象屡见不鲜。西方文论界思考文学与政治关系的“介入文学”,因从萨特的理论化研究开始,才真正使“介入”一词具有了明确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指涉。而中国当代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研究的理论体系仍待建构,因此刘锋杰对文学政治学学科的创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当代价值。《“文学政治学”十形态论》于中西比较的视野下将文学介入现实政治的历史形态以八个关键概念总述与囊括,分别划分为四个历史时期中的四种形态:古典形态、近代形态、马克思主义经典形态与当代形态。刘锋杰认为西方的四种历史形态主要以教化民众、个性解放、服务革命与文化批判为中心,而中国的形态则以教化民众、抒发性灵、建构“文化领导权”与“以人为本”为中心[5]。鉴于此,他分设了政教论、文道论、诗史论、人本论与理念论、自由论、批判论、权力论来阐释中外历史语境中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在中国历史上,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内生性的。自汉代起,历代朝廷的文治官员大多由士人集团组成,学而优则仕是古代文人的价值追求,诗歌则蕴涵了其政治理想与现实情怀。首先,以孔子的《论语》以及《毛诗序》等著作开创的政教论是儒家文论的母题,它从文学的社会功用角度探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政教论在内容与功用方面的代表有“美刺说”,以诗讽喻政治、主文而谲谏;在伦理政治的维度有“教化说”,厚人伦、美教化,憧憬一种德性政治;其艺术风格理论则有“温柔敦厚说”,发乎情、止乎礼义,主张中和之美。其次,由韩愈《原道》中“文以载道”衍生的文道论则不仅着重“文”的本体性与“道”的超越性,而且关切“载”所呈现的个体性。文道论结合了《周易》的“天道”观念与诗文的本质,因而被视为是一种揭示了历史现象的公约性的“文论原型”。再次,中国古代文论中的“诗史”概念将文学与历史学勾连,从历史性维度审视文学艺术的特征。诗史论中的“通观意识”明确指“文学创作反映和超越现实生活,从历史的宏大视野来观察和评价现实生活”[5]129。以诗为史可以见兴替,诗史论的传统既能预见局部的真实历史,更重要的是实践了文学介入现实历史的命题。然后,人本论是刘锋杰对中国当代文学与政治关系形态的新创见。以人道主义和以人为本的价值指向为核心,其中蕴涵着四重限制:中介性限制、内容性限制、审美性限制和主体性限制。例如曾永成的“人性中介说模式”[5]288、钱中文与童庆炳的审美意识形态论、李泽厚与刘再复的“文学主体论”[5]296等都将人性、主体、审美视为平衡文学与政治的核心范畴。最后,刘锋杰提出了文学想象政治与文学正义论的命题,将“想象”和“正义”视为文学与政治的中介。纵观中国历史上文学政治学的四种形态:政教论、文道论、诗史论和人本论,它们分别从功能性、超越性、历史性、审美性维度界定了文学政治,体现出了文学与政治历久以来错综复杂的关系。
在西方传统中,文学与政治的外生性关系肇始于将理性视为认知事物的工具的观念,并且认为感性的文学是低级的认知方式。浪漫主义以来的形式论传统如新批评、形式主义、直觉主义、唯美主义、结构主义、符号论等都主张将社会文化、政治内容、民族性别等外在因素排除于文学之外。而刘锋杰认为内容与形式是不可分割的,他归纳了西方思想史上四种理论形态:理念论、自由论、批判论和权力论,重构了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理论体系。首先,他认为柏拉图以降的理念论发轫于“洞穴隐喻”“理想国”“净化说”“寓教于乐”等古典文论思想,它们率先探讨了诗歌介入民主政治的利弊。“理想国”驱逐诗人、“净化说”洗涤情感、“寓教于乐”融合美教,从正反合的辩证逻辑中反映诗歌介入现实的影响。其次,发端于笛卡尔的近代理性主义思潮将自由、人道、立法视为中心,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地位。以此为旨归的自由论则强调文学幻象与政治乌托邦的有机统一,来实现人类的解放与人性的自由的普世价值。再次,基于“模仿说”“镜子说”“再现说”强调科学、自然、典型等现实主义元素的批判论,直接伸入到文学批判现实政治的领地。真实地模仿客观事物、细致地刻画人物形象成为文学再现社会的主要表达途径。最后,自尼采的“权力意志”到福柯的“话语理论”,以非理性、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为代表的后现代权力论成为20世纪文学理论转向“文化研究”的主要路径。任何的言语、图像、符号都表征着潜藏的意识形态话语,文学作为话语蕴藉的审美意识形态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盘根错节。因此,从理念论到自由论是西方哲学从神本时代转向人本时代的过程,而从自由论到权力论则表明了西方文论研究从“向内转”到“向外转”的演变。因而,西方对文学介入政治命题的讨论始终囿于上述四个历史阶段的思想与理论之中。
由此可见,中西方历经四个时期展现的八种理论形态总结与勾勒出了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历史渊源与学理演变。刘锋杰在文学“介入”现实政治的语境下重新回顾文论史、追本溯源,试图为中国当代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理论研究构筑起系统的框架体系,从而为提出有独创性见解的“文学想象政治”命题廓清了道路。
二、“文学想象政治”的中介说
“文学想象政治”是刘锋杰在研究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中,具有独创性理论贡献的命题。他认为,“要为文学政治学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核心问题就是要实现一个根本的转向——从文学为政治服务的‘从属论’‘关系论’转向文学与自由关联的‘想象论’”[6]。文学政治学成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合法性就在于要阐明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联,寻找一个贯通文学与政治的合理中介。“曾永成认为文学与政治都解答‘人性之谜’,何永康指出政治礼仪制度是政治之美的程式化体现,王元骧认为需要从伦理维度寻找文学与政治的本体关系。”[1]受以上学者启发,朱晓进以“政治文化角度研究文学的政治化”[7],将“政治文化”[8]作为文学与政治的中介,提倡一种“政治文化中介说”。胡志毅从巫术仪式视角出发探讨政治与审美的结合形式,提出“仪式中介说”[9]。魏朝勇从伦理学的视角将政治的善与文学的美联结起来,提出“政治伦理的想象中介说”[10]。而刘锋杰取魏朝勇的“想象中介说”的概念,认为文学与政治的中介正是“想象”。文学是对美好生活的想象,政治也是对美好生活的想象,它们具有一种共同的特性,即超越性。当文学的想象遭遇政治的想象时,就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文学政治’现象”[11]。因此,刘锋杰认为“想象”是关联文学与政治的最佳中介,“文学想象政治”具备阐释文学史复杂现象的能力。
那么,“想象”何以能够成为文学与政治的中介?普通心理学将“想象”解释成为高级的认知过程,它是人在头脑里对已存储的表象进行加工改造产生新形象的心理过程和思维形式,它由个体所推动并且指向未来。在文学中,“想象是贯穿艺术构思过程始终的一种心理机制”[12]。想象艺术是“用语言文字塑造形象,使欣赏者通过对文字描绘的感受,在脑海中观念地把握具体形象的艺术,主要是文学艺术即语言艺术”[13]。因而,作者通过想象创造一个与现实物理世界截然不同的文学虚拟世界,想象成为文学生成的本质特性。形象、想象、联想、幻想一组四个概念不同程度地构成了文学的创作要素,形象是想象的直观呈现;联想是关联两个形象变迁的想象过程;幻想是创造性想象的特殊形式,是与个人生活愿望相联系并指向未来的想象。而在政治中,“政治的内涵包括了理念层、制度层和政策层三层含义,理念层表达了对人类美好生活的想象”[11]。政治乌托邦幻想一种路不拾遗、天下大同的理想社会,追求和憧憬一种美好的未来生活,而这种生活本质上是一种想象的产物。审美乌托邦就是试图联结审美想象与政治想象的范式,企图用审美的方式达到政治救赎的目的。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形象与政治幻想通过“想象”的心理过程趋于同一,“想象”成为沟通文学与政治的有效中介。刘锋杰的“文学想象政治”命题正是建立在人类心理学的基础之上,利用想象作为关联性逻辑中介嫁接了文学与政治的桥梁。
然而,以“想象”作为文学与政治关系中介的文学政治学,其核心概念“‘文学政治’下辖三个子概念:作家政治、文本政治、接受政治”[14]。作家政治是指作家本身的一种政治自觉,接受政治则是指读者、观众或受众的一种政治身份和政治视角,而文本政治则体现为一种修辞化的结果,并不指向现实政治本身。刘锋杰认为:“将‘文学想象政治’具体地落实到‘文学如何用修辞去想象性地文本化政治’,就是‘文学修辞政治’。”[5]18修辞是表达想象的主要手段,它既是文学创作的重要手法,又以自身独特的方式介入文本政治生成了一种政治表现。从西方历史的视角而言,修辞学自古希腊始就作为政治的代名词,而后逐渐才成为一种语言的表现手法。二十世纪“语言论转向”后,修辞学与诠释学成为本体论和存在论思考的重要方式。在西方古典民主政治中,修辞是一门使用语言的艺术,它作为面向公众的演说,展现的是一种群体性的行为。修辞利用说服性协议的约束方式使个人之间联合成共同体,说服性的语言本质上就是一个政治概念,它实践一种政治行为来规范和协调公民的政治生活。因而,在西方古典民主政治社会中修辞家或演说家实际上就是政治家。在中国历史上也同样如此,“主文而谲谏”便是修辞策略在庙堂政治中的实践。“主文说的是诗歌创作不可失去文采,谲谏说的是批评时政要讲究方式方法,应采取委婉语词进行。”[15]古代谏官为了规避风险,希望以统治者愿意接受的言说方式来达到政治目的,因而借用文学修辞的方法来从事社会政治批判,所以委婉的讽刺成为一种合适的方式被创造、发明与应用。由此可见,不管是从本体论的视角还是方法论的维度,修辞都是“想象政治”中不可或缺的要素。文学以审美修辞的方式或隐或现地改变着政治,实现文学介入政治的理论建构,“修辞政治”成为“文学想象政治”最重要的表现方式和表达手段。
综上所述,“想象”以其独有的心理学与人类学属性沟通了文学“形象”与政治“幻象”,成为连接文学与政治的中介。“文学想象政治”是文学政治学学科创构的核心命题,它以“修辞政治”的表现方式从本体论和方法论二维试图回应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实践问题。
三、文学正义论
如果说“文学想象政治”是文学政治学奠基性的本质特征,那么“文学正义”则是文学政治学的终极价值追求。刘锋杰的“文学正义”概念来源于努斯鲍姆的“诗性正义”(poetic Justice),这是一种与文学与情感相关的正义,它“要求裁判者应该尽量站在‘中立的旁观者’的位置,尽量同情地去了解每一个独特的人所处的独特环境,尽量以畅想和文学想象去扩展一个人的经验边界,从而建构一种中立的旁观者的‘中立性’”[16]。“诗性正义”偏重于从中立性的去价值化评判维度建构一种新的正义理论,而“文学正义”则试图以文学情感为核心介入司法政治的领域,它体现为生命正义、情感正义、个体正义三个层次的意义。生命正义以“生命”延续或存在的方式指向一种生命展示的正当性,个体正义相对于群体的差异性而言体现为每一个自我在实现价值的过程中追求公正与平等的目的。情感正义则关涉直觉原则,它认为文学情感是与理性判断具有同等意义的认识活动。由此可见,文学正义论展现了文学情感、个体价值与社会平等、司法公正有机结合的思想。
文学正义的核心关键词“正义”是伦理学和政治学的基本范畴。从政治哲学的视角而言,它指个人在自我存在中实现普遍的必然性。同时,政治正义也体现为在关于世界的必然性和个人存在的论述中现实的个人如何对待具有普遍效力的国家规范、法律和传统法则的问题。在伦理学中,宇宙正义是指自然法或理性法,它在法的意义上表现为一种普适性的道德法则。自然法的伦理学说指出支配人类行为的道德规范起源于人类的自然本性,它指向一种道德评价中的公正。而文学与诗学是一种基本的感性认知,它通过审美的方式促成道德理解,达到一种文学的美与道德的善相统一的境地。诗人为自然立法和裁判的原因在于“诗人代表着‘自然法’‘天赋人权’、法治在说话,并以此在文学中进行裁判”[17]。因而,刘锋杰认为“文学正义”是一种“诗性的自然法”,自然法的普适性、永恒性和最高性也是一种诗性特点。文学是源于人类的自然本性,追求正义的价值实现也是来自人类本性,文学与正义在本质上都是人类自然天性的产物。所以,“明确的旁观者”的中性立场在文学正义论中成为非常重要的视角,它体现为一种去价值化的道德评判。由此可见,刘锋杰的“文学正义”通过伦理学意义上的“自然法”概念联通,在以人为本的价值立场上来思考文学与正义的关系。当文学与政治结合时,诗人成为代表正义的最高价值,文学将会超越现实政治。
文学正义的三个维度:生命正义、情感正义、个体正义,其中情感正义是文学标志性的特征。传统意义上情感被视为是感性的代名词,它与理性构成二元对立。而正义是理性判断的标准,因此情感正义内涵着矛盾的张力具有充足的理论生长力。刘锋杰认为:“文学的情感可直觉到事物的本来面目,它与理性认识平起平坐,若理性可以建立与丰富人类的正义观念,那么情感也可以建立与丰富人类的正义观念。”[5]374当代的情感认知理论认为情感来源于认知,认知并非是理性唯一的属性。情感发生于主体对客体的感知与认识,客体的物理信息通过视听觉等感觉接收器官传达到大脑皮层,在脑神经的加工之后输出相应的情感反应。在神经科学与心理学的证据下,认知神经美学应运而生。因此,在开展正义的价值评判过程中,文学与美学成为影响其判断的重要因素。文学情感可以促成一种道德理解,正义可以通过文学创作与情感介入的方式表现出来。由此可见,正义观念的获取并非只有理性认识一条途径,情感同样可以通过文学形式的唤醒来促成对其理解与获取。情感正义看似是矛盾体,实则充分揭示了文学与正义以及文学与政治的内在关系。
综上所述,“文学正义论”不仅探讨了“正义”作为文学与政治的中介问题,而且将文学情感与正义观念以一种直觉的形式联结起来。事实上,从情感认知理论的视角能够更加清晰地解释情感正义的合法性地位。然而,不管是生命正义、个体正义还是情感正义都将文学与正义的关系纳入到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视域之下,为文学政治学学科的创构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
四、结语
刘锋杰的《“文学政治学”十形态论》及其创构的文学政治学学科对中国当代的文学与政治关系研究具有重要影响。“文学政治”概念的核心是“想象政治”,“想象政治”的直观表现是“修辞政治”,而文学政治学最终的指向是文学正义的价值维度。在中介思维的模式下,想象与正义是刘锋杰在创构文学政治学学科中的关键基石与理论创新重点。文学与政治的交互关系历史悠久、错综复杂,历经了政教论、文道论、诗史论、人本论、理念论、自由论、批判论、权力论八种历史形态之后进入当代社会,想象论和正义论为我们重新思考两者的关系开辟了新的视点。如何有效地思考两者的关系,既不在文学的政治化和去政治化之间纠葛,又能更深入地挖掘两者之间更多的可能性,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与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