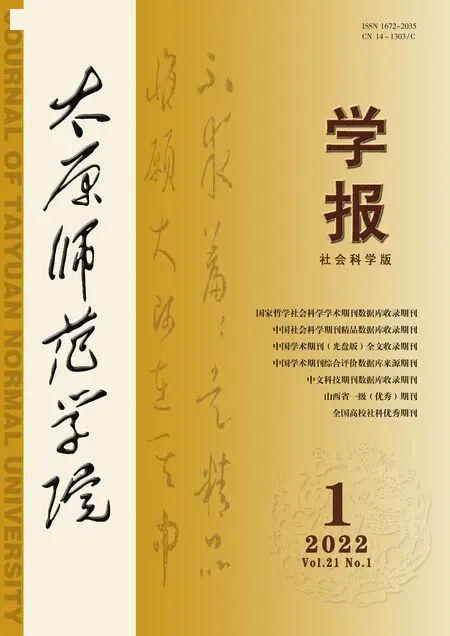傅山“古拙”说辨析
2022-03-18肖艳平
肖艳平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在傅山的文艺论述中,“古拙”是出现频次最高的概念之一。中国古代文艺美学体系中,关于“古”的概念有许多,如“古雅”“古朴”“高古”“雄古”“古韵”“古意”“尚古”“古色古香”等等,用来指称有历史质感的美学风格。“拙”常与丑相关,何以能成为一种审美概念呢?“古拙”在傅山笔下又具有什么含义呢?
一、“古拙”概念辨析
讨论“古拙”在傅山笔下的意义之前,首先要弄清楚在中国古代文艺论述中,“拙”“古拙”是如何发展成为一个审美概念的。老子言:“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1]127在老子看来,大巧才是真正的巧,大巧的东西看起来却像是拙的,因为只有它最少使用技巧。这种“大巧”其实就是“无巧”:“人多伎巧,奇物滋起。”[1]154所以,“大巧”的本质是和“拙”联系在一起的。在老庄哲学中,大巧之“拙”成为比“巧”更值得追求的审美标准。
在唐代以前的很多文论中,大多是在贬义的意义上使用“拙”,认为“拙”指的是那些技巧方面不成熟、粗劣的作品,其义为笨拙、丑拙,与工或巧相对。如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文章第九》中说:“学问有利钝,文章有巧拙。钝学累功,不妨精熟;拙文研思,终归蚩鄙。但成学士,自足为人。必乏天才,勿强操笔。吾见世人,至无才思,自谓清华,流布丑拙,亦以众矣,江南号为詅痴符。”[2]254颜之推正是在贬义的意义上使用“拙”。他认为,拙文终归蚩鄙。因作文者才思枯竭而勉强操笔,遂致其文流于丑拙。
直到唐宋时期,才逐渐将“拙”视为一种审美追求。宋代黄庭坚在《题意可诗后》一文中肯定陶渊明作诗“不烦绳削”之“拙”:“至于渊明,则所谓不烦绳削而自合者。虽然,巧于斧斤者多疑其拙;窘于检括者辄病其放。孔子曰:‘宁武子,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渊明之拙与放,岂可为不知者道哉!”[3]665黄庭坚认为陶渊明诗不烦绳削而合,具有拙与放之特征,“拙”正是陶诗优胜所在。此外,黄庭坚还把“拙”作为书法创作的自觉追求。他在《李致尧乞书书卷后》中说:“凡书要拙多于巧,近世少年作字,如新妇子妆梳,百种点缀,终无烈妇态也。”[4]1407黄庭坚认为,作书应以拙为本。若作字时,各种点缀,各种修饰,终失作字本意。陈师道曾在《后山诗话》中提出作诗“四宁四毋”原则,即“宁拙毋巧,宁朴毋华,宁粗毋弱,宁僻毋俗”。罗大经在《鹤林玉露·拙句》中指出“拙”是一种“浑然天全”境界,写字、作诗都以“拙”成:“作诗必以巧进,以拙成。故作字惟拙笔最难,作诗惟拙句最难。至于拙,则浑然天全,工巧不足言矣”[5]288。罗大经指出,于作字、作诗而言,“拙笔”“拙句”最难,如能拙,则可臻于浑然天全、大巧若拙。姜夔在《续书谱·用笔》一文中提出“宁拙毋工”主张:“与其工也宁拙,与其溺也宁劲,与其钝也宁速,然极须淘洗俗姿,则妙处自见矣。”[6]558姜夔认为书之妙处在宁拙毋工、宁劲毋溺、宁速毋钝,摒弃俗态。“拙”成为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始于唐宋,发展于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拙”论在诗文书画等艺术门类中大兴。叶燮在《原诗·外篇(下)》中说:“汉魏诗不可论工拙,其工处乃在拙,其拙处乃见工,当以观商周尊彝之法观之。”[7]62他以巧中含拙、拙中见巧评价汉魏诗歌。清代的潘德舆在《养一斋诗话》卷九中更是提出了“贵拙不贵巧”的观点:
昌黎《赠东野》云:“文字觑天巧”。此“巧”字讲得最精,盖作人之道,贵拙不贵巧,作文亦然。然至于“天巧”,则大巧若拙,非后世之所谓巧也。孟子曰:“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巧从心悟,非洞澈天机者不足语此。若以安排而得,则昌黎所云:“规摹虽巧何足夸,景趣不远真可惜”也。[8]147
潘德舆认为,“拙”是“天巧”,乃大巧若拙,不事安排,须洞澈天机才能得之。于做人、作文而言,均是“贵拙不贵巧”。概而言之,以“拙”论文艺之观点不胜枚举。
在哪些意义、哪些方面使用“拙”,傅山并没有作系统阐释。但是,通过散见在他诸多文章中的论述,尤其是通过他论文、评诗、品书、赏画等方面的散记,可以探知一二。
二、秦汉文的“古拙”
傅山论文强调拙朴、自然、真实,文应描摹现实。傅山在《览息眉诗有作》一诗中提出:“不喜为诗人,呻吟实由瘼。”[9]56诗人应物斯感,除了受外在自然景物感发外,现实生活中的人生万象也是触发其文思之源泉。在傅山看来,秦汉时代的文章与社会现实最为贴近。但是,文章发展到后来,却越来越不真实,愈写愈巧,流于修饰,流于巧媚,流于浮华,流于轻绮艳丽,“一代逊一代,文章日不真”。所以,尽管如文坛泰山北斗之韩愈,和远古黄帝时的朴拙相比,也得俯就方可:“轩辕看昌黎,山斗须俯就”[9]62。傅山推崇秦汉文,其实崇尚的是秦汉文中呈现出的拙朴之质。
在批注《管子》时,傅山在“不弃我君之有萌中一国而五君之正也,然欲国之无贫,兵之无弱,安可得哉?”处墨笔旁批:“文法之古拙至矣,后人那复能?”[9]1049他认为《管子》文法之“古拙”达到了一定程度,后人文章中很难呈现此境界。在评价《汉书》言句时他经常采用的措辞亦是“迂拙”“拙”等。他指出,《汉书》“语皆迂拙”[9]1610、“句拙而义详。今文学古文者,不能为此,亦不知为此”[9]1623,认为《汉书》语言具有“拙”的特征,今人所作之文远不能达此境界。傅山在批注《汉书》文句“泊如四海之池,遍观是邪谓何?”时朱笔旁批:“真古文古词,义味无尽。”“吾知所乐,独乐六龙,……”诗末朱笔批:“独此章古宕可喜。”[9]1585在“天子大悦,……”句旁,傅山朱笔眉批云:“此段精神陆离矣。‘采来’两字简夋,真古文乃有此不枝之法”[9]1624。傅山指出《汉书》中的文字简夋,精神陆离,唯有真古文才会有此“古拙”“不枝”之法。
如上所言,傅山在批注《管子》《汉书》等秦汉文时,颇为看重文中呈现的“古拙”特征,认为唯有真古文方能达此境界。《管子》《汉书》之文之所以会具有“古拙”“迂拙”“拙”“简夋”“不枝”等特点,其原因即在于它们要么就是秦文,要么“汉文去秦不远”,“至道原不得多言。文字之妙,皆妙于道外”。[9]1130秦汉之文其文法不需巧饰,其语言亦无需炉锤、雕琢,古拙为上。傅山所欣赏的秦汉文的文章之妙即体现在其中呈现出的“古拙”之质上。这种对秦汉文中古拙之气的激赏和他“法本法无法”理念并不相悖。傅山仰慕秦汉文的“古拙”风格,强调要得其精神内核,得其风韵,而并非要如“七子派”般字斟句酌去摹拟秦汉文。
三、诗歌之“古拙”
傅山论诗,推崇“拙朴”风格,反对文词之修饰和巧媚。在傅山看来,诗歌之“拙”首先表现为语言文字之拙朴通俗。傅山说:“文词有帝业,不屑媚兹修。”[9]59诗文者,经国之大业,不屑流于巧、媚、矫饰一途。他在《题汤安人张氏死烈辞后》中说:“文字直如此做,直朴不枝。……清清割割,造此一道,不蔓不枝。……高格高调全不用也。”[9]383他认为作诗须文字上直朴不枝、不蔓不黏、清清割割。诗歌追求真实、自然、淡远之意,须减掉语言上黏连向背处,用最为平实之语言直接抒发内心深处最真实之情感。如此,诗歌全不用高格、高调,也不用矫饰、巧媚之词,乃能达拙朴、自然之境。傅山在写给雪开士的信中说:
从来诗僧,但以句胜,不以篇胜也。宁隘宁涩,毋甘毋滑,至于宁花柳毋瓶钵,则脱胎换骨之法,以魔口说佛事,是大乘最上义。即古以诗名者,亦不多得。……《华严》原有舍得三昧之义。人教舍某字某句,不若自己回复,觉不稳处即勇舍却,如孟生之于破甑。久久,一切俗调尘气,到不得庵摩罗果笔底矣。[9]494
傅山论诗歌之语言强调宁隘宁涩,毋甘毋滑,对轻滑、巧媚之文词极力摒弃。他认为,作诗时,无须苦吟力索全诗之文词,当勇于舍弃某字某句,直抒胸臆,久之,自有佳句,即可绝一切俗调尘气。因此,他赞许杜甫五言诗“粗朴萧散”之语言,认为其优于韩愈五言诗。他用“拙”“朴”等修饰词来形容杜甫五言古诗的语言之妙。傅山在评价杜甫五言古诗《北征》时说:“愈拙愈老。……如话如画,妙在无紧要。”[10]382他认为杜甫《北征》诗胜在语言如说话般拙朴、平实,但是,越拙朴越炉火纯青,越老辣;愈如话,则愈如画,愈有韵味。傅山在评杜甫五言古诗《彭衙行》时也认为该诗“极真极朴”[10]382。
正是因傅山对“拙朴”语言文字的推崇,所以他指出:“作诗只是说话田地,便不可思议矣,只是不可说没道理话耳”[9]819。诗的语言须自然、朴直,如说话般朴实、不事雕琢,便能起到不可思议之效果。但是,如说话般朴直,并不意味着作诗就可信口开河,而是应从朴直处绽放出思想的火花。他在评江淹诗《拟杂体三十首》之《王侍中》时认为“日暮山河清”一句“直朴不凋,却不无气色”。这正印证了傅山“以句胜,不以篇胜”之观点。尽管“日暮山河清”一句用词朴素,语言通俗,但是却诗中有画,如清水出芙蓉,韵味无穷。傅山持同样标准评价韦苏州诗:“苏州《与村老对饮》:‘鬓眉雪色犹嗜酒,言辞淳朴古人风。乡村年少生离别,见话先朝如梦中。’《寄刘尊师》:‘世间荏苒萦此身,长望碧山到无因。白鹤徘徊看不去,遥知下有清都人。’亦是信口率意,读之不觉其俚,直有其高。后人为之,几何不至鼓儿词!”[9]841-842傅山对韦应物诗评价颇高,认为其《与村老对饮》《寄刘尊师》等诗信口率意,读之不觉其俚。韦应物诗歌语言貌似俚俗、朴素,然而,这恰应了傅山之“作诗只是说话田地”的观点,让人不觉其俗,而只觉其高妙和不可思议。
这种对拙朴语言文字的强调,与傅山之主“言语道断”的观点颇有关联。傅山在《用雪峰奔字再广畴昔问诗看法妄之义三十韵》一文中这样说:“语言无道断,鹦鹉踢洲翻。……若本无语言之道可断,何劳尔又自夸踢翻鹦鹉洲也?鹦鹉日日去踢洲翻矣,也是一种套子公案耳。若作是念,莫作是念。”[9]250-251傅山主张“言语道断”。“言语道断”本是佛家用语,《楞伽师资记》中说:“言语道断,心行灭处”。佛家主不立文字,言语道断。也就是说,根本就无需说、不用说、不必说。故而,禅宗讲“世尊拈花,迦叶微笑”,本就无需言语。而傅山也讲“言语道断”。既然言语道都已隔断,连言说都无必要,又何必劳烦去炉锤、雕琢,更不用说去作“徒形似”之摹拟与格套了。因此,对傅山来说,诗歌语言拙朴不雕、自然言说即可,无需修饰。
其次,“拙”表现为情感之真实、质朴。傅山主张以拙朴不雕之语抒发真情实感。傅山在《与右玄书册》中这样评价己诗:“道人之诗,道人之性也,支离率意,不衷于法。道人实不欲妄自位置,极自知丑劣不佳,……要之,中瘕癖者,酸咸土炭,本非正味,而嗜之不改者,病为之也。”[9]407从表面上看傅山是在自我解嘲其诗作,支离率意,不衷于法,因而丑劣不佳,如中瘕癖者,酸咸土炭,本非正味,但是,他仍嗜之不改。实际上,傅山颇以己诗自喜。因此,在接下来的文字中,他说:“右玄习医日精,必有攻瘕癖妙药石,且勿服之,服之则臭诗”[9]407。傅山指出,右玄精于医道,必有治瘕癖之药,但是,这种“支离率意,不衷于法”之病,不需治,治之反成臭诗、劣诗。傅山推崇、看重的恰恰是“支离率意”之诗。这样的诗作,恰是“道人之性”的直接呈现,抒发了创作主体内心深处最为真实的情感,因而是拙朴自然之表现。诗未有简而不挚、挚而不动人者。傅山说:“庾开府诗,字字真,句句怨。说者乃曰:‘诗要从容尔雅。’夫《小弁》、屈原,何时何地也?而概责之以从容尔雅,可谓全无心肝矣。”[9]834傅山认为撇开诗人当时所处的时机、境地而一味强调诗要从容尔雅是不可取的。正如司马迁《报任安书》中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面对凋零的山河、多舛的命运,让他如何从容尔雅!他认为诗歌情感真实最重要,情真才会意切。庾开府的诗就是个人真情实感的流露,所以才能达到字字真、句句怨的至高境界。
再次,“拙”表现为诗境上的自然。傅山这样评价东晋女诗人谢道韫的诗:“谢道韫《登山》诗,如‘气象尔何物,遂令我屡迁’十字,今古词人能有此几句?唐之辋川翁、浣花老,往往得此妙境。偶见谢林风此首‘气象’二句,男子未必能道此句也。尔看之,可造词入微。”[9]509素有才女之称的东晋女诗人谢道韫《登山》诗云:“峨峨东岳高,秀极冲青天。岩中间虚宇,寂寞幽以玄。非工复非匠,云构成自然。气象尔何然?遂令我屡迁。逝将宅斯宇,可以尽天年。”诗人在此诗中凭借登泰山所见“非工复非匠,云构成自然”之景,抒发“气象尔何然?遂令我屡迁”的归隐之志。不仅泰山“非工”“非匠”“自然”,其诗亦是造词入微,写得自然凑泊,天然去雕饰,如羚羊挂角,无迹可寻。傅山认为今古诗人只有王维、杜甫能得此自然妙境。他认为唐代诗人宋之问诗《侵晨发洛阳》虽称不上完美,但其自然之境值得称道。他说:“‘侵晨发洛阳,城中歌吹声。毕影至缑岭,岭上烟霞生。草树饶野意,山川多古情。大隐德所薄,归来可退耕。’此诗不甚全佳,喜其自然。”[9]840
四、书法之“古拙”
与谈诗论文相比,“古拙”一词在傅山讨论书画创作时出现的频率更高。在论书法时他屡次提到“拙”,如“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9]851,又曰“写字无奇巧,只有正拙。正极奇生,归于大巧若拙已矣”[9]511,等等。
傅山在评《曹全碑》时,极为看重其碑文之“质拙不事安排”。他说:“娟秀饶能是其所长,二三奴倠太不展样矣。至于质拙不事安排处,唐碑必不能到也。……碑中凡辵法,皆靡陋不足观。汉碑安得皆佳,但因以见当时风流一二耳。”[9]414他一方面指出《曹全碑》之长处在于“娟秀饶能”,另一方面也认为其中有靡陋不足观处。但是,值得称道的是,也是以《曹全碑》为代表之汉碑高于唐碑之处在于其“质拙不事安排”。此“质拙”恰是傅山最为看重处。他在《张迁碑跋》中提到“碑中古拙及体势风韵者特丹圈之”,关注碑中具古拙风格之字。这种“古拙”风韵是他作书时极力追求的。因此,傅山强调:“是书也,不敢犿活一画,宁钝无利,宁拙无巧,宁朴无妩,如老实汉走路,步步踏实,不左右顾,不跳跃驰。以宗智年少,须虑轻佻走滚。即大利根,亦切莫恃,直以钝根自处,勤谨精进”[9]461。傅山强调作书时宁钝毋利、宁拙毋巧、宁朴毋妩。与利、巧、妩媚相比,他宁愿、更愿选择钝、拙、朴风格。此拙朴风格,正如老实汉走路,脚踏实地,虽钝、拙、朴,但是绝去轻佻,自有其风流之处,方可达字中之天。
对“古拙”风格的推崇与傅山以“汉隶一法”为家学有关。他说“吾家世习汉隶”,因而强调习书时须宗汉法、汉隶:
吾家现今三世习书,真、行外,吾之《急就》,眉之小篆,皆成绝艺。莲和尚能世其业矣,其秀韵又偏擅于天赋,临王更早于吾父子也。至于汉隶一法,三世皆能造奥,每秘而不肯见诸人,妙在人不知此法之丑拙古朴也。吾幼习唐隶,稍变其肥扁,又似非蔡、李之类。既一宗汉法,回视昔书,真足唾弃。眉得《荡阴令》、梁鹄方劲玺法,莲和尚则独得《淳于长碑》之妙,而参之《百石卒史》、《孔宙》,虽带森秀,其实无一笔唐气杂之于中,信足自娱,难与人言也。吾尝戒之,不许乱为作书,辱此法也。[9]862
傅山从自身习书体验出发,指出习唐隶时书法之不足观,一宗汉隶,以汉法为尊,即得汉隶丑拙古朴之妙。因此,作书时,傅山以汉隶、汉法为尊,贬斥唐隶。他极为珍视汉隶,并告诫子孙,不可把汉隶视作游戏来娱乐。关于汉隶之妙,傅山写道:
汉隶之不可思议处,只是硬拙,初无布置等当之意。凡偏旁左右,宽窄疏密,信手行去,一派天机。今所行圣林梁鹄碑,如墼模中物,绝无风味,不知为谁翻摹者,可厌之甚……楷书不知篆、隶之变,任写到妙境,终是俗格。钟、王之不可测处,全得自阿堵。[9]855
汉隶之妙体现在其偏旁左右、宽窄疏密均不事安排,无人为布置之感,唯有硬拙而已。用此法作书,信手写之,天机自来。由宗汉隶,他提到,写楷书亦当知篆隶之变,否则,就算写到妙境,也是俗格。用此汉隶“硬拙”之法恰可以纠正当代书坛之“俗”病。书之“俗”体现在:“俗字全用人力摆列,而天机自然之妙,竟以安顿失之。按他古篆、隶落笔,浑不知如何布置,若大散乱,而终不能代为整理也。”[9]519俗字全由人力安顿摆列写成,而失去古篆、隶落笔时不事布置之天机自然之妙。故而,用古篆、隶“不事安排”“硬拙”之法可以医书法之“俗”。唐人史惟则书法作品《庆唐观金箓颂》中俗病之去除即是明证。在评价唐代书法家史惟则书时,傅山如此说:“史惟则书概痴肥可厌,而此本迳欲去汉不远,有酷肖《曹全碑》者,高韩择木、蔡有邻十数倍。去其唐,存其汉,尽有足观者,不可废也”[9]418。傅山指出,尽管史惟则书法大多痴肥可厌,但是他在书《庆唐观金箓颂》时仍能体现出汉隶之法,有酷肖《曹全碑》处,距汉书境界不远,故其书仍有足观者,亦高于唐书法家韩择木、蔡有邻之流,不可等而待之。
在看似古拙、硬拙的书法创作中,亦可见出“简”和“真”之意味。傅山在《赠梁檀》一文中说道:“……然亦简,惟简乃可近天,繁斯远矣。”[9]530他将简和天之境联系在一起。傅山认为写字也是在一种支离率意、不事安排布置中挥洒出“真”的韵味:“……败笔一枝,是村侨终日握之以刷土墙者,雅与老掔相宜。枒楂其豪迈,然支离实赏厥真,振懒终之。”[9]400不事安顿之硬拙中恰可以欣赏书法之“真”。
五、结语
综上可知,傅山笔下的“古拙”指的是不事安排、不事修饰、不屑巧媚、情感真挚、境界自然之美,是与当时文坛盛行的“巧”“媚”之风对立的风格。“古拙”并非枯淡,是古拙而有风致、风韵。“古拙”在文艺创作中是语言的自然天成、不假雕饰、直朴不枝、不蔓不黏,它摈弃了人工技巧方面的东西,是心灵的自由呈现,得“心手相应之妙”;“古拙”是性情之音,是情感的真实,是人之性也,支离率意,不为成法所困;“古拙”是宁隘宁涩而毋甘毋滑的超脱状态;“古拙”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之境,体现为自然凑泊、返璞归真之意,是素朴、简淡、直率、自然天机之美;“古拙”是和巧饰、妩媚相对的一种状态。
傅山对“古拙”的强调,不仅是其自觉的美学追求,更是其人格精神的自然升华。傅山身处明清易代之际,在这种特殊语境之下,遗民傅山非常注重修身立德、涵泳心性、澡雪精神。因而,傅山在品藻文人时常常从气节出发,倡导浩然之气、与古为徒,贬斥奴俗气。诗文方面,傅山推崇陶渊明和杜甫,书法上以王羲之和颜真卿为典范,绘画上则主张向吴道子和陈洪绶学习。赵园在评论傅山其人时说:“‘拙’在傅氏,是审美更是道德境界。且已非‘本色’,而是出于自觉和提炼。”[11]88白谦慎也注意到了傅山“古拙”概念背后的政治意义:“傅山鼓吹‘丑拙’,和他提倡‘支离’一样,可以理解为在满族统治者和明遗民之间的政治对抗依然十分尖锐的情形下的情感表现。”[12]1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