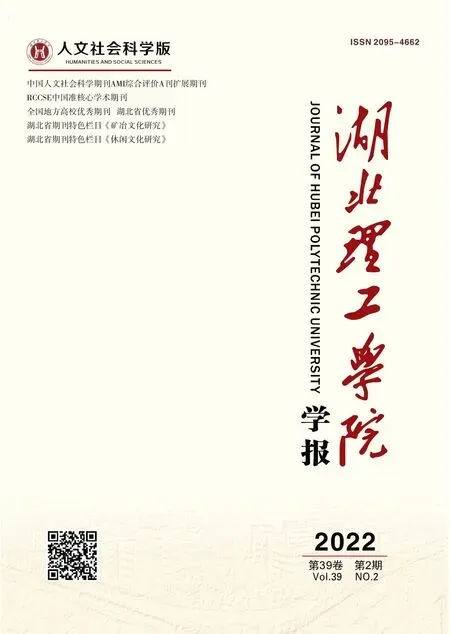摭论安徽义安方言中的民俗文化事象*
2022-03-18姚小烈
姚小烈
(铜陵学院 文学与艺术传媒学院,安徽 铜陵 244000)
引言
民俗就是民间风俗。东汉应劭在《风俗通义·序》中说:“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世代相沿成“风”,群处相习成“俗”。风俗体现着人类对环境的适应性,具有很强的民族性、地域性、社会性和传承性。钟敬文先生指出,民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它源于生活的需要,在特定的民族、时代和地域中不断形成、扩布和演变[1]。约定则俗成,民俗形成之后,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在生产生活实践和社会交往中规范、制约着人们的语言、心理和行为,成为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纵向从时间的维度看,民俗在代际之间传承;横向从空间的维度看,民俗在地域之间扩布。据此,民俗既存在于特定民族的记忆之中,也存在于日常的生产生活实践中。中国的民俗文化事象纷繁复杂,其根脉延伸至生产生活实践的各个角落。
汉语方言是汉语的地域变体,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同地域内部经济、政治、文化的相对独立和地域之间交际的不均匀的产物,也是语言发展的不平衡性在空间上的反映。方言与民俗文化相互包容、互为表里,又相互制约、互为因果,二者同为“地方性知识”。摩尔根在考察印第安部落时发现,“有多少种方言,就有多少个部落”,“人们在地域上相互分离之后,到了相当时间就会引起语言的变化;而语言的变化又会引起利害关系的不一致,终至于各自独立”[2]。摩尔根认为,部落的边界与方言的通行范围大致重叠。方言是特定地域民众的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思维工具,蕴含着他们特有的价值观、想象力与思维方式,同时也是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和传播媒介,是民俗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具有独特个性的民俗文化对方言的面貌产生巨大的影响;而方言在语音、词汇等方面的一些特征也会在民俗文化中体现出来。
义安区隶属安徽省铜陵市,位于安徽省中南部、长江中下游南岸,地处吴头楚尾、南北交界,其民风民俗“既有本土原生态的淳朴风貌,又有与吴楚风俗交融的浓厚色彩,更有与中原风俗一脉相承的历史渊源”[3]。南、北风俗在此交融,使义安逐渐形成了独特且具有深厚人文历史内涵的民风、民俗。明嘉靖《铜陵县志》载:其地“土风清和,民俗淳厚,士笃于学,农力于耕”[3]。境内长江及其支流组成的地表水系发达,西北部河网密集,中部河湖相连。在漫长的农业社会,水稻是当地的主要农作物、重要的生活物资,稻丰则喜,稻歉则悲,由此形成了以“稻作文化”为特色的文化形态。稻作文化对当地人民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信仰产生了深刻影响。方言,承载着厚重而独特的民俗文化,方言本身又是充满地域文化个性的活态民俗事象。义安的民俗文化事象经历了漫长岁月的洗涤、遴选,在动态发展的过程中,其习俗惯制、仪式规程以及口承文学,通过义安方言记录、留存。方言与民俗都是地方性知识,有着共同的基础,方言学与民族学都需要对研究对象进行文化和历史的解释,二者存在互动、互补的关系。本文以义安方言为样本,对方言与民俗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进行考察。
一、义安方言呈现的生产习俗
民俗文化是广大民众生产、生活实践经验的累积,体现着人类对环境的适应性,其形成必然要受到自然地理环境、社会环境、经济活动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生产习俗则源于生产实践,是生产实践中现实需要的体现。特定的生产方式、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着生产习俗的形式与内容。义安有着悠久的水稻种植历史,当地民众长期从事稻作农耕,以稻为食,形成了以“稻作文化”为特色的文化形态。除了从考古学、自然科学的角度研究水稻主体以及水稻的起源、流变、生产技术外,狭义的“稻作文化”主要指“由于水稻生产而影响所及的民间的生活方式和生产中种种习俗,稻区人的性格、爱好以及文化心态等等。一句话,包括由于水稻生产发生出来的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4]。稻作文化深刻影响着义安生产习俗,生产习俗与水稻的生长周期、生产程序紧密连接。根据水稻生产的各个节点,可以将义安生产习俗简单概括为:开耕习俗、插秧习俗、稻期习俗和收获习俗。
(一)开耕习俗
春耕—插秧—田间管理—开镰收割,稻作生产循环往复,似永无止境。但对农家而言,年复一年的劳作固然辛苦,但土地却是“命根子”似的存在,它给予了人们生存的一切。徽州地区“七山一水一分田,半分道路半庄园”的地理环境,使当地民众无田可耕,故“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客观上刺激了商业的发达和徽商文化的兴盛。而义安河网密集、耕地资源丰富,其地素重农耕,形成了“重农轻商”的民风。清乾隆《铜陵县志·风俗篇》载:“其民自农亩外,无商易于四方者。”义安民间有谚:“生意钱,眼面前;庄稼钱,万万年。”“七十二行,种田为王。”
【打春】义安方言称“立春”为“打春”,取“鞭打春牛、鼓励农耕”之意。立春是二十四节气之首,是万象更新的标志,也是一年农事的起点,须行迎春之礼。清乾隆《铜陵县志》载:“先一日,邑宰率官属迎春于东郊,邑人扮杂剧以迎春,观土牛以占岁。次早祀芒神,鞭土牛如仪。”[5]立春之日,春官一边鞭打春牛一边载歌载舞:“一打风调雨顺,二打国泰民安,三打五谷丰登,四打六畜兴旺。”礼成,民众争抢春牛打碎后的泥土,送至田中,祈愿五谷丰登。旧日,立春之礼异常繁复。除“打春”外,还须“送春”“贴春牛图”“耕春”“戴春”“尝春”。“一年之计在于春”,故立春日忌争吵、忌讨债。随着农业生产方式的变化,这些仪式、习俗不断简化乃至消失,唯有“打春”留在义安方言中,但很多人早已不知其本意。
传统农业生产方式“靠天收”,是丰是歉,全凭“年岁”(义安方言词,年成)的好坏。经由不断的观察,配合反复的实证,农家以谚语来概括天气变化的规律。立春日的天气尤为重要。义安民间有谚:“立春雨淋淋,阴阴湿湿到清明。”民间《十二月节令歌》:“最好立春晴一日,农夫耕田不费力。”
(二)插秧习俗
【小人望过年,大人望插田】义安方言称“小孩”为“小人”,称“插秧”为“插田”。小孩期盼新年的好吃好穿好玩,农家则盼春耕插秧,种下一年的希望,故须郑重其事。插田第一天,须备好祭品于秧田畔烧香礼神,行“开秧田门”之礼。田主要备好烟酒、吃食待客,其中“方片糕”不可或缺,寓“年年高”。拔的第一把秧苗,忌朝“太白星”,否则就会犯太岁,稻生瘟。秧插完,众人围住落后的人,以稀泥糊其头脸取乐,民谚“插完秧,糊稻仓”,田主燃放鞭炮,以告四邻,谓“关秧田门”。因“鸡”“饥”同音,待客之时,忌吃鸡。
(三)稻期习俗
【耘田不唱歌,稻都不发窠】稻期大约为120天,主要农事有施肥、耘田、除虫、灌溉、排涝等,其间又要经历梅雨天、三伏天,或连绵阴雨,或炎热伏旱,农事极其艰难。义安农家常于耘田除草之时,引吭高歌,以叹艰辛,以抒胸臆。下附歌词:
《耘田歌》
走下田来就唱歌,手中耘耙田中游。
清除杂草秧棵护,有望今年大丰收。
樱桃好吃树难栽,粑粑好吃磨难硙。
米饭好吃田难做,鲜鱼好吃网难开。
义安有谚:“有水无肥一半谷,有肥无水朝天哭。”虽河网密布,但逢伏旱之时,亦有缺水之虞。农历六月初十日,农家集资为“炎天会”,祀炎天菩萨,并唱大戏三天,谓之“炎天戏”。部分圩区则祭龙王,将龙王塑像从庙中抬出于烈日中暴晒,烧香跪拜,祈求甘霖。
(四)收获习俗
【插秧的酒,割稻的饭】《礼记·月令》载:孟秋之月,“农乃登谷,天子尝新,先荐寝庙”。义安收获习俗由“开镰”“尝新”两部分构成。每年早稻收割的第一天,就是当地的“吃新节”。开镰前,须到田头祭土地神、谷神护佑水稻生长、丰收的功德。收割后,家家户户都会用刚收割的“新米煮新饭”。饭熟后先盛上贡于香案,饷祭祖先。吃新时还讲究在新米中掺一把陈米,寓“新陈相接,永不中断”。
二、义安方言呈现的生活习俗
生产方式不仅决定着生活资料的生产,还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与生活习俗的形成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稻作文化作为一种综合性的文化,不仅体现在物质形态方面,也体现在行为与精神层面。稻作生产是义安农家劳动内容,水稻是他们生活资料中最重要的来源。在劳动生活之外,稻作文化也渗透到义安农家的消费生活和精神生活,由此形成的各种民俗文化事象又被同为“地方性知识”的义安方言忠实地反映、记录。
(一)饮食习俗
【吃饭吃米,讲话讲理】自然生态环境对人类的社会生活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北方寒冷干燥,宜种耐旱的小麦,由此形成了麦作文化;南方温暖湿润,宜种喜水的水稻,由此形成了稻作文化。清人李渔在《闲情偶寄》中写道:“南人做米,北人做面,常也。”南米北面就成了南北饮食习俗最显著的差异。义安所产水稻主要有粳稻、籼稻和糯稻。粳米性软,可煮饭、煮粥;籼米性硬抗饿,宜煮饭;糯米粘糯,宜酿酒或制作粽子。以稻米为原料,衍生出粽子、元宵、米粉、年糕、发糕、糍糕、糙米糖等食物品类。稻米是义安人饮食之根本,民间对稻米产生了一种相依为命的特殊感情,从水稻生产中也凝聚出智慧,这种感情与智慧常常依托俗语得以传递。如铜陵民谚:“吃饭吃米,讲话讲理”,在当地人看来,讲话要讲理与吃饭肯定是吃米饭一样不容置疑,体现出义安人对事理、秩序的尊重。再如“水是水稻命,水多水稻病”,蕴含着“知足常乐”的人生大智慧;“惯儿不孝,壮田出瘪稻”,则是家庭教育经验的总结;“滴水流成河,粒米积成箩”体现的是积少成多、节俭持家的朴素思想。
(二)婚嫁习俗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婚嫁习俗从古传延至今,是在特定语境中约定俗成的一整套议事规程,具有地域性、历史性和延续性。清乾隆《铜陵县志》载:其地“婚礼不事浮华,视门第相当者,与缔姻好,嫁娶从质,无秀灯彩舆之饰,惟导以鼓吹而已”[5]。婚嫁是人生大事,义安虽“不事浮华”,亦有一整套繁琐的程序,主要包括“看亲(相亲)—压庚(订婚)—朝节—婚礼”等环节。
【看亲】双方达成初步意向后,女方家人到男方家实地查看,了解男方家庭情况。如彼此满意,就择期订婚。
【压庚】旧时是订婚的前置程序,后流于形式,合二为一。双方交换“庚贴”,上书双方生辰八字以“合八字”。八字合,“不冲不克”,则择吉日订婚,正式定下婚事。
【朝节】也叫“送日子”,即通知女方亲属迎娶日期,一般选在端午、中秋、春节。旧时婚期一般选在腊月腊八,其时正值农闲。民间有谚:“腊月腊八日子好,多少大姑变大嫂。”“若要发,不离八。”
【婚礼】结婚之日,男方到女方家迎亲。女方大门紧闭,索要“开门礼”,男方须从门缝塞入小额红包,兴尽而止;出发前又有“哭嫁”之俗,先母女对哭,后姑嫂对哭,进而闺中密友、青年媳妇陪哭,俗云“闺女不哭,娘家无福”“越哭越发”;新娘出门叫“发嫁”,新娘须站在筛子里,左右开始歌唱,其词如下:
筛子歌
脚踩筛子圆又圆,留把哥哥要庄田。
山田要得千百亩,圩田要到海那边。
至男方家,所邀先生(一般为族中长者)于车前念诵“退轿神词”,其词如下:
一把五谷撒得开,新娘在轿里站起来。伏羲神通浩荡,胜德昭彰,今有本族某某家,迎娶某某女为媳,今年今月吉日吉时迎亲过门,恐有冒犯诸神或虚空过往,谨备牺牲大礼,净菜净酒,置于路口,拜送尊神。轿前轿后轿左轿右诸神,不敢久留仙驾,某某人及本族百口,恭请有堂归堂,有庙归庙,无堂无庙,各等龙宫宝殿,仙退也。
继而先生用秤杆将新娘盖头挑起,吟唱《挑盖头歌》,其词如下:
小小秤杆乌油油,我给新娘挑盖头。
盖头掀起,公婆欢喜。盖头落地,夫妻和气。盖头落床,子孙满堂。
其他还有《梳头歌》《撒帐歌》《丢筷子歌》《娶亲说好词》《送新郎入洞房词》等,因篇幅限制,不一一赘述。
(三)节令风俗
节日是常态生活的中断[6]。节令风俗是地域文化传延的重要途径或载体。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先民们顺应天时、物候的周期性变化,根据天文、历法知识来划定一年中的时序节令,将生产活动和日常生活纳入自然规律之中,在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约定俗成的具有某种风俗活动内容的时日,是为节令。节令风俗的形成、发展,往往与原始信仰有关,最早的节俗活动,意在敬天、祈年、驱灾、避邪。随着社会的发展、认知水平的提高,节日逐渐从避忌、防范的神秘气氛中解脱出来,并呈现出娱乐化的倾向。各地节令风俗大同小异,既有中华传统文化的共性,又有一定的地域特色。兹举数例。
【岁】古人把黄道附近的一周天分为十二等分,即“十二次”。木星一年经过一“次”,故又称“岁星”。古人称木星为太岁,犯之不祥,故逐渐演化为一种妖怪“祟”。民间农历除夕,终夜不睡,迎接新年到来,谓之“守岁”。守岁时门户紧闭,一说为拒“祟”于门外,一说以示留住时光。义安山区乡镇犹重守岁。年夜饭之后,户户闭门,一家人围“火笼”而坐,由有学问的长者“讲古今”。现虽不烧火笼,但除夕之夜,须灯火通明达旦,谓之“长明灯”,应是此俗之延续。此时,长辈亦须给孩童红包,谓之“压岁钱”,以压邪祟,以保平安。
【开财门】义安人将正月初一至初三称之为“三天年”。于新、旧年交替之时,家家户户开门纳吉,燃放鞭炮,谓之“开财门”。爆竹之后,满地碎红,谓之“满堂红”。爆竹屑一般要保留至初八甚至十五。
【烧茶】初一直至初七,亲戚朋友互相串门,称“拜年”。为款待来客,除了准备各式糕饼、干果,义安人还要“烧茶”待客。所谓“烧茶”,就是煮五香茶叶蛋,又名“元宝”。来客或吃或带,谓之“元宝滚滚来,大家齐发财”。
【癞癞咕年】癞癞咕即癞蛤蟆。“癞癞咕年”指农历正月十五。义安民谚:“正月十五大似年,公婆拜媳妇年。”当地旧俗,儿媳妇终年辛劳,于正月十五可如癞蛤蟆一般静卧休息,词鄙情真。元宵夜游是她们一年中难得的娱乐活动。明万历《铜陵县志》载:“上元,跨街张灯。儿童戏竹马以恣游赏。箫鼓之声彻于闾巷。妇女或夜静游行,掷瓦缶,夜除不祥。”
【送秋】旧俗,于中秋之夜,由家中长辈操持,物色两名或四名男孩,给上年度的新婚夫妇送去“秋实”。一般是柿子、芋头子、枣子等物,取其谐音“思子”“遇子”“早生贵子”。并颂唱《送秋歌》,其词如下:
八月十五天门开,玉皇差我下凡来,玉皇差我来,我坐麒麟来。一走一步踩金阶,二走二步百花开,三走三步花结果,四走四步进房来。走进房来看四边,四边挂了四神仙;走进房来看四角,四块金砖垫床脚;走进房来看四方,四方一看花扬扬。东边挂金鸡,西边挂凤凰,金鸡叫,凤凰鸣,双手捧在床面前。送你好男有五个,送你好女有一双。大郎当朝为一品,二郎及第上皇榜,三郎出入帝王家,四郎骑马戍边疆,五郎年纪最幼小,每日专心坐书房。大姐东宫为皇后,二姐配与状元郎。满门福禄,五世其昌。
三、义安方言呈现的民间口承文学
“口承文学是民众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融入了民众的生活智慧和丰富多彩的语言艺术。流行于民间的口承文学发挥了民众语言表现力和概括力的特点,作品中不但创造了各种艺术形象,同时也展示了丰富而瑰丽的想象,表现着高尚的审美趣味和深刻的理性认识,与其他民俗事象相比,口承文学具有的艺术特性是最大的特色。”[1]民间口承文学主要包括童谣、民歌等,是民众立足生产、生活实践,反映真实生活的口头创作,并主要依靠口耳相传的方式进行传布。方言是民间口承文学的重要载体,赋予民间口承文学以鲜明的地域色彩。
(一)童谣
汉《毛诗古训传》注曰:“曲合乐曰歌,徒歌曰谣。”[7]童谣是在儿童中间流传的简洁短小、符合儿童认知水平和心理特点的韵语,多数没有曲谱,以说代唱,又称“孺子歌”“儿歌”。义安民众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创作了大量的童谣,根据内容大致可以分成催眠类童谣、游戏类童谣和生活类童谣。
1)催眠类童谣大多以摇篮曲的形式出现,又称乳歌、眠歌。泰戈尔在《我的童年》中曾写道:“从母亲嘴里听来的童谣倒是孩子们最初学到的文学,在他们的心上最有吸引盘踞的力量。”[8]朱自清将其称为“抚儿使睡之歌”[9],通过恬静和缓的音韵节奏,使儿童身心安乐,自然入睡。如义安童谣《天上星》:
天上星,亮晶晶。青石板,板石青,青石板上钉银钉。
夏夜在院中纳凉,蒲扇轻摇,孩子在母亲的怀抱中看着满天星斗,气氛宁静、温存。
再如《摇篮曲》:
风不吹,树不摇,小鸟也不叫。宝宝要困觉,眼睛夹夹闭好,我的好宝宝。
催眠类童谣能够给孩童带来安全感,使其身心宁静,伴着长辈的深情低吟慢慢进入梦乡。
2)游戏类童谣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游戏性,儿童通过游戏来认识外部世界。皮亚杰曾说过:“我们不要忘记,儿童年龄越小,游戏和工作的分界线就越不清楚。”[10]吟唱童谣是游戏的重要环节,一般分为游戏前吟唱的童谣和贯穿游戏的童谣。如义安童谣《老鹰捉小鸡》:
老母鸡:天上星,朗稀稀,带咯小鸡来草地。
小鸡:叽叽叽,叽叽叽。
老母鸡:天上来了一只鹰,瞪着眼睛要抓小鸡。
小鸡:叽叽叽,叽叽叽。
老鹰:小鸡小鸡莫叽叽,我带尔们上西天。
老母鸡:小鸡小鸡不要怕,快点躲到翅膀下。
小鸡:叽叽叽,叽叽叽。
老鹰:我来咯了!
游戏规则是先选两个儿童分饰老母鸡、老鹰,其他儿童为小鸡,躲于老母鸡身后。对答完毕,游戏开始。
再如《骑大马》则是众孩童骑着一根竹竿或木棍,通过问答的方式边唱边跑,循环往复:
众:大马大马我来骑,骑到南京城里去。什么城?
分:石头城。
众:什么石?
分:青板石。
众:什么青?
分:竹竿青。
众:撇根棍子当马骑,骑到南京城里去。
3)生活类童谣的内容或歌咏自然万物,或反映成人在生产生活实践中的所思所想,或呈现乡村生活多姿多彩的面貌,其作用主要是以符合儿童认知水平的方式寓思想教化和知识传授于童谣之中。如义安童谣《偷黄瓜》:
小扁嘴,偷黄瓜,奶奶逮到打嘴巴。奶奶尔甭打,乖乖听尔话。
这首童谣语言质朴亲切,易记易唱,于潜移默化之中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社会观,正如义安民谚所言:“树小扶直易,树大扶直难。”再如《猜谜歌》:
什么外圆内四方?铜钱外圆内四方。什么内圆外四方?臼窝内圆外四方。
什么上圆下四方?稻箩上圆下四方。什么下圆上四方?筷子下圆上四方。
儿童生活的主要场景是家庭,对外部世界所知甚少,主要依靠表象符号来代替或重现外界事物。这首童谣通过句式上的反复,将空间上的“上”“下”“内”“外”、形状上的“圆”“方”和生活中的具体物件结合起来,在轻松快乐中完成知识传授。
(二)民歌
民歌是人民之歌,是在不同的自然环境、经济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中孕育出来的、由劳动人民集体创作、口传心记的音乐形式,大多用当地方言演唱,具有鲜明地方性。如《诗经》中的十五国风,就是采自15个地区的带有地方色彩的民歌。义安世称“八宝之地”,义安人民不仅创造了丰厚的物质财富,也创造了多彩的精神文化。唐代诗人李白暮年游经义安,写下《秋浦歌》:“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诗中所提“歌曲”,当是义安民众劳动时的口头创作。按照义安民歌所反映的内容和所承载的功能,大致可以将其分为劳动类民歌、生活类民歌和仪式类民歌。
1)劳动类民歌产生于生产劳动,真实反映生产劳动的状况和劳动者的精神面貌。义安劳动类民歌主要有两种形式:
一是劳动号子,包括舂米号子、打夯号子、搬运号子、打硪号子等。其作用主要是在沉重的集体劳动中协调动作、调剂精神,其结构比较简单。如《舂米号子》:
小小(来)碓窝(就)四(哟)方方(呐呕),一窝(小)糙米(我的)装(的个)中(呀啊哼啊哼)间。
旧时农村多用舂碓人工脱壳制米,专营制米的作坊叫“砻坊”。舂米时,常一领众和,歌唱。全曲共五个乐句,后三句全部由“呵哼呵哼嗨”的衬词扩展而成。
二是山歌,是除劳动号子以外各种山野田间歌曲的泛称。在水稻种植的各个环节中,如插秧、耘田、车水、打稻等等,以及其他劳动过程中,如打铁、行船等,都伴随着劳动的歌声,以振奋精神,缓解疲劳。义安农家口耳相传的山歌主要有《插秧歌》《耘田歌》《车水歌》《割稻歌》《张小二,学打铁》《行船谣》等,其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则属《铜陵牛歌》。2006年12月,《铜陵牛歌》被列为首批安徽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末年间,至今已有 100多年的历史,主要发源地是操铜陵当地土语的乡镇流潭、钟仓、朱村、顺安一带圩区”,著名作曲家时乐蒙曾称之为“汉民族人民的天才创造”[11]。其词多为不固定的即兴问答,俗称“见风挂牌”,即问即答,反复循环。
2)生活类民歌大多是以真人真事为基础,经过民间艺人再加工的叙事韵文,曲调流畅,结构规整,又称之为“故事歌”。生活类民歌内容丰富,包罗极广,有反映旧时婆媳关系的,如《婆媳苦》《苦媳妇自叹》;有反映生活困苦的,如《穷人过年歌》《穷人腊月躲债歌》;有寄托青年男女情思的,如《只爱庄稼种田人》《一粒稻,两头尖》《两人心思差不多》;有弘扬“和为贵、孝为先、勤为本、俭为德”等优秀传统美德的,如《十里亭》《二十四劝》。
3)仪式类民歌。在科学尚不昌明、生产力十分低下的时代,人们受原始宗教的影响,对很多自然现象、社会现象不能做出科学合理的解释。他们对语言的力量十分崇拜,希冀借助语言以禳灾、祈福、告祖等,于是孕育出各种仪式类民歌。根据义安仪式类民歌的应用场景,大致可以分成以下三种类型:
一是与某些传统节日或时令相关的节令歌,如上文所述《送秋歌》。节令歌的内容主要是祈愿风调雨顺、阖家安康等;
二是与男婚女嫁、贺生送亡、新屋落成等场景相关的礼俗歌,如《闹新房撒喜糖》《娶亲说好词》《上梁说好词》等;
三是乡间禳灾、治病时所吟唱的诀术歌,如《夜哭郎》,附词如下:
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哭郎,过路君子看一遍,一觉睡到大天光。
义安旧俗,大人在黄表纸上写上此歌,口念此歌并在路口张贴,当可治小儿夜啼。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生活、生产方式的改变,这些仪式类民歌,或逐渐被人遗忘,或逐渐变成普通的民歌失去原来的意义。
四、结语
语言具有工具性和人文性,它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工具性的缺失最终导致语言的替换;同时,语言与文化紧密依存,无法脱离决定生活基本面貌的民风、民俗。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方言不断被挤压、同化,方言的使用人数不断减少,无方言人群不断扩大,方言的使用场景也逐渐退缩到社会生活中越来越次要的领域。而以方言为载体的文化形式也深受影响,日趋萎缩。以义安方言为例,随着交通的便捷、科学技术的发展、大众媒体的渗透以及普通话的普及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致使义安方言不断被挤压、同化,使用范围不断缩小,主要通行于偏僻的农村地区以及老派人群,形成一个吴语方言岛。
方言既是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其本身也是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地域的民众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各具特色的民风民俗与口头传统,这些文化事象凝固在独特的方言之中,借助方言世代口耳相传,二者相互作用、相互依存、彰显特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每一种方言都承载着生活在特定地域的民众千百年来在生产、生活中积淀的认知成果,存在于真实生活之中,是民众日常经验的一部分。
方言不可再生,方言的濒危和消亡意味着具有独特价值的地域文化的式微和失传。当前,地域文化与方言面对的主要困境,一是文化与方言的自信问题。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社会变迁和发展的过程中,方言也被贴上了“土”“俗”的标签,其承载的地域文化则是“落后的”“消极的”,逐渐萎缩进而被遗忘。方言的式微,折射出的是一种对传统地域文化自信的缺失,也将导致精神归属感与文化认同度的缺失[12]。二是传播渠道的缺失。在当今的文化生活中,流行文化具有广泛的普遍性和渗透性,从家庭结构到社会团体,都蕴含着流行文化的影子。流行文化以其先天的优势,逐渐成为当代社会文化生活中的主要内容。流行文化改变了对于社会阶层“精英”或“草根”的划分,代之以通过对流行文化所秉持的态度为划分依据的“主流”或“非主流”。在文化传播中,流行文化吸引了民众越来越多的注意力,垄断着优质的传播渠道和大众传媒有限的传播资源;而作为小众的地域文化受到的关注越来越少,传播渠道日益萎缩,在与娱乐性较强的大众流行文化的交锋中,始终处于劣势。
地域文化的传承,文化的多样性的保护,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方言发挥着无法替代的作用。方言和地域文化作为一种重要资源,在现代化建设中,如何保护、开发、利用好这些资源,使其在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