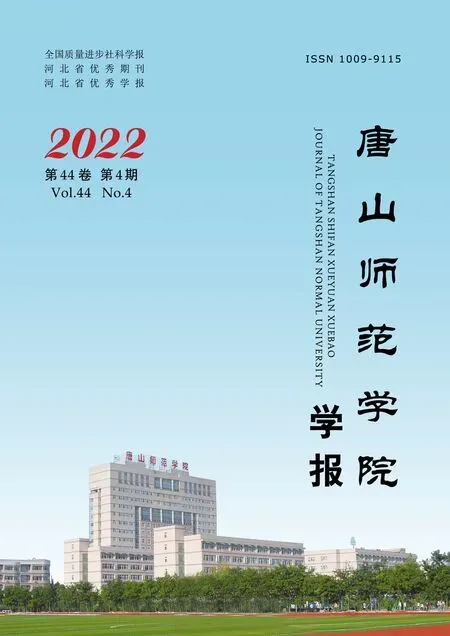同中有异,各具匠心——端木蕻良《风陵渡》与萧红《黄河》的比较分析
2022-03-18查媛媛
查媛媛
同中有异,各具匠心——端木蕻良《风陵渡》与萧红《黄河》的比较分析
查媛媛
(扬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扬州 225000)
端木蕻良的《风陵渡》与萧红的《黄河》两部短篇小说都创作于20世纪30年代末,共同处于抗日战争背景之下,两则短篇小说在主题意旨、情节结构、人物形象与艺术风格四个方面同中有异,各具特色。二者的相似特征体现出特定时期作家趋同的爱国爱民思想倾向,而其不同则归属于两位作家各自的文学匠心。
《风陵渡》;《黄河》;异同;文学匠心
端木蕻良与萧红同为东北流亡作家群中的代表作家,萧红与端木蕻良先后写于20世纪30年代末的两则短篇小说《黄河》与《风陵渡》在多个方面具有相似性。就创作时间与背景来看,1937年冬,萧红、萧军以及艾青、田间、聂绀弩、端木蕻良等作家、诗人应李公朴的邀请,来到山西临汾民族革命大学教书,在抗日战争的特定时期,萧红与端木蕻良都曾在黄土高原停留,有着共同的创作经验,从而前者于1938年9月写下《黄河》,后者的《风陵渡》写于1939年12月。端木蕻良在小说《风陵渡》中创造了一个与敌人同归于尽、壮烈牺牲的平民英雄马老汉;萧红在《黄河》中塑造的山东汉子阎胡子内心深埋着家国破碎的悲哀。写作时间、社会背景的一致为两则小说的可比性打下了基础。
一、构思立意
首先,相一致的社会背景、同一创作时代、相似的自然环境为这两则小说在构思立意上的共性打下了基础。其次,两位作家都来自东北沦陷区,对日本侵略军的愤恨与家破人亡的悲哀情感也有共通性。无论是端木蕻良还是萧红都怀揣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进行作品创作,因而小说意旨趋同,都表现了对日本侵华恶劣行径的愤恨,谴责了日本对中华民族造成的深重伤害,颂扬了人民顽强的抗日精神与强烈的民族意识。
《风陵渡》与《黄河》都以日本侵略华北为现实背景,充分体现了两位作家在民族蒙难之时的强烈社会责任感,二人在选材部分相当考究,并不直接表现宏大的抗日战场,而是将目光移到战争中普通百姓的生活来反映主旨要义。
“描写人民群众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并在战斗中锻炼成长,表现他们乐观进取、智勇兼备、英勇无畏、不怕牺牲,抒写新时代英雄主义华章,正面凸显爱国情怀,乃是端木蕻良小说鲜明的特色。”[1]《风陵渡》写船夫马老汉,一个普通渔民的抗日故事。作者以第三人称视角书写马老汉平凡朴实的一生,借马老汉的眼睛讲述风陵渡一带的风云变幻,如:赵城被汉奸毒死了两个人、报纸上透露出的不利状况、日本人的到来使得百姓背井离乡,各种恶劣行径一步一步激发了马老汉的民族意识,最终与敌人同归于尽,颇具英雄气概。端木蕻良并没有通过塑造典型英雄人物来表现抗日战争,而是从一个普通平民出发,一是能够更为直观地通过平民百姓的生活与心理来感受日本侵华战争的罪恶与百姓的疾苦;二是通过一个平民抗日故事更能体现坚贞的民族节操与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黄河》则是典型地从侧面反映意旨。小说从货船船工阎胡子与赶部队的八路军战士的对话展开,讲述阎胡子从山东辗转关东又逃至赵城,半生飘零的落寞经历。他与八路军战士共乘一条货船,两人的对话构成了小说主要的叙事线索。对话始终围绕着家乡展开,阎胡子这个看似粗鲁的男人提及家乡始终如鲠在喉,由此细节入手窥探人物内心,揭示日本侵华战争给平民百姓带来的心灵与生活的双重灾难。另外,通过一个“死了老婆”仍上前线的八路军战士来展现子弟兵“抗日为先”的无畏精神。子弟兵与平民阎胡子二人之间的心心相惜与互相照顾又很好地体现了军民鱼水情。
文艺作品是客观存在在作家脑海中反映的产物,它一定会受到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思潮和作家思想立场的影响。在意旨上端木蕻良与萧红显而易见的共识是控诉日本侵华的恶劣行径,表现中华儿女抗日的英勇精神。作家不同的气质又造成了两篇小说在主题倾向上的差异。特殊的成长经历造就端木蕻良辽阔与敏感各半的性格气质,而萧红一生命途多舛、敏感细腻。因而,在意旨表达上,《风陵渡》更加倾向于塑造一个平民英雄形象,强调民众抗日的力量。端木蕻良在小说开头写图腾艄公,在结尾写马老汉的亡灵时时发出复仇的笑声,艄公与马老汉之间形成象征关系,马老汉以其爱国精神成为黄河生命的看守者,永久地保留了最高神衹的地位;而萧红则倾向于表现日本侵华战争给普通百姓造成的内心不可言说的巨大创伤。
为了将意旨表现得更为深刻,两位作者又不约而同地赋予黄河以象征性的意味。在《风陵渡》中端木蕻良这样描写黄河:“水流带着黄浊的沉郁,带着从古旧的坟堆激荡出来的先年的白骨,在青草与水藻之间阴沉的泛流。”[2]314从太爷到爷爷再到父亲,而今是马老汉自己,几代人都曾在这条河道上捕鱼,这几代人是同黄河一齐生长起来的,当黄河受到日军侵扰时就如同受污的少女发出憎恨的声音,在端木蕻良笔下黄河象征着受屈辱的中华儿女,文章结尾马老汉将敌人推入大溜也是这些受辱的人们在坚定地复仇。萧红在《黄河》里写到:“站在长城上会使人感到一种恐惧,那恐惧是人类历史的血流又鼓荡起来了!而站在黄河边上所起的并不是恐惧,而是对人类的一种默泣,对于病痛和荒凉永远的诅咒。”[3]294萧红将黄河视作悲哀的象征,风沙、大水、渡河的敌人会带走生长的一切。两位作者不谋而合的给予黄河以象征性意味,又以不同内蕴拓宽并延伸了小说的主题意旨。
二、情节结构
倘若思想内容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思想内容的形成是将生活中的材料整理成为题材,那么情节结构的作用便是有效地将生活加工成具备一定程度艺术层次的状态。《风陵渡》与《黄河》从实际生活与艺术表达的需要出发,所见略同又别处心裁地处理了小说的情节结构。两篇相似的部分是:情节方面都以黄河作为背景,书写在黄河之上一条船一个人的事件。如《风陵渡》以黄河渔业生产集团的图腾——艄公介绍为开头,中间大段书写主人公马老汉的一生,以日军侵入为小说转折点,高潮部分马老汉利用老船将敌人送入黄河大溜,同归于尽,小说结尾部分再次提及艄公图腾,情节上前后照应。萧红的《黄河》将黄河设置为小说的自然环境,设置偶然事件:船工阎胡子与赶部队的八路军战士相遇,在黄河水道上运输军粮,一路上二人展开对话,阎胡子作为输出者,八路军作为聆听者,一步步展开阎胡子的遭遇,也在对话中流淌出普通百姓对人民子弟兵的血肉联系。
与情节相联系的是结构布局,两位作家的共性在于纵向推进的同时又都在横向上作出了自由的延伸。《风陵渡》纵向讲述马老汉抗日的英雄事件,期间又横向拓展了马老汉的生平与性格、黄河艄公图腾、黄河鱼的做法等等,这样的结构更有利于塑造人物形象,突出文章中心,同时使得文章饱满充实,颇具地方特色。《黄河》纵向讲述阎胡子与八路军战士的一路对话,但在对话过程中又横向插入了山东大水、关东逃难、其他难民逃难事件。阎胡子的形象与经历就在这些事件的叙述中逐渐立体了起来,民族危难图也铺开在读者眼里,也正是因为阎胡子面对的倾听者是人民子弟兵才会激起阎胡子这样一个粗鲁的人剖开内心世界,展现自我的脆弱心灵。
高潮部分都放置在小说的结尾处,这样的结构能够将情感推到最高点。两部小说结尾高潮定格画面形成了极大的情感冲击力。《风陵渡》是复仇图,漩涡中的老船上站着大义凛然的马老汉,他正目睹着两个狼狈不堪的日本敌人走向死亡,时时发出酣畅淋漓的笑声。《黄河》则是“报平安”图。“站住……站住……我问你,是不是中国这回打胜仗,老百姓就得好日子过啦?”“是的,我们这回必胜……老百姓一定有好日子过的。”[3]295苍黄的天空下,阎胡子与八路军战士形成的普通百姓与人民子弟兵之间的血肉联系,他们的对话是对“未来”的憧憬,也是对创伤的揭示。
在具体的处理过程中,两位作家都各有功力与匠心。在主人公与外界关系上,《风陵渡》中在马老汉复仇之前并没有其他人物出现,在复仇事件发生之前,端木蕻良竭力描绘马老汉的扁平人生,从太爷辈到自己都没有过传奇的人生,而端木蕻良让马老汉在目睹日本侵略恶行中一步步积累愤恨,最终成长为一位抗日英雄。《风陵渡》情节结构上的匠心正是马老汉的扁平人生与英雄行为之间形成的巨大反差,由此更能突出在普通民众心中压抑已久的民族仇恨也更能突出平民英雄的抗日力量。而萧红在小说《黄河》中是设置了一条“暗线”,明线为阎胡子货船载八路军战士,一路谈话。暗线实则是贯穿“谈话”过程中的“谈家”。整个对话中以阎胡子的表达为主,八路军的聆听为辅,暗线突出一生飘零的阎胡子表达的普通百姓在战争之下的内心巨大创痛,明线两个人物关系构成的正是军民浓浓的鱼水情。
三、人物刻画
小说人物塑造是作者注意的核心。无论是《风陵渡》或是《黄河》,端木蕻良与萧红都精心设置人物形象,通过正面描写与侧面描写相结合的方式塑造人物形象。《风陵渡》马老汉老实但并不自认倒霉,而是在老实与无知中带着几分狡猾,这是马老汉对外的防御方式,端木蕻良直接描写马老汉的基本性格,后面又采用心理描写——马老汉想象自己一个手榴弹甩向敌人的情景,由此表现在马老汉内心压抑已久的民族仇恨,为后文马老汉的反差埋下合理的伏笔。端木蕻良又从正面描写马老汉与两个日本人周旋,“你们会死的”采用语言描写,表现马老汉的平静,又通过河面响起的狂笑声表现马老汉视死如归的英雄精神。《黄河》以动作描写与语言描写正面表现阎胡子山东人的特质,豪迈粗鲁,而通过阎胡子与八路军战士的话里话外离不开家乡的话题从侧面表现阎胡子细腻的内心世界。
在人物刻画上的差异,两部小说也相当明显。《风陵渡》着重通过前后人物的反差来展示一个平民抗日英雄的英勇气概,因而在小说高潮来临之前,端木蕻良在进行人物形象反转的力度上下了相当大的功夫。“时日的风霜在他的灵魂深处刻画下辛苦的铜色,再把些痕迹反映到他枯皱的皮肤和松弛了的筋肉上。他就这样的像黄河似的混水似的一年比一年老了下去。”[2]314端木蕻良塑造的复仇前的马老汉具备平民百姓最典型的特征:贫穷、瘦弱、年迈,对敌人感到恐惧。正是这样的人在小说结尾爆发出了极强的民族意识,成为平民抗日的英雄。为了让人物形象更加具备合理性,端木蕻良在塑造人物过程中也埋下不少伏笔:写马老汉目睹日本人侵略村庄、让马老汉与无耻的敌人产生一次接触,从而暗示马老汉民族意识的不断积累。这样独具匠心的人物形象反差增强了结尾处的力度。萧红的《黄河》在人物形象塑造上最为明显的一个特点是设置了与主人公产生联系的其他人物——八路军战士。塑造八路军形象并不典型,作者通过简单的神态、语言描写出来的八路军总是冷静温和的。“他脸上的表情是开展的,愉快的,平坦和希望的,他讲话的声音并不高朗,温和而宽弛,就像他在草原上生长起来的一样。”[3]293正是这样的八路军战士给阎胡子带来信任感,才使得二人之间自然而然形成了一个倾诉者与聆听者的军民关系,阎胡子作为倾诉者在面对守卫家乡的八路军时不自觉地谈论家乡,从而将阎胡子豪迈粗鲁的山东性格的另外一面展示出来。萧红更善于发掘人物的内心世界,在人物形象塑造上,萧红更为细腻地发现了阎胡子这样的深受战争伤害的平民百姓内心压抑已久的悲哀,颇具代表性。小说中写道:“但当他说完了给他带一个家信,就说他在这河上还好的时候,他忘记了那杯酒是不想喝的也就走下喉咙去了。同时他赶快撕了一块锅饼放在嘴里,喉咙像是有什么东西在胀塞着,有些发痛。于是,他就抚弄着那块锅饼上突起的花纹,那花纹是画的‘八卦’。他还识出了哪是‘乾卦’,哪是‘坤卦’。”[3]295通过阎胡子的动作、神态、心理表现他此时内心的慌乱,带家信成了一种令人如鲠在喉的体验,他的内心对于未来有着极大的不确定性,交织着对苦痛的麻木与对未来的希冀。
四、艺术风格
在艺术风格上,《风陵渡》与《黄河》也颇具比较价值。庄严凝重是两部小说在艺术风格方面的共性,也是两位作家表现出来的共同的情感倾向。小说中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人物神态、内心世界都使得小说笼罩在一片沉郁凝重的氛围之中。两位作者在风格的体现方式上都善于营造环境,端木蕻良的《风陵渡》中书写风陵渡的时间的泛流是迟滞的,一切都是暗淡的昏黄,黄河水也是混黄的,两岸的冲积层如同水牛的脊背。萧红在《黄河》中对于风陵渡环境的描写是苍白、干涩、无光、压抑的。苍凉悲壮的自然环境烘托整个小说风格更为凝重。其凝重还主要表现在小说中涉及到的民众苦难的书写,端木蕻良在小说中写敌人到来之时空洞无人的村落衬得马老汉格外孤独;萧红则写城墙下拾麦稞充饥的难民。其庄严又体现在小说人物虽在苦水中泡着却从未消极低沉,生命庸庸碌碌,也偶有灵光闪烁,普通百姓生命中的庄严往往就在一些瞬间,如马老汉的牺牲、如阎胡子的“家信”都源于爱。
可以说两部小说都蕴含着“悲”感。有所不同的是端木蕻良的“悲哀”中还蕴含“悲壮”。有研究者评论:“相对于萧红的深沉和低吟的写作基调,《风陵渡》则显得高亢和悲壮。”[4]首先,这与两位作家的精神气质有密切的关系,端木蕻良骨子里有着极端的爱与恨,因而在《风陵渡》中他全部的悲壮都在于小说结尾马老汉的复仇上。1930年代端木蕻良深受左翼思想影响,抗日激情高涨,也曾参与过抗日斗争,此期端木蕻良的小说集《憎恨》与《风陵渡》多以表现人民的苦难与抗争为主。“马老汉从心里、眼里、口里、泪里和血里一齐都笑起来了,他的最后的一缕生命,都化作了笑声,尖锐的冲散在天空。”[2]327小说结尾以这样壮烈的书写表现出平民在屈辱与杀虐之下迸发出来的战斗热情,体现出作者对抗敌英雄的热情歌颂,昭示着抗日战争的光明前景,整篇小说都昂扬着一股壮烈基调。
《黄河》的细腻敏感,这部小说在艺术风格上最为明显的特征:沉郁。小说萦绕在读者心头的是阎胡子沉重压抑的内心世界。小说通过阎胡子的大段倾诉写出其内心压抑的原因:父母双亡、有家不能回、辗转逃难的未来……这样的遭遇是当时社会环境下平民百姓的普遍遭遇,阎胡子尚可通过倾诉来释放内心压抑的困兽,那那些无处释放的人呢?萧红如此关注战争之下人们的内心世界,使得整部小说也因此而格外沉郁。《黄河》与萧红的其他作品相比,已相当有力度、有气势,其力度表现在死了妻子的八路军战士仍旧选择上战场,表现在半生飘零的阎胡子主动用货船来来回回载着难民。这样的两个人的相遇给小说“悲”的基调增添了一丝希望。篇末阎胡子与八路军临别时的一问一答是小说的亮色,是光明的尾巴。“‘我问你,是不是中国这回打胜仗,老百姓就得好日子过啦?’‘是的,我们这回必胜……老百性一定有好日子过的。’”[3]295这样的憧憬使得《黄河》不至于落入沉重的深渊。
[1] 马宏柏.端木蕻良小说与中国文学传统[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73.
[2] 端木蕻良.端木蕻良文集:第三卷[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
[3] 萧红.萧红全集[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1.
[4] 王卫平,王博.论端木蕻良及其短篇小说创作[J].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8(4):29-31.
Similar but Different, Each with its Originality: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and
ZHA Yuan-yuan
(College of Humanities,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225000, China)
Duanmu Hongliang’sand Xiao Hong’swere both written in the late 1930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The two short stories hav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four aspects: theme, plot structure, characters and artistic style, and each has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The similar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wo short stories reflect the patriotic ideological tendency of the writers in a certain period of convergence, while the difference is attributed to the two writers’ respective literary ingenuity.
;; similarity and difference; literary ingenuity
I246.7
A
1009-9115(2022)04-0069-04
10.3969/j.issn.1009-9115.2022.04.015
2021-11-16
2022-06-20
查媛媛(1996-),女,安徽池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小说。
(责任编辑、校对:任海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