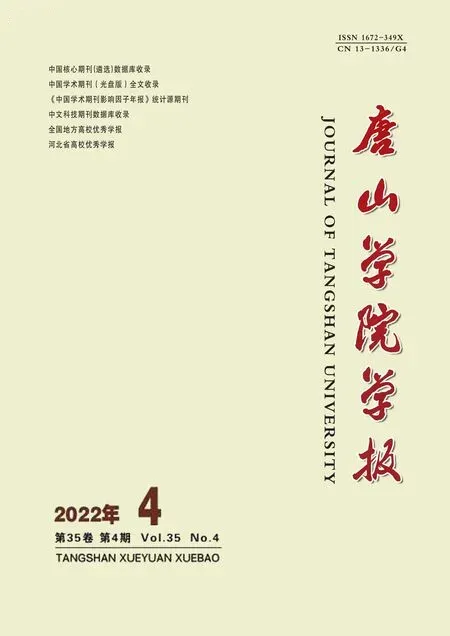中共湖北地区乡村早期组织的创建与发展
——以乡村人口流动为中心
2022-03-18丁君涛张雨尉
丁君涛,张雨尉
(湖北经济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武汉 430200)
中共湖北地区早期组织的创建与发展作为中共党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历来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1-4],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探析了中共湖北地区早期组织创建的原因、发展壮大的背景、活动状况等。中共早期组织首先在上海、武汉等主要城市创建并很快成长为全国性组织,且与共产国际保持联系,究其原因,除了革命理论的引领外,还与我国近代社会大量的人口流动密切相关,但学术界对此却鲜有研究。以社会学理论解读我国近代乡村人口的流动,为研究中共早期组织的创建与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而通过探究乡村人口流动与中共湖北地区早期组织创建与发展的关系,不仅可以填补相关研究空白,还能为探索地区革命史提供新的思路。
一、人口流动为中共湖北乡村早期组织的创建与发展创造条件
(一)人口流动与思想传播
我国近代人口流动异常活跃,特别是大量乡村人口涌入城市,还有一些境外人口也进入国内部分主要城市,武汉凭借其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成为人口迁移的重要目的地。叶调元《汉口竹枝词》中“茶庵直上通桥口,后市前街屋似鳞。此地从来无土著,九分商贾一分民”说的就是武汉外来人口的繁盛。可见,近代武汉人口的迅速增长有相当一部分是依赖外来移民,截至1930年武汉城市人口已突破10万大关[5]。
在迁入武汉的人口中,有农民、商人、学生等,其中学生占据相当大的比重。据统计,1916-1918年间,武汉仅专门大学(含公立、私立,但不包括教会学校)的学生人数已达到1 592人,占全国大学生总人数的9%,仅次于直隶,居全国第二位[6]。与周边的长沙、南昌等城市相比较,武汉在教育方面遥遥领先,在高校数量、教育投入等方面都占据优势,因此周边地区的学生大量入读武汉高校。“新式学校的存在让青年人有了一个较为固定的公共活动场所,同龄人之间的切磋熏染容易产生共鸣,有助于群体意识的形成……新式学校的出现,实际上为中国社会的重新组织提供了最基本的原动力”[2]。可以说,汇聚武汉的青年学生为湖北地区先进思想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成为早期党团组织的骨干成员。
在武汉的流动人口中,数量最多的还是农民。“乡民因农村生活艰苦,羡慕都市繁荣,离村外出者,亦日渐加多,所去之处,以汉口为多。”[7]流入武汉的农民大多从事社会底层工作,主要职业有佣工、码头夫、小艺、苦力、木工、使役、车夫以及各种实业工人等[8]。这些遍布武汉三镇、从事艰苦劳作并往返于城乡间的农民,必然会将城市中的新兴思想带回乡村并广泛传播,这种传播方式为中共湖北地区乡村早期组织的创建与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此外,在迁入武汉的人口中,来自海外的人口数量也显著增加。据统计,1905年在武汉的外国人已有2 142人(1)参见水野幸吉《汉口》第11页,光绪三十四年(1908)刊行。,其中日本人居多,占40%以上。这些外国人在武汉地区创办了大量报刊,如《汉报》《益文月报》等,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汉报》。《汉报》的办报方针是“抑制旧党,援助新党,以助长维新之气运”,标榜“发中国之风气,鼓舞中国之士民,振作政治教育,劝兴农工商务,使中国四万万之民,脱欧人将吞之虎门,以欲全同文同种同洲之义务天职”[9]。这些报刊在当时确实宣传了一些进步思想,也为武汉革命思想的传播奠定了必要的舆论基础。俄国革命胜利后,武汉更成为革命思想传播的重要地带。维经斯基在其1920年的一封书信中提到:“现在实际上我们同中国革命运动的所有领袖都建立了联系,虽然他们在汉口、广州、南京等地尚未设代表处,但我们在那里的工作,可以通过一些朋友即当地的革命者立即得到反映,在汉口,我们有可能吸收一位编外副教授参加我们的工作,此人在中国生活好几年,通晓中文,是柏伟烈教授推荐的。”[10]25从这封书信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共产国际已有意识地借助“当地的革命者”在武汉宣传革命思想。不仅如此,共产国际还有意识地推动武汉党组织的创建,将当地的“益群书店作为一个核心把这些革命团体团结在它的周围”[10]25,“把各革命团体联合起来组成一个中心组织”。共产国际代表在武汉的活动为中共湖北地区乡村早期组织的创建与发展发挥了指导作用。
(二)人口流动与乡村真空
学术界对近代中国乡村人口流动、乡村真空形成及其与中共早期乡村组织创建和发展的关系鲜有研究,从人口流动与乡村真空形成的角度探讨中共早期乡村组织的创建与发展,对于解读中共在乡村站稳脚跟并取得全国胜利的历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我国近代乡村人口的流动对乡村的冲击较大。迁移者的选择理论认为,迁移者并不是原居住地的一个随机样本,它与迁移者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相关[11]106。因此,在乡村,只有青年人与综合素质较高的人才拥有较低的迁移成本和较高的预期收益,换句话说,从乡村迁往主要城市的除了大量迫于生计的农民,还有一些手握社会资源的乡村精英。乡村精英人口的流失、农民阶层的边缘化、宗法制度的瓦解,使近代的中国乡村在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都处于一种真空状态,迫切需要外来力量引导乡村实现再整合,以改变乡村面貌。
在经济方面,一些乡村精英的迁出伴随大量资金从乡村流入城市,导致乡村融资成本进一步提高,借贷利率不断增长,特别是短期借贷增长更加迅猛:“二十二省八百七十一县之报告二千四百零八件中,六个月以内者占12.6%,六个月至十二个月以内者占64.7%。”[12]一部分投机者也趁机从中渔利,“以不到一分的利息,向金融机关借得款项,又把他们所借的款项以三分至七分的利息,借给贫苦的农民,无孔不入地发挥了高利贷的作用”[13],使农民本已困顿的生活雪上加霜,大量农民对这种经济冲击根本无力抵御,不得不放弃农耕到城市打工谋生,乡村土地兼并也因此日益严重。
在政治方面,随着近代工商业的快速发展,城市在政治、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日益重要,政府的资源也较多地流向主要城市,国家政策凸显“马太效应”。原有的乡村治理体系不断坍塌,而现代治理手段又衔接不上,加之“农村中比较有志力的分子不断地向城市跑,外县的向省会跑,外省的向首都与通商大埠跑”[14],故而,乡村的政治权力通常都被在乡的土豪劣绅直接把持,这些人“莫不藉执村事从中渔利,且往往霸公产为己产,肥己身家”[15]。因此,近代乡村在政治上已陷入混乱,农民阶层与乡村社会在政治生活中不断被边缘化,乡村及农民急需在政治上获得相应的地位与建立良性的秩序。
在思想方面,随着乡村传统知识分子不断迁入城市,在新文化难以传入的乡村,旧有的文化传统也难以为继。“频年的革命只是几个城市,内地仍然在换汤不换药的境况中。然而只这换汤式的政府严令下,已是使旧有的思想习惯日在破坏损毁,新的思想生活方式又不曾用‘换汤’的政策建立起来,是以乡间问题比城市来得更复杂可怕”[16]。近代乡村已经在文化上丧失了原有的自我调节机制,迫切需要新思想的传入以推动自身进步。
在湖北地区,大革命失败后的反动统治进一步加强了对武汉等中心城市的控制,而在广袤的乡村则存在大量的权力真空。这种真空状态为中共早期组织在湖北乡村的创建与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一些贫苦农民和乡村知识分子在革命思想影响下,怀着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义无反顾地投身于革命事业,成为革命事业发展重要的力量源泉。
(三)人口流动与“弱关系”
中国“城市文化的近代转型主要是在外力的推引下,通过通商、建租界、传教等途径输入外来文化而进行的”[17],正如鲁迅先生所描绘的:“中国社会上的状态,简直就是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自油松片以至电灯,自独轮车以至飞机,自镖枪以至机关枪,自不许‘妄谈法理’以至护法,自‘食肉寝皮’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义,自迎尸拜蛇以至美育代宗教,都摩肩挨背的存在。”[18]而大量乡村人口的迁入则使这个转型过程变得更加复杂。
农民入城大多具有群聚性。社会学迁移者网络理论认为:“迁移者并非仅仅是年轻人和高素质的人口,而是与迁入地人口有某些联系的人,他们与迁入地已有移民的联系构成的网络成为一种社会资本,起着降低迁移成本、增加收益和减少风险的作用。”[11]106因此,武汉的很多产业工人都呈现出明显的地域聚集性。如纱厂工人主要来自武汉三镇及周边的青山、蔡甸、黄陂、沔阳、鄂城和黄冈等地,还有一部分来自下江一带,另有少部分来自粤、湘地区[19]。入城的同乡农民间保持着紧密联系,并有意识地复刻原有的生活环境与文化,这种状况在当时是比较普遍的。同乡集群生活有利于文化适应,并逐步转化为一种“弱关系”,“通过弱关系可以获得更多的非常重复的或非多余的信息”[20]322。这种以“弱关系”为通道的传播格局对中共早期的思想宣传和组织发动非常有利,也是中共早期组织在武汉等主要城市和广袤的湖北乡村能够获得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熟人社会与革命落地
近代中国的乡村社会是一种以宗族关系为纽带的熟人社会。乡村运动的最大意义就是“宣传农民”[21]。中共湖北地区乡村早期组织的创建与发展,就是充分利用广大乡村熟人社会的特点,借助组织成员特别是青年学生在乡村的社交网络,动员宗族成员、熟人等加入组织以壮大力量,同时在乡村广泛建立农会、开展演讲、印刷刊物等以加强思想宣传。如林育南等人在黄冈成立平民教育社,“在年假期间,各学生回乡……鼓吹平民教育,作农村运动的先导”(2)参见中央档案馆《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2-1924)》,1983年第113页。;恽代英、林育南、林育英等在黄冈成立了共存社[22];还有一些学生在罗田、麻城成立了罗麻青年协会(3)参见中央档案馆《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群团文件1925-1926)》,1983年第287页。。特别是农民协会工作在这一时期取得了显著成果,以农运工作做得较好的枣阳地区为例,这区农协1925年底成立,“加入组织的有三十余庄,人数在千人以上……几次反抗官绅的大运动,均得胜利”(4)同②,第286页。。
中共早期开展农民运动非常倚重回乡学生。武汉的党员有三分之二为学生,相当一部分学生党员、团员在城市接受训练后被派回故乡开展工作。如枣阳地区党组织领导人程祖武即为枣阳当地人。中共早期的发展网络“基本都是利用传统的同乡关系、师徒关系、同宗关系等由复杂历史积淀而成的传统社会资本构件来推展的”[23],“正是通过……这些方式,涵盖党、政、军、群等各方面的庞大的中共组织体系在较短的时间内得以建立起来,关于中国革命的种种设想和计划也初步实现了不同程度的落地”[2]。总之,中共先进的理论宣传与传统的熟人社会相结合,使其早期组织短时间内在湖北乡村得到了快速发展。
然而,成果的背后是过程的艰辛,实现中共先进理论宣传与传统熟人社会相结合既要解决理论问题,又要解决策略问题。成立组织、开展集会宣传等城市化的传播手段无法迅速适应乡村现实,对农民的吸引力极为有限,对农民的宣传也就难以取得明显效果。对此武汉地委曾批评道:“武汉的同志三分之二为学生……而学生同志又多在城市,所以更加和农民隔绝。”(5)同②,第286页。“在韦伯看来,传统中国人之间存在着普遍的不信任,传统中国的社会信任是缺失的。”[20]281由于“中国社会的信任半径常常局限于家庭和有血缘关系的群体内”[20]280,因此中共早期乡村组织吸纳的人员主要是回乡党员、团员的宗族亲戚及一些较有影响力的乡村知识分子。虽然这种方式使中共早期组织在乡村的发展较快,截至1927年4月,“除武汉三镇外,湖北省各地党支部增至400多个,党的组织遍及50多个县、市,党员逐月锐增”[24],但由于返乡党员、团员大多出身于乡村上层社会,并非贫苦农民,在其以传统熟人社会同心圆模式吸纳成员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有传统社会网络渗入组织之中,“如公安县之四十一个同志中,竟然有三十九人为土豪劣绅及与土豪劣绅利害一致的成份”(6)参见中央档案馆《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6-1927)》,1983年第274页。。传统社会网络与中共组织之间互相渗透,必然会扰乱中共早期组织的内部沟通,导致机会主义在组织内部比较活跃。
中共早期这种借助乡村传统网络建立起来的组织很难长久稳固,原因有三。首先,对于乡村而言,从城市返乡的党员、团员在文化属性上已属外来者。传统乡村社会属于典型的机械团结社会,需要强大的集体意识维系社会秩序及成员间的联系,故此以中共的革命理论替代传统乡村的集体意识,必然是一个艰难且持久的过程。其次,传统乡村是一种典型的命运共同体,无论个体在形式上如何分割,成员间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由于从城市返乡的党员、团员在文化属性上已属外来者,因此在宣传党的理论、主张的过程中,仍要面临身份认同的问题。如“随、襄同志……是本地人,顾虑身家,工作方面有许多顾虑”(7)同上,第270页。,“各区同志均各行其是,完全不执行省委决定的策略,甚且与此策略背道而驰”(8)同上,第273页。。再次,这种组织发展方式导致占乡村多数的农民难以进入领导核心。据中共党史研究室相关资料记载,“1925年以后……指导机关仍然没有群众化……从上至下的指导机关,无形中逐渐小资产阶级或民族资产阶级化”[25]。这也是导致机会主义错误的重大隐患。此外,大革命失败后,原已逃离乡村的土豪劣绅又纷纷回乡,借助宗族、地缘等传统社会网络扩大力量,打击中共乡村组织。据中央档案馆资料记载,沔阳地区“土劣活动甚烈,纷纷下乡,并组织暗杀队三十队,欲乘机屠杀党部工运农运人员”(9)同上,第218页。;汉川地区“土劣以军队为护符,除告状外并在各处捕人,打房子、封房子”(10)同上,第219页。等。乡村反动势力利用传统社会网络对中共组织的反扑,使中共乡村组织工作一度陷入被动。大革命的失败进一步证明,完全依赖传统社会网络发展组织并不现实。此后,中共逐步调整政策,使党的组织建设更加完善、战斗力不断提升。
三、中共早期的组织再造与党员流动
大革命失败后,乡村成为中共早期组织发展的重心,大批党员流动到乡村。同时,大革命的失败也使中共内部产生剧烈震荡,党内各种分歧、矛盾复杂,组织结构受到冲击。因此,中共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党内与党外环境,不得不加强组织纪律性与纯洁性建设。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共对于乡村党组织的管控也显著加强,党内人员的调动与处理也愈加频繁,特别是中共善于通过党员的调动不断完善民主集中制,提高党内纯洁性,保持组织战斗力。
1927年中共出台《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其中提出中央要督促和帮助湖北省委进行改组并组织审查委员会,审查省委以下各级党部委员会之成分[26]。中共湖北省委也按照中央精神强化了组织纪律建设。如中共湖北省委通告(第6号)即要求下属各级党组织将秋收暴动以来犯错误同志的详细信息、犯错情况、处理状况等报告给省委,并强调如有延迟不报、敷衍从事,将以党的纪律制裁(11)参见中央档案馆《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省委文件1926-1927)》,1983年第447页。。这一时期的党员发展工作也更加规范,保证了党员的忠诚度。提高乡村组织纯洁性的工作,则通过派遣可靠党员下乡来完成,并建立了完善的组织制度。罗亦农被派往长江局工作时就指出:“我在此间的工作,是按照中央指示湖北革命的前途这一观察上,积极改造湖北的工农运动与党的组织。”(12)同上,第388页。中共湖北省委主要领导也认识到干部下乡的重要性:“(乡村)党的力量太弱,尤其是同志政治观点太薄弱,能够了解党的策略的简直是少到了极点,为使党能领导乡村的革命起见,省委应加派得力同志下乡,尤其是要加重巡视员的工作。”(13)同上,第400页。这一时期有200多名党员干部被派往湖北地区广大乡村,帮助乡村开展组织建设。中共还建立了巡视员制度,这种制度对基层党组织建设一度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通过派遣可靠党员下乡和建立巡视制度,不仅推动了乡村早期党组织建设,保证了党内的纯洁性,而且确保了中共对于基层党组织的把控。
“八七”会议后,中共通过大力批判党内机会主义及对前一阶段工作的反思,对基层组织建设存在的问题有了深刻认识,更加注重对工农党员的培养,在基层党组织建设方面也强化了理论及策略指导,“改造支部领导,建立支部生活……改造各级指导机关……积极培养和引进工人干部”[27]。经过大力整顿,党内的纯洁性更强了,党组织建设更加严密、规范,中央对于基层党组织的把控力显著增强。为了进一步加强组织建设,中共还派遣党员赴苏联学习,提高其理论水平;同时又有大量留苏学生党员回国,深入基层开展工作。无论是派党员下乡改进组织,还是派党员赴苏联学习,其目的都是加强组织内部思想的同一性,使组织在应对复杂环境时能够做到中央与基层之间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最终达成组织的稳固化。通过总结中共湖北地区乡村早期组织创建与发展的历程可以发现,中共组织建设一直是在发展中摸索、在挫折中成长并逐步走向成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