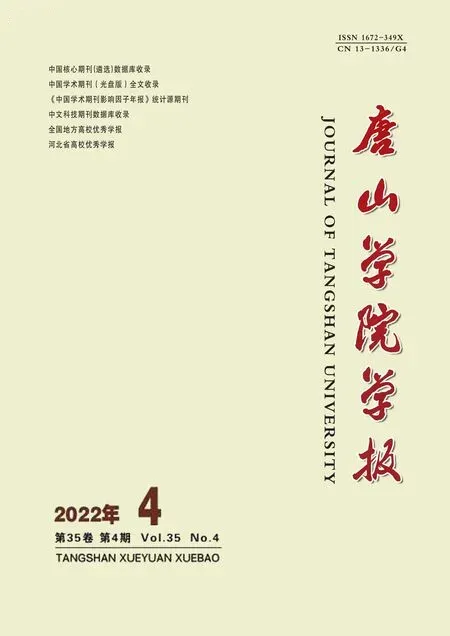明代温庭筠诗接受研究
——以明代唐诗选本为中心
2022-07-19廖明星
廖明星
(重庆师范大学 文学院,重庆 401331)
作为晚唐著名的词人、诗人,温庭筠的词秾美铺陈、清俊深曲、辞藻华美,因而被誉为“花间派”之鼻祖,但温诗在文学界的关注度却始终不及温词,直至20世纪末有关温诗研究的论著才渐多。其中,林邦钧[1]在其《论温庭筠和他的诗》中指出了温诗“典丽精工、婉曲含蓄”的特点,并引起了文学界对温诗研究的重视,进而带动了有关温诗研究论著的出版。但已有研究成果大多是对温诗风格、体裁的研究,而有关温诗接受研究的论著却很少,目前仅见张自华[2]的博士论文《温庭筠诗歌研究》。文中首次对温诗接受史进行了梳理,详细考察了明代几本著名诗话和唐诗选本对温诗的接受情况,但文中选用的明代唐诗选本较少,只列举了两本,不足以充分呈现明代温诗接受的具体情况,除此还未见其他从唐诗选本角度考察明代温诗接受情况的相关论著。明代印刷技术的提高为大量唐诗选本的刊印奠定了基础,具有代表性的如高棅的《唐诗正声》、李攀龙的《唐诗删》、曹学佺的《石仓历代诗选》等。孙琴安[3]16认为,唐诗选本能够反映某一时代对唐代某一诗人的接受度,因此“唐诗选本很有些温度表的味道,它可以使我们知道这个朝代对某一诗人是冷还是热,冷到什么程度,热到什么程度”。本文通过考察明代具有广泛影响的唐诗选本选录温诗的情况,结合明代政治、社会环境及文学思潮、价值追求等,对明代唐诗选本温诗接受差异及其成因进行研究。
查清华[4]10将明代唐诗接受史划分为三个时期:前期为洪武元年(1368)至成化末年(1487),中期为弘治元年(1488)至隆庆末年(1572),后期为万历元年(1573)至崇祯末年(1644)。以此为依据,本文分三个阶段来考察明代唐诗选本对温诗的接受情况。
一、明代前、中期唐诗选本对温诗的接受情况
明初复古思潮兴起,宗盛唐的文学理念逐渐萌芽并壮大。顺应这一思潮,明前期的文人开始重刊前代唐诗选本并重新编订符合时代审美需求的唐诗选本。其中,高棅的《唐诗品汇》《唐诗正声》《唐诗拾遗》及康麟的《雅音会编》是具有广泛影响的唐诗选本。这四个唐诗选本对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温庭筠诗的选录情况见表1。

表1 明前期代表性唐诗选本录诗情况
高棅于明初洪武年间编订的《唐诗品汇》共90卷,选取了620位唐代诗人,录诗5 769首,是一部较全面而又影响广泛的唐诗选本。他将选录的唐诗分为初、盛、中和晚唐四期,并“以初唐为正始,盛唐为正宗、大家、名家、羽翼,中唐为接武,晚唐为正变、余响”[5]14为标准来编录唐诗。高棅在《唐诗品汇·总序》中对晚唐诗的评价是“降而开成以后,则有杜牧之豪纵,温飞卿之绮靡,李义山之隐僻……此晚唐变态之极,而遗风余韵犹有存焉”[5]9。可见,高棅侧重于选录盛唐诗,而对晚唐诗多有排斥。《唐诗品汇》按照以盛唐诗为“正”的诗学标准,选录盛唐诗人李白诗386首、杜甫诗271首、王维诗163首,选录晚唐诗人温庭筠诗30首。选录最多的李白诗约为温庭筠诗的13倍,所录温诗含古诗7首、绝句11首、律诗12首,除七言绝句被单独列入“正变”外,其余均被列入“余响”。《唐诗品汇》称温庭筠七言古诗“温之美丽,虽卓然成家,无得多矣”[5]375,意思是温之七古虽然卓越并自成一家,但并不符合编订者的审美标准,所以不必多录。后高棅又编订10卷《唐诗拾遗》,补录61位唐代诗人的954首诗,其中录温诗15首,补录占比仍然不高。《唐诗正声》进一步体现了高棅宗盛唐的文学理念,在所选录的931首诗中仅录温诗3首,足见其对温诗的疏略。康麟的《雅音会编》编成于天顺七年(1463),共12卷,按照平声三十韵的顺序编排选录3 800余首唐诗,其中录李白诗293首、杜甫诗1 003首、王维诗57首、温诗21首,从中可见康麟以盛唐为正宗的文学理念,尤可见其对杜甫诗的极度推崇。从以上四个明前期重要唐诗选本选录温诗的情况来看,相较于温诗现存世的350余首[6],入选总量不及两成,可以从一个侧面证明明前期文人选家“诗必盛唐”的文学理念已经萌芽,即如明初苏伯衡所言:“自李唐一代观之,晚不及中,中不及盛。”[7]
明中期,在前、后七子所提倡的“诗必盛唐”的影响下,文人选家在选录唐诗时进一步表现出对晚唐诗人及其作品的排斥态度。其中李攀龙编订的《唐诗删》《唐诗选》深受文人喜爱,《唐诗选本提要》就提到:“李氏一选,声誉鹊起,身价百倍,批注者蜂拥而起。《三体唐诗》《唐诗鼓吹》《瀛奎律髓》等一批名重一时的唐诗选本,均被打入冷宫。”[3]11此外,邵天和编订的《重选唐音大成》、胡缵宗编订的《唐雅》在当时也具有较大影响。上述四个明中期唐诗选本选录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温庭筠诗情况见表2。

表2 明中期代表性唐诗选本录诗情况
《唐诗删》是李攀龙编订的《古今诗删》中的唐诗选录部分,与《唐诗选》一样都反映了后七子宗盛唐、贬中晚唐的诗学理念。《唐诗删》共选录155位唐代诗人的740首诗,其中李白诗最多,而温诗1首未录。《唐诗选》共选录128位唐代诗人的465首诗,其中杜甫诗最多,而温诗仅录1首。李攀龙作为后七子的领袖人物,“诗必盛唐”是其编订诗选的主导思想,从《唐诗删》《唐诗选》对晚唐诗的排斥大致可以看出明中期文人对唐诗接受的整体态度。嘉靖五年(1526),邵天和编成15卷《重选唐音大成》,共录唐诗1 565首,其中杜甫和李白诗最多,分别为251首和163首,温诗得录10首,均被列入“余音”部分。胡缵宗在嘉靖二十八年(1549)完成了《唐雅》的编订,共选录唐诗1 263首,其中李白诗129首、杜甫诗136首,而温诗仅录4首。
明前期影响较大的唐诗选本对温诗基本持疏略态度,明中期受前、后七子“诗必盛唐”文学主张的影响,选家对温诗更加排斥,选本对温诗的接受情况在明中期跌入了低谷。从明前、中期唐诗选本选录温诗的情况可以看出,高棅等人更看重温诗中的七言绝句,如《赠少年》《赠弹筝者》《杨柳枝》等,又如李攀龙的《唐诗选》仅录温诗1首,即为《杨柳枝》,究其原因是温庭筠的七言绝句“声皆浏亮,语多快心,此又大历之降,亦正变也”[8],契合了当时文人的审美标准。
二、明代后期唐诗选本对温诗的接受情况
明后期,统治阶层放松了对思想文化的控制,心学等众多学派呈现蓬勃发展的局面,文学思潮渐趋多样,其中以李贽提出的“童心说”影响最为广泛,其主要思想是以追求童心的纯真来批评复古派一味模拟前人诗歌创作的主张[9]。在李贽思想影响下,公安派提出“性灵说”以抨击复古派“诗必盛唐”的主张,竟陵派也主张追求“真”“趣”“情”等。在包容、多元的文化环境中,明后期选家对唐诗的接受也逐渐多元化。后期虽仍有选家受前、后七子“诗必盛唐”影响而多重视盛唐诗,如唐汝询的《唐诗解》和钟惺、谭元春的《唐诗归》,但也出现了陆时雍、曹学佺等选家,明显提高了对中晚唐诗的接受度,这一点充分体现于他们所编订的《唐诗镜》和《石仓唐诗选》中。上述四个选本中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温庭筠诗选录情况见表3。

表3 明后期代表性唐诗选本录诗情况
唐汝询在《唐诗解》“凡例”中提出,“一遵《品汇》之例”,“延礼(高棅)之选,已无遗珠,故是编采掇《品汇》之英,不复外索”[10]。可见,唐汝询延续了明前、中期宗盛唐而贬晚唐的思想。《唐诗解》共50卷,选诗1 546首,录诗人200位,其中仅录温诗4首,晚唐另一位重要诗人李商隐的诗也仅录5首,李白、杜甫诗的数量之和大约是温诗的44倍,可见在唐汝询那里晚唐诗仍不受重视。钟惺、谭元春的《唐诗归》共36卷,分为初唐5卷、337首,盛唐19卷、1 162首,中唐8卷、487首,晚唐4卷、255首,其中录盛唐诗最多、晚唐诗最少,仅录温诗4首。《唐诗归》录晚唐诗255首,其中曹邺32首为最多,仅录温诗4首,可见同为晚唐诗人,温庭筠仍被忽视。
从明后期重要唐诗选本陆时雍的《唐诗镜》中,可看出选家对温诗的接受情况开始出现转折。《唐诗镜》选诗人307位、录诗3 158首,其中录温诗47首,而杜甫诗是377首,较之以往温诗占比明显提高,可见选家对温诗的接受度比明前、中期有所提高。曹学佺编订的《石仓历代诗选》是明后期一部规模较大的历代诗选本,其中《石仓唐诗选》共100卷,录盛唐诗2 259首、晚唐诗2 623首,特别是录温诗74首。由此可知,晚唐诗受到曹学佺的重视,与其相应的是温诗的地位也稍有提高。
明后期文人对温诗的接受情况趋于多元化。如唐汝询等人继续秉承“诗必盛唐”的文学理念,对晚唐诗持排斥态度,因此选录温诗极少;钟惺、谭元春以竟陵派“独抒性灵”为选诗宗旨,对温诗选录亦极少,仅录了4首“幽澹动人”的五言律诗。选家对温诗接受的转折从陆时雍、曹学佺开始,陆、曹两人一改前人对晚唐诗的疏略态度,开始发掘其艺术价值,因此温诗也得到更多关注,其古诗、律诗、绝句也更多地被录入选本中。总体来看,明后期温诗地位有所提高。
三、明代温诗接受差异及其成因
温诗的接受度由明前、中期的持续低迷到明后期的多样化转折,究其原因与明代的社会政治环境、文学思潮及诗学观念变迁密切相关。
(一)社会政治环境与文学思潮的变迁
社会政治环境与文学思潮通常会影响某一时代的文学接受情况。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主张恢复汉族文化,提出“衣冠如唐制”[11]525,希望重回大唐盛世,“复古”成为明前期的主流思潮。同时,为加强君权和专制统治,明代统治者大力宣扬程朱理学,并于明成祖朱棣统治时期确立了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社会思想受到严厉控制。在文化方面,朱元璋指出“古之乐章和而正,后世之歌词淫以夸”[11]2521,主张弘扬儒家诗教。在这种政治思想和文化主张影响下,明前期的文学审美追求平正典雅、温柔敦厚,强调诗文为政教服务,以“有补于世”为创作目的,须“合于道”,即“在上者莫不歌咏帝载,以鸣国家之盛;其居山林者,亦讴吟王化,有忧深思远之风”[12]。明初金幼孜也提出“大抵诗发乎情,止乎礼义”[13]。在《故朱府君文昌墓铭》中,宋濂也曾说“诗之为教,著于礼经;温柔敦厚,本诸性情”[14],强调诗应崇经原道、注重社会教化作用。因此,在复古思潮盛行的明前、中期,盛唐诗得到了文人的极力推崇,大众接受可谓一时无两。而晚唐诗的社会教化功能则明显不足,原因在于“诗人自觉地消去儒家的用世之心而与僧道认同,从未有像晚唐这样普遍”[15],因此晚唐诗人及其作品在此一时期备受冷落实属必然。
到了明中期,明孝宗朱祐樘勤于政事、开创治世,史称“弘治中兴”,社会环境相对稳定。以李梦阳、李攀龙为代表的士人阶层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复古运动,宗盛唐文学思潮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顶峰。这种社会政治环境不仅影响了当时文人的文学创作,而且影响了文人对唐诗的接受态度,并且直接体现于唐诗选本之中,代表盛唐气象的李白、杜甫诗倍受青睐,而晚唐诗凄美、艳丽的风格则与明中期的“盛世”期望不合,同时也背离了儒家传统的诗学审美标准。在晚唐诗中,温诗尤多“艳丽”之气,既无补于世,又欠“温柔敦厚”,故明前、中期选家对温诗的接受度都不高。
后期的明朝统治已然走向没落,在政治环境愈加腐败的同时,思想文化却日渐活跃,商品经济也得到一定发展,特别是理学的正统地位受到挑战,“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16]7222,社会上掀起了反理学、反复古、强调个性真情的文化思潮。嘉靖、万历年间,阳明心学蓬勃发展,“其说风靡天下”[17],李贽的“童心说”、公安派的“性灵说”及汤显祖的“至情”追求等一些新学说、新主张也随之兴起。在社会文化思潮的巨大变迁中,文学创作趋向自由,社会审美追求趋向多元,“和而正”“诗必盛唐”等儒家正统观念对文学创作和唐诗接受的影响明显减弱。正如钱谦益所说:“万历之际,海内皆抵訾王、李,以乐天、子瞻为宗,其说倡以公安袁氏。”[18]公安派等文人群体摒弃了此前“诗必盛唐”的审美取向,开始重新审视初、中、晚唐诗的价值,温诗价值始得以逐渐被发掘。总之,社会政治环境与文学思潮的变迁,是明代前、中期至后期唐诗接受差异产生的根本原因,尽管不同历史阶段接受程度不同,但无论如何是明代开启了唐诗接受的盛世。
(二)文学主张与诗学理念的变迁
“风俗习惯、时代精神对于群众和对于艺术家是相同的,艺术家不是孤立的人。”[19]明前期,在社会政治环境和复古思潮的影响下,文坛上“透露出一股拟古和崇尚唐音的风气”[20]。为迎合这种文学主张,不少文人开始重新编订唐诗选本。选家高棅在其唐诗选本《唐诗品汇》中提到“开元天宝间,神秀声律,粲然大备,故学者当以是为楷式”[5]6,这种观点在明前期选家中有一定代表性,反映出选家对盛唐诗的推崇,且多将盛唐诗作为评判初、中、晚唐诗的参照。明代文人深受《唐诗品汇》的影响,《四库全书总目》中就曾记载:“终明之世,馆阁以此书为宗。厥后李梦阳、何景明等,摹拟盛唐,名为崛起,其胚胎实兆于此。”[21]明中期,前、后七子李攀龙、何景明等人极力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认为“文自西京、诗自中唐以下一切吐弃”[16]7307,宗盛唐的诗学理念至此达到高峰;同时明代文人多持“体以代变”“格以降代”[22]的观念,以时代划分来判断诗之优劣。温庭筠作为晚唐诗人自然是在被“吐弃”之列,又因其“绮靡”的诗风与明中期社会的审美要求相背而愈加遭到排斥,因此,明前、中期高棅、李攀龙、邵天和、胡缵宗等重要选家均对温诗持排斥和疏略态度。
明后期,思想相对自由,文学观念多元化,选家对温庭筠等晚唐诗人的态度出现分化。唐汝询等人仍沿袭明前、中期宗盛唐的诗学理念,以《唐诗品汇》《唐诗选》的选诗理念为宗。谭元春受晚明文化思潮影响,提出“选书者非后人选古诗,而后人自著书之道”[23],因此在其与钟惺合作编订的唐诗选本《唐诗归》序中写道:“真诗者,精神所为也。察其幽情单绪,孤行静寄于喧杂之中;尔乃以其虚怀定力,独往冥游于寥廓之外。”[24]表明其以清虚幽静为审美取向的诗学理念,但谭元春最为推崇杜甫、李贺诗,而对温庭筠诗总体仍持排斥态度,仅录其4首“幽情微语”“幽澹动人”的五言律诗。不过,在心学和追求独抒性灵等文化思潮影响下,明后期的文人们意识到“诗必盛唐”的局限,开始追求“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并将目光投向中、晚唐诗,温诗接受至此稍得改观。陆时雍编订《唐诗镜》重“情”“趣”和“意象”,“其大旨以神韵为宗,情境为主”[25]1763,因此对温庭筠的七言律诗、五言排律及绝句颇为赞赏,多以“三四风味绝佳”“爽气清音,扫除沉闷”“庭筠数绝,悠裕不迫,意味尽佳”[25]14来评价温诗。曹学佺的《石仓历代诗选》评温诗为晚唐第四,录温诗数量也比之前选本都要多。《石仓历代诗选》和《唐诗镜》对温诗的进一步接受,缓和了明前、中期文人对温庭筠诗的疏略态度,温诗的价值也逐渐被挖掘和认可。
四、结语
考察明代具有广泛影响的唐诗选本选录温诗的情况,是温诗明代接受研究的一个新视角。查清华认为,梳理明代对唐诗的接受史能够“从一个侧面揭示明代社会心理和文化思想变迁的轨迹”[4]2。因此,考察温诗在明代的接受情况,也有助于当代的我们了解明代文人的精神面貌与文化认同。明前、中期“诗必盛唐”的诗学理念使此一时期温诗的接受度不高;明后期随着文人选家诗学理念的转变,晚唐诗不再被极端忽视,温诗的接受度也稍有提高,其艺术价值也得以逐渐被发掘。这一变化为清代学者如金圣叹、贺裳等人进一步认识温诗价值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