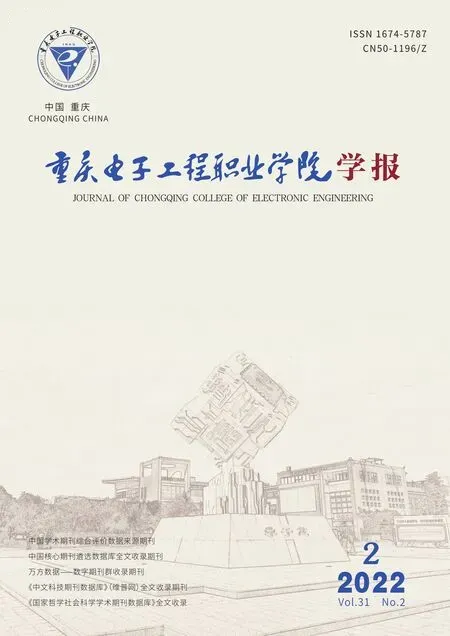从《荆潭唱和诗序》看韩愈的诗学主张
2022-03-18汪琴兰
汪琴兰
(贵州师范大学 文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新唐书·艺文志四》内记录有裴均《荆潭唱和集》一卷[1],该卷已佚,目前只存此集名。《文苑英华》内收录有韩愈的《荆潭裴均杨凭唱和诗序》,并附简短小序:“《唐艺文志》有裴均《荆潭唱和集》一卷,即此也。”[2]《全唐文》《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二十也收录了该诗序,《五百家注昌黎文集》也附小序曰:“均,字思齐,贞元十九年(803年)五月为荆南节度使,凭十八年九月为湖南观察使。荆,即荆南;潭,即湖南也。公以永贞元年佐均为江陵法曹。”[3]348故可知《荆潭裴均杨凭唱和诗序》是韩愈为裴均、杨凭等人诗集《荆潭唱和集》所作的序。德宗贞元十九年(803),韩愈被贬阳山(今广东阳山县),永贞元年(805)八月,宪宗即位,韩愈遇赦,移官江陵,为法曹参军。此时裴均正为荆南节度使,从“公以永贞元年佐均为江陵法曹”可知韩愈当时是在节度使裴均手下做事,此时裴均官居要职,当为韩愈上级。永贞元年韩愈来到江陵时,裴均与杨凭已分别在荆南和湖南任职两年有余,两人多有唱和往来,故有《荆潭唱和集》传于当时。
据该序内容可知,韩愈作此序并非刻意为之,当是裴均随从给他看了裴杨二人唱和集后所脱口而出的感慨,后抄录为该集子之序。该序文虽简短,然内容丰富,也基本涵盖了韩愈较为著名的几条诗学理论主张。兹录该序原文如下:
从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唱诗》者,愈既受以卒业。因仰而言曰:“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得志满,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今仆射裴公开镇蛮荆,统郡惟九;常侍杨公,领湖之南,壤地二千里。徳刑之政并勤,爵禄之报两崇。乃能存志乎《诗》《书》,寓辞乎咏歌,往复循环,有唱斯和。搜奇抉怪,雕镂文字,与韦布闾里憔悴专一之士,较其毫厘分寸。铿锵发金石,幽眇感鬼神,信所谓材全而能钜者也。两府之从事与部属之吏属而和之,苟在编者,咸可观也。宜乎施之乐章,纪诸册书。”从事曰:“子之言是也。”告于公,书以为《荆潭唱和诗》序。[3]348-349
该篇序文是韩愈诗歌理论主张的重要参考,具有很大的诗学参考价值。序文不仅对裴杨二人及其诗歌表示认可与赞同,且借此再次提出了个人的诗学观点与理论主张。序文内诸种观点与韩愈一贯主张的“不平则鸣”“气盛言宜”以及崇尚怪奇之美交互辉映又互为补充,并对后来欧阳修等人所提出的“穷而后工”有着很大的影响。
1 不平则鸣:愁思之声与穷苦之言
先秦两汉时,屈原、司马迁等人就以“发愤”一词诠释了如何在不幸的人生遭际中创作出不朽的作品。屈原悲痛自己因进谏而遇罚,于是在《惜诵》篇写下了“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4]180,在《悲回风》写道“介眇志之所惑兮,窃赋诗之所明”[4]348,诗人的耿介之志与奸佞小人的谄媚霸道发生强烈冲突,却仍能做到不与小人同流合污。在这样的不幸遭遇下,不得已将郁结胸中的绝望与悲苦惆怅用文字表达出来,化为诗篇,这便是屈原的“发愤抒情”。到了汉代,司马迁对屈原“发愤”精神表示肯定,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5]2482除了对屈原人格魅力的肯定,“李陵之祸”带来的肉体之痛与精神耻辱也是他对屈原推崇的主要原因。在《史记·太史公自序》的最后部分他提出:“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5]3300在该序里,司马迁认为古来卓有成就的大著作,都是古人不幸遭遇的精神产物。而司马迁本人著《史记》也再一次验证了人生之不幸是可以激发创造力、有所作为的。
时至唐代,韩愈在屈原、司马迁等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发愤”精神。《送孟东野序》曰:“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6]5612这是诗人送别命运多舛的好友孟郊远赴江南任职时所写,诗人认为文人为文之优秀者,当如同众多事物发声一般,定是在经历一些“不平”之后方能“善鸣”,即“蚌病成珠”,方能有所成就。《荆潭唱和诗序》中诗人也再次强调了这一观点,序文云:“和平之音淡薄”,“欢愉之辞难工”,在韩愈看来,描写太平盛世的语言过于浅薄而无深意,致力于欢快享乐的文辞更是难以有所成就。南朝“齐梁之风”盛行,以梁简文帝萧纲等统治者为中心的文人集团多吟咏性情,内容以风云月露、闺房情事为描写重点,形式上雕琢蔓藻、穷词极貌,内容空洞、缺乏真情实感,饱受诟病。初唐时期齐梁之风仍旧不衰,在初唐四杰、陈子昂、李杜等人的努力下此风气才逐渐消沉转变。但安史之乱后,该诗风又逐显影,大历十才子模仿宫体诗风进行创作,连白居易、元稹等人也都有不少艳情之作流传一时。针对这一不良现象,韩愈表示强烈反对。他认为齐梁宫体诗空洞无物,描写宫廷的“和平之音”与写闺情艳事的“欢愉之辞”浅薄难工,是很难有大作为、大成就的。故韩愈大力倡导诗文革新运动,反对浮靡文风,在当时乃至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序文又曰“愁思之声要妙”“穷苦之言易好”,“要妙”“易好”两个形容词表明了他对“愁思之声”与“穷苦之言”的认可与推崇。而“愁思”与“穷苦”属于“不平”之内容,“愁思之声”与“穷苦之言”则是“不平之音”的文字表达,只是在这里韩愈将不平的范围缩小,专指“愁思”与“穷苦”两种不平之音。“愁思之声”“穷苦之言”与“和平之音”“欢愉之辞”前后形成强烈对比,一抑一扬,可见韩愈态度与立场之坚定。接着“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羁旅草野”代指流落旅客与归隐之士,这些人多由于命途多舛、仕途坎坷而“沦落”于乡间草野。在韩愈看来,历来好的文学章著多出于这些人之手,正是因为他们异于常人的不幸遭遇,心中的郁结不平之气才被激发出来,使得所作文章之内容与情感更具深度,内容真实而情感真挚。这样的文章一反宫体诗风,更具社会价值与欣赏价值。而“至若王公贵人,气得志满,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则是对达官贵族之文的批判,韩愈认为他们一生畅达顺利,故其文很难“鸣”出深度,属无病呻吟之作,无法与“愁思之音”“穷苦之言”相媲美。韩愈通过一正一反、抑扬交错的两面对比,褒贬融合,直接表明自己对“愁思之苦”“穷苦之言”等不平之音的强烈推崇。这不仅是对裴杨二人诗歌的称赞,更是他一贯诗学主张的再次表露。
2 气盛言宜:人格修养与金石之音
“不平之音”是主体创作的外部环境,只有当外部环境所带来的磨难激发了创作主体的创造力与表现力时,主体内心的情感才能发而为声。这种声音的激发同时又离不开创作主体的主观认知与知识储备,也离不开文字的书面传达,故韩愈在序文中又进一步论述了文学创作之主体条件。
序文第二段韩愈先对裴杨两位上司虽官居要职仍有志于文学的态度表示称赞。“德刑之政并勤,爵禄之报两崇。乃能存志乎《诗》《书》,寓辞乎咏歌”,指出裴杨二人政治上推行德政、刑法,爵禄虽高却依然能够留心研究《诗》《书》等经典作品,并在往来中以诗歌唱和,进行文学创作。孟子《公孙丑上》篇云:“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持其志,无暴其气。”[7]孟子论述“志”与“气”,“无暴其气”表明了他注重主体道德意志的修养,又云:“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配义与道。”孟子所谓“浩然之气”是一种精神气质,是主体力量的爆发。这种“气”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靠后天“养”得的,是需要“配义与道”的,是后天通过道德修养而不断完善个人习得的。反映在文学创作中,孟子“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之“养气”重视的是创作主体后天通过学习、培养而得的道德品质、见识阅历与人格素养等。
韩愈继承孟子的这一观点并提出了“养气”说,他将作家主体的人格修养与文学作品有机结合,提出“气盛言宜”的理论主张。《答李翊书》有云:“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6]5587其中“气盛”是指作家进行文学创作之际当具有饱满旺盛的精神,这样才能成就好的文学作品,这是对孟子“浩然之气”的继承与延展。在韩愈看来,“不可以不养也,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气盛”应当以“浩然之气”重视道德修养为基础,强调作家要以仁义道德为根本,明道积义,同时又强调创作主体要多读书以培养技艺,注重知识的积累与艺术的提高。在韩愈看来,此时的裴杨二人已位居高官,衣食无忧,但依然能够致力于《诗》《书》研究,实属难得,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正是“养气”之行动表现。《诗》《书》作为五经之属与儒家经典,历来被视为教育典籍,是古人人格修养的重要参考之作。裴杨二人致力于儒家典籍的研究,便是他们注重自身人格修养与学识积累的表现,而“德刑之政并勤”便是这种精神与修养的外在行为表现。韩愈认为文章的好与坏和创作主体的人格修养、情感态度、精神气势直接挂钩,只有充分具备这些气质才能更好地驾驭语言与文字,从而创作出更好的文章著作。序文中他对裴杨二人施行德刑之政和致力于《诗》《书》研究的肯定,也就是对二人高尚的人格魅力与为文之“气盛”精神的赞扬。
具备人格修养与学识积累的创作主体在进行文学创作时还应该重视下笔时语言与声律的运用。“铿锵发金石,幽眇感鬼神,信所谓材全而能钜者也”,韩愈更是直接给予二人“材全而能钜者”的高度评价。此时韩愈为裴杨二人部下,于政治角度不免有夸大之音与奉承之意,但于文学创作而言,“铿锵发金石,幽眇感鬼神”更是他对二人诗歌语言与声韵的高度认同与赞扬,这也是韩愈“气盛言宜”文学主张的具体体现。除了重视创作主体精神气质与人格修养外,“气盛言宜”也是一种艺术上的审美表现,在文学作品中则表现为重视语言与声律如金石般铿锵有力,能感鬼神、泣天地,给人以感官与情感上的强烈冲击。作为中唐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人物,韩愈反对骈文只重形式不重语言的现状,故“气盛言宜”说要求为文应从作家的道德与人格修养出发,继而注重文章铿锵有力的语言与声律的养成。这一文学理论主张具有很大的现实功用目的,既推动了创作主体人格修养的形成,揭示了文学创作的规律,同时又对诗文革新、改变文学不良风气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3 崇奇尚怪:搜奇抉怪与雕镂文字
除“不平则鸣”“气盛言宜”等主张外,韩愈在文学创作中也表现出对雄奇怪异之美的强烈推崇。在《调张籍》一诗中他表达了自己对李杜的推崇与高度赞扬,“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徒观斧凿痕,不瞩治水航。想当施手时,巨刃磨天扬。垠崖划崩豁,乾坤摆雷硠”;“刺手拔鲸牙,举瓢酌天浆”。与“不平则鸣”重视文章内容与情感以及“气盛言宜”重视创作主体人格修养与为文气质不同,韩愈在这里推崇的是李杜诗歌的艺术手法与奇阔艺术。诗中之巨刃磨天、划崩豁、摆雷硠、拔鲸牙、酌天浆等都是天马行空、超越现实的奇特想象,韩愈将自我思想和境界提升到险怪、奇谲的至高地步。《醉赠张秘书》一诗评价孟郊、张籍的诗:“险语破鬼胆,高词媲皇坟。”从这两处来看,韩愈以力量之雄大、造境之奇特以及语言之险怪为出发点,对前人及朋友为文艺术之高超表示肯定与赞同,而这种艺术又特指造语之奇崛怪异、意境之诡谲奇特。
韩愈不仅理论上推崇这种奇崛怪异之美,他自己也是这一理论的实践者与行动者,其诸多诗歌作品都显示出他对诡谲文字的运用和对怪奇诗境的构建。如《感春四首》:“长网横江遮紫鳞”,“独宿荒陂射凫雁”,“数杯浇肠虽暂醉,皎皎万虑醒还新”。韩愈一生仕途坎坷,几度被贬,并且被贬之地环境也十分险恶,如《永贞行》:“湖波连天日相腾,蛮俗生梗瘴疠烝。江氛岭祲昏若凝,一蛇两头见未曾。怪鸟鸣唤令人憎,蛊虫群飞夜扑灯。雄虺毒螫堕股肱,食中置药肝心崩”。艰难的环境与处境惊起诗人的惶恐,忧愁百生,于是在这种苦闷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思维趋势,即对险怪意象的描绘与刻画,进一步形成了对奇崛文字的挖掘和对怪奇意境的营造。除此之外,在很多诗歌中韩愈也表现出对极丑、极恶的关注,如“昼蝇食案繁,宵蚋肌血渥”;“裂脑擒摚掁,猛毙牛马乐”等,读起来令人发指。类似造句在其诗歌作品内有很多,使其诗歌形成了以丑为美的审美追求与审美态势。韩愈的这一审美倾向也深刻影响着韩孟诗派以及稍后的诗人及其诗歌创作,比如孟郊、李贺等都表现出对奇崛怪诞语句和意境的追求。对这些怪奇之物超乎常情的描绘也成为韩愈在诗歌艺术上的主要追求之一。
《荆潭唱和诗序》“搜奇抉怪,雕镂文字”之语即是从语言角度对裴杨二人诗歌的评价,《荆潭唱和集》虽已佚,我们已无法看到裴杨诗之真面目,但能得到崇尚怪异之美的韩愈的这般评价,可见二人作诗也必定注重雕镂文字,搜罗万象。但从“搜奇抉怪”一“搜”一“抉”两个行为动词亦可见裴杨二人作诗时刻意搜奇求怪的举止,因此可推知二人诗难免流于蹇涩偏僻、怪奇有余而韵味不足的地步。韩愈在序文内又紧接着说“与韦布闾里憔悴专一之士较其毫厘分寸”,“韦布闾里憔悴专一之士”指的是那些生活在街尾里巷、生活困苦而专心进行诗文创作的文人,这就又将“搜奇抉怪,雕刻文字”的为文方式与“不平”之困苦坎坷结合起来。韩愈将裴杨“搜奇抉怪”之文与不平之士之文联系起来,从二人身居要职来看这并不是指裴杨二人之文亦是“不平”之文,而应看到在韩愈心里“搜奇抉怪”之文与“不平则鸣”之文具有同等的重要性,都是关于文学创作的具体表现。“不平则鸣”更多是从内容与情感层面对诗歌创作提出的要求,而“搜奇抉怪”则是对诗歌语言、意象、意境营构的主张,两者相互支撑,共同作用。
4 结语
作为诗文革新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与领袖者,韩愈在诗文理论方面提出了许多具有极大影响的观点主张。《荆潭唱和诗序》作为韩愈诗学理论主张表现的一篇诗序,具有极大的诗学价值,诗中所谓“愁苦之声”“穷苦之言”既是其“不平则鸣”诗学观的佐证与辅助材料,两者又相互照应;序文中对裴杨二人人格修养与诗歌语言声韵的肯定又与其“气盛言宜”的诗学观相印证;而二人“搜奇抉怪,雕镂文字”的创作态度又与韩愈对极丑、怪奇之物的推崇相照应,这也成为韩愈对二人该诗集有如此好评的原因。《荆潭唱和集》虽已佚,已无法从其诗歌内容、情感表达、艺术追求等方面分析二人诗歌对韩愈文学理论的具体体现与文字表现,但序文中韩愈在肯定裴杨二人诗集的同时又将个人文学理论主张蕴含其中,使其诗学观更加辨证通达。虽韩愈之诗学观在其个人其他文学作品中多有体现,但《荆潭唱和诗序》所体现出来的诗学理论与其一贯所主张的诗学观相得益彰,也具有重大的诗学价值与理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