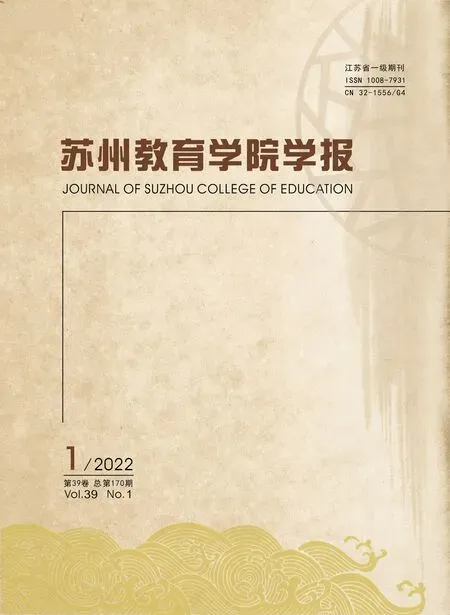上海沦陷区的新诗理论探索
——以路易士、应寸照、史美钧为个案
2022-03-18吴昊
吴 昊
(廊坊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北 廊坊 065000)
1941 年12 月珍珠港事变后,上海结束了四年的“孤岛”时期。上海全面沦陷期间的诗歌界,虽然繁盛程度不如战前,但仍有一批诗人坚守“诗领土”,在新诗创作方面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这部分诗人中较有影响力的有路易士、俞亢咏、应寸照等,他们的作品不仅出现在路易士自办的期刊《诗领土》上,还散见于《文友》《人间》《风雨谈》《光化》《新东方杂志》等上海沦陷区的杂志中。值得注意的是,在上海沦陷期间,华北沦陷区的一些诗人在上海的刊物上发表过许多作品,如沈宝基、南星、穆穆等,他们甚至是“诗领土”社的同人。可见,沦陷区的诗坛并不是一片“荒漠”。在艰难的创作环境中,南北沦陷区的诗人仍然利用有限的条件进行诗歌创作与诗学交流。
上海沦陷区的新诗理论方面也有着一定的探索。其中,有代表性的理论研究者是路易士、应寸照和史美钧等人。路易士诗论最基本的观点是“格律反对自由诗拥护”[1]。与路易士相似,应寸照的诗论也强调诗歌的纯粹性,但不否认诗歌为社会、为人生的效用。史美钧的一系列“诗人论”非常有特点,能够从思想、形式、节奏等方面对诗人作出独到的评论。路易士、应寸照和史美钧这三者的诗歌理论差异明显,但内在关联又很紧密。
一、路易士:“纯诗”追求的偏颇与悖论
上海沦陷之前,路易士的诗歌创作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他与戴望舒一起被视为“现代派”诗人的代表。他自编过《火山》、《菜花》(从第二期起改名为《诗志》)两种诗歌刊物,还在《现代》《红豆》《小雅》《新诗》等杂志上发表过大量诗作。路易士对“纯粹诗歌艺术”的追求,在这一时期的诗论中也初步显现出来。他认为,“动人的诗篇是真挚的感情和丰富的想像交织的网”,只偏于“感情”或“想像”,都会破坏诗歌的美感。路易士还认为诗歌可以使用“俗语”与“陈旧的字词”,只要“用的手段不陈旧”,也会使诗歌增添新意。[2]至于诗歌的“明朗”与“朦胧”,路易士也主张两者的适度:“意识地把属于明朗的意境来朦胧化了,那是在做谜语,而不是做诗。”[3]从这些言论可见,路易士似乎是持一种调和、辩证的诗学观,但他对诗歌格律的态度,又显得较为激进,他反对过于直白与显露的“胡适之体”,认为诗歌不是“大白话”;但他又认为诗歌不应该讲究形式,诗与散文的区别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内容。[4]“诗行”“诗节”“韵脚”等形式的特质并不足以使“诗之为诗”。[4]可以说,路易士的观点是20 世纪30 年代中后期诗歌界关于诗歌形式讨论的一部分,当时,林庚、朱光潜、罗念生、叶公超等人皆认为诗歌应该讲究格律,而路易士的观点无疑是站在了林庚等人的反面。与路易士观点相似的还有戴望舒、朱英诞。其中,朱英诞在《谈韵律诗》一文中认为“自由诗也有用韵的,则似完全失败了”[5],似乎韵律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自由诗”发展的绊脚石。
1941 年3 月,臧云远在《大公报·重庆》“战线”副刊发表了《诗的音韵美》,文中肯定了韵律与节奏在诗歌中的作用。[6]而在沦陷区,诗人对诗歌形式的探索也在继续。废名于华北沦陷区《文学集刊》杂志发表的《新诗应该是自由诗》一文可视为“自由诗”诗歌理论的突出代表。废名认为:“如果要做新诗,一定要这个诗是诗的内容,而写这个诗的文字要用散文的文字。”[7]这种见解与路易士关于诗歌形式的观点不谋而合。路易士十分推崇废名的诗歌,并认为废名的《街头》是“中国新诗自五四以来最珍贵的收获”[8]。他在推崇废名的同时,否定了以徐志摩、朱湘为代表的“新月派”,他称“新月派”把“西洋的旧诗”(商籁体)[9]带到了中国,所写的诗歌都是“豆腐干”体,没有什么“新”的地方。在“诗领土”社同人信条中,路易士以其旗帜鲜明的态度反对格律:“在格律反对自由诗拥护的大前提之下之各异的个性尊重风格尊重全新的旋律与节奏之不断追求不断创造。”[1]这里就出现了矛盾:既然有“格律反对”的大前提,那么“各异的个性尊重风格”就有很大局限。并且,路易士声称要不断追求不断创造全新的旋律与节奏,在某种程度上仍然逃避不了“格律”的影响。因此,路易士对“格律”的态度可以说是偏颇的。
在推崇“自由诗”、反对格律的前提下,路易士还持有一种“艺术本位”观,他认为诗歌应该保持自身的纯粹性,诗人不应该媚俗,不应该制造一些迎合大众口味的作品。[10]所以他对鸳鸯蝴蝶派的通俗小说不屑一顾,也反对“诗歌大众化”。另外,路易士还认为诗歌只是为了自身而存在,不应依傍于任何的政治意识形态:“一首诗的好坏,不能取决于其‘政治意识’之有无。同时,也不能因了一首诗的缺少‘政治意识’,便胡乱地斥之为‘空洞的’,或是‘无内容的’。”[3]他认为,政治与艺术是两种相对独立的意识形态,它们有各自的评判标准和规则,所以他强烈反对诗歌的政治宣传功用,称那些“为了替某种政治主张作宣传”而写诗的人是“艺术的罪人”[2]。路易士为了显示自身“诗歌艺术与政治无关”[2]的立场,对日本诗人池田克己的诗集《中华民国居留》大加赞赏,认为这本诗集所收入的作品“几乎是每一首都充满了一种战时下的国民的义务感,一种强烈的爱国心”,甚至称“我友池田克己所引吭高歌了的乃是战争,乃是胜利,乃是祖国,正如所有真正的爱国诗人一样,他歌唱得非常之热烈,非常之激昂慷慨”[11]。从这些溢美之词来看,路易士全然无视当时日军对中国领土的侵略,反而歌颂日本诗人“战时的爱国心”“对战争的‘高歌’”,这显然有悖于民族感情。虽然路易士声称对池田克己诗歌的赞赏是从艺术角度出发,无关“意识”的,但结合其现实行为来看,他已经越出了自己所宣称的“诗歌与政治无关论”的主张。1942 年至1944 年,路易士一方面在汪伪政府的《中华日报》副刊上发表大量作品,试图借此展现个人才能,也为其日后创办的“诗领土”社打下了基础;另一方面,路易士还作为“中国的代表”去南京参加了由日本军部主办的“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这些行为都与路易士本人所宣称的“纯粹诗歌艺术”观念相悖,更与戴望舒等“现代派”同人投身抗日事业的人生价值取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二、应寸照:诗歌理论的“辩证”与其局限
目前,有关应寸照的资料不多。战时,他虽然居住在上海,但他似乎并非上海本地人。有论者称应寸照“在上海的一个工厂里做会计”①参见:《应寸照和路易士》,http://blog.sina.com.cn/s/blog_5e8246090100cbin.html。,但与他同为“诗领土”社的洪山道却称应寸照是“一个商人”[12]。从沦陷区报纸的零星报道中得知,他曾在上海威海卫路开办过茶座,兼售油画、盆景[13];他在上海有一新一旧两套房子,并将旧房子作为招待外地朋友的“招贤馆”[14]。还有记者报道,应寸照发明了一种价廉物美的“拖粪机”,为弄堂里的百姓争相抢购。[15]由此可见,应寸照的生活应该较为富裕,并且有一颗热情待人之心。他文学造诣很高,还有一定的商学与工学才能。从已发现的作品来看,应寸照的创作主要集中于上海沦陷时期,抗战结束之后他的作品逐渐减少,在1949 年之后销声匿迹。有论者称其“后半生命运多厄,远戍边陲,终郁郁而亡”[16],这种不幸或许与他在沦陷区的生活经历有关。
应寸照的作品多发表于《人间》《文友》《光化》《风雨谈》等刊物上,其中诗歌理论文章的比重要大于诗歌创作。其诗论的显著特点是以概念辨析为主,概念一般是以两个一对的方式出现,有的概念之间存在相似的关系,如《含蓄与晦涩》《怪诞的措辞与警句》《生涩与新颖》;有的概念之间则存在互斥的关系,如《世故的见地与天真》《高旷的意境与贵人气息》《奔腾的才思与坐逼》《明晰与朦胧》等。他的诗论就是处理这些诗歌概念之间的辩证关系。在《含蓄与晦涩》中,应寸照认为“含蓄”是“新娘身上的轻纱”,而“晦涩”是“瞳神表面的障翳”。诗歌创作要注意避免“晦涩”,不要用生硬、怪僻的字句;而“含蓄”也要有限度,因为“含蓄得太厉害”,便又成了“晦涩”。[17]实际上,应寸照的诗论总是在强调一个“度”的问题,除了“含蓄”与“晦涩”这一对概念外,他还辨别了“缥缈”与“落实”[18]、“怪诞的措辞”与“警句”[19]等有相互联系的概念界限,认为写作要有“度”,否则过犹不及。但这并不表明应寸照总是站在中庸的立场,在区分另外一些概念时,他有时也表现出鲜明的态度。在《高旷的意境与贵人气息》中,他认为,为了营造诗歌中“高旷的意境”,诗人需要严正的态度与艰苦的工作,而不是把自己当作“贵人”,用“呵斥”的口吻来写诗。[20]此外,应寸照赞同诗人在作品中作“心曲的体认”,认为这是“追求真切”,而反对“任侠”的“仗义执言”。在他看来,“仗义执言”属于社会法则的范畴,与诗歌艺术无关。[21]应寸照反对的是仅仅站在“第三者”的立场、没有真切经验、“不过受怜悯的驱使而作的一种任侠的行为”[21],而不是对诗歌的社会功效的全盘否定。
应寸照虽然属于“诗领土”社同人,但其许多观念与路易士存在较大距离。正如上文所说,应寸照认为诗人要考虑到诗歌的社会功能,在《心曲的体认与仗义执言》中,他以穆木天《乞丐之歌》为例说明诗歌要反映民生疾苦。[21]在《诗人是孤独的吗?》中,他甚至提出了“社会底诗人”概念:“社会底诗人,他固是人们的生命之代言者,即在这些上面不作什么积极主张的罢,他也会给予一般的生命以高级的贡献。诗人是始终为人群探索人生的,为人类报告安危或虚实的,自然底‘间谍’啊!”[22]正因为诗人是“为人群”“为人生”的,所以即便“身处荒僻”,也并不孤独。应寸照与路易士的观念不同还体现在诗歌节奏方面。路易士提倡“自由诗”,对格律的态度较为极端;应寸照则重视诗歌节奏的作用,他认为“机械的音节处理”固然不可取,但诗歌是“诗”与“歌”的合体,声韵、节奏对诗歌的重要性仍然不容忽视。所谓“诗的节奏”是“声韵与意韵结合而起的”[23]。这种观念类似于郭沫若所提出的“内在律”与“外在律”的结合[24],应寸照在《诗与节奏》中确实也提到了郭沫若的《论节奏》。此外,戴望舒、朱光潜有关诗歌声韵、节奏的观点也对其观念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应寸照的诗歌节奏观念不执迷于“诗”本身,也不偏颇于“歌”,可以说是一种辩证的观念。
虽然“辩证”是应寸照诗歌理论的思维方式,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诗歌理论体系是严密的。从他发表于沦陷区报刊的一系列名为“诗论百题”的文章来看,他似乎想建立一个完整的诗歌理论体系,但这些文章间的关系是松散的,还没有形成严密的学理系统。洪山道甚至批评应寸照的诗歌理论文章是在“偶然的状态下”完成的,没有经过认真的推敲与打磨,存在“生硬与晦涩”的毛病,即便试图使用“譬喻”,也没有把握好分寸,使读者对其诗论印象模糊。[12]洪山道所言极是,应寸照虽以辩证的思维分析诗歌中的一些概念,但忽略了将具体作品分析与理论阐释相结合。从他的几十篇诗歌理论文章来看,其所举的诗歌例证屈指可数,这就使其理论文章大多成为概念的阐释,而没有严谨的学理与丰富的实践作为支撑点。
三、史美钧的“诗人论”与诗歌格律观
与应寸照相似,史美钧的生平资料也不多。陈学勇在《太太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上海女作家》的序言中认为史美钧是上海女作家,其代表作有《晦涩集》《鱼跃集》《错采集》《衍华集》等。[25]实际上,史美钧是男性,陈学勇误以为女,恐怕是其名字偏女性化之故。此外,史美钧虽然在北京沦陷区的刊物《中国文艺》上发表过一些诗人论,但综合其作品发表与出版情况来看,他主要的文学活动地点还是在上海。杨郁《胡山源生平及创作年表》中提到史美钧曾在上海集英中小学教过课[26],陈玉堂编著的《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续编)》中认为史美钧为浙江人[27],从原始期刊、报纸和名人日记来看,这两种说法更接近史美钧的生平事实。据1928 年8 月31 日《申报》广告《持志大学暨附属中学录取新生案》载,史美钧为持志大学国学系试读生;[28]张元济于1933 年8 月3 日致吴其昌的一封信中写道:“……承介绍之史美钧君,已转致馆中主者。据称编译部份职员已无空额,一时又无增揽人才之机会,属为婉达歉意。”[29]张元济与吴其昌同为浙江人,吴其昌向张元济推荐史美钧,估计是因同乡之谊。虽然史美钧没有顺利进入商务印书馆,但他却在上海的新中国出版社找到了一份工作。据1935 年12 月的《中华职业学校职业市市刊》报道,此时的史美钧已成为“新中国出版社”的总编辑,其“著作甚富,有诗集,晦涩集等,最近在编常识文库,本月间有著作在商务出版”。[30]短短几年史美钧便取得这样的成绩,一方面他的确有创作天赋,另一方面,恐怕与吴其昌的推荐、张元济的支持不无关系。但史美钧没有一直在编辑这个行业工作下去,从其抗战爆发后的作品来看,史美钧似乎回到了浙江老家从事教育工作,并在《浙江教育》杂志上发表了多篇教育类文章。
史美钧并没有在上海沦陷区工作与生活,但他在上海沦陷区的《小说月报》(顾冷观主编)、《文友》、《现代周报》等刊物上以“高穆”“叶谟”“戈予”等笔名发表了大量诗歌、散文、小说和评论。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其诗人论,如《徐志摩论》《王独清论》《戴望舒论》《于赓虞论》《冯乃超论》《路易士的诗歌》《卞之琳论》等。在上海沦陷前,史美钧还在北京沦陷区的刊物《中国文艺》发表过《朱湘论》《诗人梦家论》《卞之琳论》《王独清论》等文章。其中,《朱湘论》早在1936 年就在《青年界》上发表过,可见他对“新月派”诗人的关注。1948 年,史美钧出版了《衍华集》一书,书中收录的除上文所提到的几篇评论外,还增加了一篇《记臧克家》的评论。潘颂德在《中国现代新诗理论批评史》中对史美钧的诗人论给予了肯定,认为其“继承了茅盾三十年代开创的诗人论批评方法,采用政治学、社会学与美学相结合的批评视角,对所论及的诗人作出了比较客观、全面的分析与评论”[31]。茅盾也写过《徐志摩论》,因此他对史美钧的《徐志摩论》给予了一定关注,并在致徐志摩重庆的信中谈及此事。[32]但史美钧的《徐志摩论》的知名度显然不如茅盾,或许这是史美钧本人声名不彰之故。
茅盾的《徐志摩论》显然不是中国新诗史上第一篇诗人论。早在20 世纪20 年代就出现了大量谈论诗人及其作品的文章,比如,闻一多的《〈女神〉之时代精神》《〈女神〉之地方色彩》,朱湘的《评徐君志摩的诗》《评郭君沫若的诗》《评闻君一多的诗》,朱自清的《白采的诗》等。茅盾《徐志摩论》的突出意义在于他将传统的“知人论世”方法,自己的政治立场和对作品的细读相结合,从历时的角度解读徐志摩思想的转变,以及思想转变带来的作品的变化。但茅盾毕竟是持“左翼”政治立场的作家,所以他得出的结论是徐志摩的“生活”所产生的“思想意识”(“阶级背景”)使其感到“沉闷”,并且“不能抵抗”“再没有力量”,他未能“看见那沉闷已破了一角,已经耀出万丈的光芒”。[33]史美钧虽然也使用了“知人论世”的方法,但其政治立场并没有茅盾那样鲜明,因此他在谈到徐志摩在社会层面“非是进步的尖锋”的同时,主张不要对其“要求苛刻”,因为徐志摩“内心已经过长期交战,充分使用了勇气”,“我们不必从成功外再求全盘的成功”。史美钧的《徐志摩论》在指出徐志摩“思想之杂,产生杂的作品”的同时,还肯定了他对“节奏的创制”。[34]可见史美钧对徐志摩的论述还是较为全面的。
如前文所述,史美钧似乎对“新月派”的诗人情有独钟,除《徐志摩论》外,还有《朱湘论》《诗人梦家论》《于赓虞论》《卞之琳论》等。他称陈梦家的诗“承袭了志摩的形式,而他却是以另一种思维,表现自己到级完整的境界”[35],论述了宗教信仰对陈梦家创作的影响,并肯定了陈梦家在诗歌形式方面的创造。史美钧评论卞之琳“不肯把握时代意识”,“仅为字的排列上的成功”和“生活安逸中片断闲情或空虚的静中悲感之描写”[36],因此希望其拓展创作题材。史美钧看到了卞之琳题材的平凡一面,但没有对其哲理的另一面作进一步的探究,因此只把卞之琳的诗歌当作单纯的“咏物诗”,体现其一定的局限性。不过史美钧在论及于赓虞时,则相对准确一些:“于氏似为中国唯一恶魔派诗人”,“他主张与其丑恶的生,毋宁美丽的死,获取永恒的静息”[37]。史美钧对“新月派”诗人如此之看重,乃至于与“新月派”有微妙关系的臧克家,也在史美钧的评论范围之内。史美钧赞扬了臧克家诗歌“划破现实黑暗面,深入人心,接近泥土”的特质,认为他有“雄健的生命,但亦须求外形的匀称与节奏优美,再求深造,必更有客观”[38]。
史美钧之所以看重“新月派”诗人,与其诗歌格律观念密不可分。他十分重视诗歌格律,他在论述“新月派”诗人时无一例外地都提到了他们在格律方面的探索与不足,而在论及“新月派”之外的诗人时,他也注意分析他们作品的形式问题。在《路易士的诗歌》一文中,他指出路易士社会观念的淡薄(“路易士的思想,根本与社会无关,连社会生活与他之间也有着严密的隔阂”),还指出路易士“内容重于形式,未遑塑型”的问题。[39]如前文所述,路易士的诗歌观念是“格律反对自由诗拥护”,因此他对诗歌形式的塑造有所忽略;而史美钧批评路易士则是从支持其诗歌格律的立场出发,在一篇未收录至《衍华集》的名为《近二十年中国新诗概观》的文章中,史美钧专门从“思想”“形态”“节奏”等方面概述了近二十年来的中国新诗,并认为三者密不可分,共同构成了诗的要素。[40]较之路易士、应寸照,史美钧的这种综合性的诗学观念可谓是一大进步,这也是除诗人论之外,他在诗歌理论方面的又一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