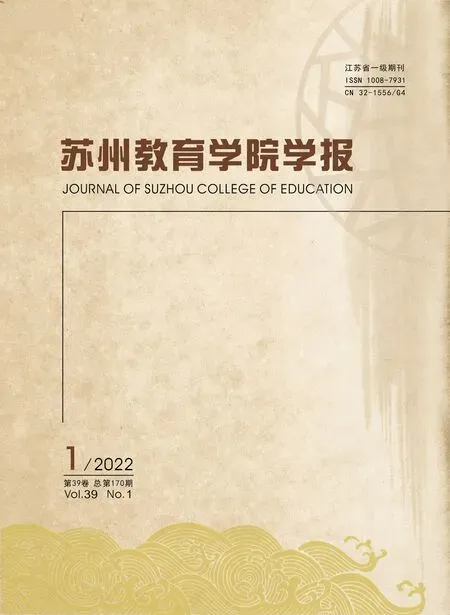中国现代散文的大众文化性探究
2022-03-18冯鸽
冯 鸽
(西北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9)
中国现代①本文所用的“现代”概念指称通常所使用的“现当代文学”中的意义,包括当代文学。散文话语建构的复杂,使我们难以清晰勾勒出其“概念地图”,言说艰难。确实,现代“散文”实际上是被当作归整遗散在小说、诗歌、戏剧之外所有文学作品的一种“杂”文学体裁,体现的是西方近代文学的分类观念,即使在传统文学概念中,“散文”也是与“韵文”相对应的一种文体概念,并非是纯文学意义上的散文概念。现代散文遍布于各类媒体中,成为现代人的主要言说话语方式,具有表达的无限可能性。面对这种无限性,在研究中,我们总是纠结于“纯文学”的“散文”的抽象性文学特质内核,尴尬于“大文学”的“散文”范畴的无边无际。因此,试图为其寻找概括性的理论范畴,建构一种纯散文文类的自洽理论体系,显然是十分困难的。
然而,现代散文文本几乎充斥于所有的文学与非文学的表达空间,伴随着中国都市大众文化的发展而成为一种私人经验的表达方式,构建了一种现代散文文化。如果我们将“散文”作为历时的文化现象来考察,以其在中国社会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学整体格局内的实际作用来探讨其文类的价值,也许能够从另一个角度解读其现代性获得的意义,从而对当下的散文创作现象进行更为清晰透彻的剖析,给予更切中肯綮的指导。在此,我们不得不再次强调,只有突破20 世纪以来形成的文学批评话语,正视中国现代散文日常文学表达和叙事习规中的非虚构性、实用性等丰富驳杂的美学特征,才能将长久以来被遮蔽和被忽略的散文表达纳入研究视野。
一
当我们使用“现代散文”这个概念的时候,往往有意无意地与“古代散文”进行着对比。在对比语境中,中国现代散文获得了一系列现代特征,从而产生了现代性的文本意义和价值,那么,其现代性的本质内涵何在?
中国古代散文具有鲜明的主流话语和精英文化表达的中心文类地位。传统文学历来以诗文为正宗,散文的地位要远高于小说、戏曲。①大致说来,中国从汉代到明代,对文体和文类的划分是逐渐展开、趋于细致的。四分法(诗歌、小说、散文、戏剧)出现于“五四”时期,是在西方三分法(叙事类、抒情类、戏剧类)的基础上,结合本民族文学的历史与现状而形成的。即使到了现代,以小说创作为职业的现代通俗小说创作群体,如鸳鸯蝴蝶派的作家也依然留存着鄙视小说的旧文人观念,而把散文看得更为正式,常常对散文有着诚惶诚恐的创作态度。从先秦至晚清,说理、教化、史传、论辩、抒情、言志、谏疏、信札、赞颂、讨檄等均为散文的纵横之域,其主流文类地位显而易见,固若金汤。
古代散文本就是在教育被垄断的社会中主流精英阶层的一种言说方式,其言说目的在于成教化、助人伦、颂功绩、诉理想、抒情感、表心迹、辩明理等,属于一种士大夫之间的交流和娱乐。因此,古代散文在传统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旨在教化民众、歌颂统治阶级和展示自我才能及理想情感,不会过多考虑读者的因素。从先秦诸子的政论文和叙事文到唐宋八大家的经典文章,无不充满了强烈的诗学气质和文以载道的人文精神,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和美学特征,形成了一种源远流长的纯粹的精英散文文化传统,可见,古代散文是一种主流文化和士大夫精英文化建构的表达。
20 世纪,现代散文在中国的发生、发展则深植于都市工业文明的语境中,拘囿并服务于现代传媒平台及其传播方式,不再是一种纯粹的文学审美理想的表达和建构,即使是表达个人的理想情感,更多的也是个性化的私人情趣,而非仅仅围绕精英性的宏大时代主题。纵观中国现代散文的发展轨迹,体现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流文化、体现百姓文化追求的大众文化和知识分子所提倡的具有批判意识的精英文化共存的局面,使中国现代散文在不同时期呈现出多种时代话语建构,如1950 年代的“杨朔模式”大抒情散文、1990 年代兴盛的学者文化散文、当代流行的“鸡汤散文”等都是极具时代特征的散文建构,也引发了多重的社会效应和评价议论。但是,在这三种文化形态相互对话、交流、融合、冲突与碰撞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比较开放的文化态势。主流政治文化为适应市场经济,对其他文化形态日渐宽容,其绝对强势的姿态逐渐减弱;精英文化陷入了失语的尴尬境地,退守边缘;大众文化则迅速崛起,泛滥蔓延,疾步登上主流文化的舞台,成为当今中国文化格局中极具市场号召力的一种精神话语建构,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传统散文的话语方式。
“现代散文成熟的基本标志应当是自身文化层面上的特性的确立,它是衡量和区别新旧散文不同价值取向的一个标尺。”[1]现代散文自身的文化特性就是从抒情言志、文以载道的宏大思考和严肃高雅的精英话语表达走向了更为广阔的话语资源,既有对时代主潮的追随,也有游离于主流话语之外的个性化的私人经验表达;既有反抗,也有顺应,逐渐构建出多元化的大众话语,获得了一种大众文化品质。也就是说,中国现代散文的现代性不仅体现于发现“人”的话语内容的现代思想观念,也体现于现代大众文化语境中散文话语的文体建构。
古代散文在文化建构中主要关注统治阶级、主流社会的伦理道德建构与个体的自我精神建构,而随着传媒业的发展、稿酬制度的完善、作家的职业化和创作的市场化,现代散文则着力于读者和作者的互动性关系的建构。由此,休闲娱乐、信息传播等功能性需求就逐渐突出。现代散文就是在这些实际功能需求中逐渐建构出来的大众文化话语,也只有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才能出现这样的现代性文学表达。[2]因此,现代散文的大众文化②这里所说的“大众文化”有一个特定范畴,主要是指兴起于现代都市,与大工业密切相关,处于消费时代或准消费时代,以现代传媒为中介,按照市场规律大批量生产的满足人们的感性娱乐需求的现代文化形态。特征是其最具现代性的标志。
中国现代散文的发生、发展是在都市中伴随着商业媒体的发展而兴盛起来的,因此,它和现代报刊传媒的关系密不可分,其大众文化特征最为直接的表现就在于——现代传媒为散文思潮、流派、社团的形成与发展,为散文作家的生存方式、文体选择、话语方式等,提供了必需的外在物质载体和文化语境,深入参与了对散文的文体形式、审美趣味的建构,体现了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和话语建构方面的现代性特征。[3]譬如当下的新媒体散文,以大量人工“塑料花”似的生活碎片全方位地刺激读者的消费欲望,职业性地用鸡汤文字伪造生活细节,直截了当地走向生产消费市场,这迥异于古代散文的审美抒情特征。虽然现代散文不断地进行一种自我化、抒情化、高雅化、情趣化的外在修饰,力图展示其艺术魅力,但是散文的纯文学性和艺术价值却日渐模糊,鲜明的商品性、通俗性、流行性、娱乐性、媒体依赖性、日常性、类型性等大众文化特征却日益鲜明。
那么,现代散文大众文化性建构是蜜糖还是毒药?这种建构给散文带来了什么?其建构话语资源来自哪里?又将如何发展?这是我们当下必须面对的问题。
二
现代散文的大众文化特征来自这一文类自身的日常实用性和鲜明的功利性,这也赋予了现代散文在大众生活中的消费价值。这种消费价值促使现代散文在现代社会形成了多种文体形式并走向繁盛,同时形成了市民话语表达的公共文化空间,成为大众话语的主要表达方式。
散文本就是一种应用文类。从古至今,优秀的散文作品多出自史论、经书、政论、序跋、祭文、碑文、表状、策问、书信、日记、书札、论文、传记、博客文章、微信公众号推文等各种实用文体,散文的文学性就存在于其中。王佐良先生就明确指出:“散文首先是实用的,能够在社会和个人生活中办各种实事:报告一个消息,谈一个问题,出张公告,写个便条,写信,写日记,进行政治辩论或学术讨论,写各种各样的书,等等。当然,它还可以在文艺创作的广大园地上尽情驰骋。要紧的,我以为是两者之间要通气,要互相增益,要将办事的实际本领同想象力的探索结合起来。”[4]在实用文体中渗透富有情调的文学内涵,正是古今散文的传统。现代散文不仅承袭了这一文类原有的各种应用功能,还适应了现代社会信息传播、舆论表达、娱乐休闲、思想交流等多种现实需求,产生了诸如新媒体散文这类极富消费性的精美文字,在微信、微博等媒体上传播、泛滥。
在现代散文发生的初期,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和都市商业的发展,现代市民阶层崛起,生活节奏加快,现代人已经不能适应传统农业社会慢节奏的田园生活,很难拥有大段的消遣时间去阅读欣赏长篇的大部头作品,传统的香艳诗词和言情故事也无法满足市民阶层对于社会发展的关注需求,短小新鲜的小品散文就成为非常合适的阅读文类。从清末到现代,战乱频繁,社会动荡,作家们的生活极不安定,难以拥有一张安静的书桌,安心撰写著作,所以多用简短的文字来表达自己对社会人生的认知和感悟。在这种情形下,作家和读者同时把目光投向了散文,现代散文成为了现代人最为方便的言说方式。
在现代报刊传媒的发展需求下,这种言说方式形成了现代散文的多种文体。初期,晚清的文界革命需要宣传各种学说政论以启蒙民众,报刊杂志作为当时最有力的宣传阵地,逐渐形成了一个公共舆论空间,文章体式也就要适应报刊杂志的刊登形式。启蒙者关注的并不单纯是文学艺术问题,而是文章如何适用于文化教育的普及和思想的传播。基于此,启蒙者才会选择小说作为启蒙利器,选择散文在各类杂志报纸上补白,使散文频繁出现于各种专栏,为小说作注解,为时代作注脚。散文才逐渐形成了各种趣味个性和文体样式,有了繁盛的局面。当下,人们的生活越加浮躁紧张,文字的言说和阅读不断简化,越加直接,高科技媒体的迅速和便捷更是推动了多种碎片化信息、情感、思考的传播,多种散文文字随意蔓延开来,渗透到各类文体中。可见,散文的实用性催生了多种现代文体的形成,丰富了文类表达方式。
杂文文体的形成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由于近代都市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起初报刊上刊登的王韬、郑观应、梁启超等人的长篇论说文章[5],逐渐变成了短论,后来干脆成了附在新闻后面的短评,犀利有趣的评论逐渐发展为时评和闲评,到鲁迅手中逐渐成熟为“杂文”。学者钱理群等就直接指出,“作为一种报刊文体,杂文与现代传播有着血肉般的联系;人们说起杂文,特别是鲁迅的杂文,总是要联想到‘五四’时期的《新青年》、《语丝》、《莽原》、《京报副刊》、《晨报副刊》,30 年代的《萌芽》、《太白》、《文学》,《申报·自由谈》等等,这大概不是偶然的……杂文是富于现代性的文体……随着现代传播对人的现代生活的日益深刻的影响,杂文(包括鲁迅的杂文)也就真正深入到现代生活中,并成为其中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样的作用与价值是其他非报刊文体所不可能具有的”[6]。那么,鲁迅的杂文从何而来?鲁迅曾写道:“我知道中国的这几年的杂文作者,他的作文,却没有一个想到‘文学概论’的规定,或者希图文学史上的位置的,他以为非这样写不可,他就这样写。”[7]可见,鲁迅杂文的出现,一方面是出于作家表达自我内心的创作欲望,从而寻找到的一种言说文体;另一方面是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中,在报刊的版面要求、读者趣味、传媒商业性等因素作用下形成的。李欧梵就此论述道,鲁迅的杂文文体是在当时伪自由的语境中,“他才能发挥‘弯曲’的、‘吞吞吐吐’的才华,才能写出像《伪自由书》这类没有自由的作品,然而又在作品中——特别是杂体混声、兼叙带评、剪贴拼凑式的形式和语言运用技巧上——为自己开创一点自由的空间”[8]。可见,现代杂文正是在独特的政治语境中,在现代报刊取悦读者、迎合市场的商业性中,吸纳多种创作方法和技巧并兼顾读者趣味后,逐渐形成的重视信息传播、时事评论、趣味引领等现代性功能的实用性文体。
学者陈平原在论述《新青年》的“通信”体时也指出:“从文体学的角度考察《新青年》的‘通信’,很容易想当然地上溯古已有之的书札。这种溯源不能说没有道理,‘通信’所虚拟的私人性及对话状态,以及若干书札惯用的套语,再在提醒这一点。但这种‘拟书札’的姿态,除了拉近与读者的距离,更多的是为了获得独立思考以及自由表达的权力。……除此之外,‘通信’还具有穿针引线的作用,将不同栏目、不同文体、不同话题纠合在一起,很好地组织或调配。……‘随感录’的横空出世,不仅仅为作家赢得了一个自由挥洒的专栏/文体,更凸显了五四新文化人的一贯追求——政治表述的文学化。”[9]这里指出了现代散文的文体选择源自于表达的需求,而非刻意的文学探索。作者对于自我文化角色的重新定位促使散文走向读者,走出孤芳自赏的状态。也就是说,现代散文将文体功能的重要性置于形式表现之上,而不像古代散文那样将纯粹的美学要求置于读者的需求之上,由“高雅”的纯粹美学走向了应用型的“大众”美学。
确实,报刊杂志的传播普及化、现代新闻的时效性以及商业化消费生产模式催生并促进了现代散文的创作。“随感录”散文与《新青年》,“语丝文体”与《语丝》,“现代评论派”的时评与《现代评论》,鲁迅的杂文与《申报·自由谈》,林语堂的小品文与《人间世》《论语》,“鲁迅风”与《萌芽月刊》,京派散文与《大公报》,1930 年代的报告文学和游记与《光明》《中流》《文学界》,1940 年代的“野草”杂文与《野草》,等等,正是现代散文与现代传媒密切关联的体现。如果论及通俗文学作家的散文创作,更是如此。他们大多都是报人,如王钝根、陈蝶仙、陈景寒、周瘦鹃等是《申报·自由谈》的主编;张丹斧主编了《新闻报》的副刊《庄谐录》,《庄谐录》后改名为《快活林》,1932 年后《快活林》又改名为《新园林》,这时的主编是严独鹤;《小时报》主编是包天笑、李涵秋、毕倚红;其他通俗文学作家如叶小凤、何海鸣、姚鸳雏、张恨水、贡少芹等都做过报人。这种报刊工作者的身份无疑使他们更懂得市民审美需求,更擅长运用散文笔法来描述都市风景、谈天说地,引领大众的舆论导向和审美趣味。他们编报时几乎每日都有散文作品发表,如严独鹤一生留下了近万篇言论性文章,他在主编《新闻报》副刊期间,基本上每天发表一篇叫作“谈话”的文章;[10]张恨水也写有数以千计的篇章,20年间平均每日写500 字的散文,积累下来数量可观。这些散文内容包罗万象,从市井闲言到国家大事,从日常生活到野史轶事,无一不可入文,无一不可议论。
在现代报刊形成的公共空间和时代语境中,散文作家不断调整着话语方式,建构了自我的散文话语和文体,为现代散文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话语资源、艺术技巧、美学趣味,形成了开放多元的现代散文格局,多种散文文体也逐渐形成,如新闻体、杂感体、随笔体、絮语体、科学小品、读后感、日记体等,将大众的趣味和作者的思想表达、艺术探索相结合,形成了个性与多元、模式化与自由化并存的现代大众日常私人经验的文化场域表达空间。
可以说,现代散文的实用性文类价值在于促成了现代市民群体性政治公共领域的形成,并且逐渐挤压了传统的精英代表型公共空间,也就是说,大众通俗性的市民话语空间不断扩大,文学的语言修辞功能被实用性所碾压、取代,现代散文就是在这一过程中被建构出新的文学话语,是由传统垄断性精英文学走向通俗开放的大众社会文学的具体表现。
三
现代散文的实用性不仅催生了多种文体的出现,还表现为具有鲜明的大众娱乐性。散文的灵动精巧既可以抚慰人们的心灵,也可以宣泄压抑的情绪,还可以博人一笑,带给人们精神上的洗涤,直接而迅速,其美感和趣味都是其他文类无法相比的。
现代报刊逼迫着散文作家开始关注读者需求、市场需求,将职业化稿酬意识带入创作,将散文创作从古典的个人精神建构文本逐渐变成大众文化文本,在文体选择、语言表达、情感趣味、思想价值等各方面进行调整,重新确立文化角色,接近甚至满足读者的需求,从社会精英阶层的教化姿态转向服务市民大众的娱乐消遣姿态,散文的新闻性、纪实性、游戏性、趣味性得以强化,从而逐渐由古代散文的严肃教化、载道慎言、讲究章法转变为现代散文的通俗、轻松、消闲、自由,呈现出尊重个性生命的现代文化意识和大众市民文化趣味。
20 世纪30 年代,小品文创作高潮与林语堂等人创办的《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散文刊物密不可分。林语堂打着中间旗号办刊,提倡“幽默”,几经摸索,成功实现了作家和读者的接轨互动,艺术成败得失暂且不论,但刊物的畅销趋势却不可忽视[11]141,这主要得益于其契合了大众读者的趣味。如老舍的《祭子路岳母文》插科打诨,引人捧腹,还有大量的新旧笑话也是极有趣味的。那时的撰稿人有鲁迅、周作人、郁达夫、老舍、俞平伯、丰子恺、简又文、姚颖等众多新文学作家,他们的作品虽不一定是风趣幽默的风格,但是实践证明这种办刊宗旨富有特色,有幽默,有思想,有情趣,有讽刺批评,当然也就受到了读者青睐和市场认可。
通俗文学作家的散文创作较之新文学作家的散文创作更能体现出这种大众文化的特性。相较于新文学作家,通俗文学作家的生活背景更复杂多元,他们很多是职业作家,不受时代主潮的禁锢、限制,也没有受到特定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只接受文学市场的调节,因而创作心态很从容,可以自觉书写各类时尚、掌故、民情、自我体验等,他们将一些新文学作家不关注的边角料题材如赌场、花会选美、健康卫生、社会趣闻等进行记录,对都市生活进行有趣细致的临摹,生动记录了城市的时代氛围。他们的文字所涉及的社会领域更是广阔多样,具有服务市民大众的文学意识,注重文学的娱乐性和商业性,而不仅仅是传统的“文以载道”儒家思想的表达,他们多以平等的创作视角和心态以及浅显风趣的语言来展示普通人的生活,表达丰富的生活情趣,吃喝拉撒无所谓高雅低俗,皆可入文,这是一种“平视”的写作姿态,与市民生活“不隔”,融为一体,具有市民文化特征。
畅销报刊的文学追求和艺术审美都与市场商业有关,有着鲜明的通俗娱乐性,譬如散文的游戏性。这些游戏文字、插科打诨是一种消遣趣味的表达,也是一种通俗的审美情趣的表现。仅从报刊名就可见一斑,《游戏报》《滑稽文》《滑稽魂》《游戏文章》《笑笑》《消闲报》《娱闲》《通俗》《笑报》《趣海》《杂咀》《庄谐录》《谐著》《戏言》《趣海》等不一而足,《游戏杂志》《消闲月刊》《游戏世界》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游戏世界》在版权页上标注的作者包括了天台山农、王钝根、贡少芹、徐卓呆、程瞻庐、李涵秋、包天笑、郑逸梅等52 人,几乎囊括了当时所有的通俗文学作家。这份杂志由周瘦鹃、赵苕狂主编,1921 年夏创刊,1923 年夏停刊,出了24 期,栏目有说苑、谈荟、歌场、趣海、谐林、艺府、余兴、杂咀等,五花八门,无所不包,吸引了大量市民读者。
但是,娱乐性不代表脱离现实。虽然在这样的创作理念指导下,通俗文学作家自然少不了创作一些轻松欢乐的讽刺文章,但是他们原创的各类笑话、滑稽诗文等不无针砭时弊之作,如程瞻庐的《蟹与军阀十二似》①程瞻庐:《蟹与军阀十二似》,《红杂志》1922 年第20 期,第62——66 页。把军阀拟为螃蟹,进行对比,极尽讽刺之能事。那些具有文学性的正经文章,也是妙趣横生,如虚汝的《鸦片烟赋》就是一篇很生动的讽刺小品文,文章细说了鸦片的来历、制作过程,吸食之状态“调崖蜜之丝丝,帘风扇碧;滴花酥之点点,炉火飞红。于是倚鸳被兮轻挑,躺象床兮不倦”,最后“神不疲而自倦,泪交流而何哀……必至灭种乃已。哀哉”[12],寥寥数笔,形神兼备地写出了鸦片烟的种种危害,其痛心之情甚切。面对社会百态,作家的笔犀利无比,如“某旦角是靠着他脸子卖钱的。他面孔的妍媸,是影响戏馆的营业和自己的包银。某文豪的笔尖,是靠着评剧和捧角出名的”[13],一针见血地揭示出二者的联系,讽刺这种利益关系无视真正的艺术。迂堂的《享乐篇》②迂堂:《享乐篇》,《黑皮书》1939 年第15 期,第24——25 页。更是讽刺,通过叙述一天的享乐经历讲述在国家危难、民不聊生的国难时期,孤岛上人们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这些文章的游戏性使其在时政讽喻之外披上了一层保护色,戏谑地表达了对社会黑暗现实的抨击。这说明通俗文学作家并不是脱离现实的白日梦写手,反而是极其关注社会人生百态的。
其实,中国自古就有借调笑喻世、劝世、讽世的滑稽文学传统。晚清小报中虽有一些无意义的噱头笑料、油腔滑调的小品文字,但更多的是那些具有讽喻意义的文章。这些小报不仅将游戏文章当作批评时政的方式,而且认为这类文章可以启聪、开智、长知识。③参见:《释〈消闲报〉命名之义》,《消闲报》1897 年第2 号。滑稽的游戏文章既可以击中讽刺对象的要害,又使讽刺对象哭笑不得,读者却能痛快地大笑起来。自然,这类文章受到作者和读者的欢迎。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名人趣事,如张恨水就写过一篇《鲁迅之单人舞》,记录鲁迅在校庆会后被逼表演节目,“先生固不善任何游艺苦辞不获,乃宣言作单人舞。郎当登台,手抱其一腿而跃,音乐不张,漫无节奏,全场为之笑不可仰。先生于笑声中兴骤豪,跃益猛,笑声历半小时不绝。此为当年与会学生所言,殆为先生仅有一次之狂欢,不可不记”[14],这种记录颇有史料价值,反映了鲁迅的性格不为人所知的一面。
作家追求文字的趣味性,固然是一种市场需求,然而这背后所蕴含的是作者与读者的避世心态。李伯元在《论〈游戏报〉之本意》中就直接说明:“《游戏报》之命名仿自泰西,岂真好为游戏哉?盖有不得已之深意存焉者也。”[15]“游戏”的深意是一介书生面对黑暗现实的无奈之举。1922 年,在李涵秋主编的《快活》杂志创刊号上,周瘦鹃发表了一篇《〈快活〉祝词》,其中言道:“现在的世界,不快活极了。上天下地,充满着不快活的空气,简直没有一个快活的人……在这百不快活之中,我们就得感谢快活的主人,做出一本快活杂志来,给大家快活快活,忘却那许多不快活的事。”[16]这都透露出游戏趣味文章不仅是为读者提供消闲娱乐,更是一种苦闷的变相发泄。这种避世心态是通俗文学作家的普遍心态,也是当时社会民众的无奈心态,在混乱黑暗的现实中,他们没有勇气和力量来改变现状,只好在游戏消遣中把家事国事都付之一笑,这也是当时这种文章大量出现的原因。
四
大众文化氛围中,现代散文建构出了一种作者与读者之间具有现代性的平等对话关系,形成了散文艺术审美的日常化。由于报刊对消费群体的关注度极高,散文作者与读者的互动性关系导致现代散文的“平等姿态”,甚至“低身段”,一改传统散文高高在上的说教腔①总体而言,古代散文的主流是实用、载道、为圣人立言,绝不是抒发个人情志的文字;而那些序跋随笔、性灵小品之类的是消闲小道的非主流,是不登高雅正殿的。,形成了“谈话风”。这种谈话风格虽然文体上受英美随笔和中国古代小品文的影响,但其实质在于作家具有的现代精神——对人的尊重和关注。“‘谈话风’的出现,不仅影响到散文,也同样影响到小说创作,影响到学术批评,影响到中国文学的各个方面,甚至可以说,这正是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标志之一呢。”[11]8-9“谈话风”在这里不仅指文风,更是指一种平等、自由、个性的现代文化精神和言说方式。
作者与读者之间的生产与消费的关系必然有互动性,形成了一种现代社会的人际交流方式,这对于构建社会族群、共同文化场域都有重要作用。在那个充满变化的自由开放的转型时代,文人们对于人生与社会有着充沛的情感和满腹的感受,他们需要自由表达这些情感与感受,散文这种信手拈来、任意而谈的言说方式自然就随处可见,散文的发达也就势不可挡,“小品散文,于是乎极一时以盛。……这三四年的发展,确是绚烂极了:有种种的样式,种种的流派,表现着,批评着,解释着人生的各面,迁流曼衍,日新月异:有中国名士风,有外国绅士风,有隐士,有叛徒,在思想上是如此。或描写,或讽刺,或委曲,或缜密,或劲健,或绮丽,或洗炼,或流动,或含蓄,在表现上是如此”[17]。
在高涨的表达欲望的驱动下,现代散文成功地将口语和白话文引入文学创作,胡适等人的浅白议论文仿佛是给学生上课的论述,周作人等人的趣味美文仿佛是和朋友聊天,鲁迅等人的杂文则是在和敌人论理,周瘦鹃等人的文章是在和同道中人分享养花养草的乐趣,他们都是在用自己得心应手的表达方式和读者“说话”,没有刻意地经营文体,自然而然地就形成了谈话风。实际上,对散文文本的消费过程,就是读者与作者互动的过程。读者阅读一个文本的过程就是一个创造过程,“是人,将鲜活的身份带入商业与文化商品的消费过程中;是人,带来了与商业遭遇的经验、感觉、社会地位与社会归属。因此,人带来了创造性的象征快感,不仅让文化商品自身产生了意义,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文化商品使自己……产生了意义”①转引自约翰·斯道雷著、常江译:《文化理论与大众文化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年出版,第291 页。。在这个消费过程中,散文审美的日常化具有了大众文化属性。
日常消费性带来的重商主义必然导致金钱资本对文学生长空间的挤压,腐蚀了文学的精神表达欲望和原创激情。作家与现实沟通的能力日益退化,逐渐失去了社会担当,沉沦于市场,自我麻醉,对现实失语,沦为市场工具,其创作也成为一种抹平了精神深度的物质文化。这种消极影响在当下创作中日益鲜明,对此,我们需要保持警惕。
五
其实,在这种功利实用的创作思想指导下的文章早已溢出文学范畴,现代散文的文类概念如何关注散文的文学艺术性?文学毕竟是为了创造审美和批评社会的艺术,而不是为了消费而生产的工业化、批量化的复制品。
“五四”时期,诗歌忙着表现文学革命具有破坏力的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小说则沉浸在以自由婚恋为标志的追求个性解放的感伤痛苦中,文本的内容如此沉重和拥塞,使文学家们无暇过多关注文体的形式。只有散文,在一开始的理论探讨中研究者就注意到了文本自身的审美艺术性。早在1917 年,刘复就在《我之文学改良观》中提出了“文学散文”的概念,并与非文学文字加以区别。[18]1921 年,周作人发表的《美文》就非常具体地指出:“外国文学里有一种所谓论文,其中大约可以分作两类。一批评的,是学术性的。二记叙的,是艺术性的,又称作美文,这里边又可以分出叙事与抒情,但也很多二者夹杂的。”[19]29他非常鲜明地表达出对散文文体审美特性的确定。之后,关于散文的理论探讨日渐丰富,从散文的概念、源流、流派到美质、形式、笔调、语言等均有论及,到1930 年代中期形成了一个创作和理论研究的高峰。为何如此?就是因为现代散文的发轫之初泛滥于各类报刊杂志,具有大众文化属性,与新文学作家的启蒙意识、审美趣味、文学理念等发生冲突,从而引发了特别关注。
早在现代散文发生初期,启蒙者就意识到古典高雅的文字不适合急剧变化的时代社会,提出“文字偏于美术,其害甚大……欲文化之普及,必自分应用之文字与美术之文字始”[20],他们认为文章的艺术性并不重要,“今日之计,学术为急”,“外此则词章文艺,非学者所必务”。[21]所论是比较偏激的,对传统文章进行了重新认知和定位。对于反对传统古文的新文化学者来说,为了大力提倡白话文,也就连带着否定了古文的形式美感,对“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的美学特征——“藻饰依地”“铺张堆砌”——深恶痛绝,“譬如古铜铸的钟鼎,现在久已不适实用……不是我们所要求的人生的艺术品”[22]。然而,这种极端的宣传本就是文学革命中矫枉过正的一种言论,具体到创作中是无法回避文学艺术性的问题的。在注重文学表达的内容思想的同时,白话文表现出的局限性亦是他们无法忽视的,一方面,他们反复强调“现在作白话文的作不出好文字,只能归罪于白话文学家的手段太低,却不能归罪于白话文的文体”[23],捍卫着白话文的地位;另一方面,他们努力地寻找扩展白话文表现力和美感的途径,譬如傅斯年就发现“白话散文的(Essay)体裁极多,很难靠他长进我们各类的白话散文”[24],所以他主张通过欧化让白话文更加精密严谨。周作人则关注到传统文言文资源,指出“中国古文里的序,记与说等,也可以说是美文的一类”[19]29,白话文写作可以“就古文学里去查考前人的经验,在创作的体裁上可以得到不少的帮助”[25]。他自己更是在创作和理论研究方面对晚明小品、六朝文章、清儒笔记等传统资源进行吸纳,经营现代散文。①参见陈平原:《现代中国的“魏晋风度”与“六朝散文”》(《中国文化》1997 年第Z1 期,第278——310 页);葛飞:《周作人与清儒笔记》(夏晓红,王风:《文学语言与文章体式——从晚清到“五四”》,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年出版,第266——303 页);季剑青:《近代散文对“美文”的想象》(夏晓红,王风:《文学语言与文章体式——从晚清到“五四”》,第92——115 页)。现代散文作家也多是得益于古文功底,才以其创作实绩完胜了古文,得以确立白话散文的统治地位。在1926 年,朱光潜就看到“想做好白话文,读若干上品的文言文或且十分必要。现在白话文的作者当推胡适之、吴稚晖、周作人、鲁迅诸先生,而这几位先生的白话文都有得力于古文的处所(他们自己也许不承认)”[26],这是试图建构现代散文、美文的一种探讨,力图在散文的大众消费性中保存旧文学传统和审美趣味。
长期以来,在建构散文理论时受西方现代文学观念中知识体制结构的影响,人们普遍认为现代散文应该是诗歌、小说、戏剧之外的一种纯文学概念,因而不断地强调散文的自我性、抒情性、想象性、审美性等,然而散文的日常实用性和个性化表达导致散文的品质难以“提纯”,使得散文的纯文学性和艺术价值显得面目模糊。新文学作家们在散文创作中不断探讨美文、杂文、小品文、絮语散文等各种理论,致力打通西方的“Familiar Essay”(小品文,随笔)和中国古代小品文之间的联系,确立中国现代“散文”文体。这种情形体现出他们对现代散文文类的理想构建,其中周氏兄弟的论述——周作人发表的《美文》和鲁迅翻译出版的《出了象牙之塔》——最具代表性,对散文构建最为有力。[27]他们的白话散文创作,无论是周作人的美文,还是林语堂的性灵小品,或是鲁迅的杂文、朱自清的抒情写景散文等,都致力于这种现代“散文”文体的确立。正是这种纯文学散文观念的制度感束缚了散文文体,弱化了散文中的学术性、随意性、思想性等,忽视了散文作为“文类之母”所具有的跨文体的文化本体性,使现代散文研究和创作都束手束脚,越来越狭隘,很容易形成模式化。比如杨朔的借景抒情散文、余秋雨的文化大散文等,除了文化统一性的影响外,也是由于对纯散文的追求而形成的。
究其本质,散文本就是个性化文体,大可因缘作文,发挥所长。学者可铺陈知识,幽默者可尽情表达幽默,抒情者可连绵咏叹,实在没有必要确立文体的“核心”性质。如通俗文学作家的散文创作,问世早于新文学,作家没有受到太多的英美散文和西方理论的影响,直接承袭的是中国古典文化,虽然他们也接触了现代散文的理念,但是他们具有深厚的古典文学素养,加之本身没有强烈的反叛传统的意识,更多地沿袭了古代散文传统。他们的创作有时评、札记、随笔、野史掌故、抒情小品等多种形式,显示出一种从容气度和古雅风趣,颇为耐读。毕竟,现代散文是一种个人经验的公众化表达。
需要说明的是,通俗文学作家和新文学作家的散文创作并未出现小说创作中那种非常鲜明的雅俗界限。新文学作家如茅盾、郑振铎等对鸳鸯蝴蝶派的通俗作家作品的批判,主要针对的是传统文学的旧文化气息和商业性表现,是在西方启蒙立场上对中国传统文学和文化的批判和排斥,也是对都市文化和市民阶层的蔑视鄙夷,其实质不外乎为传统士大夫阶层试图在现代社会建立一种精英知识文化的话语霸权。虽然这种追求体现了新文学作家对传统的逆反和遮蔽姿态,但是主要体现在小说创作中。而在散文创作中,他们的谈话风、抒情风等散文表达和通俗文学作家的散文一样,都是个性化的“人”的表现,都是通过大众媒体进行阅读生产和消费,遵循着基本的商业市场规律,共同打造了那个时代的私人经验表达的公共空间。通过比较通俗文学作家和新文学作家的办刊情况可以发现,他们都是注重市场的高明编辑。只是通俗文学作家的文化保守主义立场使其在创作中对传统文学的继承更为坦荡顺畅,媒体人的身份也使其更为鲜明地体现出大众文化的特征。
当我们认识到现代散文的大众文化属性后,就知道它必然带有消费特征。研究者的弱势在于缺乏市场经验而难以洞察其文类的功用秘密,难以及时修正它的偏差。因此,我们在面对这种创作乱象时显得力不从心。究其实质,中国现代散文理论建构的艰难正是大众文化商业性与文学艺术性的内在矛盾所导致的。
大众文化的日常化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导致了文学艺术以及整个文化领域的生产、传播、消费方式发生了变化,由此满足了人们审美与日常生活的需要。大众文化在市场消费中很容易丧失艺术创造性,呈现出商品化的趋势,变得平面化、单调化、平庸化,消解了文化个性和创造性,但是艺术的文化追求解决的是人类生存的高级需求,即精神提升和美的建构,亦即人类如何实现自身价值、发掘自身潜力、实现对人性的终极关怀。就文化审美而言,大众文化突破了艺术与非艺术、审美活动与日常生活的界限,所以在试图建构纯粹散文艺术话语的努力中,散文的日常化消解了审美的经典性。从这个意义而言,中国现代散文是借助于大众媒体普及文学艺术、使审美的经典性与日常性从针锋相对走向和谐统一的经典案例,这个论题就留待以后进行探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