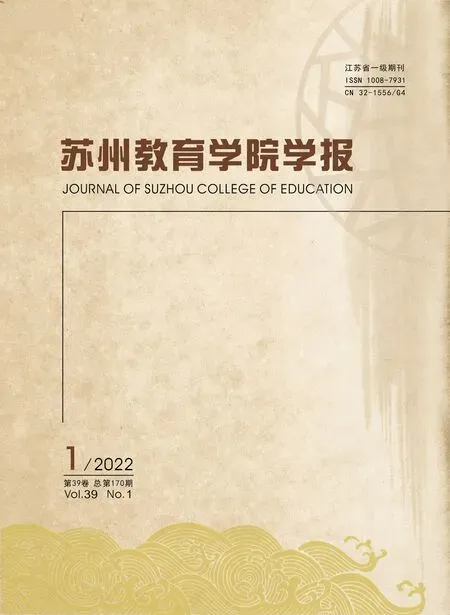因时而变的侦探小说
——一个俄国探案故事的漂流
2022-03-18左玉玮
左玉玮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素质教育中心,河南 郑州 450046)
晚清时期,随着小说地位的提升以及域外文学对知识分子的吸引,翻译小说大量出现,中国的小说类型日渐丰富。作为舶来品的侦探小说,就是在这一时期被引入国内的,并很快成为最受时人青睐的小说类型,无论是文艺期刊,还是各类报纸,几乎没有不刊登侦探小说的。据当时小说林社负责人徐念慈调查统计,小说销售市场中,以“‘小说林’之书计之,记侦探者最佳,约十之七八”[1]。鉴于侦探小说的受欢迎程度,当时很多文人都投身于侦探小说的翻译、创作,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称:“当时译家,与侦探小说不发生关系的,到后来简直可以说是没有。如果说当时翻译小说有千种,翻译侦探要占五百部上。”[2]
大量侦探小说的涌现,导致文本质量良莠不齐、一本多译的现象屡见不鲜,当时最受欢迎的福尔摩斯探案系列自不必说,一些不甚出名的探案小说也常出现这种情况。有些译者在翻译时常常不写出译本来源,甚至不标明译著名称,这给后来的译本研究造成了一定的障碍。针对同一故事出现多个翻译版本的现象,本文将以一个俄国侦探案为例,通过对比各讲述者侧重点不同的细节渲染,展现不同译创者在十余年间对这个侦探故事的演绎,呈现出社会环境变动、刊物宗旨不同对小说译创的影响,并探究文本面貌多样化的缘由,由此一窥近代侦探小说的流变。
一、凸显传奇性的侦探故事
1903 年4 月《浙江潮》第3 期刊载了一篇名为《摄魂花》[3]的小说,作者署名喋血生。故事讲述大佐、大尉叔侄二人在两三年间相继暴毙,时人皆以为是食物中毒,后医科大学学生提出质疑,经化学家化验,发现二人皆是被人毒害,老侦探假扮伯爵,找到凶手,揭开迷局。该文本语言精练,文白夹杂,开门见山,以说书人口吻直接进入案件讲述,吸引读者:“前年俄国新闻社喧传陆军将校叔侄二人两阅寒暑同病毙命,不料乃误于一剪摄魂花耳,诸君请者,且住为佳,听我演来得少佳趣。”[3]
从文本内容来看,讲述者以全知者视角向读者讲述了一桩域外奇案如何案发、如何案破,丝丝入扣,但并未用过多笔墨书写侦探的探案过程,也未过分渲染侦探的机智神勇,而是采用情节翻转的方式,在结尾处揭示了米加野侦探乔装卧底、擒拿罪犯。讲述者类似于传统传奇故事中的叙述人,当讲述到案件侦查发现蛛丝马迹时,就摆出吊读者胃口的姿态:“不料大侦探一番平淡无奇之问答,忽搜出石破天惊之怪事,述及片时,我恰倦了,且腹中辘辘作声,诸君稍待,我略休息再登坛与诸君述其机关。”[3]故事由此一分为二,随后讲述波兰伯爵在舞会上醉酒后留宿裘丽雅家中,并沉迷于其美貌,乐不思蜀。当情节发展到伯爵夜闯裘丽雅卧室意欲轻薄之际,笔锋突然一转,伯爵撕去假面,怒视惺惺作态的裘丽雅,指出她以“海娄濮儿”毒害大佐、大尉叔侄,就在这时,警察内外夹击,抓获作案团伙。这一反转令人称奇,就在读者惊叹之际,小说中作案者的认罪剖白将故事的传奇性推向高潮:“妾以大佐大尉伯叔事而将逸矣,卒败于阁下手,虽然吾罪巨矣,旅圣彼得堡毒人,若阁下果毙于妾手,正百数矣,亚历山德分予之造孽钱几盈五十万,虽然妾终非佛兰西人,妾终与君同‘画皮’手段者也。言毕剥去伪面,噫,一俄罗斯奇丑妇人耳。”[3]众人争相追逐、为之丧命的法兰西孀妇原来是一个俄罗斯妇人。除却人物身份、名字和案件发生地点有明确的域外色彩,故事情节及叙述方式与传统的话本小说无异。与这篇小说同期刊发的还有一篇名为《专制虎》的侦探小说,侦探亦为米加野,依据小说内容和侦探人物可推测,两篇小说应属同一个侦探系列。从这两篇小说的情节讲述可见,吸引刊载者选择这个探案故事的缘由应该是因其“结构离奇”[4]。
《浙江潮》是由中国留日学生浙江同乡会创办的刊物,1903 年2 月在东京创刊,孙翼中、蒋百里、王嘉祎等相继担任主编。刊物设有社说、论说、学说、大势、记事、杂录、小说、文苑、谈丛、时评、专件、调查会稿、浙江文献录、图画等栏目。刊物持论激烈,批判改良保皇,赞扬暴力革命和排满,在当时影响颇大,每期印5000 册,其中有几期多次加印,鲁迅留日期间也曾在该刊物上发文,但清政府明令禁止该刊在国内传播。《浙江潮发刊词》中陈述了刊物对栏目的定位,并详细列出每一个栏目的选文标准,其中“小说者,国民之影而亦其母也,务取其有关系者,或译或著,其类凡三:(甲)章回体;(乙)传奇体;(丙)杂记体”[5]。由小说体裁进行分类,可见当时尚未脱离传统小说的窠臼,从《摄魂花》的文体及内容看,编者应该将其归类为传奇体。此时,小说反映社会面貌、教化民众等功用虽已引起知识分子的注意,但译创者在陈述故事情节时并没有放大文本的域外文明细节,其侧重点更偏向于呈现案件的曲折离奇,凸显故事的传奇性,以此来吸引更多的读者阅读刊物,进而接受刊物中的思想。如何通过小说启智,还得从《新小说》谈起。
二、宣扬新知的“新小说”
侦探小说能够在阅读市场中大量涌现,离不开小说地位提升这一契机,更离不开宣扬小说教化功能的“小说界革命”。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小说被认为是诲淫诲盗的末流,受到文人的鄙弃,而在晚清这一特殊时期,梁启超倡导的小说界革命,一度将小说提至文学之最上乘,赋予其开启民智的功能。1902 年,梁启超在横滨创办《新小说》,以此作为小说界革命的阵地。在《新小说》创刊宣言中,他指出,“小说之道感人深矣。泰西论文学者必以小说首屈一指,岂不以此种文体曲折透达,淋漓尽致,描人群之情状,批天地之窾奥,有非寻常文家所能及者耶!……夫人之好读小说,过于他书,性使然矣”,因而可以“借小说家言,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励其爱国精神”。[6]该刊物将侦探小说作为新小说的一个类型,设置专栏,积极译创。
无歆羡斋主译述的侦探小说《毒药案》[7]刊载于《新小说》1903 年7 月的第5 期,未标明原作者。其故事内核与《摄魂花》完全一致,但讲述人及叙述模式发生了变化,在探案细节方面有了更详尽的书写,并在故事讲述中夹杂了更多译述者的点评。
《毒药案》以友人萧君讲述西洋侦探案展开,两三年前,炮台大佐伊格拿辅暴毙,医生诊断其为吃了腐坏的食物,时隔不久,大佐的侄子巴拉奴辅大尉也以同样的形态暴毙,医生给出了同样的定论。一名医学院学生认为这叔侄俩是被毒害的,写信给《嘉直新闻报》,迫于舆论压力,政府遂请一位化学家分析死者胃中残渣,发现死者确实是中了一种名为“耶列波尔”的毒药。后经俄罗斯最出名的侦探美卡威探寻案件中的蛛丝马迹,最终揭露亚历山大与焦利亚狼狈为奸、谋害有财产男子的真相。案件由萧君与“我”闲谈时讲述,模式与当时风靡的福尔摩斯探案系列的结构非常相似,在案件未破之前设置悬念,直到侦探乔装的伯爵揭穿凶手的阴谋后,听众才恍然大悟。小说开头先以两人的对话夸赞西洋侦探:“余老友萧君那一晚到我家里闲谈,谈起西洋的侦探来,实在神出鬼没,变幻机警,令人毛骨悚然。原来外国的侦探,能通几国的语言,精通人情世故,练成一种锐利的见识,加以通晓各种技艺,连容貌服饰,学那一种人,就像那一种人的。”[7]在小说界革命发起后,这种论调在很多侦探小说的译文弁言或是序跋中都能见到,西洋侦探的机智神勇似乎成了当时翻译的侦探小说中颇为精彩的着色点。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侦探的英雄形象在中国读者心中逐渐建构起来,并成为与包公比肩的睿智正义的代名词①《老残游记》第十八回“白太守谈笑释奇冤 铁先生风霜访大案”,在一件冤案的侦查审理中,白太守称老残为福尔摩斯,这是传统公案情节和西方侦探人物在小说文本中的一次有意味的结合。在传统公案小说中包公是明察秋毫、为民洗冤的清官代表,公案小说中最常见的即是蒙冤者大呼:“青天大老爷,您可要为小民做主啊!”或者称赞某一断案如神的官员为“包公转世”,而小说中作为官员的白太守却使用了西方经典侦探人物代表福尔摩斯来夸赞老残,这既是西学东渐过程中西方文化对中国浸染的表现,也可见当时侦探小说在中国的影响。。
侦探探案中对科学知识的运用、呈现出的民主意识等细节都被译者着重译述,并穿插点评。比如,大佐、大尉之死原本只被断定为食物中毒,但由于医学生的怀疑,并通过舆论推动才被立案侦查:“大尉葬后约一礼拜,莫斯科医科大学有一个学生,寄一封信去莫斯科‘嘉直’新闻,力言巴拉奴辅大尉与他叔父大佐两个,一定是被人毒杀的。且论大尉胃中的食物,分析得不大清楚,那处可疑,那处疏忽,各医生不免潦草塞责。初时人人都笑他狂谬,后详细观他的议论,很有道理,赞成这医学生的议论的,日多一日,各新闻也渐攻击政府轻视人命,办事疏忽。俄国政府向来是不恤人言,有时更把专制手段,或封或禁,不使民间訾议政府的。这次不知何故,又将就起来,大约为学术,或为法律起见,即命发掘大尉的死体,请俄国第一有名的化学大家,求他分析胃里头各样东西。这博士十二分注意,逐一考察,说大尉的死因,不是因吃腐败食物,乃是死于黑色‘耶列波尔’的毒剂……呜呼,世路崄巇,一至于此,若莫斯科‘嘉直’新闻不登这医学生一纸论说,大佐两叔侄的冤死,就没有一个知道了。”[7]译述者由此感慨到,纵使是专制政府,也畏惧舆论的力量。案件得以重查,是通过科学的手段发现问题,进而确认二人是被谋杀的,从而才有了重新侦查的机会。这样的细节描写无疑能使读者认识到科学知识的重要性以及报刊舆论的力量。故事情节跌宕起伏,侦探查案时险象环生,对西方侦探能力的赞颂、对司法体制的推崇,都在作者的译述中得到展现,这一模式正是侦探小说被赋予启智教化功能后的标准文本。
与《浙江潮》中的《摄魂花》相比,《毒药案》的译者更偏重于呈现探案细节、查案时运用的科学法律知识和建构侦探的英雄形象,以及突出民众通过舆论获得与专制政府抗衡的能力,这种种都使这一件奇案成为宣扬域外文明的载体。
三、以域外文明折射本土弊病
1904 年,《绣像小说》第21 号和第22 号连载了一篇名为《俄国包探案》[8-9]的小说,故事内核与上两篇一致,只是叙述口吻更类似于传统说书人,故事讲述者不时现身就情节进行议论,常以域外境况与国内情形进行对比。这种情况在当时的翻译小说中很常见,如周桂笙译述的《毒蛇圈》、陈冷血译述的《侦探谈》等。译述者一边讲述故事内容,一边就某一情节发出感慨,或称赞域外文明、或抨击本土弊病。他们希望读者可以通过阅读小说,了解西方的法律体制、先进思想等;在域外与本土的境况对比中,认识到当时社会的不足之处,从而意识到变革的必要性。
作为晚清四大文艺期刊之一,《绣像小说》继《新小说》之后创刊,从其发刊宗旨来看,深受梁启超小说理论观念的影响:“支那建国最古,作者如林,然非怪谬荒诞之言,即记污秽邪淫之事,求其稍裨于国,稍利于民者,几乎百不获一。夫今乐忘倦,人情皆同,说书唱歌,感化尤易。本馆有鉴于此,于是纠合同志,首辑此编。远摭泰西之良规,近挹海东之余韵,或手著,或译本,随时甄录,月出两期,藉思开化于下愚,遑计贻讥于大雅。”[10]可见《绣像小说》同样是以文化人的论调,认为本土传统创作无益,遂创此刊以新民。相较于《新小说》,《绣像小说》呈现出浓厚的传统文化色彩,从其装帧来看——线装本,逐回配以绣像插图;从其所刊内容来看——除小说外,还有戏曲、小唱、杂文。即使是域外小说,译述者在叙述中也呈现出了浓烈的本土色彩。
《俄国包探案》开篇介绍了故事发生地的风土人情,略作铺陈后,讲述者便以说书人的口吻带领读者进入故事:“看官闭目一想,就可以略见仿佛了,这些话虽则是开场,但却也不能不先行表白几句,如今闲话休题,言归正传。”[8]除了叙述方式,人物的译名也颇具中国特色,受害人大佐名坤图、大尉名伯兰,作案人名夏历山、裘丽华,如若跳出小说背景,仅看人物名字,会误以为讲述的是中国故事,译述者如此翻译应该是为了“合配中国人的心理”[11]。在描写女性形象时也是套用中国传统小说中形容美人的那些词汇,如“看官你道裘丽华是怎样一个人,这却要说书的口说,也说不上来,但听说当时俄国的人如若遇见了他,不是骨软筋酥,必定魂消魄散。如果在我们中国,丽华若做了西施,那吴王的国家必定亡得更快,丽华若做了杨贵妃,那唐明皇的乱子必定闹得更凶。总而言之,裘丽华是第一等的倾国倾城绝色佳人罢了,那些眼横秋水,靥泛桃花,嫋嫋婷婷,齐齐整整的话,也无须说了”[8]。毋庸置疑,这些话是由译述者演绎出来的,用中国历史人物进行类比,消除了不同文化之间的隔阂,使读者有更具象的认知。
在赞扬侦探的能力时,译述者也将其与中国的侠客进行类比,“这梅嘉谐不但在俄国闻名,就是全地球上,那一国不佩服他,拜倒他,说他是当今世界头等有本领的大包探。但是梅嘉谐一生办过的奇案,不知多少,就比这事再难十倍的也不在他眼里,况且他已经告老归田,本不想出来办事,因闻得伊家叔侄的事,官府无法办理,他就有些手痒起来,起了一点仗义之心,如今又出世了”[8],进而由梅嘉谐推及西方所有的侦探:“须知欧美各国的包探,有一种鬼神莫测的本领,能够做成种种的假脸,要男就男,要女就女,要老就老,要少就少,要装何等样人就像何等样人,与真的一般无二。你想他装成波兰的伯爵,在裘家住了好几个礼拜,朝夕和丽华黑奴见面,却一些破绽也看不出来,这岂不是天大的奇事么?这还不算稀奇,他又能一张口里,说出好几国的话来,大约天下有名大地方的方言,包探没一处不会说的。还有一层,任是什么学问,包探都要知道,说到文,就能晓得天文地理,格致化学;说到武,就会到处飞檐走壁,舞剑擎枪,任你是个神仙,也找不着他的踪迹。世界上有了这种人,真不知替人伸出多少沉冤,代人除去多少凶暴。若是没有这些包探,那外国人这样凶险狡诈,还成个世界么?所以我对了他,真是又可爱,又可敬,又可怕。从前我们中国人说有什么剑仙侠客,我从来没有亲眼见过,却不能信他,如今看了外国的包探,这才是真正剑仙侠客哩。”[9]域外侦探在译述中被置换成了远胜于中国传统侠客的英雄,甚至成了无所不能的超人。读者在阅读此类小说时,借由译述者的描述展开对域外侦探的想象,由此,域外侦探作为新的英雄形象进驻到中国读者的心中。
与《浙江潮》和《新小说》中的故事文本相比,这篇《俄国包探案》是以中国话语讲述域外故事,从而折射本土问题。在讲述案情过程中,译述者通过对比中西方的差异,帮助读者认识到域外文明的优势以及本土的国情弊病,甚至提出建议:“我说到这里,却有一句话要表明,你想外国的医道,比我们中国高到几倍,天地间什么东西,他不知道,但有时还看不出这种毒质,可见那用这毒药的人,本领真正不小,不知怎样能找出这样东西来,若是没有大学堂医科学生这一封信说破他,那伊家叔侄二人,那里还有伸冤的日子呢?如此看来,这学问是必定不可少的,学堂是最要多开的,我们中国就是学堂不盛,学生不多,所以弄到这步衰弱的田地。”[8]从这个文本可见译述者的良苦用心,他极力发挥小说的教化功能,将一篇侦探小说演绎成反映本土弊病的问题小说。
四、媚俗的“女色陷阱”
1915 年,这篇侦探小说再次以《摄魂花》[12]的标题连载于鸳鸯蝴蝶派的刊物《眉语》第5 号至第7 号上,故事内核依旧,但情节渲染多集中于女色危害。小说作者署名兆初,也未标明译创,由于该笔名只在《眉语》上发表过两篇小说,遂此人真实身份及相关情况未可得知。
《眉语》1914 年11 月创刊于上海,办刊宣言中介绍了创刊者及办刊缘由:“璇闺姐妹以职业之暇,聚钗光鬓影能及时行乐者,亦解人也。然而踏青纳凉赏月话雪,寂寂相对,是亦不可以无伴。本社乃集多数才媛,辑此杂志,而以许啸天君夫人高剑华女士主笔政。锦心绣口,句香意雅,虽曰游戏文章、荒唐演述,然谲谏微讽,潜移默化于消闲之余,亦未始无感化之功也。”[13]这份声称为消闲娱乐,同时也希望起教化之功用的女性同人刊物,一经出版,销量扶摇直上,在民初刊物市场中很快崭露头角。从刊物自身内容及当时刊登的广告来看,该刊商业气息浓厚,深谙市民读者的阅读趣味,刊载小说偏于情爱书写,受到当时读者追捧的侦探小说也颇受编辑的青睐。
相较于着重展现西方科学、法律、民权以及宣扬侦探智慧神勇的《新小说》《绣像小说》中的故事文本,《眉语》刊载的《摄魂花》充斥着对女色阴谋的渲染。当侦探乔装成伯爵接触嫌疑人时,完全变成了为色所驱、忘记使命的男性:“便是佩丽自己,也使出他全副的精神、浑身的本领,去笼络这位伯爵,巴结这位伯爵;竟把这久离色界、早脱柔乡的老年伯爵,好似雪狮子向火,弄得浑身融化。那有为再想着家乡的道理,不要说此时伯爵已经忘了他自己的乡里,便是用那利刃放在他脖子上面,或是用那快锯放在他颈子后背,他也不怕的了,到死也不肯醒悟的了。这样的女子实是比那蛇蝎还毒,比那追魂鬼更加利害。诸位想世界上的妇人,他那种迷人的手段,杀人的本领,利害不利害呢?可怕不可怕呢?”[12]当案件结束时,译述者感慨和告诫读者的依旧是女色陷阱的恐怖:“在圣彼得堡、莫斯科两处地方,实在不知杀了多少情男痴汉,若是倚科纳夫、波立纳夫两人的事情查不出来,这毒如蛇蝎的毒妇,更不知道要闹出什么事来呢。但是佩丽虽然有这样迷人的手段、摄魂的本领,却都是那些痴汉贪他的美色,利他的有钱,自投毒网,才去遭他的毒手,中他的奸计,到后来弄得财去命亡,非但没有得着些微的好处,却反白白送了一条性命。说来实是可怕,然而世界上面像那佩丽一般的女子不知凡几,迷人的恶妇到处都有,摄魂的毒女无地无之。我但愿多出几个梅克术来,多生几位大侦探来,一一探破他们,个个擒获他们,方可使得那一班情汉痴男,不致春蠹作茧,情丝自缚,把那自己可爱的性命、宝贵的灵魂,生生被那种毒妇恶女迷去摄去呢。”[12]之前三个文本的结尾都是简单概述作案者的结局,而在此文本中叙述者大肆渲染女色危害,将一个域外侦探故事演绎成了一篇凸显女色危害、将女性妖魔化的煽情媚俗的故事,之所以形成这样的效果,除了《眉语》自身的商业性质,也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及侦探小说自身的流变密不可分。
侦探小说传入国内后,跌宕起伏的情节、曲折离奇的故事吸引了读者的眼球,时人尤喜其“千变万化,骇人听闻,皆出人意外者”[14]。由于特殊的时代环境,小说中的法律、科学元素被放大,侦探小说被知识分子赋予了启智、新民的功能。随着社会局势的变动,侦探小说的文本自身及社会定位也逐渐发生了变化。随着稿酬制度的成熟和市民阶层的壮大,小说成了消闲娱乐之物,部分创作者为迎合市民读者的阅读趣味,将原本就很有市场的侦探小说与言情、武侠、公案、滑稽等元素相结合,生产出了五花八门的侦探小说,侦探小说中的法律元素被消解,改良社会的功能被抛弃,逐渐走上了媚俗之路,《眉语》中的《摄魂花》正是这一典型代表。
五、结语
十余年间,这个俄国探案故事在四个刊物上出现了四个版本,通过这个故事侧重点不同的呈现,我们可以一窥侦探小说的内涵是如何被译述者们丰富起来的,又是如何在近代文学场中发展流变的。《浙江潮》刊载的《摄魂花》着意凸显故事情节的曲折离奇,并未对侦探技能有过多着墨;到了《新小说》刊载的《毒药案》,侦探的智慧开始彰显,科学、法律和民主等元素在小说情节中受到推崇,侦探小说被赋予了介绍域外文明的功用;及至《绣像小说》刊载的《俄国包探案》,侦探被神话化了,译述者借助侦探小说这种在当时极度风靡的小说类型,吸引更多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思考社会乱象,发人警醒;而到了《眉语》刊载的《摄魂花》,侦探的光环淡化,小说的启智功能被消解,受外界环境影响,侦探小说走上了“俗文学”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