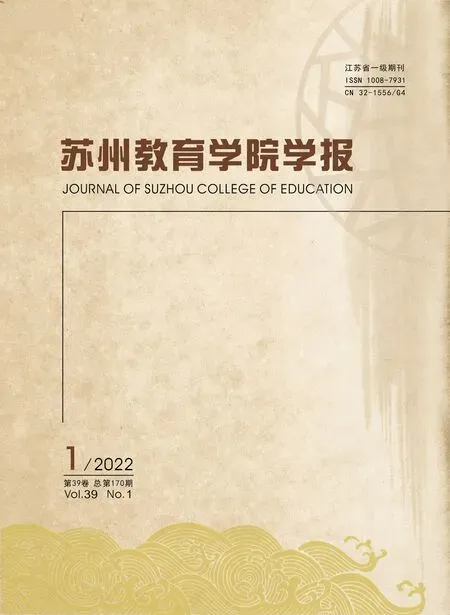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立法与管理体系建立的理论依据与实践
2022-03-18王燕
王 燕
(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公室,江苏 苏州 215006)
2013 年9 月,《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①参见:《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http://www.szfwzwh.gov.cn/zhcfg/1263。公布。2014 年起,苏州市开始了与《条例》配套的规范性文件的立法工作。由此,苏州市的非遗保护管理工作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突出特点就是从建立基本的工作体系和格局,转变为深化、细化工作内容,规范相应的工作制度,建立更为科学合理和行之有效的管理体系。2014 年至2021 年3 月,苏州市制定或修订了10 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规范性文件,加上《条例》和2006 年制定出台的《苏州市昆曲保护条例》②参见:《苏州市昆曲保护条例》,http://sfj.suzhou.gov.cn/sfj/dfxfg/200701/LRFHDMI10A4V498V66Z2LSLDVG7Y9HMJ.shtml。,苏州市出台了12 个非遗保护法规和文件,涵盖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各个方面,无论从立法的密度、深度、广度,还是立法的高度看,都是空前的。苏州非遗立法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要素、类型、保护方式等进行专项立法,在突出针对性的同时,也实现了在层次与内容上的系统性。既有总括性的《条例》,也有针对具有特殊历史文化价值的单个非遗项目进行专项立法的《苏州市昆曲保护条例》;有针对记忆性、抢救性、生产性等不同保护方式而制定的规范性文件,也有以规范相关工作管理为核心的规范性文件,如针对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保护单位、保护基地、保护专项资金等管理出台的规范性文件。这些法规文件,以《条例》为纲领,以代表性项目为核心,以传承人、保护单位、社会力量为保护主体,以保护方式为主线,在制度建设中引导激励与规范管理并举,解决现实问题与引导发展方向并重,从而形成了一个层次分明、内容完备、格局合理的立法保护体系。
12 个非遗法规文件中,有一半属于苏州市首创,填补了国内外非遗立法的空白。法规文件中的众多创建性内容为国家文化和旅游部门出台的相关文件所采纳,并为其他地区非遗立法所借鉴。苏州市非遗立法体系的建立,不仅为苏州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立法保障,也为中国的非遗立法保护提供了一些开创性的理论依据与实践范例。
立法的目的是规范指导各项具体工作。从2016 年起,苏州市在全国率先启动了代表性传承人与保护单位的评估工作,并率先公布了第一批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建立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动态管理机制。同时,在项目及代表性传承人与保护单位的认定、分类保护、后继人才培养、保护示范基地评审等具体的工作中,均体现出相对的科学性与合理性。而这些既有一定的独立性又相互高度关联的工作,共同构成了一个相对完善且行之有效的工作体系与制度体系,从而为苏州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可持续发展的政策生态环境。
苏州市能够建立一个相对合理的非遗立法体系,既源于多年来苏州市非遗保护工作实践的成果,也是苏州非遗保护理论研究成果的体现。笔者自2004 年起就开始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工作,组织参与了众多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起草了众多非遗法规文件。这些具体的保护工作,既为笔者提供了实践基础与理论来源,同时也是笔者多年来非遗理论研究的具体体现。
本文将简要论述苏州市非遗保护管理立法与工作体系的理论基础、工作思路与实践探索。
一、立法与实践的理论基础
(一)准确界定非遗的概念、范畴与类型为认定标准与保护工作开展提供依据
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言之,就是在工业文明之前就已形成且传承至今的各地、各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他们认知自身和世界的观念与知识。非物质文化遗产首先是一种文化遗产,是先人的创造,而非当下的产物。与物质遗产相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必须依赖人的传承方能表现与存续,传承者是各种有行为和思维能力的自然人,活态传承是非遗最根本的特质,因此,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核心条件是它必须至今仍然为人们传承、使用、运用。而保护的目的就是让它们继续为人所有,为人所用,并且可以在继承基础上顺应时代的发展而继续发展,依然能够激发传承者的传承动力与创造活力。由于传承者在地域、民族和个性上的不同,而呈现出鲜明的地域(民族)性、个性化和流变性。所以,历史遗产与活态传承以及与之相随的地域性、流变性与个性化,是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根本特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曾经涵盖了社会生产生活与人们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但不是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应该列入保护名录。代表性项目,就是其中具有突出的保护传承价值的项目,应当具备一定的历史、文化、艺术与科学价值。而作为植根于农耕文明的遗产,代表性项目至少应当有百年以上的历史,也应当有不少于三代的清晰的传承谱系。
因为对非遗有着清晰的界定,所以在苏州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及其传承人与保护单位及濒危项目的认定中,既有基于不同专业的定性标准,也有适用大部分认定对象的量化标准,从而避免了认定工作的随意性,也避免评审者拥有过多的自由裁量权,确保各类认定与评审、评估的公平公正与相对专业性,在一定程度上也确保了评定结果的公信力。
基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能力的评定,苏州市针对非遗项目的不同存续状态提出了具体的分类保护举措。针对那些处于濒危状态的项目,实施抢救性与记忆性为主的保护;对于有着市场潜力的手工艺项目,实施生产性保护;在一些相关文化生态环境良好的地区,实施区域性整体保护。为了更好地实施专项分类保护,苏州市先后制定了相关的规范性文件,并开展了濒危项目名录的认定工作、分类示范基地的评审工作。在保护专项资金的使用中,也针对不同存续状态的项目,给予不同的资金扶持和政策扶持。例如每年的专项资金都安排固定资金用于市级项目的数字化保存,对濒危项目给予持续的大额资金扶持,对生产性保护成绩突出的单位则给予奖励性扶持。
(二)遵循传承规律,以传承规律作为设立各项举措的依据
为非遗具体工作提供操作依据与管理规范,是专项规范性文件订立的目的。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突出立法举措的具体、专业、可操作性,具体如代表性项目、传承人、保护单位、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的命名条件、考核评估标准等都应有一定的可量化指标,才能够保证相关工作相对的公正性、公平性和规范性。由于非遗项目的多样性、复杂性和流变性,要制定具有普遍性的标准,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而如何实施具有一定普遍适用性和针对性的保护举措,是制定记忆性保护、生产性保护、抢救性保护等规范性文件的思考重点,由于这些规范性文件都是首次制定,缺少可参照范例,因此,开展保护方式的专项立法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至于濒危项目保护期限设定与期满的处置措施、民间艺术的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不是以往立法工作的空白点,就是保护工作的新难点,同时却是开展相关保护工作绕不开的重点,这成为立法工作又一个巨大的挑战。
面对这些挑战,笔者对苏州市域内的众多非遗项目进行了长期跟踪观察,同时对国内各地各类的非遗项目进行了实地调研。在观察研究了十个大类近一千个项目及数百位传承人的基础上,进行了系统的数据分析和案例总结,从中归纳出相关非遗项目传承发展规律和保护要素,以之作为制定各种举措、标准的理论依据。笔者经过多年研究发现,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工作的决定性因素为传承人,而传承人掌握非遗技艺的周期就是确定非遗项目传承与保护周期的决定性因素。在掌握大量数据的基础上,笔者还发现,一个传承人掌握一项非遗技艺至能够入行一般需要10 年;而掌握精髓至少需要20 年;达到出神入化、炉火纯青的境界则需要更长时间的磨砺和勤奋努力。也就是说,一个项目如果处于濒危状态,至少需要10 年才能够确定其能否继续传承;20 年左右才能确定其是否转危为安;经过两代人的努力,即40 年左右才能确定这个项目是否能真正稳定地传承下去。传承周期是制定各类标准与工作周期的最主要依据。因此,代表性传承人认定标准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是从业20 年以上,保护单位认定的基本条件是从业10 年以上,濒危项目名录的基本期限为10 年。而濒危项目传承经费周期最高可以到5 年的规定,就是为了确保濒危项目保护工作的可持续性。
经过深入研究,笔者还发现传承人、其他参与者(设计人员、经营者、研究者、传播者、投资者等)、受众(市场、消费者)、资料器具材料等传承物质载体、活动空间(场合)构成了项目传承的基本要素,其中传承人与受众之间互动的活跃程度决定了项目的存续状态和方向,活动空间则是保护工作最重要的外部条件。保护工作就要让这些保护要素充分发挥其各自的作用,而立法则是通过资金、政策等杠杆优化配置这些保护要素。在不同保护方式的运用中,这些要素的重点与比例也有所不同。在生产性保护中,突出市场引导作用,着重激发传承人、设计者与经营者三者的参与积极性,并且打通渠道推动三者的有机互动,同时通过约束机制,确保生产性保护的参与者能够坚持手工生产、原创性和文化内涵。而在记忆性保护中,则重点激发传承人、研究者、传播者的积极性,确保资料记录整理的完整性、真实性,其中约束机制的重点在于合理利用公共遗产资源与保护个人在开发遗产中的合法权益。在濒危项目的抢救性保护中,突出政府保护的主导作用,强调工作的重点在于传承,尤其是后继人才的培养,通过传承经费的设立激发传承积极性。抢救性保护的约束机制重点则放在各级政府和保护单位、代表性传承人等保护主体的义务的履行上。
(三)缓解非遗存续危机是保护工作的重点
在大量调查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尽管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及现状都不尽相同,但都面临着两大严重的危机——后继乏人与文化内涵的弱化消解。
后继乏人表现在三个层面上:最直接的表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缺少后继的学艺者、从业者,面临失传的危险;第二个层面为缺少年轻的后继者,尤其是40 岁以下的青年从业者;第三个层面为缺少高素质的从业者和学艺者。国家公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涉及10 个大类。苏州的159 个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包括32 个国家级项目)涉及全部10 个大类,其中60%以上的项目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后继乏人问题,其中民间文学、传统舞蹈尤为突出。
而文化内涵的弱化、消解表现亦体现在三个层面上:首先是项目基本特征;其次是地域特色或民族特色;最后是项目最高技艺或独有的绝技。在笔者调查的500 多个项目中,大部分项目与其历史上的最辉煌时期相比,文化内涵都在弱化或消解,趋于空壳化、异化。甚至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连其作为某类项目最基本的属性都在弱化。如传统美术与传统手工技艺中手工的成分越来越少,机器正在取代手工;在戏剧、舞蹈等表演艺术中,掌握其基本技艺或核心文化内容的人员越来越少,表演日益简单化;民俗活动正在沦为旅游项目或商业活动……曾经盛行于太湖流域吴语区的吴歌,在20 世纪70 年代至90 年代,尚有很多老歌手能够演唱500 首以上的吴歌,更有一些杰出的艺人能够演唱1000 行以上的长篇叙事吴歌。时隔30 年之后,能够传唱100 首以上吴歌的艺人已寥寥无几,而能够完整演唱2 部以上长篇叙事吴歌的歌手几乎找不到。
在各类传统戏剧中,文化内涵的弱化已经十分严重。其共同表现为经典传统大戏尤其是全本大戏的演出与传承的急剧减少。只有一些历史短暂、影响力小的地方小戏,目前仍然以传统经典全本戏的演出为主,其原因在于这些地方小戏的剧目本来就以角色少、时间短的小故事为主。而那些历史较长相对成熟形成了众多经典大戏的传统戏剧,传统大戏演出的减少已经成为传承的隐忧。经典传统大戏,其唱腔、身段、剧本等,经过数代演员的千锤百炼,也经受了时代和观众的考验,所以集中了该剧种的精华。经典大戏种类、数量的多寡代表了剧种的成熟程度和影响力。演员从事某剧种演出,都是从学习传统经典大戏开始,而对传统经典大戏的掌握程度,也反映了一个演员的演出水平。但是在调查中却发现,大部分传统戏剧,经典大戏的演出场次在总演出场次中的比例很低。
在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掌握最高技艺或者艺术精髓的传承人数量也在整体减少,如苏绣、苏扇、缂丝中掌握三异技艺的艺人,都已寥寥可数了;一些手工艺、传统表演艺术的绝活、绝技正在消失。以昆曲为例,在20 世纪上半叶对于昆曲的传承起了重要作用的“传字辈”中不少人能够掌握200 部左右大戏,其后的“继字辈”减少为数10 部,再其后的“承字辈”减少为数部;21 世纪后开始从艺的年轻演员,能够完全掌握一部大戏都属水平较高,他们已经以折子戏的演出和传承为主了。各类民俗活动则呈现出相关信仰缺失、相关文化事项传承后继乏人等状况,其核心的文化特征和文化特色也在弱化。如庙会中的表演内容减少或水平下降、寿俗婚俗的程序简化,等等。
由于工业革命以来交通与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地方特色在各种文化的碰撞交流中也在逐渐弱化消解,很多不同地区的同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面目越来越相似,如四大名绣无论技艺还是艺术风格,都已经很少有独特的地域特色了,彼此间的差异已经不再鲜明。
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普遍面临的这二个危机中,后继乏人的程度,直观地表现出项目的现状和存续的趋势,是一个相对显性的危机;而文化内涵弱化消解的程度,则代表了非遗项目传承的质量和层次,在很多时候,是一种隐性的危机。两者的存在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因此,解决这两大危机,既是非遗保护工作的重点,也是立法保护中制定各类举措的重点。在苏州市的各类非遗法规文件中,后继人才的培养都是重要内容。其中,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办法①参见:《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办法(修订稿)》,http://www.szfwzwh.gov.cn/zhcfg/1266。、代表性传承人评估办法与标准②参见:《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评估办法(试行)》,http://www.szfwzwh.gov.cn/zhcfg/1326。、濒危项目人才培养与管理办法③参见:《苏州市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人才培养与管理办法》,http://www.szfwzwh.gov.cn/zhcfg/1325。等规范性文件的重点都在后继人才的培养和激励方面。在鼓励青少年学习非遗知识、技艺的同时,也采取命名为代表性传承人候选人以及给予就业便利、创业扶持、资金扶持等举措来激励学徒在掌握技艺后继续从事项目的传承。同时通过命名传承基地、给予优惠政策等措施,鼓励高校、传习机构等社会力量参与项目的传承工作,以扩大后继人才培养工作的社会参与度与多元化。
为了应对文化内涵的消解弱化的危机,在各类规范性文件中,均制定一定的约束性条款,其中的重点就在于强化政府认定的保护单位与传承人、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传承基地等工作主体传承文化内涵的责任意识。导致文化内涵弱化消解的直接因素是传承人基于各种原因而放弃了对技艺和文化内涵的坚守。尽管传承人有众多的客观理由来解释他们的不得已而为之,其中最容易获得理解与同情的就是现实的生存压力,但作为政府认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与传承人,其首要的责任就是传承,就是传承文化精髓。因此强化保护单位与传承人的责任意识,是政府推动传承的一个重要内容。通过严格规范传承人和保护单位、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的申报资格、认定条件和绩效考核机制以及后续的奖惩机制来使他们意识到自身的职责与义务。所以,在记忆性保护的规范性文件中明确在非遗资料的开发利用中,不得歪曲原有的文化内涵;在生产性保护的规范性文件中,明确生产性保护的一个前提是坚守手工生产,并在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的命名中将这一点作为基本条件;在传承人、保护单位的评估中也将文化内涵的坚守作为评估重要指标。目前有一些非遗项目的传承者、从业单位把成为传承人和保护单位当作一种炒作牟利或者获取某些政策资金利好的途径手段,而不是将此视为一种责任和义务。这种现象的存在与蔓延,很容易导致保护单位与传承人价值取向的扭曲,而无法沉下心来传承非遗的文化内涵。因此,保护单位与传承人的遴选认定及认定后的考核都应将传承责任的履行状况作为重要的衡量指标,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保护单位与代表性传承人的退出或除名机制。在认定后,如果单位与个人不认真履行传承文化精髓、文化内涵的职责,就应当取消其资格。而对于那些真正传承文化内涵,使文化内涵不断丰富深化的单位与传承人,则要给予奖励。
二、整体与具体协调、务实与前瞻并存的立法原则
非遗项目复杂多样,保护工作的重点、方式各不相同,保护主体的权利、义务的重点也各不相同,这些都决定了专项立法的必要性。但在实践中,各种保护要素、保护方式、保护主体存在相互交错并行的普遍现象,这使得专项立法既要做到主旨明确、重点突出,又必须要考虑在整体立法格局中的协调平衡。而由于非遗项目传承中的流变性、发展性特点,项目的传承发展现状和趋势均在不断变化中,其是否能够良性发展,很大程度取决于保护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与保护方式实施的科学性。非遗项目传承发展和保护工作的特点决定了立法既要从现状出发,也要准确把握未来发展趋势;既要调动保护力量的积极性,也要加强规范管理。
因此,苏州市在非遗立法与保护工作实践中始终将促进非遗保护的平衡发展作为主旨,在具体条款制定和保护举措的实施中,相互错位,重点突出。如记忆性保护、抢救性保护与生产性保护,三者既有不同,又有交错。所以在记忆性保护中,突出资料的整理研究与合理开发利用;①参见:《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忆性保护工程实施管理办法(试行)》,http://www.szfwzwh.gov.cn/zhcfg/1265。在抢救性保护中,强调濒危名录的建立与管理、后继力量的培养;②参见:《苏州市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办法》,http://www.szfwzwh.gov.cn/zhcfg/1324。而生产性保护,重点则放在通过资金政策杠杆,激发传承人、设计力量、营销机构在保护工作中的积极性,并且为三者的协作建立通道③参见:《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促进办法》,http://www.szfwzwh.gov.cn/zhcfg/1544。。
注重非遗保护格局的整体把握,又注重不同类型项目特点的具体分析,使苏州市整个立法与管理工作格局呈现出相互呼应、平衡协调的特点。在具体保护举措中,既注重解决保护工作的现实问题,又为保护工作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上升空间。在订立传承人、保护单位、社会力量的具体管理措施中,既注重体现法律约束的普遍性原则,又兼顾特殊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使各项举措合情、合法,如在代表性传承人的命名、管理与评估中,强调了代表性传承人必须履行传承义务,但同时对年老体弱的传承人,又提出可以不参加评估,可以申请列为荣誉传承人等特殊规定。秉持以上这些原则,苏州的非遗立法体系呈现出整体与具体协调、务实与前瞻并存的特点。
三、保护工作的苏州创新与实践成效
(一)在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和保护单位的认定与管理中,建立动态管理机制,制定评估办法与标准
代表性项目是推动保护工作的核心,而传承人与保护单位则是实施项目保护的主体。由于非遗传承的流变特点,建立动态管理机制,制定评估办法与标准,能够及时根据项目的现状实施不同的保护举措。在传承人与保护单位的认定与管理中,建立评估与退出机制有助于激发保护单位、传承人履行保护义务的积极性,从而形成非遗保护的良性运行机制。苏州市在非遗代表性名录体系中建立濒危项目名录,拓展了名录命名体系,并通过确定濒危名录期限、期满后的处置措施,使项目的保护呈现出更合理的流动性,保护举措更为合理可行。在传承人的认定、管理、评估中,建立荣誉传承人与传承人候选人制度,明确评选标准,深化了传承人的层级,使传承人的认定与传承活动扶持更有针对性和可持续性。目前苏州市已公布了第一批6 项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④参见:《市政府关于公布〈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第一批濒危项目名录〉的通知》,https://www.suzhou.gov.cn/szdoc/uploadfile/sxqzf/szsrmzf/201710/P020171020581183096302.pdf。,针对濒危项目的数字化保存工作已全部完成,给予濒危项目重点资金扶持,使部分项目焕发出活力,濒危状态有所改善。开展了两次传承人与保护单位的评估工作,增强了代表性传承人与保护单位的传承责任感,对整个传承工作起到了激励作用。在通过认定84 位荣誉传承人后,2021 年又公布了130 位第五批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名单①参见:《苏州市第五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名录》,http://www.szfwzwh.gov.cn/chchr/c98。,建立起了更为合理的传承人梯队结构。
(二)引入市场机制和社会力量参与机制,提出生产性保护的具体促进举措
在《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促进办法》②参见:http://www.szfwzwh.gov.cn/zhcfg/1544。中,根据生产性保护涉及项目既具有文化遗产特质,又具有经济行业的特点,以及生产性保护面临的主要瓶颈问题,制定了多项创新性鼓励措施。这些举措的一个核心就是充分利用市场机制,促进非遗生产性保护的有效实施,以传承保护推动合理开发,以合理开发促进传承保护。其中,鼓励利用在线交易平台开展网络营销推广工作、鼓励建立创意集市或恢复相关传统集市等措施具有突出的前瞻性。随着时代的发展,网络推广与线下集市已经展现出应有的活力。
(三)突破部分非遗知识产权保护空白点
目前,民间文学与民间艺术的知识产权归属与使用尚无明确的法律规定,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相关知识产权的归属与使用已经影响到部分项目的保护。
在保护凝聚了无数前人智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过程中,应强调传承,强调共享。除极少数一直为某些团体或家族传承的非遗项目外,绝大部分非遗项目都不应为某个自然人或法人所独有和独享,而应强调其为所有人共享和理解。即使是少数特定人群传承的项目,尽管其传承方式具有封闭性,但对其的认知和理解也应向社会大众开放。众多流传至今的非遗正是多种文化交流的成果,文化之间的流动和交融是非遗传承创新的重要外在力量之一。
在实践中,有关非遗知识产权的争议更多地不是在使用上,而是在归属上。而归属中,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是将流传已久的非遗申请为个人或法人所有。这对非遗的传承和交流是极为不利的。因此,明晰非遗知识产权的归属,首先应该做的不是明确为谁所有,而是不应为谁所有。非遗知识产权的使用则更应强调其活态应用和交流。
在不违背国家现有相关知识产权法规的前提下,苏州市在制定涉及非遗知识产权的规范性文件——《苏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忆性保护工程实施管理办法(试行)》③参见:http://www.szfwzwh.gov.cn/zhcfg/1265。——时,遵循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应归属为少数组织或个人的原则,同时又充分尊重个人在继承遗产基础上的创造力,创造性地提出了有关非遗知识产权归属与使用的条文:“任何单位、组织和个人不得将已在民间广泛流传、经多代人不断加工而形成的民间艺术作品,以单位、组织和个人名义申报有关知识产权。”“任何单位、组织和个人在改编或再加工作品或汲取文化要素新创作品时,应注明其改编自何项目,并不得冠以项目原有名称,不得歪曲篡改原作,不得造成公众对该项目的误解。”“任何企业或个人,不得将已经流传多年,经多代人不断完善而形成的传统技艺或技术,以企业或个人名义申报有关专利或知识产权。”
通过这些规定,明确了任何组织与个人不得将历代人民创造力结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为个人知识产权,这就从地方立法层面对将非遗资源及其相关标识等申报为知识产权的不正当行为加以约束。同时,强调在非遗项目知识产权的利用开发中,保护民间的“原生态”版本,不能歪曲与恶意篡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