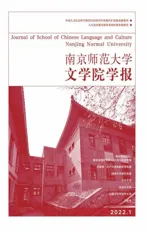清末民初上海叙述中的马路、街景及其空间现代性意蕴
2022-03-18汪贻菡
汪贻菡
(唐山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北 唐山 063000)
青楼、茶楼、酒楼,报馆、番菜馆和洋货商店,整饬宽阔的马路上商铺林立、车水马龙、灯火彻夜不明,堂子倌人、印度巡捕满街游走,满清贵胄和留学生党比肩而立……在晚清中国,这些标志性的描写都指向彼时唯一的、具鲜明异质性的本土空间,即号称“十里洋场”的上海租界。作为率先且唯一崛起的现代都会,上海前所未有地被叙述、被描摹、被谴责、被向往,其不同于此前城市叙述的是:极少有一时代之小说如此热衷于对一座城市的道路以及围绕道路的店铺、牌匾、娱乐设施等等进行风物志般连篇累牍的摹写。除却《东京梦华录》这样的地理类笔记,中国古典小说中的城市书写多集中于历朝历代最繁华城市中的地标性建筑,如唐长安之曲江、宋东京之金明池、明南京之秦淮河等,而英租界本身即构成晚清上海的“地标”,并且这描写还会深入到该“地标”内里、细致到每一条马路或街道的地理布排;同样区别于风物志或城市书写的是,晚清上海叙述中的马路,已不仅仅是地图意义上的故事背景空间,而是作为上海的“血脉”——既构成上海,也讲述上海。
一、马路与街道:作为风景
晚清上海的城厢格局,与租界“越界筑路”密切相关。英美法日各国租界设立后,加紧筑路、修建码头,在界内各自为政;1853年前后,西人以军事防御、协同上海道“剿匪”(镇压小刀会和太平军起义)为借口,开始实施小规模越界修建军路行为;后发现有利可图,为拓展租界势力范围,1863年将英法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设工部局、收管军路,开始有规模有组织地推行越界筑路,并将所开辟范围扩展为“合法”的租界属地,乃至于发展到后来,筑路几乎成为工部局的“首要职责之一”(1)杨文渊.上海公路史(第一册)[M]. 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9,第18-26页。。自1846年修筑“界路”(河南中路)开始,通过增辟、拓宽、越界延长等手段,租界面积不断扩张,至1899年,公共租界由1863年的10676亩拓展到33503亩(2)蒯世勋.上海公共租界史稿[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第401页。;1865年工部局统一路名(3)英界马路南北向干道用中国省份命名,东西向干道用中国城市名称命名,并把写有中英两种文字的路牌竖立于路角。,东西向的南京路、福州路、广州路等由北向南渐次铺开,南北向的四川路、江西路、河南路等自黄浦江由东到西,横纵交错。马路最宽处可容三四辆马车并驰,沿街几乎全为商铺,华洋杂居(1854)后租界人口更是激增,商业服务业飞速发展,从仕商巨富到小本经纪皆不吝租金寄居租界,“以租界之事事皆便也。而租界事事皆便者,马路之便也”(4)申报[N]. 1896-12-08。;宝善街、福州路一带,因诸多酒馆妓院茶楼等在此开设,一跃成为上海新城的地标式街区:“十里之间,琼楼绮户相连缀,阿阁三重,飞甍四面,粉黛万家,比闾而居。昼则锦绣炫衢,异绣扇霄。夜则笙歌鼎沸,华灯星灿,入之如天仙化境”(5)王韬.红豆蔻轩薄幸诗(下)[M].寇德江点,王韬.淞滨琐话.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第210页。;不仅如此,这里的道路还“时加修饰,不使半步之崎岖;沟池则时加疏浚,元使淤泥之稍积”,由此每日里“轮水渀沸,尘漠不飞”;同时设有华洋巡捕,“植立于各界四叉,以防行人车马碰撞之虞,虽昼夜、风雨、寒暑不改”,“以是沪上少争斗盗窃之患”(6)池志徵.沪游梦影[M]. 胡珠生标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第155页。。
道路是一座城市的骨骼,为侵略者贪欲所驱使的筑路行为,既彰显了晚清上海的殖民改造是通过对空间的掠夺与占有来实施的,又在客观上成为推进上海城市交通发展的杠杆。作为西方城市建设经验的移植范本,晚清上海从一片泥滩、三数茅屋之地发展到盖无其匹的国际都市,其现代都市景观正是在马路/街道基础上构建起来的;平面马路和高层建筑的修整带来的纵向空间层次化、良好的道路建设与照明设施、便捷的公共交通与共享的公共空间等等都市要素的成熟,均使得马路拥有了被视为“景观”的可能。在入沪者眼中,这兼具民族耻辱和都市文明象征的马路,成为其对上海印象的首要载体;而在清末民初的上海叙述里,马路与街道的出现频率极高,街道景观要么构成租界叙述的标志性开篇,要么构成外省人入沪后所见的首场“西洋景”。
《海天鸿雪记》:上海一埠,自从通商以来,世界繁华,日新月盛。北自杨树浦,南至十六铺,沿着黄浦江,岸上的煤气灯、电灯,夜间望去,竟是一条火龙一般。福州路一带,曲院勾栏,鳞次栉比。一到夜来,酒肉薰天,笙歌匝地…;
《海上繁华梦》:沧海桑田几变更,繁华海上播新声。烟花十里销魂地,灯火千家不夜城;……此时正是九点余钟,那条大英大马路上,比二人早上来的时节不同,但见电灯赛月,地火冲霄,往来的人车水马龙,比着日间更甚热闹;
《海上尘天影》:从浦滩向北到英界,过海关进三马路到大马路,但见两旁皆是洋房,果然画栏凌虚,长廊匝地,洋行商铺,货物纷罗。来往的人不可计数,有坐车的,有乘轿的,有步行的,说不尽风流富贵,热闹繁华。
《碧血幕》:单说中国第一通商口岸上海地方,是个繁华总汇,…因此市廛栉比,歌馆云连,货物山屯,帆樯林立,说不尽的喧嚣热闹。一天到晚,车马之声,震得人头脑都痛。福州路一带,更成了个狂荡世界。
类似这样的针对租界的全景式扫描在晚清上海叙述中屡见不鲜,撷其要点,大抵绕不过灯火的彻夜通明、商业的极度繁盛、倌人的花枝招展、享乐手段的无所不至,以及由此引发的声色震撼和伦理震惊。这样的震惊体验往往发生在外省人初次入沪的情节描写中,而铺陈开这些声色体验的则是租界最著名的几条街道,即自北向南依次铺陈开的大马路(南京路)、二马路(九江路)、三马路(汉口路)、四马路(福州路)、五马路(广东路)、六马路(北海路)等;其中又以四马路最为繁华:“每当夕阳西逝,怒马东来,茶烟酒雾,鬓影衣香,氲氲焉荡人心魄”;“入夜则两行灯火,蜿蜒如游龙,过其间者,但觉檀板管笙与夫歌唱笑语、人车马车之声,嘈杂喧阗,相接不绝”;“盖英界为沪上之胜,而四马路又为英界之胜”(7)池志徵.沪游梦影[M]. 胡珠生标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第156页。。对于初次入沪者,四马路开启了他们进入都市的第一个震撼性奇观,对于不曾入沪的外省人,四马路亦构成了想象中的上海;余外去一品香吃大菜、丹桂园听戏、青莲阁品茶、逛沪上花园、乘钢丝马车等等,皆不出这数条马路之范围。其繁华至此,乃至于在某种程度上,晚清上海租界的故事,便是围绕这几条马路展开的故事,那纸醉金迷、物欲横流、道德沦丧是笼罩其上的既罪恶又魅惑的底色,于底层平民/贫民而言,即便无法纵欲享受这租界繁华,就逛逛马路、饱个眼福也是好的。《海上花列传》第二十九回,赵二宝逼问其兄赵朴斋为何身无分文也不愿转回乡下,“连问十数遍,朴斋终呐呐然说不出口”,二宝一语道破:“我说俚定归是舍勿得上海,拉仔个东洋车,东望望,西望望,开心得来!”;入夜后朴斋陪伴初次入沪的母亲早早睡在客栈,却“听得宝善街上,东洋车声如潮涌,络绎聒耳;远远地又有铮铮琵琶之声,仿佛唱的京调,是清倌人口角,但不知为谁家”,遂“心猿不定”“火性上炎”(8)韩邦庆.海上花列传[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第241-242页。;而本为寻兄、入沪月余即落堂为妓的赵二宝,所喜者亦无非是吃酒听戏、坐了马车闲逛,红妆绿鬓一路穿花拂柳、送往迎来令人目眩心迷。
借助川流不息的马车、黄包车、汽车,乃至电车、自行车,街道将茶楼、酒楼、青楼和公园、戏院、番菜馆等等勾联成作为整体的上海休闲空间,拥有自己的空间秩序(由红头阿三出面维护)和空间地标(如一品香、丹桂园、张园等)。在对上海反反复复的晚清叙述中,无论是四马路还是宝善街,街道在这里都不再只是个地点,它们构成地理上海,成为晚清上海的城市名片;也构成文字上海,无论是城市全景还是细部近景,街道始终占据上海景观的主要部分——在小说家笔下,这便构成“风景”。风景在古典叙述中多与自然山水相关,而在难寻山水之胜的沪上,若说也有“风景”,则大抵由马路及街道景观构成,此处将其命名为“街景”。所谓街景,既指马路与街道上的建筑、树木等构成的固定性“物景”,亦指行人、车辆等流动性“人景”,以及人与物、人与人之间所发生的、占据一定时空的“事景”。人、物、事所建构起来的动态都市风景线,构成了晚清至民初地理意义上的“上海景观”和文字意义上的“景观上海”。检阅该期叙述上海的长篇,或以《海上繁华梦》这部可能被低估的作品中的街景叙述最为突出。
二、街景叙述与叙述上海:以《海上繁华梦》(9)海上漱石生.海上繁华梦(附续梦)(全四册)[M]. 奭石,吉士,秋谷,向明标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下文所引皆出于此,不赘。为例
在盛赞《海上花列传》并论及晚清狭邪小说时,胡适曾将《海上繁华梦》与《九尾龟》等并入一类,认为“刚刚够得上嫖界指南的资格,没有文学的价值”(10)胡适.海上花列传-序,胡适全集(第三卷)[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527页。,这句轻描淡写的评语,其时既遮蔽了该作主题的丰富性,亦是对其以市井之小叙历史之大的文学史意义视而不见。该著连同续书共两部,计一百六十万言,正书三集一百回,以苏州贵公子谢幼安、杜少牧“游沪—迷失—返乡”的情节为主线,以四马路为主要故事空间,针对各种洋场新鲜事物做了不厌其烦的指南式介绍,凡与行、居、食、游相关的每一行当的消费价格、赏玩方式、最著名的品牌并地理方位等等,均事无巨细地穿插在故事情节当中,做成一幅1892-1903年间的“上海导览全图”;续书三集一百回,以湖北掮客萧怀策如何发迹、上海富家子戚祖怡如何堕落、并在萧怀策的算计下家毁人亡为核心故事线,纵向梳理了1909-1913年间上海滩所经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三次革命等历史事件及其对小民生计的具体影响,期间上海滩街道店面的迁易、旅馆和交通工具的“升级”、妓女名号和服饰装扮的更迭、乃至租界地价和房产租赁业的波动、保险银行证券等早期金融业风潮等等,均方方面面传递给读者。虽欠缺性格鲜明的人物,亦不能说有值得称道的情节架构,然以亲历者身份,将租界开埠五十周年到“三次革命”、从清末到民初这巨大的时代更迭,举重若轻地织入这细密、琐碎而漫长的上海滩故事集当中,也不能不说是一桩盛举。这样的持续十几年(11)《海上繁华梦》初集30回于1903年由上海笑林馆出版,1906年三集100回刊毕;1909年上海环球社刊行《图画日报》,开始连载《续海上繁华梦》(计38回),1916年初由上海文明书局刊续集单行本一百回。又据《退醒庐笔记》载,辛卯秋(1891年)孙家振与韩邦庆应试北闱,场后同船南旋,曾互易阅读彼时正在创作的《海上繁华梦》与《海上花列传》,故该著写作开始时间至晚为1891年。正书开篇为1892年元宵,续书结于三次革命(1913)前后,所述上海故事跨度近二十年。见:习斌.晚清稀见小说鉴藏录[M].上海:远东出版社,2013年,第75-79页;孙家振.退醒庐笔记[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第65页。兴致勃勃紧贴生活的书写,虽欠缺了沉淀后的审视与提炼,却也赋予该作不可替代的鲜活的在场感。而街道及其风景化/景观化的书写,则是这种在场感最重要的传递方式。
与《海上花列传》不厌其烦地叙述里弄名称、堂子名称以搭建起一幅清晰的海上花事的地理指南同中有异的是,孙家振不仅将茶馆、番菜馆、戏楼、旅店、洋货铺、照相馆等穿插进四马路长三堂子间,还在四马路、棋盘街、张园之外,将大马路到六马路、抛球场、各大公园以及法租界、泥城街、南市内城、浦东等地也一并包纳进去;正续两部比较起来,续书不再黏著于妓院骗局,视野宕开,更将律所、西人公堂、养善堂、新剧场、赌场、花会、银行业、保险业等等新兴都市空间随街道一起纳入文本,铺陈出一个更加立体生动、充满历史感和流动性的、兼具情色和资本气息的更完整的上海滩。倘若说《海上花列传》所勾勒的,是一副以洪善卿为牵引者、相对静态的步行者的平面地图,那么《海上繁华梦》则是充满人车喧嚣的流动的晚清上海滩画卷。许是为了对抗晚清上海的动态与喧嚣,韩邦庆喜将笔触集中于弄堂内部,一场又一场叫局,一轮又一轮花酒,陶玉甫和李漱芳在一个雨夜的缱绻(17、18、20回),黄翠凤谋划罗子富身家的一个黄昏(6-8回),都足以支撑两三回篇目,少有的户外场景除却“一笠园”之外,便是沈小红与张惠贞因吃醋而在明园内大打出手(9回),余下片段便如灯下絮语、豆棚闲话,在一个眼风、几句拌嘴中吁吁滑过。相较之下,《海上繁华梦》则嘈杂张扬得多。与静态物景比较起来,该作更热衷于书写街头动态的人景与事景,而在这华洋杂处、五方荟萃的晚清上海街头,故事每时每刻都在发生:满庭芳街到宝善街的转弯地方,不知租界不可当街小便的钱守愚,被巡捕扭着辫子拖到巡捕房(正书二集10回);抛球场口,一群流氓挤着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子调戏,围观者喝彩大笑趁乱揩油(正书二集5回),清和坊路面上,歹徒公然持枪拦劫,从坐在黄包车里的少太太手上生生掳走金镯子《续书三集9回),更有一辆受惊的马车从法租界狂奔至英租界、一路骇跌多少车辆行人(续书初集18回);如果你插手立于街头,则能看到乞丐们走来走去玩弄各种讨钱伎俩,那些花枝招展、衣袂飘飘、安坐于高头马车敞篷座中的,未必只有时髦倌人,亦有良家姐妹,偶然飞驰而过窗帘紧闭的轿车里,可能是萧怀策和妓女镜花别院正在上演一出春宫戏(续书初集10回);倘你愿意上楼泡杯热茶、拣个二楼临街的茶座,则那居高临下的街景更为精彩,戚祖怡被薛丽鸿一伙流氓捉了“仙人跳”,因往大兴楼“吃讲茶”,结果黑吃黑引发双方十数人群殴、哄动整个茶馆(续书二集21-23回);福州路一带,虐妓的恶鸨阿金与黄家娒正戴枷游街,无数闲人拢来观看,堵得一整条马路不能通行;高居大观楼上饮茶“赏景”的谢幼安和杜少牧一群人正津津有味地看那巡捕弹压人群,却见一个披头散发的妇人从人群中钻到阿金面前痛哭,原来是正书前半部兴风作浪、逼死无辜、玩弄杜少牧于股掌之间的妓女颜如玉,终于恶有恶报,得了个失心之症,杜少牧一路尾随闲人,却见颜如玉赤身裸体地在城外九曲桥上乱走发疯(正书后集38、39回)……身为记者的孙家振,以持久的好奇心和缜密的观察力饶有兴趣地捕捉街头发生的一切,无论是四马路光鲜亮丽引领时髦的倌人还是棋盘街阴暗拐角处窘迫的底层贫妇,无论是初次进城被当作曲辫子嘲笑的乡下人还是包着红头巾手拿哭丧棒、有时恐怖有时又成为居民保护者的印度巡捕,他都细细地用文字的方式将其绘录于纸上,作为这座城市流动的风景线的一部分。
然而,与同样热衷于描绘上海滩街景的“新感觉派”比较起来,缺少橱窗和霓虹灯的晚清街景书写多数时候并不被视为是“风景”;在有关海派小说源流的梳理中,陈旧的或新旧交替的“四马路文学”被切割在“海派”之外,由四大百货公司、沙逊大厦、江海关大楼和百乐门舞场、大光明影院等巨型建筑构成的大马路(南京路),才是真正的具有现代气质的商业文化街区。倘若我们忽略大马路取代四马路,乃是“新生”的享乐主义取代了“没落”的享乐主义(12)吴福辉. 都市旋流中的海派小说[M]. 北京:科学出版社龙门书局,2018,第12-23页。,仅在马路叙述的延长线上、就街景的叙述方式来看,与1930-1940年代的海派相比,晚清街景叙述中的实用性遮蔽了审美性,投身现场的迫切感造成了距离感的缺失——而这正是“风景”构成的主要元素之一;又往往与晚清街景的叙事起点相关。包括《海上繁华梦》等在内的晚清洋场叙述中,始终涌动着一个“老上海”对新入沪者“指南书写”的直接动机。大抵初次入沪者,在震撼于租界景观的同时,亦对租界种种规定不适,而多数不适皆与街道相关:工部局制定的租界章程、道路保护条例、交通管理条例等路政法规中,均有对街道这一公共空间行为的约束与管辖,如行人需靠边行走、车辆需靠左行驶、垃圾需在九点前倾倒、店铺招牌需离地七尺以免碍及行人、不准当街晾晒亵衣、不准在街头便溺、大声喧哗、聚众斗殴等等,葛元煦《沪游杂记》谈“租界例禁”20条,13条与马路相关(13)葛元煦.沪游杂记[M].郑祖安标点.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第9页。。这种种规定于晚清国人是纯然陌生的,其着眼点在于维护居住环境的整洁、干净、安静、安全,与为了管理方便起见的坊市制、厢坊制等迥异其趣。也因此晚清上海叙述展示租界“文明”的经典片段,十有五六为乡愚入沪后在街头犯禁而遭巡捕盘训;在将租界与上海县城、或将上海与北京等外省进行比照时,亦大抵绕不开租界之街衢清洁宽阔、市容整洁之优。而在最初的不适后,这些以公共道德为基础的空间守则以无需言喻的力量为多数居民所接受,并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成为居沪者自恃“文明”的底气:《海上繁花梦》中,谢幼安寓居租界仅月余,便对上海县城街道的湫澳不堪表示不屑,全然忘记自己常居的苏州城亦是满目荒凉了无生气;刚从“淴浴”迷阵中醒悟过来没多久的杜少牧,面对新入上海滩的钱守愚,已然可以指点其出入堂子、点吃大菜的规矩了——波德莱尔曾饶有趣味地指出:现代性这种体制,是震撼别人时自己体验到的乐趣以及因永远不会被别人震撼而获得的骄傲的满足(14)Baudelaire, Charles. uvres completes [M]. VoI.II.Paris,Gallimard,1976,p.710.转引自杨振.评彭小妍《浪荡子美学与跨文化现代性[J]. 中国比较文学,2015(2),第213页。,纵然谢幼安、杜少牧等旧文人尚不能被指认为“现代人”,然其在指点钱守愚时、对租界空间秩序自发的遵守与维护,和叙述者对洋场景致十数年如一日、如数家珍的展示中,一种将租界及其秩序作为审视对象,以及将自身对该秩序的谙熟、他者对该秩序的陌生进行沾沾自喜的比照行为,又有意味地使租界及其秩序对象化、他者化和景观化了。
与此同时,铺陈洋场生活指南的动机,亦使《海上繁华梦》所书写的街景具有了成为风景的另一重可能,也即:与道德谴责同样热忱的,对洋场物质世界、消费空间的自始自终的热忱播报——这两重热忱贯穿于多数晚清上海叙述中,关于赌博、嫖娼、黑幕等细节的精准刻镂,对于所谓“警觉提撕之旨”、“警醒世人痴梦”的遮蔽,就像“上海,建造在地狱上面的天堂”(穆时英《上海的狐步舞》)这句著名的感慨一样:在惧斥之外,是深深的依恋;在观望之余,是投身其中的热切。而当时过境迁,生活指南和黑幕揭发的意义褪却,那些有关人、物、事的街头素描,则因时空间隔、逐渐凝固为一幅幅暗响浮动的晚清浮世绘:现代读者重读这将浩荡史实浸润于家长里短、街头巷尾的浮世绘,则被倒置的“风景”(15)在《风景之发现》中柄谷行人提出著名的倒置理论,其内涵之一是,作为能指的“风景”概念之诞生,往往早于作为所指的“风景”的发现。与此类似,在丰厚的上海叙述的影响下,“旧上海”作为一个怀旧概念先行植入读者脑中,循此阅读有关旧上海的文字,亦是索寻其阅读预期中的“风景”。从这百年前的文字当中浮现出来;相较于《海上花列传》油画般的质感,《海上繁华梦》更接近清明上河图,在一种需要耐心的芜杂里,传递着时代的体温。
归根结底,以故事为内核和以感觉为依据,切割了晚清叙述与新感觉派笔下上海街景叙述的差异,在相似的碎片化文本下,新感觉派的街景描写传递的是早期都市人在秩序成熟的都市空间里的挣扎与无力,种种欲望的搏动、灵魂的残片借助蒙太奇影像辅佐的文字技巧,铺陈着糜烂而苦闷、分裂而沉溺的颓荡的灵魂上海;而在晚清街头故事的拼贴与罗列中,在旧道德框定的新故事里,充盈的是吃喝赌嫖穿玩享乐的琐碎而庸常的物质上海。虽匮乏深刻的见解与精彩的描写,然而这一个物质上海,却正是新感觉派所书写的灵魂上海的铺垫;现代主体人的觉醒,乃是凭借着对物质上海和伦理倒置上海之熟稔才成为可能。也因此在被视为是时间概念的“现代性”的逻辑中,新感觉派的海派书写至少在街景叙述的延长线上,与晚清上海书写之间是一脉相承的。作为人与物的中介,街道既是“交换、商品买卖的主要场所”,也是“日常生活戏剧的展示窗口”,而“价值的变迁也产生于这里”(16)奈杰尔·科茨.街道的形象[M]. 朱国勤,译.罗岗,顾铮.视觉文化读本.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第191-192页。。马路和街景描写展示上海、讲述上海,也建构上海:凭借共享的街道与街景,新旧上海之间具有了共同的可被指认的殖民都会气息;而借助对熟悉的街道和街头故事的陌生化体认,晚清与民国读者在空间与空间规则的亲切共鸣中分享和想象着同一个上海。与此同时,在关于街景尤其是新感觉派的街景研究中始终被忽略的一点是,建构了上海地理空间的街道,不仅有文化空间的标识意义,亦存有“上海叙述”的叙事学意义。
三、叙述上海与“上海叙述”:晚清街景描写的叙事学意义
《续海上繁华梦》三集39-40回,作恶多端的萧怀策被忍无可忍的叙事者借黄衫客之手击毙于浦东乡下,叙述者耐心地铺陈了这场猎杀的全过程,诡计多端的萧怀策与为民除害的猎杀者在泥泞狭窄的黄浦江滩边围追堵截,猎杀者弹无虚发,一条突兀出现的小河和漩涡奔腾的黄浦江水掩盖了一切行迹。并非巧合的是,《海上繁华梦》三集39回,美丽而邪恶、几乎将杜少牧玩弄至家破人亡的妓女颜如玉,也同样遭遇了叙述者残酷的文字惩罚,从四马路最繁荣的长三堂子被放逐,到流落至宝和里做野鸡、及至最后受骗发疯,颜如玉一路向南回到上海县城,在九曲桥上赤身裸体地被游街——就情节逻辑而言,萧怀策和颜如玉由盛转衰的故事命运更多地来自叙述者的安排,在作者和读者共享的道德默契下,叙述者必须强行介入替读者出这口恶气;就街道叙事逻辑而言,与颜如玉从四马路被放逐至上海县城的空间轨迹相反,萧怀策由做掮客起家,钻头觅缝地从上海滩保险业、房地产、中西法堂会审等早期现代法律法规中寻找漏洞、欺骗打劫败家子戚祖怡的家产发迹,遂从县城内不知名的住处一路搬迁至英租界后马路、石库门;而承继了三十余万家产、坐拥城内老宅与租界洋房,在四马路拥有24幢市房、英租界内外数十亩地皮和地基的戚祖怡,却因丧尽天良的狂赌滥嫖及萧怀策的“帮闲”,沦落到一文不名、无家可归,最终死于华洋交界郑家木桥散发恶臭的木板铺上,被店主弃尸于暴雨中。人物居所所在马路由边缘到中心再到边缘的迁徙,与人物命运的浮沉紧密勾连;而无论是游街还是猎杀,都无法在灯火通明车轮飞驰的租界马路上实现,恶有恶报的古老规则怯于现代都会的法条禁令,惟有回归到泥土铺就的村庄,多行不义必自毙的道德逻辑才有可能兑现。
考诸《海上繁华梦》正续两部,其街景叙事开启于英租界四马路,终结于黄浦江滩一条泥泞的小径;全著囊括了英美公共租界、法租界、上海县城、浦东郊区等清末民初上海辖区的所有主要路面;其间有数回故事在镇江、哈尔滨等地展开,然并未涉及街道名称或仅提及而已。于是乎,马路与街景叙事与某种独特的空间逻辑勾连起来,在该逻辑的支配下,“故事发生在上海”演变为这是一个“上海故事”。通过都市动态风景线的建构,上海叙述中的马路与街景书写,与《点石斋画报》、《洋场竹枝词》等文字与图画媒介一起,共同打造着晚清上海洋场的空间名片;而从叙事的功能性视角切入进去则会看到,作为文字上海的重要构成,涵括了“风景”和“场景”之意的街景书写,既可展示租界景观、介绍洋场秩序、勾摹沪上风情,亦是塑造人物、扭转情节走向的重要叙事手段。更多时候,这两者是纽合到一起的,人物命运和情节走向很多时候与其身处上海滩紧密相关,例如曲婉儿被卖获救一节(续书二集5-6回),其事缘起于婉儿之父曲玣之误入上海滩“赌途”深处,家财耗尽后被骗以婉儿抵押赌债,婉儿意欲吞金,曲玣之一筹莫展,忽遇极有血性的凤鸣歧和游冶之偶然来访、听闻哭声入门询问,遂漫涨起平不平之心、倾囊相助。该故事模式中不难看到黄衫客的影子,然此黄衫客并非打马唐长安街头、因情节需要而强行介入故事的浪子,而是因为在弄堂狭窄、人口密度极高的上海租界,这样的大哭随时会引来邻人、路人乃至巡捕上门闻讯;后文遭受恶鸨虐待的花娜娜,也正是在吞烟去仁济医院的路上,在车上乱纵乱颠、槌胸顿足地大哭,霎时行人围做一团、引来心细如发的巡捕而获救(续书二集27回)。在洋场独特空间秩序的支配下,发生于晚清上海街头的故事,逐渐成为具独特沪上气质的“上海故事”;这“气质”不仅体现为街道对细部故事情节的参与,亦体现为对整部小说讲述模式的规定。
有关晚清长篇小说叙事弊病的讨论中,材料的堆砌与罗列、故事场景与主题的重复(以官场、欢场和洋场为最),以及角色肤浅、结构松散等等,被指认为该时期小说艺术水准低劣的主要表征。事实上,该叙述症候不仅与小说商品化、制式化创作方式和期刊连载的媒介传递方式相关,亦与晚清旅行叙述的“怪现状”写作模式相关:在由南至北、自西徂东、从乡村到城市的旅行者笔下,沪上书写不过是其怪现状罗列中最突出的一站而已;而街道空间与街景叙事的参与,则使沪上文本总体呈碎片化、非线性的叙述特点。以变动不居为最突出空间特征的晚清上海,其渗透了生活方方面面的巨变如此之多,也着实使得聚焦于上海的叙述难以轻易捕捉到稳定的故事核;“潮”类、“镜”类、“现形记”类和“黑幕大观”类作品之多,某种程度上亦是捕捉千变万化之上海景观与镜像的权益之计。《海上尘天影》中,顾兰生一行在扬州秀水街流馨里的数回颇具红楼意蕴,然当故事转入上海租界,叙述者唯有生造一个海上大观园一般的“绮香园”来框缚住所有人物,才能让故事维系在主要人物视点之间;《人海潮》前十回以苏州福熙镇澄泾村和安乐村为故事背景,主要人物的爱情友情乡情在极具古典意境的四季里缓慢铺陈,一俟主人公踏足上海,故事便不由自主地循着一场又一场酒局散乱地跳跃,福熙镇乡下浓墨重彩的感情线索隐没了,反复出现的街道及其建筑和始终与租界空间格格不入、在马路上漫游白相的主人公提醒着读者,这是关于上海进城者的故事;类似的还有以讲述扬州故事为主的《广陵潮》,每当笔触转到上海、武昌等地,叙述节奏便匆忙起来,人物的上下场频率格外增加,相较于扬州城内网状铺开,以云伍田柳四家为主人公,以私塾、明伦堂、校场等固定场所为背景的回目,扬州城外的故事叙述要单薄得多;包括以双线珠花、立体网状的现代性结构著称的《孽海花》,在傅彩云逃离金家来到上海重张艳帜后,诸多内容都以宴席谈话的方式展开,情节也开始游离,遂将读者带入熟悉的材料罗列的芜杂感受之中……凡此种种,既可能是叙述者笔力不逮、亦可被理解为面对崭新而“日日新”的上海,每天处在感官震撼和伦理震惊中的讲述者们,着实未能发展出一种适宜于这变动不居之都市空间的讲述方式。毕竟不是每个写作者都能如韩邦庆般,起坐于长三堂子当中、津津有味于打磨作品而不思谋官进取,其于海上花事中展示上海滩的伦理变迁之深,很大程度上是其狭邪叙述的意外收获。览韩邦庆生平创作可知,致力于描摹大时代之大上海的变迁并非其叙述旨归,对于若干欢场女子的情爱与归宿的关心,压过了对外界空间及其伦理变迁的好奇;如孙家振般数十年保持旺盛的创作精力、津津有味于上海滩风云的“实录”意识,非古典文人韩邦庆所欲为。野心既“小”(17)韩邦庆对自家作品自视甚高,《海上花列传》连载于《海上奇书》时,每期二回,均附《例言》自析文章结构、提示阅读,故这里所谓“小”,指的是《例言》10篇所论皆为故事人物细节,并无一字关乎彼时翻天覆地之时代更迭;考诸《海上奇书》所载《太仙漫稿》《卧游记》等,均指向故事的精研细摩,其于晚清说部艺术成就一面,可谓登峰造极,然其志终不在载道之“大”也。、道德姿态向后、文学姿态却是开放的,佐以极高的文学天赋,成就了《海上花列传》的文学史传奇。相较之下,热衷于征逐上海滩奇闻异事的孙家振,可是陷入了和“怪现状”“潮”类写作者们共同的抒写难题:即,如何用相对稳定的叙事模式,讲述变动不居时代里、一个正在形成中的城市。
稳定的居住空间和空间观构成相对稳定的讲述模式,然而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以家庭伦理、道德天命为核心的叙述模式开始和失序的居住空间及其伦理一齐松动;上海租界非本土的文化异质性、前所未有的人口杂糅、以“界”为单位的空间秩序的改变,及其随风云诡谲的时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敏感政治身份等等,都使得讲述上海成为一个晚清时空里的文学难题。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无论是以传奇方式讲述只有一种阐释方向的历史叙事、还是以团圆模式讲述婚恋的家庭叙事,其所依循的都是以“天命”为主导的结构形态,无论是“三言二拍”还是红楼、聊斋,情节发展的内在动因始终是与天人伦理紧密相依的命运之力;然而这种天命逻辑在晚清上海逐渐失去道德土壤和情感氛围,稳定运行的自然与伦理秩序既随晚清变局一并被打破,则受惊的人群的命运也就被迫捏在了自我选择当中。这样的局面下,与晚清旅行者叙事罗列怪现状的写法类似,孙家振以采撷街景为基础叙述单元的情节模式,便可能是《海上花列传》之外,另一种适宜于晚清和晚清上海的讲述模式。事实上这两种模式也并非不通闻问。以精雕细琢的布局谋篇独步晚清的《海上花列传》,其叙事结构是立体网状的,该作重要场面虽多发生于长三堂子室内,但场景之间的转换却大抵借助于掮客洪善卿等在里弄内的步行穿梭来实现;这样的步行中又常有偶遇,四面八方的嫖客们也总在同一个长三头牌里撞上,借助这偶遇,故事便由A到B极为自然地迁衍过去,开篇两回讲述赵朴斋进城寻亲,欲在上海谋生路,洪善卿引外甥去堂子里见见世面,顺便请客谈点生意,于是第3、4回借着酒局、故事转向席间客人王莲生、罗子富等,及其与各自相好倌人之间的纠葛;期间沈小红与张惠贞为王莲生大打出手,洪善卿受王莲生之托从中周旋,途中再遇留恋烟花的外甥赵朴斋,故事于是再由C到A迁衍回去……细密交错来回嵌织的讲叙模式,使得数目众多的主人公在相对稳定的故事空间内轮番登场,人物淡出后又会在下一场酒局中再次浮出——这样的彼此为背景幕布、相互影照的讲述里,浑然浮动一种里弄式的家长里短,伴随若隐若现的动态与喧哗。同样在街道贯穿叙事的层面,《海上繁华梦》、《歇浦潮》、《人海潮》等晚清民初上海叙述的长篇故事集,其结构模式均与《海上花列传》极为相似:若干从头贯穿至尾的主人公穿梭于不同的酒局(或茶局、戏局、赌局等),引入似而不同的故事线索;街道将具不同功能的建筑空间整合起来,以外省人“入沪观光”为由头依次领略;讲述者再以“揭发伏藏、显其弊恶”的叙述主旨将这些跨度极大的故事汇聚在同一个上海文本中,叙述遂具有了空间层面的合理性。于《海上繁华梦》而言,其对街景叙事片段的热衷,使得故事因即时而鲜活,因偶然而具不可复制性,又在不可复制背后,始终交织着外省/沪上、农民/市民、乡绅/商人、情感伦理/货币伦理等等晚清最重要最持久的社会冲突。基于此重新审视《海上繁华梦》,其正书一百回连绵不绝展开的“嫖经”背后,乃是对中西和城乡道德伦理与日常生活秩序冲突的反复演绎,其续书一百回“黑幕”所揭示的,乃是现代性图景渐失震惊效应之后,对晚清上海滩正在形成的货币与金融伦理的故事化图解。郑逸梅称道《海上繁华梦》“记录民初时代种种社会学家,多为其人其事,对研究此时历史背景甚有价值”(18)民初小说家孙玉声[M]. 郑逸梅.艺海一勺.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4,第64页。,正在于此;其所缺憾者,是过于依赖对新鲜材料的堆砌罗列,冲淡了原本可能抵达的更为精简的叙述结构。
比照孙家振与韩邦庆海上叙述得失可知晓,与力图追赶外部世界秩序的变迁相比,韩邦庆投向居沪者内心波动与内在行事逻辑的写法,既能塑造人物,亦能有效地折射外部伦理变迁,这种由“诉诸内”到“索诸外”的写法,可能是在晚清至民国半个多世纪里沪上书写所积淀下的最有效的上海讲述模式。与此同时,致力于街头景观书写亦不能说未出精品,事实上正是精彩的街景叙述构成了诸多并不精彩的晚清小说中仅有的精彩片段,与大多数立意恢弘却漏洞百出的晚清长篇相比,一些类似于街头速写的小品、短篇更能捕捉都市变幻中的精彩一瞬。该点在新感觉派小说中得到验证。虽时局动荡依旧,然而现代性的完成度渐高,而“都会人的魔欲是跟街灯的灯光一块儿开花的”(刘呐鸥《方程式》),从映出蓝的牙齿红色高跟鞋的跳跃的霓虹灯影(《大晚夜报》),到被saxophone笼罩着的充斥着酒味烟味香水味华尔兹味的夜总会(《上海的狐步舞》),半个世纪前的书写者们所无法把握的海上幻梦的都市体验正在一点点汇聚成型,其与稍晚的张爱玲、苏青等人的作品,共同构成沪上体验的两重风景:其一是外部空间趋向的,聚焦于都市街头风貌,热衷于全景扫描,以对居住者心灵的整体压迫为体验主体,是不安的颓荡的上海;其二是内部空间趋向的,以居沪者的日常生活体验、家常琐事为讲述对象,是烟火味的市民的上海。在景观的视野里:内与外、大与小,正如张爱玲作品里琐屑的生机和华丽的绝望,缺一不可。
最妙的自然是两者的结合。譬如《封锁》。开在大太阳底下的蠕蠕的电车,被“叮铃铃铃——”的封锁线止住了,头等车厢里偶然邂逅的男女主角在菠菜包子温热的麻油味中缘起又缘灭,变动不拘的空间里瞬时的“永恒”、短暂暧昧所揭示的不可灭的欲望,大时代里小人物的庸常与算计……在“当当”跑着的电车里、在包子的热气和长达几个小时的封锁线内蒸腾上升。这样的出入内外、了无痕迹的写法,在晚清民初的沪上书写中不能说没有,虽然终究是少数。《人海潮》第十五回,接受老鸨调教、好日后成为“名花”的乡下丫头银珠首次坐汽车出游,一仰头与在斜对过银翠仙家的洋台上削梨皮的姆妈对上眼,姆妈以为自己眼花:小囡一个穷身体,怎会装进汽车里去,若有这福气怎会让自己削梨皮、更不会被汽车夫为掉在车顶的一串梨皮骂个难听;银珠却是一股心酸到鼻尖:“汽车风驰电掣而去,银珠一缕芳魂好似依旧在银翠仙洋台下”,姆妈亦是“站在洋台上出神,也好似汽车虽去,像女儿一般的脸子,始终在楼下,仰首对着自己”——进城卖淫的女儿为孝心和羞耻心所拉扯着的千般羞辱、万般委屈皆浓缩在四马路长三堂子门口这个四目相对的悲怆瞬间;第五十回,为“爱”丢财丧命的钱玉吾,其棺材在冻马踯躅、寒鸦嘹唳的腊月底由老母悲痛欲绝地拉回乡下去,一同入沪的好友们前来相送,漫天飞雪中,抛夫弃子的钱玉吾“所爱”,正香软地依偎在南京路卡登饭店门口一青年小开怀中,管它是荒烟蔓草、凄风苦雪,都无法阻挡这软红尘、销金窟里的纸醉金迷。民初上海这暴雪纷飞的大马路上、进城男女的异化与被异化的悲怆奇景,无疑是值得载入文学史的(19)网蛛生.人海潮[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第257-258、797-801页。。此时距《海上花列传》刊行已三十余年,于是这样的街景书写,就不再是单纯地将街头作为故事发生的场景,街景中的人物开始有了被独立分析的意义。从注重景观到注重人物,清末民初过渡时期的上海叙述,正在酝酿一场深层次的文学变革。
从晚清上海书写到新感觉派,在对道德沉沦持之以恒的谴责当中,晚清人对现代物质文明的好奇,演变为新感觉派叙说中对物质世界的依恋,情绪从亢奋和谴责向挣扎与苦闷递进,而作品中的街道与马路,也逐渐从物化的消费空间和流动的情欲空间,向碎片化的感官空间和资本主义的批判空间延伸。借助街景这流变的现象世界,清末民初上海现代性的早期经验得以赋形,得以为上海这短暂和永恒的辩证法之都留下最初的艺术写照。(20)波德莱尔曾为现代性定义:“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换言之,艺术是短暂和永恒的辩证法。见:夏尔·波德莱尔.现代生活的画家[M]. 郭宏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