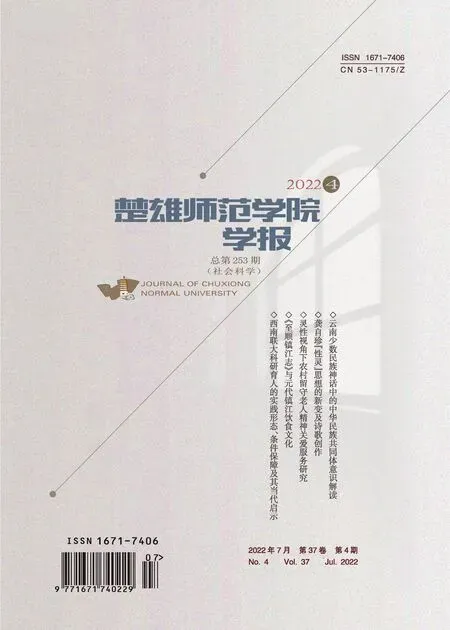云南少数民族神话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解读
2022-03-17姚霁珊季红丽
姚霁珊,季红丽,苏 宏
(1.楚雄师范学院 语言文化学院,云南 楚雄 675000;2.玉溪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云南 玉溪 653100;3.昆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信息化教学部,云南 昆明 650000)
神话是人类的一种文化记忆,是“具有象征价值并且被铭记而转换成记忆的一种理念、一个事件、一个人物或一种叙事。”①阿莱达.阿斯曼:《历史与记忆之间的转换》,教佳怡译,《学术交流》2017年第1期。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民族都有自己的神话,即使是无文字民族,也会通过口头传统流传下来。他们通过这些神话证明祖先的由来、自身文化的根谱、信仰的真实、族群的身份,神话由此成为“文化神圣的证书、保状”②参见马林诺夫斯基:《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李安宅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72页。。
云南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区,25个少数民族中,北方迁徙来的蒙古族、回族、满族由于宋末及清代才入滇,他们的民族神话流传不多,其他大多数民族均有自己民族的神话。云南少数民族神话内容丰富、风格奇异,无论从神话母题、内核乃至叙事表达范式都独具民族和地域特征,其中所包孕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多元一体民族观最充分集中的呈现,也是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虽民族众多,但民族关系团结和谐的重要原因。
一、云南少数民族神话的类型及共同特征
云南的地理环境和民族迁徙历史造就了云南成为多种文化的交汇地,大山大水的立体阻隔所形成的多元文化使云南少数民族神话不仅生态多样而且活态丰富。由于神话时期,各族先民虽生活环境不同,但面临的自然灾害等生存困难是相似的,他们渴望征服自然,渴望拥有改造自然、创造美好生活的神奇力量的神话心理是基本一致的。因此,云南少数民族神话类型与中国神话类型基本类似。从神话的母题与情节内容来看,云南少数民族神话可分为创世神话、始祖神话、洪水神话、英雄神话、发明创造神话、自然风物与动植物神话等类型,它们共同构成庞大的中华神话谱系。
云南少数民族神话类型中,创世神话、始祖神话、洪水神话最具民族特色。云南少数民族的创世神话主要讲述天地万物的形成和起源。彝族的创世史诗《梅葛》中的《开天辟地》叙述了远古时期,格滋天神创造天地的故事。云南的彝族、白族、哈尼族、傈僳族、景颇族、普米族、佤族等少数民族都有不同形式的创世神话,虽讲述的角度、方式不同,但均表达了云南少数民族对天地宇宙的原始思考和认识,体现出最朴素的原始宇宙观。
云南少数民族的始祖神话,也称族源神话,是云南少数民族祖先崇拜的一种想象和叙事,是对人类起源的思考和探索。情节大都是葫芦生人、动植物变人等,其中葫芦生人是云南最普遍的始祖神话故事。云南少数民族始祖神话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多民族同源共祖。这类神话既是云南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活现状的反映,也是多民族和谐共生的重要研究资料,更是云南少数民族寻求共同发展的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具体呈现。
云南少数民族洪水神话是云南少数民族最具特色的神话,既有世界的普遍性,又以云南各民族浓郁的民族特征而独具典型性。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关于洪水的各种神话传说文本及田野调查中的口传材料中,有17 个民族流传着完整、独特的洪水神话故事。这些洪水神话从内容上主要分为五种类型:洪水兄妹婚配型、洪水天女婚配型、洪水后葫芦生人型、兄妹开荒型以及前四种的复合型,其中,兄妹婚配型在云南少数民族洪水神话中最为典型,主要在苗族、彝族、壮族、瑶族、白族、哈尼族、傈僳族、景颇族、怒族、独龙族等少数民族中流传,情节大多为洪灾过后,幸存的兄妹占卜成婚,繁衍出众多民族。这类神话最有代表性的是流传于云南楚雄彝族中的彝族创世史诗《查姆》和《梅葛》。云南少数民族洪水神话除了洪水兄妹婚配型、洪水天女婚配型、洪水后葫芦生人型、兄妹开荒型这四种类型,还有不少洪水神话是以上四种类型黏合而成的复合型:兄妹婚配+葫芦生人型、天女婚+葫芦生人型、兄妹开荒型+兄妹婚、兄弟开荒型+天女婚。这些神话在不同民族、不同地区,故事的讲述方式、故事情节会有许多不同,但云南少数民族的洪水神话包含着许多共同的母题:洪水泛滥、兄妹婚配、人类再生、葫芦生人、民族起源、同源共祖等。这些母题是神话叙事中让人感知的最自然的基本元素,它们构成了云南少数民族洪水神话丰富的文化内涵以及云南各民族对中华民族认同的“共性”。
二、云南少数民族神话蕴含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云南少数民族神话作为中华神话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它承载并传播着中华文化,另一方面又以鲜明的自身民族特征强化民族的认同感。
(一)中华民族的认同
中华民族的民族认同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共同的民族渊源,二是共同的民族文化,三是共同的国家——中国,这三个层面共同构成对中华民族的认同。①参见郑晓云:《中华民族认同与中华民族21世纪的强盛—兼论祖国统一》,《云南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云南少数民族神话,特别是讲到民族和人类起源的族源类神话,渗透着强烈的中华民族认同感。
1.中华民族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云南境内的少数民族,由于自然环境的影响,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的居住格局。共同生活的地域不仅使他们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有众多的交流和交融,而且从民族的渊源来看,云南虽少数民族众多,但主要来源于三大系民族:西北南下的氐羌系民族和东南向西及北上的百濮系民族、百越系民族。他们与中原文化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反映在神话中,成为中华民族身份和民族认同的根谱。云南少数民族神话中分量较重的关于人类起源和族源的神话,都有一个共同的表述核心:各民族“同源共祖”,共同的民族认同,共享祖先,同出一源,兄弟血亲。流传于云南楚雄姚安的彝族创世史诗《梅葛》中讲道:由于天神不满人间人种的恶习,通过洪水毁灭世界换人种。善良的兄妹在洪水中幸存,后承天意,兄妹婚配传人种,生下一个怪葫芦。天神用金锥银锥开葫芦,“戳开第一道,出来是汉族,汉族是老大,住在坝子里,盘田种庄稼,读书学写字,聪明本事大。戳开第二道,出来是傣族,傣族办法好,种出白棉花。戳开第三道,出来是彝族,彝家住山里,开地种庄稼。戳开第四道,出来是傈僳,傈僳力气大,出力背盐巴。戳开第五道,出来是苗家,苗家人强壮,住在高山上。戳开第六道,出来是藏族,藏族很勇敢,背弓打野兽。戳开第七道,出来是白族,白族人很巧,羊毛擀毡子,纺线弹棉花。戳开第八道,出来是回族,回族忌猪肉,养牛吃牛肉。戳开第九道,出来是傣族,傣族盖寺庙,念经信佛教。出来九种族,人烟兴旺了。”①楚雄州文联编:《彝族史诗选·梅葛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4-46页。云南楚雄双柏彝族的创世史诗《查姆》中的《民族的来源》也讲到洪水后,阿普笃慕与四个天女配夫妻,婚后生下36 个兄妹配对成婚。“组成十八家,一家去一方,一家住一地,一家成一种。”“一种是一族”“各家为一族,十八分天下,十八常来往,他们是一家。”②施文贵等翻译整理:《查姆译注》,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15年,第222-223页。洱源白族的《开天辟地》里也提到洪水后兄妹经香烟汇合、滚磨盘等考验成婚,十月怀胎后生下一个狗皮口袋,口袋内有十个儿子,十个儿子各生了十个孙儿子,成了百家。从此,百家各立一姓,这就是百家姓的由来。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流传的《苦聪创世歌》中,哥哥单梭和妹妹单罗兄妹婚后,妹妹浑身上下都生娃娃,其中有苦聪人、瑶族、哈尼族、傣族、汉人。红河元阳的哈尼族神话:世界上最早的女人叫塔婆然,她感风怀孕,生出老虎、泥鳅、野猪、蛇等动物和77 个小娃娃。她给这些娃娃分别取名为哈尼族、彝族、傣族、白族、汉族等。同样的母题类型和情节,纳西族、独龙族、德昂族、布朗族、佤族、阿昌族、景颇族等民族神话中都有。另外,云南少数民族人类再生神话中还有洪水遗民婚配后生出(种出)葫芦,葫芦中走出各族人民。阿昌族神话《遮帕麻与遮米麻》中,天公遮帕麻和地母遮米麻生出一颗葫芦籽,种下后葫芦生出9 个娃娃,分别是汉、傣、白、纳西、哈尼、彝、景颇等9 个民族,9 个民族原本是一家。还有的民族神话是生出肉团,砍碎后各扔一方,每一肉块变成一个民族,四方民族都是血肉兄弟。从这些神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云南的地理环境使得各民族或居山顶、或居平坝,但他们都认为各民族的产生有同源共祖关系,或者有血亲关系,或者有地缘关系,都在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可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云南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基因中根深蒂固、活态存在。
2.葫芦文化谱系—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根藤
“神话是文化传统的核心支柱,认同一种神话也就认同了一种文化,栖居在一种神话所营造的文化母体之中,也就意味着成为这个民族文化的一员。”③田兆元:《神话学与美学论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241页。云南少数民族神话作为中华神话的一员,它在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符号的建构与传承中起着积极的作用。葫芦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是一个重要的符号,在云南少数民族神话中更是一个神圣的象征。云南大多数民族神话中都离不开葫芦,在整个传人种的过程中更是离不开葫芦。它不仅是洪水泛滥中的避水工具,还是诞下人类的母体。它是天意神授,功用神奇,受云南少数民族崇拜,成为一种图腾信仰。翻开葫芦的历史,它最早是在7000年前的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发现,据先秦文献记载,它作为盛器、食物一直出现在人们最日常的生活中;也作为文化的圣物出现在中华民族各种典籍和神话中。《诗经·大雅》中“緜緜瓜瓞,民之初生。”是中原葫芦生人的最早的记载,汉族中也有众多伏羲、女娲是葫芦化身的神话传说。云南少数民族葫芦生人的神话更是比比皆是。布朗族族源神话说,从前有个大葫芦,里面走出来布朗族和傣族。德昂族神话《人类的起源》讲述天公地母种葫芦,大葫芦被雷劈开后,出来了汉族、傣族、回族、傈僳族、景颇族、阿昌族、白族等民族的祖先以及各种动植物。拉祜族《蜂桶、葫芦传人种》的故事讲述洪水过后,幸存的老三兄弟与仙女婚配后,生下一个葫芦,砍开里面是许多小娃娃,小娃娃快速长大,成了汉族、傣族、彝族等。这样的神话传说在中国各民族中均有呈现,葫芦经过神话的神圣叙事,成了人类的始祖,由此延伸出了民族祖灵崇拜、生殖崇拜等葫芦信仰,形成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葫芦文化和葫芦文化圈。据田野调查,云南楚雄永仁县猛虎乡还有彝族在供奉葫芦祖灵。汉族典籍《晋书·礼志上》说“器用陶匏,事返其始,故配以远祖。”就是用葫芦来祭祀象征远祖。彝族民间甚至认为用葫芦做成的葫芦笙的声音就是汉、彝、傣、苗、哈尼祖先的声音。同样,汉族中也有女娲发明葫芦笙的传说。文化和神话的传播融汇能力远远超出了民族的融汇能力,虽然民族不同,但葫芦崇拜及葫芦文化的传承在我国各民族中广泛存在,形成中华葫芦文化圈,它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冀。它被尊为“宝葫芦”,无所不能;它以籽多福多、多子多福、平安和谐的寓意成为中华民族吉祥文化的象征,构成一个强大的中华葫芦文化谱系,而文化谱系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认同。有学者说“葫芦文化是中华民族凝聚的文化基因”①徐杰舜:《葫芦文化:中华民族凝聚的文化基因》,《葫芦·艺术及其他会议集》,2007年,第28-46页。。确实,共同的文化和民族文化的认同是中华民族凝聚的重要基础。葫芦文化已经深深植根于中华各族人民心中,它就像葫芦的根藤紧紧把中华各族儿女缠裹在一起,成为不可分割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二)交融共生的和谐民族关系
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区,云南的发展就是一部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云南少数民族神话中存有大量的多民族同源神话,它们呈现着云南多民族之间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和谐共生关系。据王宪昭先生在《中国多民族同源神话研究》中的统计,这类多民族同源神话,北方少数民族地区收集到9 个,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收集到10 个,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收集到178个(其中云南121个),东南少数民族地区收集到35 个。从以上数据看,少数民族多民族同源及母题神话在南方少数民族中流传更广,特别是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而西南少数民族中云南尤为突出,不仅收集到的神话众多,而且内容丰富,叙事方式和风格也是异彩纷呈,较为独特。究其原因,云南民族的迁徙历史造成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多民族共同居住的格局,给不同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创造了条件。一般情况下,每个民族为了维系自身的生存,民族成员会聚居在一起,坚守自己的民族传统,同其他民族保持一定的距离(地理空间距离和心理距离)。由于云南地区不断的民族大迁移,迁徙民族被分散为若干群体,不同文化、相距较远的不同民族生活在相邻的地域,不同民族的空间嵌入和心理情感的嵌入,导致民族间的空间和心理距离缩短,关系由此亲近,成为密不可分的共同体。这种现实常态很自然地反映在云南少数民族神话的叙事之中。怒族神话《射太阳月亮》讲述了洪灾过后,兄妹占卜成婚,生下怒族、独龙族、汉族、藏族、白族、傈僳族、纳西族。这个神话生动地再现了怒族在历史发展中与其他民族的亲密关系。在彝族《查姆》和傈僳族神话《洪水泛滥》中都讲述了云南汉族、彝族、傣族、藏族、景颇族、傈僳族等民族的同源兄弟关系,这是云南少数民族特有的同源共祖意识,它们共同反映了民族间的频繁往来和友好情感。阿昌族故事《九种蛮夷本是一家人》中,遮帕麻和遮米麻婚后九年生下葫芦籽,葫芦籽种下九年后,结了个大葫芦,葫芦成熟破开,跑出许多孩子。遮帕麻和遮米麻给他们定姓取名,并把他们分发到各个地方。“虽然生活在坝子的成了傣、汉;高山顶上的成了景颇、傈僳;半山半坝的成了阿昌、德昂等不同民族的所谓九种蛮夷,但他们都团结友爱,亲密相处。因为他们知道‘九种蛮夷’原本是一家。”①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云南卷.上)》,北京:中国ISBN 中心,2003,第183-184页。另外,在收集到的云南少数民族121 篇族源神话中,我们还发现了一个不容忽视的共性,即无论任何一个少数民族的族源神话,神话中讲述到同源共祖的民族中一定有汉族。这一方面是云南汉族与各少数民族休戚与共、辅车相依的现实关系的客观反映,其实也是“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互相离不开”的“三个离不开”思想在云南的践行和客观完美的阐释。这些神话故事既是对自身族源的解释、对周边民族的认同,也传达出生活在共同地域内的多民族人民共同生活、亲密相依的和谐关系及对多民族组成的民族共同体的高度认同。这种中华民族是一家的共同体意识在云南这个多民族地域内非常普遍,这也是云南虽民族众多、但却像一个大家庭,各成员之间相亲相爱、团结互助、共同发展的重要原因。
(三)中华民族精神的体现
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是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各民族信仰理念、价值取向、生活态度等多方面的深层积淀,是对民族文化优秀遗产的心理继承。云南少数民族神话中蕴含着丰富的民族精神,是云南少数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人文滋养。其中有许多民族共同的优秀传统,正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它们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文化基础。
“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民族精神的深刻阐释。在数千年的文明历程中,云南少数民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和其他民族共同培育、继承、弘扬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在云南少数民族神话中叙写着农耕文明的勤劳勇敢、团结进取、和谐友爱、征服自然的不屈不挠和自强不息的奋斗、创造、梦想精神。彝族史诗《梅葛》的第二部造物中《盖房子》,就突出地展示了彝族先民伟大的创造精神、奋斗精神、团结协作和梦想精神。“哪个来盖房,帕颇来盖房。盖房没有树,那个撒树种?帕颇撒树种。”②楚雄州文联编:《彝族史诗选·梅葛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7页。没有房子,彝族先民就盖房,没有盖房的木材,彝族先民就种树。大家一起撒树种,山山箐箐都撒到。大家一起撒草种,处处样样都撒了。“帕颇的九个儿子,把
树养大了,帕颇的七个姑娘,把草养大了。天上九兄弟,想盖九间房。什么地方盖房子,树林当中盖了九间房。白樱桃树盖了三间房,人间九种族,傣族来住房。坝区山腰上,罗汉松树盖了三间房,哪个来住房?回族来住房。高山梁子上,青松赤松盖了三间房,哪个来住房?彝族来住房。坝区平坝上,香树盖了三间房,哪个来住房?汉族来住房。”①楚雄州文联编:《彝族史诗选·梅葛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7页。……当房子盖好后,让各个民族和各种动物都住上,而且还豪气地说“不够再来盖”。“盖也盖好了,住的住好了,天王地王都喜欢。”②楚雄州文联编:《彝族史诗选·梅葛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7页。这就是一个民族亲密团结、共同劳动、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的图景。同样,在史诗《梅葛》的《造工具》中,天王生的九个儿子,地王生的七个姑娘(人类先民)尊天神吩咐盘种庄稼,但劳动中需要造农具,没有铜铁,先民们四处去找。找到铜铁花后,由于铜铁花太烫,“挨也挨不得,扫也扫不起”③楚雄州文联编:《彝族史诗选·梅葛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0页。。先民们硬是想出办法捡来铜和铁。没有装铜铁的筐子,人们种竹子,等竹子长大后,破竹编篮子来盛铜铁。大家分工做事,团结协作,告颇称铁,阿巴养马、俄考赶马端驮。为了找到会打铁的人,一路把驮子赶到四川峨眉、云南滇池、永仁中和直苴大村、大姚百草岭、大理宾川,又绕回大姚盐丰、姚安、大姚六苴,最后在牟定城找到打铁的人。整个过程历经千辛万苦,但先民始终勇往直前、毫不气馁,遇到困难,解决困难,最终做成镰刀、锯子、剪刀等工具。另外,在《梅葛》的造物神话中,有一个叙说兄弟民族齐心制盐的故事。相传有个放羊的老人发现盐水,“各族人跑来看,都说真是好盐水。傈僳族来煮盐,没有煮成功,汉族来煮盐,头回煮不成,后来仔细想,二回煮成了。”④楚雄州文联编:《彝族史诗选·梅葛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92页。这些神话展现了云南各族人民共同生活中团结合作的现实情境和不畏困难的大无畏精神。流传于楚雄地区的彝族神话《三女找太阳》,更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完美展示。故事讲述的是古时候哀牢山的三尖山下生活着幸福快乐的彝家人,一只野猫精怨恨太阳,用羽毛当箭射下来六个太阳,天上剩下的最后一个太阳,再也不敢出来了。于是,人们过上了庄稼不熟、牛羊不长的暗无天日的生活。于是,人们商量选出最有本事的人去找太阳,民家、傣家、苗家选去的人都没有回来,汉家选去的小伙子带着重伤回来就死了。三个美丽、聪明、勇敢的彝家姑娘站出来,带领着大家烧死了野猫精,并肩负重任去找太阳。“三个姑娘翻过九十九座高山、越过九十九个深箐,渡过九十九条河流。”⑤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云南卷(上)》,北京:中国ISBN 中心,2003年,第115-116页。她们不停地走,不知走了多少年月,头发都白了仍不停地走。途中,猛虎、巨蟒当道,没有吓退姑娘们;白眉老人的劝告也没能止住勇敢的姑娘的脚步。凭着比岩石还坚硬的志气,她们最终找到了太阳。但在太阳重回天上时,她们却永远的倒下了,变成了三座尖尖的山峰。故事展现了不同民族碰到困难时的担当和团结,特别是三个彝家姑娘身上这种勇于担当、不怕困难、不屈不挠、勇往直前,为了大家的幸福,舍身忘我的精神,这正是云南少数民族神话中最鲜明的特征。这些精神影响、鼓舞着一代代云南少数民族自强不息,奋勇向前。这些故事演绎印证着中华民族为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梦想而进行的不屈不挠的创造和奋斗,是云南各民族生命力和凝聚力的重要动力和文化源泉,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
三、云南少数民族神话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的意义
(一)唤醒、强化集体记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神话存在我们的文化之中,是人们对历史的一种特殊记忆和叙事,它是后人集体记忆的反复呈现而形成的一种文化基因。它依靠共同的族源历史、共同的生活习惯等的记忆述说排除他者形成特定的族群,并以其神性权威宣示族群内部的同一性和统一性。因此,神话是建立和维系族群认同的载体。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神话就是民族的一种集体记忆,这种集体记忆是“一个具有自己特定文化内聚力和同一性的群体对自己过去的包括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的记忆”。①马翀伟,戴琳:《民族文化遗产的国家认同价值》,《云南社会科学》2013第4期。具体来说,集体记忆包括过去的历史、事件、活动、过去的价值意识、思维形式、行为规范等,“承载着群体成员的共同经历和价值框架,能够为群体成员回忆过去、认知当下和未来提供共通的理解和解释框架,潜移默化的影响群体成员的价值观念和行为选择,进而持续汇聚群体的凝聚力”②史宏波,黎梦琴:《在强化中华民族集体记忆中弘扬中国精神》,《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1年第6期。。各民族神话中包含了许多民族的集体记忆,这些记忆汇集成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挖掘、弘扬少数民族文化中这些民族团结发展的共有文化素材,树立并强化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让各民族在民族文化的自信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云南少数民族神话承载着较多云南各少数民族对人类起源、人类文化及自然界万物的集体记忆。如云南少数民族的同源共祖类神话述说的各个民族共同的人类始祖的故事,就是各民族对族群共同的历史、经历的共同印象或回忆,这类神话传达出中华各民族是一家的强烈认同。正是这些集体记忆激发中华民族文化底色中共同的经验和集体感情的互动和共鸣,进而产生强烈的族群意识,民族自豪感、归属感以及族群内部的凝聚力也因之油然而生。由此可见,神话为民族文化的认同提供了素材和内容,神话中的集体记忆为增强中华文化的认同提供了文化和情感心理的切入点,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找到了丰盈的思想和文化源泉。
(二)传承、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中华民族认同和尊崇的心灵寄托、灵魂安顿和精神归宿的安身立命之所。”③赵阳,林园:《中国梦与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光明日报》2014年4月28日,第7版。是中华民族从古至今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精神、价值观念和情感态度的积淀。它是各民族不同特质的文化源源不断地汇注和多元融合,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培育并共享传承的情感和心灵归宿,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离不开各民族及其文化的共同参与,各民族传统文化是民族精神家园得以延续传承、发展创新的基础。云南少数民族神话中就有许多优秀的民族文化精神和传统美德的文化滋养:有缅怀祖先功绩、振奋民族精神、凝聚民族意志的;有不畏艰险和困难、坚忍不拔、自强不息的;有宣扬向善美德、宣示道德准则、社会伦理秩序的……如云南文山西畴壮族神话《布洛陀》,叙述了一位开创天地、创造万物、制定伦理秩序的文化始祖布洛陀,集创世神、始祖神、道德神于一身,在云南文山壮族、苗族等少数民族心中具有崇高的地位,他的故事激励着世代壮族人民不断奋进。云南楚雄州彝族《三女找太阳》、云南红河哈尼族《阿都射日》、云南德宏州德昂族的《祖先创世记》等神话都是讲述云南少数民族为了人们共同的幸福生活,历经艰险,战胜困难的无私无畏精神。另外,云南少数民族神话中,特别是洪水神话中,在讲到洪水泛滥、天神换人种时,大都会有一个母题情节——道德的考验。最终,洪水遗民都是因为善良勤劳勇敢而经受住了考验,成为人类的始祖。这些不同民族的文化和精神,在中华文化的整合、凝聚、认同作用下,汇聚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滋养着中华大地上的中华各族儿女。这些内蕴在神话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正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强大动力和精神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