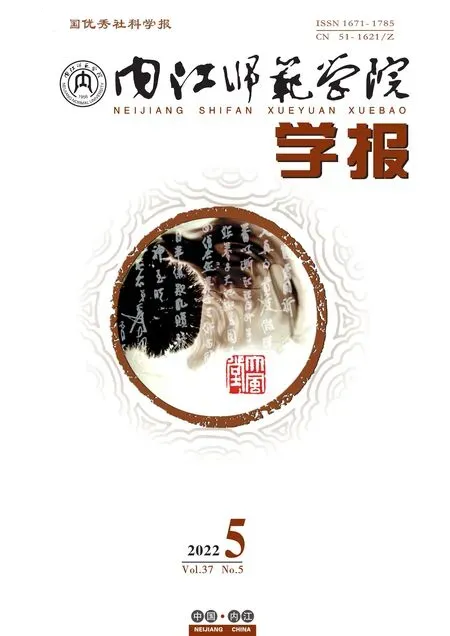论李琦诗歌的边地书写
2022-03-17刘治彤
刘 治 彤
(黑龙江大学 文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00 )
李琦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东北诗人,数十年甘于守在寂寞的白山黑水间,在边远之地进行独立的诗歌创作。她既不属于知识分子写作诗人群体,又不参与到民间写作之中,甚至与当时诗坛上翟永明、伊蕾、唐亚萍等充满反叛意识的女性诗人也有着截然不同的风格。偏远的地理位置与李琦远离纷争的性格相契合,她始终秉承着高洁独立的创作精神,不拘泥于家乡景致,将眼光投向辽阔而苍茫的边地。东北、西北、西南等边地在李琦的诗歌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成为她理想中的精神家园。
一、理想化精神家园的建立
李琦诗歌中涉及的边地包括东北、西北与西南地区,为我们呈现了各具特色的边地风貌。东北辽阔的草原、大江、湿地、森林,西北寂寥而沉默的茫茫戈壁,西南神秘深邃的三峡、九寨沟、岷江、缙云山等等无不在她的诗歌中有所展现。如果说东北是诗人的根基所在,是难以割舍的故土,西北则与诗人的灵魂契合,在这里诗人找到了她的精神原乡,而西南则以神秘的高山,纯美的自然深深吸引着诗人。正如李琦所言:“西北,东北,都是边远之地。都有边地特有的那种开阔苍凉与静寂。……至于大西南,是我的心仪之地。那里的高山峻岭与河流,有一种吸引我的神秘和深邃。那里也是边地。我书写这些‘边塞’之时好像总能获得一种特殊的能量。”[1]无论是东北、西北还是西南,都构成了诗意化的世界,建构了李琦诗中的理想化精神家园。远离俗世喧嚣的宁静边地让诗人的灵魂得以舒展,唤醒了诗人对生活的希望,“让我失望的世界/又在这里,一片苍茫的/让我相信”[2]50。
李琦通过对边地生灵、自然景致、民风民俗的书写建构了诗意化的理想精神家园。具体体现以下三个方面,分别是饱含情感地刻画边地生灵的生存图景、边地自然风光的描绘中流露出真情与哲思、以及对边地民风民俗的细致生动的展示。
李琦将目光投向一切边地生灵,从底层人民到飞禽走兽再到花草树木都在她的诗歌中有所展现。诗人对边地人民的外在样貌进行了生动细腻的刻画,赞美之情溢于言表。在《这寨子里的女人》中,她热情地讴歌了云南边地年轻女子的样貌,“这亚热带寨子里的女子/目光清澈,双乳饱满/阳光下裸露着双腿和手臂/线条动人,像涂满了蜂蜜/甜美,又闪烁光芒”,呈现了边地女子健康而富有生机的生命形态。《西北风》中,诗人对西北女子自然健康的美也有所描绘,“那西北女人每人两朵胭脂/拍红它们的/是太阳和风”,西北女子的外貌受到了自然滋养,与自然和谐地融为一体,呈现出了未经修饰加工的天然之美。《死羽》则是将阿斯哈尔健康的生命之美与都市中的男子进行对照,与都市中出入楼宇间的白皙男士不同,阿斯哈尔“涂釉的皮肤写着成熟与健康”,“我看多了都市白皙的男士/觉得这是十分动人的面孔”,边地人民未曾被都市生活的牢笼围困,他们自然健康、充满力量、散发着生命原始的魅力。
李琦见惯了都市中穿梭的病态男女,因此她格外向往边地人民的自由潇洒。除了他们外在的健康美之外,吸引李琦的还有边地人民内在的精神品质。在《听牧人唱草原》中,诗人对东北草原上的牧人进行了细致的刻画,“面孔酡红的牧人/这是你的家,你却成了最害羞的人/你沉默寡言又暗藏骄傲……”,蒙古包本是牧人的居所,可是他却因远方客人的到来变得拘谨不安,笨拙害羞中包裹着牧人纯真善良的心,不善言辞的背后尽显当地人民的朴拙与真诚。酒拉近了牧人与游人的距离,“酒杯一放歌就生了根/你轻晃着身体像在马背上/歌声浑然而来”,牧人在草原上纵情高歌,再无此前的沉默寡言。“衣衫破旧手掌温暖的牧人啊/你的歌声就是草原的草”,尽管边地人民的物质条件相对不足,他们衣衫破旧却精神富足,尽显骄傲与从容。在另一首《抚远之远》中,诗人将目光投向东北的百姓,展示了人们内心暗藏的骄傲,“那个来接我们的年轻人/熟悉地说起国界上的掌故/头脑清晰,气度沉稳/让我遥想起古代的使臣”,在沉稳从容的非凡气度中饱含了对边地家乡的自豪之情。
李琦在诗歌中还展示了边地人民的勤劳坚韧与平凡伟大,如《这一带的地名》中,诗人就用了个人化的言说方式展示了北大荒的历史,而这一历史则是由默默无闻,躬耕于此的无数边地人民创造的,“中国最寒冷最辽阔的东北角/一群人骨节粗大,面容凝重/犹如让人心动的浮雕”,勤劳坚韧的边地人民将青春镌刻在这片荒凉的土地上,又如诗中记录的那位云南籍的军官“先是褪下军装,而后/次第退下青春和壮年的英武”,他虽是千万开荒者中的平凡一员,却用一生书写着伟大的传奇。正是这些平凡而伟大的人们构筑起边地精神,在边地中书写了独一无二的人生。
李琦笔下的边地人民总是纯净而美好的。诗人在四川某个小站邂逅了乡间卖桃子的姑娘,于是在《小站》中写道,“举一篮桃子你举一篮新鲜/婴儿般的眼睛桃子样干净/”,姑娘仿佛从未经过俗世生活的熏染,清透如一汪泉水,抚慰了诗人久在都市的疲惫心灵。边地女子的爱情观也是简单淳朴的,不掺杂任何功利与算计,《这寨子里的女人》中一位名字叫黑农的姑娘这样说道,“问她会为什么样的男子动心/回答/勇敢、心好、能干活、还要干净”,简简单单的几个字却将人世间最美的品格汇集。
李琦对边地生灵的关注绝不仅限于对边地人民的书写,还包括了其它的生命形式。如在《去扎龙看丹顶鹤》一诗中,她便描绘了生长于东北边陲湿地的丹顶鹤,“气度雍容/翅膀洁白柔软/头顶一点/胭脂红”,边地的动物自由从容地生活着,简单纯粹,仿佛与冗杂的世俗生活隔离,唯有诗意的边地才能容纳下如此自由自在,不加束缚的生命形式。诗人笔下的万物皆有灵性,边地一切生命形式都是平等的,如《为羊而唱》中,诗人将自己放到和动物平等的位置,“这是一个母亲/在劝说另一位母亲”,实现了人与羊的跨物种对话。尽管生命形态有所差别,但此刻诗人与母羊都有了共同的身份,那便是——母亲。“年年岁岁/羊羔变成了母羊/额吉变成了坟茔”,母亲在用生命喂养小羊,展示着母爱的伟大与生命的轮回。从《查干湖里的鹭鸶》到《呼伦贝尔草原》,诗人赋予边地的飞禽走兽以自在从容的生命状态,进一步为我们塑造了诗意化的边地空间。
诗人也着眼于边地的一草一木,并赋予植物以精神品格。在《好大一片荒原》中“从一棵草到一片草原/渺小变成了辽阔/草的一生低调内敛/却如此全力以赴”,诗人将北大荒的草木赋予人的精神,暗含着顽强不屈的坚韧品质。在《干不死》中亦是如此,“你只是活着/活着且平静……这死寂的地带/她与自然对弈又与自然和谐”,“干不死”这一植物的顽强生命恰恰与此前提到的《死羽》中的钻井工人、苦爷等边地人民一致,他们在荒凉的边地绽放着自己的生命,尽管渺小却竭尽全力、不屈不挠。边地的一草一木起到了净化诗人灵魂的作用,诗人在《有背景的人》中写道“红松、云杉、冷杉、/樟子松、水曲柳,黄菠萝/如此珍贵的树种,又如此漂亮的名字/让已是尘埃满面的我们/忽然就自卑起来”,诗人赋予植物以高洁品性,各类植物扎根于边地,或朴实瘦弱如干不死,或高大魁梧如松柏,但却都洗涤着人们布满尘埃的心灵,召唤着人们的灵魂。
除了对边地生灵的着意刻画外,李琦对边地自然风光亦有所展示,并在景色描写中注入真情与哲思。草原、江河、雪山、戈壁、高原等自然美景均作为不可或缺的元素出现在她的诗歌中,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绝美边地风光。诗人身处边地自然中,面对至纯至美的自然从不缺乏直白地真情流露,如《酒醉赫哲族小饭馆》中的“人世上,能有几个这样的夜晚/守着最美的大江和月色/再没有任何着急的事情”,身处自然带给诗人最真实的感动。在《一种风吹进了我的灵魂》中,诗人更是直接抒发道“谁能面对这样的景色心如止水/谁能稳重到永远不动声色……尤其是当你站在深夜的村庄/眼看满天甜杏般的星斗/就要落下屋檐”,大自然总能在不经意间流露出令人震惊的美,诗人对自然中的美不自觉地发出了感慨,在边地自然风光中感受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李琦总是以一颗感恩之心接受自然馈赠,从日常的自然之景中体察不易察觉的美感。在《一种风吹进了我的灵魂》中诗人写道,“我们是有福之人/能看到大雁在头顶飞过/能呼吸尘世最清新的空气”,诗人从自然的原初之美中汲取能量,认为能感受到大自然的变化更迭是一种福分。
同时,诗人还能在自然风景中流露出与众不同的哲思,赋予自然以理趣。在《当我面对故乡的大江》中,诗人穿过江水的表象,深入到了自然的本质层面,江水“像世上所有优秀的事物一样/伟大而简朴,毫无夸张/那无边的荒凉和开阔/让人安静/如一粒灰尘/像灰尘那样看待世界/最卑微的草,我看见了它的高”,诗人从江水中汲取养分,体味到了做人的道理,认为人也应当似江水一般拥有低调的姿态与博大的胸襟。《高原的高》亦是通过高原这一自然景象洞察人生智慧,“无论你怎样向往/那巍峨之处/都要一步步/抬阶而上,而且必须/心神安稳”,诗人通过攀爬高原的经历进行人生哲理思考得出了爬山如同做人,需脚踏实地、安稳前行的结论。而《西北的点悟》则利用茫茫戈壁书写人生感悟,“我自以为辽阔的精神/却原来不过是一方天井/我从始至终的所有道路/不过只是一寸过程”,诗人面对戈壁荒漠的苍凉浩荡,感受到了人类的渺小与自然的博大。李琦从自然中汲取养份,没有进行纯客观化的写景,也未不加节制地过度抒情,而是在对自然景色的描绘中融入富有哲理性的思考,散发出阵阵禅意,带给读者多重审美享受。
在对边地生灵全方位刻画以及在自然中流露出的真情哲思的同时,李琦的诗歌中也不乏对边地民风民俗的细致描绘。蒙古族、赫哲族、纳西族等边地少数民族均在李琦的诗中有所提及。如《告别》中的“一杯上马酒/一条哈达/拥抱或者握别/查干湖,我该走了”,上马酒与哈达均为蒙古族对远方客人表达情谊的方式,诗人正是通过对这一习俗的描写将边地少数民族的热情展现得淋漓尽致。《风起呼伦贝尔》中,“在牧场、毡房、那达慕之后/在手扒肉、烈酒、奶茶之后/这天有多蓝”,也多方面展示了蒙古族的生活居住环境、节日仪式、以及饮食习俗。《酒醉赫哲族小饭馆》中的“本地小烧 粮食酒 不上头/江水炖鱼 炒鲜蘑 炸酱拌豆腐/不说喝,说走一个”,走一个与上头皆为东北方言,诗人通过质朴的语言展现东北人的豪迈与朴实,并用具有当地特色的食物展示了东北赫哲族人的饮食特色与淳朴的生活方式。《古镇日记》中则是将一系列能够代表西南边陲民风民俗的意象叠加在一起,“银器、木雕、神秘的东巴文字/铜壶、雪茶、家织布上的花纹”,短短的一句诗内出现六个高度压缩的意象,每一个意象均具有民族特色,勾勒出了至美至幻的神秘云南。李琦还创作了一系列描绘西北边地的诗歌,均涉及了边地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以及饮食习惯。如《西北的点悟》中大姐端来的酿皮子与红豆稀饭,“你端来的酿皮子真辣/你做的红豆稀饭真香”等,都展示了西北边地淳朴而又热烈的民风民俗以及富有地域特色的食物。
综上,李琦多角度地展现了东北、西北、西南等边地景象,通过对边地生灵的诗意描绘寄托了诗人对边地坚韧、自由、美好生命形式的向往。在对边地的自然景致进行描写时并未陷入无节制的主观抒情,而是在自然中发现美,融入了深刻的哲理思考,同时诗人在展示边地时添加了对民风民俗的刻画。无论是边地生灵、自然景致、还是民风民俗的展示,都为诗人搭建了理想化的精神家园。
二、边地人生的理想化与自然的神圣化
李琦在诗歌中对边地的美好进行了具体呈现,在边地人民身上寄托了自己理想化的人生样式,并将边地的自然美景赋予永恒神圣的美。诗人立足于边地人民的日常生活,“以生活为底色,叙述的平静、节奏的轻快、情绪的稳定都给人以一种平和的享受”[3]。在边地百姓平凡朴素的人生中发现动人之处,对底层百姓美好品格的书写亦是在呼唤人们美好的品格与善良的道德,满含着李琦对真诚纯粹、潇洒肆意的理想人生样式的渴望。
以李琦描写西北边地的长篇叙事诗《死羽》为例,该诗将人物放置于日常生活中进行描摹,运用极具叙事性的笔法讲述了苦爷的爱情故事,没有轰轰烈烈的海誓山盟,而是在平淡的日常中展示了人性的闪光点,让人动容。“苦爷曾娶过一个女人/那是一个三十八岁的寡妇/带着四个娃四张等吃的嘴巴/苦爷那时是精壮的汉子呢/说声住下吧就娶了她”,诗人节制的表现形式与苦爷深沉的情感相得益彰,一句“住下吧”,苦爷与寡妇便构建了一个温馨的家庭,一句“散伙吧”便使苦爷孑然一身。没有纠缠、没有计较,有的只是和这边地一样深沉的胸怀与博大的爱。李琦用闲话家常的平淡语气在日常生活中展示了边地人民淳朴厚道的一生。苦爷不计回报、无怨无悔,用平凡的一生谱写了天地间最高的道德律令。
《死羽》中除了将人物放置于日常生活中进行描摹之外,还将人物放置在碎片化的事件中进行了集中展示。眼神深邃清澈,宛如两眼井的哈萨克人阿斯哈尔、在山丹失去健全双腿的转业军人、嫁到喀什再也没有回来的北京籍阿姨……诗人通过碎片化的情节勾勒出了边地人民的生活侧面,正是这些对人物碎片化的展示连缀成一个整体,共同呈现了这片土地上人们的坚韧与情怀。正如诗人所言,西北就是这样一片土地,“没去时不敢去/去了不想回来/我们西北尽住着/这些死心塌地的人”。无论是酒泉瓜地里闪耀着人性光辉的苦爷、安西小饭馆手中拿葱倚门而笑的姑娘,还是玉门荒凉大漠中的钻井青年、阳关手拿贺饼朴素纯真的汉家女孩儿,都深深地打动着诗人,他们并不优雅,但却坚韧纯粹。李琦正是通过边地人民的一隅为我们展示了世俗中有诗意,温暖中有泪光的边地人生。
李琦注意到了边地中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边地的人与人之间十分坦诚,毫不设防。如《西北风》中的“卖瓜的汉子听说我来自远方/就说去那边买吧/我这瓜不算甜”,这与《杭州街头小记》中因为听到外地口音而悄悄抬价的小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西北,人与人的关系充满信任与和谐,毫无尔虞我诈的欺骗和算计。人与自然也构成了和谐的关系,如《和质朴的人在一起》中,“门前山水,是他们感情笃厚的世交/飞禽走兽,是他们深谙习性的近邻”,边地百姓与大自然彼此相融,在他们的眼中,人与山水草木、飞禽走兽并无本质区别,它们一同和谐地生活在自然中,自由而舒展。诗人深受感染,也在边地找回了酣畅淋漓的生活方式,正如《街津口》所言,“昨夜,他和当地人一起/在寂静的大江裸泳/这是成年后最酣畅的游动”,唯有在远离喧嚣的边地,才能不顾世俗生活的束缚。此刻,人们在这里回归了最原始的状态,与自然进行了最深度的完美融合。
通过在日常生活中展示边地人民的生存状态,诗人寄托了理想化的人生形式。李琦不止一次地在诗歌中抒发了自己对边地生活的向往之情。在《早晨是这样开始的》中,诗人写道,“看着那架出门的马车/和马车上带花头巾的妇人/忽然想变成她/住自己盖的房子,吃新鲜的蔬菜/一年四季/为长远的日子精打细算”,诗人对边地妇女简单质朴生活的羡慕之情溢于言表。在《西北的点悟》中,诗人也有过类似的描述,“忽然想吃最简单的饭/忽然想穿最俭朴的衣/忽然想省略一切形式/生一群娃娃养一群羊/在某一次雪崩中/自然地死去”,展现了诗人对抛却繁杂现实生活的渴望,呈现出对边地日常生活的认同倾向。
如果说城市是诗人安放肉身的地方,那么边地则是诗人盛放灵魂的居所。诗人在现代化的都市生活中无法寻找到精神寄托,因此她将目光投向边地,将边地自然赋予永恒的神圣之美,并强调美的救赎力量。“在物欲横流的时代,她返璞归真,歌唱神性,为同源者寻找转变的道路,显示出诗所应有的品格。”[4]在李琦的笔下,边地雪山高洁神圣,河流净化人心,这种神圣的美具有惊人的力量,能够抚慰人们疲惫的心灵,带给人们难言的感动。“一种美丽的感动如雾/弥漫了我整个灵魂。”[5]133
无论是《雪山》中“你辉煌的曲高和寡/你高洁的让我绝望”, 还是《海拉尔河》中的“我相信我看见了神迹/清凉之水/濯洗我焕然一新”,这些边地自然美景都被赋予了崇高神性,成为美与神圣的所在之地。“西北之行对诗人来说是一次心灵的朝圣。”[6]李琦在西北边地时面对佛像感慨道“一切奇妙得恍如隔世/让我不由担心/这罕见的美与神圣,会不会/被冥冥中某一个主宰,/倏然而收去”[7]135,正是这种无法言说的罕见之美让人们找到一种感动人心的力量,得以从芜杂琐碎的俗世生活中短暂脱离,“使人们逐渐蜕去平庸琐碎走向美与艺术的神性”[8]。诗人渴望将这种瞬间之美延长,成为永恒留在人间,充分表达了诗人对美的向往与永恒追求。
综上,李琦在日常生活中发现美好,在自然山水中汲取力量。无论是对边地人民的理想化塑造,还是在自然中发现美与神圣,边地都寄托了诗人的浪漫精神与理想化色彩,饱含着诗人试图摆脱繁冗都市生活,追求纯粹人生样式,向往神圣自然的美好寄托。
三、乌托邦情调与理性因素的交织
在李琦的诗歌中,理想化的边地呈现了一种“向后看的乌托邦”情调。蒂里希曾在时间向度上将乌托邦分为了“向前看的乌托邦”与“向后看的乌托邦”,“考察乌托邦的本质,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发现就是,每一种乌托邦都在过去之中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基础——既有向前看的乌托邦,同样也有向后看的乌托邦。换言之,被想象为未来理想的事物同时也被投射为过去的‘往昔时光’——或者被当成人们从中而来并企图复归到其中去的事物”[9]171。李琦在塑造理想化的边地时对传统持有一种肯定的态度,呈现了一种向后看的乌托邦情调。因此,其笔下的边地往往具有传统古典美特质,能够在传统意象的叠加渲染之下构造出和谐静穆的画面,呈现出韵致朦胧的古典意境。
《川江老渔夫》以及《今夜在巴东》均选取渔夫、江水等古典意象,勾勒出了诗意化的边地,营造出了辽阔苍茫的意境。《死羽》中则利用了烽燧、飞燕、蜃景、戈壁、羌笛、白骨等一系列东方意象的铺排,勾勒出了茫茫戈壁的苍凉之美。《三峡断章》中的景色描写更是别致,“江底宛如躺满了女人/有柔润如膏脂/匀抹在天地之间/粼光若眉目/顾盼九万里/顾盼三千年”,诗人将江水比作女子,水质柔润细腻似女子凝脂一般的皮肤,波光粼粼的江面如眼波流转、顾盼生姿的美目。江水、膏脂、眉目一同汇聚成静谧的画面与朦胧的意境。“积木一样的房子/是悠悠的家/家在万顷波上/家在一轮月下”,诗人将悠悠的家置于碧波与明月之间,营造出极具古典美的画面,“中国绘画历来主张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讲究意匠经营,追求气韵生动,含而不露”[10],李琦诗歌中呈现的画面清新淡雅,恰如一幅浓淡适宜的水墨丹青画,真正地做到了诗画一体。总之,无论是意象的选取、画面的营造、还是意境的表达,诗人笔下的边地景致都呈现出传统的古典美倾向。古典意象的层层叠加使意象之外的诗意空间涌动在诗歌的笔墨之间,呈现出的画面浮现出天人合一的东方静美。
李琦诗歌中对于传统的认同不仅体在对边地景致的描摹具有古典倾向上,更体现在其对传统乡土民间结构的肯定上。《我过三峡》的前四小节中,每一小节均营造了一个人物意象,无论是打水漂的女子、浣纱的老妪、还是蓑衣独钓的老翁、摇橹的汉子,均是极具传统意蕴的人物形象,每一小节的末句:“那个打水漂的女子是我”“那个浣纱的老妪是我”“那个钓鱼的老翁是我”“那个摇橹的汉子是我”都暗含了李琦对以上诗意化乡土民间生活方式的渴望。《三峡断章》中的“相逢一笑/说天还不错/说风到处乱走/和许多陌生的人/话桑麻”更是展现了李琦对理想化的传统农业社会的向往。
李琦笔下的边地之所以呈现出向后看的乌托邦倾向往往基于诗人对现代化都市的不满。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商业化的不断发展,金钱已成为主宰社会的力量之一侵蚀着人们的精神,城市不断地异化剥夺着人们的生存空间,知识分子的理想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实现,精神世界日益向下滑落。李琦“痛感到都市物欲膨胀、精神孱弱的人类异化,那里只有生活而无生命,理想的真正的‘生活在别处’;进而渴望寻求一种神秘未知的事物,一个魂牵梦绕的精神‘远方’,以达到内在心灵的丰富与生命活力的恢复”[11]102,因此,她在诗歌中构建了与现代化都市相对照的边地空间,蕴含着诗人对现代性的独特反思。
在《给一维吾尔族孩子》中,诗人这样写道,“你说城里没有狼为什么修那么多栅栏/城里的太阳像病了许久/城里人的歌/迈不出录音机的房间”,诗人借边地儿童进行发问,通过孩童的视角将城市与边地相对照,表现了城市间人与人缺乏信任,人与自然失去联系的病态生活场景。《路问》中“你也许做梦都没想到/山外许多与你同龄的少女/正用你爬一架大山的时光/给眼睛涂上一圈蓝晕”,将西南边地女子与城市少女的生活状态进行对照,城市女子被修饰的人工美远不如边地女子的天然之美来得动人。《查干湖里的鹭鸶》中的“我们习惯了看鸟儿惊慌的样子/所以,有人断言/这是假的,是布景/现代人的想象力/已自动规矩,到经验为止”,则对现代化都市进行了尖锐的讽刺,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人们早已对病态的生活环境习以为常,失去了想象力与创造力。《采山的孩子》则将木耳、蘑菇等山野风味在城市与乡间的不同形态对比,一切的生命形式在都市空间中都失去了它们原有的光彩,变得紧张不安。正因对现代化都市生活中的种种不满,李琦诗歌中的边地书写才会在总体上呈现出一种向后看的乌托邦情调,蕴含着对现代化的反思与对传统的认同之情。
李琦笔下的边地是一种理想化的精神家园,诗人对边地自然与民间持有明显的认同态度。作为至纯至美的理想居所,边地具有“向后看的乌托邦”倾向。尽管李琦更多地通过外乡人视角塑造边地,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理想化倾向,但正因这种美好真挚的情感深深打动着读者。李琦的一些诗歌或许展现了情感大于理性的一面,但情感与理性并不是完全相悖的,我们也不能忽略她在对纯美边地注入理想化浪漫色彩的同时也葆有着一丝理性,尽管这种理性因素可能相对隐蔽,如雪泥鸿爪,遁迹潜形。其诗歌中理性因素的介入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分别是对边地未来的清醒预见、对苦难底色的暗中呈现、以及直面现实的勇气。
诗人一方面在边地中构建自己精神上的乌托邦,另一方面又担心现代化终有一天会侵蚀边地。因此,李琦对边地的未来有着清醒的预见,边地在她的笔下呈现出了一种挽歌情调。正如《玉门一夜》中写的那样,“这一夜连月色都得意忘形/这一夜的人生松弛而舒展/”诗人在沉醉于边地的诗意纯粹与肆意潇洒时,也清醒地意识到了这种美好的短暂性,“这一夜就注定/短暂而易逝”。《去扎龙看丹顶鹤》表达了现代化对边地和谐美好自然的破坏“友人说,最好的几只鹤/它们出差了”。《街津口》中写道“这个满脸风霜的赫哲族才子/眼含热泪,两颊黑红/他指着博物馆作为展品的/一张渔网/羞涩地说,从前,这是我家的”,边地的传统生活方式及自然环境必然会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而改变。渔网本应该在大海里发挥功用,但现在却作为博物馆的陈列品出现,向人们宣告着传统的渔猎生活方式终会变为历史,被现代化的方式取代。诗人对于这种变化暗藏担忧,“正如当地的友人担心/它尚未声名远扬/我真唯恐这最后的恬静/走漏风声”。在《客栈》一诗中,李琦通过记录云南边地一间客栈的变化表明了异质性因素最终会进入到边地之中,这间坐落在边地的客栈从“庭院露天,不染尘埃/清水沐浴,香茶接风”变成了“一座接受了整容的旅店/像一个巨大的错别字”,现代化、商业化进入到了古老淳朴的边地。连远在边地的客栈都不能幸免,何况是别处。
边地的存在是李琦对一种诗意化理想生活的寄托,但她在构建理想边地时并没有对边地人民苦难生活的一面进行完全遮蔽。如长诗《死羽》在醉心于边地人民的淳朴真诚以及自然的神秘壮美时,诗人并未彻底忽视边地淳朴背后的悲剧和壮美背后的苍凉。
《死羽》中曾戍守山丹的转业军人“说完他撩起深色筒裤/那右膝下竟是一截假腿/谁也没问他致残的原因”,诗人并未在文本中交代边地军人为何失去右腿,但真相却呼之欲出,边地绝不是单一的诗意浪漫之所在,更承载着责任、血泪甚至埋藏着年轻的生命。在边地,还有这样一群年轻的钻井工人,他们将美好的时光放牧在寸草不生的荒凉边地,在最热闹的年纪经历着最寂静的青春,“石油是你们沉重的呼吸/是你们一肚子/说都不想说的苦水”,《死羽》中苦爷的故事既温暖又残忍“苦爷他抽了一袋烟/苦爷他喝了几口酒/苦爷他后来呜呜地唱了起来……”,这一生的苦楚都含在了这烟、这酒、这歌声中。这是一出好人的悲剧,苦爷人如其名,淳朴厚道却最终孑然一身,在无依无靠中死去。寡妇则因为带着四个孩子至死也无法追求自己的幸福,不得不违背内心离开苦爷带着憾恨走进坟墓。正是生活的苦难与辛酸造成了苦爷与寡妇的悲剧。因此,这片苍茫的大地上有着诗意浪漫的同时也承载了残忍和苦难。这些善良坚韧的边地人民深深震撼着诗人的内心。至此,边地的含义绝不仅是不染尘埃的诗意家园,更镌刻了厚重的底色。
李琦的边地书写并不意味着对现实生活的逃逸。诗人从不缺乏直面现实生活的勇气,没有因对边地的担忧而陷入悲观绝望情绪中,而是对未来充满了希冀。正如《死羽》中所言,“几个世纪以后/还是这个世界/一切都重新变化了/却还有橙色的黄昏/却还有饮茶的习惯/还有希望边地似花/还有遗憾丛生如菌”,现代化都市生活中,一切都在剧烈变化,但总有什么始终保持不变,恰恰是这种对未来的希望与呼唤,使人们在剧烈变动的现代化生活中拥有了前行的希望与追求美好的勇气。
四、结语
李琦身处于现代消费文化语境之下,却能够将目光投向遥远的东北、西北、西南等边地,在纯净的诗歌世界中构建了诗意化的理想精神家园,饱含情感地刻画了边地生灵的生存图景,在边地自然风光的描绘中流露出真情与哲思,并对边地民风民俗进行了细致生动的展示。诗人在具体呈现边地时,选择将边地人物放置于日常生活情境之中,呈现出对边地日常生活的认同与向往态度,在边地中寄托理想人生样式,并将边地自然赋予永恒的神圣之美,进而强调了美的救赎力量。其笔下的边地在对传统的认同与现代的反思中呈现出“向后看的乌托邦”情调,但诗人并非一味沉湎于边地的乌托邦想象中,在对纯美边地注入理想化浪漫色彩的同时也不乏理性的思辨精神,对边地未来有着清醒的预见。同时,李琦诗歌中部分人物命运的走势也暗示了边地壮美背后的苍凉,隐隐呈现了边地的苦难底色。但诗人并未放弃全部希望,而是赋予人们直面现实的勇气,在荆棘中寻找前行的动力,李琦对边地的复杂情感亦是对消费文化语境下知识分子矛盾心态的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