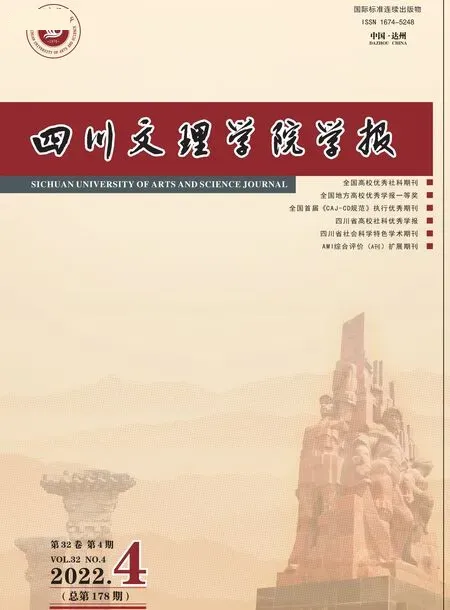《回声制造者》中的后现代身份建构
2022-03-17赵燕娇
赵燕娇
(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北京 海淀100871)
当代美国著名作家理查德·鲍尔斯(Richard Powers, 1957—)是继托马斯·品钦(Thomas Pynchon)和唐·德里罗(Don DeLillo)之后新兴的“X一代”的后现代小说家的领军人物,被誉为“后品钦时代的代言人”和美国“最有前途的小说家”。在其十余部文学作品中,荣膺美国全国图书奖的《回声制造者》(TheEchoMaker, 2006)是一部典型的融合了环境保护、生态学、伦理学和认知心理学等多专业领域知识的信息小说,也是一部“集推理小说、神经科学案例研究与生态小说于一体的鸿篇巨作”。[1]在鲍尔斯笔下,沙丘鹤是人类先祖与过往文明在当下社会的现实回音,是历史事实在现实记忆的传声筒,它们表现出超凡的记忆力,隐喻我们人类对过去理应保有的认知态度;而“双重错觉综合症”这一罕见病症则影射后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个体认知分裂和记忆错位现象,作者巧妙地将人类古老文明化身的沙丘鹤这一意象与“双重错觉综合症”这一后现代社会的医学顽疾串联起来,通过对两者之间错综复杂关系的有效编织,鲍尔斯得以不断追问并反思,“我们是谁?我们认识谁?我们又不认识谁?我们如何构建一个看似可靠的,连续的,整体的自我,即使它有时并非如此?”等一系列生存哲思。[2]实际上,罹患“双重错觉综合症”的患者并非没有记忆,只是患者的大脑中只保留了特定的记忆片段,遗忘的恰是与亲人建立情感关联的那一部分,换言之,患者对情感认可的缺失遏制了记忆的理性组合,“理智与情感”在后现代虚幻现实的“荒原”中失去了平衡,为此,“何时需要记忆,何时不如遗忘”,围绕记忆与遗忘这一宏大主题,鲍尔斯引入对个体认知分裂、记忆错位、精神异化、情感无能等后现代社会人类普遍存在的生存现象的忧思。
在《回声制造者》中,鲍尔斯独具匠心,借用隐喻、互文性和对位叙事策略等文学创作手法,借助想象,以面临家园破坏和种族灭绝的沙丘鹤沿内布拉斯加州普拉特河的年度迁徙与围绕主人公马克的车祸悬疑案为两条叙述主线,借罹患“双重错觉综合症”的“精神病人”马克的不可靠叙述、卡琳作为“正常人”的可靠回忆与“认知神经学专家”韦博对科学研究与医者仁心的辨证认识这三个叙事视角,互相交织,贯穿全文,生动再现了后现代视阈下人类的生存焦虑状况,传达出鲍尔斯强烈的生态忧患意识与对后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人与家园以及人与过往文明之间疏离现象的反思,饱含作家对由此带来的个体认知分裂与身份认同危机的文学关切。鲍尔斯笔下的主人公徘徊在记忆与遗忘、情感与淡漠、以及背离故土与回归家园的夹缝中,最终,他们在感性与理性之间寻找平衡,返璞归真,重新定义自我,选择回归家园拥抱承载人类先祖文明的故土,实现了个体身份在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归属,同时,三位主人公的身份建构之旅也照见了后现代社会人们应保有的生存法则和生活智慧,表达了作者对生活在虚幻现实中的人们如何在“孤立的个体之间寻求联结”、进而重塑自我、认识他人和建构自我身份的思考。[3]
一、身份危机:记忆的碎片与重组
虚幻现实或真实感的丧失是后现代文学作品的重要特征之一,后现代文学研究者杰姆逊认为,生活在后工业社会的人们,因为类象的大规模生产和复制,类象与真实之间的界限变得异常模糊,人们逐渐失去了对现实真实的认知,眼前所见都是对现实重复刻制的虚假的影像,正如作品中的三位主人公,均生活在虚幻现实带来的错觉中,都在不同程度上沦落为后现代社会网络、通讯等高科技技术操控下“聊以自欺”和“愚弄他者”的符码,整日为满足“虚假的需要”而机械地奔波忙碌。法兰克福学派左翼代表人物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对这一后工业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畸形供需关系的分析极具见地,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为了特定的社会利益而从外部强行施加于个体身上的,使艰辛、侵略、痛苦和非正义恒久化的需要,是‘虚假的需要’。”[4]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的选择不再出于内心真实的需求,而是为了满足虚幻社会的期待,并于潜意识中理所当然地认可其存在的合法性,致力于追求物质、名誉、利益和机会主义等带来的快感,最终,“依附于现有的制度和秩序,悲哀地实现了人的本能需要与社会需要之间的‘虚假的统一’。”[5]
鲍尔斯笔下的“双重错觉综合症”,既是对生活在虚幻现实中的人们普遍存在的心理顽疾的隐喻,又是对后现代社会和资本主义制度催生的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等生活常态的影射。在《回声制造者》中,鲍尔斯对当代美国社会的物质至上主义和极端享乐主义等集体病态深具洞察,对后现代社会给人带来的身份危机、精神异化等现象的分析鞭辟入里。小说中的三位主人公(马克、卡琳和韦博)生活在物欲膨胀的后现代社会,他们深受人类中心主义和物质至上主义的侵蚀,专注于各类通俗广告和大众媒体的教唆,被各种低俗的快餐文化和琳琅满目的商品冲昏头脑,追求庸俗的物质主义,背井离乡,沽名钓誉,最终,其鲜明的个性和迥异的性格也在后现代社会大熔炉的打磨下逐渐失去了棱角,成为鲍尔斯对病态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精神异化现象展开抨击的代表。
主人公马克是后现代虚幻社会中被物质至上主义侵蚀而致精神异化的典型受害者。车祸发生前,他专注于研究各种各样的赛车比赛等刺激性质游戏,沦落为现代宣传媒介和娱乐方式的忠实粉丝,对各式印有美女画像的海报和流行音乐情有独钟,甚至陷入电子产品和通讯网络带来的虚幻快感中无法自拔,在毒品、搏斗、血腥和厮杀的电子游戏中虚度光阴、消耗着生命,“一种新游戏马克能够连续玩24个小时,甚至都不起身上厕所”,[6]136正如生活在内布拉斯加州小镇上的居民所说的,即便不是因为车祸,马克“也会遭遇类似的祸事”,[6]169这是对马克纸醉金迷、浑浑噩噩生活方式的诟病,也是对以马克为代表的一类人的生存状态的批驳,更是对他所处时代的虚幻性的最有力控诉。
车祸发生后,罹患“双重错觉综合症”的马克失去了识别亲人身份的能力,误认为自己在世上的唯一亲人是被机器人特工所取代,随着病情的恶化,他逐渐对自己身边的其它事物也产生了怀疑,认为他的家乡、住宅和爱犬也是被匿名顶替者所代替。马克由对亲人身份的怀疑逐渐发展为对周遭一切的否定,某种意义上,对他人身份的不认同也就意味着他对自我与他人关系的否定,因而也是对自我身份的否定。虽然,姐姐卡琳等人想尽办法试图帮助马克找回对过去的记忆,但是,记忆错位的马克“始终无法将自己的过去与现在融为一体”,[7]同样,Jenell Johnson分析道,“马克的病症在于他无法将现在的自己与过去的自己等同看待,而那个过去的自己正是通过与周围的人建立社交关系而得以建构的。”[8]换句话说,“双重错觉综合症”彻底割裂了马克与过去的联系,改变了马克对自己与他人关系的认知,使他陷入对他人身份和自己身份定位的双重认识危机中。鲍尔斯引用这一病症反映出后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自我认知断裂,再现了虚幻现实中人们的病态生存状态,对鲍德里亚 “类象”和“真实”概念之间的模糊状态作出了最好的文学注解。
马克对姐姐“真实”身份的质疑成为一面反光镜,映射出卡琳的自我矛盾心理,使她开始回望过去,审视自身,重新思考自己在社会中的定位,寻求身体和精神两个层面的统一与富足。由于卡琳和马克姐弟俩从小生活在一个缺乏温情与呵护的家庭中,父亲酗酒成性,母亲淡漠冷酷,卡琳一直都想逃离这个随时会带来“暴风雨”的家庭。在一定程度上,童年的家庭遭遇导致后来的卡琳与家园逐渐疏离,并辗转于背离故土和回归家园的两难选择中。长大后的卡琳来到了苏德兰市,按照别人对成功的标准过活,用他人的评价丈量自己的得失,她满足于一份带来不菲收入的工作,一套象征成功与名望的公寓,甚至一段带来盲目和虚幻的快感的恋情。表面生活的光鲜也遮挡不了她内心莫名的孤独和虚无感,甚至她自己也慢慢地开始拒斥这种戴着面具的生活,卡琳的自我认知在后现代病态社会这块滤镜下处于分裂状态,误以为有妇之夫卡什是最“懂她心思的人”,是一个能够“让她找回真实自我”的人。[6]44实际上,卡琳和卡什之间的爱情是一种交易,是一种卡琳逃离内心孤独与寂寞的大胆尝试,是个人纵欲在污秽的都市生活中得以宣泄的手段,更是一种排遣内心虚无感的方式,结果不言而喻,卡琳在自己追逐的这份功利性的爱情中迷失自我,异化自我,丧失了辨别人的情感真假的能力,宛如马克难辨真伪的“双重错觉综合症”,卡琳成为人的情感层面的“错觉综合症”患者。直到她意外获悉马克企图自杀的消息,才领悟到弟弟在自己与特工和机器人之间难辨真伪并非没有原因:
她终于明白了弟弟不认她的原因。她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识别的特征了。她已经被扭曲的面目全非了。一个小小的欺骗行为重叠在另一个欺骗行为之上,直到连她自己也无法道出自己的状态,说出她在为谁工作。她推诿、否认、撒谎,甚至对自己隐瞒事实。对所有人隐瞒所有事情。…
她一无是处,卑微无名。比卑微无名更糟的是,她内心一片空白。
她必须改变自己的生活,从她那污秽的巢穴中挽救出点什么。[6]407
卡琳开始意识到导致自己情感无能的病因,并积极为拯救自我开具良方。她逐渐从一个没有情感和思想的“寄生虫”蜕变为一个有着道德思辨和理性判断能力的“正常人”。她认清了自己所生活的社会对人身体和灵魂的腐蚀性,拒绝继续充当被谎言编织的社会网络里的“空心人”,个体虽然渺小,依然努力寻求精神“荒原”中的“星星之火”,于是,她摒弃了世俗眼中的物质和虚荣,看清了以奸商卡什为首的精致利己主义者的虚伪、贪婪和疯狂,同时,也感受到了以丹尼尔为代表的环保主义者的真实、无私与伟大,终于追随自己内心真实情感的呼唤,在婚姻与家园归属选择中重新定义自我,重新建构自我身份。
如果说马克的身体顽疾——“双重错觉综合症”,割裂了他对人际关系在“过去”的真实认知与在“现在”的虚幻认定之间的联系;卡琳幼年时代的家庭创伤与成年后的情感无能使她联结过往记忆与当下现实,进而找到重构自我身份的基点;那么,认知神经学专家杰拉德·韦博的身份建构之旅则融合了他在科学试验(对马克病症的疗愈)与精神需求(对卡琳情感纠葛的见证与对妻女态度的转变)的双向成长与蜕变。韦博最初决定对患有罕见病症的马克展开科学研究,其目的无非为自己博取名利,借“双重错觉综合症”,韦博把马克的故事写进自己撰写的畅销书中,活生生的病例成为他在科研专著中大肆叫嚣的文字符码,成为自己沽名钓誉的镢头,尤其,在对马克病情的描述中,韦博夸大其词,掩盖了马克病情的真实情况。他窥探病人的隐私,却不能对病人的遭遇感同身受,介入患者的病症,却对患者的痛苦熟视无睹。韦博在初见卡琳时许诺的针对马克病症的认知疗法“戏弄了大家的期待,甚至玩弄了马克的友谊”,[6]183“双重错觉综合症”、马克和卡琳都沦落为韦博为博取名利而进行的科学研究的试验品,成为物化的存在。
韦博的思想转变得益于姐弟二人在配合自己接受诊疗的过程中,姐弟二人表现出的患者对医生的超乎寻常的配合、信任与托付,这使已有妻女的韦博深受触动,他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认知开始悄然发生改变。当新书《惊讶之国》的出版饱受恶评、负面评价将他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卡琳也开始对他的研究表现出质疑时,韦博才真正的开始反思自己的科研动机,审度救死扶伤的职业操守,追问医者仁心的道德品性,终于,他深刻检讨自己以往过分关注马克的“病症”,却对马克作为“病人”秉持淡漠的“不介入”的态度,意识到他不应该把病人当作科研的素材,试验的标本,更不应该利用马克的罕见病症作为吸引大众眼球、诱导众人舆论与提升个人关注度的幌子,相反,医者需要将“病人”视作“变化着的生命形式”,尊重他们与“非病人”一样的生命体的尊严,关注他们的人性,对病人加以平等看待,并注入人文关怀。[6]308
“双重错觉综合症”将三位主人公拴在一起,透过这一病症,我们见证了人类生命的脆弱和人性的弱点,也感受到了自我完整的认知对人类精神异化的救赎力量。在小说中,鲍尔斯对人的“记忆”话题的引入,“打破了时间的线性(叙事)特点,模糊了自我与他者的界限,进而在人类与自然之间建立一个共同体。”[9]马克、卡琳和韦博的身份危机就是在马克认知分裂的前提下,通过不断地记忆与回望,在过去与现在之间搭建桥梁,寻找自我在过去与现在之间、自我与他者之间以及自我与自然之间的“共同体”而得以化解。
二、自我定位:家园情节与情感召唤
美国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生态女权主义理论家查伦·斯普瑞特奈克(Charlene Spretnak)指出,在后现代社会,生命成为一架灵肉分离的机器,被动而机械地脱离了曾经熟悉的、给予他们心灵滋养的“自然”和“地方”,到钢筋水泥构筑的城市里,过着“非真实”的生活。因此,现代性兴起并盛行的表现之一便是割裂个体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同时“逃离地方”。[10]作为一位具有强烈的生态忧患意识和家园情节的后现代小说家,鲍尔斯在《回声制造者》中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后现代社会“身体”“自然”和“地方”三者之间的矛盾存在关系,并积极为化解个体身份危机寻找济世良方。一方面,在鲍尔斯笔下,马克的“双重错觉综合症”成为他对后现代病态社会带来的认知障碍与灵魂异化现象的隐喻,这一病症造成了马克的自我认知断裂,割断了他与至亲的情感纽带,成为斯普瑞特奈克笔下灵肉分离的机械性存在;另一方面,这一病症也成为以卡琳和韦博为代表的“普通人”和“医生”实现个体身份重构、寻求自我精神救赎的契机,通过不断地回望过去、反思当下,卡琳和韦博思忖着自我身份建构的方方面面,从与亲人和家园的纽带中寻求情感的依附和精神的寄托,尤其,鲍尔斯对卡琳和韦博的归家之旅中情感的蜕变与强烈的家园情怀着墨甚多,足以照见作家对见证人们成长、承载历史创伤与记忆的土地或“地方”在重塑自我、维系自我与他人亲密关系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卡琳长大后远离家乡,生活在大都市,但是每次当她“刚刚开始新的生活,试图以常人的姿态出现时”,她的家乡卡尼小镇就会把她“拉回来”,对卡琳而言,卡尼小镇就如同一片磁场的磁源,幼年时候的她千方百计想要逃离,但是,无论她怎样挣扎,强大的磁力总会把做离心运动的她拉回来,实际上,卡琳“根本不曾离开”,[6]75使卡琳产生向心力的是故乡和家庭在思想和精神上根深蒂固的影响,来自家园亲和力和家庭温情的召唤使她始终无法抹除那段记忆留下的烙印,即便在卡琳长大后远离家乡,依然不能从内心深处真正摆脱曾经生养她的那片土地。当卡琳因为马克的车祸返回卡尼小镇时,家乡熟悉又陌生的景象使她从心底“生发出一种怪诞的,不正常的”家的感觉。[6]6这种怪诞感和不正常感源于卡琳幼年时期的创伤记忆,体现了卡琳从小到大因亲情缺失而对故土文化所秉持的逃避心理,同时,也反映出卡琳对来自家乡和亲人关爱与呵护的渴望。所以,面对世上的唯一亲人,她选择了遵守曾经对父亲立下的誓言,“无论发生任何事情,绝不抛弃对方”,[6]425事实上,卡琳从内心深处非常珍惜这次照顾弟弟的机会,这是她得以重温记忆,感受曾经与弟弟亲密无间的亲情的最佳时机,也是弥补幼年亲情缺失的最好办法,于是,卡琳顺从内心深处时常被“拉回来”的家园情结的召唤,她辞掉了大都市体面的工作,重返质朴单纯的卡尼小镇,凭借自己的回忆逐渐唤起认知断裂、难辨真伪的弟弟的记忆,与马克一起守护这片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土地。
认知神经学家韦博虽然没能如卡琳一样最终选择返回家乡,但是,作为专门研究马克的“双重错觉综合症”的“专家”,在对马克的认知障碍病症的研究过程中,韦博意识到了人的完整的记忆的重要性,也逐渐体会到,为了在认知神经心理学领域有所建树,他曾经急功近利,罔顾作为一名医生的职业操守,最终声名狼藉,与妻女关系疏远。一定程度上,马克病症的疗愈得益于他逐渐接受自己与过去的联系,尤其表现为马克和姐姐卡琳之间关系的改善,相较而言,经历了感情和事业的双重打击,韦博开始从记忆中重拾完整自我的组合碎片,终于明白,“他失去的并非作为一名著名作家和心理学家的光环,而是通过回忆过去能够与他人建立的精神纽带。”[9]于是,他从内心深处更加珍视自己与亲人之间的情感维系,决定修复自己与故乡的弟弟之间的关系。尤其,当他揭开芭芭拉的真实身份,晓得导致马克车祸的罪魁祸首就是整日陪在马克身边,照顾他日常起居的芭芭拉时,马克对芭芭拉的宽恕启迪韦博,使他结束了对芭芭拉的痴迷,鼓起勇气踏上“归家”之旅,努力征求妻女的原谅,更为珍视自己与妻子希尔维两人之间美好的回忆,他们曾经“一起拥有宝贵的东西,拥有无法言说的过去”。[6]451这份珍贵的过去和无法言传的记忆“正是韦博想要和妻子一起重建的‘地方’,那里有他‘真实’的家园”。[11]
在鲍尔斯看来,故土家园这一意象在确保自我认知,维系自我与他人、自我与家园之间的关系中至关重要。它不仅见证了家乡物理环境的兴衰变迁,也是承载个人创伤记忆、情感认知与精神救赎的地方。弃井离乡、背离故土会割裂自我完整的身份认知,进而陷入精神异化的危机中。个人自我身份的建构离不开与之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曾经熟悉”却又“不断陌生”的地方,“从大世界着眼,由小地方做起,做有爱心的‘地方人’,是缓解生态危机、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的重要途径。”[12]
三、身份之根:呦呦“鹤”鸣与远古记忆
贯穿《回声制造者》全文的除了马克车祸悬疑案以及与之相关的系列情感纠葛这条线索外,还有面临家园破坏和种族灭绝的沙丘鹤与人类之间千丝万缕的关联。它们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正如享有“现代环保之父”美誉的美国环保主义先驱李奥帕德在《沙郡年记》中描述的那样,“当我们听到鹤的鸣叫时,其实我们听到的不仅仅是鸟鸣声,它是我们无法驾驭的过去的见证,也是那不可思议的漫漫岁月的象征,这些漫长的岁月又是生物和人类生存环境变迁的见证。”[13]在文中,鲍尔斯追本溯源,挖掘沙丘鹤在各国古文明中或褒或贬的指涉,从古希腊神话中阿波罗的鹤身原型假说,到印第安科里族的沙丘鹤携兔奔月的传说,再到鹤鸣给人类启迪而创造的拉丁语、波斯语和阿拉伯语等语言,甚至鹤文化在中国和日本等东方国家不同的文化指涉,从西方到东方,由古至今,鹤文化源远流长,无所不包,为此,鹤成为一种承载文化记忆的符号,它唤起我们对遥远的古文明的回忆,诚如Siegleman所言,“对鲍尔斯来说,沙丘鹤首先指代对远古的记忆,是一种承接过去与现在的符号,它们传递出源自大自然的最本真的祝福,而我们人类对待自然却总是肆意地践踏,无情地掠夺。”[1]又如Stock所说,该小说“强调的主题之一就是现实与传统之间怪诞而显著的冲突。”[14]沙丘鹤不得不面对人类的无情射杀,它们赖以生存的家园被破坏,处于濒临灭绝的边缘,其生存现状影射了后现代社会人类与过往文明之间的疏离与割裂,而人们对鹤群生存状态的熟视无睹恰如马克对姐姐的认知错位一样,最终导致个人自我身份的不完整,与此同时,作品中的沙丘鹤这一意象也引发我们反思鲍尔斯的生态忧患意识与生态伦理主张。
从小说开篇起,沙丘鹤的悲壮出场场面就集中体现了人类与自然、人类与文化的分裂状态。围绕沙丘鹤年度迁徙的是以卡什为首的旅游业开发商与以丹尼尔为代表的生态保护主义倡导者两股势力之间的较量。卡什是后现代社会典型的身心均被异化的形象,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他信奉“人类中心主义”机制,在看待人类与过往文明关系的问题上,他深受“物质至上主义”思想的侵蚀,孤注一掷,对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等生态伦理嗤之以鼻,他大肆开发鹤群的栖息地,罔顾这些生灵的生命安危,打着发展旅游业以振兴地方经济的幌子博取公众眼球。卡什高喊口号,“保护自然的目的正是为了让人们欣赏”,这冠冕堂皇的辩词恰恰印证了开发商生态保护主义谎言掩盖下的人类中心主义机制,卡琳就此坦言,“整个人类都罹患了双重错觉综合症。”[6]347在此,鲍尔斯借卡琳的口吻将马克的“双重错觉综合症”影射到整个人类身上,流露出对人类集体认知错乱状态的批判,讽刺了活在虚幻现实中的人们,因迷失在物质主义至上的欲望中而丧失人的本性,贪婪地向自然界过度索取,抢占其它物种的生存空间,并蔑视其生命尊严,这是鲍尔斯对人类生态短视的抨击与鞭挞。
事实上,作为人类自远古时代幸存下来的活化石,沙丘鹤与人类之间源远流长的超越物种和血缘的亲缘关系不可否定。“那些翩翩起舞的鸟儿就像人类的近亲,它们的模样就像人类的近亲;他们呼叫,表达意愿,生儿育女,在飞行中确定方位,这一切都像人类的血肉至亲。”[6]347-48同样,评论家Harris也认为,“鹤类如果不是我们的血亲,也无疑是远亲,它们和我们有着一样的基因链,追溯到30亿年前我们有着共同的祖先。”[15]时间逐渐改变了人类和沙丘鹤之间的物种分界,但是,时间抹不掉两者之间古老的亲缘关系,改变不了人类与沙丘鹤之间曾经血脉相连的事实,即便现在,沙丘鹤依然饱含情感,充满灵性:这群曾经跟我们拥有共同祖先的精灵以它们独特的方式表达着对亲人的怀念,比如,有一家三口在飞行时遭遇人类的枪击,当鹤宝宝看到“父亲”被射伤躺在地上时,它和鹤妈妈在空中不停地打转,不停地绕圈,不停地呼唤,以这种“宗教仪式”祈求死者的复活,祈祷鹤爸爸重新回到它们的身边,但是“它没有出现,只有昨日,只有去年,只有六千万年之前的时光,只有迁徙的路线,只有盲目的自生自灭的回归”。[6]278鹤爸爸被与它们拥有共同祖先的人类射死了,留给鹤妈妈和鹤宝宝的只有记忆,只有亘古未变的飞行路线和迁徙轨迹,它们凭借曼妙的舞姿和凄婉的啼鸣表达出对同类的怀念、记忆和追悼,与人类相比,沙丘鹤具有更牢靠的记忆,它们的记忆就是一幅幅地图,每年的飞行路线就印在它们的脑海中,使它们能够在一年一度的迁徙中准确导航,不至迷失,而这理应是对人类情感表达的真实写照,理应是我们对待逝去的文明应该持有的姿态。
作为承载着人类古老文明在当下社会的记忆符号,沙丘鹤唤醒我们对人类先祖与过往文明的记忆,沙丘鹤与人类基因的相似性,以及它们在记忆能力上表现出的超越性,成为鲍尔斯对罹患“双重错觉综合症”的整个人类族群生存状态的辛辣讽刺和无情批判。因而,在环境保护倡导人丹尼尔的感染下,卡琳和马克姐弟俩决定追随他的生态保护理念,在小说结尾处,恢复了正常记忆的马克开始潜心钻研李奥帕德的《沙郡年纪》这部倡导生态保护的专著,逐渐成为一名热心公益、致力于生态保护的环保主义倡导者,而姐姐卡琳毅然决定留在卡尼小镇接管沙丘鹤的保护工作,通过在自己与家园、自己与自然的亲密接触中建立联系而重新建构自我身份,可以说,小说主人公卡琳最终的选择折射了生活在后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寻求人类先祖之根、寻找断裂的文明以获得灵魂救赎的理智之举。
结 语
在《回声制造者》中,鲍尔斯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丰满真实,他没有规避人性的脆弱:记忆错位,自我迷失,精神异化,情感无能,家园缺失等都是对后现代社会人们普遍的生存状态的真实再现;而“个体与躯体之间的关系,以及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与家庭的关系、与文化的关系等,都是个人身份的构成性元素。”[16]对此,鲍尔斯在小说中敏锐地捕捉到了致使后现代社会个体身份异化的种种因素,借助文学想象,以“虚构”的故事展现“真实”的现实,批判了后现代社会发展带来的身份危机。在后工业时代,由于物质至上主义和精致利己主义等思想的侵蚀,人的精神逐渐被异化,慢慢偏离了文明发展的正常轨道,整个人类都成为“双重错觉综合症”患者,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以及人与过往文明之间均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割裂和疏离。
即便如此,鲍尔斯依然对医治这一后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认知分裂、身份异化顽疾保有信心,在这个“理智与情感”被科技逐渐操控甚至取代的精神“荒原”中,人类虽然渺小,但是,依旧可以“自由地扮演自我,自由地冒名顶替,自由地即兴表演,自由地想象任何事情,自由地通过我们所爱的事物塑造我们的心灵”。[6]426“亘古律动,现实回声”,鲍尔斯倡导的自由精神不失为给迷失在商品符码的机械社会中的人们开出的一剂良药,使他们逐渐摆脱人类中心主义机制的圈囿,摒弃物质至上主义和精致利己主义思想的侵蚀,正视记忆,追随内心情感的真实需求,重塑自我与他人、自我与家园、自我与先祖文明的关联,回归自我身份的真实性,最终,实现精神的救赎与灵魂的皈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