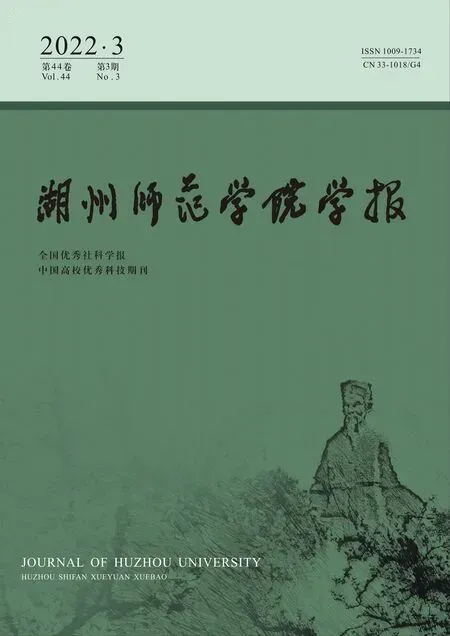国际邮寄送达在美国的适用及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2022-03-17储德林张利民
储德林,张利民
(苏州大学 王健法学院,江苏 苏州 215026)
一、引言
国际邮寄送达因高效的特点能有效减少国际送达程序的拖延,但在《海牙送达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之下,一些国家对其中的邮寄送达条款提出了保留,使得这一送达方式在实践中引发了诸多纠纷。在《公约》实施之后,此类争议在其原始成员国的美国表现尤甚,既包括美国本国对公约条款理解上的差异,也包括美国向外国邮寄送达产生的冲突。但从晚近美国司法态度的转变及其国内诉讼法显现出的特征来看,其中存在一些经验值得我们重新思考我国对国际送达的认知。无论对于送达采取何种观念,国际民事诉讼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为私方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如此,我们似应秉持这样一种立场:凡有利于解决争议,有利于提升国际送达效率,在不损害核心主权利益的同时,放开对邮寄送达的束缚也未尝不可。这又需以熟悉国际邮寄送达在美国的具体适用为前提,所谓“审视他人,检视自身”,以一种更为开放的态度对待国际邮寄送达,可以拓宽邮寄送达的适用,便捷国际送达程序。
二、美国对于《公约》第10条(a)项的理解
在美国早期的理论界及司法实践中,结合国际民商事案件,对《公约》第10条(a)项是否允许《公约》缔约国直接邮寄送达存在争议。美国一些法院和法律评论员将《公约》解读为允许原告向外国被告直接邮寄文书,但另外一些法院则持反对观点,认为《公约》并未授权原告采取直接邮寄方式(1)Charles Bankston v.Toyota Motor Corporation, 889 F.2d 172(8th Cir.1989).。探讨《公约》体制之下的域外送达途径有助于理解美国实践中产生的争议。
《公约》第2至第6条确立了中央机关送达途径,在该机制下,每一缔约国必须指定一个中央机关负责接收或向其他缔约国提出送达请求,并对此类请求进行形式审查;在审查无误后,中央机关需自行或安排其他主管机关执行送达请求,在执行结束后,还应将送达结果告知对方中央机关,如此形成一个闭环。与此同时,《公约》也确立了替代性的送达方式,第10条规定:“如送达目的国不表异议,本公约不妨碍:(一)通过邮寄途径直接向身在外国的人送交司法文书的自由,……”。但在《公约》的英文文本中,第10条(a)项中使用的表述为“send”,而在《公约》的其他条款中均使用的是“service”或“to be served”类的表述。因而,对于这一条款是否允许邮寄送达,在美国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并在实践中形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做法。
美国第二巡回法院认为只要送达目的国不明确反对这一条款,第10条(a)项允许国际邮寄送达(2)Alkermann v.Levine, 788 F.2d 830(2d Cir.1986).;但第八巡回法院认为第10条(a)项与其他款项下的表述差异,原因在于《公约》并不意图使第10条(a)项同于其他条款中所确立的送达方式,即第10条(a)项并不属于《公约》允许使用的送达方式。因此,第八巡回法院认为“send”的含义是指在通过其他获得《公约》授权使用的送达方式完成后,可以将送达后的文件加以邮寄(3)Charles Bankston v.Toyota Motor Corporation, 889 F.2d 172(8th Cir.1989).。其他巡回上诉法院以及地区法院对这一条款的理解也存在分歧。如华盛顿地区法院以及第三、第五、第九巡回法院认为根据第10条(a)项,美国原告可以使用邮寄送达方式完成域外送达,第一、第十巡回法院却持相反立场,第四、第七以及第十一巡回法院对此亦观点各异(4)See Jeffry B.Gordon, Service of Process by Registered Mail on a Japanese Defendant Is Ineffective under Article 10(a)ofthe Hague Convention of November 15, 1965 on the Service Abroad of Judicial and Extrajudicial Documents in Civil and Commercial Matters, Bankston v.Toyota Motor Corp., 889 F.2d 172(8th Cir.1989), 23 VAND.J.Transnat’L.851, 854(1990).。
在联邦法院之外,美国州法院对《公约》中的国际邮寄送达问题亦未达成一致观点。早期实践中,加利福尼亚州法院审理过一个典型的案件,认为第10条(a)项允许邮寄送达,但这一理解为加州上诉法院推翻。此外,纽约州、亚利桑那州法院也认为第10条(a)项不允许邮寄送达。
对于前述争议,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于2017年3月22日在Water Splash, Inc.v.Tara Menon(5)Water Splash, INC v.Tara Menon, 137 S.ct.1504(2017).的判决中做出了最终认定。在该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Alito大法官认为《公约》并不禁止国际邮寄送达,并废除了此前反对邮寄送达的判例。其理由如下:首先,《公约》明确规定其并不影响各缔约国送交司法文书的自由,而送交(send)的含义十分宽泛,并未排除基于特定目的而完成文件的送交。因而,送交应当属于送达的上位概念,送交的含义本身就包括送达。并且,《公约》起草者在将《公约》提交国会审议批准的美国总统以及国务卿的报告中,均认定《公约》允许直接邮寄送达,其他缔约国亦做出此种认定,如中国就因反对邮寄送达而提出保留。其次,最高法院亦提出直接邮寄送达需同时满足《公约》确立的两项条件:一是送达目的国不反对邮寄送达,二是其他“准据法”授权使用邮寄送达。于此,美国确立了国际邮寄送达的双向法律适用规则,即综合考虑本国以及送达目的国对邮寄送达的态度来决定邮寄送达的法律适用。在该案之后,美国联邦和地区法院对《公约》第10条a项是否允许邮寄送达达成了一致意见。在Jian Zhang v.BaiDu.Com Inc.(6)932 F.Supp.2d 561(S.D.New York.2013).案中,纽约州南区法院对原告向百度的邮寄送达给予否定。原因在于:中国在加入《公约》时,对其中的邮寄送达提出了保留,因而前述第一个条件无法得到满足。法院还进一步认为,百度公司签收了原告邮寄的传票和起诉书虽已构成对被告的实际通知,但此等实际通知并不构成美国宪法所要求的适当送达。
三、邮寄送达在美国的适用
(一)邮寄送达的主体
美国为普通法系国家,采取的是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构造模式,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法院处于消极裁判地位。反映在美国的送达体制中,送达的主体主要是当事人及其聘请的律师,且律师在送达中的身份为当事人的代理人,其行为的发生及后果均依附于当事人。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早期的司法实践中,送达并非私人事项,主要由法院官员执行。18、19世纪,美国采用了英国普通法中的送达规则,对被告的送达通常由法院官员诸如法警或送达执行员来执行(7)See Sinclair, Service of Process: Rethinking the Theory and Procedure of Serving Process Under Federal 4(C), 73Va.L.Rev, 1197-1212(1987).。晚近以来,随着邮寄送达在美国各州的普及,现在的邮寄送达更多地通过非政府或司法途径来实施。例如,美国在2002年向海牙国际私法会议提出,将其原先指定为中央机关的美国司法部变更为一家从事邮政业务的私人公司,让后者负责转递其他国家的送达请求。此举表明送达程序的“私”属性在美国的最终确立,然而此种转递机关并非我们所说的送达主体。实际上,根据美国法律,送达主体仅包括当事人和法院(8)Fed.R.Civ.P.4.(2004).,具体体现为在确保外国当事人能收到邮寄送达的文书前提下的当事人自行邮寄送达,以及美国法院根据当事人申请而裁定由法院书记员进行邮寄送达。
(二)邮寄送达法律适用
美国传统意义上对邮寄送达的法律选择的规定一般受法院地法支配,对此,1971年的美国《冲突法》第二次重述第126条、1986年《对外关系法》第三次重述第471条都作出了相应的规定。根据这一规定,美国联邦法院的邮寄送达程序便由《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4条支配。但晚近国际私法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表明,单纯依据法院地法进行送达程序的法律选择难以满足国际民商事案件判决承认和执行的需要,如送达目的国的法律可能禁止某些特定的送达方式,进而影响判决在送达目的国的承认与执行。在此背景之下,关于邮寄送达法律选择的依据亦有所丰富。在Brockmeyer v.David C.May案中,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指出,“我们必须跳出《公约》来寻找允许使用国际邮寄送达的依据。允许使用国际邮寄送达的任何授权性规定以及如何完成送达的要求,必须来源于审理案件的法院所在国的国内法规则”(9)Brockmeyer v.David C.May, 383 F.3d.798(9th Cir.2004).at 802.。因而,在《联邦民事诉讼规则》中,作为邮寄送达的法律依据或可包括以下三种。
第一,美国国内法明确允许使用国际邮寄送达的规则为《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4条f款(2)(C)(ii)项。根据该项规定,在相关外国法律不禁止此类送达方式的前提下,美国原告可以使用附带签收证明的国际邮寄送达,但需由受理案件的联邦地区的执行员进行邮寄送达。本条规定的逻辑前提是送达目的国的国内法并不禁止邮寄送达,这是由于国际民商事案件一般超越一国领域,而送达程序的顺利完成需要国家之间的互相配合,因此必须附加尊重送达目的国的国内法的现实需要。同时,本条所规定的邮寄送达主体为美国法院的执行员,因而排除了原告以及原告律师直接邮寄送达的可能。在Brockmeyer案中,法院便以邮寄送达的执行主体并非法院执行员为由,认定原告进行的国际邮寄送达不符合此项规定。此外,本条对邮寄送达的具体形式亦作出了要求——必须采取附带签收证明的邮寄方式,而禁止不要求签收收据的常规邮寄方式。实际上,无论是要求法院执行员来执行邮寄送达,还是要求需以附带签收收据的邮寄形式,均是为确保外国当事人实际收到、知悉邮寄送达的文书内容的权利而确立的形式兼顾内容的“双重安全标准”。
第二,《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4条(f)款(3)项规定,联邦地区法院可采取不为国际协定所禁止的任何方式进行送达。根据该项规定,只要不为国际协定所禁止,原告可采取任一送达方式来替代规则中明文规定的送达方式,这自然也应包括邮寄送达。在美国实践中,本条提及的替代性送达方式包括平信、电子邮件、公告以及电报等。但实际执行情况并非如此简单。对于能否使用替代性的送达方式仍需取决于地区法院的裁量权,即在获得地区法院许可的前提下,美国原告可以通过邮寄方式向外国个人或公司进行送达。在1965年的Levin v.Ruby Trading Corp.案(10)Levin v.Ruby Trading Corp, 248 F.Supp.537(S.D.New York.1965).中,法院根据修订前的第4条(i)款(1)(E)项授权允许原告通过常规邮件方式进行送达,但常规邮寄形式不符合前述“双重安全标准”。因而法院最终认为,虽然根据第4条(i)款(1)(E)项,原告可采取常规邮件方式进行国际邮寄送达,但出于确保充分送达的“双重安全标准”的考虑,减损了常规邮寄方式在本案件中的适用。可见,若原告选择邮寄送达作为本条中的替代性送达方式,其必须首先获得上级法院的批准使用替代性送达方式的许可。
第三,《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4条(f)款(2)(A)项规定,若不存在国际一致同意的方式或可适用的国际协定,则允许原告使用其他的送达方式,只要送达能够给予被告合理通知。对于本条是否允许邮寄送达,美国学界和律师界存有争议。反对的理由如下:其一,一般认为本条的适用情形为个人送达;其二,第4条(f)款(2)(C)(ii)项已经对国际邮寄送达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因而对于第4条(f)款(2)(A)项不应将其解释为授权使用邮寄送达的依据。美国当时的立法咨询委员会认为“只有当向受送达人送达的邮寄形式为要求附带签收收据时,邮寄送达才适当”(11)See Gray N.Horlick, A Practical Guide to Service of United States Process Abroad, 14 Int’l Law.637, 640(1980).,从这个角度而言,第4条(f)款(2)(C)(ii)项包含了所有对于国际邮寄送达的要求,故不宜将第4条(f)款(2)(A)项再度解读为允许国际邮寄送达。
因而,从美国最高法院确立的适用邮寄送达两项原则来看,对于邮寄送达的法律适用需要结合文书发出国与文书发往国的法律来共同决定。具体为:在特定的国际民商事案件中,由审理案件的州法院依据该州送达规则来决定是否能使用邮寄送达;其后,法院还应当考察文书发往国是否对邮寄送达提出保留,以决定在该案中是否应当适用邮寄送达。换言之,在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4条允许邮寄送达的规定仅能作为法院在认定本案中的邮寄送达是否合理的依据之一,而最终决定向外国当事人邮寄送达是否适当的依据则需要依据《公约》共同决定。若外国对《公约》第10条(a)项的邮寄送达提出保留,则美国原告向外国当事人进行的直接邮寄送达会被认定为不构成适当送达。
四、邮寄送达在中国的适用
(一)中国态度难满足司法协助之需要
从大陆法系国家来看,法国、比利时、意大利、荷兰、西班牙等国家对邮寄送达并未提出保留,而德国、日本、瑞士对《公约》第10条(a)项提出了保留(12)参见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官网,https://www.hcch.net/en/instruments/conventions/specialised-sections/service,访问时间截至2021年12月13日。,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对该项的保留直到2018年12月21日才正式向海牙国际私法会议提出保留声明(13)参见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官网,https://www.hcch.net/fr/instruments/conventions/status-table/notifications/?csid=407&disp=resdn,访问时间截至2021年12月13日。。若将视角拓宽至《公约》全部成员国,反对邮寄送达的国家达35个,持“相对保留态度”(Qualified Opposition)的国家有4个,不反对的国家有40个(14)保留的国家有:阿根廷、奥地利、比利时、巴西、保加利亚、中国、克罗地亚、捷克、埃及、德国、希腊、匈牙利、印度、日本、韩国、科威特、立陶宛、马耳他、马绍尔群岛国、墨西哥、摩纳哥、黑山共和国、尼加拉瓜、挪威、波兰、摩尔多瓦共和国、俄罗斯、圣马力诺、塞尔维亚、斯洛伐克、斯里兰卡、瑞士、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土耳其、乌克兰、委内瑞拉;持“相对保留态度”的国家有:澳大利亚、拉脱维亚、斯洛文尼亚、越南。。
在中国立法和实践中,对待邮寄送达采取的态度为“双轨制”,即在纯国内民事案件中允许邮寄送达(15)《民事诉讼法》第88条规定:直接送达诉讼文书有困难的,可以委托其他人民法院代为送达,或者邮寄送达。邮寄送达的,以回执上注明的收件日期为送达日期。;而在具有涉外因素的案件中,对邮寄送达所采取的态度不尽相同。其中,在向非位于中国境内的当事人送达时,其法律依据为《民事诉讼法》第267条,该条第6款规定“受送达人所在国的法律允许邮寄送达的,可以邮寄送达”;而在外国向位于我国境内的当事人进行送达时,我国又对作为此种送达的法律依据的《公约》第10条(a)项提出了保留。我国对待邮寄送达的态度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理解:其一,在我国法院向外国进行邮寄送达时,需以该外国法律允许外国向其境内邮寄送达为前提,如果相关外国法律并未做出此种授权,我国法院便不能采取邮寄送达;其二,由于我国针对邮寄送达提出保留的事实,外国并不能向我国境内的当事人进行邮寄送达。
从上述规定来看,中国与其他大陆法系国家不同,本身并不排斥邮寄送达在国际民商事案件中的适用,其所反对的仅为外国向我国境内邮寄送达文书,而反对的理由为“邮寄送达将会侵犯我国主权和安全”。而实际上,1977年的《公约》特委会会议便已经达成一致意见,即不应将邮寄送达司法文书视为侵犯送达目的国的主权[1]139。除此之外,一方面认为外国向中国进行邮寄送达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和安全,另一方面在外国法律允许邮寄送达的情况下,我国法律又允许向受送达人所在的外国进行邮寄送达。这种矛盾导致了我国域外邮寄送达制度的封闭性,显然不符合国际司法合作的趋势。除此之外,学界对我国“双轨制”邮寄送达还存在互惠性的讨论。有学者认为,按照互惠原则,对于邮寄送达应当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态度[2]6。由此,若认为在国际送达领域存在互惠性的要求,显然中国的态度及做法并不满足这一要求。
(二)送达主体单一
送达,有学者将其定义为“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的程序和方式,将诉讼文书交给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行为”[3]266。这表明我国民事诉讼送达被定性为人民法院的一项职权行为,其主要目的在于保障诉讼进行,是法院单方面的职责和义务,诉讼中由此产生的不能送达的风险和诉讼拖延责任也由法院单方承担。而从国际民事诉讼法的角度来看,“送达指向被告投递诉讼书状的渠道”[4]155。笔者认为,后一表述似乎更能体现出送达的桥梁作用,完成送达的主体并不会造成送达秩序的混乱,因为多主体进行的送达方式的目的均为确保诉讼程序的进行,最终实现的是“殊途同归”的效果。并且,我国对于送达的定性也导致法院在送达领域中承担了过重的责任,这不仅浪费了司法资源,拖延了域外送达程序进程,也与我国对司法效率的渴求背道而驰。
如前所述,在美国,邮寄送达的主体可以是当事人自行邮寄或当事人申请由法院执行员进行邮寄送达,《联邦民事诉讼程序规则》并未赋予送达主体任何其他权能,只要送达程序符合法律规定,满足法律对正当程序的要求,即可构成正当送达。事实上,送达主体的多元化不仅能满足正当程序的需要,也能提升送达效率、减轻法院负担。与之相对应的是,在我国法院司法资源短缺的背景下,国内民事诉讼法学者们也曾提出送达主体多元化的建议。如有学者指出,“从尊重当事人的程序主体权出发……跳出送达的职权本位观,省思民事送达制度的应然目的”[5]89,更多地发挥当事人在送达程序中的主体作用。
诚然,公正是司法所孜孜以求的终极目标,但从整个社会利益来看,必要的司法效率也是公正的一种体现,毕竟“迟来的正义是非正义”。因此,对法院而言,需以最小的成本实现司法公正;对当事人而言,也需以缩短诉讼周期和成本的方式实现正义,而允许邮寄送达并提升当事人在邮寄送达中的参与度将会使得送达效率大大提升。
五、中国对邮寄送达的完善
(一)送达职权主义观念的调整
我国对于送达的定性与大陆法系国家一致,即认为送达是法院的专属职权。从我国职权主义的诉讼构造来看,对于送达的这一认知原本也无可厚非。只是在司法资源日益匮乏、“案多人少”压力陡增的今天,我们需要重新思考送达在诉讼中的性质问题。
目前,我国的诉讼构造有进一步向当事人主义趋同的趋势,学界也主张在送达领域可以构建一种“法院送达为主,当事人送达为辅”的送达方式。对此,综合考虑送达效率与诉讼经济原则后,笔者认为可以借鉴美国的相关经验,拓宽送达主体,以实现减轻法院负担的目的。在此基础上,笔者对外国向我国直接邮寄送达是否损害我国司法主权持商榷态度。原因有三。首先,即使我国仍坚持认为送达属于法院的职权,但这一职权与司法主权并不存在直接相关性。如前所述,送达的主要功能在于通知当事人,并由此带来程序或实体上的法律效果。送达功能本身更多地体现了一种在诉讼程序中的中介行为,该行为的履行或不履行虽然也会产生诉讼上的效果,但并非对诉讼的干预,因为司法权的本质是判断权,而送达行为并不会干预这种判断权的行使,其只是为判断权的行使提供前提基础。其次,在国际民商事案件中,鉴于案件双方本质上属于私法关系的当事人,所以案件所牵涉的利益也仅为双方利益,并不涉及国家。基于此,向一方当事人邮寄送达并不会对送达目的国的国家安全和利益带来损害。即使在极端情况下,邮寄送达并不符合正当程序的要求,如出现由于邮寄送达文书未经翻译导致当事人无法读懂的情况,当事人也可通过相应途径提出送达不适当的抗辩。最后,在美国的实践中,当事人可以作为邮寄送达的主体,其所进行的邮寄送达亦属于私人行为。根据国际法,一国可以禁止外国在其领域内实施国家行为,而私人行为与外国官方和司法的行为性质不同,若认为私人行为侵犯国家的主权,则也很难说得通。因而,对于私人采取邮寄送达的行为并没有违反国际法,也没有侵犯外国的司法主权。
据此,笔者认为正如何其生所言,“将送达仅视为一种手续、一种程序,可能会使我们在进行制度设计时,放下思想的包袱,……更能灵活和科学地采用各种方式、各种技术手段实现送达的目的”[2]36。
(二)撤回对邮寄送达的保留
关于我国对国际邮寄送达的态度,有学者主张应当撤回对邮寄送达的保留,从而拓宽外国当事人向我国进行送达的途径。本文赞同这一观点。但也有学者出于我国现行的职权主义构造以及对国内当事人保护的立场上表示反对。反对理由如下:我国在审判方式上仍属于职权主义国家,因而对于邮寄送达有着特殊的程序和要求;邮寄送达通常不要求文字的翻译,我国国民并不能理解文书的含义;外国邮寄送达的方便,会引起我国公民诉讼成本的增加;在职权主义下,我国公民不能向域外邮寄送达,而外国当事人可以向我国邮寄送达,因而会对我国当事人产生不利[2]36。
对此,笔者认为,对于诉讼构造的原因可以通过观念转换的方式进行解释,在不否认送达具有“公”的性质的同时,可放开承认其“私”的性质,进而允许私人进行送达,此时,我国公民亦可向外国进行邮寄送达。因而,结合职权主义诉讼构造的现状,可以通过立法上的完善加以明确。加上晚近要求当事人在诉讼程序中承担更多责任的呼声,放开承认邮寄送达的“私”的性质也可作为拓宽邮寄送达主体的理论前提。于此,可通过立法,先行拓宽送达主体引领观念革新,再逐步完善当事人邮寄送达的具体规定。可采取以下方式来完善我国现行的域外送达程序:对于邮寄送达的选择,可由当事人向法院提出申请或法院依职权裁决,在法院批准或裁决之后,邮寄送达程序的完成可由当事人自行完成。由此,当事人参与送达程序,既能减轻法院的负担,又能发挥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的主体作用,进而推动送达效率的提升。
对于当事人利益保护涉及的两个方面,笔者认为,对于邮寄送达的翻译要求,完全可以在撤回保留的同时提交一份要求“凡向我国境内当事人邮寄送达的必须附带中文文本翻译”的声明,于此便能解决我国国民不能理解邮寄送达的文书内容的问题;对于允许外国向我国邮寄送达会增加我国当事人诉讼成本的这一观点,虽然禁止外国向位于我国境内的当事人邮寄送达可以延长外国的送达时间,却并不能阻止外国向该当事人送达,因为《公约》之下还规定了其他送达途径。禁止外国向我国邮寄送达所带来的唯一影响即为延长送达时间,拖延诉讼进程而已,而拖延的诉讼进程也会导致我国当事人卷入诉累,从根本上不利于国际民商事争议的解决。
(三)明确允许邮寄送达的国家名录
由于国际邮寄送达跨越国境的特征,加上不同国家对邮寄送达定性的分歧,综合导致国际邮寄送达的法律适用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体现为需要兼顾文书发出国、送达目的国甚至判决执行国的国内法规定。在目前的实践中,我国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由于现实的局限性,无从考证哪些国家允许邮寄送达,哪些国家不允许邮寄送达。加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外交部也并未提供这方面的资料,这就使得法院在处理这类事项时无从着手。因而,出于便利法院在特定案件中授权允许或裁决适用邮寄送达方式,我国还需要制定允许邮寄送达的国家名录,以明确哪些国家允许邮寄送达,哪些国家不允许邮寄送达,并发挥对法院在邮寄送达的法律适用上的指导作用。
六、结论
邮寄送达为《公约》下最为简便的送达途径,但其在我国的适用并未产生便利送达的结果,因为我们在域外送达的定性上坚持司法文书的送达属于法院的司法职权行为,因而具有严格的公属性和属地性。这种观念无疑会严重束缚我国目前实践中对送达效率的需求。并且,外国向我国直接邮寄送达并不会干预我国司法权的行使,因而也不会侵犯我国的司法主权。由此,本文认为我国需要借鉴美国对国际邮寄送达的态度以及在实践中的做法,对我国现有的观念加以革新,并撤回在《公约》中提出的保留。于此,方能实现域外送达的便利性,提升域外送达效率,这才能与《公约》的宗旨和目的相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