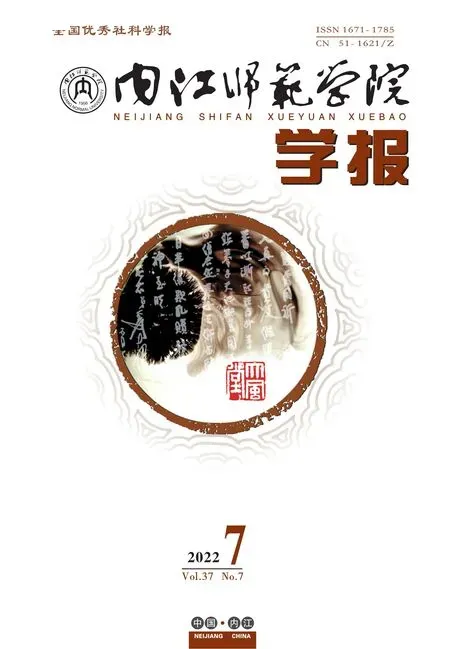是谁渴望永久的梦幻
——史前“玉”文化蕴含的生命美学
2022-03-17范藻
范 藻
(成都锦城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 四川 成都 611731)
从“离宫别窟,游息之处”的西天王母到“抟土造人,化生万物”的创世女娲,再到“开辟鸿蒙,谁为情钟”的红楼一梦,它们共有的文化符号就是古老而流传至今、晶莹而光耀千古、神奇而万人崇奉的天下奇石、世上珍宝——玉。从距今9000多年前的黑龙江饶河小南山文化,一直到4000多年前的甘肃齐家文化等,这些史前文化遗址均出土了大量的玉器。从零散的玉珠到规整的玉饰,从实用的玉斧到祭祀的玉龟,从小巧的玉佩环到硕大的玉人像,从朴拙的玉龙猪到精美的玉璇玑等;再加上琼楼玉宇的想象、金玉良缘的传说和金风玉露的美景,还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玉不琢不成器、化干戈为玉帛的说法。对此,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叶舒宪教授名之曰“玉教”或“玉石神话”“玉教伦理”和“玉石里的中国”。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玉代表神灵,代表神秘变化,也代表不死的生命。这三者,足以构成支配玉文化发生发展的核心观念。”[1]玉,不但成为中华文化的瑰宝,而且被视为民族精神的象征,更蕴含着史前审美意识的发生并昭示着中国生命美学的起源。
在中华民族美学的历史进程中,如果说有文字表述的“美”是以孔子的“里人为美”、荀子的“充实为美”和许慎《说文解字》揭示的“羊大为美”为代表,它们属于文明时代人们理解美的思维成果。那么,无文字的实物叙事就是以大量出土的史前玉器为代表,形象地展示了远古人类有关生命意义的美学思考。如黑龙江小南山遗址发掘出土200多件包括玉玦、玉环、玉管、玉珠、玉斧、扁珠、璧饰、锛形坠饰等玉器,表明远在石器时代的人们就用既不能果腹也不能蔽体的玉作为精神追求的审美对象来装饰日常生活又寄托来世人生。这充分说明了9000多年前我们的先人不但开创了较为发达的物质文明,而且开始了十分丰富的精神生活,及至其后4000年左右,东到山东大汶口的玉璇玑礼器,西至四川三星堆的鱼嘴形玉璋,南到岭南澳门的玉石作坊,北至河西走廊的齐家文化的鱼形玉刀,这些几乎覆盖了整个华夏的玉文化现象,不但是“‘玉’见中华”,而且是“‘玉’成中国”,从而将我们民族追求美和思考美的历史由文字记载的“小传统”推进到了玉器叙事的“大传统”。从时间上看,将中华民族的审美历史至少提前了五千年,当然也是生命美学盛开在远古的一束玉树琼花。
众所周知,文字叙事的美学由于受造字观念、行文规范和表意要求等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将原本鲜活而充满力量、灵动而富有激情的美严重地遮蔽了。如《毛诗序》开篇就说:“《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将文明初始“桑间濮上”男欢女爱呈现的火热生命置若罔闻而荡然无存。因此,要真正探寻民族审美的源头活水,还必须回到生命的本身情态,必须返归生命的原初状态。对此,当代中国生命美学研究的开创者和领军人潘知常教授认为,中国美学“传统的真正源头应该回溯至《山海经》”,因为“《山海经》里的人物,乃是最为本真的中国人。‘生日月’的羲和、‘化万物’的女娲是中国的开辟女神;舞干戚的刑天、触不周的共工是中国的血性男儿;衔木堙海的精卫、布土堙水的鲧禹父子是反抗命运的悲剧英雄。《山海经》写了生命的激情和拼搏,欢欣和渴慕,反抗和追求,它是中华民族真正的血性之源。”[2]由此启发我们,史前玉器就是一部渐次展开的形象光灿、魅力四射和意蕴深远的鲜活而生动的生命美学“史书”,更是我们民族在钟情于玉和寄情于玉的审美活动中,让朴拙的生命尽显精致、让粗犷的生命变得精巧、让愚钝的生命获得精灵——因审美而生命!这是潘知常一直思考的“审美活动为什么能够生成生命”的生命美学的核心问题,他紧扣人的生命感觉说道:“关于审美活动,我们可以用一个最为简单的表述来把它讲清楚:凡是人类乐于接受的、乐于接近的、乐于欣赏的,就是人类的审美活动所肯定的;凡是人类不乐于接受的、不乐于接近的、不乐于欣赏的,就是人类的审美活动所否定的。”[3]的确,有着本能性的爱美让蒙昧生命完成了向文明生命华丽的转身!
由物及人,由表至里,由形而神,璀璨而温润、纯净而坚密的远古之玉,究竟蕴含和承载了哪些生命的美学和美学的生命,即生命美学的远古奥秘呢?
一、质色光盈:晶莹炫目的视觉美感
视觉反应是所有生命接触外部世界的重要途径,这种趋光性甚至还是植物重要的本能特性,所谓生长的光合作用。在人类使用的木器和石器工具里,无疑石器比木器在砍砸、切削、击打等方面的功用和效能更胜一筹。而在漫长的石器时代,原始人在使用和加工石材的过程中,发现了有一种石头不但非常坚硬,而且十分闪亮,在一大堆顽石中显得与众不同,这就是玉石。中国首届工艺美术大师李博生说道:“人类在长期制造使用工具的活动中,比较、选择、保留了一批可做母工具之材料,从而有意无意地完成了一次从原始人类进化到人类的跨越。而从石头中分离出来的这一部分,较其他石头更坚硬,重量更大,颜色肌理更美丽,纹理更清晰。人们更珍爱的那一小批石头,后来西方人称之为宝石,而形成了宝石文化;东方则称之为玉石,从而东方则形成了玉文化。”[4]这种独特的石头,不但尖利无比,是很好的劳动工具,而且纯洁无瑕,是很美的观赏物品。这也印证了普列汉若夫在《没有地址的信》著作里通过对南太平洋岛国土著居民原始文化考察得出的结论:实用先于审美。但这二者也不是“楚河”“汉界”泾渭分明,而是利于、便于和优于实用工具的必然最先走向审美,即溢出实用的精神性要素为审美打下了基础和做好了预设。德国艺术学家格罗塞在论证原始艺术的起源时说过:“物品固然要实用,但也要有快感。我们已经说过,最简单的用具装潢,在每个民族中都是有的。”[5]由此可见,玉的光亮或打磨得更加光亮,既是一种可观的视觉效果,也是一种可用的工具效果。
由于玉首先在视觉上迥异于周围的石,故能引起人们的关注,相应地,做成的工具必定要突出它的色彩效果。在新疆罗布泊地区的楼兰遗址,考古人员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玉斧,是用和田羊脂白玉制成,玉质细润光滑。还有红山文化玉器,不但质地细密,硬度较高,而且色泽均匀,光亮晶莹,这些玉的颜色有苍绿、青绿、青黄、黄色,也有玲珑剔透的碧玉和纯白色玉。1971年8月的一天下午,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村民张凤祥偶然发现的一件“玉雕龙”,在阳光下还能发出碧绿的光泽。对这些颜色比较鲜艳、光泽比较明亮、纹理比较细致的石头就会油然产生喜好的情感。对此姚士奇先生在《中国的玉文化》一书开篇就说道:“这种感觉开始还是出于人的本能,后来便上升为一种原始的审美形式。久而久之,这些漂亮的石头就被归为一类,称之为玉。这就是中国上古时代玉石的起源。”[6]《说文解字》释之曰:“玉,石之美。”
还有相较于史前文明的文字时代的后人在陈述玉时多半要加上一个色彩词。《山海经·西山经》曾记载:“峚山其上多丹木,员叶而赤茎,黄华而赤实,其味如饴,食之不饥。丹水出焉,西流注于稷泽,其中多白玉。”《山海经》还对“碧”情有独钟。《山海经·北山经》云:“又北三百里曰维龙之山,其上有碧玉,其阳有金,其阴有铁。”文化人类学家杨骊女士指出“《山海经》还认知了玉的各种形态,如玉膏、玉荣。‘碧’‘水碧’‘瑶碧’‘青碧’‘碧玉’‘碧绿’都指称的是绿色软玉,全书共提及32 次,可见这是当时人们认知最明晰的玉石种类。”[7]《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死而利国,犹或为之,况琼玉乎。”《汉书·西域传》载:“莎车国有铁山,出青玉。”西汉文学家东方朔的《海内十洲记》也把和田玉誉为“白玉之精”。《续汉书志·舆服志上》:“卿大夫五旒,黑玉为珠。”以至于对色彩的强调成了中国玉石文化的重要特征,仅在命名上就可见一斑:玛瑙、琼瑶、青金、珊瑚、琥珀、水晶和绿松石等。
这种对玉由色泽而质地的喜好和崇拜,一直延续到文明时代诗人创作对玉的情有独钟。在历代文学作品中留下了大量的有关玉的形式美和以玉喻人的佳辞丽句。《诗经·卷阿》:“颙颙昂昂,如圭入璋,令闻令望。”这是写君子仪表堂堂,如玉器一般威武壮美。屈原在《大司命》中有“便衣兮被被,玉佩兮陆离”。这里诗人写出了玉饰品七彩杂沓、“光怪陆离”的审美感受。陆机《西北有高楼》“玉容谁能顾。倾城在一弹”一句写出了女孩娇艳粉嫩的面容。唐代王维的《洛阳女儿行》有“自怜碧玉亲教舞,不惜珊瑚持与人”等。诗人还喜欢在诗词中以“玉人”指代美女。如杜牧《寄扬州韩绰判官》的“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 。而南宋词人辛弃疾有多首词都提及“玉人”:“有玉人怜我,为簪黄菊”“玉人好把新妆样,淡画眉儿浅注唇”“玉人今夜相思不,想见频将翠枕移”“玉人还伫立,绿窗生怨泣”。在中国古代诗文里,还有用“玉颜”“玉容”“玉貌”形容美女。
二、质体细腻:温润可人的触觉美感
玉在视觉上晶莹透彻,剔透玲珑,而握之在手则温润细腻。这首先体现在远古时代将玉打磨制作成为刀斧、棒槌或符章等实用工具时的手感上。尽管这时的玉器还没有开始承担祭祀亡灵、崇拜先人和祷告苍天的通神功能,还属于形而下的物质意义上的玉。但是,玉石经过“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加工就会成为玉器。的确,同样是狩猎或劳作的工具,玉器握在手上的舒适感是石头和木棒不可同日而语的。而舒适感是一种从身体到心理的快慰感。尽管这还带有生理性的、自然的和本能的因素,但已经是“人”的感觉了,开始趋近于审美感觉了。而一旦当玉器的工具性逐渐消失后,伴随社会性作用的增多和精神性价值的增值,就上升为纯粹心情舒畅和精神愉悦的审美感受和美学价值。因此,玉所具有的温润而温和、细致而细腻、舒服而舒畅的触觉美感,使得原始人特别热衷于玉与身体的密切接触,进而产生由表及里、由外而内,甚至是由物理而至心理、由此岸而及彼岸的神奇效应。
远古的人们热衷将玉作为佩饰。距今9000年前的小南山遗址就出土了能够环绕在手腕的玉环、佩戴于脖子的玉管和配饰在胸前的玉珠、悬垂于耳朵的玉玦等。虽然这些饰物有着种种复杂的含义和神奇的象征,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玉器符合人体工程学,能够给人带来舒适感,这演变为后来的“玉养人”的说法。一是它能入药养身。东晋葛洪在《抱朴子》和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都分别论述过玉石入药养身。如李时珍就说:“玄真者,玉之别名也。服之令人身飞轻举,故曰:服玄真(玉石),其命不极。”二是它能保身健体。现代科学表明,玉石含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如锌、镁、铁、铜、铬、锰等。古人的嘴含玉,是借助唾液的营养成分与溶菌酶协同作用,具有生津止渴,除胃肠热,平烦懑气的功效。宋朝医学文献《对济录》中记载:“面身瘢痕,真玉日日磨之,久则自灭”。三是它能美容养颜。我国最早的中药学著作《神农本草经》就曾记叙过商朝时用天然矿物白玉石制作粉黛,以后的如《刘渭子思遗方》《肘后备遗方》《拾遗记》等都有用朱砂、琥珀、白玉等矿物制作美容原料的记载。清代慈禧太后也每日用特种白玉石做成的玉辊子在面部搓擦,惹得宫中嫔妃竞相效仿。其实慈溪的养颜就是穴位按摩,亦等同于现在一些老人如经常把玩玉器,以增加其手部灵活性,带动周身血液循环。清代的玉学大家刘大同就说过:“佩玉无论冬夏皆相宜。……玉之美德,温润而泽,足以和人之气血,养人之心性,是以君子无故玉不去身也。”[8]
人在玉与身体的亲密接触中不但获得了身体的快感,而且得到了心理的满足和精神的愉悦,进而期望这样的感觉能够永久保留并延续下去,于是就有了用玉来陪葬的做法。很多史前文明遗址的墓穴里都有用玉作为陪葬的。在6300年至4500年的大汶口文化,也出土了大量的直接附着于身体的指环、臂环、玉镯、玉管和玉珠、玉佩、玉坠等。例如,其中10号墓出土的玉环佩在死者右臂上,玉铲放在股骨上;35号男女合葬墓,玉管戴在女性颈部。胶县三里河墓葬,璿玑放在胸部,玉琀出于口中。景芝镇2号墓,玉镯戴在左腕;7号墓,玉镯戴在右腕;2号墓玉璧放在胸间,与江苏新沂县花厅村墓所放位置一致。2号墓玉坠放在胸间;1号墓玉珠放在颔下,与西夏侯墓出土位置一致。《周礼·春宫·典瑞》说道:“组圭璋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 ,以敛尸。”最著名的是1968年在河北满城发掘出的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和妻子的金缕玉衣。这是一件由2498块颜色基本一致的玉片,用金线缝制而成的华丽而华贵的衣服。甚至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还记载了殷纣王着玉衣而自焚:“登鹿台,衣其宝玉衣,赴火而死。”不管其中有多少深刻而神秘的含义,玉和肌肤天然的亲密感是毋庸置疑的。这又是后来儒家讲究“君子必佩玉”,“无故,玉不去身”。
不论是原始人还是现代人,玉对它们而言,都是由视觉的愉悦感到触觉的舒适感,进而产生其他更深刻和深远的生命意义。换言之,史前文明的玉崇拜最先是由身体引发的,因为人类的感觉就是身体的感觉,是身体在和世界交往过程中产生的感觉和意识,这也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阐述的“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只是由于人的本质的客观地层开的丰富性,主体的、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如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才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出来。”[9]由此说明,具有美学意义的“玉”由于外表的感性特质,因此能成为远古人类确证自我、认知世界和寄托意义的中介,当然更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最佳首选物品。
三、质料纯净:高洁忠贞的直觉美感
所谓白璧无瑕,瑕不掩瑜,说的是玉质料因纯洁无杂质而显得冰清玉洁,进而给人以忠贞高洁和洁净高尚的美感。以中国玉文化的代表和田玉为例,由于它形成的时间是在5亿多年前的寒武纪,凝聚成的结晶体是指玉石结构基元在空间固定而时间变迁过程中,通过有规则、高密度的三维周期排列而形成的纤维交织结构。加上青藏高原的地壳运动而引起的地质变化产生的应力和其他有机物的浸入,它就不像普通石头那样易碎而多裂纹,而是变得密实坚韧,还具有晶莹明亮和温润细腻的感性特征,更有天然的质料纯净。直观看上去,尤其是把玩在手,一种高洁忠贞的直觉美感油然而生。尽管也许它是一块顽石但是可打磨成玉石的,就像《石头记》里青梗峰下的石头变成了“宝玉”。这种直觉不仅仅是当下性的形式美感受,还应该是历史性的意蕴美感悟,即在它的背后一定蕴含着深厚而悠久的有关玉文化的神话传说,只不过它已经通过集体无意识的方式沉淀在了时间的河床深处,而人们能感受到的是浮在时间表层的纯粹洁净。
被神话后的昆仑山就是中华民族信奉的“宇宙山”。《史记·大宛列传》也记载:“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寘(阗),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在《山海经》里,“玉”出现过137处,其中127处与山结合,昆仑山孕育了两大与玉文化有关的西王母神话和女娲神话。尤其是在记载西王母的《海内北经》《大荒西经》都说西王母在“昆仑虚北”或“昆仑之丘”。还有《西三经》称西王母所居为“玉山”,她还“蓬发头戴玉胜” 。“玉胜”就是美玉做成的发饰。昆仑神山以产玉著名,因此也叫“玉山”。西王母是母系氏族部落首领,居住在昆仑山。由于昆仑山出产优质美玉,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当然会发现它和使用它。所以,“西王母蓬发头戴玉胜”,以玉显示自己的高贵。《穆天子传》里说道:“昆山为天下之良山,瑶玉之所在。”瑶玉就是优质的白玉,为所有玉石中的上品。以至于白玉成了最尊贵的专用之玉,如表示皇上尊崇的冕琉,象征皇权意志的玉玺,显示帝王身份的玉带,宫廷专用的玉几等,都是用上等的白玉精制而成的。
在先秦“以玉比德”的理念影响下,玉石已然被人们认为“吸收了天地之精华,孕天地之万物”。凡是那些美好而幸福、纯洁而坚贞的东西,都跟“玉”沾边。比如说冰清玉洁友谊、琼浆玉液的美酒、金风玉露的爱情、琼楼玉宇的建筑、金玉满堂的财富、守身如玉的贞洁、朱唇玉面的容颜等。从古至今民间男女婚恋的定情物,也是用玉做成的手镯、发簪、耳环、戒指、佩饰,《诗经》里就有“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瑶”的说法,梁朝陶弘景在《真浩》中记述了仙女萼绿华曾赠羊权金和玉的故事。蒲松龄《聊斋志异·白于玉》中写书生吴生偶入仙境与一个紫衣仙女欢好,临别时,仙女把自己所戴金腕钏送给吴生留念。玉因其色泽雅正、肌理清澈、质地坚密而象征爱情的纯真与无邪、忠诚与执着、永远与诚信,所谓以玉定情,历久弥坚。
远古的人类喜欢玉,能从它质料的纯净里感悟到高洁忠贞的意蕴,这种直觉的美感是感性直观与理性顿悟结合后,在与玉接触的审美活动中,达到超越性的神奇效果。以直觉思维为基础的原始思维,首先是对大自然经验材料的大量占有,在这个基础上再运用非逻辑的“互渗”和“类比”,在奇特的想象中使得现实世界和神灵世界合二为一。就如列维-布留尔说的“互渗”,原始人的所见所闻, 都变成了“以‘神灵的形式’出现的并被感觉的”东西了[10]。在直观中和直觉中将玉人格化,赋予有限的作为能指的“玉”以无限的具有所指的“人”的意义,以至于进入文明时代后,形成了玉所具有的坚贞品格。
还有,以玉来比喻为人的坚毅正直,如春秋齐国国相管仲曰玉有“九德”。其中能揭示玉的纯正高洁的就有“廉而不刿,行也;鲜而不垢,洁也;折而不挠,勇也;瑕适皆见,精也”等优秀的品德。《楚辞·七谏·自悲》:“厌白玉以为面兮,怀琬琰以为心。邪气入而感内兮,施玉色而外淫。”诗人屈原有着高洁的人格和凛然的正气,在这里把自己的外表和内心都与玉媲美。用玉隐喻节操的坚定不变,《后汉书·王龚传》:“以坚贞之操,违俗失众,横为谗佞所构毁。”唐韦应物《睢阳感怀》诗:“甘从锋刃毙,莫夺坚贞志。”还有玉象征品质的坚硬纯正,经久不变。《晋书·王祥传》:“西芒上土自坚贞,勿用甓石,勿起坟陇。”唐聂夷中《客有追叹后时者作诗勉之》:“荆山产美玉,石石皆坚贞。”真可谓“玉汝于成”。
四、质地坚硬:永世恒久的幻觉美感
玉之所以能成为从远古到今天人们的至爱,它的审美感觉除了前面说的亮度、温度、密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硬度。作为玉石之王的新疆和田玉的硬度甚至可达到摩氏7.5,而岫玉只有5.5。硬度高则抵抗外界打击的抗压度也强。自然界中抗压硬度最高的是黑金刚,标记为10度。其次就是和田玉,抗压硬度为9度,翡翠、红宝、蓝宝为8度,钻石、水晶、海蓝宝石为7-7.5度,像和田玉这样韧性极好的玉石在加工过程中可塑性非常强。人们可以做成各种形状并雕刻很多图案在上面。在新石器中后期,如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出土的造型精美的玉珠、玉锛、玉玦和逼肖真人的玉面饰、夸张变形的玉龙猪,具有了相当高的工艺水平。为了让这种坚硬度而产生的永久感在国家象征上发挥作用,秦始皇登上王位后,命李斯制作了一枚传国玉玺,上面有五龙交汇的图案,正面刻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篆字,以作为“皇权天授、正统合法”的信物。
记载远古玉最多的典籍是《山海经》。其中昆仑和田玉堪称“以玉为美”的代表,体现的是前历史时期生命崇拜之大美。许慎也在《说文解字》中对玉的解释是“玉,石之美者”,“象三玉之连其贯也”。为什么“三玉之连”能贯通天地人三界,其中蕴藏远古人类困惑于生命的有限。如何能在“被褐怀玉”时,在“仰观俯察”中领会宇宙的奥秘,进而企及生命的无限。遗憾的是,许慎语焉不详。然而,被誉为“上古奇书”的《山海经》却给我们提供了不少的信息。如书中“玉”字出现248次,是所有矿物质中出现最多的字。还有黄帝食玉的记载:“天地鬼神,是食是飨;君子服之,以御不祥。”吃了含玉的食物,就可以逢凶化吉,战国时期的屈原在《九章》演绎成了:“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齐光”的长生不老的观念。还有掌管生育长命百岁的西王母居住瑶池的神话、夏启操环佩璜乘龙升仙不死的神话等。
我们再以长生女神西王母为例,她为何被赋予了生命不死的意义。叶舒宪指出:“要揭开西王母的神秘面纱,除了要参悟她所在的地点‘瑶池’和她头戴的‘玉胜’之文化底蕴以外,最关键的是领会昆仑神山的秘密。……传统中国的神话地理学却一直坚信一个饮水思源的信条:河出昆仑。这个信仰的实质,是要把哺育华夏文明的母亲河之源,追溯到现实中出产和田美玉的那一座新疆南疆的高山。”[11]与玉有关的“瑶池”为西王母长生不老之地,玉做成的发饰“玉胜”,“西王母之‘戴胜’特征,莫非是出自仿生学的联想:模仿象征生命萌生的戴任鸟?……戴胜象征春天来临和生命萌生”[12]。
还有女娲补天为何要用五色的“玉石”?叶舒宪在《玉石神话信仰与华夏精神》一书中解释为“以玉为天的信仰”,因为“天是永生之神灵的居所,象征天体的玉石,不仅能够代表神明,也代表一切美好的价值和生命的永恒。”[13]还有嫦娥奔月的传说。偷吃了不死药的嫦娥,飞升到了月亮里,和吴刚相会,月宫里有一株永远也砍不断的桂树,还有一个捣药的玉兔。不也是寓意着生命的永恒吗?李商隐有诗“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表现的还是生命不死的观念。的确,在死亡率极高的洪荒时代,有什么能比活着更有价值呢?可是包括人在内的所有生命是总有一死的,于是远古人类就渴望像坚硬的玉一样生命不朽,生前“锦衣玉食”,死后“金缕玉衣”。他们坚信玉是通神的,承担巫师职责的宫中贵人和民间高人,乃至传说中具有神奇力量的英雄和神魔作用的女王、仙女就是神的代言人,他们要么衣锦玉身,要么披褐怀玉;因此被神化了的玉,是那个时期至高无上的神器和通天达地之圣物。如红山文化最著名的通神之器勾云形玉佩,它就是神权与王权的象征及通神的灵物。
同为质地坚硬的宝物,西方是钻石,中国是玉石,它们的广告词分别是“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姻缘亿万年,翡翠一线牵”。相比于钻石的人工合成,玉石则是自然天成。因此,玉就更具备了天长地久的意义。其实这种观念并不是当今商业营销的炒作,而是有着史前文明的久远传统的。这是因为玉的质地坚硬而引发出初民渴望有限的生命像玉一样能够无限地延长和永久地存在。为什么远古西王母、女娲和嫦娥三位华夏女神都和玉,尤其是和昆仑之玉有关。这种原始思维的特性就是英国文化人类学家泰勒所揭示的“万物有灵”观念,也是法国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互渗律”的体现。原始人用“以己度物”的思维方式把自然界的事物和力量予人格化,赋予它们以人的灵魂、生命和意志。这种精神意念和神灵想象的幻觉美感,实质上是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所谓的原始人类“生命一体化”观念作祟的结果。
星移斗转,沧海桑田,逐渐形成了人类史前文化史上独特的玉审美文化,远古的原始生命已经不再是茹毛饮血的动物状态,而是在“玉”所具有的隐秘而持久的导航和鼓励、熏陶和感染的神性作用下,塑造并成就了华夏民族迥异于西方民族“金枝”崇拜的爱美的中华生命,由此表现出的“中国特色”,可视为我们先民对人类审美历史的伟大贡献。这就是“玉”崇拜在完成了因审美而生命后,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因生命而审美”的伟大历程,并由此而开启了“自然的人化”,将日月星辰尽收眼底,“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把江河湖海揽入胸怀,“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将动物人格化,“侣鱼虾而友麋鹿”;把清风情绪化,“托遗响于悲风”。正如潘知常所言:“审美活动成为人类生命的最高存在方式,这也就是:因生命而审美。从而,以文化为手段的审美优化方式取代了以本能适应的生物进化方式,人的优化‘应对’取代了动物的进化‘反应’。于是,审美优化提升着人,也造就着人。”[14]这也是本文努力表达的意思,借助生命美学理论,从一个更独特而幽深的“审美”和“美感”的角度,重新揭示史前文明原始人为何对玉情有独钟的巨大的生命与文化的奥秘,从而走进人类审美的史前历史和思考原始文明的美学内容。
此时的“因生命而审美”的生命和审美,或曰生命中的审美和审美时的生命,对于远古生命美学意识的揭示,有着这样三个方面的意义。
一是超越实用而欣赏形式。在原始人使用的工具中,石头比树枝更方便而原初,它可就地取材而信手拈来、随手而用,近可砍砸树木,远可投掷野兽。而同属于石头的玉石,和一般的石头相比,它既有坚硬和锋利的工具性价值,也有明亮和温润的审美性价值。然而,它最初一定是作为工具而具有实用性价值的。但由于它比一般的石器更耐用好用,加之又特别的稀少,因此它逐渐从工具的价值范畴中脱颖而出而具有了独立的价值。著名学者刘骁纯教授在《从动物快感到人的美感》书里认为:“对贵重材料的崇尚和对质地美的狂热追求,它使越难找到、越难加工的材料越有超凡价值。它促使人们不辞千辛万苦找矿、不惜消耗巨大的劳动去采石和加工极为坚硬的石料,并最终导致玉石工艺的产生。”[15]如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器,多达300多件,除了一百余件玉钺、玉斧、玉戈等,装饰性的玉环、玉瑗、玉璜、玉珠等占了多数。时间更早的黑龙江小南山遗址出土的玉器,也是如此。专家们认为那些玉质的钺、斧、戈已经不是真正的劳动工具了,而成了礼仪用器。工具性的玉钺、玉锛,以及玉环、玉瑗、玉璜、玉珠都被打磨得外形工整、线条流畅和表面平滑,加上玉本身的色泽鲜亮,原始人已经超越实用而开始欣赏它的形式美了。试想,没有经年累月积聚起来的“因审美”而成就的人类“生命”,能有此情此景一代又一代积淀下来的爱美本能的“因生命”而“审美”吗?
二是超越快感而进入美感。通常的审美心理活动是一个由快感到美感的递进过程,美感揭示的文明生命意义毋庸置疑,而快感蕴含的自然生命意义也是毋庸讳言,但是经过数千年“玉成”后的生命,已经成了能够审美的生命,进而具有超生物意义的快感,即有了对玉表面的凹凸、粗细、冷暖、轻重和滑涩等与触觉有关的前美感;这体现在玉在同人的接触过程中,能带来并产生舒适的手感和温润的体感、醒目的光感和密实的质感、便捷的好感和沉稳的实感,这种感觉所折射出的人性,就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论述的“人的感觉与感觉的人性”。其实,这明显地已经超越快感而进入了美感,我国当代著名珠宝美学专家沈理达女士在论述“宝石肌理的触觉美”时,科学地阐述了这种包含快感的美感,“翡翠、和田玉等多晶矿物宝石,由于晶体是由很多具有相同排列方式但位相不同的小晶体组成,一般透明度较低;玻璃光泽到油脂光泽,抛光后光滑感相对较高;又带有一种与肤质相近的温润感,盘玩愈久,表面肌理也会更光亮平滑,似乎沾染了人的温度与气息,更令人喜爱。”[16]这种美感对于远古的人而言,是包含并超越快感的美感,正如墨子说的那样:“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超越实用而审美的生命,说明能够欣赏玉的原始人在一定意义上,已经成为文明人了。
三是,超越死亡而走向信仰。尽管文明时代玉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诸如吉祥、富贵、和美、平安等意义,但是,早期玉崇拜所承担的最伟大而神圣的意义却是长生不老的祈盼和生命不死的祈祷,寄托着人生永恒的信仰,这也是叶舒宪在《玉石里的中国》和《玉石信仰与华夏精神》等著述里多次论及的“玉代表永生不死”。不论是上海崧泽遗址,还是安徽凌家滩遗址,也还是山东大汶口遗址,墓葬主人公口中都含有玉石。汉代曾侯乙墓中的人居然含了21枚各种动物造型的玉器,借助动物的生命来延伸人的生命,渴望能够永远像生前那样衣锦食玉。还有,为什么玉与昆仑山有着不解之缘,并且远古中国两大女神西王母和女娲都和玉及昆仑山有关?在《山海经·西山经》里有43处写到了玉。及至今日,那些美好的事物都爱用玉来形容,如“玉叶”“玉体”“玉人”“玉面”等。叶舒宪解释道:“作为生物体的生命之始源,都可以被华夏神话思维追溯到承载着神力和正能量的玉石。换言之,文化符号的编码是分层级展开的:先有昆仑山和田玉的实物,催生出昆仑瑶池的仙界想象,再有人格化的掌握不死秘方的西王母想象,最后才有西王母蟠桃会的想象。总之都指向一个神话理想:生命的永生不死。”[17]以至于美丽的死亡叫“玉殒”,崇高的牺牲叫“玉碎”,埋葬死人的地方叫“玉山”,亡灵回归的故乡叫“玉里”。当把这种永生信仰赋予神灵的意义后,就是《说文解字》“灵,灵巫也,以玉事神。”更有最近发掘的三星堆出土的玉器,都同祭祀活动有关,是玉死亡崇拜或玉文化信仰的证明。
玉,远古的精灵,华夏的瑰宝,从雪山走来,从域中走来,从中国的东南西北走来,带着晶莹的光芒,带来远古的呼唤,回荡清澈的声音,诉说着古老的信仰,祈盼着生命的永远,更寄托着人生的超越。其中所蕴藏的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是什么呢?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会长徐德明先生在为沈达理撰写的、地质出版社2019年出版的《珠宝美学》一书的“代序”里说道:“玉,深刻体现了中国珠宝的核心文化价值,那就是:永恒的财富,永远的纪念,永久的珍藏,永生的安宁。也就是说,珠宝虽属万物,与人执念成‘一’,但使‘物我合一’,超然‘心外无物’,力图从瞬息万变的宇宙中,体悟到亘古如一的‘真相’,继而获得适意与安慰,最终实现生命的超越。”
毛泽东有诗云:“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正是这历经数千年磋磨的玉石——集天地之精华、凝日月之精粹、寓万物之精英,渴望生命永久的梦幻,不但开启了生命美学史前时代的温柔实践,而且留下了中华民族生命美感的远古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