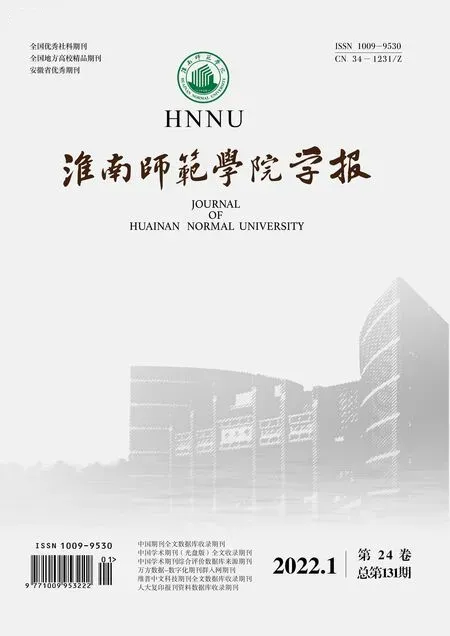孟子“《诗》亡而《春秋》作”说的文学史意义
——论杜诗“诗史”说的思想渊源及其生成的学术逻辑
2022-03-17吴怀东胡晓博
吴怀东,胡晓博
(安徽大学 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中国文化高度重视历史的经验,史学在中国古代异常发达①,连带而及出现了“诗史”的概念,虽然被后代称为“诗史”的诗人有多人,但均未获得后代普遍的认同,至今“诗史”几乎只是杜甫诗歌独享的誉称②。学术界对于杜诗“诗史”说的内涵、演变已有比较深入的研讨并形成了某些共识③,然而,由于学术界对这个概念的“前史”缺乏深入的讨论,导致对“诗史”观念形成的根本依据、生成源头与思想资源缺少准确认识。 我们试图回到“诗”“史”的源头即《诗经》与《春秋》及其关系,考察这个复杂的文化观念与深远的思想传统,并进一步讨论其与杜诗“诗史”说的关联。
一
关于《诗经》与《春秋》的关系,最早的资料即《孟子·离娄下》中所记载孟子的一段描述和评论: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 ”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1](P267)
孟子对《诗》有系统性认识,这段话尤为知名。对于孟子这段话,以往的研究者比较关注的是其史学以及经学史上的意义,其被认为是对孔子与《春秋》关系以及《春秋》传统之内涵的最早描述,其实,这则材料也体现了中国最早的对诗、史及其关系的理解。 蒙文通认为,孟子此说揭示了真正史书文体的生成,具有史学功能却属于文学的《诗经》在公元前七、八世纪之际结束而大约在公元前八、九世纪《春秋》类的史书出现[2]。 然而,孟子此说背后实涉及深刻而复杂的制度变迁与思想传统的建构。明代学者焦竑认为,“诗亡”与周天子巡狩观诗制度终结有关,“窃意《王制》有曰:‘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自昭王胶楚泽之舟,穆王回徐方之驭,而巡狩绝迹,诸侯岂复有陈诗之事哉?民风之善恶既不得知,其见于《三百篇》者,又多东迁以后之诗,无乃得于乐工之所传诵而已。至夫子时,传诵者又不可得,益不足以尽著诸国民风之善恶,然后因鲁史以备载诸国之行事, 不待褒贬而而善恶自明,故《诗》与《春秋》体异而用则同”(《焦氏笔乘》卷四)。 清代学者章学诚说:“孟子曰……盖言王化之不行也,推原《春秋》之用也。”(《文史通义·内篇·书教上》)按照钱穆先生的解读,“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揭示了从西周“宣王以后”到“平王东迁”建立东周这段政治史上的重大变化:“周王室是天下之共主,周王是一位天子,一位王者,每到冬天,他所封出的四方诸侯都得跑到中央来共朝周天子,而周天子在那时祭其祖先,更主要的是祭文王,许多诸侯一同助祭,就在这庙里举行祭祀时唱诗、舞蹈,唱的便是周文王一生的历史功绩”。可是,随着周王影响力下降,诸侯势力扩张,就不再到中央朝廷来拜祭文王,而周王朝分派的史官到各诸侯国,“义不臣于诸侯”, 如实记录诸侯国发生的重要事件[3](P15-16),换言之,“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反映出一种分封制度的颓败,也正因为周王朝根本制度的破坏,孔子才起而叙《春秋》,寄托其“尊王攘夷”之“微言大义”和政治理想④,因此,当今学者提出“《诗经》文本的形成与传播史, 实质上从另一侧面展现了周代礼乐制度建立、 发展、 完善乃至走向崩溃的兴衰历史”[4](P2),这里便涉及《诗经》所收录诗歌的产生或“生产”过程的问题。 《诗经》中“颂”诗,所咏就是民族历史。 清代史学家顾炎武解释说:“《二南》 也,《豳》也,《小、大雅》也,皆西周之诗也,至于幽王而止,其余十二《国风》,则东周之诗也。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西周之诗亡也。诗亡而列国之事迹不可得而见,于是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出焉。 是之谓《诗》亡然后《春秋》作也。 ”(《日知录》卷三)根据马银琴等当代学者的研究,“诗”本来是《国风》收录作品的专名,“只是讽谏怨刺之辞”[4](P15),其与产生于西周早期的配乐可唱、被称为“歌”的“雅”“颂”不同,但二者在西周末期即周厉王时期都被写定为同样的文本形态,“诗”“歌”概念之别因此逐渐模糊。被朱自清称为中国诗学“开山的纲领”(《诗言志辨》)产生于“诗”“歌”两种类型的诗歌合流和两个专名合一的这个特定历史节点, 如同钱志熙所说,“诗言志”这个概念的产生实际上基于“国家政教体系成立、诗乐舞综合艺术形态之发达、伦理观念的成熟这样三个方面的事实”[5],换言之,《诗经》的“生产”与编辑、传播具有鲜明的现实政治性,质言之,从使用的角度看,《诗经》被赋予了鲜明而突出的政治性。
《诗经》和《春秋》之所以能够承担如此重大的政治使命,显然与其特定的内容有关。 《春秋》具有明确的政治性自不待言,而《诗经》是否具有相同的内容或性质?钱穆先生就说,“古人之史也不完全在《书》(按,指《尚书》)里,而有在《诗》里的。古诗三百首,其中历史事迹特别多。远溯周代开始,后稷公刘一路到文王,在《诗经》的《大雅》里整整十篇十篇地详细描述,反复歌诵,这些都是历史。 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历史,或许比《西周书》里的更重要”[3](P18-19)。可见,在《诗经》中,这些内容其实就是历史的记载,从而在实际政治制度中承担着明确的政治功能,换言之,这里存在着一种自觉的解读逻辑:历史就是政治,而诗歌就是历史,诗歌也因此就是政治。
这里还涉及另外一个重大的学术观念——“经”。 众所周知,《春秋》《诗三百》乃至《尚书》等孔子之前产生的文字作品,被孔子及其儒家学派奉为“经典”。后代学者大多认为其中的《春秋》属于史书而其他的并非史书,但晚明王阳明认为:“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传习录·徐爱录》)。后来清代学者章学诚继承并强调了这个观点并产生更大的思想影响:“六经皆史。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文史通义·易教上》)。 这种认识非常深刻⑤。他们认为《春秋》之外的其他典籍也属于史,不过不是史书,而属于史料,是对政治活动的如实记录, 它们之所以被视作经典是因为其中包含着大道。 古代关乎“史”的概念中其实包含着两个层次的内涵:史迹与史料、史书与史学。 在这种学术价值观和学术体系中,史学即经学,而史学、经学都通向政治,“就五经之本意而言,原不在叙事,只是记述具有创制立法意义的要紧之事, 即载道之事”“六经皆史,要义在于事与道(或曰理)两者为一体,道理为体,事情为用,两者有着互相构成的关系”[6](P4-5),这其实建构了中国史学关联政治的史学传统和中国文学批评反映历史、反映政治的政教文学传统⑥。
二
从人类认知规律来看, 细分和分类是总体趋势。从社会分工的角度看,春秋以来,文字逐渐变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分工。 《论语·先进》中记载孔子弟子“四科十哲”:“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 政事,冉有、季路。 文学,子游、子夏”,此处之“文学”所指正是以文字为媒介的工作。同样是文字文本,“六经” 之内也还有二级区分,孔子说过:“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论语·雍也》)孔子所论虽然不是文字表达问题,但“文”“史”概念的区分显然包含后代所热衷讨论的作为两种文体和思维类型的文、史分合问题。
从本源看,文学与历史的区别很明显:文学是作家生活的书写和情感的表达, 而历史更强调对社会与政治的关怀, 两者在表达方面也存在明显不同⑦。 实际上,随着人类社会生活渐趋复杂、认识的更加深化,“诗”与“史”作为不同的社会文化活动方式和文体形态,自先秦以来总体的发展趋势是渐行渐远,直接体现在书籍分类和图书编目之中。 西汉刘歆汇录的中国第一部官修目录和第一部目录学著作《七略》将传世之书籍分为六类,即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这种分类被班固《汉书》所继承。 汉末曹丕《典论·论文》提出“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汉代以来,随着社会文化活动的日益丰富和著述的增多,文体间的界限区分显得十分必要和明显⑧,这既反映在图书编纂的分类和学术的分野(沈约《宋书·雷次宗传》记载元嘉十五年分立儒学、玄学、史学和“文学”四科),更直接表现为文论家对文体内在规范越来越清晰的辨析(如《诗品》、《文心雕龙》、《文选》等),“文之于史,较然异辙”(《史通·核才》)。章学诚说:“自东京以还,讫于魏晋,传记皆分史部,论撰沿袭子流,各有成编,未尝散著。 惟是骚赋变体,碑诔杂流,铭颂连珠之伦,七林答问之属,凡在辞流,皆标文号,于是始以属辞称文,而《文苑》《文选》所由撰辑。 彼时所谓文者,大抵别于经传子史,通于诗赋韵言。 ”(《文史通义·杂说下》)初唐史学家刘知几正是在严文、史之防的基础上讨论史书诸文体的写作规范⑨,虽然他认可“文之将史”,但反对南朝以来史书对文学的过度学习,批评说“树理者多以诡妄为本,饰辞者务以淫丽为宗”(《史通·载文》),还批评说:“大唐修《晋书》,作者皆当代词人,远弃史、班,近宗徐、庾。 夫以饰彼轻薄之句,而编为史籍之文,无异加粉黛于壮夫,服绮纨于高士者矣”(《史通·论赞》)。此外,他还赞美《左传》之文对文学手法矜持的学习:“或腴辞润简牍, 或美句入咏歌,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将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史通?杂说上》)。应该说,对文、史分野的刻意强调,是当时对两类文体特点认识的深化, 也有力地促进两种文类的发展⑩。 由此可见,在杜甫之前,诗歌与历史的边界渐趋清晰、严格。
杜甫是否强调诗、史之别?众所周知,杜甫诗歌也和其他咏诗史一样咏叹前代、 前朝历史事实,显然,这不构成杜甫诗歌的独特性。 杜甫具有很强的历史感,其核心的内涵是历史的无限性与个人生命有限性的矛盾,如其诗曰:“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旅夜书怀》)、“百年歌自苦”(《南征》) 等,不过,这种历史感与史学书写意识是两回事。 作为生活在刘知几之后的诗人,杜甫对文、史边界的理解十分明确、清晰,如其云“文包旧史善”(《八哀诗·故秘书少监武功苏公源明》)、“十五富文史”(《送李校书二十六韵》),他反复赞美秉笔直书、实录的史臣书写,“直笔在史臣”(《八哀诗·故司徒李公光弼》)、“波涛良史笔” (《八哀诗·故右仆射相国张公九龄》)、“不愧史臣词”(《哭李常侍峄二首》之二)等。从有限的杜诗用例中还可以观察到,杜甫史学意识的核心就是“直书”,并未涉及史学其他具体问题。虽然杜甫感叹过“文章一小技,于道未为尊”(《贻华阳柳少府》),但是,生当盛唐诗歌大盛之际,杜甫一生甘作官员诗人而不是史学家的选择是自觉而强烈的, 他说:“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吾人诗家流”(《同元使君舂陵行》), 他对自己的诗歌才华颇为自负:“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 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 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 ”(《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通过“鼓吹六经,先鸣诸子”(《进雕赋表》),以实现“致君尧舜上, 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人生理想。 杜甫早年有诗谓“独立苍茫自咏诗”(《乐游园歌》),后来在《发秦州》中的“大哉乾坤内,吾道长悠悠”两句一语双关,都包含着在历史的长河和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坚持自己信念和诗歌道路之意。这也是盛唐时代诗人普遍的人生道路选择和人格心态⑪。 可见,杜甫进行诗歌创作时并没有明确的历史书写意识。
杜甫诗歌毕竟是对自己时代生活的呈现,在杜甫生前、身后直到孟启之前,是否有人从诗、史会通的角度评价杜诗;对其他诗人是否有类似阐发,厘清这些问题很有必要。 从现有文献看,在杜甫生前,就有人赞美其诗, 并在身后逐步获得与李白比肩的崇高地位,如“大名诗独步”(韦迢《潭州留别杜员外院长》)、“新诗海内流传遍”(郭受《杜员外兄垂示诗因作此寄上》)、“黄绢词”(任华《杂言寄杜拾遗》)、“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韩愈《调张籍》)等,却没有发现以“诗史”或类似概念评价杜甫的文献证据⑫。
三
事实上,从杜甫诗歌内容看,他对诗歌与历史的分野与边界是充分自觉的。但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为什么在这个背景上人们却“逆向而行”、用“诗史”来称誉杜诗;其渊源与深意何在。
文学与历史并非 “水火不容”, 因为从根本上说,文学所叙也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从文学中可以看到社会, 从个体经历中也可以看到时代与社会的缩影。从诗歌中寻找历史的真实性,这只是后代人阅读的视角,洪业就说“杜甫的同时代人并不需要通过他的诗歌去了解他们时代的风俗和事件”[7](P8),只有时过境迁,杜甫诗歌对当时社会状况的呈现才会被视作具有历史的意义而受到关注⑬。 但是,“诗史”说的内涵显然不在于此。 一般认为,最早提出“诗史”概念的是晚唐孟启,其在《本事诗·高逸第三》借评论李白,赞誉杜诗具有“诗史”的品质:“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孟启所言“诗史”之内涵却不同于宋代以来流行的理解⑭,但是,孟启发明或沿用“诗史”的概念却有着深刻的背景,这反映了中唐以来《春秋》学以及先秦儒家文学思想复兴这一社会思潮与文化趋势。
晚唐时期, 孟启能够从诗史关系角度认识杜诗,固然有时过境迁的这个基础条件,但主要还是出自其自觉的学术意识。孟启除了引用“诗史”概念之外,其《本事诗》中关注文、史会通的撰述意图的表述极其明确。 据孟启《本事诗》自序,此书完成于唐僖宗光启二年(886 年)十一月,正是中唐之后。据孟启为其妻所撰墓志,他自述“读书为文,举进士,久不得第,故于道艺以不试自工,常以理乱兴亡为己任”,后终于及第[8](P1-17),其生平经历和文化活动都进入当时主流。孟启这部书被后代学者认为乃诗话之源头,而其诗言情理论、“四始”之说、“为小序以引之”的体例等,证明其远源于儒家尊奉的经学文献《诗序》及《韩诗外传》,从中可见经学的巨大影响。关注诗歌与现实、特别是政治的联系,是汉代《诗经》解释学、诗教的重要理论;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文学活动的丰富,有关诗歌创作活动的记载也逐渐丰富,如《世说新语·文学》;而到了盛唐,吴兢著《乐府古题要解》研究乐府诗题,亦往往推求诗“本事”。孟启《本事诗》继承此前的诗学传统,不过,其受中唐《春秋》学及史学兴盛之影响更加突出⑮。《本事诗·序》介绍此书编著之意图云:“诗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其间触事兴咏,尤所钟情者。不有发挥,孰明厥义? 因采为《本事诗》。 ”孟启喜好诗歌和诗人,此书编写目的就是介绍诗人及其诗歌的“本事”,以增加对诗歌的理解、对诗人精神魅力的感悟。书名“本事”及前述对杜甫的评价中所使用的“推见至隐”等概念,皆来自史书之祖《春秋》以及中唐勃兴的《春秋》学。 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太史公”评论云:“《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之以显。 ”[9](P3037)《春秋》是“本事”,《左传》则是显示《春秋》的隐讳。 《汉书·艺文志》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 《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榖梁》、《邹》、《夹》之传。 四家之中,《公羊》、《榖梁》立于学官,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 。 ”[10](P74)东汉桓谭《新论·正经第九》亦围绕《春秋》及《左传》立说:“《左氏传》遭战国寝废。 后百余年,鲁人穀梁赤为《春秋》,残略多有遗失;又有齐人公羊高,缘经文作传,弥离其本事矣。 ”[11](P36)我们因此可以说,孟启对“本事”的强调以及“诗史”概念的引用,正是继承儒家经典《春秋》之传统。
今天流行的理解则是杜甫以“三吏三别”为代表的诗歌反映了“时事”——安史之乱及其对唐王朝的严重破坏,这种观念的建立是由《新唐书·杜甫传赞》首开其端:“(杜)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 其实,白居易《与元九书》按照“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标准审视唐代诗史, 唐诗史呈现出完全不同的一种面貌:“唐兴二百年,其间诗人不可胜数。 所可举者,陈子昂有《感遇》诗二十首,鲍防《感兴》诗十五篇。 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迨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 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 至于贯穿古今,覙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焉。然撮其《新安》《石壕》《潼关吏》《芦子关》《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首。杜尚如此,况不迨杜者乎?”(《新唐书·杜甫传赞》)正是将“诗史”概念与“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结合起来,赋予“诗史”全新的内涵。“诗”“史”从文体角度看完全不同,而“诗史”中“史”的概念,应该包括两个层面:第一,纪实性和叙事性,这个内涵不必讨论;第二,政治性,就是用文学反映当代重大历史事件,表达作者对社会的关怀和参与。
从更广泛的视野来看,安史之乱导致大唐盛世的结束, 催生了中唐人在对盛世的追怀中不断反思、总结诗歌发展的经验,换言之,政治激发了文学的反省与革新,韩愈、柳宗元发动的古文运动⑯和元稹、白居易示范的新乐府运动不谋而合,都是强调复古,强调回归儒家政教文学传统,强调文学活动的伦理性、政治性⑰,而这正是中国文学活动生成期形成的“胎记”或曰“基因”——“《诗》亡而《春秋》作”发生作用之生动表现。 杜诗被定性为“诗史”,既是“《诗》亡而《春秋》作”古老“基因”作用之结果,也是唐宋之际儒学复兴宏大文化运动之重要诗学指征⑱。
注 释:
①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还从文化学角度提出中国文化是“史官文化”(《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人民出版社,1949 年),所论已不是具体、微观的史学与史书文体及其表达, 而是中国文化价值观与思维方式的根本特点。 最近有学者指出,相对于古希腊以哲学为本、犹太文明以宗教为本、 古罗马和现代西方国家- 法律为本,“中国有个以历史为本的精神世界”(参见赵汀阳 《历史·渔樵·山水》第 1 页,三联书店,2019 年)。
②也有其他诗人诗作被赞誉为“诗史”,比如李白、汪元量、文天祥、黄道周、吴伟业、钱谦益等,但这些观点在批评史上没有形成共识,参见许德楠《“诗史”桂冠的排行榜及理念定位》(《南京社会科学》2001 年第 8 期)。 按, 裴斐认为:“至于‘当时号为诗史’,一如刘昫所说‘天宝末甫与李白齐名’,并无文献依据,实为史家稗官惯用的假托之词”(《唐宋杜学四大观点述评》,载《杜甫研究学刊》1990 年第4 期),目前还没有发现孟启之前出现“诗史”概念的证据,孟启所谓“当时”确实属于“史家稗官惯用的假托之词”,但孟启说“当时”而非自创,表明他对这个概念内涵具有共识性的体认。
③类似的讨论甚多,其中张晖《中国“诗史”传统》(修订版,三联书店,2016 年)对唐代以来“诗史”概念的内涵与演变有深入、系统梳理。
④历代学者围绕孔子是否“修《春秋》”产生了很多争论,这里暂且不论。
⑤杨国荣说:“历史生成于人所作之‘事’。 离开了‘事’的多样展开,历史将流于抽象和空洞,脱离了具体的‘事’,历史主体也将虚幻化。”(《“事”与“史”》,载《学术月刊》2019年第1 期)所述正是章学诚的意思。
⑥南帆说:“当 ‘诗史’被解释为‘以诗存史’、‘以诗证史’或者‘以诗注史’的时候,前者仅仅是一种工具或者补充资料,后者才是真正的目的。 ”(《文学批评中“历史”的概念》,载《中国社会科学》2019 年第3 期)这也是中国古典学术强调“文史不分家”的意图所在。
⑦近代学人主要是从两种不同的学术领域甚至文体立论,陈寅恪“诗史互证”的成功实践更广受世人推崇,而钱钟书在 《谈艺录》、《宋诗选注》、《管锥编》 等著作中发掘了“史蕴诗心”的文化现象,其在诗史会通中特别强调诗的独特性。后现代史学也强调史书的“诗性”特点,参见怀特海著《元史学》(陈新译,译林出版社2013 年)和张进《历史诗学通论》(暨南大学出版社,2013 年)。
⑧参见逯耀东《魏晋史学思想与社会基础》(中华书局,2010年)、 胡宝国 《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商务印书馆,2003年)、郝润华《六朝史籍与史学》(中华书局,2005 年)。
⑨刘知几《史通》论史学往往兼及文学,其实并不是认可“史之将文”,而只是着眼于史书也是文章而已,他们实际上是特别强调史书写作与文学写作的界限与分野。 而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提出著名的“六经皆史”命题,弥纶文史、经史,强调“古无经史之分” (《丙辰劄记》,《章氏遗书》外篇三)、“文史不在道外”(《姑孰夏课甲编小引》,《章氏遗书》卷二十九,外集二),显然,意不在讨论文、史分野,而是论哲学与思想之“道”问题,其观点是对顾炎武、戴震“经学即理学” 的积极回应 (详论参见余英时 《论戴震与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内篇五之论述,三联书店,2012 年)。
⑩诗歌或文学与历史、哲学的异同问题,在古希腊学者中就引起了讨论,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了“驱逐诗人”的思想, 柏拉图既是哲学家又是政治家, 他所构想的理想国,应是一个“哲王之治”的理想国家。他认为只有哲学才能为我们分辨什么东西对社会和个人是正义的。 除非是真正的哲学家获得政治权力或出于某种神迹, 政治家成了真正的哲学家兼王者,否则人类就不会有好日子过。这就是西方著名的哲人王理论的雏形。 “从荷马开始,诗人这一族群都是美德影像的模仿者, 或是他们 ‘人为制造的’其他事物的影像的模仿者。 他们完全没有把握真相,而是让我们看到事物的影子。 ”在《法篇》中他更明确地讲:“我们应当用真理作为衡量的标准, 无论对真理作何种解释,而不要用其他东西作标准,尤其是诗歌中的那种标准。 ” 柏拉图认为,人的灵魂由两部分构成:一是灵魂的最高部分,这是理性部分,人只有靠理性,才能真正把握可知世界,领会和认识到正义、幸福、真、善、美的“相”;另一个是灵魂的低劣部分,这是一些非理性的成分。因此理想国的公民必须以理性控制情感, 以便使自己的生活更美好、更幸福。 而远离诗歌是实现这点的第一部。 柏拉图所论,涉及诗歌与理性问题。 而柏拉图的学生、另一位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则在诗歌与历史之间, 肯定诗歌:“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地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而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所谓‘有普遍性的事’,指某一种人,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会说的话,会做的事,诗要首先追求这个目的,然后才给人起名字;至于‘个别的事’则是指亚尔西巴德所做的事或所遭遇的事。 ”
⑪做史学家虽不是杜甫和盛唐时代文人的理想, 前代史书的史料素材、 史学精神对他们的人生理念和文学创作却还是产生了深刻影响,如郝润华《论杜诗的写实性与〈史记〉实录精神》(《西北大学学报》2010 年第 1 期)所论,不过,我认为在写作手法层面并没有直接继承或体现,而孟启对杜诗“诗史”特点的发现和强调之内涵主要恰恰在这个层面。
⑫今本郑处诲《明皇杂录》、康骈《剧谈录》述唐史事,引杜诗作证。 据华文轩《杜甫卷》(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编者所考,其所引杜诗都是宋人方深道转引时所增(第24 页。中华书局,1964 年)。 说亦见张忠纲先生《杜甫诗话校注五种》(书目文献出版社,1994 年)。
⑬对于杜甫“诗史”的内涵,宋人胡宗愈有一个与众不同的解释:“先生以诗鸣于唐,凡出处、动息劳佚、悲欢忧乐、忠愤感激、好贤恶恶,一见于诗,诗之可以知其世。 学士大夫谓之诗史。 ”(《成都草堂诗碑序》)刘宁归纳为“读者可以从诗人的‘一人之诗’了解‘一代之史’”(《杜甫五古的艺术格局与杜诗“诗史”品质》,载《文学遗产》2009 年第 3 期)。
⑭ 拙文《〈本事诗〉“诗史”说与中晚唐学术脉动》,载《文史哲》2018 年第 4 期。
⑮关于中唐《春秋》学,近年学术界有深入探讨。陈弱水发现中唐人“最受偏爱的对象仍然是《春秋》”(《柳宗元与唐代思想变迁》第 145 页,广西师大出版社,2009 年),查屏球也说“元和之后,《春秋》学已成为一个学术中心”(《唐学与唐诗》第 39 页,商务印书馆,2009 年)。 另参杨世文《经学的转折: 啖助、赵匡、陆淳的新春秋学》(载《孔子研究》1996 年第 3 期)、杨世文《啖助学派通论》(载《中国史研究》1996 年年第 3 期)、葛焕礼《论啖助、赵匡和陆淳〈春秋〉学的学术转型意义》(载《文史哲》2005 年第 5 期)、高淑君《陆淳对啖助、赵匡〈春秋〉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载《孔子研究》2012 年第 5 期)等文。
⑯韩愈将原来文字学意义上的“古文”改变为一种普遍认可的文章意义上的“古文”(《题欧阳生哀辞后》。详论参见房本文《唐代古文运动发微》,安徽大学出版社,2018 年),也是儒家政教文学传统回归的表现。
⑰韩经太《传统“诗史”说的阐释意向》(载《中国社会科学》1999 年第3 期)注意到“诗史”说以及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政治的关联,却没有强调这其实是对一个古老政教文学传统的回归。
⑱从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进程看, 日本学者铃木虎雄提出的唐宋转型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解释框架, 而从中国思想史发展的总体脉络来看, 中唐开始了另一个影响深远的大转折,儒家思想传统出现回归,“古文”与“诗史”说出现姑且不论,宋代的道学与韩愈“原道”思想的内在关联已属于常识,在此不必赘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