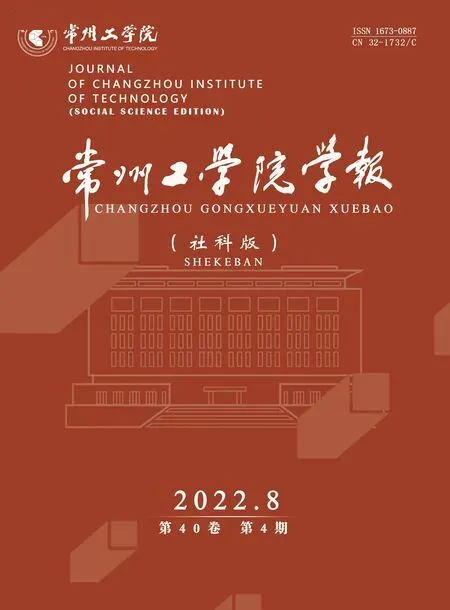鲁迅《伤逝》与森鸥外《舞姬》的比较研究
2022-03-17万宇翔吴雨平
万宇翔,吴雨平
(苏州大学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青年男女追求个性解放与爱情自由”的主题向来是各国文学作品着重表现的对象。鲁迅与森鸥外分别是中国现代与日本近代的文坛巨擘,《伤逝》与《舞姬》展现了作家对这一主题的思考。在两位作家笔下,青年男女的爱情皆由于男主人公对现实的投降最终走向破灭,从而呈现出“由必然的反抗走向必然的投降”的规律。受到早年留日学习的影响,鲁迅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森鸥外的影响。这种影响既使得《伤逝》与《舞姬》在情节、叙述手法等方面展现出相似性,又构建了两者进行比较研究的材料事实基础。
一、《伤逝》与《舞姬》的渊源
比较文学研究强调研究对象之间的事实联系。正如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学者梵·第根在《比较文学论》中指出的,“真正的‘比较文学’的特征,正如一切历史科学的特质一样,是把尽可能多的来源不同的事实采纳在一起,以便充分地把每一个事实加以解释;是扩大认识的基础,以便找到尽可能多的种种结果的原因”[1]。所以,我们在对《伤逝》与《舞姬》进行比较研究之前,需要先讨论两者之间是否存在事实联系。
鲁迅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三月留学日本。在留学期间,他阅读了大量日本文学作品。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鲁迅真实地记录了自己对夏目漱石和森鸥外两位日本作家作品的青睐:“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就特别多。也曾热心的搜求印度、埃及的作品,但是得不到。记得当时最爱看的作者,是俄国的果戈理(N.Gogol)和波兰的显克微支(H.Sienkiewitz)。日本的,是夏目漱石和森鸥外。”[2]那么,作为文坛前辈森鸥外的早期浪漫主义代表作《舞姬》,鲁迅有没有读过呢?我们认为,鲁迅一定读过森鸥外的《舞姬》。具体原因有以下两点:
首先,两部作品本身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这些相似性主要表现在小说情节线索、叙述手法、艺术特色等方面。如在小说情节上,两部作品都以男女主人翁从自由相爱,到为爱情积极反抗封建守旧思想的压迫,再到两位男主人公皆无法承受生活与社会压力走向投降,最终爱情破灭为线索;在叙述手法上,两位作家都采用了男主人公第一视角下的忏悔性叙述,同时,这种忏悔性的叙述皆以现在的“我”在痛苦中回望过去的时光开始,并以“我”在无奈中面向未来结束;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两部作品皆通过心灵自剖的方式表现其内心世界及感情的变化过程;在艺术上,两部作品都洋溢着浓烈的抒情色彩。这些相似之处使人难以相信鲁迅在创作《伤逝》时并未受到《舞姬》的影响。杉野元子在《悔恨与悲哀的手记——鲁迅的〈伤逝〉与森鸥外的〈舞姬〉》中从“从周围人的干扰逃避出来的安静房间”“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孤立的同居生活”“恋爱同居后被免职及之后转为文书业”等方面指出这两部作品有“许多相似之处”。她说:“这样的相似应该不是单纯的偶然,而是在鲁迅看过《舞姬》之后产生的影响关系。”[3]3所以,我们认为鲁迅应该是看过《舞姬》后,整合自己的生活体验,并结合中国的具体时代特征进而创作了《伤逝》。当然,鲁迅的《伤逝》也表现出了与《舞姬》的不同之处,展示出了鲁迅在特定时代下对“青年男女追求个性解放与爱情自由”主题的独立思考。
其次,就鲁迅的翻译活动来看,他应该读过《舞姬》。正如上文所言,鲁迅在1933年的随笔《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已经明确地提到森鸥外并对其作品青眼有加。1923年,鲁迅与周作人在北京共同编译了《现代日本小说集》。此书收录了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的短篇小说及森鸥外的《沉默之塔》《游戏》,并且在同书《附录·关于作者的简介》有关森鸥外的那一节中,周氏兄弟也对其进行了简单介绍。所以,就鲁迅的翻译活动而言,可以得知其应该是相当熟悉森鸥外的。既然如此熟悉,怎么可能不阅读其早期浪漫主义代表作呢?尽管从目前的鲁迅的日记与藏书目录中无法获得鲁迅读过《舞姬》的确凿证据,但我们可以推断鲁迅应该是相当熟悉森鸥外并读过《舞姬》的。日本学者杉野元子就此问题也发表过见解:“无法确认鲁迅是否读过《舞姬》,但作为森鸥外作品的爱好者、翻译者的鲁迅不应该没有看过森鸥外的代表作《舞姬》。”[3]3
总之,鲁迅应该是阅读过森鸥外的《舞姬》进而结合自身生活实际与中国时代特征创作了《伤逝》,两者之间存在着事实联系,《伤逝》是在《舞姬》影响下诞生的富有自身特点的小说,这点是无可争议的。
二、《伤逝》与《舞姬》之异同点
正如上文所述,《伤逝》与《舞姬》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但亦存在着不同。通过对两部作品异同点的具体分析,两部跨时代的作品被“打通”,使我们从中既可以看到不同时空中青年男女追求个性解放与爱情自由的天然愿望以及两位文豪对青年人爱情问题的态度,又可以发掘出两位作家对这一题材进行处理时所独运的匠心。
首先,两部作品的情节颇为相似。《伤逝》与《舞姬》在情节上都以男女主人翁“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自由恋爱为故事的开始。从《伤逝》中子君对涓生坚决地表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4]115到《舞姬》中太田丰太郎热烈地感叹“总之,从此刻起,我对爱丽丝的爱意骤然浓烈,终于变得难舍难分”[5]32。爱情给予了两部作品中两对“新人”敢于反抗生活的动力。但故事的情节很快就由于两对“新人”皆无法承受社会与生活的压力而急转直下。《伤逝》中涓生不满于子君的种种做法却不愿明说,只是选择外出躲避;《舞姬》中丰太郎纠结于自己的回国之路与名誉而内心痛苦万分,爱情此时变得如蝉翼般脆弱。最终,两部作品皆在男主人公的投降中走向尾声:《伤逝》中涓生抛弃了子君,《舞姬》中丰太郎决绝地分手,爱情最终在现实面前成为了泡影。
其次,两部作品在叙述手法上展现出很大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主要表现在叙述人称与叙述视角上。《伤逝》与《舞姬》皆采用第一人称展开忏悔性叙述。在这种第一人称的叙述下,作者不仅拉近了读者与主人公的距离,使读者更真切地感受到主人公在悲剧发生后的痛苦与无奈,如《伤逝》开篇的“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与悲哀,为子君,为自己”[4]113,以及《舞姬》中丰太郎所言“一桩不为人知的恨事”[5]24;同时也在叙事的过程中“隐藏”了作者本人,从而减少了作者对小说的介入,让两位作者的价值观可以在作品中更为直接地展现,如两部作品中的男主人公皆叙述了抛下爱情自顾自奔向前程后内心的悔恨,这暗示了两位作者对这种行为的强烈反对。并且,在叙述视角上,两位作者都选择了内视角,利用人物的感观去感知这个世界,进而将这种感知传递给读者。在两部作品中,两位作家大量运用心理描写来表现男主人公在爱情与现实产生矛盾时的心理变化与斗争,如《伤逝》中涓生的内心从热恋时期对子君到来的企盼发展到困顿时内心对子君的埋怨;《舞姬》中丰太郎对是否回国并恢复名誉的内心纠葛。这些内视角下真实的内心自剖既向读者淋漓尽致地展现了特殊时代下,弱小的“新人”内心中对自我解放的无尽渴望与爱情濒临破灭时对爱情理想的无尽眷恋,同时也使读者真切感受到男女主人公在踏上“新生路”时艰难的心理历程。内视角的特殊张力增添了故事的悲剧色彩。
同时,鲁迅与森鸥外在两部作品中都塑造了觉醒的“新人”形象。这“新人”形象的相似性在于其形象自身都携带着极强烈的反封建、崇尚自我解放的个性。他们都接受了新思想的熏陶,也都饱含对人生、对爱情的热切渴望与憧憬,于是他们在面对封建势力的压迫时起初都表现出不屑一顾的态度与战斗到底的信念。如《伤逝》中子君面对路上讥讽的目光总是“大无畏的”[4]117;《舞姬》中丰太郎在做通讯员时也“长了另一种见识”[5]34。然而,两位作家所塑造的“新人”形象也都是脆弱的。这种脆弱表现在其自身力量的弱小以及斗争意志的不够坚定两种特点的相互交织上。自身力量的弱小表现在两对“新人”皆没有独立谋生的能力,在外界中断其生活来源后,其追求个性解放与爱情的理想被现实击得粉碎,使其不得不面对生活的荆棘。缺乏独立谋生能力使他们的生活陷入无尽的困顿,进而嫌隙丛生,《伤逝》中子君因涓生杀鸡放犬而怄气,《舞姬》中丰太郎因纠结于生计而闷闷不乐。这些现实原因皆导致他们的爱情最终走向了破灭。但是,其自身力量的弱小这一事实实际上可以被强大的斗争意识所补充,两对“新人”若皆具备顽强的斗争意识,且能够在艰难岁月中相互理解、相互鼓励,那么完全可以抵挡住现实的风风雨雨,可作品中的两人却恰恰相反。两对“新人”过分执着于理想而不愿面对现实,子君纵使自己饿肚子也要养象征理想生活的油鸡和黄狗,丰太郎始终放不下对回国和恢复自己名誉的渴望。在这两种弱点的交织下,两对“新人”的现实生活“一地鸡毛”,他们的爱情也是“油尽灯枯”。最终当现实和封建势力的制裁大棒一同降临时,一切理想都烟消云散,两对空有斗争的愿望却无斗争的能力与意志的“新人”最终只能迎来劳燕分飞的结局。
最后,在艺术上,两部作品皆通过诗意的语言展现出浓烈的抒情色彩。《舞姬》作为森鸥外早期浪漫主义的代表性作品,其抒情色彩自然不言而喻。它以浪漫抒情的笔调和诗意的语言记录了男女主人公相爱时的欢畅以及爱情幻灭后的痛楚哀伤;《伤逝》虽然是一部现实主义作品,但其抒情色彩依旧洋溢在字里行间。鲁迅在刻画涓生与子君热恋中的深情、新婚时的喜悦、子君感情濒于破裂时的痛苦、子君死后涓生的悔恨和悲哀等方面都具有强烈的抒情性,如作品中常常有“我爱子君”“她爱我,是这样热烈,是这样纯真”等感情的直接流露。两部作品的强烈抒情性在渲染真挚爱情的同时,也为爱情的破灭增添了悲剧色彩。
尽管两部作品在叙述手法、艺术特色等多方面展现出异曲同工之妙,但二者在细微之处也各有千秋。森鸥外的《舞姬》在创作时偏向于自我情感的抒发,他并未对引起这一悲剧的社会现实进行过多批判与深入的分析,以至在文章的结尾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好友相泽谦吉,并发出了“然而,直至今日,我心中却依然存有对他的一点怨恨之意”[5]44,从而使作品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批判世俗的色彩。而鲁迅的创作则表现出其一如既往的关切现实的特点,展现出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鲁迅在文中直接将矛头对准了导致子君、涓生爱情悲剧的始作俑者——封建守旧思想,也明确指出了“新人”自身力量弱小和斗争意识不坚定的缺陷,最终提出了“个性解放、个人奋斗对于社会地位低微的广大中下层知识分子来说,是根本行不通的;只有和人民群众相结合,实行社会的根本变革,这才是一条‘新的生路’”的道理[6]。同时,鲁迅也将作品的主题深化到了妇女解放这一问题,《伤逝》中爱情的悲剧并非由涓生一人的投降导致的,子君的未脱尽旧思想束缚的个性也是他们的爱情走向覆灭的原因之一。因此,鲁迅在提出青年知识分子解放的同时,亦提出妇女思想的解放。这是对其《娜拉走后怎样》中妇女解放思想的延续与深化。如果说《娜拉走后怎样》是号召广大的妇女同志争夺“口袋中的经济权”,那么《伤逝》则深化为女性的彻底斗争,即不仅向经济权斗争,也要向封建势力、封建思想展开斗争,从而获得彻底解放,获得属于自己的真正的自由。而这一点是森鸥外小说中忽略且未表现的。
同时,若深挖《伤逝》中鲁迅对妇女解放问题的反思,我们会发现《伤逝》中凸显了女性意识,而《舞姬》则缺乏这一层面的深入。徐艳蓉在《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二十年》中指出,女性意识一方面是指对女性意识的经验性内涵的强调,另一方面是指女性要求平等自由的政治诉求。其在定义中既强调了女性的独特体验与感受,又指出了女性在社会、情感等方面需获得与男性一样的平等地位与自由身份。以此反观《舞姬》,则会发现整部小说中的女性意识并不鲜明突出,从“女性经验”这一层面上讲,整部小说并未对爱丽丝的女性独特情感有过多着墨,作者将大量的笔墨用于刻画丰太郎因情感纠葛而产生的复杂内心情感,而爱丽丝的情感则永远被置于因丰太郎的搭救而感激和害怕丰太郎离之而去的惶恐中。爱丽丝并未从自身角度与造成其落魄生活的社会不良势力作斗争,也未能产生独立生活的思想,而是表现出弱女子逆来顺受、需要被搭救的形象,以致整部《舞姬》陷入东方传统文学中“女子沦落风尘,男子不计前嫌搭救”的俗套情节之中。
并且,从“女性的自由与平等”这一角度看,爱丽丝这样一个女性与男性始终不是自由与平等的,她对丰太郎的经济、情感等方面的依赖使其陷入不自由的境地;她作为被搭救对象的身份也让她无法获得与丰太郎平等的地位。这一特征最初表现在其与丰太郎的第一次邂逅中,丰太郎在一次散步中遇到了需要帮助的爱丽丝,继而以“出超”的姿态降临到女主生活中并解救了她,这使两者的地位从一开始就处于不平等的状态,女子在小说中永远是受助的对象,永远依附于男主人公而存在。因此,地位的不对等导致其爱情的不对等、不自由,爱丽丝始终处于丰太郎可能离她而去的惶恐中,甚至最后以怀有身孕苦苦哀求,爱丽丝的女性意识与女性地位在《舞姬》中荡然无存。纵使他们产生过爱情,那也仅仅是丰太郎当初的怜悯之情和痛失母亲时的孤独无助之情衍变出来的,其软弱性和不坚定性自不待言。综上所述,森鸥外早期的《舞姬》中缺乏鲜明的女性意识。
而《伤逝》中女性意识则很鲜明。从“女性经验”这一层面上讲,鲁迅生动刻画了子君从自己女性的角度对生活、爱情等方面的感知。从其最初对路上看客讥讽眼光的“大无畏”心理,到婚后逐渐局限于小家庭生活的麻木、平庸,再到与涓生理念不合时的不满,鲁迅细致刻画了子君这样一个并未彻底觉醒的女性对生活与爱情的态度与感知的变化,使其形象丰富而鲜明,也指出了子君自我思想解放中存在的局限性。同时,从“女性的自由与平等”这一角度讲,子君首先是一个富有新思想的女性觉醒者,她曾表现出对自我爱情与个性的解放鲜明且富有动力的追求,然而随着情节的发展,其思想逐渐停留在“女子在婚姻自由中获得解放”这一浅层,以至最终停止了自我革新,永远停顿在“因油鸡而和房东太太明争暗斗”之中。《伤逝》中女性意识是鲜明的,作品中女性意识的变化反映出鲁迅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亦表现出鲁迅对女性如何达到真正解放这一问题的深入思考。
三、《伤逝》与《舞姬》“汇通”之因
比较文学的“比较”并非简单地对两部作品进行异同性分析,而是在于“汇通”。所以,明晰《伤逝》与《舞姬》的异同点后,我们进而要思考两位作者在作品中想表达什么样的共同观点和主题。在两部文本不同的时空背景中,封建守旧思想作为永恒的“敌人”,对青年人的个性与爱情自由步步紧逼,使其不得不走向反抗,而汹涌的新思想则鼓舞着青年,并给予他们反抗的精神力量。因此,反抗是特定时代下青年人为个性解放与爱情自由所作出的必然选择,从而表现出青年人思想的进步性。但是,作家又客观且真实地记录了过于薄弱的个体力量与意志在反抗中最终走向投降的现实,使两部作品呈现出青年男女在追逐个性解放与爱情自由的过程中,由“必然的反抗走向必然的投降”这一共同主题。
联系《伤逝》和《舞姬》的创作背景,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发现两部作品皆诞生在封建守旧思想尚为浓厚的时期。《伤逝》诞生于1925年,此时中国封建守旧思想的内涵主要是封建伦理道德。尽管“五四风雷”、辛亥革命等运动都曾激荡过中国社会,引发了社会的一系列变革,但封建伦理道德在民间依旧根深蒂固,如:1921年北洋政府修订了《褒扬条例实施细则》,进一步强化封建礼教;保守派文人如梁启超和梁漱溟则高唱中国文化优越论,反对学习西方的文化,反对中国革命派,同时抵制马克思主义。封建伦理道德在民间占据主流,以至新思想反而成为了社会的“异端邪说”,支持并笃行新思想的新青年成为了不道德的对象。封建礼教宣扬的“三纲五常”让新时代的青年服从于封建伦理纲常,从而失去了自由;其提倡的旧婚配制度让新时代的青年人听令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从而失去了爱情。1925年的中国青年已然备受新思想的熏陶,表现出对个性解放、自由恋爱的强烈追求,断然不会接受封建守旧思想对他们的控制,如郭沫若在《凤凰涅槃》中发出呐喊:“我们年青时候的新鲜哪儿去了?我们青年时候的甘美哪儿去了?我们青年时候的光华哪儿去了?我们年青时候的欢爱哪儿去了?”[7]青年人渴望个性的解放与恋爱的自由,面对依旧在民间“吃人”的封建伦理道德,青年人逐渐走上了反抗的道路。
《舞姬》发表于1890年,彼时明治中期的日本社会正处于黑暗的“冷笑时期”,其封建守旧思想主要是指日本文化中长久以来的狭隘的“忠与孝”观念。日本伦理观念中的“忠与孝”起源于中国儒家思想,后在日本的传播过程中逐渐本土化,并于明治时期发展成为狭隘的“忠君”“服从”等观念,如日本《教育敕语》中指出:日本国体的精华就是“忠”和“孝”这两个字,国家的道德之本在于教育之本,德育的结果是造就出“义勇奉公”的“忠良臣民”,用以“扶翼”天皇。这种暗示日本臣民需无条件服从天皇,日本臣民需做盲目听从指令的工具的封建守旧思想牢牢把控着日本思想界。纵使西方自由、民主思想已经在当时日本社会产生了一定影响,使“人们感叹日本人道德混乱”,但日本民间“还保存着不少日本人的优良风尚”[8]。面对这种封建守旧思想的压迫,不少有志之士作出了反抗,如:文学上,夏目漱石在作品中大胆批判社会现实,并在1911年拒绝接受政府授予的博士称号;社会上,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在日本勃兴,青年人成为这一时代社会运动的主干力量。因此,面对同样封建旧思想占主导的时代,中日两国受新思想影响的有志青年不愿意再继续成为其牺牲品,于是必然选择反抗。如1925 年3月17日,哈尔滨进步女青年才镜石、李淑贞、孔繁贞等人鉴于“滨江妇女界向居被动地位,且有时即被动亦不可能”,决定创立哈尔滨妇女团体联合会以改善妇女地位;日本1908年6月的“红旗事件”表现了对封建压迫的反抗,中日两国不同时代的封建守旧思想的压迫使得两国青年人皆选择了必然的反抗。
中日两国的青年人选择反抗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封建守旧思想的压迫,另一方面在于新思想的鼓舞。在《伤逝》和《舞姬》分别诞生的1925年与1890年,西方新思想经过两国知识分子的介绍,已经进入了中日社会。在中国,经过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先进知识分子的介绍,西方民主、自由的思想在中国社会广泛传播,尤其影响了广大的青年和学生。这种提倡平等、自由与个性解放的新思想革新了中国青年和学生的精神面貌,为其自我觉醒提供了崭新契机。在这一时期,无数觉醒后的青年人“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视之若仇敌,若洪水猛兽,而不可与为邻,而不为其菌毒所传染也”[9]。“五四风雷”就是这个时代青年觉醒后展现的最强音,子君和涓生就是这一时代觉醒青年的写照。而在日本,西方新思想的传播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如:福泽谕吉最早喊出了“天不生人上人,也不生人下人”[10]的警世名言,明确表示要打破日本士尊民卑的传统观念和思维方式;加藤弘之极力提倡国民平等思想,其提出的“天皇人也,人民亦人也,惟于同一之人类中,有尊卑高下之分耳,绝非有人畜之悬隔”[11]思想,在西方新思想的影响下,自由主义运动在日本广泛兴起,《舞姬》中丰太郎对日本等级森严的封建官僚制的反抗便是受此影响。总之,封建旧思想的压迫和新思想的鼓舞使得两国青年不约而同地走上了反抗的道路,但是这一必然的反抗并未局限在《伤逝》与《舞姬》中。与鲁迅同时代的庐隐的《象牙戒指》和与森鸥外同时期的二叶亭四迷的《浮云》等作品对这种“反抗”皆有所表现。可见,青年人反抗封建压迫,并追求个性解放和爱情自由是文学永恒的主题,两位作者在作品中揭示了“必然反抗”这一通律。
然而,这一慷慨激昂的反抗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低潮,最终幻灭消散得无影无踪。《伤逝》与《舞姬》两部作品中皆以男主人公的主动投降迎来了爱情的悲剧与反抗的失败,这一必然的投降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很深刻的个人原因与社会原因。青年人纵使积极地为自我的人生幸福而奔走,但现实的阻力使其不得不“缴械投降”,最终,青年人崇尚并追逐的个性解放与爱情不可避免地成为过往,其反抗也不得不成为过去。
从社会思想层面看,《伤逝》与《舞姬》中由“必然的反抗”走向“必然的投降”的原因都在于封建守旧思想过于根深蒂固。在中国,封建守旧思想中的封建婚姻观念毁灭了子君和涓生的美好感情。《伤逝》中子君的叔父、“鲇鱼须”的老东西、告密者、街上的看客等皆是封建婚姻观念的坚实捍卫者,在他们眼中两人的结合是不道德的,是一定要被扼杀的,他们使尽浑身解数,让两位“新人”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和极其冷漠的人际关系中。尽管两位“新人”都竭力反抗,但封建婚姻观念这一敌人过于强大,这一无形的敌人一手制造了这场悲剧,使得“必然的反抗”走向了“必然的投降”。同时,现实中在封建守旧思想折磨下的鲁迅也走向了投降,他与朱安有名无实的婚姻便是被迫投降于封建婚姻制度的结果,尽管鲁迅后来与许广平再结良缘,但这一制度对鲁迅,尤其对朱安的伤害是不言而喻的。鲁迅将自身这段经历的感受融入《伤逝》之中,增添了作品的现实批判意义。
而在日本,代表封建守旧思想的“忠孝”观念无时无刻不在束缚着人性,《舞姬》中丰太郎便饱受其荼毒。在留学时,他担心自己学问不成从而承担“不忠”之名,急于辩解与爱丽丝的关系;在坠入爱河后,又抵挡不住大臣恢复名誉的帮助而抛弃爱丽丝。封建守旧观念在丰太郎头脑中根深蒂固,使其追逐爱情理想时束手束脚,瞻前顾后,最终丰太郎主动向其投降,导致了悲剧的发生。然而实际上,这种封建守旧思想折磨的并非仅是丰太郎,更是森鸥外本人,森鸥外自身的儒家文化修养使其天然地对有利于其发展的封建势力保持着亲近。李均洋在《论森鸥外早期小说的浪漫主义》中指出:“鸥外少年时期曾随藩儒攻读汉籍, 儒家的一套君臣、父子伦理于他来说, 是根深蒂固的。”[12]所以,森鸥外定然不会对保守封建势力发动挑战,同时,森鸥外在作品中也暗示了封建保守势力对他事业上的帮助。《舞姬》中的天方伯爵就是其日后附庸的内务部大臣山县有朋,据史料记载,森鸥外留学归日后不久, 有一自称为鸥外恋人的德国姑娘追到日本,森鸥外没有去会她, 而是让亲友出面说话, 把她打发回国。这一事实让日本文学评论家吉田精一坦言:“《舞姬》是作者对自己深刻的体验加以艺术化的作品。”[13]森鸥外自己思想中深刻的“忠孝”观使其失去了一次感情,更让其一生都在为日本封建官僚阶级服务,他对封建守旧思想敢怒而不敢言,只有将自身的深切体会投射到《舞姬》中,使得作品中的悲剧意味无比浓厚。
在时代浪潮的裹挟下,《伤逝》与《舞姬》中两对“新人”过于弱小的个体力量也是其必然走向投降的现实原因。这种个体力量的弱小表现在较弱的经济实力与薄弱的斗争意识两方面,这两个缺陷最终导致其走向投降。首先,就经济实力而言,两对“新人”皆无法靠一己之力谋得生路,都需要依附于封建统治者从而获取微薄的薪水以供养他们超前于时代观念的爱情。这种弱点是致命的,当封建统治者切断他们的经济后路时,他们不得不从爱情的幻梦中清醒过来,进而面对残酷的现实。如《伤逝》中涓生原以为可以靠翻译赚钱度日,但结果却是一场空梦,只能杀了子君心爱的油鸡和黄狗勉强度日,这加深了两人的感情裂缝;《舞姬》中这种金钱危机变得更为现实,丰太郎从始至终都在担心微薄的薪水,他换个公寓和吃饭的餐馆才能勉强度日。马克思曾说:“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14]面对已经坍圮的“经济基础”,两对“新人”的爱情已经岌岌可危、朝不保夕。如《伤逝》中,涓生甚至觉得子君“捶着自己的衣角”,致使他难以摆脱眼前的困境,“远走高飞”去寻求新生路,失去现实经济保障的爱情最终只有走向投降。其次,就斗争意识而言,两对“新人”也并不具备强烈的、风雨同舟的斗争意识。正如上文所言,自身力量的弱小这一事实实际上可以被强大的斗争意识所补充,现实中也不乏“贫贱夫妻百事哀”的例子,但两部作品中的男女主人公都缺乏这一精神,最终都走入为了自己的狭小境地。《伤逝》中子君在实现婚姻自由后便停止自我革新,最终回归了平庸的家庭主妇的身份,她失去了与涓生一同为生活斗争的锐气,并常常因生活的不尽如人意而与涓生怄气,以致爱情最终破灭;《舞姬》中的丰太郎放不下“名誉”“归国”的念头,其斗争思想从一开始就显得十分脆弱。两对“新人”所缺乏的斗争意识使其斗争行动难以在残酷的现实中继续,最终只能走向投降。
总之,外部世界根深蒂固的封建守旧思想,以及两对“新人”自身存在的缺陷使其不可避免地走向投降,悲剧在这一特殊的时代下从其结合的开始便已注定。两位作者揭示了特定时代下青年人追求个性解放和婚姻自由走向的必然反抗,在给予肯定与同情的同时,也指出了其必然走向投降的通律。
四、结语
《伤逝》与《舞姬》作为鲁迅与森鸥外的代表作品,对特定时代下青年男女追求个性解放和爱情自由时的现实行动与内心情感作了细致且真实的刻画。两位作者既肯定其反抗精神,又指出了其自身存在的不足以及走向投降的必然性。两部跨越时代的作品同中有异,在展现出各自艺术价值的同时,共同揭示了一代年轻人对现实的“必然的反抗”走向“必然的投降”的规律,表现出超越时代的深刻现实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