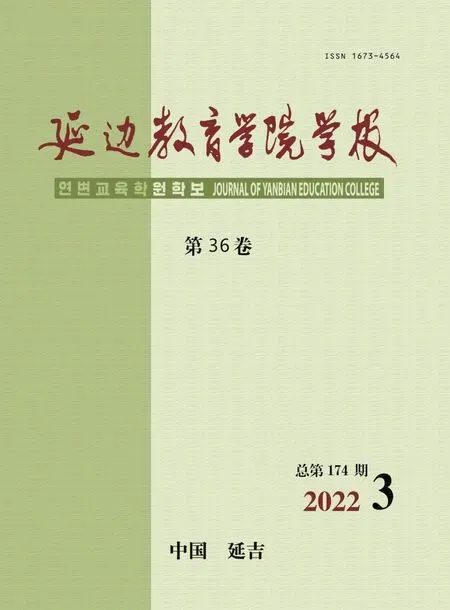李渔拟话本小说《连城璧》中的男性形象解析
2022-03-17李典达赵玉霞
李典达 赵玉霞
(延边大学 朝汉文学院,吉林 延吉 133002)
近年来,对李渔拟话本小说的男性形象研究逐步受到关注,研究成果大都散布在对李渔拟话本小说的人物形象塑造总论当中。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拟从塑造因缘的角度对《连城璧》中男性形象按照商人、义者、才子、隐士、官吏和其他等六类作了划分,并进行专题解析。
一、商人形象
朝代更迭,带有民族情绪的明朝遗民李渔选择放弃科举出仕,转而成为身份低下的书商来谋求生活。康熙五年,李渔进京时写下了“我爱黄金天却吝,人恋乌纱神不许”[1]。从这句互文中,可以看他在社会身份转变的最初时期是特别矛盾和痛苦的。《连城璧》就是在这段时期创作的。因此,他通过贬低书中的商人形象,以此抒发自己当时的内心感受。
在《连城璧》各卷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商人形象有檀越[2]富翁、赵玉吾、阙里侯、杨百万、韩一卿、单龙溪、施达卿、王小山等8 位。李渔主要从处事原则这个方面对这些形象进行贬义书写。在具体故事情节中,他们或好色胆小、或刻薄吝啬、或蠢笨丑陋、或放债取利、或多疑悭吝、或迂腐封建、或爱财如命、或生财无道。总结来说,李渔赋予这些商人形象共同特点就是自私算计。在书中,将商人自私算计展现得最淋漓尽致的就是《连鬼骗有故倾家 受人欺无心落局》一卷中“千方百计,定要扯他下场”“不输个干净不放出门”贪财成性的赌场老板王小山。他在骗得王竺生一些钱财之后,仍不满足,非要让他输尽家财。小山在估算着一张张的欠条累计差不多是竺生全部家财之后,果断收网,但狡猾自私的王小山并没有立马翻脸不认人,而是假惺惺地骂众人揪住王竺生不放,让王竺生反过来感激他一番。李渔还在故事结尾,安排王小山遭到因果报应不得善终,以此表达自己对见利忘义、多行不义的商人们的憎恶和告诫。
李渔在《连城璧》中描写商人形象时,还通过对其外貌进行贬义描写,来表达对商人的鄙夷。在《美女同遭花烛冤 村郎偏享温柔福》一卷中先是用细节描写将财主阙里侯的外貌刻画的十分丑陋。而后,在具体故事情节中,先使用对比描写将阙里侯丑陋蠢笨和先后迎娶三位美女夫人的才高貌美进行整体对比,然后又通过美女夫人的才华相貌一个更胜一个的情节将这种对比效果逐次拉大来进一步凸显他外貌丑陋,达到贬义效果。阙里侯是《连城璧》中唯一一位外貌丑陋的男性主人公,李渔刻意将他的社会身份定位为商人,可见李渔在创作之时对商人的鄙夷。
二、义者形象
明末政治上“诸臣但知党同逐异,便己肥家!”,经济上资本主义萌芽,商品经济的发展刺激了人们的消费欲望。在社会上层人士的带动下,人们开始狂热地追求糜烂穷奢的生活。在这股黑暗腐败、糜烂穷奢的社会风气笼罩下,晚明人民的生活变得苦难不已。经历过明末苦难的李渔,对社会上层人士失去信心,便在《连城璧》中创作社会地位低下但却能坚守社会道义的义者形象,希望以此引导广大普通民众主动担当起捍卫社会道德责任。
最典型的义者形象就是李渔在《乞儿行好事 皇帝做媒人》一卷中刻画贫而不改其道的乞丐“穷不怕”。“穷不怕”因仗义施财、援手他人而家财散尽,沦为街头乞丐。可即便成为乞丐,他仍乐于助人。“他就做了叫化子,依旧还轻财重义。自己要别人施舍,讨来的钱钞又要施舍别人。”在全城的财主、乡宦不能施舍一分,“穷不怕”仍然给素昧平生的老妇人倾囊相助。作者通过在文中写出财主、乡宦和乞丐在救助行为上的对比,丰满了“穷不怕”的义者形象,作者也正是借着这个鲜明对比结果,直接呼应本文中心思想,“谁叫此辈也成名,只为衣冠人物少。”
此外,类似的义者形象还有《重义奔丧奴仆好 贪财殒命子孙愚》一卷中的义仆百顺。他在不肖子孙为争夺家产而抛弃病危家主的时候,千里救主,为其送终安葬,更在得知老家主后继无人之时,不忍家主绝嗣,便自刻了一个“先考龙溪公”的神位,供奉在家。待到祭祀之时,“自称不孝继男百顺,逢时扫墓,遇忌修斋,比亲生子更加一倍。”
三、才子形象
明末清初,以描写青年男女的爱情与婚姻为题材的才子佳人小说大量涌现,一时形成潮流。书商李渔也关注到这一潮流。他在吸取这类小说的题材、情节和模式基础上,在具体创作中加以突破,塑造了和以往不同的才子形象。李渔笔下的才子更加注重佳人的美貌,在故事情节中,才子们十分直白地表达对“色”的追求。《谭楚玉戏里传情刘藐姑曲终死节》的谭楚玉一出场,李渔便写道,“一见刘藐姑就知道是个尤物,要相识她于未曾破体之先。乃以看戏为名,终日在戏房里面走进走出,指望以眉眼传情,挑逗他思春之念。乃以看戏为名,终日在戏房里面走进走出,指望以眉眼传情,挑逗他思春之念。”[3]
《寡妇设计赘新郎 众美齐心夺才子》的吕哉生也是这种好“色”才子。他在见到妻子丑陋得相貌后,“几乎气死,悔也悔不得,就又就不得,只得勉强睡了几夜,就寻个僻静书馆,到外面去读书。”[4]李渔还为了丰满吕哉生好“色”形象。在故事结尾写道“吕哉生据了五美,也就心满意足,不想再遇佳人。”[5]
四、隐士形象
“李渔的小说,在他之前的古典小说相比,一个显著的不同之处就是,作家小说创作的自我意识大大加强了,即作品出现了作家自我形象的寄寓。”[6]李渔在《连城璧》中最知名的一次寄寓就是刻画隐士莫渔翁。这一寄寓所体现的心迹最早可追溯到李渔早年间在山中避祸隐居之时。那时,李渔自得其乐地创作了大量带有田园隐居风格的诗词。其中,重点表达对垂钓打鱼生活向往的是《忆王孙》:“不期今日此山中,实践其名住笠翁。聊借垂竿学坐功,放鱼松,十钓何妨九钓空。”和《伊园十便·钓便》:“不蓑不笠不乘舠,日坐东轩学钓鳌。客欲相过常载酒,徐投香饵出轻倏。”后来,李渔为谋生计被迫出山从商,便将这种渔夫式隐居生活寄寓在《连城璧》中的隐士莫渔翁身上。
在书中,李渔借莫渔翁之口说“这样的快乐,不是我夸嘴说,除了捕鱼的人,世间只怕没有第二种。”以此道出对这种隐士生活的喜欢。后来,更是用《渔家傲》在谭生任满回京之时,点化了他的利欲之心,“竟在桐庐县之七里溪边,买了几亩山田,结了数间茅屋,要远追严子陵的高踪,近受莫渔翁的雅诲,终日以钓鱼为事。莫渔翁又荐一班朋友与他,不是耕夫,就是樵子,都是些有入世之才、无出世之兴高人,终日往还,课些渔樵耕牧之事。”[7]
五、官吏形象
官吏形象是拟话本小说中的重要群体,为小说发挥教化社会、启迪人心起到突出作用。李渔在《连城璧》中也塑造了一批官吏形象。为了让更好地教化读者,启迪人心,李渔在《连城璧》中塑造了与市民阶层接触更多的下层官员和底层小吏形象,如知府、知县、皂隶、运弁等。这些官吏形象在书中的作用各不相同,但总体来说,李渔更偏向底层官吏从正面发挥教化作用、因此在小说中他们基本都是正面形象。下层官员形象则反之。
在具体故事情节中,起正面教化作用的大都是微末小吏。这些小吏有的行为端正,处事公允,如《老星家戏改八字 穷皂隶陡发万金》中那个“在刑厅手里不曾做一件坏法的事,不曾得一文昧心的钱”的蒋皂隶;有的替民申冤,为民作主,如《待招喜风流攒钱赎妓 运弁持公道舍米追赃》的“我既目击此事,如何不替你处个公平?”的正义运弁。
因此,在具体故事情节中,起负面教化作用的大都是主政一方的“父母官”,有的不辨是非、草草结案,如《待招喜风流攒钱赎妓 运弁持公道舍米追赃》的江都知县;有的主观臆断、率性断狱,如《清官难受扒灰谤 义士难伸窃妇冤》中那位“凡有奸情告在他手里,原告没有一个不赢,被告没有一个不输到底”的知府;有的任情用刑、造成冤狱,如《乞儿做好事 皇帝做媒人》中审案时不由分说,也不查证,就直接屈打成招,定下“穷不怕”死罪的知县;有的虽断案公正,但舍弃法律采用鬼神之道,如《贞女守节成异谤 朋侪相谑致奇冤》中的已经审明案情,但仍要假借神明之手的包知县。
六、其他男性形象
除了上述五类男性形象之外,《连城璧》中还有一些男性形象是李渔为了娱乐受众、取悦市场、增加销量而塑造的。这类男性形象主要有两部分,一部分是依照人们迷信鬼神学说的思想而创作的算命先生形象;一部分是为了突破固有题材,刻画之前小说中少见的男性同性恋形象和女强男弱婚姻家庭生活中的“懦”夫形象。
算命先生最典型的代表就是《老星家戏改八字 穷皂隶徒发万金》一卷中帮穷皂隶”蒋晦气”改八字的华阳山人和《寡妇设计赘新郎 众美齐心夺才子》中的无名算命先生。这类算命先生形象,在书中起转折和引起下文的作用。华阳山人是在蒋皂隶背字走到极点,故事无法进行下去时,及时出现为其改运,以此转折。无名算命先生在吕哉生想求娶孀妇曹婉淑,奈何阻力重重情节无法发展之时,借用“难星在命,少吉多凶,若要消灾,除非见喜……”的鬼神之言,引出下文让故事能够继续发展,使得吕哉生成功娶得美人归。
男性同性恋形象就是《婴众舍命殉龙阳 抚孤茕全身报知己》一卷中的为爱变卖家产的许季芳和那位一生都为亡“夫”守节,恪守妇道的“男孟母”尤瑞郎。“懦”夫形象最典型的就是《妒妻守有夫之寡 懦夫还不死之魂》中的穆子大。这两种男性形象在刻画时主要通过反转来为了吸引读者目光。其中,同性恋男性形象是将“才子配佳人”反转成“才子与才子”进行刻画的;“懦”夫形象是将封建社会的传统婚姻家庭中男强女弱反转成女强男弱进行刻画的。
这类男性形象,虽然是为了迎合市场而创作,但没有背离拟话本小说的教化作用。算命先生是为了告诫读者世事无常,同性恋男性形象的重情不重色表达的是传统儒家观念、“懦”夫治妒则是引导封建家庭更加和睦。
《连城璧》中塑造的男性形象众多,身份主要集中在当时社会的中、下阶层,以下层为主。以塑造因缘的角度解析这些形象时,我们可以发现他们能够基本反映出清初南方城市男性的生活状态和当时社会的基本情况。但李渔为了迎合市场需求,不得不大量创新、创作,导致男性形象出现过于媚俗、类型简单、不够丰满等不足。尽管这些形象有不足之处,但也是李渔对当时男性形象的综合再现和艺术塑造。解析这些男性形象,能够帮助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和理解《连城璧》的小说内容和创作思想,同时也对理解同时代其他拟话本小说作品中的男性形象不无裨益。
注释:
[1]《帝台春·客中秋兴》1666 年 李渔作.
[2]檀越,指‘施主’,即施与僧众衣食,或出资举行法会等之信众.
[3]李渔.连城璧[M].哈尔滨:黑龙江美术出版社,2015:10.
[4]李渔.连城璧[M].哈尔滨:黑龙江美术出版社,2015:134.
[5]李渔.连城璧[M].哈尔滨:黑龙江美术出版社,2015:147.
[6]钟明奇.耕云钓月 绿野娱情——试论李渔对渔樵人生的艳羡企慕[J].苏州大学学报,1993(4):85-91.
[7]李渔.连城璧[M].哈尔滨:黑龙江美术出版社,2015: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