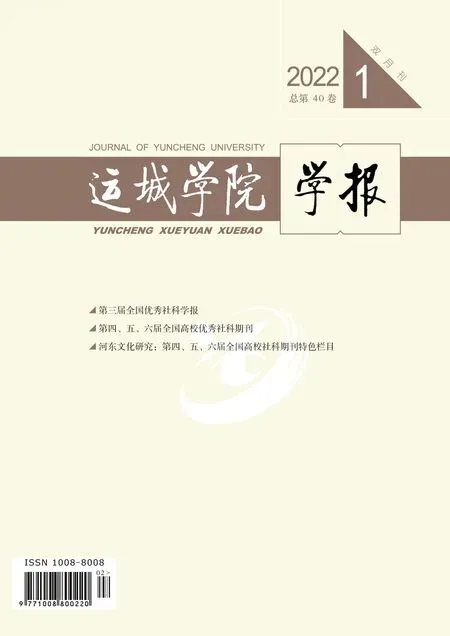“天人不相预”“天人相济”与唐宋儒学进路
2022-03-17张丽
张 丽
(运城学院 中文系,山西 运城 044000)
天人关系是中国哲学和文化中的重要和基本的命题。天人关系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提出展开与当时社会的主要问题息息相关。在唐宋时代特殊的语境下,柳宗元和司马光分别提出了“天人不相预”和“天人相济”,其天人观既代表对当时普遍问题的关注,也表达出一定的知识理性和政治理性,共同构成了新儒学发展很重要的基点,影响宋学深远。
这一时期思想文化领域的成就赖于众多思想家在历史变革的合力下共同推动,但两人的贡献尤为突出。柳宗元以元气论为天人观的哲学基础,极大消解了汉儒以来的神学观,对理学的气本论有直接的影响,其出入三教的思想也启发理学的体系建构。司马光游离于理学宗师的身份,与北宋五子相比,理学体系建构尚薄弱,但其思想如“天人相济”,实以礼为内核,长其善而去其恶,以学治心等,极富有理学精神,在理学发展过程中不容忽视。宋史学者漆侠高度评价司马光:“在经学上的成就足以成家,对宋学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作用。”[1]366
柳宗元和司马光的天人观在唐宋思想领域较为突出还在于他们不仅仅是思想家,更是仕宦经历丰富的政治家,有较高的政治视野和学术地位,其天人观的阐述不只是思辨领域的推进和理论建构,而是体现出鲜明的政治理性和现实政治的实践性,有助于儒学发展起非止于伦理本体的内省之学,向经世致用开发。因而本文的论述重在探讨两人是在什么样的立场和语境中阐述天人观,又以何种方式践行他们的天人思想;他们在政治主体精神高涨、政学兼行、自觉的哲学思辨意识等方面虽有相似之处,但对天人关系的知行存在理论的分野,对这些问题的分析期望有助于深化唐宋儒学发展的内在理路。
一、天人不相预与天人相济
(一)柳宗元“天人不相预”的思想渊源
柳宗元在《答刘禹锡天论书》中提出“天人不相预”的观点,云:“生植与灾荒,皆天也。法制与悖乱,皆人也。二之而已。其事各行不相预”[2]503,此说认为,生植与灾荒出自“天”,而法制和悖乱当属人事,两者互不干涉,各司其职。“天人不相预”观点与柳宗元对天的认识密切相关,他在《天说》《天爵论》《时令论》上下、《断刑论》及《贞符》并序等篇目中都阐发了对“天”的认识。《天爵论》云:“庄周言天曰自然,吾取之”[2]51,《天说》云:“彼上而玄者,世谓之天。下而黄者,世谓之地”[2]286,《天对》中认为天地未形成之前,“曶黑晣眇,往来屯屯,庞昧革化,惟元气存”[2]228,提出了“惟元气论”,即天和万物一样,都是由元气构成的,强调天是一客观存在的物质实体,不可能有意志,有道德属性来主宰人类社会,更不具备赏功罚过的能力,因而人非受制于天。可以发现,柳宗元天人观的阐释中,“天”的范围较以往有所缩小,“人”的范围和作用却扩大了,肯定天人各自的运行规律,否定和剥离了天的神秘性,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进化有更客观的认识。
从思想渊源来看,荀子的天人相分和王充元气自然论都对柳宗元有借鉴意义。荀子提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著名论断,认为天有自己的运行规律,人要“明于天人之分”,才不会对天寄予无妄的依附。荀子还进一步提出“制天命而用之”,即不是隔绝天和人,而是说人可以通过有意识的社会行为发挥主观能动性,对自然和社会产生作用,进而使“参于天地”成为可能。柳宗元明显受到荀子的影响,《封建论》中说:“荀卿有言,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2]44,在天人观问题上柳宗元很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王充的天人论思想对柳宗元也产生了较大影响。《论衡》自然篇中王充提出天道自然即无为,以万物之生,皆禀元气,以此质疑“天人感应”和“君权神授”。王充这一思想无疑动摇了天命论的神秘和政治权威,援引道家思想探索天之自然性的理论思想对柳宗元亦有启示意义。不过王充对天的认识尚不清晰和深刻,在反对天人神命之说的问题上,并未明确指出汉儒的价值根源一归于天这一关键点,消解天人感应的同时未能自觉追寻新的价值之源,且对孔孟原始儒学心性论发展甚少。
“天人不相预”提出的语境。柳宗元的天人观产生于安史之乱后复杂的社会文化环境下,代表着当时文儒对自然和天命、天道和人道等持续性命题新的思考,在与韩愈、刘禹锡等人的论辩中柳宗元进一步丰富了天人思想。韩愈对天的看法似不确定,既有自然性的一面,如《原人》中说:“形之上者谓之天,形之下者谓之地”,又有明显的天命意识,《与卫中行书》云:“凡祸福吉凶之来,似不在我。”[3]217韩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天有赏罚功能,人道对天道无能为力。柳对此说进行反驳,云:“天地,大果蓏也。元气,大痈痔也。阴阳,大草木也。其乌能赏功而罚祸乎。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欲望其赏罚者大谬。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谬矣”。[2]286柳宗元对韩愈的驳论主要在于,柳认为天地元气阴阳亦是自然物质,并不具备赏功罚恶的功能,否认推天引神说,据此,人事祸福非天人感应,功者自功,祸者自祸,这是人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社会行为的结果。韩愈重视“天”的权威神性,柳宗元则重视人之现实主观性。在批判天意、天命神学论上,柳宗元和刘禹锡是高度一致的,都认同天道和人道有不同的运行规律,但刘认为天与人是“交相胜”的。柳宗元正是在对此说的回应中,提出天人各行不相预的观点。《答刘禹锡天论书》云:“子所谓交胜者,若天恒为恶,人恒为善,人胜天则善者行。是又过德乎人,过罪乎天也。又曰:天之能者生植也,人之能者法制也。是判天与人为四而言之者也。余则曰……其事各行不相预”[2]503,称刘说有“以乱为天理、理为人理”之嫌。
以柳宗元、刘禹锡等为代表的天人观折射出中唐士人较为进步的社会历史观和对一些社会思想及现实问题的批判思维。任继愈先生对此高度评价,“(中唐)通过对当时天人关系的讨论,把人们对天命观的怀疑和否定引向对汉以来整个儒家经学传统的怀疑和否定。”[4]534他们天人观的认识和讨论实际上推进了中唐的儒学转型。
(二)司马光的“天人相济”
“天人相济”的内涵。司马光对天的认知有些矛盾,既认为:“天者,万物之父也。父之命,子不敢逆;君之言,臣不敢违……违天之命者,天得而刑之;顺天之命者,天得而赏之。”[5]1504此说充满天命论色彩,但司马光论天又有自然性的一面,《潜虚》中提出“虚”和“气”。在天人关系上,司马光非唯天命论之。对天命的理解上,司马光基本与孔子重人事,轻天命存而不论的思想一致,《原命》中说:“夫天道窅冥恍惚,若有若亡,虽以端兆示人,而不可尽知也。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於此?是以圣人之教,治人而不治天,知人而不知天。”[5]1402《迂书·天人》中说:“天力之所不及者,人也,故有耕耘敛藏;人力之所不及者,天也,故有水旱螟蝗”[5]1508,提出“天人相济”思想。司马光既相信天命的决定作用,又认为人不是完全被动的,人有主动适应改变能力,此说是在不否定天命的前提下,不否认人为,极大降低了天命之为的偶然性和任意性。“天人相济”不同于天人感应。天人感应思想集中体现于董仲舒的学说中,董仲舒认为:“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遵也。”(《春秋繁露·郊义》)[6]541“人受命于天,有善善恶恶之性。”(《春秋繁露·玉杯》)[6]33将天神秘化、人格化和道德化。董仲舒还提出:“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天地之阴气起,而人之阴气应之而起……其道一也。”(《春秋繁露·同类相动》)[6]484从同类相动、物类相应等说明天人一也,来彰显天的意志。
司马光天人相济思想与《易经》在宋代的发扬密切相连。《易经》说的“道”异于老子、孔子之“道”,包涵会通天道人道且生生不息的宇宙观和辩证思想,此思想在宋儒之前并未受到重视。宋儒大多表现出对易学的关注,注易成风,但大都淡化思辩色彩,这与他们以易学义理重建儒学的努力不无关系。受此影响,司马光提出天人相济的天人观有两层哲学内涵:
第一层,在天人问题上,司马光没有把天进一步神秘化,而是发挥易学推天道以明人事思想。司马光撰写《易说》三卷,《系辞》两卷,认为王弼对周易老庄式的玄渺注解并未切近易之微言大义,司马光从天地人会通角度解说周易,并进一步阐发其天人观,《温公易说》云:“天以阴阳终始万物,君子以仁义修身,以德刑治国,各有其事也”[7]28,他对易说“出于天,施于人”的思维特征有深刻的认知,强调人事也有主观能动性,突出人的价值。
第二层,从司马光的天人思想可以看出,宋代思想家在复兴儒学过程中,在思想领域一直探索儒学新价值和现世伦理秩序的本体层面依据。张岱年先生说:“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宇宙的第一原理也就是道德的最高准则,认识真理的方法也就是道德修养的方法,这在先秦儒家、道家的学说中,在宋明时代的哲学中,表现最为明显。”[8]125司马光天人相济的天人观是包涵道德维度的宇宙观,其话语系统就成为一种被设定的和谐。在对天的理解中,司马光提出“虚”,云:“万物皆祖于虚”[9]295,又由虚派生出气、体、性等,司马光认为虚不仅仅是万物生化的时空幻境,而且具有本源本体的性质。虚与极同,“易有太极,极者,中也,至也,一也。”[7]77对于人道之本体“虚”的指向,司马光又提出“其惟纲纪乎,纲纪立而治具成矣”[9]296,内涵天人秩序的一致性。通过人道对天道模拟,司马光在对天人关系认知和发展中建立起道德最高准则的理论进路,建立起现世伦理政治秩序之本体论基础。
与柳宗元重视天的自然性,非所以尽天人之际相比,司马光思想中,天既有自然规律的意义,又有道德标准的涵义,并且司马光更重视天道的秩序,将天道、天理融入德性道义,从天道世界观人生观的精神空间和实践意义上重塑儒学。
“天人相济”提出的背景和意义。司马光对天人关系的阐述蕴含北宋中期内忧外患下的探索。有学者指出:北宋思想体系建立集中于两点,一个是要为统一社会成员的意志以配合政治上的高度集权专制,找到神圣性的最高依据,提供哲学理论的证明;再一个是理想人格的培养。[10]155司马光复兴儒学的抱负,是基于鲜明的抗衡佛教,维护儒学主体的立场,他对天道恒常的思想承继包含着对当时现实政治绝对合法性的支持,这对稳定北宋政治秩序是有现实意义的。从“天人相济”可看出,与其他宋儒重视精神世界的内省不同,司马光更重视具体现实情境中人道对天道的践行。司马光反对北宋前期官场佛道思想弥漫,儒家事功精神缺失的时风,认为不能摒弃现实生活,寻求非理性的超越。在《颜太初杂文序》一文中他阐释自己对“儒”和“所求之道”的看法,提出真正的儒士是要有儒家精神的,不仅要学道,而且要践行之,达到自我实现和经世致用。司马光的政治实践尤为重视人伦和维护封建统治,以重振儒学为出发点,构建社会应然的理想体系,在这个方面看司马光的天人观实际上为封建社会后期的等级秩序和政治社会提供了理论根据和哲学基础。
柳宗元“天人不相预”和司马光“天人相济”天人观的表述看似矛盾,但从儒学思想螺旋式的上升来说,两者都是儒学发展的重要节点。我们知道北宋中期儒学复兴上承中唐而来。宋人继承了中唐文儒力求摆脱经学束缚,打破天命神学的桎梏,着意建立利于解决现实问题的思想理论内核。两人的天人观体现出唐宋思想家缘于深厚的政治理性和知识理性来探索人道天道问题,从儒学内部进行反思和革新,并且对佛道思想都有批判借鉴,因而能生发新的理论视野和现实意义。
二、两人天人观内在理路的差异
(一)柳宗元重“势”
柳宗元继承发展了自荀子、王充以来的元气论,并充分利用唐代自然科学的成就提出新的天人观,与其天人观相呼应,柳宗元提出“势”。《封建论》中柳宗元云:“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势之来,其生人之初乎?不初,无以有封建,封建非圣人意也。”[2]43柳宗元将封建这种人类历史的发展变革,归因为非圣人意,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使然,是势也,并说“势”体现的是“生人之意”。之前的思想家对势也有所认知,如《孟子·孙丑上》:“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老子·五十一章》:“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这些势论都侧重客观形势,外在环境。相形之下,柳宗元对势的理解更具有哲理性,是认识论上的极大提升。在柳宗元的其他论著中,也贯彻此思想,《天说》:“功者自功,祸者自祸”[2]286,可视作对“势”的注解。《非国语·三川震》更是连用八个“自”,“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阴与阳者,气而游乎其间者也。自动自休,自峙自流,是恶乎与我谋?自斗自竭,自崩自缺,是恶乎为我设?”[2]748来说明自然万物的形成变化都有其客观规律,非承天的意志而来。结合“势”可以更清晰的看出柳宗元天人论的主要思想是强调社会现象的内在动力在于人自身,所以不能依赖于“天”。“是故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惟人之仁,匪详于天。”[2]22柳宗元认为变祸为福,易曲成直,不在天命而在人力,人力可为,但亦有所不为,为与不为就需要大中做指引。“圣人之为教,立中道以示于后,曰仁、曰义、曰礼、曰智、曰信,谓之五常,言可以常行者也。”[2]55柳宗元认为要寻求真正的圣人之道、大中之道,需重振以仁义为核心的五常,并据此作为人事的原则驳斥汉儒的祥瑞灾异论,“苟以合五事配五行而施其政令,离圣人之道,不亦远乎”[2]53。
柳宗元强调天之客观自然,人之主观能动,将两者置于互不干涉的领域,这与他在现实政治中跌宕起伏的经历和力求改变言天不言人的治政原则分不开。在《贞符》中柳宗元云:“臣为尚书郎时,尝著《贞符》。言唐家正德受命于生人之意,累积厚久,宜享年无极之义。”[2]18从历史背景来说,柳宗元的天人思想反映了中唐以降伴随着传统贵胄的衰落,中小地主阶层想要获得政治话语权,推进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呼声。他认为要发挥生人之意去革新政治而非延续天命史观、英雄帝王史观的以威以怪来继续强调等级和特权统治。
(二)司马光天人思想之遵“礼”
礼是贯穿司马光史学经学思想的核心,司马光以礼统摄万物,思想中多处提及礼的价值功能和现实意义,认为“国家之治乱本于礼,而风俗之善恶系于习”(《谨习疏》)[5]603,“礼法者,柱石也”(《司马光集·进五规状》)[5]536,在司马光看来礼规范社会秩序,是纲纪,是等差,尊卑之义也是礼之本,维护礼就是维护等级秩序,就是立纲纪。《温公易说》中云:“礼者,人所履之常也……夫民生有欲,喜进务得而不可厌者也,不以礼节之,则贪淫侈溢而无穷也。是故先王作为礼以治之,使尊卑有等,长幼有伦,内外有别,亲疏有序,然后上下各安其分而无觊觎之心,此先王制世御民之方也。”[7]19司马光重视以礼维持君臣士大夫和庶民之间的尊卑有序,进而建国驭民发挥重要的政治功能。
不仅如此,司马光认为礼代表社会秩序的最高原则,对礼经世致用的功能认识与其天人观结合起来,便是以人道补充天道,通过礼制途径,恪守礼,使天道在人道的实现成为可能,这样礼就具有了自然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双重意义,将礼内在的社会规范道德特质提升至宇宙本体普遍性的意义。正如有学者评述:“司马光着眼于天人之合,一方面援引天道论证人道,另一方面又按照人道来塑造天道,因而在他的天道观中蕴含着人文的价值思想,在他的人道观中蕴含自然法则的客观依据,天人不二,相互渗透……”[11],司马光通过礼实现了天道与人事之间相互渗透,达到了宇宙论、方法论、价值论的统一。
司马光不仅从道的高度研究礼的精义,而且严格履践礼,在建立和推行礼的内在机制上,司马光认为“治国首先正人君”,奏章《三德》中云:“臣窃惟人君之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妪煦姑息之谓也。兴教化,修政治,养百姓,利万物,此仁君之仁也……”[5]527,谏言皇帝要按照礼的要求来修德治国,“上行下效谓之风,熏蒸渐渍谓之化”。这是封建社会后期,权利高度集中的绝对君权趋势下,对君权的限定。司马光认为政局的长期稳定真正依靠的是德,这是非先天命定的,司马光特别强调统治者的道德影响和表率作用,即以统治者的德行感召力推动王道政治的运作,而不是单纯的利用权力和法规,这样就把道德教化与政治运转相连,也是儒学从礼乐思想的经典形态向道德规范转移的表征。
前代的礼治教化主要对应贵族,随着唐宋社会阶层间的流动和变动加剧,礼从士庶天隔,不下庶人向庶人阶层日常生活渗透。司马光尤为重视家礼民礼,《居家杂仪》《温公家范》中仪礼记载均为日用切要,谨言慎行之事。与以往家训家规在实践主体和理念上有了很大改变,虽仍限于家庭主体的日常伦理,但非专为一家一宗族所制,而是旨在规范所有的家庭主体。司马光将个人、家庭的道德完善视为规范整个社会关系的基础,扩大礼所对应的主体对象至整个社会。
柳宗元关注天的物质性自然性,而不是哲学意义上的天,消解了作为最高权威的主宰之天和作为伦理道德本原的义理之天,以“势”为武器破除束缚庶人参与现实政治和政治体制革新的思想障碍。在“天人不相预”的前提下,道德伦理和政治伦理关联不大。而在“天人相济”的前提下,一定程度会强化道德在个体生活及社会现实政治中的文化功能意义,极易将道德伦理扩展到社会和政治领域。两者都对儒学的发展方向提供了指导,此后的宋学既从儒学内部创制出一个连贯个体与社会政治结构的价值体系,同时又强化了儒学走向泛道德化倾向。
三、两人的天人思想与体用落实
柳宗元和司马光都不是单纯的在形而上学视域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他们很重视体用落实。在他们身上体现出唐宋文儒艰辛的理论探索,期望为当时的社会困境找到变革的依据和理想的发展模式。司马光重视宗法伦理和社会秩序,为重建秩序寻求理论支撑;柳宗元则更多地关注破除天命桎梏进行革新。二人理论有差别,但两者都对天人关系进行有价值的整合建构,为人和社会的现实存在寻找可靠的理论根据,其天人观都蕴含丰富的社会历史内容和对时代命题的积极回应。
首先,两人都呼应了中唐以降的疑经思潮,推动了变古之风。晚清学者皮锡瑞评唐宋经学:“自《正义》《定本》颁之国胄,用以取士,天下奉为圭臬。唐至宋初数百年,士子皆谨守官书,莫敢异议矣。”[12]207传统的谨守官书,对传经解经的重视,很容易束缚经学的正常发展,抑制对儒学的承继和创新,削弱儒学作为一种社会政治伦理学说本身应具有的经世致用。当社会面临重大变革,社会统治体制的整体功能衰退,儒学未能对失序的社会状况做出说明时,这种缺失更为明显。唐宋以柳宗元和司马光为代表的士大夫深刻意识到面临时代的多重变革,儒学须从寻章摘句中解放出来,恢复其内在的社会功用和道德实践性,深层次的探索心性并回应现实的社会问题,才能有新的突破。因此,柳宗元在学术上和行事原则上追随春秋学派,突破株守章句,依据大中之道重振儒家大义。司马光则援佛道入儒家,阐释和发展了中庸思想。
其次,柳宗元和司马光的天人观体现了唐宋社会变革下士人的政治和文化主体意识渐趋增强。这一时期士大夫群体作为社会生活的主要推动者,区别于之前的“封建贵族”“士族门第”及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仰禄之士,可以说是正身之士的代表,突出特点为现实政治的诉求强烈,责任感明显;以道进退而非爵禄。《邵氏闻见录》记载神宗问程颢,“朕召司马光,卿度光来否?”后者回答,陛下能用其言,光必来;不能用其言,光必不来。[13]1766这则著名轶事较为形象地说明了当时士大夫鲜明自觉的政治主体意识。柳宗元《寄许京兆孟容书》云:“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2]480,司马光自述其志,“臣自结发从学,讲先生之道,闻君子之风,窃不自揆,常妄有尊王庇民之志。”[5]1072他们均秉承了儒家强烈的事功精神,具有传统儒家积极入世、济世的淑世情怀。尤其司马光处于北宋较为宽松的政治文化环境下,更容易激发起复兴儒学,重建合理政治秩序的积极治事态度。加之柳宗元和司马光两人都有丰富的社会阅历和仕宦经历,对社会弊端有真切感受,对时代问题看得深远,自觉的批判意识使他们的天人观和对儒学发展体系的认知都区别于单纯的经学家。
再次,他们的探索促进天人观自身理论的演进。柳宗元和司马光都将天人思想用于指导实践,通过天人关系的思考反观儒学自身,丰富了天人论的层次和内涵。他们对天人关系探索远超出汉儒对人与自然的认知,而且超出纯粹形而上学的思维,明体达用,体现出新儒学的发展趋向。
张跃赞誉柳宗元思想,称之“冲破经学的藩篱,进行了大胆的理论创造”[10]48。柳宗元还原“天”元气自然性的同时解构“天命”,将天人关系重心由“天”对“人”的主宰向“人”主体活动能动性转移,为彰显人道提供理论支撑。其天人观不仅对当时的社会实践有指导意义,也启发了人们的理论思维和解决问题的现实能动性。
我们知道原始儒学缺乏严谨细微的思辨理论体系和形而上学的追问,宋以后儒学发展存在融合佛道的趋向,同时又竭力摆脱佛道影响,如李泽厚先生所说“宋明理学的这种吸收,改造和批判主要表现在,它以释道德宇宙论、认识论的理论成果为领域和材料,再建孔孟传统。”[14]221综合司马光对天、天命、道等观点来看,司马光虽认为天是有意志的存在,但非唯天命论之,而是肯定天道存在,并努力将天道与伦理相连,得出道德不是人类自身产物,而是宇宙法则在人道的再现,这样使道德具有了权威性和普遍性,由自然本体回归伦理本体。司马光的天人观很重要的一点,即提出德行根源不在客体,而在主体自身。《中和论》中司马光说:“道之要在治方寸之地而已”[5]1453,治方寸之地即治心,通过治心,达到天人合一,再建孔孟之道。借鉴佛、道的理论和重释周易,司马光在道、理、心、性、气等概念上开拓新义,进行形上层面的理论建构,推动传统儒家学说不再拘守于政治伦理等领域,在修身成德及思辨之域更进一步。劳思光指出了宋学的这一内在转变,“盖自宋至明,中国思想家欲脱离汉儒传统而逐步求价值根源之内在化,宋明理学即此内在化过程之表现。”[15]88司马光“天人相济”的思想正处于宇宙论向形而上学观的过渡,两者有混合,将重点落在内圣上,而宋儒正是承内圣之学而发展。司马光构建天人观的直接动机是重建纲常秩序,将个人道德修养与社会政治问题相结合,以儒家伦理道德作为核心因子重塑社会政治人格。这种经世致用之道与形上思辨、治心的结合,使司马光天人论区别于单纯的天人感应论。“天人相济”思想还包含同于天的境界,以及实现这个过程中人应当追求和达到的一种超越境界,这又延伸出新儒学的内在超越性,从天而人,在理论建构和视野上引导了儒学体用发展。
结语
天人关系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命题,有相当长的理论认知发展的渊源,柳宗元和司马光的天人观体现了一定历史进步性,两人都政学兼收并蓄,基于较为深刻的哲学底蕴和对现实的批判精神及自觉的儒学自我革新思想,他们提升了天人论的理论和实践高度,不仅为其现实政治的践行提供了哲理基础,而且强调“人”之道德主体性和历史主体性,体现了唐宋儒学由外向内对心性之域拓深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