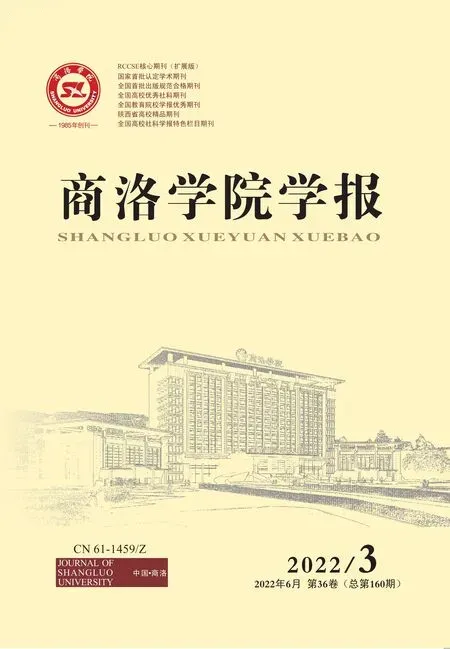颓土危机下美丽难改的生命歌吟
——评贾平凹《秦岭记》
2022-03-17杨云超
杨云超
在当代知名作家中,贾平凹素以对秦川大地的深刻摹写而著称,作为“陕军东征”的代表作家,他带有浓郁地方气息的书写模式也引导整个文坛关注民众的生存困惑、历史记忆保存等重大问题。
新世纪以来,贾平凹的小说多围绕秦岭写生态、民俗等乡野故事,秦岭成了贾平凹笔下许多故事的发生地,并由此形成了所谓的“秦岭志”系列。而他近期的新作《秦岭记》则不同于他以往发表的长篇小说,更趋于志怪奇谈的笔记体小说,五十六个章节各有不同的故事,如《人民文学》卷首语所评价:“阅微杂览间,隐约可见生存的时变境迁之痕、风俗的滤浊澄清之势,以及山地深处的人生底细和生活况味。”本应有着如田园诗般规律的生命形式的生灵们,在现代文明的叩问中一次又一次地震荡着,逐渐立于一片空有其深邃,实则被边缘化许久的,颓土式的秦岭。
相比较于其他典型的“颓土上的歌吟者”,贾平凹在《秦岭记》中并没有致力于展现现代文明对原始静谧之境来势汹汹的猛烈冲击,作为“外来者”的现代文明世界反而是引起故事的线索,也是在缓和的叩问中逐渐与迷蒙中的秦岭生灵产生互动,而这或许更突出了贾平凹的危机意识——缓和的叩问,或许会带来更彻底的颠覆,对自然生命本应具有的敬畏正在被卷入商业和遗忘的漩涡之中。第五十五章的张铁匠在秦岭传统生活形态的梦中被惊醒,又在现代商业的叩问中永远地睡去。贾平凹更多地选择以故土上那些美丽难改的、魅影般的生命形式的野性歌唱来化解这种淆乱的无力,这集中表现为动植物的“野蛮生长”,尤其是在人的落寞、疲敝之下。如第四章中,观音崖侧翻的吉普车代表了文明社会叩问秦岭大地的失败,白衣男子捡拾纽扣、留下纸条则是一种对现实无力的抵抗,最关键的是,遗落纽扣的地方生长出的野菊逐渐密密实实地挤满山谷,这是自然生命以野性滋蔓的形式对“失衡的淆乱”的最好回应。此外,对于动物而言,野性的生命也突破着人对其的禁锢、压制,以充满迷魅的手段来对人加以“反击”,又诸如第五十二章,一辈子阉猪的武来子在下坡路上被一头猪阻拦,躲闪不及,跌下悬崖,在昏迷之间“觉得石头都在动,是卧着站着的一群猪,再看,那群猪又是白石头和黑石头”。
《秦岭记》延续了《怀念狼》《秦腔》等系列作品“以实写虚”的手法。“实”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其他生灵草木之间的互动、纠葛,而“虚”则是作为“颓土”的秦岭上天地众生这个和谐系统的异动与淆乱,正如费秉勋、叶辉所说,“一个形而下的意象表现的是形而上的生态与人类关怀”。贾平凹在本书中借助五十六个精短的故事传达了一种万物有灵的意识,万事万物的灵魂依附于特定的禀气和时空机缘,在物和物、生命和生命之间相互转化。第二章中买树失败的蓝老板返回城市时,发现城市“那么高的楼都是秦岭里的山,只是空的,空空山。那些呼啸而来呼啸而去的车辆,都是秦岭里的野兽跑出来变的……”又如第十三章中,一个颇具象征性结构的故事——标志着都市享乐、贫富差距的康养别墅“白城子”被一个叫王长久的年轻人反复状告而拆除,而王长久的父亲是一个曾经向往进入“白城子”打工的,“出神”的神汉……这也从侧面展现了,人与自然、生灵并没有那样明晰的区分界线,它们之间是谐和同一的综合体,而当现代文明走向与这个自己原本在其中的大系统的对抗后,加上其他原因,这个大系统就历史性地失衡、混乱了,而只有秦岭和“有故事的秦岭人”(第十三章)会有自己的策略来对现代的文明展开反抗。
科技的发展、商业化的意识形态并没有给人带来真正的幸福感,而只能促成秦岭这片孕育着无限美丽生灵的伟大土地成为一片“颓土”,那些美丽难改的生命形式在歌吟过后终究会直面这生态失衡、道德沦丧的惨象,贾平凹却并没有直接将其揭露出来,而是通过黑顺在箱中的白骨(第一章)、魔术师鱼化腾莫名其妙地突然死去(第三章)来展现的。但问题是,作者是否给出了抵抗这种精神荒漠,寻找生命力量的途径或结局?
作品的最后一章,“似乎”给出了答案。五十五个“千岩万转路不定”的瑰丽奇特的故事之后,视角终归于洛水流经的“仓颉造字地”,一切嘈杂的、冷漠的、沉沦的声响,都归于启山上那小小的仓颉书院里传来的,“声闻于天”的钟音。书院里那个叫立水的孩子,父亲和母亲都是残疾,却“生得棱角崭新,平和沉静,时常冥想”,他人如其名,立于水上,观真相假象,观秦岭内外,观过去未来。至此,谜底已经不言而喻。在淆乱的宇宙间,贾平凹还是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了愿意读书、愿意思考的下一代,纵使他们的上一代在“现代”的侵蚀中,身体或精神已然残疾荒芜,但沉浮于生长之门的他们,会在自然的抚慰下,睡在秦岭的怀抱中,也会理解秦岭的庞大、雍容、不可动摇,也会找到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快乐。只是,他们“似乎理解了父亲的瞎、母亲的哑再也无药可医”,那一代被抹去记忆的“秦岭人”,再也找不回自己的眼睛、自己的耳朵。在与“现代”的交互中,秦岭不会动摇垮塌,可那些在其中飘荡着的瑰丽精魅与鸟兽传说,便也永远地和钟声响过的寂静共同沉没了。那些美丽难改的生命形式依旧以自己的方式存在着,只是化为了这篇颓土上的“一棵若木、一块石头”,秦岭的孩子,“现代”的孩子,似乎会缅怀,似乎会理解,似乎在书院的钟被敲起的时候会明白——“自己的理解只是似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