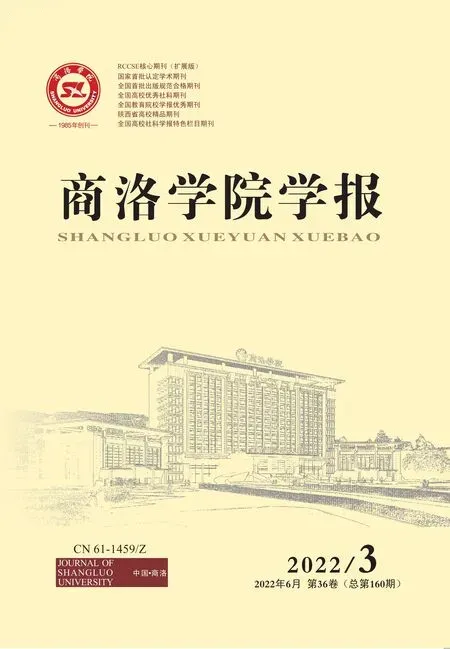总体性的重构与笔记体的内在难度
——关于贾平凹的《秦岭记》及其他
2022-03-17徐勇
徐勇
(厦门大学 人文学院,福建厦门 361005)
发表于《人民文学》2022年第2期的《秦岭记》(贾平凹),被认为是“长篇笔记小说”,其中呼之欲出的《山海经》的气息,容易让人想起福柯《词与物》开头的笑声。福柯惊叹于博尔赫斯的一个文本,这个文本据说引用于“某种中国百科全书”,其中有这样的记载:“动物可以划分为:属皇帝所有;进行防腐处理;驯服的;乳猪;鳗螈;传说中的;流浪狗;包括在目前分类中的;发疯似的烦躁不安的;数不清的;浑身绘有十分精致的骆驼毛;等等;刚刚打破水罐的;远看像苍蝇的。”这样一种奇怪的分类或并置,可以用来形容《秦岭记》,文本似乎把各种看似不相容的内容杂糅在一起,没有规律,长短不一,时间不定。但若只是看成杂糅则显然误读了贾平凹,因为这一杂糅也是某种“陈述”,其看似随意的杂糅中并非毫无章法和逻辑可循,或者还可以说,贾平凹把数十则简短的故事杂糅在一起,置于“秦岭”这一共同的空间之下,空间的确定性与时间的模糊性之间所构成的张力关系,为长久以来困扰他的某些命题(比如《山本》中提出的“现代性、传统性、民间性”[1]526)的思考提供了某种新的可能。
一、非虚构或秦岭方志
眼尖的读者在读完《秦岭记》后,会把此书视为作者写作《山本》时剩下的素材杂凑而成。因为,两个文本都是写秦岭,而且其中都出现了麻县长和关于他的秦岭志的写作实践(《山本》中麻县长写的是《秦岭志草木部》和《秦岭志禽兽部》,《秦岭记》中是《秦岭草木记》);而据贾平凹《山本·后记》所说,他“曾经企图能把秦岭走一遍,即便写不了类似的《山海经》,也可以整理出一本秦岭的草木记、一本秦岭的动物记”[1]522。因此,《秦岭记》似乎可以看成是“秦岭方志”之类的作品。如果说贾平凹为此收集到了大量的素材的话,那么作者把他收集到的材料,一部分用于《山本》中以编织成相对集中的时空、贯穿始终的人物和若隐若现的故事主线,剩余的边角料则构成了《秦岭记》中故事的罗列和堆积,因为小说中满布着发生在漫漶的时空中毫无关联的零散的人物、故事,这些人物或故事仅仅像是些素材,无法编织成完整的故事,《秦岭记》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被称之为“笔记体小说”。
这种解读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似乎又略显不足。因为显然,两个文本分属不同文体,而两种文体之间的比较,其有效性常常是可疑的。细细比较两个文本便会发现,《山本》中的大多数地名,如平川县和涡镇等,其实乃出于虚构,而《秦岭记》中的地名,则大体是真名实地;对于《秦岭记》,这里的麻县长之官职属地当是城固县,因为里面提到了高坝乡,高坝乡是一个真实的所在,隶属于陕西汉中市。而且,《秦岭记》采用的似乎是隐退幕后的第三人称的客观视角——也即不介入的游记的写法。这似乎表明,《山本》乃虚构,《秦岭记》则属于非虚构;近些年来,非虚构十分盛行,贾平凹似乎并非不为所动。对《山本》和《秦岭记》这种文体的分类,看似一目了然,但仍有复杂问题简单化的嫌疑。因为显然,《秦岭记》中所记载的诸多事情,也并不都是实有其事或实有其人。其中的奇人异事,传说色彩很浓,比如说捞娃(第四十八节),甫一出生就不寻常:头发眉毛皆白,腿极短,且只有四个脚趾,只吃墙土;种种异象似乎都与他的异能相呼应——他能预知身边人与事的未来。显然,这一写法并不是非虚构所为。
而若结合贾平凹的创作历程来看,《秦岭记》又似乎是《商州初录》和《商州再录》(而不是《商州又录》,《商州又录》中是“地也无名,人也无姓”)的扩展版:都看似笔记体,只是把空间由原来的商州扩大到整个秦岭。但两者的不同也不可忽略。在“商州”系列中,作者总难免以建国后的50—70年代作为“他者”,而在《秦岭记》中,作者所构想的“他者”则变成了现代化和城市化。如此种种,都似乎表明,《秦岭记》既非“秦岭方志”,也不能仅仅视为非虚构,而只能看成是作者多年来思考的综合或总结,至于是否乃集大成之作,那又是另一个层面的课题。
二、立言或失语
表面看来,《秦岭记》沿袭的是《山海经》的写法,即以山或海作为线索,展开奇人异事的故事。《山海经》的叙事语法主要表现为:某地有某山,向某方向又有某山,山上有某物或某人。或某海之外某个方向,有某山。有意味的是,《秦岭记》中,除了以山或河为坐标之外,还以公路或道路为线索。比如说“从西固山出发,公路一直在半山腰上逶迤……”(第四节)。应该看到,就与《山海经》对比的层面看,公路的出现,其意义是极具象征性的,它使得由山、河、海所主导的世界空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公路的出现,使得人力的因素凸显了出来。很显然,公路是现代社会中的“人”的因素介入自然世界的产物,公路的出现,使得身处世界中的“人”与山川河流之间有了直接的沟通——人类通过公路做到彼此沟通;而不像《山海经》,其中“人”与山川河海的沟通是抽象和模糊的,或者说因为“人”的神力存在,路的存在是可有可无的——距离的远近对《山海经》中的主人公们来说并不重要。而也恰恰是“人”的因素的介入,使得《秦岭记》不同于《山海经》,甚至也不同于“商州”系列,因为这里的主人公身处于加速时代的今天。小说因此有了时代症候或诊断的象征意义。
这就有必要联系到结尾部分。小说最后两节(即五十五和五十六节),对理解小说至关重要。可以说,正是这两节的存在,使得《秦岭记》颇不同于《山本》。在《山本》中,作者还可以感慨着“巨大的灾难,一场荒唐,秦岭什么也没改变,依然山高水长,苍苍莽莽,没改变的还有情感,无论在山头或河畔,即便是在石头缝里和牛粪堆上,爱的花朵仍然在开,不禁慨叹万千。”[1]523《秦岭记》中,作者虽然也在借第五十六节中立水的视角表达这种笃定:“似乎理解了秦岭的庞大、雍容,过去是秦岭,现在是秦岭,将来还是秦岭。”云云。但第五十五节,又写到了张铁匠的儿子内心的“瞀乱”。战火纷飞之下,涡镇倾颓在即,《山本》中的陈先生甚至陆菊人尚且可以做到处乱不惊,《秦岭记》中张铁匠的儿子内心“瞀乱”又是由何而来呢?
立水的顿悟当然没有问题:秦岭始终都是秦岭。就空间的层面看,秦岭似乎并没有大的改变。那么,从时间的角度看呢?就像齐格蒙特·鲍曼在《流动的现代性》中所说,“时间不同于空间,这是因为,它不像空间,它能够被人类加以改变和控制;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分裂因素:一个时空结合中的变化不断的动态角色。”[2]有些理论家则干脆说“现代性就是时间的加速”[3]19。《山本》中的主人公们还不可能感受到时间的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压力,因为彼时,现代化的程度在秦岭地区还不明显。但到了21世纪的今天,情况早已大变。城市化的触须已经深入到秦岭地区的沟沟岔岔,全球化几乎已经影响到中国大地的每一个角落。当下的秦岭人越来越感觉到时间的快速发展所带来的压力。某种程度上,张铁匠儿子的内心“瞀乱”就是这种时间压力的表征。其压力集中表现在人与土地关系的改变上。就当前的状况来看,生长在秦岭中的人们可以不必依附于这一片土地而生存得更好,用《秦岭记》中张铁匠儿子的话说就是“种一年地抵不上打一月工”。因此很多乡民纷纷离开土地,去往城里。那么,对于那些还留在土地上的乡民呢,情况又是如何?此前的生产关系中,人与土地之间构成一种彼此应和的闭合结构,土地上生产的东西主要用于土地上生存的民众的生存之需,土地与人类之间是一种契合的关系,因此可以做到和谐,甚至天人合一。但是现在,这一生产关系在潜移默化中发生着巨变,现代性社会中的“同时期的不同时性”[3]186使得秦岭地区的人们不得不受制于外面开放社会的冲击。即是说,土地对于人而言,其价值不再局限于满足生存之需,而在于能否创造更多的财物和促使资本更快地循环,任何不能加速资本循环的东西,都在这种逻辑面前黯然失色。无怪乎张铁匠再也不打齿耙、犁铧、钢钎和撬杠了,因为这些都已无人问津,用它们生产出来的粮食谷物并不能带来太多的剩余价值;他改而打铁叉和钉子,因为这些直接和资本的再循环密切勾连在一起。张铁匠慢慢悟出了这一道理,但为时已晚,故而只能拂袖而去,除了撒一掊眼泪,别无他法。可以说,贾平凹所想不明白的、最无奈的,也不甘心的,正是这点:技艺得自祖传的张铁匠,到最后打出来的却是“这些小零碎”,这可是没有多少技术含量的物件啊!由此不难看出,贾平凹一方面在慨叹传统技术“灵韵”的消失,一方面也在表达对时间所暗含的“分裂因素”的忧虑。贾平凹所执着的,还是他一直以来念兹在兹的常与变的辩证关系。他看重“常”的存在价值,但也无法阻挡“变”的推动力量,两者之间的关系,既令他痴迷,也让他感到无奈。《山本》(甚至《古炉》)中的贾平凹之所以能淡定,是因为这部小说处理的是现代时期的秦岭,一旦笔触伸入到全球化的当下,贾平凹就不可能淡定了。虽然贾平凹曾一度呼唤乡土社会的改革,写出诸多乡土改革文学的代表作品,但改革带来的负面效应(传统的有价值的事物在改革的进程中变得可疑了),以及现代化进程对自然生态造成的破坏终究让贾平凹不安,这种不安在《浮躁》《商州》《秦腔》和《老生》等作品中都有表现,在《秦岭记》中更是表现为对物件的“灵韵”的渐渐消逝的喟叹。时间的加速发展,令贾平凹措手不及。越想留住什么,似乎到头来什么也不能留下。可以说,正是源于对时间加速发展的恐惧,《秦岭记》的最后一节中,贾平凹才试图通过回溯仓颉造字时的情境,来回避时间的加速发展。
故事结尾立水超然物外的顿悟(第五十六节),很容易让人想起《山本》的结尾部分陈先生的辩证法命题:“常”与“变”彼此蕴含、互相生发。但这只是看似,因为立水的顿悟,并不是基于佛教式的禅宗或儒家世界观,而基于哲学、文学、音乐和美术的三年学习经历之后的体悟;其中暗含的反讽不难发现。毕竟,所谓哲学或文学之名,早已不再是古代中国的哲学或文学,而是西方的理论旅行传入中国后的现代性的产物,即是说,这些学问是现代性进程中的构成部分。可见,贾平凹是用“变”来思考“不变”(即“常”),而且这是全球化时代的“变”。仓颉造字时所体会到的忘我和天人合一,早已被加速时代的今天的现实所打破,要想用“仓颉创造的文字”充分表达当前时代的现实,难免会有失语和言不及义之处。可见,立水的顿悟和不着一字,并不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实在是他内心的混沌,难以落笔成字、点字成文。既然混沌一片,又何来与之对应的文字呢?立水想“在仓颉创造的文字中写出最好的句子”,最后只能是把自己静默成不动的若木和石头。
《秦岭记》中,贾平凹似乎想表明一点,即所谓变与常、立言与无言、多与少,但其实是没有区别的,或者说是辩证一体的。小说中,有麻县长所写《秦岭草木记》的部分摘录。这自然可以看成是《秦岭记》的“戏中戏”式的嵌套——《秦岭记》嵌套着《秦岭草木记》。其中有这样的内容:“读懂了树,就理解某个地方的生命气理。”“树的躯干、枝叶、枝间、表情,与周遭情形的选择,与时间的经历,与大地的记忆,都不是无缘由地出现。”这分明是贾平凹自己的口吻。但也透露了以下充满悖论的两点。第一,与“树”相关的草木动物,它们之间彼此关联、气息相通,构成一种所谓“大地的记忆”,但这些都需要作为主体的“人”去把握和体悟;第二,这些草木动物之间的和谐关系,又因为“人”的存在而被打破,“人”实在是和谐关系的破坏者形象。那么,作为主体的“人”,既然是破坏者的形象,又如何能深深体悟其中满布着的“时间的经历”和“大地的记忆”呢?破坏者和体悟者之间能否达成有效的平衡?如果不能达成,所谓体悟和把握,都是无从谈起的。贾平凹似乎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或者说他把这个难题提出来了,而没有去做解答。
三、故事体和笔记体
纵观贾平凹的创作历程,不难发现,他始终在故事体①和笔记体之间摇摆,甚至一度彷徨。贾平凹早年曾写作“商州”系列(即“商州初录”“再录”和“又录”),中间亦有涉及,临到最近又有《秦岭记》出现。可以说,笔记体的写作贯穿贾平凹创作生涯的始终。表面上看,笔记体的篇什之间仅有似有似无的联结,故事体则讲求故事人物的连贯、紧凑和起承转合。这当然是显层次的观察。就深层次而言,两种文体的差别实在是贾平凹内心矛盾和紧张的体现。《山本》虽然写的是动乱频仍的现代时期的秦岭史,但作者内心却是笃定的。他十分清楚,任是炮火连天,秦岭中的“常”的因素和恒定的东西并不会有根本的改变。但是在《秦岭记》中,隐匿其间的作者的内心却是“瞀乱”的,因为他深深地感觉到了时间的加速发展所带来的冲击,他既无法抗拒,又无从把捉,小说结尾,虽然主人公立水获得了超然物外的顿悟,但这种顿悟里面显然有着难以克服的矛盾和悖论。
同样是有意搜集关于秦岭的故事,为什么贾平凹要创作出风格殊异、厚薄悬殊的两部作品?这里有必要从两部作品所属的文类特征入手。如果说秦岭是一个能指的话,文本的写作就可以理解为朝向能指的所指的建构,但对两种文体而言,其建构过程显然是不同的。故事体和笔记体的最大区别在于,故事体的情节并不具有单独的价值,其价值表现为通过一个个情节编织成一个整体的故事,而在笔记体中情节和人物却是独立的,一个情节(或者说每一篇什)就是一个故事,笔记体中的故事和故事之间、人物和人物之间,彼此并不勾连。因此可以说,故事体写作,体现出来的其实是一种功能论阐释学实践。小说中首尾连贯的细节,就像一个个功能单位,旨在达到对预设的阐释学对象,也即秦岭这一能指的有效阐释。其结果是把具有无限可能性的能指化约成了有限的所指。这种化约,一方面使得有关秦岭的故事杂凑成了一个时间闭合的有头有尾的整体,同时也内在地保证了作者或主人公们的笃定,即是说,只要这种闭合结构不被破坏,他们内在的笃定就不会坍塌。与之相反的是,笔记体则可以看成是一种整体论象征感应说的构建,即意在从无数的所指(每一篇什或每一则故事构成为具体的所指)出发达到能指的构建,这样一种建构,倚靠的是感应和顿悟,以期把众多的篇什建构成一个整体。
历史地看,笔记体小说的重要源头之一可以追溯到《山海经》。《山海经》的出现,对志怪小说的生发有很大影响,贾平凹的笔记体多以此为摹本。就《山海经》所代表的笔记体小说而言,其颇类似于福柯所说的16世纪“相似性的语义学网络”[4]18和巴赫金所说的“意想不到的毗邻关系”的表征。在福柯看来,这是由“适合”“仿效”“类推”和“交感”关系所组成的“网络”[4]18-27。在巴赫金那里,这种毗邻关系最重要的表征即所有的事物都是按照它们的本性自由地结合起来[5]358。概言之,笔记体中,篇什、人物和故事之间,处于一种奇怪的因应关系中。表面上看,它们彼此间毫无关系或逻辑而言,各个故事似乎讲述的是彼此不同的事件,但实际上又具有内在的关联,彼此应和、相互感应。这些都一再表明,人与其所处的世界和自然是连为一体的,彼此有着神秘的联系。那么,需要我们做的,无非就是把它们记录下来,并建立起其中的神秘关联。在其中,时间乃关键因素,其既是抽象模糊的,又具有“有效生长”和“循环往复”[5]398-401的特性。“在个人生活没有分离出来、时间完全统一这种条件下,从生长和繁殖的角度看,应当直接毗邻的有如下的现象:交媾和死亡(大地的播种、受孕),坟墓和女人受孕之怀,饮食(大地的果实)和死亡、交媾,如此等。属于这一系列的还有太阳活动的不同阶段(昼与夜的交替,四季的交替);太阳在这里和大地一样,是生长、繁殖事实的参加者。所有这些现象都卷入一个统一的事件中,只是各自从不同角度来说明同一个整体事物,即生长、繁殖和体现生长繁殖的生活。”“这时,毗邻关系中的所有成员(整体的所有成分),都具有同等的价值。”[5]402据此可以看到,这里存在着彼此对立的景观,其中,对立的一方是零碎的事件、人物和故事,另一方则是“统一的事件”“同一个整体事物”与“完全统一”的时间,表面看来,两极互不相关,但其实是联系在一起的,它们之间有着内在的关联,或者还可以一方是现象表征,另一方乃本质所在。笔记体所要做的就是把这些彼此关联的事件和人物组合在一起,至于能不能从它们的表象中把内在的神秘关系揭示出来,既是对作者,也是对读者的考验。
但这种情况,在《秦岭记》中有了较大的变化。其变化表现在小说中引入了线性的时间观,线性时间的引入使得小说在时间意识上呈现出内在的分裂,最明显的表征就是,小说有两条线索,彼此各行其是。即是说,时间在小说中是以两条线索穿插展开的,一条是相对明晰的时间线索,这一线索主要指向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城市化、全球化进程,一条是相对模糊的时间轴线,看不到具体时间的影子。这也决定了小说中,大凡涉及到“变”的主题时,时间的轴线总是相对明晰的。大凡涉及“常”的主题的时候,时间的轴线则显得模糊不清。贾平凹虽尝试把两条线耦合在一起,但结果显示,他其实是在做着“无用功”。其较为典型的例子是第一节中和尚与黑顺的死。通常意义上,得道高僧的死叫圆寂或坐化,小说中“和尚尸体在窟里并不腐败”,仍旧是“全身肌肉紧致,面部如初,按之有弹性”(第一节)。黑顺自跟随和尚之后,处处向和尚学习,自以为“也该功德圆满,便在窟寺(即和尚圆寂后村民为和尚修的小庙——引注)下的旧池址上放置一木箱,他坐进去,让人把木箱钉死”(第一节),但换来的却是腐烂的白骨。在这里,黑顺的死所呈现的其实就是同中之异的表征,之所以如此,显然与时间的介入有关。具体时空在和尚那里既是形相,也不是形相,因此仅仅纠缠于是什么或不是什么,是无法看到背后的本相的。比如说他“看着放在脚旁的藤杖,觉得是条蛇,定睛再看,藤杖还是藤杖。”(第一节)这一“是—非—是”的闭合结构,显示出来的就是对具体形相的超越和对本相的指认:这时候的“藤杖”显然指向超越具体时空束缚的抽象内涵,即不是那一个“藤杖”,而是作为类的“藤杖”本身。黑顺则始终为具体形相所囿,他看到“将飘落的树叶一一衔走”的净水雉,就说“今黑里做梦,我也做净水雉”(第一节)。可见,净水雉的存在在黑顺眼里是有具体时空限制的量的存在,他看不到背后的“能指”(能指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类的属性)的存在,因而只能在梦里做净水雉,而不可能成为现实当中的净水雉。
因此不难看出,小说从第一节开始就把两种时间观内置其中了,其中暗含的矛盾和悖论,贯穿始终,或者说决定了笔记体小说的整个反讽式结构,小说的内在紧张关系自此得以显现。这一紧张关系,在豆沙垭的豆在田那里同样有极具症候性的显现。豆在田把蛇视为枯木,最终在睡眠中被蛇咬死(第八节)。豆在田视蛇为木的细节,让人想起第一节中和尚把藤杖视为蛇又不是蛇的辩证法观念。基督教传统中,蛇是欲望和幻化的象征(也即魔鬼撒旦的形象);《秦岭记》中,蛇的形象同样具有宗教色彩,只是这里还掺入了佛教的因素。在这里,蛇的形象具有双重性内涵,其既是欲望和幻化的象征(在豆在田那里),也是形相。豆在田不切实际的“幻想”品性被时代的浮躁之气鼓噪膨胀成了欲望,其表征就是为了出风头拿着三张伪造的老虎照片到县政府邀赏,并向采访他的记者索要采访费。因此,豆在田被蛇咬死既象征着其被欲望所吞噬,同时也意味着他执迷于形相,看不到本相。
黑顺和豆在田的例子表明,形相和幻相(欲望就是一种幻相)都是罩在人们头上的迷障,只有去除这一迷障才能发掘其内在本相,就像和尚那样。但问题是,城市化和全球化进程正以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方式渗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思维当中,这是时间的“动态角色”的显现。黑顺死后尸肉的腐烂和豆在田在梦中被蛇咬死,所表明的就是时间的“变”的力量及其造成的伤害:时间的流逝并不是无关痛痒的,而是决定事物和人物内在的因素。相反,时间的“动态角色”在和尚那里却是没有影响力的,或者说时间只是抽象的存在,与事物的本相相匹配,代表着永恒,任岁月流逝,某些东西仍复如此。关于这点,可以从经验命题中得到理解。传统社会中,经验可以超越具体时空而具有普遍的意义,因此是彼此并列和累积的关系,但现代性社会中的经验却具有“时空同一性”的特征,即大都“通过时空坐标来确认”[6],因此经验与经验之间是一种绵延、连续和递进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经验的失效和更新就是常有的事情。即是说,线性时间观的进入使得传统社会中形成的经验逐渐贬值和失效:任何不能在这种线性秩序中占据一定位置的经验,都可能会贬值、失效甚至被取代。笔记体小说是传统社会的产物,其中篇什的零散是与传统社会中经验的超越时空性特点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或者可以说,传统社会经验的并列结构内在地决定了笔记体小说中篇什的零散化特点,因此具体时空在其中就显得无关紧要了。
这样来看就会发现,贾平凹的笔记体小说中,正是因为时间因素的介入,使得他的笔记体小说不像古代的笔记体。其创作于20世纪80年代的“商州系列”,时间的线索主要聚焦在20世纪50—70年代。这一时段的中国社会,虽然有着激进革命现代性的侵入,但其对传统社会累积起来的经验的摧毁,却并不是致命的。之所以说不是致命的,是因为随着“文革”的结束,被摧毁的经验又被重建,经验间的关系得以修复。但这种平衡关系,在《秦岭记》中则被打破。其被打破是因为现代化、城市化和全球化密切勾连,现代化的“加速”发展所带来并造成的经验的失效,越来越不可修复。经验的分裂现象日趋凸显,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同样的行事风格,得到的结果却是两样。其集中表现在黑顺和他的和尚师傅身上(第一节),黑顺向他的师傅学习,得到的结果却是两样。第二,同一种经验无法在代际之间传递下去。其集中体现在张铁匠和他的儿子身上(第五十五节)。这一头一尾(第五十五节属于倒数第二节)两个方面的情况都在表明,经验的分裂不可避免地出现,而出现这一分裂的原因,则主要是时间的因素。因为时间不再是循环往复的了,不再只专注于生长和繁殖,而是倾向于生产和增值。时间具有了线性维度。这就使得经验的修复成为难题:时间因素的介入,使得经验坍塌并趋于碎片化,无法重构成一个整体。
这种内在的紧张关系,使得作者在处理时间关系时常常显得进退失据,小说内在的裂缝到处可见。其表现有:一是传统器物“灵韵”的消失和感伤气氛的弥漫。犁铧等大铁器被钉子等“小零碎”取代就属于前者(第五十五节)。“山外的城市”的“日益扩张”,使得秦岭的奇花异木被纷纷移购,无时间的力量即使是以鬼怪的形式表现出来,毁得了一棵银杏树,但毁不了所有的银杏树(第二节)。二是冗余物形态的奇怪存在。冗余物是与失效的经验联系在一起的。当经验的分裂和两重时间冲突而使矛盾无法解决时,从原本“毗邻关系”中游离出来的事物和人便具有了冗余物的特征。在小说中,那些留在村子里未出去打工的青年,是贾平凹特别青睐的冗余物形象。比如说高涧村的苟门扇,“脑子差成”,生命力却极旺盛,成了守村人,说话却神神叨叨。成为附近沟沟岔岔的多余存在(第五节)。比如月亮湾的陈冬,陈冬因为呆傻留在村庄,通过替无法回村的人家祭奠和哭丧,竟活到了八十岁(第十八节)。对这些冗余物,贾平凹既抱有极大的同情,又慨叹其无用无能终被淘汰。
四、结语
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两种文体之间的区别,其实也是两种整体观的区别。故事体小说所代表的是功能论式的整体观,世界具有属“人”的性质,并有一个整体性的存在,我们需要做的是在作为主体的人和作为整体的世界之间构筑一个阐释学的框架,以确立自己的位置和行为方式。笔记体小说所代表的则是象征感应式的整体观,世界是一个先验的整体存在,其中的万物之间彼此感应、相互应和,我们所需要做的是在彼此不相干的人事之间建立起相互感应的关联,以确立自己的位置和行为方式。换言之,故事体对应的是现代性,其所建构的是“人”的主体性,而笔记体则内在于传统社会,属于“非人”范畴。
因此不难看出,就故事体的写作而言,世界的整体性架构是一种阐释学实践的结果,即是说,通过故事的编织可以人为地建构起世界的整体性架构。但对于笔记体而言,世界的整体性架构却需要两方面的合作,就创作而言,需要象征联结,就读者而言,则需要顿悟。这当中,一旦构成笔记体的经验②(也即一个个具体的故事)之间的“可传递性”和“可交流性”(也即毗邻关系)被打破,整体性就无法完成。同样,如果宏观世界观在作者那里或创作之初就有着不可弥合的裂缝,这样的笔记体也就只能是碎片化时代的表达,而不可能做到阅读过程中的顿悟。以此观之,写作“商州”系列时的贾平凹,还能通过经验的重构和修复,建立起某种总体性。《秦岭记》中这一总体性重构的努力,则因为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而变得不再可能。这种不可能,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线性时间的介入所导致的经验的贬值。可见,对于笔记体而言,如果处理不好时间的问题,其重建都只能是一厢情愿。《秦岭记》既显示出贾平凹重构的努力,也显示出其重构的虚妄。
《秦岭记》看似“秦岭志”,文本中,不论是实有,或非实有,贾平凹所关注的还是“人”。《秦岭记》所涉及的,仍旧是“人学”命题,也不是生态学意义上和谐和保护自然的主题,甚至也不是中国古代哲学观念中的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表象。这样理解《秦岭记》都有其片面性,“人学”命题的难题,既内在地决定了这部笔记小说的深度,也决定了其限度。
注释:
① 所谓故事体,简言之,就是小说中的故事有其自身的发展线索和内在的逻辑,而不是宿命、神意或隐喻的象征。
② 这里需要注意区分故事和故事体。故事是与经验相对应的,故事体则是现代性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