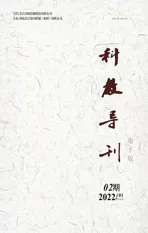真实源于内心的创伤
——浅谈鲁迅《伤逝》的创作心理
2022-03-17段文迎
段文迎
(山东省聊城一中 山东·聊城 252000)
艺术源于生活。想必鲁迅先生定能对人世间的情感参透一二,方能创作出情感细腻而又悠长深刻地涓生与子君。想要更深层次地探究其创作《伤逝》时的心理动态,必然离不开鲁迅创作时特定的生活状态与情感状态。实际上,鲁迅先生在1926年12月29日写给韦素园的信中就曾否定过这部小说与自身情感生活状态的关联。但是一句“做人真愈做愈难了”,亦道出了鲁迅当时所处的尴尬境地。当知,1925年10月21日为《伤逝》的创作完成之日,而这一段时间,正处于鲁迅与许广平的热恋时期[1]。情趣相投,自由热烈,自然是鲁迅先生精神上的极大愉悦,但源于封建婚姻下的重重社会道德压力以及对人生的苦恼对鲁迅先生而言亦是不可解脱。正如《伤逝》中的涓生与子君。
在写到涓生与子君确定恋情的文字中,可谓颇为别致的细致描写。
我的心宁帖了。
她总是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奇的光泽。
——没有见过,也没有再见的绯红;孩子似的眼里射出悲喜,但是夹着惊疑的光,虽然力避我的视线,张皇地似乎要破窗飞去。[2]
在这里描绘的是恋人之间的场景,却又像是老师面对于自己敬仰又充满好奇心的学子。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涓生的眼里,子君是自己的恋人,却常以稚气浓郁的“孩子”来对其称呼描绘。就师生恋而言,两人的年纪相差甚远,而身为长者、多经世事的鲁迅先生自然对这些有着别样的感受与体会,所以小说中子君的勇敢、稚气才格外显得真切而动人。再去细品《伤逝》中涓生在会馆中等待子君时的寂寞、苦苦思恋而辗转反侧的精微与传神,不禁让人感叹,“倘非身在其中,焉有如此笔墨”。事实也确实如此,身处热恋时期的鲁迅先生,怎会在创作过程中完全搁置浓烈的亲身情感体验而凭空虚构创造他人情感呢?
《伤逝》中涓生与子君初恋时微妙的心理描写让人动情,而更令人感到惊异的是两人的恋爱悲剧,以及涓生所表现出来的痛苦悔恨的心理,让人刻骨铭心,不忍卒读。正是这样的情感抒写,才使得《伤逝》不仅以其浓郁感人的情感性牵动读者的心弦,更是以其深刻透彻的思想刻画在同时代甚至于中外文学史上的所有爱情小说中独树一帜。这也正是鲁迅先生的思想独到之处,在小说创作中对主人公情感问题思虑周全,感受敏锐而痛切。既然涓生与子君的恋爱在一定程度上是影射的自己,那么为什么在爱情结局上却是这样天差地别,且涓生的痛悔之情又从何而来?众所周知,鲁迅先生与许广平相恋时与朱安并没有离婚,像这样的婚外恋在当时的社会下必然是不能被接受的。而鲁迅先生“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所以作为这一复杂的情感纠葛中的鲁迅先生自然更是诸多顾忌,忧心思虑,对这段感情的前景亦是渺茫难测。鲁迅先生自然明白,若只为一己之私,作为原配妻子的朱安必定在冷眼中陷入绝境甚至死去。而与自己的心爱之人建立起来的新生生活必然也要经历社会上怒风恶浪的重重冲击,且随之而来的还有可能是经济上的压力,生存境况的窘迫。但是鲁迅先生要决心获得新生,必然而然要直面这一严峻的人生现实。因此,鲁迅先生在执笔创作时,也会自然而然地“因情立体,即体成势”[3],巧妙地将重重困难压力糅合在一起进行深度的艺术加工和创造,从而成就了爱情小说《伤逝》的浓重的悲剧色彩。也就是说,小说中所展现的涓生与子君美好的感受以及幸福的心理是源于鲁迅先生本人的恋爱真实感受,而小说的悲剧结局则是因为鲁迅先生对即将开始的新生的忐忑及深刻忧虑。
作为恋爱中稍微年长的鲁迅先生,因为看到了社会中的太多不幸,因而虽热情但不失清醒。虽然预测到了最坏的结局,但是对此却束手无策,无力回天,只能既无奈亦无助地任其发展,在极度忧虑与痛疚中等待有可能降临的最坏的结局。这样,回过头去再看《伤逝》的开篇:
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4]
就不难理解,在一篇小说开头为什么如此突兀而又震撼人心。这确是涓生经历这一场恋爱劫难之后的痛彻肺腑的言论。但是人们往往忽略的却是“如果我能够”这五个字所蕴含的深刻意味。世态炎凉,世道艰难,作为新婚丈夫,涓生不仅不能够担起护卫家庭的责任,反而却仓皇求生,自顾不暇,更甚者视子君为自己生活的累赘。便萌发离弃之意,最好子君主动地“决然舍去”,要么死去,否则自己就没有生计,生活没有希望,最终只会受子君拖累并与之“一同灭亡”。尽管这一念头刚刚萌生就“立刻自责、忏悔了”,但也暴露出涓生内心深处的幽暗与自私。对此,涓生亦对自我做过深刻反思:
我看见我是一个卑怯者,应该被摈于强有力的人们,无论是真实者,虚伪者。[5]
正是这样的卑怯,使得涓生能做的就是热切地希望子君主动离弃自己,尽管预感到这样会导致子君的灭亡;既然如此,涓生为了解脱生计之累依然舍弃子君而不惜子君最终死去,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子君之死,凶手不仅仅是社会的压力、世人的冷眼,还有涓生的鄙弃。所以,当得知子君死去时,涓生所感受到的不仅仅是一般的自我痛责与诅咒:
我愿意真有所谓鬼魂,真有所谓地狱,那么,即使在孽风怒吼之中,我也将寻觅子君,当面说出我的悔恨和悲哀,祈求她的饶恕;否则,地狱的毒焰将围绕我,猛烈地烧尽我的悔恨和悲哀。我将在孽风和毒焰中拥抱子君,乞她宽容,或者使她快意……[6]
虽然鲁迅先生担心新生的幸福是否能够抵受住社会风雨的强烈冲击,但立场气概远比自己坚定果敢的许广平绝不会如小说中的子君一样悲苦丧命。而朱安不同,一旦离弃,必然悲惨。既然如此,鲁迅先生又不能断然终止与许广平的新生恋情去勉强维持旧的婚姻,一定意义上来讲,鲁迅先生犹如小说中的涓生一样亲手将他们推向深渊。与其自造罪孽而使灵魂不安,倒不如朱安事先死去来免去自己的罪责。在与许广平的来往信件中,鲁迅先生针对许广平面对哥哥和父亲去世而嫉恨那些与其父兄同龄而活着的人们时,有这样颇费思量的话:
“而我正相反,同我有关的活着,我倒不放心,死了,我就安心,这意思也在《过客》中说过,都与小鬼的不同。”[7]
这样含蓄模糊的言语隐含着难言的非常之情。结合鲁迅先生具体的生活处境,联系特定语境,我们就不难推论出朱安的存在是其生活进退维谷,难以安心舒神的心结所在。只有朱安死去,他才能无所顾忌地与许广平并肩携手开辟新的生活。在这段话之后,鲁迅先生谈及自己思想时就常常处在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矛盾之中,还特别指出“我的思想太黑暗”。这件事之后近半年,鲁迅先生终于决定在婚姻问题上实行“个人主义”,离弃朱安,与许广平一起开始新的生活。
小说的结尾可谓意味深长:
我活着,我总得向着新的生路跨出去,那第一步,——却不过是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
我仍然只有唱歌一般的哭声,给子君送葬,葬在遗忘中。
我要遗忘;我为自己,并且要不再想到这用了遗忘给子君送葬。
我要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我要将真实深深地藏在心的创伤中,默默地前行,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8]
涓生在新生路上的第一步的艰难也正是鲁迅先生走向新生过程中的沉重与艰难。“将真实深深地藏在心的创伤中”,又怎会轻易遗忘且在作品创作中不漏痕迹呢?像鲁迅先生这样的情感真挚之人又怎会在这样的世间矛盾中如此简单的解脱。抒于笔墨,大概是他真正能够聊以自慰的方式了,这也正是鲁迅之所以创作《伤逝》的深层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