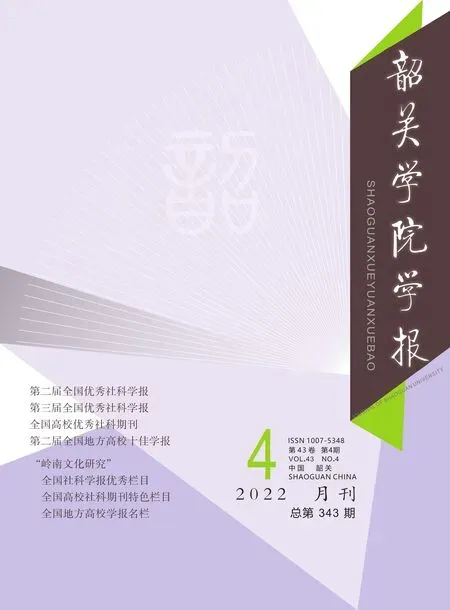王士禛《古诗选》成书时间及编纂缘由新考
2022-03-17胡韬
胡 韬
(桂林学院 语言文学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0)
《古诗选》是清代学者王士禛编纂的一部诗歌总集。此选分五七言诗两部分,收录诗歌的范围自先秦直到宋元,选诗范围较广,与当时诗坛宗唐宗宋、分立门户的态度截然相反,显示出一种包容的胸襟。《古诗选》主题是复古,即追溯汉魏诗歌传统。又因王士禛主盟诗坛及姜宸英、叶方蔼、蒋景祁等人的助力而得以广泛流传,后来更有桐城派将《古诗选》和《今体诗钞》作为学习诗歌的教科书。《古诗选》作为王士禛众多诗歌选本中的一种,对于研究康熙年间唐宋诗论争演变、王士禛诗歌选本、王士禛诗论思想等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一、王士禛《古诗选》初稿时间
《古诗选》成书时间的表述见于《渔洋山人自撰年谱》:“康熙二十二年癸亥,五十岁。在成均。是岁,撰五言七言古诗,姜西溟宸英序之。”[1]5087即《古诗选》成书于康熙二十二年,且姜宸英序之。据此,欲考证《古诗选》成书时间先需考辨姜宸英作序的时间。此可根据梁同书辑《明清两代名人尺牍》中王士禛写给姜宸英的书信来作推论。
由于条件所限,见不到梁同书辑《明清两代名人尺牍》,故只能转引蒋寅《王渔洋事迹征略》一书中所载:
昨文驾入都,以久病甫起,人事如蝟集,匆匆无暇。比卜日奉邀为文字饮,而轩车已返潞河矣。(中略)尊集一册,缄付来手。附启者,弟客岁偶撰五言诗十七卷,凡例寄请教正,欲得大序以发明此书之旨。此书成,未敢示人,唯讱庵读学见之,颇为不谬。此处正觅解人不得,唯先生了不异人意耳。”末署日期为端午后一日。[2]272
关于此信落款时间,蒋寅在该书新旧两版中所记不同:2001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本所记为康熙二十三年甲子(1684)五月初六;2014 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本记为康熙二十一年壬戌(1682)五月初六。蒋寅对新版的改动并未详述原因。但学界恐少有人注意到此差异,未能有疑,更未能在引述材料时加以辨析,这就造成了诸如谢海林①谢海林在《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14 年第1 期的《王渔洋〈古诗选〉的刊布及其影响史》中征引此条材料时所用的正是错误的时间:“康熙二十三(1684)年‘五月初六,致函姜宸英,告以编成《五言古诗选》,请为之序’”。除此篇外,谢海林在《文艺评论》2013 年第6 期的《王士禛〈阮亭古诗选〉编撰缘由、背景及旨向刍议》中征引此条材料时仍用的是错误的时间:“次年‘五月初六,致书姜宸英,告以编成《五言古诗选》,请为之序’”。另由于这两篇论文刊登年份均为2013 年,推测谢海林可能也并未看到2014 年版《王渔洋事迹征略》。倘若他在征引材料时能够细读原文,查阅下“讱庵”的生卒年,再推敲一下“客岁”,便可避免此问题,但他并未对引述材料作考辨,是为疏漏。、王悦①王悦在2018 年硕士论文《王士禛〈古诗选〉研究》中考证《古诗选》成书时间时征引此条书信材料仍为2001 年错版,并据此得出“《古诗选》从萌芽到完成应在康熙二十一年七月至康熙二十三年即1682-1684 年”的错误结论。但彼时2018 年的硕士论文又怎会没有看过蒋寅2014 年版的《王渔洋事迹征略》呢?此甚为疏漏。等人混用不辨而致误的情况。
此封书信原是因姜宸英求王士禛评点其集,王士禛便借机也向姜宸英求序。“弟客岁偶撰五言诗十七卷”,“客岁”乃“去年”之意,此句意谓王士禛于去年偶撰五言诗十七卷。又《渔洋山人自撰年谱》中所载《古诗选》乃成书于康熙二十二年,依此推理:王士禛求序之信应为康熙二十三年,则2001年版《王渔洋事迹征略》所记符合。
但事实并非如此,所证有二:
一则乃康熙二十二年《古诗选》成书之时,姜宸英序已成,故求序之信不可能后于序而出,则2001年版《王渔洋事迹征略》所记不符,以下详述之。
王士禛《香祖笔记》卷九中有载:“余初撰五言七言诗成,京师同人钞写,只有七部,即蒋京少景祁所刻阳羡本也。”[1]4667《古诗选》成书后,最初以手钞本的形式在京师流传,后其弟子蒋景祁据钞本刊刻成“阳羡本”,此本是手钞本后刻本中最早的。而在《古诗选》的诸多刻本中,《古诗选》三十二卷(四部备要本)是中华书局于1929-1936 年用丁氏仿宋活字排印后陆续编辑出版[3],扉页内印有“上海中华书局据康熙原刻本校刊”的字样[4]。因此四部备要本中有姜宸英写的《阮亭选古诗原序》,可推康熙原刻本中已有此序。而阳羡本又是据此前流传的手钞本校成,即王士禛《古诗选》在康熙二十二年初撰成时就应已收录姜宸英的序。换言之,在康熙二十二年《古诗选》成稿之前王士禛应已写信向姜宸英求序。
二则此信札中有言:王士禛“去年”写成《古诗选》后只给叶方蔼一人观之,又叶方蔼卒于康熙二十一年四月,则若按2001 年版《王渔洋事迹征略》中该信写于康熙二十三年五月,则《古诗选》初稿应于康熙二十二年五月完成,但这显然与叶方蔼生卒年不符,故2001 年版《王渔洋事迹征略》所记不准,以下详述之。
上文所引梁同书辑《明清两代名人尺牍》中有一关键处:“此书成,未敢示人,唯讱庵读学见之,颇为不谬。”即《古诗选》初稿写成后,王士禛只给“讱庵”一人观之。“讱庵”乃清代叶方蔼号②有些文献资料中常将叶方蔼之号“讱庵”误写成“纫庵”,故此处特予以说明。,《渔洋续诗》卷十四载诗《讱庵翰长招同荆岘侍讲羡门编修过善果寺》,蒋寅书中对此也有记:“康熙二十年四月十八日,浴佛日。叶方蔼招同汤斌、彭孙遹游善果寺。”[2]263另据蒋寅《王渔洋事迹征略》载:“康熙十九年,王士禛在翰林院侍读任,满掌院学士为库勒纳,汉掌院学士为叶方蔼。”[2]254王士禛与叶方蔼同朝为官,又浴佛日共游,可见两人关系友好。又《清史稿》中有载:
十七年,充《鉴古辑览》《黄舆表》总裁、经筵讲官,直南书房。上勤于典学、故事……上特意属方蔼,兼掌苑学士,兼礼部侍郎。十七年,召试博学鸿词,命方蔼阅卷,总裁《明史》。[5]7851
可见康熙皇帝对叶方蔼学识的认可。如此便不难理解诗选初稿既成,王士禛只给叶方蔼一人观之了。
又叶方蔼于康熙二十一年四月二十八日卒于京,据《清史稿》载:“二十一年卒,遣奠茶酒,赐白金二百。”[5]7852即《古诗选》初稿写成最晚应在康熙二十一年四月前(叶方蔼卒前),则2001 年版《王渔洋事迹征略》所记有误。而若以2014 年版的《王渔洋事迹征略》所载康熙二十一年五月初六的时间反推之,则康熙二十年五月前后《古诗选》初稿编成,二人同朝为官,见面机会甚多,又于康熙二十年四月共游善果寺,那么王士禛将诗集初稿给叶方蔼观之的条件充分且符合叶方蔼生卒年实际,故2014 年版所记时间成立。又姜宸英《苇间诗集》卷三有《辛酉十二月初至京投宿慈仁寺袁君寓舍集杜赠之》,可知康熙二十年十二月姜宸英至京师,住在慈仁寺。则康熙二十一年五月二人书信往来也更便利。
综上所述:梁同书辑《明清两代名人尺牍》中王士禛写给姜宸英的信笺落款时间应以2014 年版的《王渔洋事迹征略》所载康熙二十一年五月初六的时间为准。且据王士禛所言及叶方蔼生卒年可知:康熙二十年五月前后《古诗选》初稿编成。
二、京师祝园集会非《古诗选》编纂缘由
过去诸家皆依蒋寅所述:“王士禛编选《五七言古诗选》的直接刺激是康熙二十二年七月与徐乾学、陈廷敬、王又旦、汪懋麟在北京城南祝氏园亭的一次集会有关。”[6]33“王士禛因徐乾学之言……着手编选《五七言古诗选》。”[6]34为《古诗选》的编纂缘由,即《古诗选》的编纂与京师祝园集会有关,乃顺应弟子徐乾学之意编成。
但这次集会的确切时间还需进一步考辨,现摘列两则材料如下:
材料一:徐乾学于王士禛《十种唐诗选》书后所记:
往岁郃阳王黄湄、江都汪季角,邀泽州陈说严、新城王阮亭及余五人,集于城南祝氏之园亭为文酒之会……是为癸亥岁 孟秋之月……回思城南之会荏苒遂已十年……康熙三十一年嘉平月徐乾学健庵书。[7]446
文中共有两处线索谈及城南山庄集会:一是徐乾学落款的“康熙三十一年嘉平月”,即康熙三十一年十二月,由此反推十年前乃康熙二十一年十二月;二是“癸亥岁孟秋之月”,“孟秋之月”指农历七月,“癸亥年”应指康熙二十二年。又据“遂已十年”可知至少应是康熙二十一年十二月前。
材料二:汪懋麟所作的《城南山庄画像记》,载于《百尺梧桐阁集》卷三:
懋麟自顺治末受知于济南王公……乙巳得交郃阳王公,丁未得交昆山徐公,已酉应阁诗入京,得交泽州陈公,相与论诗有合焉……又二年辛酉王公始来给事门下,陈公继入再领翰林,五人者始聚而不散……于是壬戌七月相聚于城南山庄,赋诗饮酒相娱乐,命兴化禹生貌五人像为一图,属懋麟为之记。[8]
此中谈及城南山庄相会时间为:“壬戌七月”,即康熙二十一年七月。
观上述材料,可知此次集会地点乃北京城南祝氏园亭,参与人员共五人,分别是王士禛、王又旦、徐乾学、陈廷敬和汪懋麟。虽两则材料对集会时间有出入,但都在共同时间跨度内,即康熙二十一年。考辨两处材料记录时间,第一则是站在十年后回顾往昔,而第二则从“属懋麟为之记”可知应写于集会结束不久。故第二则材料更具时效性,也更具可信度。故此次集会的时间应为康熙二十一年七月。而蒋寅书中对此次集会的时间记载也需明确:2013年11 月初版的《王渔洋与康熙诗坛》中所记“康熙二十二年七月”有误,2014 年版的《王渔洋事迹征略》中所记“康熙二十一年七月”可信。
前文已考辨《古诗选》初稿完成的时间范围,据此推断:康熙二十一年七月的北京城南祝氏园亭集会并非《古诗选》的编纂缘由或动机。因为在这次集会前,此诗选初稿就已完成。
故王士禛编纂《古诗选》不仅与此次集会无关,且非顺应徐乾学之意编成。则蒋寅在《王渔洋与康熙诗坛》《王渔洋事迹征略》《〈唐贤三昧集〉与王渔洋诗学》等书中所言有误。然学界仍多依蒋寅论述为据,如谢海林在其论文中曾多次引用:“《阮亭五七言古诗选》编撰的直接诱因是徐、汪唐宋诗之争”[9]“综上所述,王士禛编纂《古诗选》的直接诱因是汪懋麟错解其师法宋人的真实意图,接受徐乾学邀请而撰成的”[9]“王渔洋编纂《古诗选》的直接诱因是康熙二十一年(1682)秋应徐乾学之邀”[10]“康熙二十一年(1682)七月,渔洋应徐乾学之邀而编纂《古诗选》”[11]等。而王悦在其2018 年硕士论文《王士禛〈古诗选〉研究》中论述《古诗选》的编选动机时也提到:“王士禛编选《古诗选》与徐乾学、汪懋麟在城南祝氏园亭集会上的唐宋诗之争有一定的关系”“王士禛编选《古诗选》外在的原因就是汪懋麟、徐乾学两人的唐宋诗之争”“可见王士禛编选《古诗选》与徐乾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正是徐的劝说使王士禛付诸行动”[3]10-12等字句,可见考辨王士禛《古诗选》编纂缘由的重要性。
此集会既已非《古诗选》编纂缘由,是否另有他意?徐乾学在《十种唐诗选》后记中可提供线索:
余与诸公共称新城之诗为国朝正宗,度越有唐。季角为新城门人,举觞言曰:“诗不必学唐,吾师之论诗,未尝不采取宋、元。辟之饮食,唐人是犹粱肉也,若欲尝山海之珍惜,非讨论眉山、山谷、剑南之遗篇不足以适志快意。吾师之弟子多矣,凡经指授,斐然成章,不名一格。吾师之学,无所不该,奈何以唐人比拟?”余告之曰:“季角君新城弟子升堂矣,未入于室……先生诲人不倦,因才而笃,各依其天资,以为造就。季角但知有明前后七子剽窃盛唐,为后来士大夫讪笑,常欲尽祧去开元大历以前,尊少陵为祖,而昌黎、眉山、剑南以次昭穆。先生亦曾首肯其言,季角信谓固然,不尊诗之源流正变,以合乎国风雅颂之遗意,仅取一时之快意,欲以雄词震荡一时,且谓吾师之教其门人者如是。先生渔洋前后集具在……其造诣固超越千载,而其体制风格未尝废唐人之绳尺。君熟读自得之,何可诬也……先生何不仿钟嵘《诗品》,杼山《诗式》之意,论定唐人之诗,以启示学者,即今日不须辞费。”先生笑而颔之……今新城先生选定《唐贤三昧集》,又选刻《十种唐诗》,余畴昔倡言可以晓然共喻,回思城南之会荏苒遂已十年。[7]446
汪懋麟认为“诗不必学唐”,乃因其观唐诗犹如“粱肉”,观宋诗却是“山珍海味”,于是提倡作诗应学眉山三苏、黄庭坚、陆游之诗方尽味。徐乾学笑其“升堂未入室”。徐乾学认为王士禛为师注重因材施教,汪懋麟因王士禛肯定宋、元诗而误认为王士禛宗宋祧唐,此乃不妥。而汪懋麟自己论诗弃汉魏唐诗传统,只学宋诗,更为不妥。此材料也曾被诸家看作是徐乾学为王士禛宗唐的辩护。
而后,徐乾学才向王士禛提出:既然连门人学生也不明王士禛论诗真意,何不学钟嵘作《诗品》、杼山作《诗式》,以选本的形式表明自己的论诗倾向,启发海内学者呢?王士禛听闻“笑而颔之”,肯定徐乾学之意愿。至于王士禛受徐乾学所言编纂成何诗选呢?观其时间顺序,其后有《唐文粹》《十种唐诗选》及《唐贤三昧集》依次成书。故笔者认为,此集会的真正目的是辨明王士禛提倡宋诗的缘由,而从此后其诗歌选本中便可见王士禛唐宋兼采的诗学倾向。
三、王士禛《古诗选》的编纂缘由:矫枉时弊,正本清源
相较于明代宗唐之风的盛行,清初诗坛始有宋诗风渐起。黄宗羲提倡宋诗,创立浙西诗派。“他通过对唐诗传统的新诠释将尊唐者对立起来的唐、宋两个传统化为同一个传统”[12],有利于宗唐者接纳宋诗。钱谦益认为作诗要转益多师,其诗学主张兼采唐宋。此时多在肯定唐诗的基础上重视宋诗,至康熙年间遂形成宋诗热。
康熙二年,吴之振受浙西诗派影响,与吕留良、吴自牧等编选《宋诗钞》,在康熙十年刻成。吴之振携多部刻本入京,大量赠予京中好友欲加以宣传,还与陈敬亭、宋琬、王世禄、王士禛等人唱和交游。康熙十一年吴之振在《八家诗选自序》中言:“余辛亥至京师,初未敢对客言诗,间与宋荔裳诸公游宴,酒阑拈韵,窃窥群制,非世所谓唐法也。故态复狂,诸公亦不以余为怪,还往唱酬。”[13]自述论诗不以唐法,但诸公并不怪之。故知康熙十年,京师应已有不少论诗主宋之人。
当时流传的宋诗选集很少,《宋诗钞》的出现立刻引发热议。宋荦在《漫堂诗说》中云:“至余友吴孟举《宋诗钞》出,几于家有其书矣。”[14]可见此书影响。但京师对此书反映不一,如沈荃论诗宗唐,他在康熙十一年为曾灿《过日集》所作的序中则对此学宋诗风持批判态度:“近世诗贵菁华,不无伤于浮滥,有识者恒欲反之以质,于是尊尚宋诗以救弊……且今之好为宋诗者,皆村野学究肤浅鄙俚之辞……此不过学宋人糟粕,而非欲得宋人之精神也。”[15]蒋寅认为这是“清初诗坛对宋诗风最早的反应。”[6]26虽《宋诗钞》有助清初宋诗风的兴起,但并不等同自康熙十年后,诗坛学宋蔚然成风。“在康熙十三年至十五年间,宋诗仍遭轻视。即使有陈廷敬、曹禾这样的爱好者,也未形成风气。”[6]27计东曾言:“自宋黄文杰公兴而天下有江西诗派,至于今不废。近代最称江西诗者,莫过虞山钱受之,继之者为今日汪钝翁、王阮亭。”[16]钱谦益在康熙三年就已去世,故康熙诗坛唐宋之争于他并无太大关系。因而康熙诗坛中的主宋人物便是汪琬和王士禛。
汪琬由宗唐到宗宋,《宋诗钞》风行后他曾作《读宋人诗五首》,对黄庭坚、陈师道、范成大、陆游等宋代诗人进行品评。汪琬在《黄清诗选序》中言:“今且区唐初、盛、中、晚四之,继又区唐与宋……且宋诗未有不出于唐者也。”[17]肯定宋诗是对唐诗的继承,倡导融合唐宋。
王士禛少年学诗由唐诗入门,崇尚七子:“七岁通章句,九岁学唐人诗。”[18]530虽如此但并不排斥宋元诸家:“顺治十三年,山人自乙未年五月买舟归里,始弃帖括,专功诗,聚汉魏、六朝、四唐、宋元诸集,无不窥其堂奥。而撮其大凡。故诗断自丙申始。”[1]5061对宋诗也多有接触:“尝读东坡先生集。”[19]康熙二年在《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第十六首》中有:“耳食纷纷说开宝,几人眼见宋元诗。”[20]批评诗坛忽视宋诗价值,提倡作诗亦可学宋。自康熙四年入京后,眼见诗坛显出宗唐祧宋的弊端,故“中岁越三唐而事两宋,良由物情厌故,笔意喜生,耳目为之顿新,心思于焉避熟。”[1]4749此时的王士禛对宋诗已多有研读,尤喜苏黄之诗。康熙八年,王士禛作《冬日读唐宋金元诸家诗,偶有所感,各题一绝于卷后,凡七首》,其中第一至七首分别为韩愈、杜牧、苏轼、黄庭坚、陆游、元好问、虞集七人[18]483-484,皆是宋元名家。
自康熙十年京师宋诗热兴起后,王士禛并未正式提倡宋诗。一方面,康熙十年吴之振辑刊《八家诗选》时,王士禛还未主盟诗坛,只是“八家”①这八家是一个在京城以龚鼎孽为主盟的群体。详见裴世俊《王士禛传论》,中国戏剧出版社2001 年版第88 页。之一。直至“康熙十二年九月十二日,龚鼎孽逝世”[2]210。另一方面,王士禛于“康熙十二年六月十五奉命为四川乡试主考官”[2]189,离京赶赴四川。同年十一月又因母亲去世而回乡奔丧,在家服丧三年,于康熙十五年五月才回到京师上任。因此,康熙十年京师虽有宋诗热,但彼时王士禛尚未主盟诗坛,且后几年也不在京师,故而其提倡宋诗应在回京前后,如蒋寅所言:“王渔洋大力倡导宋诗,是在乡居服阕入朝以后,即康熙十五年五月后,这时宋诗风在他的倡导下方开始强劲起来。”[6]28
自康熙十六年十月王士禛在京师刻成《十子诗略》,此时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孽已病故多年,王士禛跃起而成为诗坛盟主。裴世俊认为:“《十子诗略》的刊刻是王士禛意欲迈向诗坛领袖的第一步。”[21]而“十子”中如宋荦、田雯、汪懋麟等人诗学倾向皆尚宋,由此王士禛正式提倡宋诗。此外田雯、宋荦、查慎行等人也是清初诗坛宗宋的代表人物。田雯对苏轼和黄庭坚评价极高。
当时与王士禛并称“南朱北王”的朱彝尊,其诗学主张是宗全唐,对七子宗盛唐和清初宗宋的风尚持批判态度。“朱彝尊认为,唐诗是正,宋诗是变,学诗应以正为本”[12]389。他以唐诗为范来丈量宋诗,自然眼见许多不足。此外,冯傅、毛奇龄、施闰章、徐乾学等都是主宗唐,对于宋诗风皆持批判态度。
此时康熙诗坛唐宋之争正激烈,而王士禛于此时主盟诗坛,因此诗坛上无论宗唐、宗宋者都喜欢援引其言作为论据。这就让一些人误以为王士禛抛却汉魏唐音的传统而提倡学宋,从而将宋诗热兴起后的流弊统归究于王士禛,赵执信就是其中之一。为了给王士禛正名,其门人及友人纷纷撰写《渔洋续集》之序为王士禛辩白:施闰章言:
客或有谓其祧唐而祖宋者,予曰不然。阮亭盖疾夫膚附唐人者了无生气,故间有取于子瞻,而其所谓《蜀道》诸诗,非宋调也。诗有仙气者,太白而下,惟子瞻有之,其体制正不相袭。学《五经》《左》《国》、秦汉者,始能为唐宋八家;学《三百篇》、 汉魏、八代者,始能为三唐,学三唐而能自竖立者,始可以读宋、元,未易为拘墟尠见者道也。[18]685-686
施闰章认为王士禛能够兼采宋元诗的前提是对唐诗学有所成,这就将王士禛与宗宋派区分开来,明确他是在学唐的基础下学宋。
徐乾学言:
先生之于诗,择一字焉必精,出一词焉必洁,虽持论广大,兼取南北、宋、元、明诸家之诗,而选练矜慎,仍墨守唐人之声格,或乃因先生持论,遂疑先生《续集》降心下师宋人,此犹未知先生之诗者也。[18]687
这里徐乾学强调王士禛虽兼取宋元诸家,但仍是遵守唐诗传统的。金居敬言:
学宋人诗而从其支流余裔,未能追其祖之所自出,以悟其以俗为雅,以旧为新之妙理,则亦未得为宋诗之哲嗣也。此先生他日之言也……康熙二十三年岁次甲子四月。[18]693-694
此为金居敬转述王士禛昔日所言,即王士禛批评时人学宋诗没有从苏轼、黄庭坚等学起,反而学末流之诗,不得宋诗真意。
曹禾言:
俗学不知拟议,安知变化,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如越人之髢瞽者之,非唯无用,从而仇之。纷纷籍籍,诋曰学宋。不知先生之学非一代之学,先生之诗非一代之诗,其学何所不贯,其诗亦何所不有。彼蚍蜉之撼大树,亦笑其不自量而已……康熙二十年岁次辛酉腊月。[18]690-691
强调王士禛学诗非局限于一代,而是将所学融会贯通。
虽然施闰章和徐乾学之序并未标明时间,但由曹禾和金居敬的落款可推知,康熙二十年至二十三年,诗坛学宋弊病渐起,且将之归于王士禛提倡学宋。但正如其门人所言,此非王士禛之罪,实乃一则时人不解先生提倡宋诗之本意,二则时人不明学诗不可分唐界宋,学宋者更不能否汉魏唐诗传统,不能学末流而不观唐宋名家、大家,否则不得宋诗真意,自陷泥淖。要知王士禛虽提倡宋诗但非专学宋诗,他于论诗中寻求新意,却并没有抛弃汉魏唐诗传统,他对宋诗的提倡是为给宋诗正名,是想让更多人看到宋诗之价值,使黜宋之人得见宋诗全貌,而非一味沿袭前人指称宋诗为“腐”的观点。
王士禛读诗范围宽广,论诗又重融通。他性格宽厚,喜结交朋友,常诗酒唱和,所收门人弟子众多,却不强求门人所学。这种人生态度反映在论诗上,就是对学盛唐、学中晚唐、学宋者都予以肯定,王士禛并非宗宋祧唐,而是站在学唐的基础上提倡学宋,并对诗坛分唐界宋(宗宋祧唐或宗唐抑宋)之举表达不满。康熙二十一年,王士禛在《黄湄诗选》序中抨击诗坛时弊,言明自己提倡宋诗正是矫枉明以来独宗盛唐、黜宋弃宋的态度:“予习见近人言诗辄好立门户,某者为唐,某者为宋,李、杜、苏、黄强分畛域”[6]33。
自诗坛学宋弊病渐起后,王士禛又开始复归唐音。“康熙二十六年,取宋姚铉《唐文粹》所收诗删为六卷,名曰《唐文粹诗选》。”[2]322后又“取唐人选唐诗九种并宋姚氏所选《唐文粹》古诗,荟萃成编,共为十选”[7]278,可见此选实质是将全唐诗的面貌呈于世人。“康熙二十七年三月归里,是岁,撰《唐贤三昧集》三卷。”[1]5089-5090王士禛言此集乃“妄欲令海内作者识取开元、天宝本来面目。”[22]又姜宸英于《唐贤三昧集》序曰:“选《唐贤三昧集》者,所以别唐诗于宋元以后之诗,尤所以别盛唐于三唐之诗也。”[23]可见《唐贤三昧集》是欲突出盛唐诗歌。由此王士禛成为力挽尊宋祧唐风气之人,在诗坛树立起以唐为宗,兼采宋元的诗学倾向。自此诗坛对宋诗热渐趋冷静,在回归唐音的同时也开始反思学宋流弊。至康熙四十年左右,诗坛已突破明代惟宗盛唐诗,转而以四唐诗并举,康熙也顺应此潮流,提倡全面认识唐诗。
四、结语
观《古诗选》中姜宸英之序:“学者合二集观之,于以辨古诗之源流,而斟酌于风会之间,庶乎其不为异论所淆惑矣。”[24]言后世学人若合《五言诗》与《七言诗》二集观之,自可辨清古诗源流。《古诗选》的编纂背景乃康熙诗坛唐宋之争,此选既成,自是为表达王士禛诗学倾向。不论王士禛提倡宋诗还是回归唐音,其本质都是在抨击诗坛分唐界宋,矫枉诗坛时弊。王士禛希望能够引导人们学诗时先辨其源流,正确认识全唐诗和宋诗的价值,再择其性近者师法其诗,最终融会贯通,成一家之诗。而《古诗选》的编纂,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即意欲矫枉时弊、正本清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