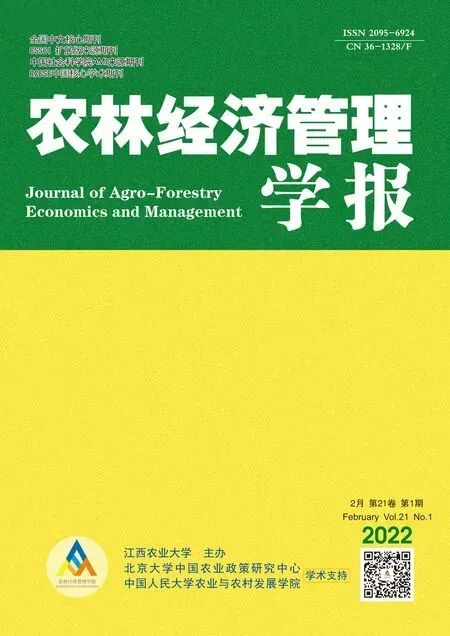留住社区感:互动仪式理论视角的农村零售市场购买决策生成机制
2022-03-17李艳军
李 堃,李艳军
(1.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天津 300191;2.华中农业大学湖北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0;3.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乡村零售店是村民就近获取商品的重要来源。在当前农村消费环境升级、大量资本和现代零售企业纷纷进驻农村的背景下,由本村个体户经营的零售店(简称“小卖部”①作此处理的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为与外来资本所经营的零售店相区别;二是在实地调研中,村民常将由本村个体户经营的零售店(包括日杂百货店和农资店)称为“小卖部”“小店”“店子”等,而称呼由外来资本经营的零售店为“超市”“连锁店”“加盟店”等。)并未被取代,且仍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小卖部的持续存在,说明在当前市场大变迁的趋势中,农村市场仍存在某些“不变”的内核。具体而言,这些“不变”根植于农村社区内部,源于本村的零售店经营者(简称“店老板”)与村民之间存在的以“亲、近、信”为主要特征的人际关系,是由双方围绕这种关系所展开的诸多交往与互动所共同构建的社会和人文等方面的“软消费环境”[1]。那么,这种“软消费环境”又将对村民购买决策产生怎样的影响?当前,学界主要从嵌入性理论视角探讨人际关系对村民购买决策的影响过程,这些研究通常以乡村农资零售市场作为研究情境,提出村民往往更信赖那些和其关系距离较近的零售商,也因此对这些零售商所经营的店铺有着更高的光顾意愿[2-3]。例如,村民迫于农资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而“被动信任”农资零售商[4],农资零售商为适应乡村社会而不得不采取赊账的销售策略[5]。尽管这些研究结论表明构建和维系村民与零售商之间人际关系的重要性,却也从侧面反映双方暗含的某种冲突关系以及潜在的理性算计,体现了购销主体对嵌入性的一种无力感与被动性。笔者认为,这源于外来市场经济进入乡村社会所产生的冲击,以及村民和农资零售商之间的对立、磨合与适应过程。此外,就内在的过程机理而言,学界往往以城市或泛化的经济交易活动为背景,认为买卖双方基于重复交易所展开的频繁互动能有效促进人际关系的发展并培育信任。同时进一步地,买方将这种信任转移到卖方销售的产品上,弱化对所选商品的感知风险,从而促进个体作出购买行为[6-7]。少数以农村零售市场为背景的相关研究则更重视村民与零售商之间的既有人际关系,探讨村民和店老板基于乡村零售市场的嵌入性所作出的一系列经济决策,这些研究往往先验地推断出村民与零售商之间存在更近距离的人际关系以及更高水平的人际信任,缺乏对人际关系本身的动态发展过程的深入探究,导致对农村零售市场购销环境的理解仍较为模糊与抽象,亦未能在此基础上对村民购买决策进行更为准确的预测。为此,本文基于互动仪式理论,运用质性研究方法,考察乡村零售市场“软消费环境”的形成与演进,以多情境、动态性角度分析村民互动所产生的情感及其对购买决策的影响,探索村民与零售商之间作为内群体成员的互动,反映农村零售市场嵌入性特征的形成与发展过程,验证买卖双方人际互动对个体购买决策产生的多路径和跨情境作用,在时间维度上发现人际关系对消费者购买决策与行为相互强化的循环性作用,丰富人际关系对购买决策影响的解释机制。本文聚焦农村社区中买卖双方对零售市场嵌入性环境的积极建构,探讨这种嵌入性是如何基于村民与店老板之间的多种互动而形成的,凸显购销主体的能动性,由此进一步深化对嵌入性理论研究的运用,也丰富熟人社会环境下人际关系对购买决策作用的解释机制。基于研究结论,笔者从社会化角度为零售商培育顾客忠诚、乡村零售市场升级、管理者治理乡村提供建议与启示。
二、理论分析
(一)互动仪式理论视角下的农村零售市场
互动仪式理论从微观视角考察个体之间具有表达性意义的互动过程,认为个体与他人进行互动的内在动机是获得情感能量。这种情感能量源自个体对参与社会互动以及获得归属感的渴求,具有明显的社会性导向,与暂时性情绪存在本质区别[8]。个体从互动仪式中获得情感能量的前提,分别是与其他群体成员共同在场、有共同的关注点、有共同的情感体验[9]。在实践中,个体首先投入一部分暂时性情绪,继而在与他人互动过程中产生长期、持续性的情感,如归属感或群体团结感等[10]。互动仪式在生活中随处可见,如问候寒暄、串门闲谈、消遣娱乐等,其常对个体行为产生影响。
在消费者行为研究领域,买卖双方人际关系及互动潜移默化地影响个体购买决策[11]。特别是在农村,村民与店老板之间日常交往的互动仪式产生更多与情感相关的心理结果,继而对村民购买决策产生更为复杂和多样的影响。这是因为,一方面,店老板不仅仅是商业经营者,更是本村内群体成员的一份子,村民在与店老板进行互动的过程中更在乎店老板对其所持有的态度以及自尊与社会认同感的实现;另一方面,村民光顾特定小卖部是村民与店老板之间日常互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行为选择并非只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更因受到某些社会化因素的影响而内含“关照彼此营生”的意味。这也使得有些村民或会购买小卖部老板极力推荐的而并非其最中意的商品,或会尽量平均光顾本村中几家小卖部的次数。可见,村民与零售商之间的人际互动构成农村零售市场中独特的购销环境。
(二)买卖双方人际关系与购买决策
消费者与零售商之间的关系往往与交易活动协同发展[12]。面对面交易活动越频繁,买卖双方就越有可能建立更亲密的人际关系[13]。人际关系还具有多维度特征,即买卖双方的互动还可能延伸于消费情境之外,使得互动过程中的个体产生除信任以外的更为多样的认知与情感体验,进一步对个体购买决策产生重要影响。
由于村民与店老板共同生活在农村社区这一特定的熟人社会环境中,双方所建立的是一种以先赋的亲缘与地缘为基础的内群体成员关系[14],这就使得村民与店老板之间的互动场景更为多样、互动次数更为频繁,双方人际关系也更为亲密,从而导致村民基于同时实现理性与情感的双重目标而作出购买决策。具体而言,一方面,村民以实现自我利益为目标,在与店老板进行互动的过程中获得许多有关产品质量、售后等相关的客观认知性信息,并基于这些信息形成对店老板及其销售产品的信任,指导其购买决策,旨在获得最大化商品价值这一功能性收益;另一方面,由于双方是内群体成员关系,村民希望在与店老板进行互动的过程中获得归属感和认同感等情感体验,因此基于人际间互动原则以及群体层面的社会规范作出购买决策,旨在获得最大化的情感性收益。由此可见,嵌入性零售市场的购买决策影响因素是十分复杂的,但已有相关研究未能从全局、动态的视角对这种复杂性进行揭示。基于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说:买卖双方的人际互动所构建的“软消费环境”将通过多种情感性认知与体验对个体购买决策产生复杂的多路径影响。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分析
(一)研究方法
本文以浮现性设计法指导调研与数据收集过程,该方法适用于对现象缺乏相对直观的理解而无法预计数据收集与分析情况的研究[15]。浮现性设计法要求在田野情境中建立对现象的理解,然后再在田野情境中对这种理解的真实性进行检验,这就需要进行多次半结构式的深度访谈。调研者在每次访谈结束后总结归纳发现,在下一次访谈中对前次访谈产生的发现进行检验,同时试图提炼其他新的发现,这种采用持续比较方法的迭代过程将一直持续至收集数据的概念性类属达到饱和。课题组在对湖北省荆州市下辖某村的村民进行访谈时发现,村民往往会基于不同目的到小卖部选购商品。一些访谈者提到,在附近小卖部购买商品更可靠些,因为和店老板是同村人,店老板不敢欺骗村民,出现问题也会帮忙解决;但也有访谈者提到,光顾自家附近小卖部,更多的是一种照顾邻里生意的表现,也是维系与店老板之间人际关系的方式。笔者基于访谈过程建立对现象的理解,认为尽管外来资本冲击导致乡村零售市场发生变迁,但根植于乡村社会的某种内核具有不变性,是基于村民与店老板之间的人际互动所构建的消费软环境。然而,已有嵌入性研究往往将这种消费软环境作为一种固有的背景,忽略其形成与演进过程,导致未能全面与深入地阐释人际互动中的其他情绪感知对购买决策的影响。为此,在深度访谈中,调研人员请村民详细描述其与店老板进行互动的情况和过程,试图从中挖掘多种情绪与感知。访谈提纲如表1所示。

表1 访谈提纲主题及题例
(二)数据来源
本文在农村社区环境中探讨村民与店老板互动对购买决策的影响,对作为被访者的村民及其所选定的店老板的范围进行限定:一方面,要求村民及其选定的店老板应均为本村原住居民,以保证双方在日常生活中有频繁的互动;另一方面,要求选定店老板经营的小卖部坐落于本村,并服务于本村居民日常消费需求,以保证村民与该店老板在经济交易中存在频繁互动。据此,经营农资零售店与日杂零售店的店老板被纳入调研范围。尽管农资与日用杂货分属投入品和消费品,两者的购买逻辑可能存在差异,但本文关注的是基于村民与零售商之间的内群体互动所产生的情感在农村零售人文软环境形成中的作用,这是农资购买和消费品购买中都存在的逻辑,因此将两者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
调研人员通过随机走访的方式,与被访者进行一对一的半结构式访谈。基于对语言、文化以及自然村落完整性等方面的考虑,选择湖北省、山东省以及河南省的自然村进行实地考察。依照浮现性设计流程,在调研过程中采访53 名村民,以此循环验证和发现新的概念类属,在结束对第17 名村民的访谈后,文本数据中包含的各种概念类属不再增加,运用与此后36 位村民进行访谈所得到的文本数据验证这些概念类属,无新的概念性类属出现,这意味着17 名访谈者提供内容能有效代表所有访谈者提供的信息,所收集文字数据在理论构建上已达到饱和。17名访谈对象的基本情况如表2所示。

表2 访谈对象基本情况
(三)数据分析
本文运用扎根理论法对访谈资料进行处理,通过开放编码、主轴编码以及选择编码提炼新的概念。开放编码由3人运用多重归纳法独立完成。例如从访谈文本“他说像我这样掏现钱的才是有能力的,穷人才赊账”中提取编码“赞赏现款交易”;从访谈文本“主要是自己的原因,配药时候没留意,(自己)中毒了……他听说了以后就立刻去医院看我,买了牛奶和水果……走时候还要留钱”中提取编码“主动慰问”;从访谈文本“来了客人,借点油、借个鸡蛋……要是逢上大事情,桌子、板凳和碗筷都要借”中提取编码“大型仪式上的帮忙”;从访谈文本“平时凑一起都像家人似的……都是一个村的肯定特别亲”中提取编码“社区感”。除去因三人意见不一致而被放弃的,最终有54个分析单元进入正式编码域。主轴编码由开放编码整合而成。例如,开放编码“赞扬成绩”“赞赏现款交易”可被整合为“受店老板称赞或受到认可的互动”这一主轴编码。选择编码是将实践中观察到的现象作进一步的主题提取,即将主轴编码归纳到框架体系中。例如,主轴编码中“受店老板称赞或受到认可的互动”“店老板就经营计划询问自己的意见”“种植情况交流的互动”“接受店老板帮助的互动”均可以被概念化为“基于人的个性化服务”。在选择编码形成后,对访谈资料进行重新检查,发现访谈材料中所有相关主题的分析单位均可被纳入现有的选择编码结果中,未出现新的编码结果和关系,即已有选择编码的结果在理论上是饱和的,数据分析详情如表3所示。

表3 编码提取及归纳
四、嵌入性零售市场的购买决策成因及路径分析
基于对选择编码之间逻辑关系的构建,形成嵌入性零售市场中的购买决策模型,提出村民与店老板之间的人际互动对购买决策存在多路径、跨情境、循环强化性的影响。
(一)路径一:经济交易情境中人际互动对购买决策的多路径影响
在经济交易环境下,村民与店老板的互动通过两条路径对购买决策产生影响,其一为功能性认知路径,其二为情感性感知路径。
在功能性认知路径中,村民基于互动过程中店老板呈现的个人特质形成人际信任,并将其作为对产品质量感知的重要前提,从而促使村民作出购买决策。从访谈内容看,村民对店老板个人特质的感知主要包括感知专业性、感知责任感以及感知公正性。
感知专业性是指在互动过程中村民认为老板具备扎实与系统的产品知识及应对各种复杂问题的能力。显然,能向村民提供其所需的相关产品信息,并对推荐产品作出全面详细介绍的店老板往往可能积累更丰富的专业性知识,所以村民认为店老板所销售的产品也应是经过其严格把关和值得购买的,故而作出购买决策。
“别个(指其他店老板举办的产品宣传介绍会)我很少去,他的我肯定要去听……因为讲的都是自己慢慢收集的当地实际问题和窍门,比较实在……我去他那里拿东西的时候从不问贵贱的,只和他说地里现在出了什么问题,就能给我拿对症的药……”
感知责任感是指互动过程中的村民认为店老板做事是认真负责的、对突发事件(通常是负面事件)是不推诿的,并且其承诺与行为是相一致的,从而能推动村民形成对店老板所销售产品的信任,继而作出购买行为。
“……他来我这儿做药物效果示范田……结果没出几天叶子都黄了,感觉要绝产了……好在他也没推卸责任,上网查、拍照片、找经销商问……后来他说可能是这两天一直没下雨,突然用大量氨基酸会叶子发黄,让我等两天,如果秧苗都死了他全部照当年产量赔偿……后来叶子缓过来了,看着嫩嫩绿绿的,比没用过的那些要好很多……这事儿以后我就觉得他虽然有些(能力)还达不到,但起码能做到极力补救不推脱责任,挺负责的……以后买东西肯定更愿去他那,我觉得(售后)有保障才是更重要的……”
感知公正性是指村民从店老板的行为与言语中感受到店老板处事是有原则的、在任何时间和任何情境下都以相同的态度和行为对待他人,店老板秉持自有的原则,对所有人态度如一的行为是村民形成公正性感知继而对店老板产生信任的基础,对村民的购买行为存在显著影响。
“……有一段时间我就想换别家的化肥试试,所以好久没去他家了,后来再去还有点不好意思,结果人家态度(和过去)是一样的,也不会因为你一段时间不来了就给脸色看,都喜欢和这样的人打交道……购买到一定袋数送电饭锅,我差了几袋没达到,就和他说直接送我算了,但他不肯,说这样不公平……那个老板挺明理,待人也公正……拿东西放心不用担心被宰……”
在情感性感知路径中,由于村民与店老板是内群体成员关系,因此在互动过程中产生特定的情感体验以及情感上的满足,从而更愿意在经济交易中选择与该店老板进行人际互动和联结,并产生一种以维系人际关系为主要目的的购买决策。质性研究结果显示,村民如果在互动过程中产生高自尊、内群体归属感、人际团结感会促进其作出购买决策。
高自尊来源于在互动过程中店老板对村民能力的积极评价。在农村社区,具有经济头脑、守信用、种地有丰富经验与实力等是村民理想自我的重要部分,店老板对村民这些方面的认可和赞扬,对村民的自尊具有重要的强化作用,使其产生更为积极的情感,继而作出购买决策。
“……他和我说,村里要是多几个我这样有主见有技术有实力的大户那他这个买卖就好做又省心了……我每次还都和他现款交易,他说现在掏现钱的才是明白人呢,赊账其实是最不划算的……谁被夸奖都感觉脸上有光嘛,买卖是一方面,也图个开心……我需要买东西的时候更喜欢往他那里跑……”
内群体归属感源自于店老板为农村社区内部成员利益而努力的行为,因为在差序文化的背景下,这一行为通常意味着店老板将村民视为“自己人”,村民也由此感知到自己的内群体身份得到认同和强化,即内群体归属感。在这一积极的情感体验作用下,村民在未来也会因优先考虑作为内群体成员的店老板的获益而到其经营的小卖部进行购买。
“……他那时候代理了一个销得很火的化肥,方圆几十里没有第二家,供不应求……但是他和我说,(有货的话)肯定要先留给我(本村的人),还给送到地头去,然后余下的再卖村外的人……肯定是要同村的更向着自己人,别人不会尽心帮你的……所以只要他那里有我能买到的,那我就先他店里买,肯定先让自己人赚钱啊……”
团结感源自于村民与店老板的合作型互动过程。在该互动过程中,与店老板共同努力、共同承担风险、共同克服诸多困难的经历使村民产生人际团结感这一积极情感体验,双方人际关系被进一步强化,也使村民增加对店老板的承诺,继而作出到其小卖部进行购买的决策与行为。
“……当年我是村里第一个种彩椒的……很多人不敢,风险有些大的……只有他那时候愿意帮我去省城打听种彩椒的事儿,还帮我带回来一些适合彩椒专用的农药和水溶肥。我俩那时候都不知道这些搭配合不合适,就地块分成几个,轮流试,看看哪个更好……也捏了一把汗。他那时也是一有空就总跑过来我地里看看……最后产量不错,那一季基本上我俩一起从头跟到尾,我俩一起研究出来了一个适合我们这儿种地的经验……成功了大家肯定都挺开心……关系上肯定感觉更亲了,以后也从他那里拿货……”
可见,经济交易过程中的人际互动对购买决策存在多重影响,一方面,村民基于店老板的某种个人特质产生人际信任,并将这种对人的信任转移到对物的信任上,认为产品同样是高质量、可信赖的,从而作出购买决策;另一方面,村民在互动过程中产生特定的情感体验,获得情感上的满足,即人际情感性收益,继而作出购买决策。
(二)路径二:日常生活情境中人际互动对购买决策的跨情境影响
村民与店老板在日常生活情境下展开频繁互动,村民由此产生的诸多情感,对村民的购买决策产生跨情境影响。质性研究结果表明,日常生活中村民与店老板互动所产生的内群体归属、人际团结感可以跨情境地影响村民购买行为。
内群体归属感缘于村民在与店老板日常互动过程中感受到的鼓舞、欢欣以及信心等积极情感,其强化了村民的社会群体身份以及在群体内与其他成员的人际关系,使村民对该店老板作出内群体偏袒行为(in-group favoritism)[16],即村民会优先到该店老板处进行购买。
“做顿好吃的都要给她家分分……吃血汤(当地风俗)的时候,邀请来自己家里热热闹闹吃上一顿。我们祖辈就是邻居,两家走动又多,自然热闹又和睦,今天她来我家串个门,明天我去她家串门,蹭个饭……孩子城里工作,过年带回来的新鲜玩意儿,叫上她家的一起看看,或者分分……一起玩的姐妹,有好吃的东西或者有好玩的东西也会一起分享……今天我家的枣子熟了送给她们家尝一尝,明天我去她们家菜地里挑点青菜……相处的像家人一样好……前两年她开了个小超市开始做买卖,我以后就没去别的地方(买东西)……关系好自然什么好事情也要先向着她们家,来这儿买东西也是照顾她家生意的意思……”
人际团结感缘于生活中的村民与店老板相助相帮、共渡难关的经历。共同的经历增加村民对店老板的承诺与依赖,并且为了使这种良好的人际关系得以持续和强化,曾经接受店老板帮助的村民也会在未来到该店老板处进行购买,并将其作为对在日常生活中受到店老板的关心与照顾而作出的“报偿”。
“……上午有事情出个门,就和他打个招呼帮我带一下孩子,饭点要是还没回来中午就在他家吃饭……小孩闹脾气,大人劝不住,有时候他过来哄一哄还能听话呢……今天我帮你,明天我有困难你拉我一把……后来他父亲(患上了)尿毒症,其他的儿女都在外务工,家里只剩老伴和他这一个儿子,照顾不过来,我们就轮流去陪他、照顾他……那时候日子过得真团结,不是有句话叫抱团取暖么……虽说是顺手帮忙的事情,但邻里和睦团结就是日积月累这样相互帮出来的……大家团结在一起什么事情都能克服,去年他有一批化肥压房头(指滞销),我们这几家关系好的、这些左邻右舍的,一人买个几袋给用掉了,他就少亏些……”
可见,在农村社区买卖双方在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互动对购买决策产生跨情境性影响。这是因为村民与店老板具有内群体成员关系,村民对互动过程以及店老板的行为进行社会化意义的解读,并以互惠规范为指导,作出优先到其小卖部进行购买的购买决策。
(三)路径三:全局动态情境下人际互动与村民购买决策的相互作用与强化过程
访谈内容还表明,特定时间段内的村民购买决策反过来影响村民与店老板之间的人际关系,从而对村民的下一次购买决策产生影响,即人际互动与购买决策的相互作用及强化过程。具体而言,由于村民与店老板是内部群体成员关系,遵守相同的互惠规范,因此双方对互动过程中特定行为与决策所内含的社会化意义的解读也大致相似[17]。村民在互动中对店老板的语言和行为蕴含的社会化意义进行解读从而产生情感与认知并作出购买行为,而店老板也能对村民作出的购买决策进行社会化意义(如照顾生意、人际联结意愿等)的解读并产生特定情感与认知,并将其带入下一次与该村民互动过程中,从而影响其对待该村民的态度与行为,而村民也会再一次地对这些互动过程进行社会化意义的解读,从而作出特定的购买决策与行为。
“……用他的话说,我就算是他‘铁杆户’(忠诚客户)了,连着五六年了吧,年年都在他这里拿(指购买商品),雷打不动。一年尝试两年习惯,三年四年到现在早就是非常亲的朋友了……我每次去他那里拿货都不多问价钱效果,对他信任……这个相信不是一天两天(就建立)的事情,要做到风吹草动都不变是困难的……两个人一起努力,我不辜负你,你也不能辜负我……最早的时候他刚开始干,人年轻又缺经验,没人敢在他这里拿肥,而我又是大户,相当于冒着一定风险,在他这里一拿就是几十袋,他就说既然这么信任我,我也一定对得起你(的信任),以后东西在我这儿拿我一定帮您选性价比最高的,使用有什么问题和危害我全额退款给您……头几年经常跑我地头上来说请教问题,挺好学。踏实又肯干,这两年也成‘气候’了,这样的人都愿意和他打交道,有时候他推荐我用一个新产品,我也不太细问,相信他不会坑害我的,种地也感觉越来越省心了……前段时间,有个直销商过来找我又是请吃,又是送礼,让我去他那里拿货,因为他的便宜,我现在拿的价格贵些,我都拒绝了。他听说以后特别感动,不停对我说感激我对他的信任……这样你来我往关系就会越来越亲近,没得说……”
五、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本文通过探索村民与零售商之间作为内群体成员的互动,反映农村零售市场嵌入性特征的形成与发展过程,验证买卖双方的人际互动对个体购买决策产生的多维度和跨情境作用。结果表明:买卖双方人际互动通过提升村民的自尊体验、内群体归属感、人际团结感、信任感等,对购买决策产生多路径、跨情境影响;村民解读互动蕴含的社会化意义,导致买卖双方人际互动与购买决策之间存在相互影响和彼此强化的动态、循环过程。这意味着,在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农村社区小卖部承载着商业、社会和文化意义的多重功能。其不仅能满足村民日常购物需求,更因承载着村民与店老板之间的人际互动,而源源不断地为村民提供社区感、向村民输送着“社会热度”[18],这些都会影响村民的购买决策并进一步促进人际关系的再生产。可见,小卖部并非仅仅是一个经济交易空间,是店老板表露自我并与村民建立亲密人际关系的展演空间;是村民通过与店老板互动收获群体归属感、认同感的娱乐空间;是村民与店老板彼此关心、谈论日常生活的对话空间。
(二)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应保留或积极构建农村零售市场的社会化功能。具体而言,经营者可以通过组织活动、为村民提供人际互动交流场所和便民服务等,将零售店融入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以消费软环境的构建推动村民产生社区感,这不但有利于培育消费者忠诚,更可助力提升村民生活的幸福感。第二,政策制定者应鼓励并善用传统乡村零售店所具有的社会化属性。乡村小卖部经营显著区别于纯粹的商业活动,也在某种程度上为村庄创造社会化价值。第三,政策制定者应重视本村零售商拥有的相对密集的人际网络及其在村庄社会环境构建过程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在适当情况下可以依托乡村零售店的力量达成某种社会化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