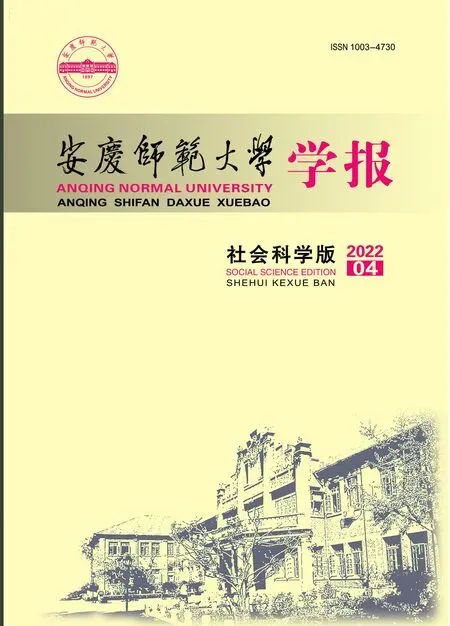抗战时期安徽省内迁教育研究
——以国立九中为中心的考察
2022-03-16黄伟
黄 伟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安徽 合肥 230051)
卢沟桥事变后,国民政府教育部于1937年冬在河南淅川设国立河南临时中学,以收容河北、察哈尔、绥远及平津等省市中等学校的流亡员生。1938年1月又在贵州铜仁、四川合江分别设立国立贵州临时中学和国立四川临时中学,主要收容江苏、安徽、南京及上海等省市中等学校流亡之员生。此后,教育部颁布《国立中学暂行规则》,各校之名依照规定将“临时”二字取消。1938年开始,教育部设置国立中学的步伐加快,2月在陕西安康设国立陕西中学;3月在甘肃天水设国立甘肃中学,湖北郧阳设国立湖北中学,陕西洋县设国立山西中学;8月又在湖南乾城设国立安徽中学;9月在四川江津设国立安徽第二中学;10月在甘肃清水设国立甘肃第二中学。武汉沦陷后,邻近战区的国立中学开始向后方迁移。1939年4月,教育部根据各校成立之顺序,以数字为校名,国立第一安徽中学更名为国立第八中学,国立安徽第二中学更名为国立第九中学,同时又分别在湖南武冈及四川长寿设立国立第十一中学和十二中学[1]。到1940年,国立中学的学生规模已初步成型,如国立一中1 116人、国立二中1 986人、国立三中1 586人、国立四中1 065人、国立五中989人、国立六中2 457人、国立七中1 141人、国立八中4 322人、国立九中1 686人、国立十中2 329人、国立十一中1 431人、国立十二中1 218人[2]。抗战时期一大批学生在国立中学成长成才,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国立中学的创设为我国中等教育的持续发展和人才培养做出了积极贡献。
一、抗战时期国立九中创设
抗战时期在省会安庆岌岌可危之际,1938年2月,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兼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宗仁在临时省会六安“宣誓就职”[3],简单训话后他要求教育部门应使各类学校于短期内尽快复课。此后,省教育厅要求皖北、皖南的6所省立学校在原地继续开课,同时另在皖西山区组设4所省立临时中学,收容战区流亡学生就读,因而短暂停顿的安徽中等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恢复。5月徐州沦陷后,教育部派方治和邵华作为代表到安徽省考察教育迁移问题,他们为保留安徽中等教育的种子,建议省立中等学校迅速迁到武汉,另设国立安徽临时中学。于是,省教育厅要求在大别山区的4所省立临中尽快转移,原在皖北的3所中等学校在奉命撤到河南潢川后也同样迁到武汉。至此,除皖南3所学校继续上课外,安徽省原有省立中等学校的大部分师生都内撤到武汉。对此,教育家杨亮功曾说:“抗战时期,有组织地把战区的学校内迁,是始自国立安徽中学。”[4]
随着武汉沦陷后战局的不断恶化,安徽省立4所临时中学又奉命迁往湘西合并为国立安徽中学。但由于各种因素制约,不少教育员生纷纷经宜昌进入四川。安徽旅渝同乡会鉴于本省中等学校员生来渝者日益增多,教员无从施教,学生无处求学,群议设法救济。8月7日,该会举行理监联席会议决定筹办安徽中学,并向教育部请求拨款办理,而此时的教育部亦认为确实有必要,于是决定在重庆设国立安徽第二中学,以收容入川之皖籍学生为对象。9月15日,教育部委任国民党中央执委陈访先为校长,此后他聘请邓季宣为教导处主任,胡子穆为总务处主任,程勉旃为高中部主任,吴天植为初中部主任,许凝生为师范部主任。与此同时,为遵照教育部的命令,陈访先又在校内设立训导委员会,加聘叶伟珍、周庆孚、章道衡、吴逸凡等为训导委员,并聘周庆孚为女子部主任,同时在重庆成渝饭店设立国立安徽第二中学临时办事处。该校在初创时期内部机构仅设教导、总务二处及高中、师范、初中、女子四部。各处及各部均各设主任1人,教导处下设教务、训导、体育三组,总务处下设会计、庶务、文书、卫生四组。
在校舍方面,安徽旅渝同乡会曾打算租赁重庆南岸大佛寺为校舍,陈访先担任校长后认为此地房屋过少,难以容纳大量学生,附近又无其它适当场所可资租用,且临近重庆市区易受到日机的轰炸。于是他派邓季宣、胡子穆、程勉旃到重庆附近的江津县选择适合地点作为校址。最终,他们在当地的协助下借用德感坝至善图书馆全部馆址为校本部,并在附近租赁三共祠、四卫祠、云庄祠、五福祠、五美祠、竹贤祠为高中、师范、初中和女子各部之用。又另在图书馆空地建教室4座、女生宿舍29间、房屋7间、医务室2间、保管室2间、校工室2间。
在筹备建校的过程中,安徽旅渝同乡会曾举办皖籍失学中学生登记,前后登记学生达1 200人。国立安徽第二中学成立后,该会将全部名册移送,此后学校在重庆的办事处又办理200余学生的登记。10月1日登记工作截止,2日至10日学生陆续到办事处报到,但因江津校舍添建部分未能完工,因而于26日至11月10日学校才陆续发给学生旅费津贴2元,令他们分批到江津报到。不久教育部发交由四川教师服务团登记合格之皖籍失学中等学生100余人亦到校。彼时,按教育部规定该校仅可收容皖籍学生1 200名,但继续请求登记者络绎不绝,学生名额日益超过规定数,因而校长陈访先多次向教育部呈请扩充400名额并增加经费。
在学生陆续抵达江津后,国立安徽第二中学组织编级试验委员会,12月1日至2日举行初中编级试验,3日至4日举行高中编级试验。此后由编级试验委员会决定录取办法:凡高中、初中三年级学生平均不及50分者,二年级学生平均不及45分者,一年级学生平均不及40分者降班;其平均分数虽及格而一科零分或二科不及格者试读;平均分数在20分以下或二科零分或三科在10分以下者降级。根据此办法,高中降班者84名、试读11名,初中降班者123名、试读者18名、降级者2名;12月18日,该校又将另外登记之400名学生举行第二次编级试验[5]。1938年12月下旬,教育部正式委任张效良、虞焕宗、潘赞化、吴硕民及周汉夫为国立九中校务委员,并委张效良为该中学高中分校校长,程勉旃为师范分校校长,吴天植为初中一分校校长,吴硕民为初中二分校校长,周庆孚为初中三分校校长[6]。全校设高中、初中、师范、女中四部,共42教学班。
12月25日,学校正式开学,教育部长陈立夫亲临讲话,他指出国立安徽第二中学于远距故乡千里之外的江津上课,其规模性质与通常之省立、公立、私立学校不同,“设置目标亦非全在于救济,而为谋改造中等教育制度,以应战时之需要”,“安中全体师生自脱离战区以来后方,数千里跋涉山川,都已饱尝艰苦,今日得聚首一堂,必能以家人父子之亲爱精诚,甘苦与共,为卫国卫乡作积极之准备,而凛然于自身重大之责任。”陈立夫还对全校师生提出六点要求:“以安徽过去之光荣历史言之,当以继往开来责任之重大”;“以安徽物产丰富之地利言之,当知利用厚生责任之重大”;“以全体师生之切身经验言之,当知抗战建国责任之重大”;“以学校设置之目的言之,其全体师生不可存避难苟安之心理”;“以流利转徙之经历言之,全体师生不可忘尝胆卧薪之教训”;“以足资鉴戒之言之,全体师生不可无泯除畛域之努力”。最后,陈立夫希望全校师生“于备尝艰苦之余,知忧戚玉成之意,乘时奋勉,以达成其使命,为中等学校树立更生之楷模,为安徽教育奠定复兴之基础,倡导力行,师勉其弟,以充实健全之新生活,创造笃实光辉之新生命。”[7]此后,学校正式开始运转,但条件却异常艰苦。学生宿舍是几个破旧的祠堂,教室是用竹篱笆盖的,四面透风,冬天学生冻得直打哆嗦,晚上同学们只能在桐油灯下自修。由于学生是从几千里外跋山涉水而来,因此他们对于求知充满渴望,也深知自己肩负的责任重大。
1939年4月,学校奉教育部令改名为国立第九中学,同时开始兼收其他省份的流亡学生和本地的川籍学生,5月2日该校又举行插班考试,“以谋于尽可能范围内尽量收容沦陷区学生”[8]。截止5月,国立九中教职员共153人,学生1 612人,其中安徽1 529人,四川73人,南京2人,江苏2人,湖北2人,江西2人,河南1人,贵州1人,男生916人,女生616人;学级方面高中278人,初中650人,女中592人,师范92人。具体以女中分校学生为例,安徽籍占94.4%,四川三县占4.8%,江苏一县占0.2%,湖南、湖北、江西各一县各占0.2%。在安徽47县中又以合肥居第一位,怀宁次之。鉴于学校规模不断扩大,7月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决议安徽省两国立中学经常费用1月至3月每月为6.7万元,4月至12月每月为8.2万元,“计本年度内共应追加二十一万九千元,并依院议移列于各国立中学经费科目之内”[9]。此后因实际的需要,该校不少分校陆续成立,并在陈访先、邓季宣、邵华、苏家祥、胡秉正等人相继主持下,学校充分发挥皖籍教师的骨干作用,努力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把教学工作开展得成效卓著。
1945年8月,日寇宣告投降,消息传到江津后,全校师生和德感坝群众欢呼震天,“鞭炮声、锣鼓声、歌唱声不绝于耳,炮竹纸屑积地盈寸”[10]。此后学校开始有计划地筹备复员工作。1946年春,教育部正式通令各国立中学的学生复员回籍,留川学生就近转入他校继续完成高、初中学业。3月,安徽省教育厅长汪少伦专程前来四川江津县,欢迎国立九中全体师生回皖,并召开大会向师生简单介绍了复员后的教育安置情况。4月13日,汪少伦赴南京与教育部次长杭立武、国立八中校长苏家祥等人商量本省教育复员事宜。对于后方教育迁回由安徽省办理问题,经讨论决定国立八中之女生迁移到芜湖,男生分配在贵池和太和两地;国立九中之女生迁移到安庆,男生大部迁移到东流[11]。国立九中在四川办学八载,毕业学生达15届,计3 500多人,加上在校学生总计5 000多人,以学生籍贯分布而论涵盖27个省市,皖籍者占三分之一强,位居首位。当然,学校也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如“两弹元勋”邓稼先就是从该校走出的优秀毕业生[12]。
二、抗战时期国立九中教育特点
抗战时期物资紧缺,师生们条件非常艰苦,学生每天吃不饱是常事。尽管如此,老师认真教学,学生刻苦学习。国立九中从1938年至1946年的八年中,历任校长有五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第二任校长邓季宣。他曾指出政府对于青年的重视可谓前所未有,因而希望学生对“民族精神”与“科学精神”,能有“观察与确切的认识,而发生真诚的信仰”[13]。在他的领导下,国立九中学风严谨而又比较开放,教学和文体活动等都开展得有声有色。每逢校本部的总理纪念周全校集合,他必定亲自主持并不拘一格邀请一些外地进步学者来校做报告,使学生眼界大开。当然,对于本校办学特点,末任校长胡秉正曾概括为两条,“一曰切实恪守纪律,以养成严肃之校风;一曰厉行学科考绩,以提高学力之水准”[14]。
(一)重视对学生知识的传授。国立九中始终将向学生传播知识作为自己的重要使命,为增强学生对知识的吸收,该校各科经常召开研究会商讨教授办法。如女子分校采取“三段教学”方法,即上课前先由教师指定应授功课,令学生先预习,并简单告之预习方法。上课时根据预习所得学生向教师提问,此时由教师令其他学生“讨论”,再由教师详实解答;或由教师直接答复。最后,教师将所授教材加以“整理”,做一归纳说明,再指示下次教材,令学生预习。学生在这种教学方法训练之下,个人学习能力不断增强。同时,为督促学生学习,该校还注重课前课后的考试,成绩考察除依教育部规定考察办法外,还于上课前抽短暂时间作简单之试验。当然,教师在对学生传授知识时也非常认真,正如时人回忆自己在该校高三分校读书的经历,“教我班的国文老师姓张,是位老夫子式的胖老师,一天到晚笑呵呵,对学生很关心,作文以后,他常常给以个别指导。一次,我经过他的寝室门前,他叫住了我,说‘你作文中用了祸起萧墙这成语,用得很准。’接着又问‘萧墙’是什么?一下子把我难住了,他笑了笑,给我作了解释。事情虽小,但对我启发很大。以后在行文中使用成语时,往往引起我对这一情节的回忆,促使我勤查来历,弄清词意。数学老师是卢福泰,也教得好,很容易弄清问题,使得我做题比较快,交作业,交试卷比较快,但只是贪快,不仔细检查,不愿意多做未指定的题,也常常受到他不点名的批评。”[15]
(二)重视学生的课外活动。国立九中为了培养学生的全面能力,在各分校都建有社团组织。如高中分校级会组织的宗旨是:“增强学生自动研究学术及治事能力与兴趣”“激发学生抗战情绪并提倡后方社会服务及救亡工作”“陶冶学生对学校教师及同学间之亲爱精诚”。各级级会的活动包括演说、辩论、交游旅行、壁报、体育竞技、各种座谈会、课外阅读、文艺研究及习作、音乐歌咏等。具体来说,1939年5月,该分校各级级会分别成立后即开展活动。如课外阅读方面,或由分校学生借阅书籍,或由学生组织小规模之阅览室,供给杂物读物,并由教导课印制读书报告表,分发学生“以备考察”[16]。该校还让学生自己管理膳食,如此以来学生可以监督蔬菜大米的买卖活动,让他们更加了解社会,贴近生活。对于学校丰富的课外活动,该校学生曾言:“学生在周末参加音乐会,文艺演出活动的积极分子颇多,尤其是我班,很有几个爱好戏剧的同学,其中最突出的是黄宗权。他是著名演员黄宗英的弟弟,在高二时,他组织导演了京剧《探阴山》等节目,由李光谷同学操琴,演员全部是同学,在校演出后很受欢迎。后来,他又去高二分校约请了王冰等几位女同学排练话剧《生死恋》,黄宗权任导演,并演其中一个角色。接连几个星期天,在我家楼上排练,又由我们几个四川同学帮助借道具、服装,在戏院公演。后来听说其中有几个同学终于从事影剧工作。”[17]除上述活动外,为增进学生组织能力及运动能力起见,该校女中分校于每日下午六时,举行篮球或排球比赛一次,其主要方法是高中组采用单循环制,初中采用淘汰制。如此,使全体学生都能参加体育锻炼,增强他们的身体素质。
(三)注重学生家国情怀的培养。国立九中因抗战而立,由是学校特别重视对学生爱国主义的培养。如历史课注重讲授本国史,以加强学生爱民族之观念;讲授社会发展史,使学生明了社会进化之方向;讲日寇侵华史,以增进学生对抗战之认识;公民课注重中日社会经济状况之研究,国家现势之分析等。有一位地理老师的授课总让学生回味无穷,当他讲到山河破碎,陆游的诗就从他嘴里脱口而出:“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接着,“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令学生为之动容[18]201。1943年11月,冯玉祥到国立九中发动节约献金救国运动,当他乘船抵达江津时,国立九中校长邵华、江津县长及许多群众到长江码头迎接。第二天,在邵华的陪同下冯玉祥过江到德感坝国立九中校内各处参观,感到“整齐清洁”四字当之无愧,当即作题为《国立九中》诗一首,对该校进行赞誉。晚上学校师生举行晚会,师生高唱抗战歌曲,吹口琴,拉胡琴,十分热闹。冯玉祥在晚会上唱了一曲《爸爸在家》的山东土调,“唱得许多同学都哭起来了”[19]。当然,爱国情绪在国立九中校内献金竞赛大会中得到充分表现。18日下午献金台前欢呼声与军乐并起,“献金人学生、工友、校警、号兵、女佣、厨工皆有,附小学生有2人竟爬在献金台各献1 100元,女工郑大姐献52元,女生张淑瑜先献6 100元,并献戒指一枚,继将所余之220元亦全部献出,音乐教员瞿安华,视之甚为感动,立时借来2 000元捐献。高一分校高三下一班,全系来自战区无钱可献之学生,乃绝食一日,将膳费献出,其他各班学生亦相继响应。最后全体学生、工友一律绝食一日,将膳费捐献,初三分校女生决定全体食稀饭一日,将省下之饭费献出。学生陈东浮个人捐献34 000元,李文懋献32 000元,初中女生刘永兰献23 000元,其他女生纷纷献出珍贵之纪念品、珊瑚珠、金银链之类。”[20]全校捐献总数除实物外达50万元,与1942年成都五所大学献金总数相等,以战区学生占多数的国立九中有此成绩,江津各界“无不为之震动”[21]。1944年10月,蒋介石发表《告知识青年从军书》,号召知识青年投笔从戎,全国各省市知识青年踊跃响应。“四川射洪、绵竹、绵阳县中学生各100名,江津国立九中男女学生100余名,要求参加远征军。”[22]
(四)注重对学生的精神训练。国立中学作为抗战时期教育改革的特殊产物,非常重视精神训练。此种情况下,国立九中亦注重对学生的思想管控。一般来说,该校每天有晨会夕会,每日晨五时左右举行升旗礼,早操完后有导师简短的生活提示或纠正。该校每星期都有纪念周,每周月曜日上午七时举行总理纪念周,宣读青年守则后,由校长、导师轮流讲演总理遗教及青年训练大纲之各问题,如陈访先讲《现代妇女之责任》,邓季宣讲《从战区内流亡出来的青年应如何求学》,周庆孚讲《青年对于抗战建国意义之认识及应有之努力》,杨实秋讲《抗战时期青年应有之态度》,葛振邦讲《现代学生对于抗战建国应负之使命》等。该校还规定凡国民政府举行之纪念节,均由教师讲解本纪念节之意义及其与抗战建国之关系,如总理诞辰纪念、革命先烈纪念、国耻纪念、六三禁烟纪念等。此外,该校每月还有月会,主要由学生报告自己的学习与思想体会。当然,国立九中对学生精神管控最明显的方面表现为导师制的推行。根据学校规定各导师的任务较多,主要包括:“指导各该部之学生生活,训练学生思想,改善团体风纪,实施人格熏陶”;“与各该部学生共同生活,并随时检阅饭厅、自修室、宿室等处整洁及秩序”;“切实考察学生作息秩序,并按日登记”;“考察各该部学生之思想学业、纪律、服务卫生、整洁及勤惰等事项”;“举行学生个别谈话并将谈话内容,摘记谈话记录”。学校还明确规定每学期终了时,由级导师将该级学生各月精神训练成绩相加,以月数平均,即为学期精神训练成绩,导师还需要将其成绩分数、等级、总评登载在学生精神训练成绩记分表上,“除一份留存外另缮写一份送教导处汇总”[23]。在严格的导师制之下,学生成为书本的奴隶,对政治活动极少关注。
(五)鼓励学生参与战时后方服务。抗战时期安徽省数千青年在日寇炮火的威胁下远走他乡,极流离播迁之苦,此后他们有了读书的场所,能安稳地照旧读书。但是他们的读书目的是否已经达到了?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为读书而读书,为学问而学问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读书只是一种方法,一种手段,读书为的是要解决问题,为的是要明了生活的意义和生活的方法,为的是要达到生活的美满与充实。”[24]因此,自教育部颁布《中小学社教推行委员会组织大纲暨工作纲要》后,该校除组织总社推行委员会外,各分校均设有分校社教推行委员会。如师范分校依据工作纲要及环境在委员会下设八组,主要包括推广宣传组、慰劳伤兵组、民众学校组、流动教学组、通俗演讲组、社会调查组等。1939年6月4日,该校高中分校发动慰劳伤兵工作,是日该校五四歌咏团全体团员暨各级代表组织慰劳队由两位教师率领整队前往德感坝三王庙131后方医院。抵院后慰劳队分头开始工作,张贴标语,布置会场。待全体伤兵齐集后即整队表演,首由歌咏团总干事报告并致辞,随即表演合唱、独唱、口琴独奏、金钱板、平剧等节目,临时并有孩子剧团参加表演快板、唱歌、讲演三幕。再有德感坝民众与该院司书合奏平剧一幕,后由该院受伤同志代表致谢词。最后,双方合唱“全民抗战”一歌,全体精神振作,充溢欢愉和乐空气,并散发“告负伤同志书”[25]。女中分校为服务战时后方特成立歌咏队,工作多与宣传、家庭访问各队相互配合,如系单独工作还会加入讲演,歌咏队的主要材料包括“流亡三部曲”“到敌人后方去”“游击队歌”“全民抗战”“打倒日本”“军民合作”等。又如,初中分校为辅导学生及启发民众智力,增强抗战力量起见,特在初中分校职教员中敦聘吴大植等16人为社教推行委员,组织社会推行委员会,负责规划指导学生参加社教活动。此外,考虑到学校所在地江津德感坝旧历每逢三、六、九赶集,因而学校各分校也在相同时间组织宣传队,鉴于语言不通又辅助携带图书画报,并配合歌咏以引起民众的兴趣。国立九中服务战时后方的活动得到各界的高度肯定,1940年教育部奖励1939年度兼办社教成绩优良之专科以上学校及直辖中等学校名单中,国立九中与国立师范学院、华西协和大学、江苏教育学院等16校名列其中[26]。
三、抗战时期国立九中评述
实事求是地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并没有“国立中学”这一概念,只是抗战爆发后鉴于失学学生增多,教育部才在后方省份组设国立临时中学,专门进行收容。因战事而立的国立九中成立后在举办登记招生的同时,又就教育部发交审查登记合格之皖籍中等学校教职员中尽量选聘,同时规定初中教员每周授课16~20小时,高中及师范教员每周授课14~18小时,薪俸标准分为四级,每级5元,初中月薪自40~55元,高中45~60元。虽然待遇不高,但该校教师却鞠躬尽瘁,如音乐教师瞿安华经常带领班上同学到河滩拉胡琴,由是学校逐渐掀起一股二胡学习之风。学生彭修文亦受到其极大的影响,并得益于瞿安华的悉心指导,对二胡产生浓厚兴趣,进而“坚定了学习二胡的信念”[27]。著名历史学者章开沅曾表示国立九中的老师给他留下一辈子的深刻印象,“他们对我的影响是一生的,我很庆幸在国立九中结识了多位好老师,教会了我读书做人的道理。姚述隐和朱彤两位老师分别教授高一分部的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他们进一步激发了我对文学的爱好和写作才能。正是这两位老师,把我引上了文学青年的道路。姚述隐老师教学深入浅出,严谨而又不失风趣,他的元曲讲得特别生动、吸引人,我们常常忘记下课。因为姚述隐老师的元曲课,我常常沉醉于‘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的优美意境中。……有一次,朱彤老师带学生去一处劳动条件极为恶劣的煤矿。有的工人在长期暗无天日的劳作中已双眼失明,皮肤也被煤灰渗透成灰黑色,但仍勉强背煤,摸索爬行,惨不忍睹。当时,这幕地狱般的场景刺痛了我的内心,促使我更加同情和关心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18]198-199
从另外方面说,学校的成立也给流亡到后方的皖籍学生带来希望,当时学校食宿费是由国家提供,这对穷苦无依的学生是巨大帮助。然而,学生依然过得很清苦,他们的宿舍在两座破败的老祠堂里,教室是一大片临时搭建的简易竹篱茅舍。上课条件更艰苦,晚自习时学生每人各用一个碟子或一个破碗,里面放上灯草和桐油照明。为节约起见,学校还规定每盏灯最多用两根灯草,且一盏灯要供两张桌子四人共用。“小小的火焰还有黑烟,可想而知,亮度是十分微弱的。”[28]学校伙食条件也很差,营养先不论,填饱肚子都很成问题。米饭是掺杂着沙砾、稗子、米虫等杂物的“八宝饭”,难以下咽,菜也没有什么油水。如学生回忆,“我们第一年还能勉强吃得饱,可是随着物价的不断上涨,很快就开始变得三餐不继。记得当时一天给一斤稻谷,两顿稀的一顿干的,按说也不错了,可就是没有菜吃。开饭的时候,八个人才一钵菜,一个人没捞到几下子就没有了,而且天天都是卷心菜之类的素菜。到一个月头上,可以吃一次肉,可能因为肚子里的油水越来越少,大家一吃肉就闹肚子。一顿两顿吃不饱还可以扛一扛,顿顿吃不饱,就靠吃稀的,肚子越吃越大,越是这样,越是能吃,经常吃了上顿等不到下顿就饿了。”[29]著名史学家李国祁曾回忆自己在国立九中的难忘生活,“学校中午供应的是干饭,早晚是稀饭,初一时,大家就吃不饱,会抢饭吃,通常大家第一碗都盛少一点,吃完了赶紧抢第二碗。到后来,饭越来越不够吃,一个人平均只能吃到一碗饭,于是每个人都去买小脸盆作饭碗,盛饭时就尽量压,努力多盛一点。每天没有什么菜,可以说就是吃饭,而且越抢饭吃得越多,为了要我们少吃点,老师甚至还骗我们,‘饭不能多吃,多吃头会变大!’到最后学校没有办法,实行分饭制,一桌一个小桶,中午每人可分到一斤二两的干饭,以示公平。”[30]
对于学生的实际情况,时任教育部长陈立夫曾勉励道:“国立中学之设置,草创于人力物力拮据之中,缔构于国家民族艰危之日,其为不当更言享受,而尤应刻苦躬行。”[7]鉴于学生的实际情况,该校当局也曾做出不懈的努力。如起初,学生膳食由学校供给,每人还发给夹制服一套,1939年冬天时学校呈请教育部速发衣被,以为学生御寒之用。又如学生书籍原定每名每期由校津贴3元,但因书籍昂贵,高中学生书籍费没有7元无法办到,于是校方想方设法到处筹集。当教育部将公费生的救济金一律改为贷金后,国立九中又呈部认为师范生向来应以公费待遇,“与贷金有别,应准免膳费”,此后教育部照准并通令各国立中学遵照[31]。对于教育员生的困难,继任教育部长朱家骅在1945年7月7日发表《抗战第八年之教育》中坦陈:“因为物价的波动,各级学校教员生活异常清苦,此亦系战时不得已现象。幸多数教员,均能共体时艰,过着极苦的生活。”[32]
艰苦日子磨砺了学生不屈的品质,也使他们懂得相互谦让并加深了彼此间的友谊。如任继愈之弟任继周院士进校不久得了一场痢疾。那时没有特效的药品,校医就采用“以炭灰吸收毒素”的土办法,医生说治疗期间不能吃饭,要空着肚子吃炭灰。“任继周卧病期间,一个人住在学校边祠堂。同学们一下课就来陪他,下下棋、说说话,还帮他洗衣服,像一家人一样,让任继周很是感动。”[33]
毋庸置疑的是,国立九中的学生总是保持乐观的态度,他们在校园里安静的生活,日复一日不知疲倦地学习,甚至有学生还憧憬抗战胜利的场景。“残冬的早晨,太阳从云缝里钻了出来,露出了绯红的笑脸,轻暖的照着大地。人们在微笑欢呼,江水在奔腾狂流,在朝天门的码头上,拥挤着成千累万的人群,这一群不管是大人孩子,每个人的脸上,都挂上了笑容,这笑容是内心骄傲的笑容,我挤过了人群,跨上了乘长风破万里征程。我挤进了船舱,舱里满是人。都在谈笑着,喧哗着,一直到八点钟,汽笛一鸣船身渐渐离岸,船上人和岸上人互扬着手巾,帽子,珍重的叫着‘再会’,我也挤出了舱门,向着重庆这将成为历史上名词的新都,民族的复兴地,行着最后的告别礼:‘再会吧!重庆!’”[34]
四、余论
抗战时期日寇大举侵略中国,为保存中国的教育命脉,国民政府决定尽可能将沦陷区教育迁往大后方。但在此过程中,不少流亡到后方的学生失学,有鉴于此,教育部长陈立夫创设国立中学,主要招收沦陷区的学生,并给他们提供各种免费的待遇。由是,中国教育能在抗战时期保持继续发展。就安徽省来说,为求得本省将来的发展和青年学生的实际需要,根据教育部的命令,该省起初也将大部分师生迁移到后方,以维续教育发展。此后随着战事稳定,安徽省又在临近战区的地方重新建立教育,以应对日伪的奴化教育。如此双重教育措施,既在教育战场使本省立于不败之地,又为抗战胜利后本省教育的快速复员奠定了重要基础。当然,国立九中在办学过程中也表现了自己的特点,如为培养学生成才和守纪律,该校规定了严格的作息时间。一般情况下,学生每天5:30起床,6点晨会,6:30-7:30为早读,8点到12点上课;午后1点到3点上课,3点后多为课外活动,包括校外和校内两部分;下午5时半夕会,6点晚餐,7点到8点半自修,9时就寝。爱国情怀的培养,也使学生精神面貌有极大的改变,因而很多学生都自发请求参军到前线去。诚如一学生所言,“时代昭示我们伟大的任务,我们抗战的生力军应该站在最前线!在中国的青年应该在战争中去锻炼学习。”[35]
此外,国立九中的成立对于流亡后方的皖籍知识分子也给予了极大帮助。如安庆沦陷以后,1938年6月陈独秀全家与邓季宣等同乘一条轮船抵达重庆。此后,邓季宣在江津筹建国立九中的时候,想起了陈独秀住在重庆,生活困难,于是就写信邀请其全家来江津同住,并准备聘请陈独秀担任高中国文教员。陈独秀接信后,便于8月3日偕妻子潘兰珍与全家抵达江津,与邓氏在一个院子一起生活。由于教育部没有批准陈独秀在学校任职,加之长时间住一起终感不便,1939年5月,陈独秀一家由江津城迁居鹤山坪的石墙院。尽管如此,后来邓季宣还是邀请陈独秀到国立九中作过一次讲演,受到全校师生的热烈欢迎。考虑到陈家的实际困难,邓季宣还曾聘请陈松年到总务处当职员,兼教初中生物课。
抗战时期因时事的发展,教育部在后方四川设立国立九中以救济流亡的安徽青年学生。由于战前教育多与实际脱离,因而国立九中与其他国立中学一样被赋予了完成中等教育改革试验的使命。此后,随着国民政府在敌后建立不少游击政权,沦陷区学生奔赴大后方的人数减少,于是国立九中开始招收少量本地学生,如此一来无形中为本地培养了一批人才。总之,国立九中在川八年,不仅为安徽省和四川省培养了大批人才,也为全国教育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诚如赵鹏大院士回忆:“我在江津求学的一年,不但是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一年,而且还是我人生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28]因此,就事而论,抗战时期国立九中的存在值得后人肯定,其办学经验也值得去总结和借鉴,我们亦不能轻易否定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