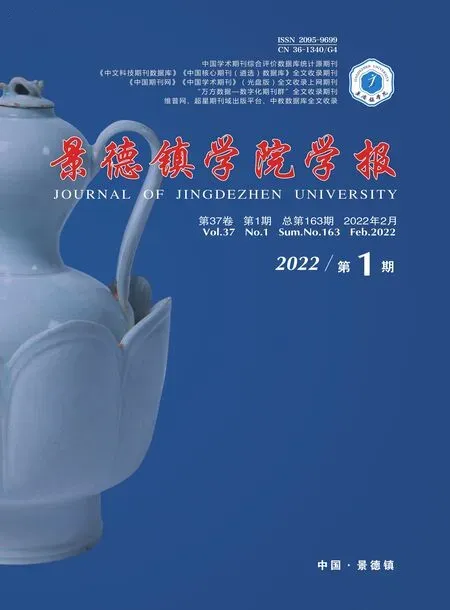乌干达文学源流考论
2022-03-16武子惠
武子惠,黄 晖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武汉430079)
乌干达,全称为乌干达共和国,位于非洲东部,横跨赤道,境内多为海拔1200 米左右的高原,多湖,有“高原水乡”之称,史称布干达,在不同时期又被称为卢干达、巴干达、干达。19 世纪中叶,布干达成为东非地区最强盛的国家,1850年以后,随着阿拉伯商人和英国、德国殖民主义者的相继进入,布干达王国内爆发了基督教新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间的连年战争,王国迅速衰落;1890 年,布干达被划为英国的势力范围;1932 年,乌干达宣布独立,成为英联邦成员国;1967 年9 月,建立乌干达共和国;1971 年伊迪·阿明发动政变后,军人专政,政治混乱,经济凋敝;到1986 年穆塞维尼执政,政局逐渐稳定,其国内的经济文化广泛地受到外来影响。乌干达官方语言为英语和斯瓦希里语,通用卢干达语等地方语言。各部族均有自己的语言,但大多数只有发音而无文字。虽然东非文学早期明显地落后于非洲大陆其他年轻的文学,但之后慢慢赶上来了,并且出现许多饶有兴味的作品。虽然东非文学的突出代表是肯尼亚文学,不过乌干达文学,特别是20 世纪70 年代以来,仍以自己独特的风格为肯尼亚文学和地区的文学交流做出了许多贡献。
一、文学的萌芽与发展概况
乌干达早期文学以口头文学的形式出现,那时产生语言,但未形成文字,人民凭借记忆力,将原初文学口口相传地保存下来。祖先创世的神话传说、各族头领与勇士们的传奇事迹、王国历史以及寓言和民间故事,都穿插着不少谜语和谚语,有浓郁的地方色彩。人们通过口头文学传递尊老爱幼、福祸共享、互助友爱精神以及那些能凝聚族人力量的传统道德。口头文学维系着传统社会的安宁和秩序。
书面文学出现较晚,1896 年乌干达语《圣经》的问世标志书面文学萌芽。乌干达文字的产生可追溯到19 世纪50 年代英法德的入侵,殖民者把当地语言用拉丁字母写成文字,卢干达语纸质版《圣经》问世之后不久,本土作家以当地的历史和习俗为题材,创作出乌干达的第一批书面文学。这一阶段的代表作家阿波罗·卡格瓦(Apollo Kagwa,1865-1927),根据本族与邻族的历史和习俗创作出卢干达文版的《布干达国王》(1901),此书成为了解乌干达历史的重要读物,后被译为英文。此外还有《巴干达民间故事》(1902)、《蚂蚱氏族手册》(1904)、《巴干达人的习俗》(1905)。他的秘书汉姆·穆卡萨(Ham Mukasa,1868-1956)和当时的布干达国王也是颇受欢迎的作家,作品内容以干达诸王的历史和干达人民的习俗为主。从1896 年书面文学产生到1932 年乌干达独立,这一时期的作品总体上数量较少,题材狭隘,形式单一,以传记和故事为主,创作者主要是当时掌握着文字的上层阶级,大都使用本土语言。
进入现当代以来的乌干达文学又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从原初的萌芽状态逐渐成熟。第一个阶段,1932 年国家独立到1971 年伊迪·阿明政变开始前,这期间时局稳定,乌干达出现了一批优秀的作家,英语写作出现且势头渐强。第二个阶段是1971 年到1986 年,伊迪·阿明政变使乌干达政局动荡,大批出逃海外的作家创作流亡文学,国内作家则以反映政治动荡为主题进行创作,英语文学占主导的同时非洲口语文学被重新提及。第三阶段,从1986 年穆塞维尼执政至今,乌干达国内政局稳定,创作群体和主题扩大,女性开始参与创作,文学呈现多样化发展的态势。
二、“舶来”文明冲击下的传统重建
乌干达现代文学的第一个阶段,从1932 年国家独立到1971 年伊迪·阿明政变开始,这一阶段的作品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显著提升,还产生了诗歌、小说、戏剧等体裁。其发展得益于三个因素:第一,1932 年作为英国“保护国”的乌干达建立了自治政府,宣告独立。第二,1948 年东非文学局建立,不过早期东非文学局的书籍主要用于扫盲和宣传说教。第三,1962 年乌干达创办了第一本文学和社会政治的综合性杂志《过渡》,促进了英语文学的发展。不久,乌干达的马凯雷雷大学也创办文学刊物来吸引广大文艺爱好者。60年代后,大批作家脱颖而出,作品围绕三大主题:1.强调非洲传统价值,抨击西方教育、文化及其制度;2. 揭示60 年代后期政府对布干达地区实施的暴力和高压统治,以及干达人恐惧且艰辛的生活;3.论述道德观和人生观。其中,第一类主题的作品最多,也最具时代特征,白人掠夺和统治非洲的历史过程中,奴隶贸易、殖民统治的思想基础即认为黑人天生低人一等的种族主义一度畅行无阻。只能凭借自身途径去获取尊严和独立的黑人,“首先必须纠正历史偏见对民族的误读、种族的歧视,才能焕发自信去争取独立。修复创伤和塑造自信的双重使命,让非洲文学有着非同一般的丰厚内涵。”[1]
诗歌异军突起。奥克特·普比泰克(Orcutt Pubitek)的四部诗歌作品奠定了他在东非文学的地位。自由体叙事长诗——阿乔利语版的《拉维诺之歌》通过被丈夫抛弃的拉维诺之口,斥责男方不顾传统道德而追求西化的行径,反映了传统价值观与西方价值观之间的矛盾,诗人表现出对本民族文化的热爱和赞颂。该作品对整个非洲都影响深远,被译成英文后轰动世界文坛。诗作《奥科尔之歌》则站在拉维诺的前夫奥科尔的角度,辩解其狂热追捧西方文化、追求繁华生活、抛弃糟糠之妻的行为,揭露了奥科尔自私的本性和他在社会变迁中的挣扎与苦恼,回击了当时社会上逐渐泛化的“奥科尔现象”。长诗《囚徒之歌》创作于朋友遇害和自己被无端指控的背景下。这三部作品,前两部是延伸性的戏剧独白,第三部是一系列的内心独白,以自我反思式的讽刺漫画的方式,探讨非洲过去与现在的关系以及现代非洲的困境。《玛利亚之歌》(1971)通过街头妓女来揭示新型非洲城市中的社会问题。受阿乔利口语的影响,这些作品都是以简短清晰、快速移动的线条勾勒出简明的图像。“这四首歌就是非洲经历的真正罗盘指针。”[2]《拉维诺之歌》和《囚徒之歌》是辩护诗;《奥科尔之歌》和《玛利亚之歌》是出击诗。然而它们都是极大绝望的诗篇,不仅表现讲话的个人的转变与危机,而且也表现他们自己的文化的转变与危机,作者在四首长诗中强调了非洲文化和民族意识,揭示西方文化带给非洲的弊端。奥克特·普比泰克的作品对后来非洲青年们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很多作家争相模仿《拉维诺之歌》的写作风格,采用叙事与独白结合,散文与韵文杂糅的松散文学形式。
奥凯洛·奥库里(Okello Oculi,1942-)在继承前辈成果的同时融入了自身独特的体验与思考,使诗歌达到又一个高峰。他出生于乌干达北部,就读于索罗蒂(Soroti)大学、托罗罗(Tororo)和基苏比(Kisubi)的大学以及马凯雷雷大学,担任过校报编辑,之后在英国获得政治学硕士学位,在美国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最后在乌干达和尼日利亚的大学里任教。奥库里凭借自身多元的文化背景,整合了诸多建构在非洲意象、谚语和民间智慧基础上的长诗。他的作品借自身丰富的背景经历,批判时人对主流统治文化的无耻模仿,同时重申非洲田园生活的尊严,有乡村对话的习语。奥库里最有名的诗作是处女作《孤儿》(The Orphan)(1968),延续了奥科特·普比泰克(Okot p'Bite)在《拉维诺之歌》(Song of Lawino)(1966)中开创的“歌曲传统”(song tradition)。这首长诗以韵散结合的形式哀悼非洲原初价值观的失落,用孤儿的困境隐喻非洲后殖民社会里地位低下的贫苦人民面临的问题。在东非的一个无名小国中,孤儿遇见了他的对话者,从不同的人物视角解读独立后的东非,正如孤儿被困在传统与现在、过去与未来交汇的十字路口,作者认为要建立美好的乌干达必须走背叛或妥协的道路,因为殖民地人民在没有选择权的时候就只能成为西方定义的世界中的“永久游客”。长诗《马拉克》(Malak,1976)和《库科莱姆》(Kookolem,1978)描写伊迪·阿明独裁统治下,非洲所面临的现代和传统之间的冲突,这一主题在他的小说《坎塔·雷蒂》(Kanta Riti,1972) 中也有表现。奥库里也出版了许多表现爱、死亡和文化冲突主题的短诗,这些诗作跨越30 年的时间,内容涉及非洲的政治和宗教信仰。小说《妓女》(Prostitute,1968)从妓女罗萨的视角探究统治阶层精英们的生活,对非洲独立后出现的社会问题进行分析和评论。
小说逐渐兴盛,有作家结合自身的留美经历进行创作。埃内里科·塞鲁玛(Eneriko Seruma,1944-)活跃在20 世纪60 年代末70 年代初的东非文坛上,他先后在乌干达和美国接受教育,因小说《经验》(The Experience,1970)而名声大噪。主人公汤姆·密提是一个黑人,在美国学习期间一直是种族主义者嘲笑的对象,回到乌干达后,他反而像那些“白人朋友和受过教育的非洲伙伴”一样轻视未“西化”的黑人们。小说讽刺和批判了像密提这样接受了西方的高等教育后被“白化”的非洲人,他们虽然是非洲血统,实则同种族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几乎没有区别。恩里科·塞鲁玛(Henry S. Kimbugwe,1944-)的小说《经验》讲述一个在白人世界里求生存的黑人的故事,是半自传性作品。《出卖心脏的人》讲述一个与女秘书偷情的白人在报纸上求购心脏的故事,侧面反映了非洲人在美国的艰辛生活,揭露和讽刺种族歧视与不平等。
三、对传统与外来问题的理性思考
1971 年乌干达国内发生伊迪·阿明政变,大多数作家离开了这个政治混乱的国家,流亡他国。这批作家对其他国家的文学发展做出了诸多贡献,也促进了跨地域的文化交流。尽管如此,乌干达国内文学也取得了独特的成就。这一时期的国内文学继续探讨殖民与独立、外来与传统的关系;不过,相较于上一阶段作家们“一边倒”地强调非洲的传统价值,用非洲民族主义的心态去抨击西方,这一阶段的非洲作家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对本土文化的维护超越了狭隘的种族主义,也能更客观和理性地评价西方文明。这一阶段的文学在形式上以诗歌为主,间或有散文、小说和诗剧。英语文学继续发展,具有非洲母语特色的口语文学被重新重视。
在占主导地位的诗歌和散文方面,约瑟夫·布鲁加(Buruga, Joseph,1942-)的长诗《废弃的小屋》(The Abandoned Hut)继承了奥克特·普比泰克《拉维诺之歌》的传统,审视非洲文化与欧洲价值观的矛盾冲突,作品批评西方化的女性芭西雅,意在揭露东非人盲目效仿西方的行径,反对非洲精英阶层抛弃传统的智慧、稳定和道德。塔班·洛·里永(Taban Lo Liyong,1938-)是东非文坛上最有争议和颠覆性的人物之一,他在大学时就开始思索新兴崛起的东非文学并发表了文章《我们可以纠正东非文学的荒芜吗?》(Can We Correct Literary Barrenness in East Africa),他的诗文因纯熟的技巧和对国际性先锋问题的讨论而闻名。他自认为是文化牛虻,不满于后殖民文化,他假定写作是一种破坏习俗的形式,认为要打破文化和语言中已建立的权威。里永诗意的核心是像超人一样的神话,是面对社会的局限时能够超越它们的尼采哲学的品质,是个人对理性意志的信仰驱动。这种生活哲学是灵魂在宗教和社会惯例之上的凯旋,正如《穿制服的男人》(The Uniformed Man,1971) 的序言:自然和文化都被破坏了,原本应该像镜子一样反映它们的艺术也确实只能记录下破碎的画面。20 世纪60 年代末达到了创作高峰期,以反对美洲偏见和批判非洲这一时期流行的意识形态为主题。在这一时期,我们会发现一个矢量经常性地移动到另一个——从对非洲文化的防卫到激进地解构。《固定器》(Fixions,1969) 和《正在午餐的首领们》(Eating Chiefs,1971) 显示了对非洲文化的拥护,作者阐释、整合和恢复民间故事与歌谣;但同期的文集《最后的世界》(The Last Word,1969),《穿制服的男人》(The Uniformed Man,1971)和《林波的冥想》(Meditations in Limbo,1970),作者讽刺非洲文学中强烈的文化民族主义。里永同期的诗歌作品也呈现这种特点,诗集《弗朗茨·法农的不均匀肋骨》(Frantz Fanon’s Uneven Ribs)是对西方历史体系性的错译,旨在为非洲文学的发声创造空间;但《不发达的民谣》(Ballads of Underdevelopment,1976) 又破坏了非洲传统的哲学和诗学基础。20 世纪80 年代是里永在非洲的第二个创作高峰期,这一时期诗歌中的非洲格言几乎消失了,抒情性的音节成为他与后殖民主义危机相遇的标志,50 年代在美国的生活给里永一种倾向美国的观点,见之于《掌握棕榈树知识》(Carrying Knowledge up a Palm Tree) 和《农场的奶牛》(The Cows of Shamba)等作品中。奥斯汀·布肯亚(Austin Bukenya,1944-)的诗剧《新娘》(The Bride) 描述了那些厌倦传统文化和偏见观念的年轻人与自视传统守护者的老年人的冲突,不过在批判非洲传统的同时,该剧也展现了非洲文化宽容、平静与友爱的一面。作者用非洲习语给这部剧以泛非洲视角,打破了非洲在人类学研究中学术僵化的局面。他的诗歌同样探讨不求回报的爱、传统文化的地位等。
小说方面,布肯亚的小说《人民的学士》(The People′s Bachelor)用滑稽戏谑的语气审问非洲精英阶层的不当行为,这些人不顾社会民众的贫困,沉湎于享乐和晦涩的社会变革理论。戈得夫利·卡里穆戈是20 世纪70 年代乌干达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涵盖非洲文学新旧两个主题,既反映殖民前的非洲社会,也反映殖民后的欧非文化冲突以及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邦尼·鲁贝加是一名小说家和儿童文学家,也做过编辑、教师、记者、编剧和电台节目制作人,其作品《燃烧的灌木》(The Burning Bush,1970)、《流浪者》(The Outcasts,1971)、《蜂蜜罐》(The Pot of Honey,1974),涉及熟悉的主题,如文化冲突、社会政治危机以及个人在社会中的异化。他编写的卢干达语词典,对乌干达地区的语言普及产生了重要影响。
约翰(John Ruganda,1941-)的《负担》(The Burdens,1972)是典型的非洲后殖民主义剧本,通过一个家庭的内部矛盾探讨长期困扰非洲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戏剧《洪水》(The Floods,1980)展示了伊迪·阿明独裁统治下的悲惨生活。《没有眼泪的音乐》(Music Without Tears,1982)和《沉默的回响》(Echoes of Silence,1986)探讨政治环境、社会压力和个人奋斗之间的关系,虽然从日常生活切入,但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和浓厚的悲剧色彩。
口语文学方面,尽管英文写作毋庸置疑地占据主流地位,不过本土口语文学的呼声也越来越高。里永主张废除英语系而建立淡化语言意识的“文学系”,意在聚焦非洲人的口头文学和文学创作。他是非洲口头文学课程的第一位老师,出版了《东非的大众文化》(Popular Culture of East Africa)。布肯亚也是口头文学的先驱者,他为非洲的口头文学带来了超越种族主义的纲领性新方向,与简·恩达瓦(Jane Nandwa)合著的《学校非洲口头文学》(African Oral Literature for Schools) 确定了非洲口头文学的定义和分类程序;《口语是非洲发展中的工具和技巧》(Oracy as a Tool and Skill in African Development) 认 为口头文学和表演是辩论性的修辞和组织性的工具; 另一本合编文集《理解口头文学》(Understanding Oral Literature)是口头文学方法论研究的开山之作,让读者警惕视口头文学为落后文化的倾向,认为口头文学的即时性更适于沟通的艺术,在先进社会里也是惯用的和富有活力的。
四、视野走向多元化和国际化
伊迪·阿明政变导致乌干达在长达15 年的时间里内战不断,直到1986 年穆塞维尼执政国家才恢复秩序,和平环境下文学创作迎来第二次高潮。乌干达作家的视野不断扩大,从横向看,由限于本国的政治和文化习俗逐步走向非洲的其他国家,走向欧洲乃至全世界;从纵向看,由反映政治混乱、人民苦难和殖民问题转向具有全人类性质的种族、性别等问题。文学体裁也逐渐多样化,长篇小说受作家喜爱,剧本也开始流行。
摩西-伊塞家瓦(Moses Isegawa,1963-)成长于乌干达的天主教神学院,后移居荷兰。其小说《阿比西尼亚历代记》讲述了阿明统治时期,归国留学生的一系列升迁、失宠和遭到迫害的经历。在叙述70 年代的阿明统治时,与独裁前后的民主体制做对比,揭露了独裁统治下畸形的国家体制,他将独裁的国家领导比作专横残酷的父母并巨细无遗地记录下家族的灭绝,既复刻了被驱逐到印度和西方犹太社区里的非洲流亡者的生活经历,也刻画了战争蹂躏和艾滋病入侵的乌干达的本土生活,“一块错误的盛有残渣的土地,在这里在每一个无底洞下面都有另一个等着去诱捕人民进入罗网”[3]。另一部小说《蛇穴》(Snakepit) 同样描述了70 年代的堕落腐败和残暴,主人公巴特获得剑桥学位后返回家乡,在参孙(Samson Bazooka Ondogar)的帮助下成为电力和通讯部部长;参孙将军的漂亮女间谍维多利亚爱上了巴特,但价值观不合的两个人逐渐变得矛盾重重,维多利亚因爱生恨,把巴特陷害入狱,巴特在狱中被恐吓得几近崩溃。巴特的经历与国家陷入恶性循环的轨道相一致,作者暗示个人是无法在堕落的国家里重生的。小说通过谋杀、酷刑和抢掠等细节,例证这个后殖民国家在独立的第一个十年里的困顿和绝望,对偏执的权力斗争和充满敌意的恶性竞争进行了反思和探讨。短篇小说《占星师》(The Astrologer)是对《蛇穴》中一个章节的延伸和重写,小说以老师的视角讲述母校被童子军攻击的故事。《耳朵的战争》(The War of the Ears,2005)描绘了被内战恐惧掌控着的乌干达——政府军与伪宗教游击队战斗的时期,童子军们希望长辈们可以在政府拿着喇叭敲门宣传的时候,将他们的耳朵切下来。
诗人提摩西·旺古萨以诗集《敬礼:1965-1975 年诗集》(1977)而知名。1994 年该诗集增添了新内容后重新出版,改为《尘埃图案:1965-1990 年诗选》,主要描述农村的田园生活。近年来,乌干达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女作家,比如乌干达女作家协会创始人之一的戈雷蒂·克约穆亨多,她发表了4 部小说《第一个女儿》(1996)、《不再有秘密》(1999)、《维拉的悄悄话》(2002)和《等待》(2007),还创作了儿童读物《不同的世界》(1998),她主要关注妇女问题,如家庭暴力和社会对未婚生育妇女的偏见。
五、结语
乌干达的知名作家大多有国外留学、流亡或侨居的经历,他们用生动的笔触,以诗歌、讽刺小说、短文和文学评论等方式,描写处于社会变迁和不同政治时局下的人生百态,抨击社会弊病,讴歌勇于抗争和顽强生活的人民,宣扬本土文化,赞美乌干达恬静的田园生活。近年来,得益于和平发展的国际国内环境,乌干达文坛不少青年作家脱颖而出,给这个年轻的独立国家带来新的生机和精神食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