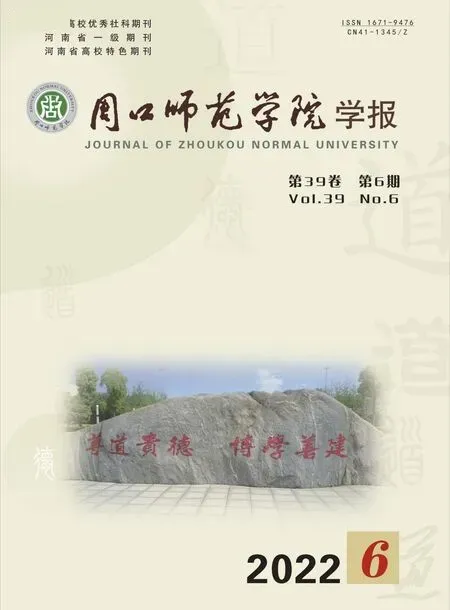道教对南诏大理国认同中华天文历法的影响
2022-03-14颜文强黄俊杰
颜文强,黄俊杰
(大理大学 民族文化研究院,云南 大理 671003)
天文历法对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无论哪个民族、哪个地区皆是如此,只是程度有别而已。唐宋时期,地处祖国西南边疆的少数民族政权南诏大理国就已经设有职官进行专门的天象观测和历法推算。唐樊绰《云南志·卷九》记载曰:“军谋曹长,主阴阳占候。”[1]笔者认为,南诏大理国的天文历法知识除了少数受印度佛教影响外,更多的是来自中原。其中,以阴阳历算见长的中国本土宗教——道教对中华天文历法文化在南诏大理国的传播、认同产生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目前学术界对于此专题研究尚处空白,故本文拟对此进行稽考,以抛砖引玉。
一、五星七曜
《南诏图传》是南诏时期杰出的绘画代表作,绘制于南诏蒙舜化贞中兴二年(公元898年),故又称为《南诏中兴画卷》《南诏中兴二年画卷》,其《文字卷》记载了南诏已有“五星七曜”的天文知识:
广施武略,权现天兵,外建十二之威神,内列五七之星曜[2]。
文中的“五七之星曜”即是指“五星七曜”,其中“五星”指五大行星,即木星(岁星)、火星(荧惑星)、土星(镇星)、金星(太白星)、水星(辰星),又称为五曜;“七曜”是指五星加上日(太阳星)、月(太阴星)。此外,由大长和国内供奉僧、崇圣寺主、义学教主、赐紫沙门玄鉴所编纂的《护国司南抄》也出现了“月朔”“月望”“在天为五星”“日在东、月在西”等天文学知识。“五星七曜”是我国古代先民对宇宙部分天体运行规律观察的总结归类。早在《易·系辞》就有对此的记载:“天垂象,见(现)吉凶,圣人象之。此日月五星,有吉凶之象,因其变动为占,七者各自异政,故为七政。得失由政,故称政也。” 古人由“天文”推及“人文”,认为人事的吉凶与天象密切相关,所以“七曜”又称为“七政”。《史记·封禅书》记载了西汉前已建有祭祀五星七曜等反映星辰崇拜星辰的祠庙:“雍有日、月、参、辰、南北斗、荧惑、太白、岁星、填星(镇星)、辰星、二十八宿……之属,百有余庙。”[4]398两汉时期在“天人感应”观念的影响下,谶纬风气盛行,以日月五星运行的天文星象占验人事国运吉凶成为常态。《史记》记载了用五星星象进行预测占卜的情况,如《天官书》云:“火犯守角,则有战。”[4]352“火犯守角”的“火”指五星中的火星,“角”指二十八星宿中东方七宿的角星宿。“火犯守角”意思是火星运行到角星宿附近,古人认为此天象不吉会有战事发生。今天看来,战事发生与否与此并没有直接关系,但从中却反映了古人迷恋星占术的现象。汉代以后星占观念依然盛行,《晋书》《魏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唐会要》等历代史料记载了大量星占事迹。
基于古人星占观念的长盛不衰,道教自从成立起就一直有“夜观星象”的传统,并将对天文历法的研究推算作为传道弘道的内容,从而为中国的天文学做出了重大贡献。如东晋道教医家葛洪撰有《浑天论》,南梁道教医家陶弘景“尤好五行阴阳,风角气候,太一遁甲,星历算数”[5],著有《天文星经》五卷等。隋唐之际道士父子李播、李淳风也是星算大家。李播撰有《天文大象赋》,李淳风是唐朝太史局负责以天文历算推测国运的官员,其与袁天罡合著的《推背图》一书更是流传至今、闻名遐迩。值得一提的是,隋唐之际出现了一部名为《丹元子步天歌》的天文学著作。该书是中国天文学史上记载“三垣二十八宿”体系最早、最完整的文献。而该书作者丹元子则是一位地地道道的道士。教育部长江学者、著名道教研究专家盖建民教授曾考证指出:“不管《丹元子步天歌》的作者是否真为王希明,我们都可以判定,《丹元子步天歌》肯定出自隋唐道徒之手,是道教天文学的珍贵文献。”[6]道教不是停留于对天文历术的推算,而且进一步将日月星辰拟人化、神格化、制度化,建立起富有自己特色的道教天学体系,从而广泛应用于数术推断、斋醮法事等宗教活动中。道教认为人事的吉凶与日月星辰关系密切,道教尊称五星七曜为“五星七曜星君”。约出于唐宋间的道教经典《太上洞真五星秘授经》详细阐述了五星七曜星君的服饰神像特征、功能执掌、祭祀祈祷方法等情况:“东方木德真君,主发生万物,变惨为舒,如世人运炁逢遇,多有福庆,宜弘善以迎之。其真君,戴星冠,蹑朱履,衣青霞寿鹤之衣,手执玉简,悬七星金剑,垂白玉环珮。宜图形供养,以异花珍果、净水名香,灯烛清醴,虔心瞻敬,至心而咒曰:木星真君,动必怀仁。悯见志愿,寿我千春。西方金德真君,主揫敛万物,告成功肃,如世人运炁逢遇,多有灾怪刑狱之咎,宜弘善以迎之。……南方火德真君,主长养万物,烛幽洞微,如世人运炁逢遇,多有灾厄疾病之尤,宜弘善以迎之。……北方水德真君,通利万物,含真娠灵,如世人运炁逢遇,多有灾滞劾掠之苦,宜弘善以迎之。……中央土德真君,主四时广育万类,成功不愆,如世人运炁逢遇,多有忧塞刑律之厄,宜弘善以迎之。……太阳真君,主照临六合,舒和万汇,如世人运炁逢遇,多有喜庆,宜弘善以迎之。……太阴真君,主肃静八荒,明明辉盛,如世人运炁逢遇,多有惨惨之忧,宜弘善以迎之。”[7]道教认为,金木水火土五星真君和日月太阳真君、太阴真君各有权责分工,因此必须有针对性地用不同祝祷词进行祭祀祈祷。道观中常常供奉有五星七曜星君的神殿,在道教斋醮科仪中也常迎请五星七曜星君降坛驱邪禳灾。《太上洞真五星秘授经》此段论述规整和详尽,为道士做法事以及民间祭祀提供了较好的指南。
唐朝时期多位帝王对道教的推崇使得有意归附大唐的南诏受到了道教文化的深刻影响,其中对于五星七曜星君信仰文化的传播也无形中促使中华五星七曜等天文学知识在南诏大理国的传播与认同。值得注意的是,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李晓岑教授曾指出:“《中兴二年图传·文字卷》上有‘内列五七之星曜’的句子,说明印度历所用的七日周期制已传到了南诏。”[8]35对此,笔者不敢苟同。笔者认为,诚然南诏“七曜”知识可能或多或少也会受到印度天文知识的一些影响,但南诏与大唐关系密切,而“五星”对应“五行”的观念则起源于中国,且体系之完备以中国为最;1973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在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五星占》的“写作年代约在公元前170年左右”[9],为我国最早的天文学著作,表明至少在2000多年前我国已经有系统利用五星进行占卜的现象了。此外,唐朝时期五星与七曜合并归类的系统性、完整性则以道教的阐述最为系统规范。因此,笔者以为《南诏图传·文字卷》和《护国司南抄》所记载的南诏的天文知识应是受到道教文化的影响居多。
二、北斗七星
20世纪50年代大理北汤天村出土的大理国时期的写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中出现“七星”的记载,70年代在大理崇圣寺的千寻塔的维修过程中则发现了一批南诏大理国时期的佛像、写经等文物,在这些文物中有一张绘有30多颗星体的大理国时期的绢帛符咒图。对于上面所绘星体内涵,科技史专家李晓岑教授指出“其中有七颗应与北斗七星有关”[8]35;对于其上的符咒来源,宗教史研究家段玉明教授直接指出:“这是一张典型的道教符箓,虽然其中杂糅了密教的成分。”段玉明教授进一步分析说:“符咒上点(即星)的数目分别为五、六、七、八、九,代表东、南、北、西、中‘五斗’,‘为太一之形,‘力去田鼠’之类字样实是道教劫鬼、驱鬼之符。道教相信,礼斗朝真可以消灾解厄、增福延年。除了绘有‘五斗’图形与咒符之外,这张符箓还同时绘有曼荼罗图形与梵文。这不仅向我们证实了大理时期道教较为兴盛的事实,更重要的是证实了大理时期的道教与密教关系很深。”[10]结合图像内容来看,段玉明教授解读的“五斗”应为李晓岑教授指出的“北斗七星”的部分。基于这两条信息可以看出,大理国受道教文化的影响已经具备了北斗七星等天文学知识。
北斗七星是指由天空北边的北极星附近的天枢星(贪狼星)、天璇星(巨门星)、天玑星(禄存星)、天权星(文曲星)、玉衡星(廉贞星)、开阳星(武曲星)、摇光星(破军星)共七星组成。由于这七星相连如古代舀酒斗状,故称为北斗;如果再加上旁边比较暗的两个星左辅星(洞明星)、右弼星(隐元星),则共有九颗星,称为“北斗九星”。我国先民观察到北斗七星总围绕北极星转,故很早就利用北斗七星的指向来确定季节。古天文历法研究专家、贵州省社会科学院院长蒋南华教授指出:“早在六千四百年以前,我们的祖先通过长期的天象观测,不仅有了二十八宿的整套观念,懂得了用二十八宿的方位和拒度来定月份和季节,而且对北斗星这一散星的运行规律及其重要意义也有十分透彻的认识。”[11]河南濮阳出土的6000多前仰韶文化45号墓葬也证实了这一点。该墓主人两侧为蚌壳组成的苍龙、白虎,此为早期四神兽之二,墓主人脚底旁则为两根人胫骨和蚌壳组成的北斗七星图。战国时期道家典籍《鹖冠子·卷上》记载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12]西汉时期以道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淮南子·卷三·天文训》曰:“帝张四维,运之以斗,月徙一辰,复返其所。正月指寅,十二月指丑,一岁而匝,终而复始。”[13]《史记·天官书》云:“北斗七星,所谓‘旋、玑、玉衡以齐七政。’杓携龙角,衡殷南斗,魁枕参首。用昏建者杓;杓,自华以西南。夜半建者衡;衡,殷中州河、济之间。平旦建者魁;魁,海岱以东北也。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4]351可见,我国古代先民早就通过“观象授时”方式利用北斗七星的运转来推定季节时令以指导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成语“斗转星移”即是来源于此。
制度道教形成后进一步将北斗七星拟人化、神格化,称为“北斗七元星君”,分别为天枢宫贪狼星君、天璇宫巨门星君、天玑宫禄存星君、天权宫文曲星君、玉衡宫廉贞星君、开阳宫武曲星君、瑶光宫破军星君。道教认为人的吉凶祸福与斗七星密切相关,因此需要祈祷祭祀以禳灾祈福、趋吉避凶。约出于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上清派经典《北斗九皇隐讳经》引《黄老经》曰:“北斗第一入(当为“天”字)枢星,则阳明星之魂神也;第二天璇星,则阴精星之魂神也;第三天机星,则真人星之魄精也;第四天权星,则玄冥星之魄精也;第五玉衡星,则丹元星之魄灵也;第六开阳星,则北极星之魄灵也;第七瑶光星,则天关星之魂,大明也;第八洞明星,则辅星之魂精,阳明也;第九隐元星,则弼星之魂,明空灵也。”[14]宋李思聪编撰的《洞渊集·卷七·北斗七元星君》详细阐述了“北斗七元星君”的执掌分工情况:“北斗第一天枢,贪狼天英星君。上管室、氏、房、心、箕、牛、宿,下管扬、郑、充、徐等州分野,管天下子生人身命禄,筭注世人求官觅职之事,掌北斗阳明延生真炁。……北斗第二天璇,巨门天任星君。上管亢、昴、井、鬼、张、翼等宿,下管临、荆、楚、周分野,管天下丑亥生人命禄,注世人求仙学道之事,掌北斗阴精度厄真炁。……北斗第三天机,禄存天柱星君。上管娄、胃、参、柳等宿,下临宋、豫分野。管天下寅戌生人命禄,注世人求财庄宅之事,掌北斗真君保命之炁。……北斗第四天权,文曲天心星君。上应牛、危等宿,下临吴、越分野。管天下卯酉生人命禄,注世人寿福身相之事,掌北斗文明益筭真炁。……北斗第五天冲,廉贞天禽星君。上管玄、尾、女等宿,下临赵、冀、魏、晋等分野,管天下辰申生人官禄福命,注世人婚姻妻妾之事,掌北斗丹元消灾真炁。……北斗第六开阳,武曲天辅星君。上管房、斗、牛等宿,下临燕国分野。管天下巳未生人禄命,注世人兴生业次财帛之事,掌北斗北极散祸真炁。……北斗第七摇光,破军天关星君。上管虚、轸、角、奎、觜等宿,下临青、齐、卫、并州等分野。管天下午生人禄命,注世人福德相貌妻妾奴婢之事,掌北斗天关扶衰真炁。”[15]849-850道教将北斗七星的自然天体升华为神灵星君,使得在星占观念浓厚的汉唐时期大大促进了北斗七星等天文知识的传播。崇圣寺千寻塔出土的大理国时期绢帛符咒图出现的道教符咒与北斗七星图案反映了道教文化对大理国的影响,从而客观上促进了南诏大理国对中华天文历法文化的认同。此外,大理国写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中除了有“七星”文字,还出现了“二十八宿”的记载。当然此处需要指出的是,虽然道教对中原“二十八宿”天文知识的贡献甚大,但由于目前关于二十八宿的起源有中国起源说、古印度起源说和古巴比伦起源说等多种观点,且《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为佛教经典,故无法判断大理国的“二十八宿”天文知识是否受道教的影响。不过从内容来看,此处所反映的大理国“二十八宿”的天文知识当是受印度佛教影响为多。
三、“天辅”“上元”年号
年号是古代君主纪年的一种方式,始于西汉汉武帝时期,用于象征新政气象。在南诏大理国历代君王的年号中,有两个既有天文历法内涵,又具有道教文化底蕴的年号——“天辅”年号和“上元”年号。
(一)“天辅”年号
《云南志略》和胡本《南诏野史》记载了大理皇帝段智祥的第二个年号为“天辅”,如胡本《南诏野史》记载曰:“智祥,南宋宁宗乙丑开禧元年即位。明年,元天开。又改元天辅、仁寿。”[16]即指出,在南宋宁宗乙丑开禧二年(公元1226年),大理国王智祥改年号为“天辅”。
我们知道,北斗第六颗星开阳星在道教中又名武曲星、天辅星,并进一步神格化为武曲星君、天辅星君或武曲天辅星君。《洞渊集·卷之七·北斗七元星君》直接指出北斗第六星开阳星是“武曲天辅星君”,而且阐述了其所执掌的人事吉凶的情况:“北斗第六开阳,武曲天辅星君。上管房、斗、牛等宿,下临燕国分野。管天下巳未生人禄命,注世人兴生业次财帛之事,掌北斗北极散祸真炁。纪明之宫,武曲主木,披青霞瑞云之帔,戴七宝星冠。武曲即天之太常,星围七百里,光照万国。”[15]850《灵宝领教济度金书·卷二百二十二·科仪立成品》记载了道教斋醮科仪奉请北斗九星君的名号:“具位奉行玄灵璇玑经忏道场清醮法事:臣某与临坛官众等谨同诚上启:太上无极大道斗中高上玉皇尊帝,太微玉帝,北极玄卿大帝,北斗太上宫贪狼玉晨君,北斗天任巨门玉晨君,北斗天柱禄存玉晨君,北斗天心文曲玉晨君,北斗天禽廉贞玉晨君,北斗天辅武曲玉晨君,北斗天冲破军玉晨君,北斗天内外辅玉晨君,北斗天蓬内弼玉晨君……”[17]其中第六颗星就称为“北斗天辅武曲玉晨君”。当然,也有把北斗第四颗星称为天辅星的,如约出于唐宋时期的道经《太上洞玄灵宝护诸童子经》曰:“道言:道能生成,道能育养。七神童子者,是中天北斗七星之精炁也。凡人荫在胎中,七月之时,下降人身,开明九窍,记于姓名,便属管系。一曰天蓬,二曰天内(当为‘芮’字),三曰天冲,四曰天辅,五曰天禽,六曰天心,七月(当为‘曰’字)天柱。”[18]此处即是将北斗第四颗星称为“天辅星”。不过无论“天辅星”是北斗的第六颗星还是第四颗星,但“天辅”一词来自天文学,用于指北斗七星(九星)中的一颗星辰,当是无疑的。道教典籍《太上三元飞星冠禁金书玉箓图·步九宫斗诀》更细致描述了道教科仪踏罡步斗模仿天上北斗九星进行禳灾祈福的情形:“斗要妙,十二神。乘天罡,威武陈。气彷彿,如浮云。七变动,止应天。知变化,右吉凶。步斗宿,天关前。入六律,持四禁。傍天英,履天任。拥天柱,接天心。从此度,登天禽。倚天辅,望天冲。入天内(当为‘芮’字),出天蓬。斗道通,刚柔济。天富禄,清泠渊。入杳冥,千万岁。”[19]在中国历代皇帝年号中,有两个皇帝在位期间有名为“天辅”的年号: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第二个年号,大理皇帝段智祥的第二个年号。而无论古代还是今天,对于将“天辅”一词作为星辰名号进行使用的主要是在道教界和道教学界。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天辅”作为大理国皇帝的年号,应是受道教文化的影响所致,从中也表明道教对南诏大理国认同中华天文文化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
(二)“上元”年号
“上元”是南诏国王异牟寻的第二个年号,始于公元784年。“上元”是道教上中下三元节日之一。其中农历正月十五为“上元节”、七月十五为“中元节”、十月十五为“下元节”。笔者窃以为,三元节日来自天文历法,三者皆指一月中的月圆之日。
我们知道,从地球上看月亮的圆缺,主要取决于日、月、地三者位置的不同,即地球上看到的月球被太阳照明部分的视觉形象,天文学称为月相。一月中,最重要的有四种月相:朔(农历初一)、上弦(农历初七或初八)、望(农历十五或十六)、下弦(农历二十二或二十三)。其中,当月亮位于太阳和地球之间,日月黄经差为0度,月亮暗的一面面对地球,此时为“朔”;当月亮绕行至地球后面,黄经差为180度,月球被太阳照亮的半球面对地球,此时为“望”。月球引力对地球的影响会给地面的人类活动产生影响,特别是月圆之日,月球引力对地球的影响最大,因此月圆之夜一般不宜进行激烈的活动。上中下三元日是一年之始、中、终三个特殊的时间节点,因此月球引力对地球影响较其他月份的月圆之夜影响更大,给人事活动带来的影响也最为显著。道教将此天文历法知识进一步改造,认为三元日与人事吉凶颇为密切,从而赋予了人格化、神格化的天地水三官信仰。道教经典《上清六甲祈祷秘法》指出:“上元九炁赐福天官,中元七炁赦罪地官,下元五炁解厄水官。”[20]就是说,上元天官赐福,中元地官赦罪,下元水官解厄。约出于南北朝末至隋唐之际的《太上洞玄灵宝业报因缘经》详细阐述了三官神祇的职责分工情况:“正月十五日为上元,十天灵官、神仙兵马,与无鞅数众上圣高尊、妙行真人同下人间,考定罪福。七月十五日为中元,九地灵官、神仙兵马,与无鞅数众名山洞府、神仙兵马同下人间,校录罪福。十月十五日为下元,九江水帝、十二河源溪谷大神、水府灵官同下人间,校定罪福。”[21]100“三元者,谓上、中、下也。一者上元,正月十五日,天官主禄。二者中元,七月十五日,地官主禄。三者下元,十月十五日,水官主录。”[21]120“上元”是一年中的第一个月圆之日,为天官赐福之日,也是斋戒祈祷求福的上佳时机。南诏王异牟寻之所以在公元784年改年号为“上元”,当是因为公元779年南诏军队被大唐打败后的一种心理反应:一是为了取悦于大唐朝廷,为以后归附大唐做好铺垫。因为异牟寻即位前不久的唐高宗李治和唐肃宗李亨曾各有2年名为“上元”的年号时期,分别是公元674年—676年、公元760年—761年。二是异牟寻可能希望“上元”所蕴含的天官赐福内涵给兵败不久的南诏官兵百姓带来福佑,以起到安抚民心的作用。尽管道教对“上元”内涵作为一种信仰进行建构和传播,但却顺应了当时人们的普遍心理诉求和社会需要,而其本质上反映的天文历法事实也无形中促进了南诏大理国对中华天文历法文化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