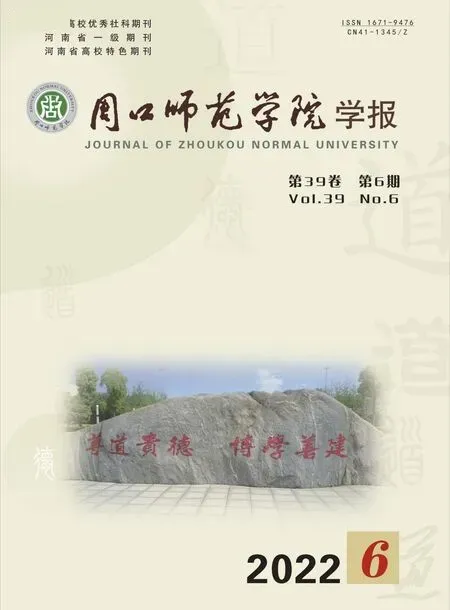“韩柳齐名说”新论
2022-03-14郭发喜
郭发喜
(洛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洛阳471934)
近世以来,研习古文者莫不以“韩柳”为宗,然而二人并称始于何时、齐名之缘由,各家论点则大有可商榷处。刘城、杨再喜将杜牧作为“韩柳”齐名说的首倡者,因其《冬至日寄小姪阿宜诗》有“李杜泛浩浩,韩柳摩苍苍”[1]214句,前者据此称他“首次把韩愈与柳宗元并称”[2]73-77,后者称赞他“在文学史上第一次明确地将柳宗元的文学地位同韩愈相提并论”[3]54-55。汤江浩则认为“至晚唐五代逐渐形成了韩、柳并称之说,至宋初则已广为世俗所接受”[4]69-76。以上说法都有可取之处,然考索中晚唐文史资料,则可知“韩柳”齐名说并非特例,而且时间上还可追溯至更早。
一、韩柳齐名之渊源
唐人重文名,喜并称,如“文章四友”“沈宋”“李杜”之类。中唐之时,韩愈接续独孤及、梁肃所开创的古风革新风气,以大量雄健、充实、新奇的作品在文坛上打开了局面。一时之间,文士翕然宗之,共尊其为文坛领袖。故当时论文者,莫不以韩愈为首。
第一,最早与韩愈齐名并称者,并非柳宗元,而是萧存等人。《尚书比部郎中萧府君墓志铭》载:“大历初,(萧存)与昌黎韩愈、天水赵赞、博陵崔造素友善齐名。”[5]7084萧存(739-800)为萧颖士之第二子,史称其“能文辞,与韩会、沈既济、梁肃、徐岱等善”[6]5770。曾与颜真卿、陆鸿渐交好,并“作书数百篇”。萧存于韩愈有知遇之恩,“韩愈少为存所知,自袁州还,过存庐山故居”[6]5770。赵赞,两《唐书》无传,德宗时人,事迹散见于《册府元龟》《唐会要》等书,建中年间曾任礼部郎中、中书舍人权知贡举、户部侍郎,著述不详。崔造(737-787),《旧唐书》有传,史称其“少涉学,永泰中,与韩会、卢东美、张正则为友,皆侨居上元,好谈经济之略,尝以王佐自许,时人号为‘四夔’”[7]3625。大历之时,韩愈尚为孩提,三人之中,除赵赞生卒年不可考外,萧存长韩愈29岁,崔造长韩愈31岁,皆为其长辈。再联系“四夔”之称,疑《尚书比部郎中萧府君墓志铭》中“昌黎韩愈”当为“昌黎韩会”之讹。
第二,有李观与韩愈并称之说。李观(766-794),《新唐书》载:“观属文,不旁沿前人,时谓与韩愈相上下。及观少夭,而愈后文益工,议者以观文未极,愈老不休,故卒擅名。陆希声以为‘观尚辞,故辞胜理;愈尚质,故理胜辞。虽愈穷老,终不能加观之辞;观后愈死,亦不能逮愈之质’云。”[6]5779欧、宋编《新唐书》用陆希声《唐太子校书李观文集序》,略有省文,其原序云:“贞元中,天子以文化天下,天下翕然兴于文。文之尤高者李元宾观、韩退之愈。始元宾举进士,其文称居退之之右,及元宾死,退之之文日益高。今之言文章,元宾反出退之之下。论者以元宾早世,其文未极。退之穷老不休,故能卒擅其名……”[5]8550李观、韩愈同李绛、崔群复有“四君子”之称,《唐摭言》卷七“知己”条载:“贞元中,李元宾、韩愈、李绛、崔群同年进士。先是四君子定交久矣,其游梁补阙之门;居三岁,肃未之面,而四贤造肃多矣,靡不偕行。肃异之,一日延接,观等俱以文学为肃所称,复奖以交游之道。”[8]1641李观与韩愈年岁相仿,兴趣相投,文章工力悉敌,又同游于梁肃之门,共于贞元八年(792)“龙虎榜”登第。贞元十年(794)病卒。韩愈曾作《李元宾墓铭》,称其“文高乎当世,而行出乎古人”[9]1515。李观英年早逝,其古文成就自然无法与韩愈相提并论,二人齐名说亦影响有限。
第三,有欧阳詹与韩愈齐名之说。欧阳詹(约759-799年),泉州晋江人,与韩愈、李观等同榜进士,《新唐书》有传。史称“其文章切深,回复明辩”[6]5787。欧阳詹年长韩愈数岁,与之交好,并对其提携之恩。“詹先为国子监四门助教,率其徒伏阙下,举愈博士。”[6]5787欧阳詹死后,韩愈作有《欧阳生哀辞并序》,称“其文章切深,喜往复,善自道”[9]1278。唐人李贻孙为欧阳詹文集作序,称其时“常与君同道而相上下者,有韩侍郎愈,李校书观”[5]5514,以三者相提并论,其说始于大中六年(852)。明确提出欧阳詹与韩愈齐名说者,当推晚唐黄滔,其《莆山灵岩寺碑铭》有云:“欧阳垂四门之号,与韩文公齐名,得非山水之灵秀乎?”[5]8699其论言之凿凿,然亦流传未广。
第四,有张籍与韩愈并称之说。该说始自张籍《祭退之》诗,其云:“公文为时帅,我亦有微声。而后之学者,或号为‘韩张’。”[10]913张籍(约767-830),字文昌,与韩愈年岁相仿,然及第较晚,加之他多次被韩愈提携,故诗文风格也受到后者影响。张籍与李翱都曾随韩愈学文,“近李翱从仆学文,颇有所得。然其人家贫多事,未能卒其业。有张籍者,年长于翱,而亦学于仆。其文与翱相上下”[9]817。然张籍文名不及其诗,史称其“以诗名当代,公卿裴度、令狐楚,才名如白居易、元稹,皆与之游,而韩愈尤重之”[7]4204。张籍此处明言己文亦与韩愈齐名,一则缺少旁证,二则后世学者亦不以为然。钱钟书《谈艺录·张文昌诗》评此诗云:“张文昌诗云:‘公文为时帅,我亦微有声;而后之学者,或号为韩张。’是退之与文昌亦齐名矣。然张之才力,去韩远甚;东坡《韩庙碑》曰:‘汗流籍湜走且僵。’千古不易之论。”[10]1200韩张齐名说大约始自韩愈逝年(824),附和者亦少。
第五,有孟郊与韩愈并称之说。此说始自韩愈,其《醉留东野》诗云:“昔年因读李白杜甫诗,长恨二人不相从。吾与东野生并世,如何复蹑二子踪?东野不得官,白首夸龙钟。韩子稍奸黠,自惭青蒿倚长松。低头拜东野,愿得终始如駏蛩。东野不回头,有如寸筳撞巨钟。吾愿身为云,东野变为龙。四方上下逐东野,虽有离别无由逢。”[11]404孟郊虽长韩愈十余岁,然而他的文名远不如后者,反而要受到晚辈韩愈的推奖。韩愈《送孟东野序》称“唐之有天下,陈子昂、苏源明、元结、李白、杜甫、李观,皆以其所能鸣。其存而在下者孟郊。东野始以其诗鸣。其高出魏晋,不懈而及于古,其他浸淫乎汉氏矣”[9]983。故唐人赵璘《因话录》卷三载:“韩文公与孟东野友善,韩公文至高,孟长于五言,时号‘孟诗韩笔’。”[12]846韩孟并称之说在二人在世时流传已广,后世沿袭不辍,然多指孟郊诗名足与韩愈相抗。
第六,李翱与韩愈并称之说。李翱(约772-837),此说始自刘禹锡所作《唐故中书侍郎平章事韦公集纪》,其文曰:“初,蕃既纂修父书,咨于先执李习之,请文为领袖,许而未就。一旦,习之悄然谓蕃曰:‘翱昔与韩吏部退之为文章盟主,同时伦辈,惟柳仪曹宗元、刘宾客梦得耳。韩、柳之逝久矣,今翱又被病,虑不能自述,有孤前言,赍恨无已,将子荐诚于刘君乎!’”[13]228开成二年(837),韦蕃为其亡父韦执宜求文集序,首诣李翱,因其被病,遂举荐刘禹锡,梦得挥毫而就,方有此文传世。以文中三人所持论而言,则韩愈在世之时,士人皆认为唯有李翱之文可与韩愈并驾齐驱,而刘、柳者,皆韩、李之亚也,自不可相提并论。李翱《答韩侍郎书》篇首曾引韩愈评语:“还视云,于贤者汲汲,惟公与不材耳。”[5]6408可见韩愈生前亦尝主动与李翱并论,可证此说所来非虚。韩、李齐名说不仅在中晚唐影响很大,后世也不乏附和者,如刘昫《旧唐书》赞曰:“天地经纶,无出斯文。愈、翱挥翰,语切典坟。”[7]4216又云:“韩、李二文公,于陵迟之末,遑遑仁义;有志于持世范,欲以人文化成。”[7]4216欧阳修《苏氏文集序》云:“韩、李之徒出,然后元和之文始复于古。”[14]614其《读李翱文》亦称:“凡昔翱一时人,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韩愈。”[15]1050皆以韩愈与李翱并举,而不言柳宗元。受欧阳修影响,元人赵汸有“韩、李并称,可无愧矣”[16]524之语;清人储欣有“韩、李并称,所从来久”[17]908之论。
第七,刘轲与韩愈齐名之说。刘轲(约782-约840),新旧《唐书》无传,早年游心释老,后于元和十三年(818)登进士第。《唐摭言》载其事迹稍详,称“轲慕孟轲为文,故以名焉。少为僧,止于豫章高安之南果园。复求黄老之术,隐于庐山。既而进士登第,文章与韩、柳齐名”[8]1673。范摅《云溪友议》载刘轲与韩愈交往事,称“吏部侍郞韩愈素知焉,曰:‘待余余暇,当为一文赞焉。’愈左迁。其文不就也”[18]61。然小说家流,未可轻信。清人屈大均《广东新语》称“昌黎过韶时,尝欲为文以传之(刘轲)不果”。其事不知何据。屈氏又言“君故能文,当时与韩、柳齐名。学士大夫之称韩、柳者。未尝不言及君”[19]324,则当本于《唐摭言》。此说始于五代,亦影响有限,多出自小说家流。
第八,柳宗元与韩愈并称之说。韩柳虽生于同时,且相互仰慕,然其“交往最密切的时间当在贞元十九年秋冬间同任监察御史的短短两个月左右的同僚时期”[4]69-76。元和以后,韩柳分列南北,共以古文为时所称,二人书信不绝,精神上仍联系密切。韩氏诗云“吾友柳子厚,其人艺且贤”[11]590;柳氏文曰“儒者韩退之与余善”[20]673。正如宋人罗大经《鹤林玉露》所论,“韩有《平淮碑》,柳有《平淮雅》;韩有《进学解》,柳有《起废答》;韩有《送穷文》,柳有《与韦中立论文》;韩有《张中丞传叙》,柳有《段太尉逸事》”[21]93。韩柳皆有以文明道之志,书信交流频繁,故互有影响之处。如前所论,开成二年(837),刘禹锡虽最早使用“韩柳”一词,然其所谓“韩、柳之逝久矣”[13]228句,尚无韩、柳并称之意。开成五年(840),杜牧作《冬至日寄小姪阿宜诗》,其中有“李、杜泛浩浩,韩、柳摩苍苍。近者四君子,与古争强梁”[1]214句,当是明确提出“韩柳”并称的最早说法。咸通七年(866),李彀作《唐故乡贡进士陇西李府君墓志铭》,其云:“吾季德用讳毂等伯仲业班、马、韩、柳文,时时缘事剪刻,四六五七之言,皆不为人下”[22]629,则是明确主张韩、柳文章并称的最早记载。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有云:“唐代韩愈、柳宗元,洎李翱、李观、皇甫湜数君子之文,陵轹荀、孟,穅秕顔、谢。其所宗仰者,唯梁浩补阙而已,乃诸人之龟鉴”[23]139,则改变刘禹锡的古文名家排列次序,将柳宗元居于李翱之上。五代至于北宋初,韩柳并称说则流传已久,为士人普遍接受。《旧五代史》称李愚“为文尚气格,有韩、柳体”[24]890。柳开以“五代文格浅弱,慕韩愈、柳宗元为文,因名肩愈,字绍先”[25]13024。欧阳修《集古录跋尾》评《唐南岳弥陁和尚碑》云:“自唐以来,言文章者惟韩、柳。”[15]2278正说明韩柳文章并称之说的受众范围非常广泛,远远超过其他诸说。
以上八种说法,萧存等人与韩愈齐名说当为讹误,欧阳詹、李观、张籍与韩愈齐名说流传未远,影响有限。孟郊与韩愈齐名为举世公认,不过时人所谓“孟诗韩笔”,其着眼之处并不在孟郊之文,而在于诗。刘轲与韩愈齐名说始自五代,事迹多见于小说家流,未可轻信。最后两种说法皆见于开成年间,传播广泛,影响皆深远。其中李翱与韩愈文章齐名说在中唐时影响最大,刘禹锡等士人大都认为柳文应居于李翱之下。晚唐五代之时,柳文声誉日上,韩柳文章齐名说逐渐取代了韩李文章齐名说,成为社会舆论的主流。北宋之初,欧阳修重新提倡韩李齐名说,并取得部分士人的支持,以至于后世历代不时仍有附和之声,然而并未根本改变韩柳齐名说的地位与影响。此外,宋人尚有“韩欧”“韩苏”并称说,由于这些说法与本文关涉不大,兹不赘述。
二、韩柳齐名的矛盾之处
中唐之时,与韩愈齐名者不啻数家,其中尤以与李翱齐名之说在当世认可度最高,然而从后世的接受与传播角度而言,“韩柳”说不仅流传范围最广,而且影响力远远超过“韩李”诸说。然考“韩柳”二家故实,则不难发现此说内在有许多矛盾之处,远不及韩愈与李翱共通之处多,不得不说是文化传播史上的一桩怪事。
首先是韩柳文风不同。在唐人评价话语体系中的并称者,几乎都有风格相近或类似的特点,如“王孟”恬淡流丽、“高岑”雄浑悲壮、“元白”坦易通俗、“韩孟”奇崛险怪等。韩愈与柳宗元虽皆以古文擅名,然后世学者论二者文风,则以相异之处为多。正如明人康海所云:“论文至言古人言以见志,故其性情、其状貌,求而可得焉。此孔子所以于师襄得文王也。故昔人陶则陶,杜则杜,韩则韩,柳则柳,咸自成家。今或不能自立,傍人门户,效嚬而学步。”[26]1664-1665在康氏看来,韩与柳别是一家,其差别大约如陶渊明与杜甫相较之类。
大致而言,历来学者评价韩柳文风之异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韩柳古文有源流正变之别。持此论者主要从道统与文统的角度而言,认为韩文议论雅正,源出自六经,偏重于传道说理;柳文词语峭拔,文采斐然,源出自楚辞及史家,然于传道则稍逊之。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一四曾分析二人文风差异的成因,其云:“韩退之之文自经中来,柳子厚之文自史中来。”[27]763沈作喆《寓简》分别概括了韩柳古文风格特点,指出“柳子厚作楚词卓诡谲怪,韩退之不能及。退之古文深闳雄毅,子厚又不及”。在他看来,韩文雄毅持正,而柳文词语谲怪,风格差别很大。胡应麟《少室山房集》观点与前者大致相同,“论诗文雅正,则少陵、昌黎;若倚马千言,雄辞追古,则杜、韩恐不及太白、子厚也”[28]763。分别指出韩文说理有雅正之风,而柳文则胜在文词拔萃。方鹏《责备余谈》卷下则认为韩柳文有主理与主气之别:“韩之文主乎理,而气未尝不充。柳之文主乎气,而于理则或激之太高,拘之太迫,奇古峭丽则有之,而舂容隽永之味则不足。”[29]3309实则仍是强调韩愈道胜于文,柳宗元文胜于道。二是行文章法之别。从这一角度探讨韩柳之异的学者,大都认为韩文规模浑厚,柳文章法谨严。宋人吕本中《童蒙诗训》曾评价说:“韩退之文,浑大广远难窥测;柳子厚文,分明见规摹次第。”[30]1036由于二人行文风格与章法结构相差很大,他建议“初学者当先学柳文,后熟韩文,则工夫自易”[30]1036。朱熹对韩柳文章法之异也有论及,《朱子语类》云:“韩退之议论正,规模阔大,然不如柳宗元较精密。”[31]3302宋人林光朝《读韩柳苏黄集》以建筑之法譬喻二者作文之异,其意略与二子同,“韩柳之别,则犹作室。子厚则先量自家四至所到,不敢略侵别人田地。退之则惟意之所指,横斜曲直,只要自家屋子饱满,初不问田地四至,或在我与别人也”[29]3619。
相较于柳宗元,李翱文风显然与韩愈更加接近。宋末元初,马端临《文献通考》评价李翱文亦有浑厚之风,“翱性峭鲠,论议无所屈,仕不得显官,怫郁无所发。从韩愈为文,词致浑厚,见推当时”[32]6357。在介绍李翱文集时,他又转引苏舜钦语:“唐之文章称韩、柳,翱文虽词不逮韩,而理过于柳。”[32]6357苏氏之语,即以韩、李文皆有承继道统的特点,虽文辞或不及柳,然而较之柳文,却更擅长议论说理。
其次,思想不同。韩柳皆力勤于古文,但是二人思想观点却常有抵牾之处,正所谓“详观子厚之言,则韩、柳之见,岂不天渊也哉!”[29]3621大略而言,韩柳思想不同之处有三:一是所明之“道”不同,二是师道主张不同,三是政治观念不同。
一者,韩、柳都有文以明道之理论主张。然而二人对所弘扬的道,却有不同的阐释。韩愈所谓的“道”,仅仅指的是传统儒家之道。为了维护“道”的纯粹性,他明确将佛、老排斥于外,其《原道》云:“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9]4而柳宗元不仅尊崇孔孟之道,同时对佛、老思想也有所取舍,并非完全摒弃。其《道州文宣王庙碑》曾说:“夫子之道阂肆尊显,二帝三王其无以侔大也”[20]121,说明他也是儒家学说的忠实信徒。而《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同时又有“予观老子,亦孔氏之异流也”[5]5849语,《送僧浩初序》亦有“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诚乐之,其于性情奭然,不与孔子异道”[29]1680句,则表明他对佛、老之道亦有好感,故欧阳修等人有韩、柳“其为道不同”[15]2276之叹。
二者,韩愈以明道之故,忿于师道久为流俗所轻,慨然而作《师说》,倡言“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9]139。并身体力行,广泛招揽学徒,当时名士如张籍、李翱、皇甫湜、李汉等人,皆从之游,史称“愈性明锐,不诡随。与人交,终始不少变。成就后进士,往往知名。经愈指授,皆称‘韩门弟子’”[6]5265。“韩门弟子”群体的形成与文学活动不仅促进了中唐古文运动的发展,也成就了韩愈的文宗地位。柳宗元似乎不认同韩愈的做法,其《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云:“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29]2177《答严厚舆秀才论为师道书》云:“仆才能勇敢不如韩退之,故又不为人师。”[29]2197皆明言其不肯为人师的缘由,与韩愈之论形成截然对比。学者黄唐由此评曰:“由退之之说,则学者不敢恃己之长,有所资于人。由子厚之说,则学者轻人之能,而终于自是。”[29]1340-1341因韩柳师道之说相差巨疑,故黄氏又云:“韩柳优劣,由此而判。”[29]1340-1341
三者,韩柳政治观点常有不同。如柳宗元曾积极参与永贞革新,明确反对宦官专权,为国家改革之事积极筹划。而韩愈却自始至终置身事外,不仅与当时宦官首领俱文珍有来往,而且还作有《送汴州监军俱文珍序并诗》。永贞革新失败后,更作《永贞行》,讽刺此事为“小人乘时偷国柄”[11]168。再如韩愈被贬潮州后迅速悔过,并作《潮州刺史谢上表》鼓励宪宗封禅,并愿亲自撰文“纪泰山之封,镂白玉之牒”[9]2922。柳宗元则撰有《贞符》,此文反对董仲舒天人感应之说,指出所谓“封禅”等事,“皆《尚书》所无有。莽、述承效,卒奋骜逆”[29]78。并告诫皇帝“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6]5138。又如韩愈曾主持修撰《顺宗实录》,有权贵担心史书所载对其不利,于是往往横加干涉。韩愈后作《答刘秀才论史书》述其当时恐惧且无奈之状,并总结说:“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哉!”[9]3103柳宗元早年与韩愈皆有为史之志,读此文后愤而作《与韩愈论史官书》,直言自己“私心甚不喜”,并责之曰:“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无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祸非所恐也。”[20]809韩柳思想相差之巨异,大略如是,故宋人王十鹏“切疑二人阳若更誉而阴相矛盾者”[29]1341;元人刘谧亦叹曰:“详观子厚之言,则韩、柳之见,岂不天渊也哉!”[29]3621而韩愈与李翱曾共著《论语笔解》,二人之道统说与性情论一脉相承,相互羽翼,在思想史上亦颇有影响。
再次,文坛地位不同。韩愈在世之日,便自诩文章盖世,声言“于当时之文,亦未有过人者”[9]2922。即便与古人相比,“亦未肯多让”。时人更以文宗推许,如张籍《上韩昌黎书》称赞他说:“自扬子云作《法言》,至今近千载,莫有言圣人之道者,言之者惟执事焉耳。”[10]994赵德《昌黎文录序》赞曰:“昌黎公,圣人之徒欤,其文高出,与古之遗文,不相上下。”[5]6276皇甫湜《韩文公墓志铭》称其文“姬氏已来,一人而已矣”[5]7040。皮日休《请韩文公配飨太学书》亦有“吾唐以来,一人而已”[23]31之语。中晚唐之时,柳宗元虽亦有文名,然而“由于其罪臣的身份及久居贬地,致使其长期远离人们的关注,故而他的影响力远不及韩愈”[33]4。其时以“韩柳”并称者,实则有借韩愈文宗之名,抬高柳宗元地位之意。
北宋之时,柳不如韩几乎成为学者之共识,学界之通论。北宋姚铉编《唐文粹》,其序文云:“惟韩吏部超卓群流,独高遂古,以二帝三王为根本,以六经四教为宗师,凭陵轥轹,首倡古文,遏横流于昏垫,辟正道于夷坦,于是柳子厚、李元宾、李翱、皇甫湜又从而和之。”[29]3610姚氏之语很有代表性,在他看来,韩愈在唐代古文家中居于独尊地位,其他诸人不过是其陪衬而已。大约同时,宋祁《宋景文笔记》卷上亦云:“柳州为文,或取前人陈语用之,不及韩吏部卓然不朽,不丐于古,而语一出诸己。”[34]72稍后,王安石《上人书》亦评曰:“自孔子之死久,韩子作,望圣人于百千年中,卓然也,独子厚名与韩并。子厚非韩比也。”[30]3610至神宗元丰七年(1084),诏追封韩愈为昌黎伯,令其与孟子等先贤“以世次先后,从祀于左丘明二十一贤之间”[25]2549。至此,韩愈的文宗与道统地位得到北宋官方正式承认,而柳宗元等其他古文家则未有所闻。
此后迄于晚清,则几乎可以断定:韩愈无论是在道统,还是在文统层面,都长期保持着对柳宗元的绝对压制地位,虽然偶尔有晏殊等人为柳宗元张目,然而响应者始终寥寥无几。至于明人茅坤编《唐宋八大家文钞》,唐宋八大古文家座次排位始定,故其观点在当时学界颇具有权威性与代表性。茅氏《论例》云:“予览子厚之文……然不如昌黎多矣。”[29]3623有清一代,桐城古文派长期统治文坛,林纾《韩柳文研究法》总结说:“桐城人号称能文者,皆扬韩抑柳,望溪訾之最甚,惜抱则微词。”[30]3631此外,诸如李涂、魏了翁、王若虚、叶子奇、方鹏等历代学者,皆有类似之语。可见,自中晚唐以至于清末,相较于柳宗元等古文家而言,韩愈一直都近乎居于独尊地位,“柳不如韩”始终是思想界与学术界的主流观点。
至于新文化运动以来,西学东渐日盛,“柳胜于韩”遂呼声日高。近代诸如章士钊、黄云眉、王芸生等学者皆有力作传世,然而因此时古文赖以存在的文化土壤早已不复存在,故本文于此节不复讨论。
以上所论可知,韩愈与柳宗元无论是在古文风格上,还是在思想主张上,抑或是在地位上,皆相差巨异,矛盾重重,甚至可谓泾渭分明。“韩柳齐名说”产生于中唐的文化环境中,实际而言,此说与“韩李齐名”等观点既无本质区别,也无特殊之处。之所以“韩柳齐名说”能够压倒诸说,并在思想界与学术界产生长期而深远的影响,主要是因为口耳相传之故,约定俗成所致。大略如欧阳修所论:“自唐以来,言文章者惟韩、柳,柳岂韩之徒哉?真韩门之罪人也。盖世俗不知其所学之非,第以当时辈流言之尔。”[15]2278
三、“韩柳齐名说”的理论建构
如上所述,中唐之时,韩愈以其杰出的古文创作贡献,在文坛居于独尊地位,故而被时人共推为一代文宗。当时论文者,常以韩愈为标准而品评其他人物,遂有“韩柳齐名”“韩李齐名”等八说。作为其中的一个普通观点,“韩柳齐名说”的社会认可度起初并不及“韩李齐名说”。然而,在后世评价话语体系中,“韩柳齐名说”逐渐后来者居上,影响力超过其他诸说,最终成为压倒性的主流说法。概括而言,这一过程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品评混乱期”“舆论统一期”“理论建构期”。“品评混乱期”持续时间很短,大约于韩愈在世前后。在此阶段,韩愈文名籍甚,品评者莫不以与之并称为荣,代表性的说法主要有“韩李”“韩柳”“韩孟”等数种之多。这些观点既有自我攀附者,如“韩张”说等,然乏旁证;亦有韩愈主动与之并称者,如“韩孟”说、“韩李”说等,然又乏客观。凡此种种,各具缘由,百家争鸣,说法混乱不堪。“舆论统一期”大约在韩、柳殁后而至于宋初。这一阶段,“韩柳齐名说”在众多观点中逐渐脱颖而出,并且在社会舆论层面获得了相对统一的认识。宋初至于清末,是“韩柳齐名说”的理论构建时期。在此漫长的接受与评价时期,历代学者主要从师风、文风、诗风三个层面丰富并完善了“韩柳齐名说”的理论建构。
首先是师风齐名层面的理论建构。韩、柳在世前后,二者虽然所宣扬的师道观不同,然而他们在举荐和奖掖人才方面的做法并无二致,这一点也正是他们被后人连类并称的缘由之一。
韩愈好为人师,曾作《马说》而以伯乐自居,尤爱举荐人才。孟郊、张籍等人,或长于韩愈,或与之年岁相仿,都受到韩愈的推荐,《旧唐书》称“愈性弘通,与人交,荣悴不易。少时与洛阳人孟郊、东郡人张籍友善。二人名位未振,愈不避寒暑,称荐于公卿间,而籍终成科第,荣于禄仕”[7]4203。至于接引后辈、弘扬道义,则更加不遗余力,“韩门弟子”群体即其证也。史称韩愈“颇能诱厉后进,馆之者十六七,虽晨炊不给,怡然不介意……后学之士,取为师法”[7]4203。时有俊才李贺,因避父讳而不得举进士,韩愈作《辩讳》为之张目;又有董生邵南数举而不中,愤而欲仕于藩镇,韩愈作《送董邵南游河北序》殷勤挽留。其惜才也如此,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柳宗元以罪臣的身份远谪蛮荒,出于避祸的心理,他并没有提出类似《师说》《马说》式的师道宣言,甚至还作《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明言自己不肯为师之原因。不过,从他的人生轨迹来看,其亦多有践行师道之举。据柳宗元回忆,永贞革新之前,其“往在京都,后学之士到仆门,日或数十人”[29]2200,又说:“吾在京都时,好以文宠后辈,后辈由吾文知名者,亦为不少焉。”[29]2209韩愈亦称柳宗元其时“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诸公要人争欲令出我门下,交口荐誉之”[9]2407。当时与柳宗元结交者,既有普通士子,如《答贡士沈起书》中的沈起等,亦多“韩门子弟”,诸如李翱。据孙昌武《唐代古文运动通论》考证,其于“贞元十四年,进士及第,授校书郎,并与柳宗元交游”[35]244;皇甫湜,“年轻时即与韩、柳结交”[35]250,宗元殁后,作有《祭柳子厚文》。
贬谪后,柳宗元与南方士子来往密切,虽然他并不以师者自居,然却有指授之实。其《答严厚舆秀才论为师道书》云:“仆之所拒,拒为师弟子名,而不敢当其礼者也。若言道、讲古、穷文辞,有来问我者,吾岂尝瞋目闭口耶?”[29]244又云:“幸而亟来,终日与吾子言,不敢倦,不敢爱,不敢肆。苟去其名,全其实,以其余易其不足,亦可交以为师矣。”[20]879其《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亦毫无保留传授为文之心得体会,虚怀若谷,颇有长者之风,书云:“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无取乎?吾子幸观焉择焉,有余以告焉。苟亟来以广是道,子不有得焉,则我得矣,又何以师云尔哉?取其实而去其名。”[20]873-874故柳宗元与后辈探讨为文之道时,常以友人的身份,如其《与友人论为文书》等;落款之时,也多用“宗元白”之类的谦辞,完全没有为师者的架子。即便在其逝世前后数月,也不厌其烦地向杜温夫等后辈传道授业解惑。韩愈《柳子厚墓志》称“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者,悉有法度可观”[9]2405,即是当时情形的真实写照。《新唐书·柳宗元传》亦称“南方为进士者,走数千里从宗元游,经指授者,为文辞皆有法”[6]5142,也是对其功绩的客观描述。
由于韩柳皆多次提拔和奖掖人才,所以中晚唐士人阶层也将他们赏识与拔擢人才作为塑造形象方面的共同特点之一。唐人赵璘《因话录》载:“元和中,后进师匠韩公,文体大变。又柳柳州宗元、李尚书翱、皇甫郎中湜、冯詹士定、祭酒杨公、余座主李公,皆以高文为诸生所宗,而韩、柳、皇甫、李公皆以引接后学为务。”[8]1641韩、柳所共同接引者,如来鹄,《唐摭言》卷一〇载:“来鹄,豫章人也。师韩、柳为文。大中末、咸通中,声价益籍甚。广明庚子之乱,鹄避地游荆湘,南返。中和,客死于维扬。”[36]1066再如柳仲郢,《旧唐书》称其“撰尚书二十四司箴,韩愈、柳宗元深赏之”[35]4307。
韩、柳前后所称扬文士众多,史所明载。然尤可注意者,是二人称荐牛僧孺之事。《唐摭言·公荐》载:“韩文公、皇甫湜,贞元中名价籍甚,亦一代之龙门也。奇章公始来自江黄间,置书囊于国东门,携所业,先诣二公卜进退……俟其他适,二公访之,因大署其门曰:‘韩愈、皇甫湜同访几官先辈,不遇。’翌日,自遗阙而下,观者如堵,咸投刺先谒之。由是僧孺之名,大振天下。”[8]1626奇章郡公即牛僧孺。韩愈荐拔牛僧孺之事流传较广,然而此时得势的柳宗元显然对其科举仕途帮助更大。杜牧《唐故太子少师奇章郡开国公赠太尉牛公墓志铭》载:“丞相韦公执谊,以聪明气势,急于褒拔,如柳宗元、刘禹锡辈,以文学秀士,皆在门下。韦公亟命柳、刘于樊乡访公,曰愿一得相见。”[1]595遂于贞元二十一年(805)“登进士上第”[1]595。柳宗元结识牛僧孺之后,对其文章亦复推崇,其《非国语上·城成周》有云:“吾友化光《铭城周》,其后牛思黯作《讼忠》,苌弘之忠悉矣。学者求焉。”[29]3171牛思黯即牛僧孺。柳氏此文大约作于元和三年至四年,牛文所作年代应略早于此。可见柳宗元与牛僧孺的交往并未因政治风波而完全中断,至少说明二者友情深厚,结交甚笃。
再可注意者,亦柳宗元与吴武陵之师生情谊。吴武陵,《新唐书》有传,生卒年不详,元和二年登第,曾与柳宗元同贬永州。柳氏名篇《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中所谓“同游者吴武陵”[29]1912,即此人也。柳宗元《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曾载吴武陵常师事自己之事,其云“(吴武陵)每以师道命仆,仆滋不敢。仆每为一书,足下必大光耀以明之”[29]2070。大约在元和十年前后,吴武陵遇赦北还,并多次向执政者为柳宗元鸣冤、叫屈,言辞甚是感人。史载:“初,柳宗元谪永州,而武陵亦坐事流永州,宗元贤其人。及为柳州刺史,武陵北还,大为裴度器遇。每言宗元无子,说度曰:‘西原蛮未平,柳州与贼犬牙,宜用武人以代宗元,使得优游江湖。’又遗工部侍郞孟简书曰:‘古称一世三十年,子厚之斥十二年,殆半世矣。霆砰电射,天怒也,不能终朝。圣人在上,安有毕世而怒人臣邪?且程、刘、二韩皆已拔拭,或处大州剧职,独子厚与猿鸟为伍,诚恐雾露所婴,则柳氏无后矣。’度未及用,而宗元死。”[6]5792
作为“韩柳齐名说”较早提出者,杜牧曾先后受大恩于吴武陵与牛僧孺,他虽未直接与柳宗元交往,但是难免会受吴、牛二人影响。“韩柳摩苍苍”句将“韩柳”并举,既有赞颂韩柳文章齐名之意,同时更有称颂韩、柳皆能行师道荐拔人才之举。联系杜牧生平,则此论不乏有借韩愈文宗地位以抬高柳宗元之意。
韩柳举荐人才,不仅载著史书、笔记,同时也行诸于诗篇,流布于人口。晚唐郑谷有《赠杨夔二首》,其二云:“时无韩柳道难穷,也觉天公不至公。看取年年金榜上,几人才气似扬雄。”[37]7763此诗感慨杨夔空负才学却无人赏识,以至于多年应举却不能及第。作者假设以弘道为己任的韩、柳如果在世,那么他们肯定愿意提携杨夔这样的人才,不使其才学埋没。可见,中晚唐之时,韩、柳并称的说法,主要指的是他们皆能荐举人才、弘扬师道的行为。
其次是文章齐名层面的理论建设。如上节所述,中唐之世,韩、柳在文风、思想、文坛地位上皆不相同,二者文章并称的说法矛盾处较多,且并未广泛流行,故早期韩、柳齐名主要体现在二人皆能弘道且兼有师者之风方面。随着“韩、柳”并称说影响力的扩大,此说也逐渐脱离原先的狭义语境,概念范畴不断衍化发散。大约在晚唐五代之时,韩柳文章齐名说最终为士人阶层广泛接受。之后,此说之内涵也不断被后人丰富、完善。该层面的理论建设主要以两种方式展开:
一是罗列柳文可与韩文齐名之缘由。“韩柳齐名说”虽确定于晚唐五代,然而系统的理论建构多出现在宋代之后。韩愈的文宗地位在中唐以后不断提高,至于其被官方认可从祀孟子等先贤之后,其地位遂不可动摇,故学者在论证该命题时,多详细罗列柳文可与韩文并列的具体原因。
如北宋张舜民认为韩柳在弘扬儒家之道上各有其功,二人齐名并称实乃必然,柳文在“兼诵博记,驰骛奔放”方面甚至超过韩文。其云:“扶导圣教,剗除异端,以经常为己任,死而无悔,韩愈一人而已,非独以属辞比事为工也。如其祖述典坟,宪章骚雅,上轹三古,下笼百氏,极万变而不华,会众流而有居,逌然沛然,横行阔视于缀述之场,子厚其人也。彼韩子者,特以醇正高雅,凛然无杂,乃得与之齐名尔必也。兼诵博记,驰骛奔放,则非柳之敌。”[29]3610
南宋李朴《谒顾子敦侍郎书》将韩、柳之文作为唐文的最高成就,其云:“唐兴,三光五岳之气不分,文风复起。韩愈得其温淳深润,以为贯道之器。柳子厚得其豪健雄肆,飘逸果决者,仅足窥马迁之藩键,而类发于躁诞。”[29]3611
南宋王十朋《策问》论曰:“韩愈、柳宗元俱以文鸣于唐世,目曰韩柳,二人更相推逊,虽议者亦莫得而雌雄之。”[29]1341
宋末黄仲元认为韩、柳文虽有正、奇之别,然各有优长,其《郑云我存藳序》云:“唐人语言妙天下者,莫若韩柳氏。韩以李汉一序传,柳以刘宾客一序传。二序之所以传者,序乎文也。文者天地之正气,亦天地之奇气。天地间惟正人能养天地之正气,故其文正,韩氏似之。惟奇人能发天地之奇气,故其文奇,柳氏似之。柳之醇正固不及韩,柳之奇崛,亦韩所不及。”[16]307
明王世贞《艺苑卮言》认为韩柳文乃唐文代表,皆有“实”之特点,其云:“韩、柳氏,振唐者也,其文实。欧、苏氏,振宋者也,其文虚。”[38]985明末清初孙琮《山晓阁选唐大家柳柳州全集认为柳文成就不凡,足与韩愈并列,其文曰:“韩柳并驱,当时已有同称……夫其(柳宗元)驱驾气势,掀雷扶电,撑抉于天地之垠,与昌黎倡和千古。”[29]3628
清人黄世三《读柳子厚文集》条分缕析,所论最为精微,他系统地修正了韩、柳文思想差异的问题,认为韩、柳文异中亦有同,其云:“唐之文,韩、柳二子为冠,定论也。而文有同有异,异者未尝不同。”[29]3629
韩文独尊,而柳文亦足以同韩文相抗衡是“韩柳文章齐名说”的核心论点,其说之内涵随年代累积而日益完善。早期与其并列的“韩李齐名说”虽不时仍有学者提倡,但其理论建设却几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故影响力始终有限,而“韩柳文章齐名说”最终成为学界的主流认识,影响至今。
二是抬高柳宗元的地位。韩愈是唐宋古文创作的旗手与标杆人物,后世论文者多以其为参照对象。随着“韩柳齐名说”日益深入人心,学者对柳宗元文章也投入了更多的关注。他们在充分肯定柳宗元文章价值的基础上,一反“韩胜于柳”的主流观点,提出“柳胜于韩”的观点,试图通过这样的方式抬高柳宗元的地位。如北宋初年,晏殊便认为仅以文章其成就而言,柳宗元远胜韩愈等唐代诸人,其云:“韩退之扶导圣教,划除异端,自其所长;然其祖述坟典,宪章骚雅,上传三古,下笼百氏,横行阔步于缀述之场者,子厚一人而已矣。”[29]3611
第一,由正常生长状态下温度突然大幅下降到0℃以上的低温,不但会降低葡萄的生长速度,其细胞内原生质也会变成像果冻一样的凝胶状态,此时给我们的感觉是芽、花蕾和叶片等器官变得僵硬了,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冷害”。如果气温很快回升到正常水平,葡萄的芽和叶片等也会恢复到正常状态,但对花器的发育可能会造成轻微的不可逆转的伤害,进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开花结实率。
宋人陈长方认为柳宗元才华在韩愈之上,早年文章或不逮韩,然迁谪之后,遂远胜于韩。其云:“柳子厚之才,韩退之有所不逮,但韩公下笔便以三代为法,其文章如人少年、暮年,毛发不同,而风仪皆此人也。子厚在中朝时尚有六朝规矩,读之令人鄙厌,至永州以后,始以三代为师。至淮西一事,退之作碑,子厚作雅,逞其余力,便觉退之不逮子厚,直一日千里也。”[29]3612
宋人李如篪尤偏爱柳文,认为其文几乎完美无缺,“无不如意”,可直追三代,而韩愈文章则间有瑕疵,其《东园丛说》卷下云:“退之之文,其间亦有小疵。至子厚,则惟所投之,无不如意。如退之《元和圣德诗序》,刘辟与其子临刑就戮之状,读之使人毛骨凛然,风雅中安有此体?至子厚《平淮雅》,读之如清风袭人,穆然可爱,与吉甫辈所作无异矣。”[39]278
宋人严羽《沧浪诗话》认为柳宗元文章独得骚人之旨,而韩愈等人则不及,其云:“唐人惟柳子厚深得骚学,退之、李观皆不及。”[40]689
以上提倡“柳胜于韩”者,大多着眼于文章的辞采与艺术技巧,认为柳宗元较韩愈亦有优胜之处。而持“韩胜于柳”者,则往往不拘文章或道统层面,故立论者众多,论述也更加全面而充分。“柳胜于韩”虽非学界的主流观点,但是毕竟也取得了一定影响。从实际效果而言,此说确实大大提高了柳文的地位,使“韩柳文章齐名说”的认可度超过“韩、李”等其他观点。
此外,宋代文宗欧阳修虽主张以“韩、李”代替“韩、柳”,然而其编撰《新唐书》之时仍然大量采用韩、柳之文,从而在事实上沿袭并巩固了“韩、柳文章齐名说”,也为后世学者丰富完善此说提供了事实依据与支撑。清人赵翼《廿二史劄记》卷十八《新旧唐书》“新书好用韩柳文”条载:“欧、宋二公,皆尚韩、柳古文,故景文于唐书列传,凡韩、柳文可入史者,必采摭不遗。张巡传则用韩愈文,段秀实传则用柳宗元书逸事状,吴元济传则用韩愈平淮西碑文,张籍传又载愈答籍一书,孔戣传又载愈请勿听致仕一疏,而于宗元传载其贻萧俛一书,许孟容一书,贞符一篇,自儆赋一篇,可见其于韩、柳二公有癖嗜也。”[41]381
中唐之时,“韩柳”与“韩、张”“韩、李”诸说相比,并无特殊之处。宋元之后,随着学者对“韩柳文章齐名说”的普遍接受,他们通过详细罗列柳文可以同韩文并列的缘由,从各个方面进行理论建设,遂使此说内涵日益丰富,体系不断完善。部分学者所持“柳胜于韩”之论点,虽然不是学界的主流观点,但仍然极大提高了柳文的地位,在事实上强化了“韩柳文章齐名说”的学术影响力。而“韩、李”“韩、张”诸说,则由于在后世缺乏类似的讨论与理论建构,其影响力遂不能与“韩柳”说同日而语。
再次是诗歌齐名层面的理论建设。韩柳在世之时,为士人所推崇者在于他们皆能荐拔人才,不独在于文章。韩柳殁后,其文章齐名乃为世人接受,成为定论。然就后世评价来看,“韩柳齐名说”的内涵不断增殖衍化,其范畴逐渐扩展到诗歌领域。学者在构建“韩柳诗歌齐名说”主要以两种方式。
一是细数韩柳诗歌可以并举的具体缘由。或以韩、柳诗风各具优长,如苏轼《评韩柳诗》云:“柳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退之豪放、奇险则过之,而温丽清深不及也。”[42]33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引阙名《雪浪斋日记》云:“为诗欲词格清美,当看鲍照、谢灵运,欲浑成而有正始以来风气,当看渊明,欲清深闲淡,当看韦苏州、柳子厚、孟浩然、王摩诘、贾长江,欲气格豪逸,当看退之、李白。”[43]10高棅《唐诗品汇总叙》论曰:“柳愚溪之超然复古,韩昌黎之博大其词”[44]7;胡应麟《诗薮》外编卷四云:“元和而后,诗道浸晩,而人才故自横绝一时。若昌黎之鸿伟,柳州之精工,梦得之雄奇,乐天之浩博,皆大家材具也。”[29]3642或以韩、柳诗渊源相似,如姜夔《白石道人诗说》评曰:“韩、柳之诗,《雅》出也。”[41]681或以韩、柳之诗,各如其人,如陆时雍《诗镜总论》云:“读柳子厚诗,知其人无与偶。读韩昌黎诗,知其世莫能容。”[38]1420或以韩、柳诗文兼善,如洪亮吉《北江诗话》:“有唐一代诗文兼善者,惟韩、柳、小杜三家。”[29]3649或以韩柳诗作法相似,如孙奕《履斋示儿编》所云:“杜与韩、柳喜取别声押韵,然自建安而来已皆然矣。”[45]144
以上所论,以品评韩柳诗风而立论者稍多,其语虽有不同,然其意皆在于证明二人之诗足以抗衡。其他诸如韩、柳诗渊源相似等论,也从各个方面完善了“韩柳诗歌齐名说”的内涵。
二是比较韩柳诗歌成就以权衡二人高下。“韩柳诗歌齐名说”是“韩柳优劣论”蔓延到诗歌领域的表现,正如李调元《雨村诗话》卷下所说:“柳子厚文配韩,其诗亦可配韩。”[29]3649
与“韩柳文章优劣论”类似,学者在论述韩、柳诗歌成就时,或认为“柳诗胜韩”。如北宋张耒《明道杂志》所云:“退之作诗,其精工乃不及柳子厚。子厚诗律尤精,如‘愁深苑猿夜,梦知越鸡晨’‘乱松知野寺,余雪记山田’之类,当时人不能到。退之以高文大笔,从来便忽略小巧,故律诗多不工。如陈商小诗,叙情赋景,直是至到,而已脱诗人常格矣。柳子厚乃兼之者。”[46]173再如吴可《藏海诗话》,其云:“有大才,作小诗輙不工,退之是也。子苍然之。刘禹锡、柳子厚小诗极妙,子美不甚留意绝句。子苍亦然之。”[38]337再如宋刘克庄《后村诗话》前集卷一所论:“柳子厚才高,它文惟韩可对垒。古、律诗精妙。韩不及也。”[32]6550其《竹溪诗序》亦云:“唐文人皆能诗,柳尤高,韩尚非本色。”[48]3996再如张谦宜《絸斋诗谈》卷五所论:“柳文让韩,诗则独胜。”[29]3647刘辰翁亦以诗评“韩柳齐名说”,其曰:“子厚古诗短调,纡郁清美,闲胜长篇,点缀精丽,乐府托兴飞动,退之故当远出其下,并言韩、柳亦不偶然。”[44]609
或认为“韩诗胜柳”。持此论虽然不多,然亦不乏名家。如宋人陈知柔《休斋诗话》所论:“柳子厚小诗幻眇清妍,与元、刘并驰而争先,而长句大篇,便觉窘迫,不若韩之雍容。”[49]472再如宋人张戒《岁寒堂诗话》所云:“柳柳州诗,字字如珠玉,精则精矣,然不若退之之变态百出也。使退之收敛而为子厚则易,使子厚开拓而为退之则难,意味可学而才气则不可强也。”[38]459
诸位学者虽然在评价韩柳诗歌时的出发点与着眼点并不一致,但是从实际效果而言,无论其强调“柳诗胜韩”或“韩诗胜柳”,皆是在承认韩柳之诗可以相提并论的前提下进行的,客观上都对“韩柳齐名说”起到完善与补充的作用。“韩柳诗歌齐名说”命题的确立,使“韩、柳”说的内涵文化与理论建设进一步延展到诗歌领域。与“韩柳”说相比,由于“韩李”“韩张”诸说并没有随时代变迁而增殖衍化,其文化内涵始终相对简单,且理论建设几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而“韩柳齐名”这一刻板印象遂在学界得以定型并日益固化。
四、结论
至德、元和之世,韩愈文章独步天下,堪称一代文宗,当时论文者多以其为标准而衡量诸家。至于韩柳齐名之说,中唐即有此论,然而与“韩张”“韩李”诸说相比,并无特殊之处。而且,从社会认可度与实际影响而言,“韩李说”曾稍胜于“韩柳说”。晚唐五代之时,“韩柳说”逐渐脱颖而出,影响力日渐超过“韩李”等说,逐渐成为舆论界共识。北宋之初,欧阳修敏锐地认识到“韩柳齐名说”存在着相当尖锐的内部矛盾,远不及韩愈与李翱的共同之处多。此后,围绕“韩柳说”的内在矛盾,历代学者主要从文风之异、思想之异、文坛地位之异等三方面展开论争,试图从正面彻底瓦解此说的理论基础,系统纠正其内涵偏差,进而在文统和道统层面重构并替代以“韩李齐名说”。客观而论,虽然很多学者都指出了“韩柳齐名说”的内在矛盾,但是在强大的舆论氛围和历史惯性影响下,此说之地位却愈加牢固。从历史角度来看,回归到理论源头,在“韩柳齐名说”诞生的最初阶段,此说主要是指韩柳二人皆能培养、荐举人才,颇有师者之风。作为“韩柳说”的较早提倡者,杜牧曾间接受益于韩、柳奖掖人才的行为。宋元之后,学者或通过抬高柳宗元的文坛地位,或通过详细列举柳文可以与韩文并列的缘由等方式丰富和完善了“韩柳文章齐名说”,弥补了韩柳文相互抵牾的内部矛盾和理论漏洞,从而将该命题从一种社会舆论发展为一套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分明的理论体系。随着年代的累积,“韩柳齐名说”逐渐延展到诗歌领域,在“韩柳文章齐名说”之外,又形成“韩柳诗歌齐名说”,进一步充实和丰富了该命题的理论内涵。与之相对应的是,由于“韩李齐名说”的理论建设几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所以后来此说的传播范围与影响力上较“韩柳说”远远弗及。正如章学诚《文史通义》所云:“仁智为圣,夫子不敢自居。瑚琏名器,子贡安能自定。”[49]506“韩柳齐名说”经过千余年的传播与接受过程,先后经受了无数学者的严苛反省与理论检验,其含义早已超越了最初的师道并称之说,故能最终压倒中唐诸说,成为中国文学史中的经典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