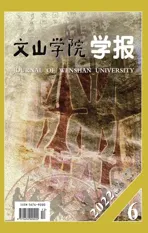区域、疆界及治理视域下的滇越边民跨境流动问题
2022-03-13逯慧娟郑翠斌
逯慧娟,郑翠斌
(红河学院 人文学院,云南 蒙自 661199)
云南地处西南边疆,在东南及南部有三个市、州的七个县与越南接壤。普洱市的江城县处于滇越疆界最西端,向东依次为红河州的绿春县、金平县、河口县,文山州的马关县、麻栗坡县和富宁县。境外接界的分别是越南的莱州、老街、河江三省。滇越边境地区民族的分布,经历了一个绵延不绝的历史过程。长期居住在一个地域内的人们,无论民族何属,却因经常性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往来,而形成区域性社会生活系统。
一、民族迁徙、定居、开发与跨境流动的自然状态
滇越边境地区生活着十几个跨境而居的民族,范宏贵认为:“按中国已确定的民族成份来计算,有十三个民族:壮、傣、布衣、苗、瑶、汉、彝、哈尼、拉祜、仡佬、京、回、布朗,莽人民族成分未定。按越南已确定的民族成分来计算,有26个民族”。缘于两国不同的民族划分标准,在中国是一个民族的,在越南则被划分为两个或多到五个民族,如中国的壮族,在越南则是岱族、侬族、布标族、拉基族、山斋族。另外,两国也有将同一民族成份划入不同民族的情况,如“越南的山斋族由高栏和山子两部分组成,在中国高栏是壮族的一部分,山子是瑶族的一部分。”[1]
中越跨境民族中,有的民族在历史早期便在中越边境地区居住,如莽人,是早于傣族在西双版纳居住的土著居民①。十八世纪在地方部族冲突中,莽人遭受镇压,很多迁往境外,留在境内的又多融入傣族中。“民国时,几十户芒(莽,金平没有芒人)人散居在国境沿线……12个村寨,小的村落仅四五户,大的不过十来户”[2]131。至于莽人何时来金平定居则无从考证。越南境内的莽族,主要分布在金平、绿春对面的莱州省三个县。
同早期的开发者相比,今天边境上的许多民族则经历了一个迁徙、定居和开发的长期过程。作为滇越边境地区主体民族之一的哈尼族,与彝族、拉祜族、纳西族均源于古代氐羌族。在哈尼人的传说中哈尼先人曾游牧于遥远北方一个叫“努玛阿美”②的地方。“唐代‘昆明’部族中出现了‘和蛮’及‘和泥’的分支,这是历史上最早的哈尼族称。因频繁战乱,哈尼先民被迫离开滇中腹地,南迁进居红河南岸的哀牢山”[3]。《江城县志》记载:“过去哈尼族迁徙频繁,有不少人迁往越南、老挝。同时也有不少人从元江、墨江、普洱、绿春相继迁来江城。历史上总的趋势是由北向南,不断迁移。”[4]《绿春县志》的记载,则给出哈尼人从“努美阿玛”迁出在宋朝以前的时间③。
越南哈尼族比较集中的分布在莱州省的孟碟县和黄连山省的巴沙县,“现在居住在莱州、黄连山两省的哈尼族人的祖先都是从中国云南省金平县和绿春县迁徙来的。据老人们说,大约三千年前,哈尼族的祖先来到莱州,开始有五、六户人家,居住在越中边境的我国一侧,不久后又搬回云南。十二年后,由于忍受不了中国封建统治者的残酷剥削,哈尼人又来到莱州”。其中的“三千年”之说,要么是传承错误,要么是笔误,比较合理是在三百年前。黄连山的哈尼人到越南定居稍晚一些,“大部份哈尼人是在一百五十年前到越南的”[5]344。
今天滇越边境地区的民族分布格局,基本奠定于明、清和民国时期。富宁县的壮族大部分为土著居民,但“天保支系明末从广西天保(今德保)迁入东南部,落业半山区;隆安清中叶从广西隆安迁入剥隘、谷拉山地;蔗园清乾隆年间从广西迁入,先在剥隘,后到归朝、洞波,喜居热带;龙音清嘉庆年间从广西天等迁入,落业谷拉九弄,少数迁入新华、归朝、板仓;布雄清末从广西那坡、靖西迁入,分布在板仑、郎恒、归朝、新华、洞波、阿用;其他壮族支系于民国年间从广西迁入”[6]160。
《金平县志》记载:“金平的彝族不是土著,而是自外而入,是清代从石屏、建水、蒙自、开远、个旧、元阳等地陆续迁入。”[2]122。清代雍正年间推行改土归流,居住在云南腹地的彝族遭到镇压,于是加快向边地和山区迁移。《绿春县志》记载:“本县的彝族是在清雍正七年(1729年)至乾隆三十九年(1775年)间,先后从今元江、元阳、建水、石屏等地迁入的。”[7]135有越南学者认为倮倮族迁入越南北部的时间或在南诏亡国或更早时期,而另一些则认为“明朝(约公元十五世纪)才是倮倮族历史的里程碑”[5]338。由于不堪封建剥削,倮倮酋长举族南迁,进入越南北部定居。前一说法,以南诏主要由彝族参与创建为基础,学术推论的意味很浓;后一说法,既有传说为依据,也与彝族在云南南部迁徙的时间较吻合。比如,《红河县志》《江城县志》均载,彝族迁入的时间在明清时期。《绿春县志》记载的时间更为具体:“本县彝族是在清雍正七年(1729年)至乾隆三十九年(1775年)间,先后从元江、元阳、建水、石屏等地迁入。”[7]135
河口主体民族瑶族迁入的时间在清朝乾、嘉年间,县志记载:“据瑶族的家谱、信歌记载和墓碑调查,瑶族进入河口定居约在清朝乾、嘉年间,至今近三百年,其迁徙路线大都是从湖南进广东转广西,经文山或临安进入,亦有少量从广西转道越南进入。”[8]93-94关于瑶族进入越南北部地区定居的时间,《越南北方少数民族》一书给了一个很宽泛的时间段:“这个过程可能发生在隋唐到明、清时代,直至本世纪初还在继续。”[5]303可见中越之间民族的迁徙流动,在历史上曾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
苗族迁入滇越边境地区的时间在明朝初年。《麻栗坡县志》记载:“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派兵30万征云南,除了派大批汉军屯兵云南和迁来大批汉民开发云南外,同时也强征大批苗军和苗民屯田云南。麻栗坡县苗族大多是这个时候入境的。”[9]159康熙年间,苗族跟随吴三桂反清,失败后被迫迁居到中老、中越边境地区。富宁县境内的苗族多在明末之后迁入,“西南部多由越南、广南、麻栗坡迁入,如吴、朱、杨、侯、熊、陶、王、古等姓均于中法战争时从越南到此定居。多分布于与越南接壤和广南县相邻的西南部边境的高山崇岭之中。西北部多从贵州、广西入居”[6]189。最早一批苗人迁入越南北部,“距今三百多年前,到达边界的河宣省、黄连山省。此后,迁移浪潮延续至1950年中国完全解放的时候,其中有两个大的迁移阶段:距今二百多年和一百多年的时间。我国几乎所有的苗人还记得他们是从贵州迁移来越南的”[5]274。
滇越边境线上的其他跨境民族,也多由临近区县迁徙而来。据《绿春县志》记载,县境内的拉祜族是在“清朝中后期(1786-1886年),由当时的郎厅陆续迁来的”[7]151。傣族很早便在滇南边疆居住,河口的傣族也多是清代迁来。据县志载:“桥头乡傣族古墓碑文载多是乾隆五年自阿迷州土老寨和开化府的马塘、麻栗坡、那岭冲、田湾、老头寨等处迁来。”[8]117麻栗坡的傣族,却是在“宋朝末年来自泰国经越南迁入县境”[9]188,而仡佬族则是来自贵州和云南的广南县。越南的仡佬族,是辗转从贵州迁去的。最早迁入的一批仡佬族人,约有一百五十到二百年的历史。
滇越边境民族的跨居状态,使得边民跨境流动体现为一个族内或族际自然交流的社会活动。在边民生活中原本只有婚丧嫁娶、赶圩、耕作这些日常事务,区域内基于族内或族际的经常性跨境流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如果政治疆界比较模糊时跨境流动问题只是一件生活琐事,那么随着中越两国陆上边界的最终确定,滇越边民跨境流动作为政治问题,便日益凸显出来。
二、疆界划清凸显滇越边民跨境流动问题
据史书记载,云南、越南进入中国统一版图均在秦汉时期。《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10]2993据考证,常頞所修五尺道起自宜宾,南至曲靖,可见此时云南部分地区已经在秦朝的控制和管理之下。《云南省志》大事记中认为:“秦在邛筰地区设置郡县,委派官吏统治西南夷地区。”[11]36方国瑜著《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据《史记·西南夷列传》指出“邛筰”实为“邛都”、“筰都”,分为两地,均在滇以北地区。其中“金沙江以北为邛都区域”[12]。
《史记·南越列传》有关于秦朝攻取越南北部地区并置郡县的记载:“秦时已并天下,略定杨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与越杂处十三岁。”[10]2967其中象郡辖境已包括今天越南北部及中部地区。秦朝灭亡之后,赵佗建立南越国,“击并桂林、象郡”,从而领有越南中、北部地区。“汉十一年”,刘邦遣陆贾使南越国,封赵陀为南越王。汉文帝元年(前179年),陆贾再次出使南越,赵佗臣服,成为诸侯王,从而使越南中、北部地区归入汉朝版图。武帝时南越丞相吕嘉叛乱,“元鼎五年秋”,汉武帝遣命“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故归义越侯二人为戈船、下厉将军”及“驰义侯”“咸会番禺”[10]2975共击吕嘉。叛乱平定后,南越国旧地“遂为九郡”,其中,九真、日南、交趾三郡治地在越南中、北部地区,各郡设太守分治其地,归交趾刺史部监察。
《云南通志稿》在凡例中说:“云南自六朝即沦于夷,复经蒙段窃据,考订非易。”[13]4此说不知所本,或仅从搜集方志资料而言。虽然自三国开始中国疆域剖割,政权叠兴,云南地区也相继崛起一些地方政权,但总体上并未游离中国区域之外。西晋时云南改设宁州,为当时十九州之一。及至隋朝及唐初大一统局面出现,云南再次回到中央政权之下。唐宋时期,云南地区先后出现南诏、大理两大政权,却保持着与唐、宋密切的臣属关系。在此期间,历届中央政权基本保持了在越南的统治,直到939年吴权称王建立政权,968年丁部领统一越南北部建立丁朝,从此结束了所谓“北属时代”,开始了“自主时代”④。独立后的越南历代王朝,基本维持了与中国的藩属关系。
在宗藩关系框架下,中越边界几经变动,但却从未全面勘定过。中国历朝统治者基于“华夏中心观”,长期奉行“守中治边”“守在四夷”为核心的治边政策,对周边藩属国恩礼有加,以达到“四夷怀服”的目的。雍正三年正月,云贵总督高其倬再向雍正帝报告越南蚕食云南开化府边界的情况。雍正的批复为:“治天下之道,以分疆与柔远较,则柔远为尤重。而柔远之道,以畏威与怀德较,则怀德为尤重。据奏都龙、南丹等处在明季已久为安南国所有,非伊敢侵占于我朝时也。安南国我朝累世恭顺,深为可嘉,方当奖励,何必与争明季久失之区区弹丸之地乎?且其地如果有利,则天朝岂与小邦争利?如无利,则何必争矣。朕居心惟以至公、至正,视中外皆赤子。况两地接壤,最宜善处,以安静怀集之,非徒安彼民,亦所以安吾民也。即以小溪为界,其何伤乎?”[14]正是基于这一指导思想,清政府于雍正六年将上述争议地区赐予越南⑤。
滇越疆域相连,又长期同隶于中央政权之下,人民跨疆域流动也只是一个内政问题。即便进入宗藩时代,受传统政治思维影响,滇越间仍少有此疆彼界的纠纷。滇越间虽有行政治理上的分界,但古代部族的迁徙却无边界。考虑到古代中央政权或区域内政权的管理水平,生息于滇越边境地区的人们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行政管理的约束,实属未知之列。至于古代国家严厉的边境管理律例,能否在绵延的边境线上贯彻执行,并无资料可供印证。从民族史零星的记载来看,边民跨境流动,无论在日常经济文化生活中,或是特殊情况的族群迁徙,均处于自然无管理状态。只是当政治边界细划,政府的民政管理进入乡村级别,边民的跨境流动问题才变得日益严重。
如果在宗藩体系下“内地”与“外藩”可“一毫无所分别”,而当越南逐渐为法国所侵吞,不再为中国藩属国时,中越间勘查划界便成为迫切之事。中法战争结束后,按照《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十款》第三款的规定,自条约画押之后起“限六个月期内,应由中法两国各派官员赴中国与北圻交界处所,会同勘定界限。倘或于界限难于辨认之处,即于其地设立标记,以明界限之所在。若因立标处所,或因北圻现在之界稍有改正,以期两国公同有益,如彼此意见不合,应各请示于本国”[15]。1885年8月,清政府指派内阁学士周德润为勘界大臣,会同云贵总督岑毓英、云南巡抚张凯嵩办理中越边界滇越段的勘界事宜,这是滇越间正式划界的开始,从勘界、谈判到形成条约,前后历时十二年。
云贵总督岑毓英等希望借此机会收复自明代失去,雍正六年正式赐予越南的大小赌咒河之间的疆域。他在奏片中说:“臣伏思越为中国外藩要地,归藩原系守在四夷之意,不必拘定撤回。现在越几不能自存,何能为我守险?应否俟堪界时,将都竜、南丹各地酌议撤回,仍以大赌咒河为界,以固疆圉而资扼守之处。”[16]在随后的中法滇越段谈判中,清朝并未实现恢复中越旧界的目的,但也收回雍正六年赐予越南的部分领土。至1897年,中法“勘定滇越边界”及立碑的全部工作结束,主要签订了六个条约。二战后,中、越新政权先后建立,在边界问题上双方均表示尊重中法界约划定的边界线,对于历史遗留的少数地段问题在双方政府协商解决之前,应严格保持边界现状。
1991年,中越两国在陆地边界问题上经过双方协商,同意以中法签订的《续议界务专条》和《续议界务专条附章》为依据,核定边界的全部走向⑥。1999年12月30日签订《中越陆地边界条约》,2001年11月,两国政府成立中越陆地边界联合勘界委员会,负责勘界立碑工作,并起草两国陆地边界勘界议定书及其附图。到2009年2月,中越双方陆地边界的勘界立碑工作完成。同年11月双方举行陆地边界勘界文件签字仪式,签署《中越陆地边界勘界议定书》及其附图、《中越陆地边界管理制度协定》和《中越陆地边境口岸及其管理制度协定》等三个文件。至此,中越历史上遗留的陆界问题,得到彻底解决。
政治疆界的变化,自然会影响到特定区域人们的生活,但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他们不会因政治关系的变化,便轻易放弃或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边民虽然在政治层面发生着身份的变化,但在社会生活层面则延续了传统和习惯。何况古代国家对于疆域尽头,在管理上原本鞭长莫及,边民也少受此疆彼界观念的困扰。边民的跨境流动,自始便是一种自然且政治上无意识的日常生活内容。所谓“边民的跨境流动问题”,便是一个纯粹政治视角的边地治理问题。
三、意指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边民跨境流动治理之路
滇越边境地区,谷深林密,交通闭塞,早在政治边界形成之前,古代民族在区域内的布局已经形成,且随历史递嬗不断调整。自越南脱离中国统一版图以来,滇越边境地区的民族迁徙、分布,基本保持着自然递进的状态。边境居民在经济区域、基本族群内组织日常生活、生产,跨境流动的政治特性被生活的真实所忽略。中国历朝政府,为西南民族的犷悍所难,政策上倾向“羁縻”,依靠土官进行间接治理。滇越边境地区在古代政治思维中界临化外,自元至民国,中央政府推行土司制度,由土官、土吏依民族习俗管理。虽然古代王朝就边境管理制定了严格的律例,但在实际执行中具体情况如何,并无确切记载。考虑到古代政府管理能力及土司制度的存在,边民自由跨境流动则是一种日常形态。这虽然与古代国家国土治理能力的局限有关,但滇越边民跨境流动地域内的民族、习俗等自然因素,或许才是这一历史过程的原本情由。
据《中越边界(文山段)跨境民族调查报告》一文观察,文山州边贸的发展主要体现为中越比邻村寨边民集市的小额贸易,而官方口岸却难以繁荣。可见,边民的经济交往,仍然延续了区域内、族群间构建信任关系的传统模式。这一点也与《中越边界(文山段)跨境民族调查报告》一文的调查结论相一致:“由于中越边境都是山区,对外交通不方便,形成了天然的大大小小的‘地缘圈’,在这个圈内,有着大大小小的自然通道300多条,把当地的经济文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人们在这个很小的范围内往来,互通有无,彼此间往往十分熟悉,到边境对面做生意,也很放心地把货物存放在相熟的人家里。”[17]
《滇越边民跨国流动与社会稳定研究》一文所举金平跨境莽人的生活、生产状态,便能充分说明封闭经济环境下,边民跨境流动的地域性和习俗性特征。金平莽人村寨龙凤村与越南莽族南年村隔山背居,“‘文革’时期,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曾使山居莽人远离中国,向越南迁流”。由于中国一边经济在改革开放后迅速发展,对越南村民产生吸引,越南妇女外嫁到龙凤村的情况增多。另外,每逢“鼠”日,“很多越南人身背五六十公斤土产,翻山越境过山来出售。越南边民多是提前一天到龙凤村,托亲谢(引者注:歇)脚过夜,第二天赶集后才返家,往返一次需两天时间”。越南边民跨境到中方集市兜售土产,只是完成了整个行程的一半目的。“南年人上集将随身背带的东西卖后,再从联防集市买回粮种、大米、油、盐、蔬菜、衣服、鞋等生产、生活用品”。[18]
基于以上观察,有关滇越边民跨境流动的治理问题,可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在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框架内,或先于一体化进程推进,或紧随一体化步伐,顺势推动滇越边境区域社会经济向着一体化方向发展。在这一构想基础上可预期更深层次区域协作关系的构建,包括社会、文化协同发展的步骤。滇越间相邻区域内,相同或相近民族的迁徙和分布,是边民跨境流动的内驱因素,而这也恰是推进区域一体化的天然优势。在跨境分布的民族那里,相同或相近的生活习俗、社会文化,可为边境区域内一体化进程提供系统性社会支撑,也为接续加入更广阔毗连区域提供天然的沟通、过渡基础。
注释:
① 据范宏贵:《越南民族与民族问题》[M],广西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第286-287页。
② 这是《红河州志》中的记载,《江城县志》记载此地名为“努美阿玛”,《绿春县志》记为“努马昂美”。
③ 绿春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绿春县志》[M],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15-116页。
④ 据[越]陈重金:《越南通史》[M].戴可来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⑤ 到2009年中越历史上遗留的陆界问题,得到彻底解决。
⑥ 据云南省志编纂委员会总纂,云南省外事办公室编撰《云南省志》[M],卷五十三,外事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9-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