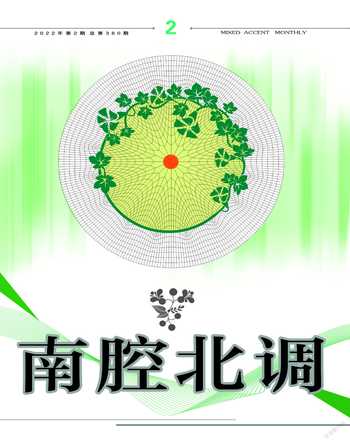论张洁长篇小说《无字》中“爱”的书写
2022-03-11周茹
周茹

摘要:作为不断探索爱与人性真谛的理想主义殉道者,张洁一直怀着对理想之爱与至美人性的憧憬,不断探索人性的本质与爱的本真。在对“不能忘记的爱”进行了深刻地反思之后,张洁“以血为墨”,历时12年在耳顺之年写下了自己最好的作品《无字》。这部长达80余万字的爱的“史诗”,倾注了作家对爱的坚守以及对情的失落。分析文本中爱之抒写,形成立体感知,进而挖掘爱之建构与破碎背后的原因,以期达成对张洁情爱观及写作局限性的进一步认识。
关键词:张洁 《无字》 爱情 女性 婚姻
《无字》可以说是张洁积蓄了10余年力量,将心彻底沉淀、将泪与血消耗殆尽后铸就的一部力作,正如张洁所说:“真正的写作是从《无字》开始的……哪怕写完这部长篇小说马上就死,我也心甘了。”[1]在看过太多动荡年代、体制改革中人性的嬗变与情爱的破碎后,张洁以自身不幸的童年与婚姻为蓝本,将她对爱的多维度把握以及对人性的深入洞察诉诸笔端,在解构爱情神话的同时将不同层面的爱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在文本中奏响了关于爱的交响曲。
“文学需要织造出一种多层次/多面性的世界景观。”[2]如卡尔维诺所言,新时期以来,公式化概念化的写作逐渐被作家摒弃与排斥,取而代之的则是具有“繁复”特质的多维度抒写。在张洁早期的创作中,爱情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从《爱是不能忘记的》到《祖母绿》再到后来的《方舟》,张洁以女性独特的生命体验与细腻的笔调对两性世界进行了描绘,勾勒出伤痛年代大背景下的爱情。《无字》的出现标志着张洁创作的进一步成熟,作品仍是以男女主人公——吴为与胡秉宸——的爱情纠葛为主线,但除却爱情之外,其中还有对残缺的父爱、厚重的母爱以及本真的人性之爱的剖析,多维度的爱之间又存在紧密地联系,从而较之以往文本中单一的两性之爱更为立体丰满,对两性世界的描绘也上升到对人性的揭露与反思。张洁最初美好单纯的理想寄托在与残败现实不断地碰撞中零落,从而转向反抗与自我救赎的道路。
一、爱的荒芜与失落
作为一个作家,并且有着极强女性意识的作家,张洁的创作处处彰显着对男权秩序的审视与反抗,这种意识追根溯源则是绵延千年的父权文化统治。对父权话语反抗无果便形成压抑,而作家内心巨大的精神压抑对其思想与行为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在精神分析学视域中,这种压抑是长期积淀、持续作用的。正如弗洛伊德所说:“只有具有列奥纳多童年经验的人才能画出《蒙娜丽莎》。”[3]文艺家往往将被压抑到深层的童年记忆呈现在作品里,童年时期的心理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对作家的创作起支配作用,故我们在近代以来很多女性作家的作品里都能看到一系列残缺病态的父亲形象,这与她们童年时期的父爱创伤经历有着莫大的关系。诸如张爱玲笔下的男性形象要么处于叙述的空白点,要么呈现出畸形病态,贯穿其大多数作品的主题都与“弑父”心理密切相关。《无字》中的父亲形象同样带着地位缺失、行为卑劣的色彩,文本中关于父女间不和谐关系的描绘,更多集中于女主人公吴为与父亲顾秋水之间,但将历史的车轮倒转,我们不难看到吴为的姥爷叶志清——叶莲子的父亲,在父亲角色的扮演上也是失败的。墨荷难产而死,叶志清利索地配合家里人找来薄板将心甘情愿为自己做了一辈子“篮筐”的妻子送入火海,这给叶莲子的内心留下了难以消逝的伤害,尔后他再娶,叶莲子虽为亲生女儿却被当作大户人家的粗使丫鬟使唤,过上了寄人篱下的生活。继母的嫌恶、堂兄弟的欺辱、叔父的苛待……让还是6岁小女孩的叶莲子过早地懂得了“这辈子再苦、再难,大概是不能靠谁,也靠不上誰了”这样成熟的人生道理。可以说,叶志清的父爱缺位促使叶莲子以顽强生长、忍辱负重的姿态过完了后来被顾秋水毁坏的苦难人生,而当他们俩意识到这份父女情义,想去珍惜的时候,却面临永久地离分,真算是“白做了一世的父女”。
叶志清不过是让叶莲子过早地成人,而顾秋水则毁了吴为的一生。童年的经历是作家创作的基点,在此期间形成的心理结构对作家日后的创作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冰心曾指出一个人童年中“有许多印象,许多习惯,深固地刻画在他的人格及气质上,而影响他的一生”[4]。顾秋水只顾跟随包天剑闯天下的男子气概与赤胆忠心而将为人夫为人父的责任抛至脑后,不光情感上冷漠淡薄,就连最基础的经济责任也推诿逃避。当叶莲子母女实在难挨生活的困窘不远千里来香港找顾秋水时,只一句“你怎么来了?”便让叶莲子的心凉了半截。遂后,顾秋水为了摆脱她们母女,不惜一切残忍的手段百般折辱,竟当着只有两岁的吴为与女佣阿苏肆意狂放地做爱,甚至如畜生般赤身裸体地对叶莲子拳打脚踢,这些暴戾残忍的场面在吴为稚嫩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阴影,摧毁了她眼中关于爱与人性的所有设想与期待,也摧毁了其正常的性爱观,这种摧毁是毁灭性的。当仅仅只有两岁的吴为被顾秋水惨无人道地扔向楼梯,便造就了她绵延一生的奴性悲剧。对暴力越是仇恨则越是对其迷信与崇拜,如此,顾秋水便在吴为的灵魂深处播下了对男性仇恨的种子,伴随这种仇恨的还有要命的敬畏与极度的依赖,这种创伤极大程度上酿就了后来吴为与胡秉宸的婚恋悲剧。纵观文本,叶莲子失去母亲独自面对飘摇苦难的人生,吴为一生怀着对顾秋水的恨,禅月从小就宣告:“我没有爸爸,我的妈妈就是我的爸爸。”父亲的角色始终处于残缺的状态。
《无字》将大量的笔墨集中在描写两性之爱上。诚然,爱情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巨大的,巴尔扎克说恋爱是人生第二次脱胎换骨,那么对生性敏感、细腻多思的女性来说,爱情则意味着一场甜蜜却又痛苦的战争。“千百年来,爱不仅是女性的特殊生活领域,而且事实上一直是女性能够实现她们一切愿望的唯一或重要门径。”[5]透过张洁笔下四代女性的爱情婚姻状况,我们可以洞悉祖孙四代迥异的爱情婚恋观,亦可一窥作者对男女两性关系的审视与反思。
墨荷作为旧式封建家庭的女性,将“投篮”视为婚姻的实质。作为女人无权拒绝男人的投篮,所以她一生都在与叶志清无爱的婚姻里熬煎,甘愿沦为家庭的奴隶、传宗接代的工具,最终难产死去却被视为不祥之兆扔进火海,结束了自己苦难的一生。第二代女性叶莲子与母亲墨荷相比,受过一定的教育,但其脑子里从一而终的封建道德观念却依然根深蒂固。在与“兵痞”顾秋水一生的婚恋纠葛中,叶莲子饱受屈辱,但很难说叶莲子与顾秋水的婚姻丝毫没有爱的成分。婚后的前几年顾秋水带着叶莲子游览四方景色、拍纪念照片,甚至连穿的衣服都是顾秋水亲自设计的,这段日子被叶莲子视为一生最好的日子,“以后,再好的日子也似乎好不过这时。”可当顾秋水看到了叶莲子生活上的“不随意”,总是给人一种“不自在”的感觉,最初的点点温情也被消磨得一干二净,被抛弃、被毒打、被侮辱、被背叛……在与顾秋水的婚姻中叶莲子默默地咀嚼着伤痛悲苦,还要以女性薄弱的身躯担负家庭的重任,即便做了多年的一家之主,却仍然固执地认为:“一家之主非男人莫属。”
到了吴为这里,爱情似乎被抬升了一个高度。如果说吴为将其与韩木林的婚姻视为市场交换,那么胡秉宸则是她的精神之爱。吴为亲手建立起与胡秉宸灵魂之爱的城堡又亲手将其摧毁,诚如刘慧英所说:“女性不断地找寻却没能找到一个终极的完满答案,这也是女性未趋于完全解放的一个标志与象征。”[6]在吴为与胡秉宸20余年的爱恨纠葛中,吴为与白帆胡秉宸离婚作战小组的厮杀、与人世舆论冷眼的对抗、与自我责任心和道德感的斗争,这一切几乎将她自己的命搭了进去,直至最后吴为撕下自己“亲手造的胡秉宸”虚伪的面具,才认清自己毕生抛弃所有去追求的男人不过是个诿过自保、自私卑劣的魔鬼,由此吴为便再不能以正常的眼光看待异性,再也不能陷入情爱,“由胡引发的对男人的总体失望,才扼杀了她在男欢女爱、两情相悦上的物质力量。”三代女性在两性世界中都显示出了可悲可怜的奴性。直到禅月说出:“咱们家的这个咒,到我这儿非翻过来不可!”叶家女人在两性关系中的地位才有了翻转。禅月在两性关系中的独立自尊与吴为的无条件牺牲、无底线妥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也从侧面喻示了吴为誓死追求的“真爱”神话的彻底破碎。
二、爱的修补与寄托
《无字》的扉页题献写着:“献给我的母亲张珊枝。”可见小说倾注了作者对母亲深沉的爱与永久的憾。在文本中,父爱的缺失与真爱的破碎,使得吴为将此生最难忘也最沉重的爱压在了母亲叶莲子身上,应该说,男性的先导性缺席,父亲角色的缺失,已经注定了她们母女的生存结构和生活结构。
因为叶莲子的存在,吴为才义无反顾地来这世上走一遭,即便后来的岁月里充满了腥风血雨,她也在所不惜。父亲顾秋水对吴为的抛弃、伤害,一方面模糊了吴为对父亲角色的原有认知甚至产生憎恶与报复的“弑父心理”,另一方面更加重了对母亲的依恋与爱。顾秋水对家庭责任的淡漠,使得叶莲子一人分饰两角,既要面对充满饥饿与苦难的现实世界,又要对抗充满不公的男权压迫。正是叶莲子将沉重的母爱,不吝一分地压在吴为身上致使吴为一辈子都觉得“唯有她和叶莲子,才是这个险象环生的世界中相依为命、须臾不可分的至爱”。对至爱的这种执念,也影响了吴为后来在爱情中对分寸的把控,与胡秉宸几经波折的“真爱”破碎后,吴为终于明白了对任何男人的情爱都无法超过对叶莲子的爱,对叶莲子的爱也不仅仅是以血缘维系的母女之爱,而是超越了一切情爱的“共生固恋”。
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这种固恋是内在于人的最基本情欲之一,外化为行为表现则是寻求保护的欲望、对无条件的爱的希求。在父亲缺位、爱人形象坍塌的境遇下,母亲无疑成为这一固恋的第一化身与切实保障。故吴为在叶莲子去世后终于意识到:“她对胡秉宸的爱,只能是一种可以交出生命,却无法交出完整的心的爱。”因为那一颗残损的心装满了对母亲叶莲子的深爱与愧疚,叶莲子给予吴为超越生命的爱,岂是胡秉宸施舍的经不起岁月命运击打的虚妄之爱可以相比的?直到吴为生命的最后,几乎忘却了自己之前写的所有文字,却只记得“妈妈”这两个字。正如张洁所言:“爱人可以更换,而母亲却是唯一的。”与母亲共生的信念,无法让失去叶莲子的吴为独自苟活于世,所以,吴为疯了,当一个人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也就无法再制造意义。
面对时代话语下的历史与现实,知识分子不得不承担起启蒙的神圣使命。作为痛苦却坚定的理想主义者,张洁选择了爱作为救赎的路径。她在早期的創作中,充满了理想主义情怀,笔下的人物永远带着对生活的希望以及对未来的向往,因而文本中永远笼罩着充满大爱的怜慈与温情;在后期的创作中则一改前貌,文本中充斥着大量的对灰色现实的批判与揭露,以往那个为了美好人性与崇高理想奔走呼喊的张洁,似乎变得沉静冷酷甚至刻薄。于此,笔者并不认为这是张洁的“倒退”。相反,在后期的创作中,其对人性与理想之爱的坚守,并未动摇且更加坚定。“当作家转而去描绘当代现实生活时,这种行动本身就包含着一种人类的同情。”[7]尽管我们在《无字》中读到的大多是生活的丑恶与精神的沉重,但这泪与血背后深藏的是作者对大爱的坚守与诉求。
张洁这种悲天悯人的大爱关怀,在文本中首先体现在对弱小人群苦难命运的关注上。《无字》堪称一部“女性家族的苦难史”。墨荷一生为奴,唯一一点欢爱寄托在自己幻想、虚构出来的男人身上。叶莲子在生活打压下被迫“雄化”,用单薄的臂膀为吴为与禅月遮风挡雨。吴为一生找寻那个集理想人格与理想人性于一体的完美男人,最终不得不因现实而败下阵来。张洁以细腻的笔触写尽了女人们承受的疼痛与屈辱,给予女性命运深切的关注。这不单是作者个人经验的揭露,在更高的层面上,亦是社会某种集体经验的象喻。在此经验中,女性成了历史的蒙难者,她们的自我成长、自我救赎的过程也是重建良好的两性秩序的过程。
张洁在文本中描绘了前三代女性的婚恋悲剧,最终借禅月之口表达了对平等爱情的认知以及和谐两性关系的憧憬。与同时代其他女性文学作家不同的是,张洁并未将爱的关怀视角锁定在女人身上,在抨击文本中虚伪懦弱、残暴自私的男性形象的同时,她也给予了这些男性人格异化、人性嬗变的理解与同情。胡秉宸在感情婚姻中的步步为营、诿过自保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革命年代政治的异化直接导致了胡秉宸人格的异化,故在与白帆与吴为的婚恋战斗中,胡秉宸始终秉持着在政治斗争中的那一套,让婚恋关系充满了浓厚的政治硝烟味。张洁对男女两性命运的关注,上升到了对人性的拷问与命运的反思,这种俯瞰人世、深触人类命运的大爱,包含了张洁对建立一个社会公平、两性和谐的世界的美好诉求,这种诉求在一次次与现实碰撞后受到冲击,只会愈发强烈与深刻。
三、从建构爱到撕碎爱:外压与内抗
《无字》的出现,标志着张洁爱情理想的失落与彻底解构,人们不禁怀疑这个张洁还是当年那个对不能忘记的精神之爱无限咏叹的张洁吗?张洁在一次访谈中曾提到了自己转型的原因:“对理想、爱情之类的渴望支撑着很多人的一生。”所以,初入文坛的张洁总是带着清新、明朗的理想主义情怀,“但如果没有这种渴望和梦想以及它们的破碎,人生也就淡然而无趣了”[8]。转型后的张洁在创作中将自己真实的精神体验与现实创伤大胆地揭露出来,爱情经由“撕碎后再拼接”,逐渐显出原色。从最初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到《祖母绿》《方舟》,再到《无字》,鲜明地呈现了张洁创作风格的转变,同时也折射出这20余年来张洁苦痛难挨的情感经历。
文学艺术就是一场“白日梦”,而一个幸福的人是不会幻想的,只有那些愿望未能得到满足的人才擅长幻想。这恰恰说明童话作品的出现是源于生活的苦难。张洁从小喜欢读童话,她也曾表示生活是需要童话的。面对生活的百般刁难,作家与其他人的不同在于他们并非在作品中直接倾诉生活具体的艰难困苦,而是构造一个虚拟的世界来寄托自己的情感。弗洛伊德在《诗人与幻想》中论述诗人的创作动机时提出了“创作回忆说”,他认为作家的创作其实反映了他们对童年时期所受创经验的回忆,这种回忆引发的弥补愿望需要通过创作来完成。
联系张洁的生平,童年时期“无父”的情感体验影响了她的一生。“我出生一百天我父亲就抛弃了我。我母亲是农村小学教师,是她含辛茹苦一个人把我拉扯大的。”[9]“一般说来,我应该叫做父亲而又不尽一点父亲的责任的那个人,一家伙把我和母亲丢下,一个大子儿不给的岁月,我们全是靠稀粥度过艰难岁月。”[10]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张洁对父亲的怨怼与愤恨,即便人生暮年谈及父亲,也只平添了几分同情而罕见爱的成分。虽然情感上充斥着不满但爱与期望却是生生不灭的,现实中父亲的形象有多不堪,理想中自造的父亲形象就有多完美。父亲的形象在张洁心中早已积淀成为理想男性的化身,因而在张洁的童话世界里,一直苦苦追寻的不过是集理想人格于一体,能如慈父般疼爱自己的男人。她曾在随笔里写道:“我的先生是我的骄傲,我的爱。”[11]在她眼里,先生孙友余智勇双全,是自己内心的英雄,前期的张洁一直坚信只有这个英雄能将自己从没有父爱滋养的泥沼里拯救出来。
将张洁的童年经历与其作品中女主人公的经历作一比较,两相对照,我们会发现二者十分相似甚至相同。精神分析学认为,每部作品的主角归根结底是自我,文学表现生活的功能首先体现在作家从自己的人格结构出发,从而在自己的历史命运中体验生活。也许对于别的作家来说,这未必是定律,但对于身处20世纪90年代风靡一时的自叙性书写浪潮中,且有着类似童年经历的女性作家张洁来说,却并不令人奇怪。《无字》中的吴为同样缺少父亲的疼爱,再加上作家极强的幻想再造能力,使之在心中构建起了一个完美男性的形象。张洁心中所有关于好男人的形象,实则都是带着圣洁光环的‘好父亲’的形象的外化体现,代表着她心中的标准男人形象。吴为亲手给胡秉宸造了一个巨型光环,当光环黯然失色后,她才发现真正能交付生命去爱的却只有母亲,与母亲的共生固恋正是在真爱破灭之后才显示出唯一性与珍贵性。纵观吴为的一生,她就像是一只勤勉的蜘蛛,一直在“织网——网破——重织”的循环劳作中承受得到与失去的更迭变换。其实,张洁一生又何尝不是不断地在进行着梦的建构,就算失望,也依旧孜孜不倦。除了父爱的缺口,张洁自身的文学基因在她的创作中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受18、19世纪西方小说与苏俄文学的影响,张洁骨子里对骑士风范、英雄情结的膜拜与崇敬早已稳定成为其人格气性的一部分,这使得她对革命总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愫。当这种情愫与爱发生联系,便会被无限放大,爱恋对象就会被无限地神化与圣化。可以说,吴为爱上的并不是胡秉宸本人而是他身上的附属物——革命经历。这一点就足以让吴为缴械投降,至于其他残缺的部分吴为会不遗余力凭自己的幻想去修补以促成其形象的完美,这也正是由张洁苛求完美、挑剔要强的性格所致。张洁从小与母亲生活,母亲的脾气秉性、三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她性格的形成。即便生活拮据,但对生活中的细节母亲仍十分在意。在母亲的影响下,一直很注重生活品质的张洁在爱情里自然也臻于完美,过度苛求。她自己也承认文学创作于她早已不再是一种简单的社会文化事业而是个性的唯美追求,所以,在她早期的作品里,对爱的建构都是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也正是因为对爱所持的期待过高,后期才会有歇斯底里地挣扎与深深地失望。
现代社会是一个不断消解神话的时代,“随着我们对生活的理解在拓展和改变,神话也会改变。没有哪一种神话能够完全准确地阐释我们的真实存在。”[12]时刻关注着人生存境遇的张洁自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故而在《无字》中,她最终解构了自己笔下的爱情理想,消解了爱情的神性,让读者清晰地认识到现实中爱情的真相,也对两性关系进行重新审视与定位。重新把握两性关系,当然不是张洁的最终目的,她最根本的目的在于站在独立的女性视角,发出属于女性个体的声音,试图打破男性话语神话。
解构爱情是张洁在转型后创作的一个重要表现,这种解构来源于现实生活本身。张洁在与先生孙友余长达27年的苦恋中幡然醒悟:原来现实中的爱情是如此残破,令人心碎的。《无字》中吴为与胡秉宸婚恋的失败,其实是张洁在进入第二段婚姻后对爱情的回望,是在经历了两性纠葛磨难之后,重新审视自己曾经的盲目崇拜姿态,进而对其作出否定与反思,即通过对这场本就“不合时宜”的婚恋关系的描写,进一步彰显其对两性关系的深度思考。前期的张洁写爱情总是抱着少女般美好的幻想,笔下的爱情往往建立在平等、尊重、忠诚的基础之上,处处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唯美光辉;而到后期,很多评论家则认为张洁的创作由审美进入“审丑”阶段。于此,笔者认为所谓的审美与审丑二者并非完全对立,随着年岁的增长,生活经验的丰富,张洁对人性的洞悉有了质的改变,对两性关系的认识也更加深入,她深深地体会到男女两性在爱情中的不平等地位。
在《无字》中,我们很难看到男女两性在感情中维持平衡的关系,即便在最初关系建立时看似达到了平衡点,但究其实质二者始终针锋相对。吴为在爱情里的卑躬屈膝与胡秉宸对感情的政治性操控似乎一拍即合,但胡秉宸極度的大男子主义倾向却与吴为执拗要强的性格水火不容,这样的撕裂与纠缠,不可避免地终将酿成曲终人散的悲剧。透过吴、胡个体的差异,我们可以洞悉男女两性本身在对待感情上的差异。叔本华的话或即此理:“男人在天性上,恋爱时是善变的,女性则倾向不变。男人的爱情在获得满足后,便显著地下降。”[13]对男人来讲,女人只是他世界里的一部分,但女人却将男人视为她世界里的全部。从这个维度上讲,男女两性对对方的认知与界定就是不平衡的。这样的不平衡久之便会导致处于被压迫的一方进行反抗,吴为在这场感情拉锯战中醒悟并最终疯掉、死亡即是反抗男性话语的一种手段。
需要注意的是,张洁在后期很多作品中对爱情进行解构并不意味着她对爱情彻底死心了,那个理想主义者的背影一直没有远去。可以说,张洁在文本中表现对男人有多失望与仇恨,她在男人身上寄予的希望就有多大。对男人强力、压迫地位的不满与否定实则是变相承认女性的柔弱、屈从的本性。因而,在给予女性关切与同情的同时,往往透露出一种隐藏的男性观照视角。张洁自己对此也并不否认:“我觉得自己看女人常常是以一种男人的眼光或中性人的眼光。”[14]所以,她的作品里不乏雄性化的女性形象。这种形象的建构,看似是张洁想同处于弱势的女性地位决裂,寻求自身的独立,其实是偏离女性身份的一种表现。总之,张洁在文本中解构爱情,是为了呼吁人们关注女性在婚恋中的生存境遇,同时也寄托了自己对重建和谐两性关系的美好期望。

四、爱情与婚姻分离,灵与肉对立
三大卷的《无字》凝聚了张洁在几十年情爱炼狱中的心酸苦泪。从最初脑海中美好爱情理想的建构到亲历艰难曲折的情爱再到最后对情爱的看破与失望,张洁对婚姻与爱情的认识渐趋深刻,她向世界呐喊出属于自己的情爱宣言,进一步认清自己作为女性在两性关系中的独立位置,这一过程实际是“一个使女性的隐秘经验,包括历史经验、心理和生理经验,从一片话语的涂盖之下,从一片话语真空中发掘和昭示于世的过程”[15]。这一女性经验随着吴、胡婚恋悲剧的叙述而展开,文本中处处充斥着爱情与婚姻割裂、灵与肉对立的不平衡现象。
张洁一直认为婚姻是这个世界上最难解的谜,爱情与婚姻之间的关系也是人们千百年来未能穷尽的难题。在张洁的创作中,她始终都是歌颂爱情而拒绝婚姻的。她在伤痕文学浪潮期间创作的《爱,是不能忘记的》中的老干部和“我的母亲”钟雨为爱情死守20余年,《祖母绿》中的曾令儿“用一个晚上走完了一个女人的一生”,为了爱情可以背负政治罪名去边疆受苦。《方舟》中三位女主人公虽然一直想在社会中找寻女性独立的位置,但心中始终保留着一份对爱的期待。在张洁看来,爱情是美好且令人向往的,一旦进入婚姻,爱情就凋零了。所以,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文本中她都透露出对爱情的向往:“即便到80岁遇到倾心的男人,我也决不会犹豫,只可惜没有遇到罢了。”但远观爱情的确是甜蜜的,亲历却总是充满劫难的,张洁在亲身经历中感受到了爱恋的苦痛,这在她的随笔中可见一斑:“想当初为了嫁给先生,真是上刀山、下火海、波澜壮阔、九死一生。”[16]可见,张洁为了追逐爱情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待熬出头终于与先生修成正果,走入婚姻,张洁早已心力交瘁,对婚姻失望透顶。
文本中的吴为为了胡秉宸牺牲一切,走入婚姻后只10年便又分道扬镳。结束婚姻这一形式后,这一对旧情人才重燃心中爱的火苗。到底是婚姻埋葬了爱情,还是爱情腐蚀了婚姻?张洁在经历两次失败的婚姻后终于认识到:爱情只是一个短期性的行为,婚姻也不是一个很好的形式,结婚莫不如同居。这样些许偏激的话语背后是张洁对婚姻的失望与恐惧。对于张洁这样一个带有理想主义情怀的女性,对具有烟火气息的世俗婚姻失望是情理之中的事,她始终追寻着自己内心的那份真爱,但当爱以婚姻的形式固定下来后她又觉得怅然若失,丧失了爱的能力。可见张洁在创作中并非为夭折的爱情而难过伤心,而是为人类所不具备的爱的能力而哭泣。
谈到爱情与婚姻,必然就免不了牵扯到性,作为人类的自然天性,性是人类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亦是人性的试金石。但在张洁的创作中,她往往是回避甚至贬斥、丑化性爱的。她认为男女两性走在一起的前提是精神灵魂的契合,这种结合是过滤了性爱、肉体之亲的单纯的精神之爱。《爱,是不能忘记的》中的男女主人公的爱情完全是柏拉图式的,相爱20余年竟连手都未曾牵过。《祖母绿》中曾令儿为了还债交出自己初夜,在那个夜晚却宛如“一具还魂的僵尸”。《方舟》中的柳泉对丈夫关于性爱疯狂的渴求感到害怕与厌恶。同样,在《无字》中吴为也是一个丝毫不会调情的女人,在与胡秉宸做爱时眯着眼睛像一部X光机无所事事地观察着胡秉宸。无论哪一时期的作品但凡涉及性爱的描写,张洁都流露出极强的“厌性心理”。一方面,对性的厌恶其实是对男人厌恶的延伸。张洁恨透了男人,借用作家张辛欣的话说:“他们不是男人,不过有个阳具而已,我没有,但我比他们更像条汉子!”[17]无父的苦难童年与曲折感情的磨砺,让张洁柔弱的女儿之身多了些坚韧刚强的男儿气魄。其实,这种对男性的极度仇恨与批判是一种自我内心恐惧的掩饰与保护。张洁在爱情与婚姻中负伤累累,特别在第二段婚姻中,為了先生卷进离婚风波、政治浪潮,忍受了太多沉重的舆论压力,见识了人性的卑污与丑恶。当初的温情逐渐消减,残余的爱也转化为恨。
此外,中国传统的“贞洁观念”“禁欲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张洁。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性是不能言说、无比羞耻的东西,人们认为谈性就是一种耻辱。在两性关系中,女性贞洁的问题备受重视。张洁的很多作品都有涉及这个问题。一方面,张洁反抗男权话语的思想,让她不自觉地带着批判的眼光去看待女性的贞洁问题,她清晰地认识到这种贞操观念其实是封建礼教文化强加给女性的,其实质还是男女两性的不平等;但另一方面,张洁也难以摆脱这种观念对自己年长日久的熏染,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将其内化为自身理应遵循的准则。如此看来,张洁将灵与肉对立开来,歌颂、推崇纯洁的精神之爱,贬低、丑化肉体之爱与其意识深处的贞洁观念有很大关系,这也足见其性爱观的片面性与偏激性。性爱确乎是人的自然天性,真正恰当的两性之爱应该是灵与肉的统一,片面地强调哪一方都有失偏颇。
结语
《无字》是张洁拼尽全力,毫无保留地一次自我解剖,虽然一直以来饱受争议,甚至被人认为有借写作“泄私愤”之嫌,但不可否认的是,张洁这种敢于解剖自己、袒露灵魂的极限写作是值得钦佩、让人感动的。
联系张洁早期的创作,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其在性别视角上的超越与进步。性别叙事无法避免,女性主义文学不可避免地会隐蔽一些不利于自己叙述的事实,但在《无字》中我们可以看到张洁对男女两性关系进行剖析与反思时,不仅对女性受到男权压迫给予同情,也对女性骨子里的软弱与奴性进行了批判。于此之外,更为可贵的是,她同时也对受政治熏染而人格异化的男性给予了同情。
但张洁并未真正实现超越性别的写作,其笔下雄化的女性看似是对男权价值规范的反叛,实则是变相地认同男性话语的合理性。这样看来,张洁一直被笼罩在男权话语的阴影里,尽管很努力地挣扎却始终未走出男性话语的阴影。因此在创作中,她将男女两性的关系走向不再归因于具体的个人,而指向难以言说的命运。而命运带有极强的神秘色彩,男女两性关系的走向问题依旧未得到强有力的说明,这是其创作的局限所在。
参考文献:
[1][9]张英.真诚的言说——张洁访谈录[J].北京大学,1999(7):91,91.
[2][意]卡尔维诺.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M].杨德友,译.辽宁: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7.
[3][奥]弗洛伊德.列奥纳多·达·芬奇和他的童年的一个记忆[M]//弗洛伊德论美文选.张唤民,陈伟奇,译.北京:知识出版社,1987:85-86.
[4]范伯群.冰心研究资料[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42.
[5]陈志红.永远的寻求:一代人的精神历程——兼谈知识女性形象的形而上趋势[J].当代作家评论,1990(06):11-19.
[6]刘慧英.走出男权传统的樊篱——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批判[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60.
[7][美]R.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M].丁泓,余徴,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23.
[8][德]K.莱因哈特,F.麦耶尔.《明镜》周刊编辑部采访张洁记录.[M]//何火任编.张洁研究专集.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100.
[10]张洁.潇洒稀粥[J].收获,1993(1):97.
[11]张洁.吾爱吾夫[J].青年博览,1994(9):32.
[12][美]波利·扬—艾森卓.性别与欲望:不受诅咒的潘多拉[M].杨广学,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18-119.
[13]李瑜清编.叔本华哲理美文集[M].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7:43-44.
[14]陈纯浩.试论张洁小说中的女性意识[J].汕头大学学报,1995(4):16-23.
[15]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36.
[16]张洁.人家说我嫁了个特权[M]//《无字我心》.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184.
[17]张辛欣.撕碎,撕碎,撕碎了是拼接[J].中国作家,1986(2):195-201.
注 :本文以张洁单行本长篇小说《无字》(1—3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5月)为准进行原文引用及探讨。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3141500338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