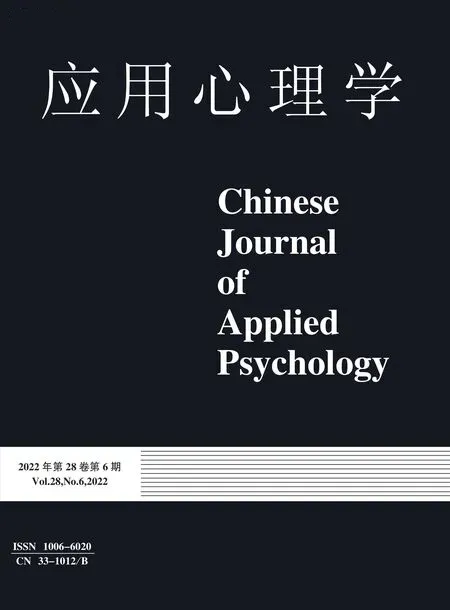悲伤的力度:案件受害者的情绪表达效应*
2022-03-07艾娟
艾 娟
(天津商业大学法学院心理学系,天津 300134)
社会生活中,人们对他人的情绪表达具有敏锐的感知,并会以此为依据来判断其说辞、行为等方面的可靠性。在司法领域内,案件受害者的情绪是否会对案件相关的非审判结果与审判结果产生影响也是一个颇受关注的话题(Ask & Landström,2010;Bollingmo et al.,2008;Bollingmo et al.,2009)。一般来讲,司法心理领域主要集中对受害者情绪及其影响展开研究。因为在犯罪证据不清楚的情况下,受害者情绪等外部信息就可能成为罪行认定的重要影响因素(Peace&Forrester,2012),受害者的可信度会随着情绪表达的变化而变化(Kaufman et al.,2003;Wessel et al.,2006)。可见,全面揭示案件受害者的情绪表达及其后果十分重要,一方面可以深入了解受害者情绪特点对诉讼价值实现的影响,另一方面可以促进司法实践重视受害者情绪对司法过程的“带节奏”作用,真切实现司法正义。
1 受害者情绪表达效应
当性侵案件中嫌犯与受害者的陈述相互矛盾且缺乏进一步的证据时,司法人员对该事件的判断将部分取决于他们对嫌犯和受害者的可信度判断,而可信度判断的重要标准就是嫌犯和受害者的自我表现方式或者自我表现风格(Vrij & Fischer,1995)。性侵案中受害者的自我表现风格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有些受害者在性侵后情绪表现得比较平静,有些受害者则表现出明显的痛苦悲伤。这些不同情绪表达影响到了观察者对她们的评价,相较于平静的受害者,悲伤的受害者可信度更高,也会让自己较少受到来自社会外界的二次伤害(Calhoun et al.,2011;Winkel & Koppelaar,1992)。后来研究者将性侵案件中受害者情绪表达或者展现情绪性行为特征影响观察者对其可信度感知的现象,称为“受害者情绪表达效应”(emotional victim effect,EVE;Ask et al.,2010)。这种效应在很多性侵案件中得到了印证,相关研究沿着两条主线展开。
首先是探讨受害者情绪的“有无”对可信度的影响。表现出情绪的受害者(相对于那些没有任何情绪表现的受害者)通常被认为更加可信(Bollingmo et al.,2008)。强奸案件中的女性受害者、性骚扰案件中的儿童受害者(Landström & Sara,2013)以及性虐待案件中的儿童受害者(Golding et al.,2003)等系列研究均发现,悲伤受害者要比平静受害者更具可信度(Golding et al.,2003;Landström et al.,2013;Wessel et al.,2013)。在案件陈述内容一致的情况下,声泪俱下的受害者比情绪平静的受害者,让人认为其说辞更可靠,对其给予更多的同情,认为其在案件中的过错责任更小(Ask et al.,2010;Bollingmo,et al.,2009;Golding et al.,2003;Hackett et al.,2011;Kaufmann et al.,2003;Rose et al.,2006;Sperry,2009)。
其次是关注受害者情绪表达是否“合适”对可信度的影响。Vrij等(1997)研究了受害者悲伤和愤怒两种负面情绪产生的影响。他们要求英国大学生阅读一段关于强奸案的简短描述,然后观看警方采访受害者的两分钟视频片段。结果发现,男性参与者认为悲伤的受害者比愤怒的受害者更痛苦、更可信。Kaufmann等人(2003)通过呈现给参与者强奸案中受害者悲伤、中立、快乐三种不同情绪,结果发现,“适当”(悲伤)情绪条件下的受害者可信度最高,“不适当”(快乐)情绪条件下的受害者可信度最低。即使对儿童证人的可信度也显著受到其表现出的情绪影响。参与者在观看警察采访一名11岁儿童的录像(儿童展示出愤怒、悲伤、中性和积极四种情绪)之后,对儿童可信度的判断明显受到了情绪的影响,相比悲伤情绪,愤怒情绪与积极情绪会显著降低儿童的可信度(Ellen,2015;Wessel et al.,2013)。
司法领域的不同从业群体比如警务人员(Bollingmo et al.,2008),警察培训生(Ask et al.,2010)以及陪审员(Golding et al.,2003)的看法也相对一致:受害者的悲伤情绪是他们判断受害者是否可信的重要指标之一(Lens et al.,2016)。受害者的悲伤情绪还会间接影响到案件相关的审判结果,比如,会影响到司法过程中对犯罪性质的判断与案件裁决(Bollingmo et al.,2008);导致法官作出基于情绪而不是做出完全基于犯罪事实的惩罚决定(Mcgowan & Myers,2004);会导致陪审团对受害者的责任归因明显降低,建议给予嫌犯更长的刑期(Wevodau et al.,2014);尤其是当受害者的情绪反应与遭受到的伤害严重程度一致时,陪审员会对嫌犯给予更高的惩罚性评级(Rose et al.,2006)。
诸多研究达成的共识性在于:相比没有情绪(比如平静、麻木)或“不合适”情绪(比如愤怒、快乐)的受害者,悲伤的受害者会唤起观察者更多的信任。悲伤情绪作为受害者的核心情绪特征在受害者情绪表达效应中得到较高的关注,因此,受害者的悲伤情绪在对其可信度判断方面具有强劲的影响力度。
2 受害者情绪表达效应的解释
“冷认知”与“热情感”两种解释对此作出回应。其中,“冷认知”涉及的是对受害者角色的期望信念,受害者悲伤情绪表现更符合观察者对受害者角色的期望;“热情感”关注的是个体悲伤情绪表达的功能性,悲伤情绪更容易引发他人的同情(Ask et al.,2010;Ask et al.,2012)。
2.1 对受害者角色的期望
角色期望假设认为,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人们形成了很多用以应对社会判断的认知模式,内化了对“个体受到伤害后应该如何表现”的观念,当处于一定的情境中时,这些观念会自动启动并影响人们对受害者角色是否恰当的认知判断(Landström et al.,2015)。一般来讲,悲伤痛苦的情绪表现是与受害者角色期望一致的,这种情绪就是“合适的”(Kaufmann et al.,2009)。而当受害者的情绪表现与既有的受害者角色期望不匹配时,观察者就会产生明显的期望违背体验,降低对受害者的总体评价(Ask et al.,2010;Lens et al.,2014)。
受害者表达的悲伤情绪并非越多越好,要在一定时机恰当地表达自己的情绪以“扮演”好受害者角色。悲伤的强度和持续性要与受到伤害的严重性相一致(Rose et al.,2006),当受害者表现出过度的、与伤害程度不匹配的悲伤情绪时,观察者也会体验到较高水平的期望违背感,降低对受害者的信任度(Lens et al.,2014)。在特定情况下,受害者应该表达什么样的情绪、表达到何种程度才算“合适”,更多反映出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对受害者角色的刻板印象,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期望偏见。大多数人逐渐形成并内化了受害者“正常反应”的刻板观念,那些不符合角色期望的“异常”受害者,很可能会因为他们违反了既有的角色期望而遭到一些不利的“对待”(Ellison &Munro,2009)。
2.2 对受害者情绪的心理推论
受害者的悲伤情绪作为一种刺激引发了观察者的同情进而导致“偏向于”受害者的判断和行为(Ask et al.,2010)。人们对于受害者角色的认知集中关注其无辜、脆弱、经历伤害和无助等方面,并会表达出更多的同情(Lewis et al.,2019)。大家更愿意为一个确定的受害者施以帮助,而识别受害者的明确线索则来自于其表现出的情绪特征。如果受害者可以通过情绪表现得到识别和确定,那么对他们的同情也会随之增加(Kogut&Ritov,2010)。因此,当受害者的消极情绪(如悲伤)更容易被观察到时,就会更多地将注意力聚集在受害者身上,激发出更多的同情,利用较少的认知资源去思考事实因素(Ask et al.,2010)。
另一方面,情绪表达在社会互动中具有重要的信号作用(Hareli&Hess,2012)。不同情绪的表达影响人们对表达者做出何种回应(Van Kleef et al.,2011)。当人们评估受害者是否需要社会支持及其对社会支持的需求程度时,受害者的情绪表达发挥着重要的功能。感知到受害者悲伤会对受害者产生更多的同情,增加人们提供帮助的趋势(Hendriks et al.,2008)。受害者表达出的悲伤情绪可以看作是一种“说服性信息”,更容易启动他人的助人倾向,促进人们更积极地帮助那些处于不利情境中的个体(Campbell & Babrow,2004)。当然,观察者会依据受害者不同的情绪表现对其心理需求做出不同的判断。研究发现,性侵案件中悲伤的女性受害者最可信,愤怒的受害者最不可信(Bohner&Schapansky,2018)。相比愤怒的受害者,观察者倾向于认为悲伤的受害者更需要社会支持。这是因为,不同的情绪会让观察者在两个维度(温暖和能力)上对受害者的特点进行认知推断(Cuddy et al.,2006)。表达悲伤而非愤怒的男性(而非女性)更需要社会支持,表达悲伤(相对于愤怒)的受害者更温暖。愤怒代表受害者是有能力的、有强大主导地位的,而悲伤则更容易让人感到其柔弱(Wrede et al.,2015)。其实,在受害者情绪功能方面的探讨需要翻越“同情心”的藩篱。受害者的悲伤也有可能引发观察者同情之外的其他反应,比如愤怒,厌恶等。在家暴、成瘾等案件中,悲伤的受害者可能会引发观察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愤怒以及“自作自受”的厌恶,而愤怒、厌恶如何影响观察者对受害者的可信度判断还缺乏深入的探讨。
2.3 道德领域的整合性解释
案件发生后伤害是必然存在的,道德判断由此发生,伤害与道德自然地融合在一起。二元道德理论(dyadic morality)指出,道德判断实际上是一个人的不道德行为故意给第二个人造成痛苦的过程(Gray et al.,2012)。受害者的在场与确认就很关键,他们对伤害造成的痛苦进行表达以彰显出其较高的感受性(Gray & Schein,2012),而当个体感知到受害者的高感受性特征,则表现出对他们更高的同情与信任(邵晓露,2019)。二元道德理论强调对伤害认知模式激活,源于不道德行为(如谋杀、强奸、攻击和虐待)中存在的故意伤害、源于受害者的痛苦情感力量,以及人们对伤害与共情的关注(Schein & Gray,2015),在广泛的道德层面上对受害者情绪表达效应提供了更具整合性的解释。
基于道德角色理论(moral typecasting)认为,道德和不道德的行为通常需要侵害者与受害者两种角色来承担(Gray&Wegner,2009)。个体只能成为侵害者与受害者中的一个角色,即强奸犯绝不可能是被强奸的人。当伤害事件发生后,角色塑造的过程就是要区分侵害者与受害者,二者相互排斥。鉴于受害者痛苦悲伤的表现,使得他们很难被视为侵害者,反而更强化了他们作为受害者所遭受的痛苦以及可能需要得到的帮助(Gray et al.,2011)。道德角色理论与角色期望假设存在相通的地方,即强调受害者角色应该具有相应的情绪行为表现。
3 受害者情绪表达效应的影响因素
对强奸案的既有研究进行元分析后发现,成年女性受害者的痛苦情绪显著增加其可信度,其影响为小到中等且这种影响是比较稳健的,并不会受到案件中受害者痛苦呈现方式(书面的或视频的)的显著影响(Nitschke et al.,2019)。总体来看,来自观察者、受害者以及其他因素会影响到受害者情绪表达效应的实际效果。
3.1 观察者因素
从观察者相对稳定的心理特征来看,首先,对受害者的角色期望程度存在着个体差异性。对受害者角色的期望水平差异作为先在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观察者对受害者及其情绪表现的判断是否符合预期,进而影响对受害者的可信度感知,那些对受害者情绪表达具有强烈期望的观察者,对悲伤受害者的可信度判断更高(Louisa et al.,2010)。其次,信息处理方式存在不同。有的个体偏好采用经验加工,一种高度情感导向的、基于过去经验的自动化处理方式;有的个体善于采用理性加工,体现出分析性、逻辑性、反思性的特点。经验加工者更容易受到法律外因素的影响,更依赖于直觉而不是基于事实做出判断(Gunnell & Ceci,2010;Lieberman et al.,2007)。当受害者表现出高度的情绪煽动性时,采用何种信息处理方式就会对罪责判断产生重要的影响(Klippenstine &Schuller,2012)。尤其是当陪审员面对模棱两可的强奸案件进行判断时,如果受害者没有表现出预期的或适当的情绪,就会降低其可信度(Peace,2014)。再次,共情水平是不同的。对强奸受害者的共情越高,就越相信受害者,越倾向于对犯罪嫌疑人进行罪行指控(McCaskill,2010)。不同性别的个体面对同样的受害者产生的心理反应不同,相比女性,男性对受害者陈述内容的可信度评价更低(Peace&Forrester,2012),而女性对受害者的共情水平则显著高于男性(McCaskill,2010)。个体对受害者的共情水平存在差异可能是因为与受害者“不够熟悉”导致的,如果让参与者长时间、更深入地接触受害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他们对受害者的同情(Barab&Alexis,2013)。
从观察者具有变化性的特征来看。首先,来自职业经验的影响。与没有相关司法经验的人相比,专业从业者(例如警官或法官)更熟悉案件判断的背景,更愿意在判断受害者可信度时考虑一些复杂的案件信息(Reinhard et al.,2012)。相比非法律专业的人员,法律专业的学生会在信息处理时质疑并减少受害者情绪举止对其可信度判断的影响,保持他们的判断不受外部因素的影响(Bohner&Schapansky,2018)。对那些经验丰富的法庭法官而言,受害者的情绪表现对可信度判断没有显著的影响(Wessel et al.,2006)。但不同的声音认为:即便是警察和检察官等也可能会将受害人的情绪作为判断其可信度的信息。他们在判决案件时会依赖直觉推理,对那些同情或与自己具有共同人口学特征的受害者更有利(Nitschke et al.,2019;Rachlinski &Wistrich,2017)。其次,观察者的认知负荷水平会增加受害者情绪表达效应。如果让参与者在观看受害者情绪表现的视频前,先去记忆一组8位数的数列,观看视频结束后要求他们立即报告记忆的数列,会发现参与者的认知负荷增加使他们表现出更明显的受害者情绪表达效应,更相信悲伤受害者的陈述(Ask et al.,2010)。时间压力下个体更多依赖于简单的认知策略、情绪反应以及刻板印象(Gilbert,2002)。来自受害者的情绪是一种非常容易识别且能够轻松感知到的线索(Ask et al.,2012),个体在认知负荷较重、认知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倾向于捕捉和采用外部可见的、轻而易举能够获得的情绪信息线索,或者采用个体的内部观念进行相对省力、简单的推断,决策质量和决策满意度降低(车敬上等,2019)。因此,要警惕高强度、高压力等导致的高水平认知负荷,这会提高个体对受害者情绪的敏感性与易得性,高估受害者的可信度。
3.2 受害者及其他因素
受害者情绪表达效应不能有效适用于男性受害者。相比女性,男性受害者表达的悲伤情绪并不能对其可信度增加带来明显的益处(Landström et al.,2015)。基于性别期望假设,悲伤情绪表达的“特权”往往与女性角色建立了更加稳定的联结,假如男性表现出明显的悲伤则很容易颠覆社会对男性的既往认知,违背对男性角色的期望,对其可信度产生负向影响。除此之外,男性受害者表达悲伤或者愤怒还可能会让人对其能力水平进行消极归因,认为其软弱无能,对其产生厌恶或愤怒,使得其可信度以及判罚结果更糟糕。
案件审判过程中的因素研究主要是从如何改善这种效应为切入点的。比如,是否存在小组讨论会影响对受害者的可信度判断。没有经过陪审团讨论而让陪审员独立判断受害者的可信度与犯罪嫌疑人的罪行时,受害者的情绪强烈地影响到了判断倾向,而经过陪审团讨论则显著削弱了受害者情绪的影响,情绪受害者效应借由小组讨论得到了明显的抑制(Dahl et al.,2007)。其次,司法过程中具有“前置提醒”也很重要。如果明确告知观察者,受害者的情绪特征不是判断其可信度的依据,可以有效减少受害者情绪的影响(Bollingmo et al.,2009)。
4 受害者情绪表达效应的学术与现实回应
受害者情绪表达可能会使司法审判存在潜在风险(Myers et al.,2018)。因此,从学术层面上全面探讨受害者情绪表达效应十分必要。而从司法实践来看,既要充分肯定受害者表达情绪是其个体特性表达的权利,同时也应该准确评判这些情绪可能产生的司法功能。
4.1 学术回应
首先,关注受害者情绪变化的复杂影响。目前对受害者情绪的划分或者被简化成“有或无”的二元分离状态,或者被认为是“非此即彼”的情感独立状态,由此忽视了受害者情绪变化对其可信度产生的影响。受害者可能会在不同的时间节点上表现出情绪的动态变化,需要遵循受害者可能产生悲伤、愤怒、恐惧等情绪变化的特点来探讨受害者情绪表达效应。既有研究发现,受害者的情绪反应随着时间推移影响观察者对案件及犯罪嫌疑人的看法,比如受害者在两个时间节点上(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与审判期间)表现出前后一致的情绪,观察者对他的可信度会更高,更有可能对犯罪嫌疑人做出有罪判决(Klippenstine&Schuller,2012)。可以推断,随着案件时间的变化,受害者的情绪表达方式、内容和强度都会发生一定的变化,持续时间过长的案件诉讼很可能会因为这些变化而产生不同的影响,这需要得到进一步关注,以期为司法实践提供深入的思考。
其次,关注观察者不同情绪相互作用及其对认知结果的影响。有研究指出,愤怒和厌恶的结合可以预测道德上的愤怒,而道德愤怒对法官的有罪判决信心产生重要的提升性影响(Horberg et al.,2011;Salerno&Peter-Hagene,2013)。通常来讲,法官等司法人员对案件产生的体验往往是混合的,既有对犯罪嫌疑人的愤怒,也有对受害者的共情,它们对受害者情绪表达效应产生影响的路径机制值得探讨。目前的研究发现,在性侵案件中,受害者的高情绪表现(或被告的低情绪表现)都会增加受害者的可信度,造成对被告更大比例的有罪判决。而当被告具有高情绪表现时,情况正好相反,他被认为更可信,更有可能说真话(Peace,2014)。可见,来自受害者与犯罪嫌疑人的每一种情绪信号的释放都可能影响到观察者如何加工、推理、决策,探讨观察者是如何加工受害者与犯罪嫌疑人的情绪进而影响到其判断就变得非常重要。
再次,结合案件特点研究受害者的情绪表达效应。以往研究通常以性侵案件中的女性为重点或者以虐待中的儿童为对象,基于这类案件展开对受害者情绪表达效应的研究,具有一定的“便利性”,比如鉴于性侵案件的隐私特点可以较少关注伤势程度,而更注意识别受害者的情绪反应。但受害者情绪表达效应的研究不能仅局限于性侵案件中。比如,家暴案件进入诉讼阶段之后仅凭陈述、证人证言等而难以形成证据链时会面临取证难的问题(郝登荣,2016)。对于这一类信息不确定、证据相对缺乏的案件受害者(家暴、虐待、霸凌等),其情绪表达特征以及功能也需要得到关注。因此,充分结合案件的案情特点(比如案件严重程度)分析受害者情绪表现对可信度判断与罪责决策的影响,更体现出司法过程的全面性与严谨性。
最后,扩展受害者情绪表达效应的影响因素研究。一是观察者的人格特征、公正世界信念、个人背景等因素还有探讨的必要。比如,精神变态人格特征广泛存在于人群中,表现出冷酷、缺乏同情心等特点(Blais & Forth,2014),他们不容易产生共情,对犯罪嫌疑人的量刑结果更严重(Johnson et al.,2002)。那么,他们对受害者情绪及其功能的认知又是怎样的呢?另外,公正世界信念会影响个体采取何种策略来看待受害者及其情绪。当采用不同的策略维护自身的公正世界信念时,贬损或者污名化受害者的个体可能会对受害者的痛苦情绪及其可信度产生不利影响(Gaucher et al.,2010),认为受害者应该自作自受。个人经历也需要考虑。研究发现,在与性别相关的案件(如性骚扰)中,有女儿的法官比没有女儿的法官,支持女性受害者的可能性高出7%(Glynn&Sen,2015)。二是加强对受害者因素的考量。受害者的年龄、种族、职业、心智特征等都可能在受害者情绪表达效应中产生影响。研究发现,当感知到受害者的高感受性特征时,相较于主体性特征(比如积极反抗),会表现出对受害者更高的同情与信任(邵晓露,2019)。这一研究从道德判断的视角出发,为深入探讨案件受害者特征对可信度的影响提供了新的思路。因此,有必要采用整合性的思路,深入探讨不同主客体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它们共同影响受害者情绪表达效应的复杂机制。
4.2 现实回应
首先,需要有效辨识和判断受害者基于案件的真实情绪。警惕受害者的伪装情绪影响到对犯罪性质的判断与案件裁决(Guri&Bollingmo,2007)。受害者的伪装情绪有时会被策略性地应用从而达到个体特定的目的(冯柔佳等,2020)。要“读懂”受害者的情绪及其真实性,构建必要的专家与技术介入机制,对受害者的情绪进行全面评估,减少情绪对司法判断的影响。
其次,要加强受害者情绪表达效应的司法规制。国外这一类研究多数基于英美法系的特点采用陪审团范式,使用了简短的受害人证词摘录或者视频作为研究材料,却没有明确提及案件的审议活动,这就意味着审判过程未得到检察官审查或辩护律师质证。既有研究发现,受害者情绪表达效应可以通过陪审小组审议得到调节(Dahl et al.,2007)。质证活动可以通过突出不符合受害者刻板印象的受害者行为来降低司法人员对受害者可信度的过高判断,建议司法实践纳入更多审议程序环节,减少或者规避受害者的情绪表达效应。
最后,利用智慧司法模式来减少受害者情绪表达效应是一种有益的尝试。近年来,部分司法审判借助现代化智能手段进行。与视频呈现相比,现场审判调动了参与者更多的感官以接收与加工受害者表达的信息,受害者的情绪更容易被感知,引发参与者更多的情感参与,对受害者的可信度判断产生影响(Landström et al.,2015;Landström et al.,2018),线上审判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对受害者情绪的现场感知与卷入,保证法庭审判集中于实质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