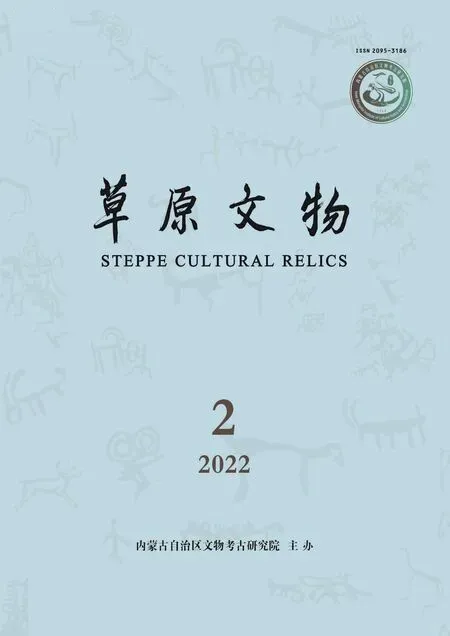试论北方凿刻类岩画的岩石选择
2022-03-06丁升鹏
丁升鹏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对于岩画的记载最早见于战国著作《韩非子》:“赵主父令工施钩梯而缘播吾,刻疏人迹其上,广三尺,长五尺,而勒之曰:‘主父常游于此’”①。此外,在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中亦记载有“河水又东北历石崖山西,去北地五百里。山石之上,自然有文,尽若虎马之状,粲然成著,类似图焉,故亦谓之画石山也”②。我国近代对于岩画的研究始于20 世纪初,时至今日,对于岩画的研究仍在进一步深化和扩展中。中国目前发现岩画的地区,范围涵盖巨大,遍及一百个以上的旗县。岩画按照类型可分为凿刻岩画与彩绘岩画两大类。其中,凿刻类岩画又可细分为磨刻、划刻、敲凿三类。根据目前的岩画调查数据来看,凿刻类岩画数量较大,主要集中在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青海、西藏等省(自治区),整体呈现“东北—西北—西南”的半月状分布,因为其岩画特征具有相似性,且区别于其他岩画体系,有学者将这一区域岩画统称为“中国北方地带岩画”③,或者“北方体系”④。该岩画带基本上分布于游牧、畜牧业发展地域,在历史上曾有较多少数民族及部落聚居生存,因此岩画与游牧民族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它不仅仅是游牧民族的艺术作品,其中更包含着游牧民族的文化信息,诸如原始的宗教认知、战争、生业等。
目前,岩画的研究受到技术的局限,测年仍是比较困难的,因此对于岩画的研究也较多倾向于图像的释读、典型岩画的相对年代分析以及岩画本身所包含的精神文化的研究。但是研究者们在研究岩画的时候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图像上,忽略了画面的载体——岩石。在诸多有关于岩画的论著中,对于岩石的表述只有寥寥几语,多从质地颜色入手,没有进一步的研究,似乎显得岩画的载体“无足轻重”。但是如果详细研究就会发现“载体”亦包含有许多信息,从北方地带岩画的发现来看,其岩画的载体反映有一定的选择性,并非盲目进行凿刻。《原始思维》一书提到:“一幅特制的图画,画在某个地方,什么意义也没有;但如果它是画在其他地方,他又会完全确切地告诉你,这图画应当表示什么意思”⑤。根据笔者实地走访调查以及相关文献资料记载,岩画地点的命名以及资料上对岩画点的概述,较多出现“黑色”“褐色”相关字眼,例如“黑石峁岩画”“黑山岩画”“大黑沟岩画”等。岩石颜色的论述也有较大相似性,黑色、褐色岩石作为其岩画载体。笔者认为,岩画载体选择黑色岩石有其现实因素、宗教影响以及族群崇拜这三个方面原因。
一、现实因素
(一)岩石因素
无论是文字还是画,都需要载体承载。而载体又会受到人们生产力水平的影响和制约。在纸没有发明以前,先民选择用帛和竹木简作为文字和画的载体,岩画亦是如此。古代游牧民族自身独特的生业方式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从目前已发现的大量凿刻类岩画来看,常见的岩画载体有砂岩、玄武岩、片麻岩、花岗岩等,其中砂岩占比较大。岩画载体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反映凿刻岩画主体的生产力与生产工具,上文所提到的岩石莫氏硬度差异较大,从4~7 不等,这就意味着使用石质工具进行凿刻的岩画所选择的岩石载体硬度不会太大。相较于花岗岩和玄武岩一类硬度较大且敲凿费时费力的岩石,结构较为疏松的砂岩则会更受青睐。而当游牧民族的凿刻工具发展到使用金属器物时,对于凿刻岩画的岩石就有了更多的选择,借助金属工具的硬度与韧性,岩画的载体也就变得多样化。
此外,上述岩石中,玄武岩、片麻岩石材通体为黑色,在此类石材上凿刻岩画,初期会形成白色凿刻痕迹,系石材表面被破坏残留的石材粉末,内里石质与外表所受外力作用形成的岩晒表皮颜色差异较大,故显色新且白。随着时间推移与内外力因素影响下,岩画凿刻痕迹会逐渐风化变黑,与岩石颜色趋同。而砂岩、花岗岩由于岩石表里颜色存在差异,当打破黑褐色岩晒之后显现内里的白色或黄白色石色,可以形成相较于其他岩石更为清晰的反差色,而这种反差色也会因为岩石硬度、凿刻深浅的影响而随着时间推移缓慢变色。根据目前已知的凿刻类岩画,人面像岩画是较早出现在岩画内的题材,阴山岩画中的人面像岩画仍然能够较清晰地看出岩画与岩石表面之间存在的色差。这一情形表明,在岩石表面形成稳定的黑色氧化层,其至少需要数千年甚至近万年的时间。这样看来,古人在岩画凿刻时是有一定的选择性的,体现了原始的色彩视觉冲击,使画面更明显,更富有特殊意义。
(二)岩石选取的范围
岩画是人类的艺术,必然需要人去完成,北方岩画带的产生与游牧民族离不开关系。游牧民族的生业方式决定了其生存和发展离不开水源和草场。史书中对于游牧民族常使用“逐水草而居”⑥这样的描述。但是随着近现代考古学的研究发现,游牧民族也有较为稳定的居所,以及一定规模的墓葬⑦。贴切点说,应该是一种“季节性转场游牧”⑧。这从侧面说明史料记载亦有疏漏。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岩画的凿刻亦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若凿刻内容多范围大,时间可能会更长,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不足以支撑其完成规模庞大的岩画凿刻。经常性地迁徙,不论是原始崇拜或是后来的宗教影响,失去了信仰和崇拜的族群,岩画也就失去了凿刻的意义。从发现岩画的地点可以看出一些规律:岩画的发现地点周边常存在较为稳定的水源。根据实地考察,可依据水源类型分为两类:一类为流域类型,岩画多分布在河流两岸以及周边山崖之上;另一类为泉域类型,该类型的岩画受到水源地条件限制,多分布在山区丘陵以及沟谷坡脚等较易出现泉的地区。此类型岩画凿刻时受到水源地的地形和岩体限制,甚至出现有目的性的找寻水源地一定范围内黑色岩石凿刻的情况。但是也不排除随着时间变化泉水枯竭,在此类地方仍然有岩画发现,或许从地理环境以及地名中可窥视一二。
二、宗教影响
约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原始宗教便已经产生。原始宗教信奉万物有灵观念,与人类息息相关的大自然便成了原始宗教最理想的崇拜对象。此时的人类对于自然的改造能力仍然很弱,过着采集狩猎生活,自然的威力让他们恐惧又崇拜,自发产生的意识又无法对其进行解释,于是将其归因于“神灵”“精灵”,拥有着无穷的威力。人们信仰、敬畏、崇拜它们,由此催生了大量的神灵,也同时催生出了一群专司沟通天地鬼神的巫师,这种原始宗教是全球性的,有着许多共性,因此相关学者将其统称为“萨满教”。近年来对于岩画的研究,有不少学者提出岩画中的人面像题材很有可能就是巫师的形象,也就是萨满⑨。也有学者认为,岩画所凿刻的图案,更多的是一种巫术行为,例如凿刻动物岩画,并在其身上凿刻箭矢,对猎物施加巫术影响,以此来影响狩猎的成功率⑩。岩画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与宗教仪轨、万物有灵论或原始萨满紧密相连。张光直先生曾提出,中国古代文明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萨满式文明,在今日大量的岩画资料以及考古实物资料的出土,似乎印证了这个观点。原始萨满教思维中,天地山川百兽都拥有着神秘力量,信奉并且崇拜它们,并通过“媒介”就可以获取到这种力量。在这种思维作用下,黑色崇拜以及山石崇拜,成为了岩画岩石载体选择的诱因之一。
(一)萨满教的黑色崇拜
我国北方游牧部族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构成了我国绚丽灿烂而又多元化的历史。北方游牧部族受自然环境的制约,发展游牧畜牧业,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低下,部族势力也时有变化,因此除了南下中原之外,各部族之间的战争也很频繁。万物有灵的原始自然崇拜基础以及地缘关系的接近,加之较为原始的婚姻制度以及血缘性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产生一种被普遍广泛接受的宗教再正常不过。或许各部族崇拜的图腾不尽相同,但关于原始宗教普适性的内容应该是相同的,即对万物有灵观念的信仰。在中国历史上十分活跃的匈奴、鲜卑、高车、丁零、突厥、肃慎、契丹、女真、高句丽、蒙古、满族等北方民族历史上都信仰过萨满教⑪。时至今日,在我国北方少数民族诸如蒙古族、满族等人群中仍留有萨满教遗风。
原始的萨满教形式仪轨如何,现在已无法再现,但是通过大量的民族学资料可以帮我们还原原始萨满教的一些信仰行为。蒙古族信仰萨满教有着悠久的历史。元朝时,八思巴大师将喇嘛教传入蒙古,对本土蒙古萨满产生了巨大冲击,一部分萨满接受藏传佛教改造,被称之为“白萨满”,而拒绝接受藏传佛教改造的则被称之为“黑萨满”,黑萨满是较为原始的传统萨满⑫。对于黑白萨满的区分,则是由于两类萨满巫师所穿法衣以及所信仰的神灵不同,白萨满身着白色法衣,崇尚白色;黑萨满则身着黑色法衣,崇尚黑色。对于黑白萨满的论述与研究,在米尔恰·伊利亚德的著作中提到:“布里亚特族提及了‘白萨满’和‘黑萨满’,清楚地描述了二者的区别,白萨满与天神有关,黑萨满与神灵有关。他们的服饰也不同,前者穿白色的衣服而后者穿黑色的衣服。白萨满信奉天神,天神很少参与人类的事情;而黑萨满则信奉‘无极全能神’‘他是天空中唯一一个落入这个充满眼泪的苦难人间的能力超凡者……是他赐予人类火,创造萨满,教萨满战胜不幸……’”⑬。布里亚特人为蒙古人的一支,也是保留原始萨满教内涵较多的一支。除此之外,蒙古科尔沁博也有着悠久的尚黑礼俗⑭,为原始萨满教尚黑传统提供了佐证。
西藏在金属时代所产生的宗教信仰为原始苯教,后续发展为雍仲苯教。其中原始苯教时期也有着与萨满教相似的万物有灵观念以及入迷术,因此有学者也将原始苯教纳入了泛萨满教体系内⑮。从现有的苯教文献以及巫术仪轨中仍可窥见一些苯教的尊黑因素。苯教有一种黑色禳解仪式,用以祭祀土地神萨拉,因此黑色也就成了土地神的代表色⑯。藏族苯教存在一种防雹巫术,巫术仪轨进行时要身穿黑色咒衣和黑帽,借助与本尊神身体颜色相近的衣物,能够更好地借助神灵的力量⑰。因此尊崇黑色也体现对某些苯教神灵的尊崇与信仰。从蒙古族遗留的萨满教习俗以及现存西藏苯教的相关内容来看,原始萨满教保留有较多黑色崇拜内容。
萨满教崇尚黑色,还有传统宗教观念中的“二元对立”思想的影响。所谓二元对立思维,是指“相反的两方之间的关系为对抗和对立”⑱。二元对立思维最为基本的概念就是黑与白、光明与黑暗的对立关系。在岩画中似乎更能体现这一观念:选取表面为黑色或者褐色的岩石进行凿刻,凿刻结束后形成的图像显现出白色,这种“破黑显白”的岩画凿刻行为恰好符合了萨满教最为原始的“二元对立”的传统思维观念。
(二)原始宗教的山石崇拜
除了对黑色的原始崇拜,在万物有灵观念影响下,萨满教对山石也有着崇拜行为,这点可以通过原始社会人类的生产生活探析缘由。原始人类多居住于洞穴之中,是山给予了人类居住之所,使得人类得以延续,躲避食肉动物的攻击。获取肉食则必须通过狩猎获得,而作为被狩猎对象的食草动物则大多隐匿于山林中。人类对于山林提供食物和住所心存感激,而无法战胜的凶猛食肉动物则就成了山神的化身。山的亘古不变,以及对于老虎等食肉动物的恐惧,一系列复杂的情感统一并转化后,就产生了原始的崇拜和信仰。例如阴山岩画中的“群虎图”,古人把老虎当做山神的化身,用以祭祀,老虎线条细腻流畅,可以说明在凿刻时是带着十分虔诚的信仰进行的⑲。
在萨满沟通天地时,常常把山当做地到天之间的桥梁。天空直接的、自然地解释了自己的无限高远,解释了神性的超验性。先民选择高山凿刻岩画,其一是因为高耸的山峰具有超然的力量与存在,山是神的家园,在那里深奥的知识可能通过仪式的剥离获得⑳。借助宗教仪式攀登山的过程中,人或者巫师萨满已经停止了作为一个人的存在,以某种方法,分享到神圣的状态。在众多关于萨满教的记载中提到,萨满可以通过爬这个桥梁,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去。另一方面,山峰的高耸使得先民相信山被授予神秘的权力:在干旱的土地上,它们往往是雨的来源。在暴雨即将来临之时,黑云没过山峰,雷雨与若隐若现的山峰就构成了具有神圣性和超验性的神圣空间。这种天地相交的特殊表象即是一种神圣表象,表明神在这一刻的圣显。雷雨时的山峰超越了世俗时间和空间局限,并且会在雷雨来临之际神圣化。寻常天气下的山峰是世俗的,雷雨激起了山峰神圣的表征㉑。因而萨满或者巫师就会更加青睐这里,在这些山峰所在空间的岩石上凿刻岩画,增强岩画的神圣性。史料记载,匈奴、乌桓、蒙古族皆有山崇拜以及祭山行为。匈奴以阴山、杭爱山为“神山”,乌桓以赤山为神山,“贵兵死,敛尸有棺,始死则哭,葬则歌舞相送。……特属累犬,使护死者神灵归乎赤山”㉒。赤山在辽东西北数千里,如人以死之魂神归泰山地。蒙古族则以不峏罕山作为远祖之地加以祭祀㉓。辽契丹人有祭山习俗,尤重木叶山与黑山。《辽史·礼制》记载,木叶山是契丹人的祖庙所在,黑山则是契丹人的魂魄之所归,契丹人对神山“俗甚严畏,非祭不敢近山”㉔。而据有关学者研究认为,黑山和木叶山山体皆为黑色㉕。
而石脱离于山,也有着神秘的力量。这些岩石处在特殊的空间具有了神圣性,岩石本身作为一块石头而言,“绝不会改变自己……通过类比的方法向人们展示了自己的恒久性和绝对性”㉖。这种神圣性也使得岩石本身成了宇宙的显圣物,而被人们所崇拜。
三、族群选择
氏族社会时期对世界的认知是颇为原始的。对于黑色的原始认知源是危险的,正是这种认知,反过来使得人们去崇拜他。太阳落山后万物笼罩于黑暗,暴风雨来临之际的黑云阵阵,都无时不在提示着黑色的恐惧与庄严。在高原草原地带,这种黑霭的暴风雨似乎更为常见。因此在这种环境下生存繁衍的原始人类更容易接受并去崇拜这种未知的伟岸。当一种共识在族群中出现并稳定下来,就成了这一族群的统一认知。这种认识将会随着部落之间的征战、族群迁徙以及原始血缘宗族观念等因素逐渐扩大成为一个区域内的统一认知,将会在族群的兴衰演进中形成固定的族群“符号”,一直流传下去。
进入奴隶社会之后,统治阶层的意志和选择将会进一步成为一个国家的社会意志。《礼记·檀弓上》记载:“夏后氏尚黑”㉗。商时,以玄鸟为图腾。《史记·殷本纪》载:“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㉘。周时,玄色亦为尊贵之色。据《礼记·月令》记载:“天子居玄堂左个,乘玄路,驾铁骊,载玄旗,衣黑衣,服玄玉”㉙。秦时“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㉚。西汉时黑色亦是尊贵之色,《后汉纪》云:“汉初,文学既阙,时亦草创,舆服旗帜一承秦制,故虽少改,所用尚多”㉛。通过史料可以得知,自黄开始到秦汉这一时期,是崇尚黑色的。这一时期的黑色崇拜,更多的是对于“天”的崇拜。《易经》云:“天玄而地黄”㉜。天为玄色,许慎《说文解字》注曰:“黑而有赤色者为玄”㉝。玄色,其色象征天未亮而将亮时的颜色,也就成了华夏族群对天崇拜的渊源。
中原成为了华夏民族生存发展的聚居地,而北方草原地带则长期被游牧民族所占据,并时常南下袭扰中原。而作为北方少数游牧部族的羌、狄、戎,和炎黄二帝之间也有着紧密的血缘关联㉞35。其后的东胡亦是戎人发展而来,而匈奴,据史书记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㊱。而与匈奴同时期的西域各国,如月氏、乌孙等,史书中对其社会风俗的描述大多为“习同匈奴”。通过此我们可以得知,在夏之后的北方少数民族,多与中原有着密切关联,那么中原的尚黑崇天理念就有了族群基础,而这基础则源于华夏中原。而这一时期随着部族首领的权力日益扩大,对于祭天敬神的权力也就从巫师转移到了部落首领手上,政教合一也预示着宗教观念和族群崇拜的统一与融合。
秦汉之后凿岩画作品则更多地展现一种“沿袭与模仿”的行为,随着生产工具的进一步改进以及农业和畜牧业的进一步发展,原始宗教因素以及传统思维对游牧民族的影响也在进一步弱化。汉对西域的一系列战争活动,大量游牧族群占有的地域划归中原王朝管辖,随着中原人口内迁入河西,与当地游牧部族杂居融合后,西部游牧文化逐渐走向衰落。在岩画数量和题材上有着清晰的反映,汉魏之后的岩画数量很少,这归因于文化交流以及中原对西域的重新控制与管理。除西北地区外,北方其他少数民族占领地区仍能发现鲜卑、突厥等民族遗留的岩画遗存,凿刻地点的选择仍保留了传统选择性,或者就凿刻于早期岩画上。“凿刻岩画地点很重要,以至于岩画制作者在这块地方找不到理想的岩画时,宁愿再打制一遍,也不使用其他地点”㊲。
四、余 论
在笔者岩画调查的过程中发现岩画除了有岩石选择性之外,还对于岩石的朝向有选择性:岩画的凿刻更青睐于南向朝阳方位的岩石,也就是山阳面;北向背阴面也有凿刻,但是数量相较于南向朝阳岩画的数量来说,寥寥无几。岩画选择南向朝阳凿刻,在上个世纪盖山林先生调查阴山岩画时就已发现㊳。笔者参与了甘肃省以及西藏自治区部分地区岩画的调查,并记录了岩画的朝向情况,通过统计分析,大部分岩画都凿刻在朝南向阳面。例如甘肃永昌青口顶岩画㊴和涝池沟岩画㊵,青口顶发现岩画144 组,剔除岩面朝上岩画59 组后,以90°— 270°为界划分南北方向,统计得北向18 幅,占比21.2%,南向67 幅,占比78.8%;涝池沟岩画共计136 组,按照同一标准划分,剔除3 组岩面朝上岩画㊶,北向11 组,占比8.3%,南向122 组,占比91.7%。西藏阿里地区日土县2021 年岩画调查共计发现1372 组岩画,剔除175 组岩面朝上和活动岩石岩画后,统计得北向308 组,占比25.7%,南向889 组,占比74.3%。通过以上数据可知,岩画在凿刻过程中确实存在朝向选择情况。笔者认为,这与原始宗教观念有一定关联:苯教传统上一般把东方当作“生存之域”,南方是“不灭之域”,西方是“教法(智慧)之域”,北方是“苯布乐土(死亡之地)”㊷;在布利亚特萨满教观念中,“人们将其分为邪恶神灵和善良神灵,分配到不同的地区:55 位善良神灵住在西南区域,44 位邪恶神灵住在东北地区。这两组天神长期处于斗争状态”㊸。传统观念中也对于北方较为忌讳,《礼记·礼运篇》说:“故死者北首,生者南乡”㊹。
可以看出无论是宗教影响下的选择还是传统观念,都对于北方有着忌讳,认为北方代表着死亡与邪恶,人们在岩石上凿刻动物和人的形象,是为了给与其“法力”,让人充满神力,战胜狩猎对象,让动物健康多繁育后代,都是一些美好的祈愿。而将形象凿刻在北向岩石上会对人和动物产生不利影响。另外,在实地调研中也发现,山峰南坡植被生长状况也较北坡要好,我国处于北半球,南坡即阳坡,接受阳光照射的时间更长,牧者也更青睐于在南坡放牧,因此也就会有更多时间在南坡的岩石上凿刻岩画。
岩画是我国游牧部族创造的艺术瑰宝,蕴含着先民对世界的原始认知,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囿于岩画测年的困境,岩画研究需要更多地去参考民族学、宗教学、社会学的相关理论进行深化探讨。岩画蕴含的信息丰富,不能仅仅将其作为图像进行研究,在调查时,更要全面记录原始信息,才能有利于我们剖析岩画蕴含的深层次内涵。
注 释
① 〔战国〕韩非著:《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 年。
② 〔北魏〕郦道元著:《水经注》卷三《河水》,商务印书馆,1933 年。
③ 张文静:《中国北方地带岩画分布的特征分析》,《中原文物》2012 年6 期。
④ 龚田夫、张亚莎:《中国岩画的文化坐标》,《黑龙江民族丛刊》2006 年1 期。
⑤ [法]列维-布留尔著,丁由译:《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出版社,2017 年。
⑥ 〔东汉〕班固著:《汉书》卷九十六上、下《西域传第六十六上、下》,团结出版社,1996 年。
⑦ 王建新、席琳:《东天山地区早期游牧文化聚落考古研究》,《考古》2009 年1 期。
⑧ 贾伟明、丛德新:《蒙古高原传统游牧形态的考古学观察》,《北方文物》2022 年4 期。
⑨ 盖山林:《贺兰山巫师岩画初探》,《宁夏社会科学》1992 年3 期。
⑩ 班澜、冯军胜著:《阴山岩画文化艺术论》,远方出版社,2000 年。
⑪ 色音著:《中国萨满文化研究》,民族出版社,2011 年。
⑫ 阿斯儒、雅茹:《蒙古族萨满教变形神话之生命观探析》,《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年1 期。
⑬ [美]米尔恰·伊利亚德著:《萨满教:古老的入迷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年。
⑭ 湖林、白翠英:《科尔沁博的尚黑礼俗》,《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06 年4 期。
⑮ 谢继胜:《藏族萨满教的三界宇宙结构与灵魂观念的发展》,《中国藏学》1988 年4 期。
⑯ 曲杰·南喀诺布著,向红笳、才让太译:《苯教与西藏神话的起源“仲”“德乌”和“苯”》,中国藏学出版社,2014 年。
⑰ 格勒:《藏族本教的巫师及其巫术活动》,《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 年2 期。
⑱ 汤惠生、田旭东:《原始文化中的二元逻辑与史前考古艺术形象》,《考古》2001 年5 期。
⑲ 班澜、冯军胜著:《阴山岩画文化艺术论》,远方出版社,2000 年。
⑳ [美]唐娜·L.吉莱特等编,王永军等译:《岩画与神圣景观》,宁夏人民出版社,2017 年。
㉑ [罗]米尔恰·伊利亚德著,王建光译:《神圣与世俗》,华夏出版社,2002 年。
㉒ 〔南朝宋〕范晔著;《后汉书》,太白文艺出版社,2006 年。
㉓ 李焕青:《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名号与崇山习俗考论》,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 年。
㉔ 〔元〕脱脱等撰,宋德金等标点:《辽史》卷五三《志第二二 礼六》,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 年。
㉕ 葛华廷:《辽之圣山木叶山、阴山、黑山及三者关系琐考》,《辽金历史与考古》2020 年。
㉖ [罗]米尔恰·伊利亚德著,王建光译:《神圣与世俗》,华夏出版社,2002 年。
㉗ 〔西汉〕戴胜著,崔高维校点:《礼记·檀弓上 第三》,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年。
㉘ 〔西汉〕司马迁著:《史记》卷三《殷本纪第三》,崇文书局,2010 年。
㉙ 〔西汉〕戴胜著,崔高维校点:《礼记·月令第六》,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年。
㉚ 〔西汉〕司马迁著:《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崇文书局,2010 年。
㉛ 〔晋〕袁宏撰,李兴和点校:《袁宏<后汉纪>集校》卷九《孝明皇帝纪第九》,云南大学出版社,2008 年。
㉜ 〔商〕周文王著,佚名编:《周易·上经 坤》,中国文史出版社,2018 年。
㉝ 〔东汉〕许慎著,汤可敬撰:《说文解字今释》,岳麓书社,1997 年。
㉞ 徐杰舜:《汉民族支源戎狄论》,《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 年3 期。
㉟ 沈长云:《华夏族、周族起源与石峁遗址的发现和探究》,《历史研究》2018 年2 期。
㊱ 〔西汉〕司马迁著:《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第五十》,崇文书局,2010 年。
㊲ 汤惠生、张文华著:《青海岩画 史前艺术中二元对立思维及其观念的研究》,科学出版社,2001 年。
㊳ 盖山林编著:《阴山岩画》,文物出版社,1986 年。
㊴ 丁升鹏、于春:《甘肃省永昌县青口顶岩画调查与初步研究》,《草原文物》2021 年2 期。
㊵ 涝池沟岩画调查资料待刊。
㊶ 资料版权归属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阿里文物考古援助项目”,系该项目2021 年度考古调查成果。
㊷ 孙林:《藏族苯教神话的象征思维及其固有模式概述》,《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 年2 期。
㊸ [美]米尔恰·伊利亚德著:《萨满教:古老的入迷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年。
㊹ 〔西汉〕戴胜著,崔高维校点:《礼记·礼运 第九》,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年。